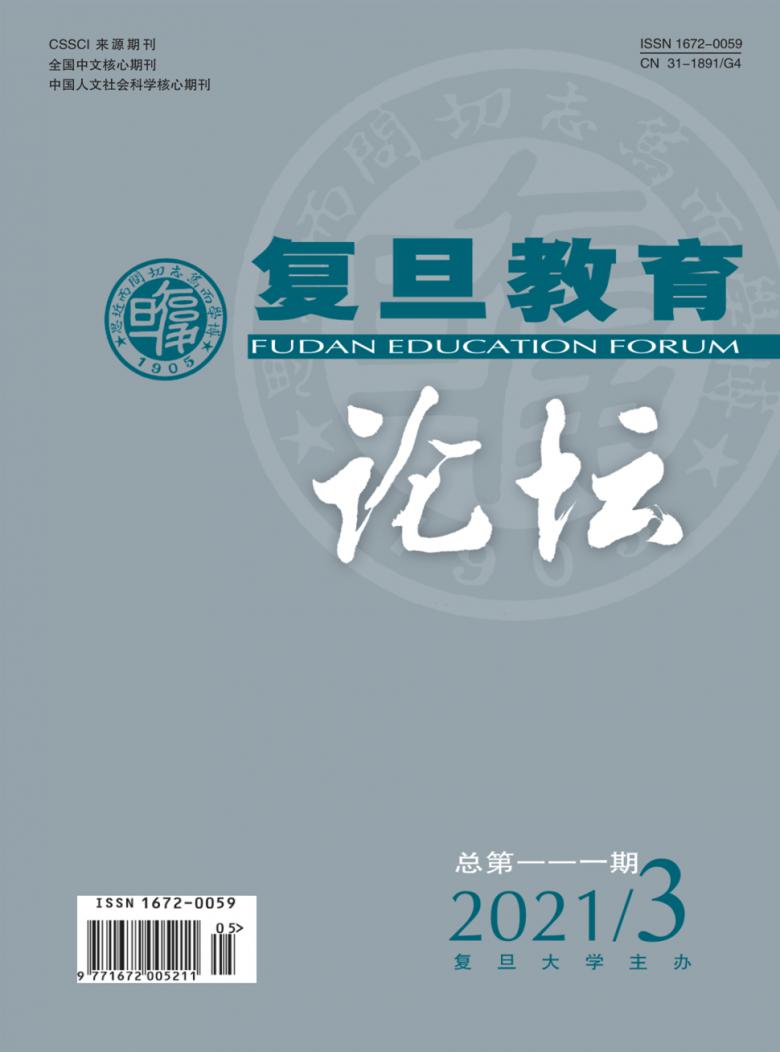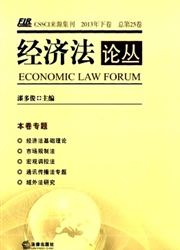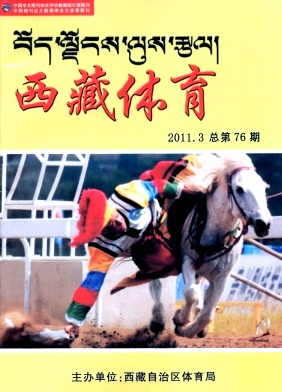“现实主义冲击波”下的现世主义
童月 2006-01-20
有两种立场始终不甚调和地存在于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一种是“现世主义”的,它使作家们对当下的现实种种作出细致而缺乏距离感的描摹;另一种却是“浪漫主义”的──刘醒龙便曾宣称:“我一直不大相信自己这个被人强加的‘现实主义’者,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写作是浪漫主义的。”①“现世”的羁绊使作家们始终无法超拔于庸常现实的泥沼之中,“浪漫”成了一剂拯救现实的药方:以旧道德理想的复归,以所谓的“大善”来分享艰难;以受难的、奉献的,甚至禁欲式的英雄来供奉这个“拒绝崇高”的年代;以“苦戏情节”的现代翻版为当下提供安于现实的强心剂。“现世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使他们笔下的英雄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冲突与痛楚却无法崇高;虽然具有受难与献身的表征却不够悲剧。他们的形象不够高大,甚至有些畏琐;他们背后虽有一圈“道德”的灵光,但那光环总也不够圣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英雄形象”总是作为楷模,向读者作出意识形态的询唤,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英雄却不再是“效仿”的对象,而作为“感动”的对象登场;他们上演的不是“悲剧”,而是“苦戏”,为90年代以来在茫然失措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麻醉与抚慰。
一 宿命化的艰难
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可用两个字来概括:艰难。无法抗拒亦无法摆脱,“宿命”便成为解释艰难并使人承受艰难的最佳籍口,正如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犯下的罪恶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解释为人类几千年苦难的源头。“现实主义冲击波”亦采取了这种策略,它们照相式地描摹当下的艰难: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并试图使之日常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成为不幸生于此时代者无法逃避的命运,成为步入许诺之中的“明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表面看来,作品中所描述的“困境”有其显见的形成原因:《大厂》中那个“越来越不景气”,“已经两个月没开支了”的厂子是因为前任许厂长“弄走了厂里好几十万块钱”,最终自己也“让戴大盖帽的带走了”。《年初》中的“太阳厂”之所以“一堆烂事”是因为“上一届厂长老许光吹了两年大话,什么正经事也没干出来,临下台跑到海南做生意去了”。无比简洁而明了的答案。作家们似乎也在思考其深层原因,在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为一厂、一镇生存而挣扎,付出健康、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厂子却每况愈下时;在他们遭遇权力网、关系网却无力冲破时;在目睹社会黑暗面却无力回天时。然而他们的思考只是为了验证一个先验的答案:“改革是有阵痛的”。这便如命运的宣判,或隐或显于作品之中,并决定了文中人物的思考方式:“上级领导”以此为籍口,轻易地做出合并或裁员的决定;厂长们却认为,这“应是企业的痛苦,不应转嫁到工人身上”。
这种思维方式有其历史原因。自建国以来,在种种政治风潮的影响下,“历史唯物史观”逐渐演变为庸俗的“历史决定论”。人们将“共产主义”或“四化”的乌托邦幻想锁定于未来,锁定于“历史进化的必然方向”上,认为时光之轮正滚滚向其迈进。于是,“未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同时具有了终极意义,宛若宗教中的天国花园。同时,“现在”也因其处在“通向天国之途”中也具有了某种神圣性。然而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巨大鸿沟永远不可能消弥,在盲目乐观中躁动了几年后,国人忽然发现自己已陷身于艰难现实的泥沼中,看不到前方的路,来时的脚印也被淹没在一夜间长出的荒草中。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却仍在说服人们相信“历史”,相信未来:“历史”依自身的轨迹走至目前的混乱局面,但“阵痛”过后必将是新生命的诞生。只是,“历史”需要祭品,“也许,这就是一种历史的代价,一种需要我们来付的代价”。而“我们”──无论是吕建国、贺玉梅、周天,还是春梅、陆明,以及千千万万的工人──这个概念的圈定并非由于他们做了什么或未做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出生于这个时代。因此,为了将艰难成为时代的特征,成为当下人们的宿命,“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往往采取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写法,以场面与场面的更迭来完成叙事。在情节上缺乏一条明晰的冲突线索,没有“英雄”与“敌手”,只有道德论理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划分。“艰难”也并非如山洪爆发一般席卷而来,而是被日常化、生活化,不动声色地磨砺人们的肉体和灵魂。于是,小说的叙事也无法闭合在文本之中,它只像是从生活中随意截取的一段,始于一个乱糟糟的上午,终于艰难暂时缓解的间隙。
二 “基督受难”的情节模式
如果仅仅彰显“艰难”的历史宿命而未开出承担它的药方,仅仅发出命运的哀叹却未加以抚慰,一部作品显然无法实现其意识形态目的。正如一切主导文化(如好莱坞类型电影),“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的意识形态策略也是将冲突建立在当下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却又加以“想象性的解决”。在《大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干草车》等作品中,“宿命化艰难”的策略已将人民与时代/社会的冲突转换为个人与命运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不会诞生任何经典意义上的命运悲剧。尽管作家们一再强调自己的“普通人”立场:“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三驾马车)“唯一相通之处是大家在作品中透射出的对人的善意”。②然而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人民”被“群众”代替,他们或是“无名者”,群体出场(围攻厂长时的一群,偷盗工厂财产时的几个);或虽有姓名却无性格内蕴,只作为情节因素或象征因素存在(如《大厂》中女儿生了白血病的小魏,《干草车》中下岗却不忘交党费过组织生活的阚师傅)。“普通人”总是被置于读者的视域之外,而代替他们(而非代表他们)承受艰难的却是吕建国、周天、陆明等等党政领导,“英雄”形象。他们并无力量解救工厂、人民于历史的车轭之下,而只能以一已身躯作为铺路石。这便如《新约》中所载:当世界道德败坏、物欲横流,人类的罪恶不可被上帝宽恕时,神子耶酥便走上十字架,以自己的血来清洗世人的罪恶。然而世人无法理解,世人对耶稣加以荆冠和唾骂。三日后耶稣自死亡中归来,同时归来的还有世人的信仰。自此基督教便有了“领圣餐仪式”。人们分食象征基督血肉的红酒与面包,同时承继基督的精神。而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若干作品中,当现实的艰难实在令人难以承担,当“命运”的谎言无法阻止苦难的呻吟时,作家们便不再徒劳地编织拯救的故事,而是娓娓讲述“基督受难”的现代版本:“英雄”以“大善”来为人民承担苦难,人民又将承继“英雄”的受难精神。宛若宗教传说的故事象征性地弥合了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模式化的情节使一些仪式性场面在作品中频频出现。
1、戴荆冠仪式
如果能找到苦难的源头,苦难或许会在怨恨、诅咒甚至是报复中变得易于承受。在一些工厂题材的作品中,群众(或曰群氓)总是轻松地把一切责任堆到领导者身上。“围攻”场面便成了“戴荆冠”行为的仪式化展现。然而众人的愤怒总是能轻易地被领导者的“大善”或者真诚化为理解。谈歌的《年初》中便有这样一个戏剧性场面:工人们围攻厂长刘志明,质问为什么厂党委书记周天可以下班后卖菜,自己却不能到东风厂去打工。但当韩师傅说明周天是在代他卖菜,且每月都拿出100元支援他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便被缓解,“一屋子的人都悄悄流下了眼泪”。
2、十字架仪式
肉体的受难改为灵魂的受辱;以血洗罪变成了以泪承难,原木钉成的十字架变成了掌权者的办公室、高档酒店……“现实主义冲击波”实质上是一部部“当代基督受难史”。“英雄”们一次次以人格的受辱,以流泪来感动那些掌权者,使工厂得以存活,使“子民”的艰难得以分担。、
3、领圣餐仪式
事实上,在“戴荆冠仪式”和“十字架仪式”中,“英雄”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感动”他人:感动自己的子民,也感动执掌生杀大权者。“感动”从来就是一种仰视与乞怜的姿态。因此,为了取得平衡,最终完成“英雄”的形象,小说中必须安排“领圣餐仪式”,让“英雄”以“俯视”的姿态,自上而下地自己的精神传给子民。“大会”、“发工资”、“探病”都可视为这种仪式的变体。至此,这个“受难”的故事才能宣告结束。
自然,当下流行的“受难故事”有其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传统苦戏情节的现代翻版。尽管“现代苦戏”的主人公不再是窦娥、赵五娘……不再处于社会的底层,等待“青天老爷”的救赎。相反,他们身居高位,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但他们同是现存秩序的顺民,挣扎于秩序的缝隙间苟延残喘;他们缺乏自主行动的力量,只能在外界灾难袭来时被动地做出反应(如《大厂》中的吕建国从未主动地做过什么,只是忙于应对纷至沓来的一系列不幸。而这些不幸大多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反复,只有量的累积而无质的突破);他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便是“感动”,感动领导或感动子民。(往往是很有效的方式。或许悲剧与苦戏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提出问题却无力给出答案,后者却迫不及待地作出回答。而任何形式的答案都是对思考的阻碍。)
“现实主义冲击波”并未对庸常现实造成任何冲击,相反,它是一种抚慰现实的手段。在抚慰中,千疮百孔的现实感觉逐渐麻木,痛变做痒,痒又化做无,最终,在麻木中沉入忘乡。
注释:
①②:刘醒龙:《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