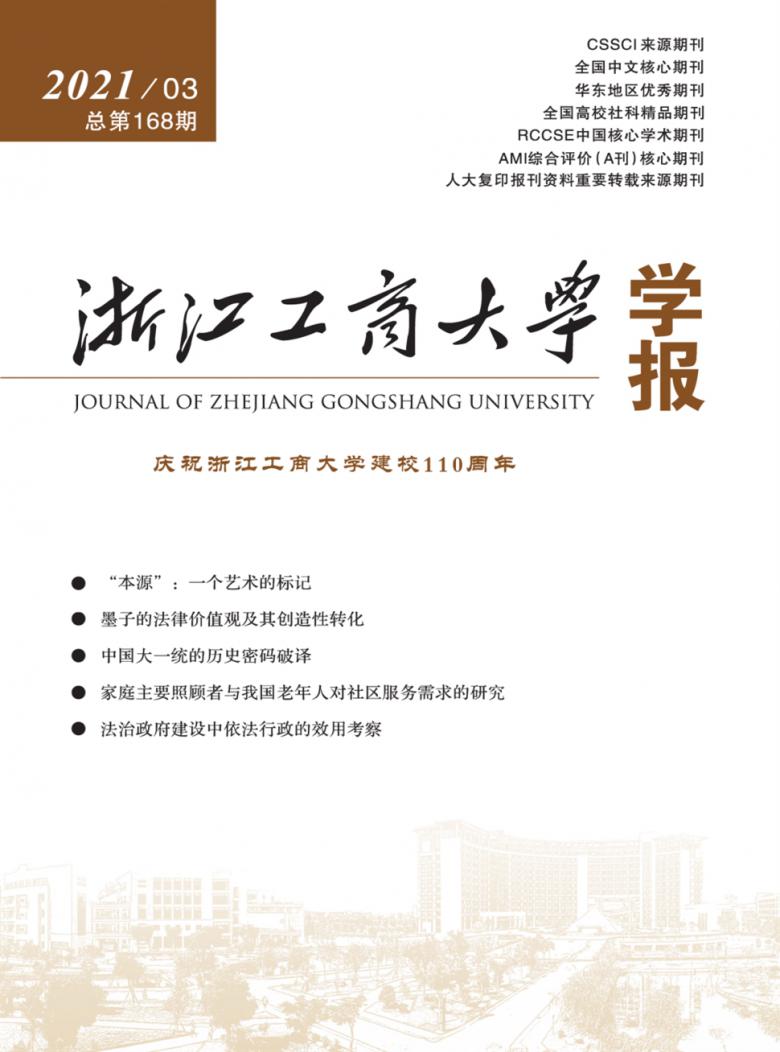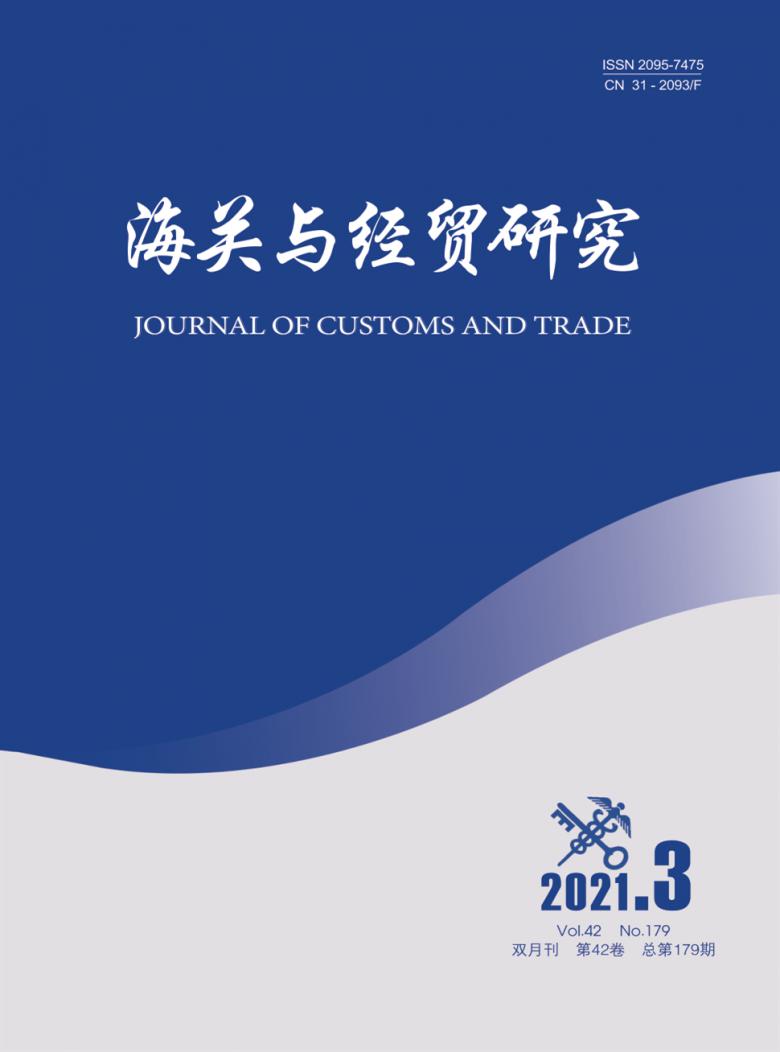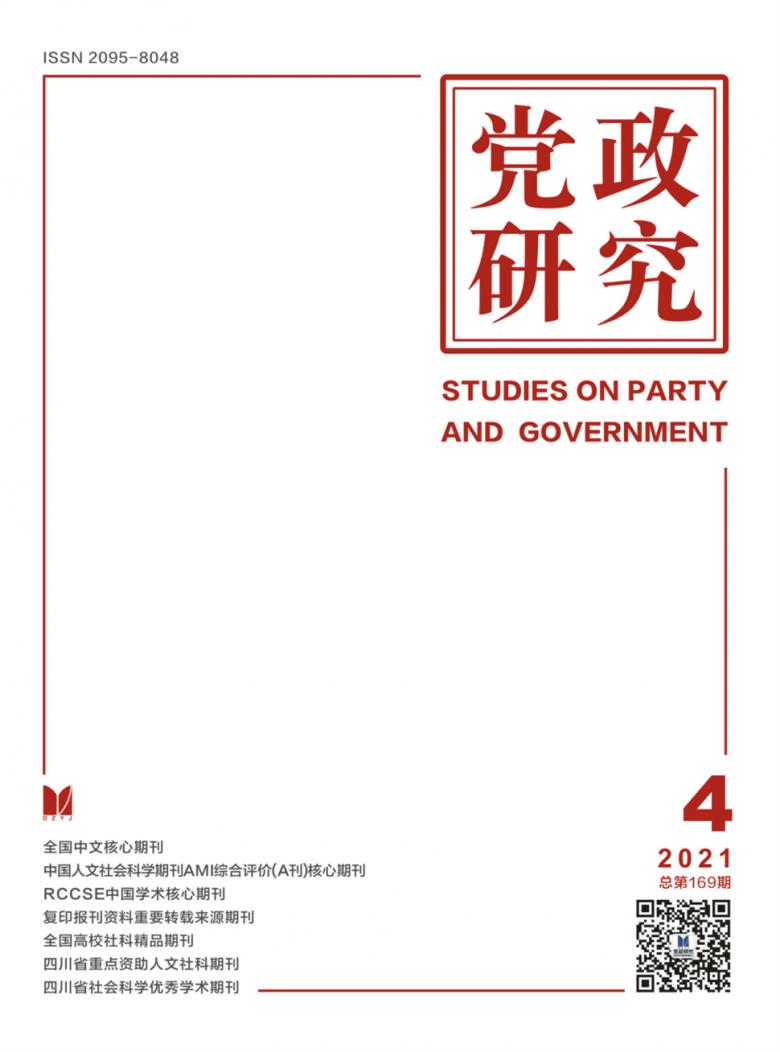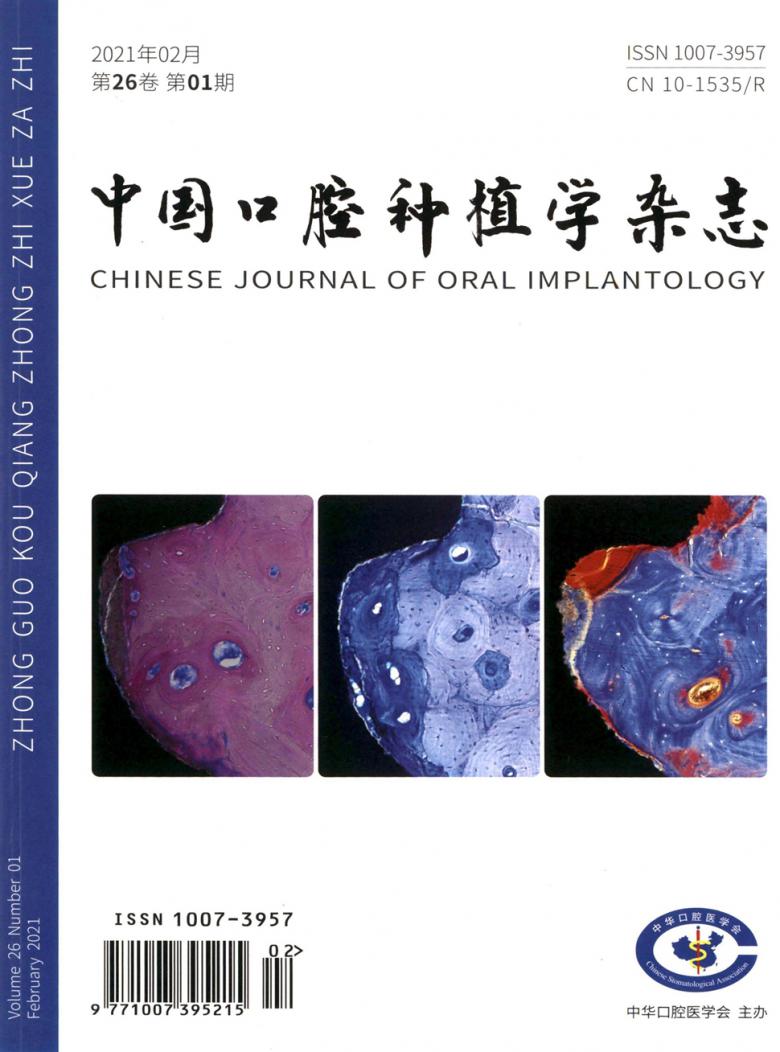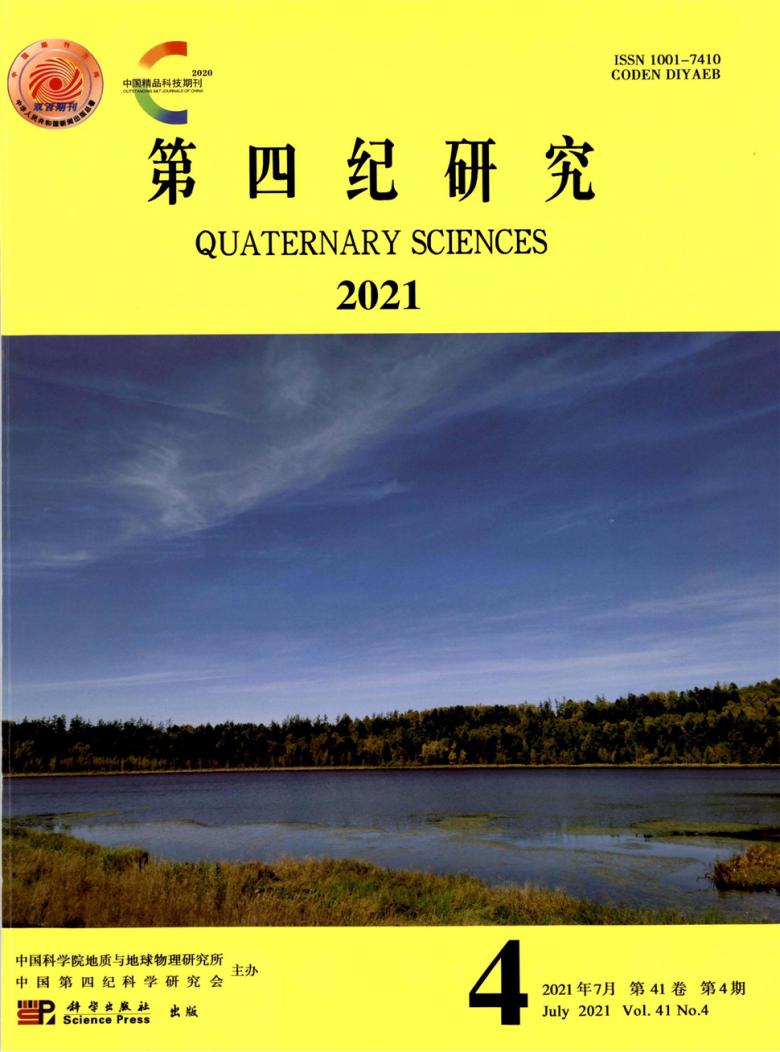中国画传神论的思想史背景
张建军 2008-06-04
[东晋]顾恺之 洛神赋图 (局部 宋摹本)
一、“神”的历史:从神之“神”到人之“神”
“神”,许慎《说文解字》卷一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又同书卷十四说:“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臼束,从臼,自持也。”
当代古文字学家认为:从字形发展来看,“申”本为象形字,像电光回曲之状,其语义隐含有对自然神祗崇拜的意义。后来由于汉字形声化的原因,申字增加了一个与对祖先之神灵崇拜相关的符号“示”,就构成了“从示从申、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之“神”字。“申”本与自然神祗相关,“示”本义则是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神字产生之后,“申字隐含的自然神祗崇拜的意念,融汇入神字的语义里”,同时,神字增加了“示”符,由于“示字所表述的是祖先神灵崇拜,这就使得新创造的神字的语义内涵扩大,自然神祗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这两方面的意念,都包含在神字的语义里了”①。因此,由申字加注祖先崇拜的象征物“示”符,所构成的新字“神”,其所表述的语义概念,已经不是单纯指自然神祗,而是“把自然神祗与祖先神灵糅合起来,合二为一地表述所有与‘神’相关的观念”。
从神灵之“神”到人物之“神”,这中间转换的一个关键是“神”的抽象化与向形而上的形态的转化,抽象化倾向首先体现在“神”之语义从专指雷电之神到泛指自然神灵,再到自然神与祖先神的通称,《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昭王问于观射父,日:“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平?”对日:“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
这里“明神降之”中的“神”,已经带有了一定的形而上色彩,是指神灵之所以为神灵的所具备的“神性”,而非指神灵本身。
“神”的进一步抽象化与形而上学化可以从汉初《淮南子》中见出,《原道训》说: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原作“生之充”,据王念孙校说改);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二”原作“三”,据王念孙校说改)。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另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使也。
在这里,“神”已经成了与“形”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概念,是指人之所以“眭然能视,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另同异、明是非者”的依据。
“神”从神灵本身进而指神灵所具有的“神性”,从神的“神性”进而指人所有的与形相对的一种概念,它是人“眭然能视,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另同异、明是非者”的依据,“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神是“生之制”,而形则是“生之舍”,神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蔡仲德说:“《淮南子》认为人的‘生’(生命、性)是‘形’、‘气’、‘神’三者的统一体,‘形’是其物质载体,气是其根本,而神是其主宰。”②
与“形”相对的“神”在《淮南子》中又被称为“君形者”:
《说山训》: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葛路《中国绘画理论发展史》说:
这里所说的“君形”,我认为就是神似。古人经常把君、臣一类的词借用来形容事物的主次关系。山水画有把主山比为君,群峰比为臣的。画西施虽然美但不使人喜欢,画孟贲眼瞪得大,却不令人生畏。原因何在,没有做到神似,即没有表现出他们各自特有的神态。③
其实,《淮南子》这段话,无非是说画中的美女西施“之面”,是“美而不可说”,勇士孟贲“之目”,是大而不可畏,是因为没有“君形者”,即那个与人之形相对而存在的人之“神”,因为画仅仅是画,画中人并非真人,而“君形者”——“神”是只存在于活生生的真人那里的。对于《淮南子》来说,不是批评某一幅画不能传神的问题,而是根本认为绘画就不可能传神。
神之“神”已经转换成为人之“神”,但人之“神”能否及如何表现于“外”,被感官所感受到,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二、形神问题的发展
神能够成为“君形者”,是形神这一对对偶范畴发展的结果,而形神问题的发展最终为传神论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
按照张立文的看法,形与神作为一对对偶范畴,是思想史发展的结果,本来,神与形各为单一范畴,神指神灵,形指形象、形体。直到战国时,形神概念才有长足发展,而逐渐接近后来所谓形神对偶范畴的含义。④
神本来是与人相对成立的一对概念。《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后来却又开始与形成为对立概念,其间的转换,经历过“精”与“精神’’两个范畴的过渡。
《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大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又说:“思之而不能,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精气之极也。”张立文说:“形体由地而来,精神由天而来,精是一种细微的气,它相对于构成形体的气来说,是精气,这种精气在人体中具有思虑智慧的功能。‘恩之而不能,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精气之极也。’把人的精神活动、意识现象看作是一种特殊物质构成的,形体与精神可离为二,因为精气在形体之外独立存在,又可合一而为人。这是对形神关系的稚气的探索。”⑤这里与形对立的还不是神,而是精。
《庄子知北游》:“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在宥》:“抱神以静,形将自足。”又曰:“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天地》:“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成玄英疏:“禀受形质,保守精神,形则有丑有妍,神则有愚有智。既而宜循轨则,各自不同。”第一例句中,出现了“精神”一词,而“形本生于精”,“形”仍与“精”相对,第二、三例句中,“抱神以静,形将自足”,“神将守形”,“神”已经成为与“形”对立而成的概念。
《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不苟》:“形则神,神则能化矣。”形与神两者已经明确地作为对偶概念而成立。
从神灵到神灵的抽象的“神”即神性,再到人所具备的形体之外的“精神”,神的概念,由与人对立而存在的概念,转换成为与形对立的概念,这是《淮南子》中以神为“君形者”观念史的史前史。张立文说:“形与神范畴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由天道部分向人道部分演变的关节点。”⑥
但是,自《庄子》到受其思想影响很大的《淮南子》,尽管确立了形与神作为对偶范畴的成立,其对于形与神之间的关系,认识仍然是含糊不定的,而且这个神仍然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抱神以静,形将自足”,“神将守形”(庄子)也好,“形具而神生”(荀子)也好,“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淮南子》)也好,这些说法都只注意了形与神对立存在性与相互依存性,但很少有对人之“神”的自身的特性,进行分析与定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徒慧远的关于形神的论述,可以说是“神”由抽象的纯粹与“形”相对的概念,进化到可以表现于“形”的“神情”的一大关捩。慧远说:
神也者,图(应为圆)应无生(应为主),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物感,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夫情数相感,其化无端,因缘密构,潜相传写。……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说:“……慧远也承认神是‘感物而动,假数而行’的,即神的活动要以‘物’和‘数’(自然之数,即自然运行的规律、法则、过程)为凭借,但慧远认为‘神’不是‘物’,也不是‘数’,所以‘物’虽灭而‘神’不会灭,‘数’虽尽而‘神’不会尽。慧远通过对神的不可名言的微妙性的强调,最后把‘神’看作是可以独立于物和数而存在的。其次,为了证明神可以独立于物和数而存在,慧远又声称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他把神与情联系起来,生的变化推移是和情的感物分不开的,而神又为情之根,因此‘情’在感物化生的同时也就把‘神’暗暗地移传给不断产生的新的生命了。这就是他所谓‘情数相感,其化无端,因缘密构,潜相传写’。前形虽死,‘神’却可以暗中传于后形,就像前薪之火可以传于后薪,不绝地燃烧下去一样。”⑦
李泽厚、刘纲纪还认为慧远所说的神的“潜相传写”、“神之传于形”可以启发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顾恺之的传神论可能是受到了慧远的形神论的影响:
顾恺之在绘画上提出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看来和慧远的说法是类似和相通的。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传神写照”,从画家的创作来说,亦即把所画人物的“神”传之于所画的人物之“形”。它也类似于慧远所说“前形”与“后形”的“潜相传写”。“前形”为画家所画的人物,“后形”为画家所作的画像,画家的创作在于将“前形”之神传于“后形”。不过这“后形”虽不完全同于“前形”,却不是慧远依据佛教生死轮回说所说的完全不同于“前形”的“异形”。在绘画创作中,从“神”对“形”的关系说,正与慧远的说法相似,是使“神”“传于形”;反过来看,从“形”对“神”的关系说,则是顾恺之所说的“以形写神”。而绘画上的“形”、“神”双方的这种关系,从理。论上说,显然又是以慧远所说“形神虽殊,相与为化,内外诚异,浑为一体”为前提的。如果“形”、“神”是相互分离的,那就既不可能使“神”“传于形”,也不可能“以形写神”。这里可以看出,慧远对形神关系的分析可以应用于绘画,它为绘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⑧
我们认为,通过“潜相传写”、“神之传于形”这两句本来是用于形容“神不灭”的话,就断定慧远的说法与顾恺之传神论类似和相通,有失于武断,而且文中说“传神写照”就类似于慧远所说的“前形”、“后形”的“潜相传写”,也显得有些牵强。
慧远的形神论是为其“神不灭论”服务的,“传写”是讲神不灭,通过前形传于后形,与绘画中“传神写照”并无直接的联系。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慧远在神的概念中引入了“情”,或者说在形神关系中间,又加进来了一个有效的中介——“情”,使抽象的人之神成为了具有具体可感的特点的“神情”。
“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这里关键是需要弄清一个词——“化”的含义。
按“化”字在古代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指变化、改变:《庄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可指死:《孟子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也可指生,造化,自然界生成万物的功能:《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素问五常大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由自然界生成万物的功能延伸,也可指自然界生成之物:《礼记·乐记》:“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佛教传人后,又有“化生”之说,《俱舍论》:“有情类,生无所托,是名化生。”
慧远所用的“化”字,与佛教中的“化生”的观念有关,在这种观念中,“化以情感,神以化传”,通过“情感”,人得以“化生”,具有“形”,形体因情而“化生”而成,这里的“化”也包含有“形体”的意思,而“神”为“情之根”,化是情之感应的结果,人的神要凭借“化”来传递,而化的结果是化为形体,因此,人的神就可以通过“化”——形体而传,在“神不灭”中,这是“神之传异形”的保证,在现实的人的感官世界里,这是人之“神”有了“情”的性质,而“情”是可以被感知,可以通过“形”而传达的,因此人之“神”也是可以被感知,可以通过“形”而传达的。
这里最重要的是在人之形与人之神中间引入了一个中介“情”,因为神包含了情,而情又体现于形,是可感的,因此神也是可以通过形来表现的。
形神问题的发展,为传神论解决了哲学上的前提问题。
三、“神情”:人的发现
在魏晋时代,除了通过佛学、玄学的讨论解决形神问题哲学上的依据之外,作为人的“发现”的人物品藻的实行,更为人之“神”的走向具体、可感,提供了直接的语境。
对人的“神情”的重视与关注在先秦及两汉就已经开始了。
如《诗经》里的:
《卫风 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卫风 竹竿》:“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磋,佩玉之傩。”《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齐风 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又如《论语·乡党》记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人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蹄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又如《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些都可以表明当时人们对人的“神情”的重视,不过这里关注的都还是具体的表情、动作、姿态,而缺乏一种对气质的提炼,像魏晋时期常用的神、风、韵等都还没有出现在对人物的描写中。
只有到了魏晋时期,人的“神情”才得到更普遍的重视,而且脱离了政治、道德的因素制约,成为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审美对象。
宗白华说:“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一一同时被魏晋人发现。人格美的推重已滥觞于汉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视人格及其气象。‘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所以‘看杀卫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时人目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⑨这种器识与精神的美,基本上是不带道德因素的(如对被视为枭雄的桓温等的品藻),而且这些“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尽管可能需要有较高的观察力与领悟力,但都是可以用眼睛去发现的。
人的“神情”——形于外表的风姿、气度成为审美对象,这与汉末到魏晋的人物品藻是分不开的。
按照余英时的看法,在汉晋之际出现了士的“个体自觉”,而且这种个体自觉“又可征之于其时的人物评论”,而“人物评论与个体自觉本是互为因果之二事。盖个体之发展必已臻相当成熟之境,人物评论始能愈析愈精而成为专门之学,此其所以盛于东汉中叶以后之故也。但另一方面,‘人伦鉴识’之发展亦极有助于个人意识之成长”⑩。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察人之术大体为由外形以推论内心,自表征经推断本质”。《人物志九征》曰:“盖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情性这理甚微,而元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行。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人之本既然“出乎性情”,而只要是“有形质者”就总“可即而求之”,这就为魏晋时期对人的“神情”(内部的性情与形于“形质”的外部的容姿的结合)的欣赏创造了条件。
人物品藻又被称为“目”,张法《中国美学史》说:“对美学来说,重要的是这种‘目’的品藻方式,即用最简洁的语言对一个人做有特点而又全面的概括性结论。‘目’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说,一是指亲眼所见得来的认识(目观之目),二是指这种认识固形为一种本质上的定性(纲目之目)。刘劭《人物志》把人分为12类,用的也是精练性词组:强毅、柔顺….…—都属于政治人才学的人物品藻。时至魏晋,人物品藻由政治学上的材量人物转为美学上的欣赏人物。这就使人物品藻之‘目’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11)
《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当时名士之“神情”(内部的性情与形于“形质”的外部的容姿的结合)的“目”即评论,谨依李泽厚、刘纲纪所举例句如下:
“神气不损(《德行》)”、“神明开朗(《言语》)”、“形神惨悴(同上)”、“神色恬然(《雅量》)”、“神衿可爱(《识鉴》)”、“神姿高彻(《赏誉》)、“形似道而神锋太隽(同上)”、“神气融散(同上)”、“精神渊箸(同上)”、“神候似欲可(同上)”、“器朗神隽(同上)”、“神怀挺率(同上)”、“神意闲畅(同上)”、“风神清令(同上)”、“神气,豪上(《豪爽》)”、“神姿锋颖(《自新》)、“神色卑下(《贤媛》)”、“神情散朗(同上)”、“神明太俗(《巧艺》)”、“神意甚暇(《任诞》)”、“神气傲迈(《简傲》)”、“神明可爱(《纰漏》)”。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说:“由此可以看出,‘神’这个词可与不同的词搭配使用。其中,‘神明’、神锋侧重于指人的智慧、思想,神怀、神情、神意、神气、神色侧重于指人的风度。而所有这些用法,都同人的各个不同的具体表现相关,所以可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词藻去加以形容。神既与姿、怀、意、情等等相联,也就是与人的精神的感性表现相联,不同于对人物在道德上的善恶的抽象评价。,’(12)
所谓“与人的精神的感性表现相联”的“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具体可感的、包含着人的情感感性因素的、内部性情与形于“形质”的外部的容姿的结合的特定所指——“神情”。
徐复观说:
神的全称是“精神”。精神一词,正是在《庄子》上出现的。老子称道为精,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称道的妙用为神,六章“谷神不死”。庄子则进一步将人之心称为精,将心的妙用称为神。合而言之,则称为精神。……魏晋之所谓精神,正承此而来,但主要是落在神的一面。……但此时的所谓精神,或神,实际是生活情调上的,加上了感情的意味;这是在艺术活动中所必然会具备的。因此,“神”亦称为“神情”。……人伦鉴识,至此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的实践性,及政治的实用性,而成为当时的门第贵族对人自身的形相之美的趣味欣赏。(13)
徐复观对魏晋时期由于人伦鉴识的激发,而导致的“对人自身的形相之美的趣味欣赏”的论述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他提到的魏晋时期人之“神”的情感化、艺术化问题时说,此时的所谓精神,“实际是生活情调上的,加上了感情的意味;这是在艺术活动中所必然会具备的”,虽然言之不详,却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艺术是以可感的对象而非抽象观念为其对象的,作为抽象的概念的“神”无法成为艺术的对象,而“神”的情感化,其结果是使神“加上了感情的意味”,即成为可感的对象,成为“神情”。
名士风流,既体现于“发言玄远”的清谈,亦体现于“美姿容”的人物外表,更体现于一个人精神外现的“神情”。人之“神成为审美的对象、艺术的对象,为传神论的出现提供了保证”。“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来说还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⑩
“魏晋风度”中“人的发现”是双重意义的:是“眼睛”发现了“人”,发现了人之“神”,也是人“创造”了“眼睛”,创造了能够观察、欣赏到人之“神”的“一种特别的审美的感官”⑩,人之“神”只有对于懂得欣赏者来说才是美的对象。正如只有在音乐的欣赏中培养“音乐的耳朵”一样,正是在人之“神”的欣赏中,魏晋士人培养出了欣赏人之“神”的眼睛与心灵。
对于魏晋士大夫来讲,“神”已经是可以体察到、鉴别出的一种审美对象,在实践领域中“神”成为审美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神论的提出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注释:
①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第4页。
②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③葛路《中国绘画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④⑤⑥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62页。
⑦⑧(1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0页,第345~346页,第473页。
⑨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77~278页。
⑩余英时《土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3~274页。
(11)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1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