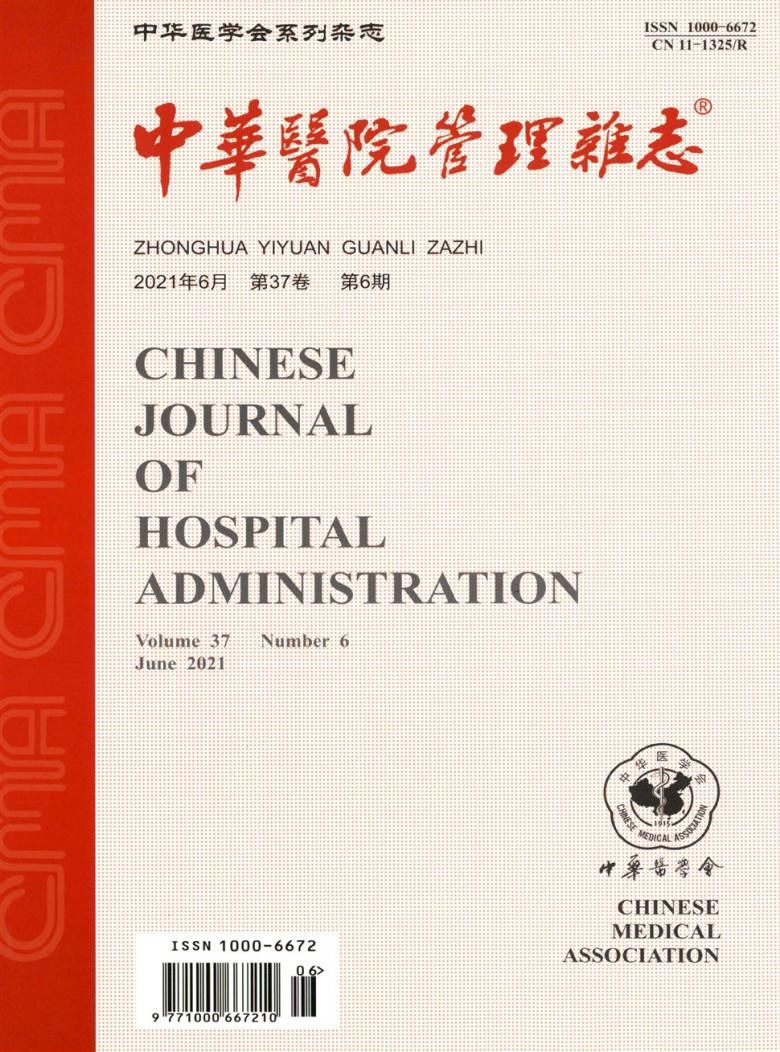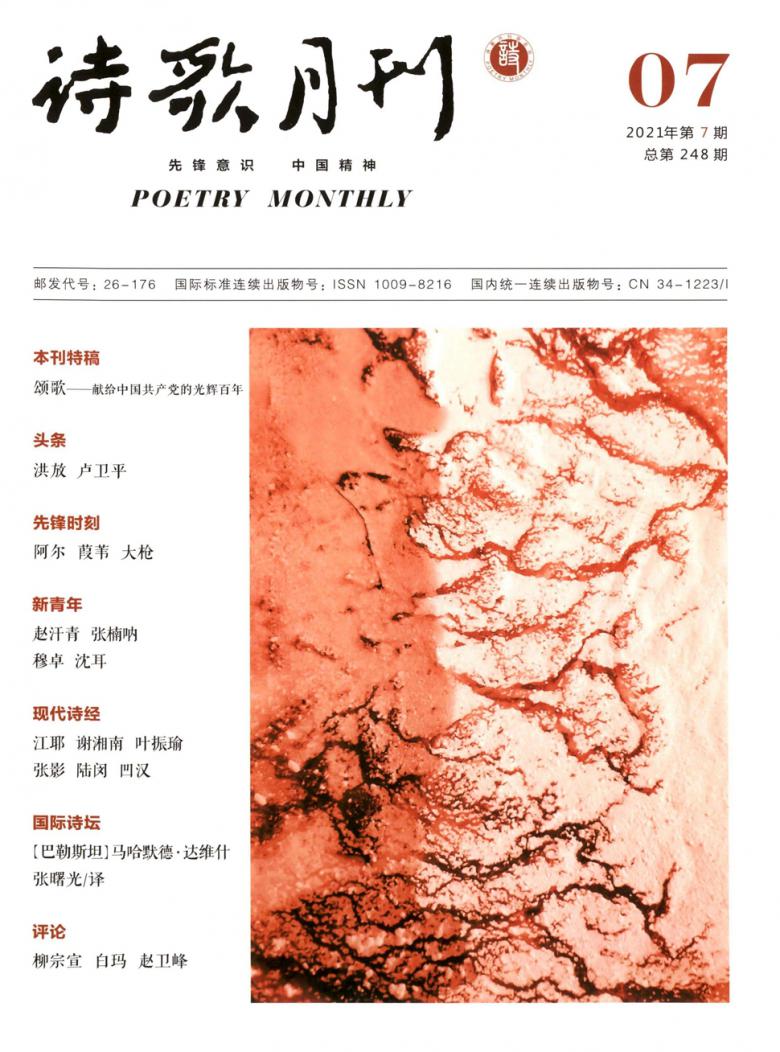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穆光宗 2003-04-26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 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 ,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 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 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 )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 月5 日至7 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 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 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 章,前4 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 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 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的"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 )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 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 )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 )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 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作为第三种见解如果成立的话,笔者的看法主要是:其一,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其二,"逆淘汰"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总的来看,"正淘汰"是主要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也是不足为忧的。其四,"逆淘汰"现象大概可归为三种:一是自然性逆淘汰,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引发的;二是遗传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统长久地自我封闭,导致通婚圈缩小,出生人口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的趋势。三是社会性的逆淘汰,这是指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教育卫生条件落后,导致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研究人口素质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开放人口系统的重要性。事实上,要遏止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人口流迁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系统。人口流迁对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括向度和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