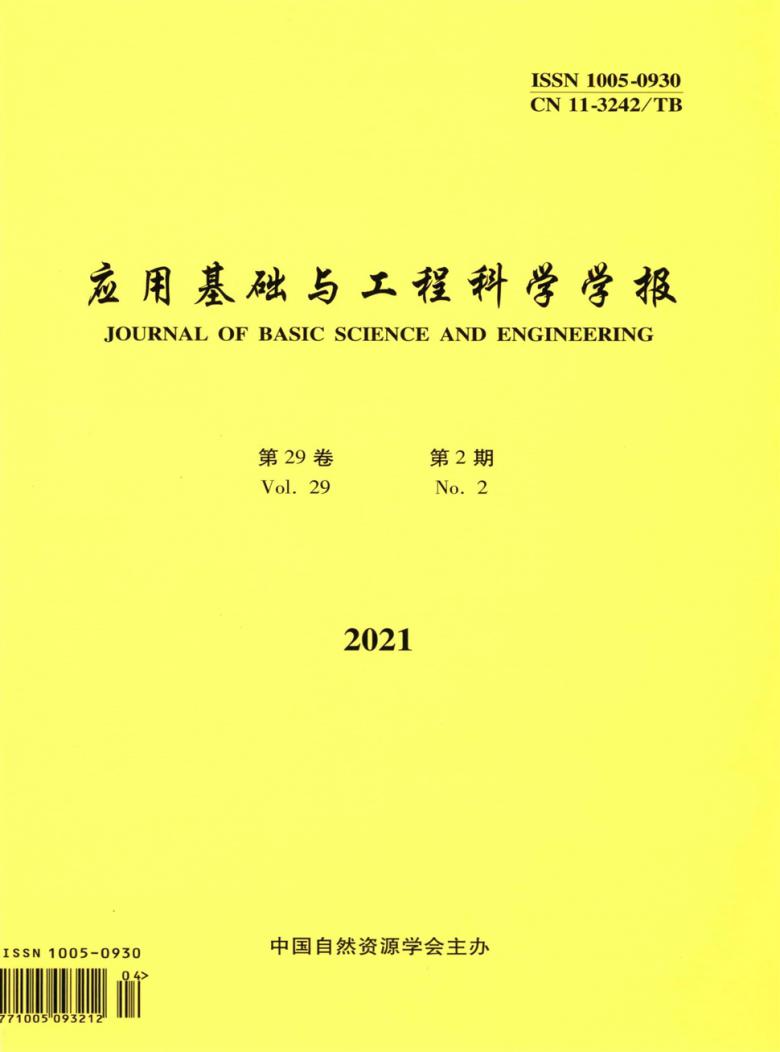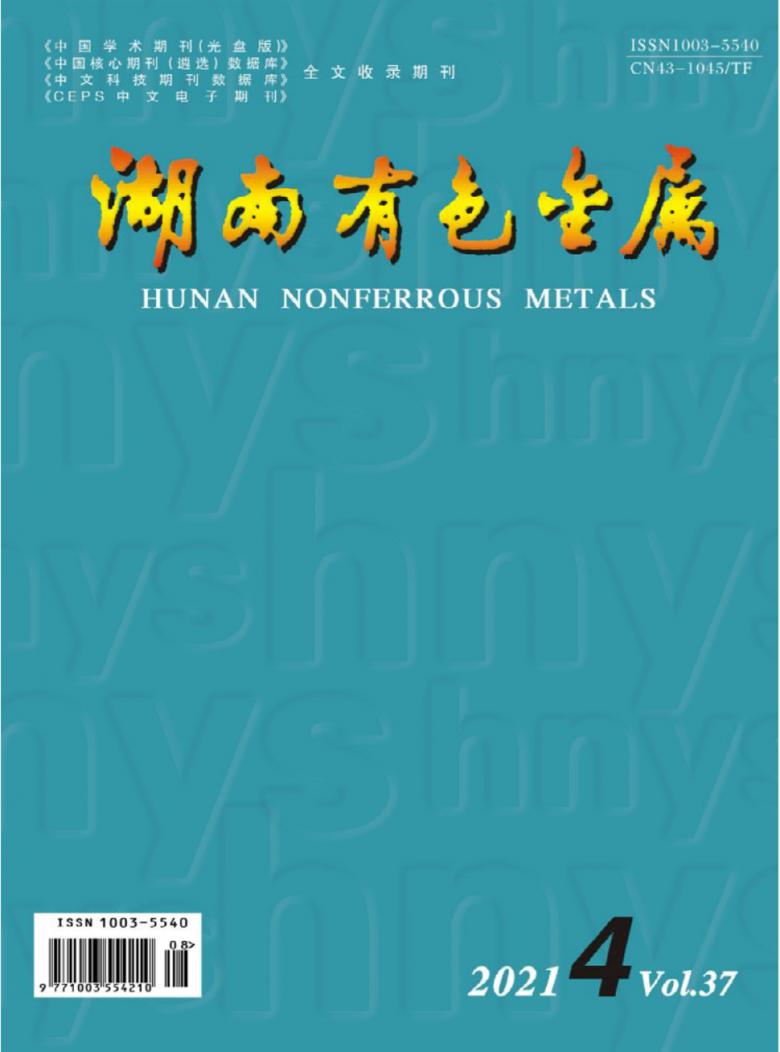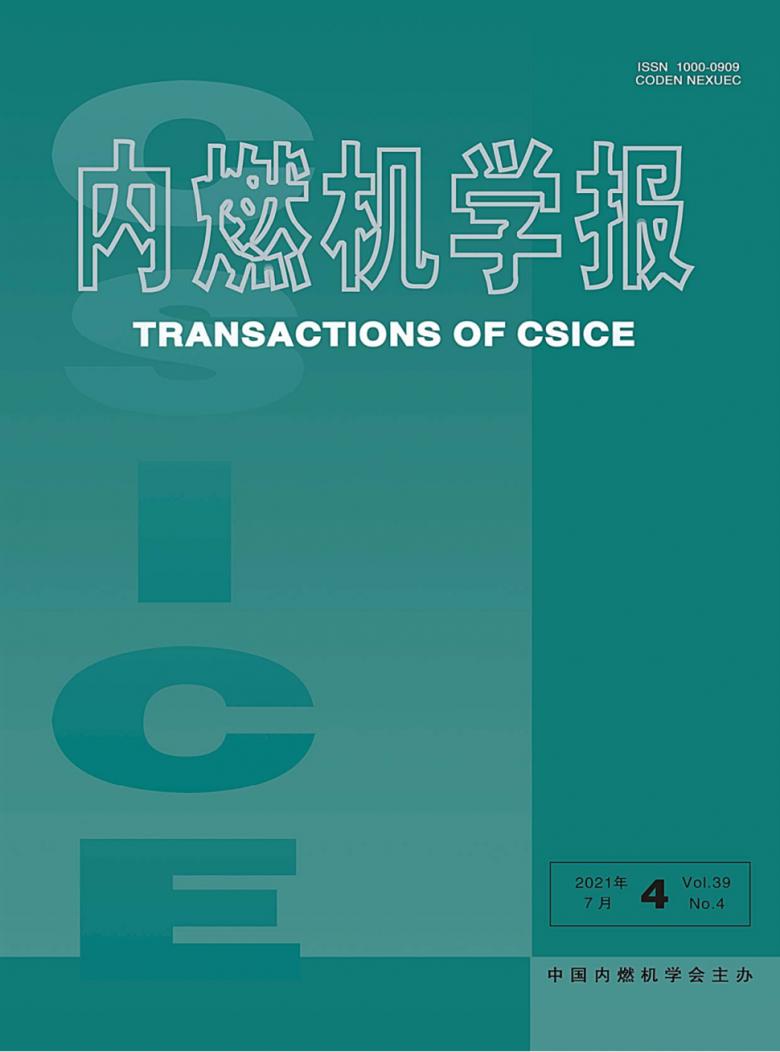试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从《受戒》看汪曾棋的佛教文化意识
李金凤 2011-04-20
论文关键词:汪曾棋《受戒》佛教文化人性欢乐
论文摘要:和尚恋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禁区.汪曾棋的《受戒》却将宗教与爱情,佛性与人性和谐地融为一体.《受戒》消解了佛教作为信仰的严肃性,漠视佛教的清规戒律,张扬人性,倡扬人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间佛教”中,构建了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美好世界。这是《受戒》中体现的佛教文化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道佛教精神共同构成的艺术化的人生.
汪曾棋的代表作《受戒》发表于1980年们匕京文艺》,讲述了一个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的纯真恋情,概而言之,就是和尚恋爱的故事。和尚恋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禁区,有违教义,作家往往避开或者持一种贬斥的态度。在佛教教义中,现实的人生是一片苦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的只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僧会苦、求不得苦以及五阴盛苦。造成诸苦的原因在于“无明”(愚迷暗昧,不明佛理)和“渴爱”所引起的贪和欲,从而导致生死轮回。因此就要念经、修行、持戒、彻底断灭人在世俗中的欲望,达到无苦“涅架”的境界。显然,佛教是主张克制、压抑、甚至消灭众生的各种欲望包括爱欲,达到无爱无欲、无死无生、寂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功德的至高境界。
但在汪曾棋的小说《受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小说描写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生活情景,人们在这里自由快乐地生活着。本来,佛教象征着信仰,可小说完全消解了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严肃性及其修行的庄严性。《受戒》中和尚出家之地叫“草莽庵”,庵本住尼姑,和尚应住在庙里才符合佛理,在小说中却产生了错位,本是菩提庵还被人们叫讹成了草荞庵。仁山,作为庙里的方丈,他的工作本应是做法事、念经,可他在庙里不穿袭装,袒露着肚子,跟拉着僧鞋,一天到晚抱着算盘做会计,好似店里的小伙计。当然他们偶尔也做法事,常做的是放焰口,可庄严的法事被他们这么一弄也变成了耍把戏似的:“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装装,飞饶。……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明海出家既不是为逃离人间苦海,也不是尊崇佛教信仰,而是为现实的功利目的所诱惑的:“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和尚,在当地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明海受戒也是为了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价值观在小说中轰然瓦解.
既然漠视佛教信仰,那么让这些出家和尚格守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必然是一种不可能。佛家讲戒、定、慧三学,以戒为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佛祖入灭前曾有弟子问:“您走后我们依靠谁?”佛祖慈悲教示:“己戒为师!’’但在《受戒》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戒”的迹象。佛教讲“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可革莽庵的和尚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不同的是要在猪升天的时候念一道“往生咒”。事实上,这是一道虚伪的形式,本质上己触犯了杀戒.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的和尚大大触犯了淫戒.和尚二师父仁海带着老婆来庵里避暑,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有一个貌美的年轻女子,三师父仁渡的相好有好几个,还赤裸裸地唱着情歌等妄语,小明海和小英子更是在佛门圣地里两小无猜、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地成长和恋爱,这明摆着犯了淫戒,可“在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可见,佛教的清规戒律在他们眼里形同虚设。没有清规戒律,他们活得舒心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家的当家,乘凉的乘凉,风流的风流,恋爱的恋爱,完全和常人一样,率意随性地过日子.尤其是明海和英子的恋爱更是描写的如乐园一般温馨可人.他们白天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松自在地唱着山歌,晚上并肩坐着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老婆婆纺纱,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滑过,多么和谐美好的俗世人间!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是那么地欢乐,人们也是那么地惬意,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也在大自然的清风软语中渐浓。小英子故意用脚踩他的脚,明海看着“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的一串脚印”,“傻了”,他“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都搞乱了’,.而“搞乱”也是一时,当明海在善因寺受完戒回来,小英子得知明海将前途光明地当上沙弥尾或方丈,忍不住将内心的真实情感大胆地说出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开始只是“嗯”,最终大声地宣布: ‘要!’,没有忌讳、没有压抑、没有矛盾、没有两难,性爱,被表述成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宗教与爱情,人性与佛性,和谐地融合一体。
在和尚恋爱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人性和佛性往往是对立、冲突的,主人公往往处在情佛两难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最终在痛苦无奈中放弃爱情,阪依我佛。例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三郎与静子谈诗作画,情投意合,互相爱恋,母亲和姨妈也有意将静子许配给三郎,可三郎终因“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也”为由拒绝了静子,最后不得不逃离静子的爱。作出逃离的选择对三郎而言何其艰难,文中的心理描见证了情与佛的碰撞冲突使三郎的内心充满无奈和痛苦,“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三郎“初以恋亲而离佛,继以畏佛而拒爱,终以拒爱而弃亲。既以拒爱而弃亲矣,又复千里吊爱,似俗非俗,此盖宗教与爱情之冲突点也”。佛教认为“爱为秽海,众恶归焉”。阪依我佛,就必须遵守戒律,舍弃女色,斩断情根,才能领悟佛门禅理,进入涅架境界。
但是,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们看到的是佛国的清修与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与凡夫的爱欲,两者是兼而得之、互不冲突的。它反映了汪曾祺本人对于佛教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见解。“在作者看来,佛不是要人断绝人生乐趣,而是要人们在佛智的启导下充分地享受人生的欢乐,佛性与人生之至高境界是一而不二的,是融会在一起的.”因此,汪曾棋在小说《受戒》中正视人的各种欲望,宜扬人的爱欲,并且无意于用各种清规戒律来禁止它。相反,在“佛性”与“人性”当中,他选择了人性的解放和张扬,在“佛性”与“人性”融汇之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任何一个人都难把凡间事物一刀了断。《圆觉经》云:“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可知众生的存在与淫欲密切相关,淫欲的烦恼在人类世界是难以戒绝的,而否定、压制人的各种本能欲望包括爱欲也是对人性的扼杀,不合人之情理。汪曾棋在谈到他的《受戒》时也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汪曾棋在小说中描述着和尚有滋有味地过日子,正是将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即慈爱众生,给予快乐;悲,即怜悯众生,拔出困难。可是,“佛教文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普度众生的良药,现代意识的复苏可能冲击佛教的某些理念”。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在中国“汉化”和“民族化”,不少统治者和一些社会改革家对佛教不断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民情.1913年,太虚大师吕淦森和杨仁山等人在南京创设了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教一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使佛教回到人间并世俗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一些出家僧侣和在家修行的居士极力推行“人间佛教”的佛教改革。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和发展,不仅是有识之士推崇并改革以适应中国的结果,也是“广泛深厚民间信仰的结果”(s(.民间信仰与宗教改革者共同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和人情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意识己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更是给予了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汪曾棋经历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革命运动和文化变革,发表《受戒》之时正是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来了百花齐放的良好艺术氛围。一路走来,深受传统文化儒释道浸润的汪曾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思考和反省.汪曾棋认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色彩的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应该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但却不能因此精华与糟粕全收。 汪曾棋从小就生活在相当佛化的家庭氛围中,他的祖父、祖母、继母包括家里的拥女大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汪曾棋家里常做法事,童年时代就浸染了经声法号,上学后,他就读的小学旁边是一座承天寺。1937年,因侵华日军占领江南,他随父亲等人到庵赵庄上的和尚庵住了半年,小说《受戒》中的草莽庵的原型即是此庵,人物原型也多取自于此.汪曾棋去西南联大报考的路上也深受一位高邮和尚的热情相助.解放后,汪曾棋常与寺庙和尚交往论禅,1989年还与台湾星云大师交谈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棋常参观各地的名寺古刹,观看佛教诗文和佛事活动.他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下写了一本普及型的佛教专著—《释迎摩尼》。可见,汪曾棋本人与佛教是有不少因缘的。有人指出:“江曾棋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多与少只是程度问题。佛家—禅宗思想对江曾棋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文学创作,而且还渗透到他的艺术观、人生观。”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是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包含与潜伏着共时性的文化转换与历史性的文化积淀。汪曾棋的佛教文化理念都会在它的作品中相应地表现出来。汪曾棋认为,佛教不应该成为生本不乐,诸般皆苦的教义,而应该扫荡传统的厌世情绪,倡扬人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间佛教”中,这恰是汪曾棋在《受戒》中体现的佛教文化意识。
在谈到《受戒》时,汪曾棋表明作品“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生活是美好的,有前途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f81,因此,无论是版依我佛的僧侣们还是普通的俗人,他们都应该以现世为基础,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这样才能感受到佛所言的“喜无量心”,也才符合佛对菩萨最根本的教导。慧能大师在《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门。”离开了佛教的世俗化、人间化,佛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是佛应该给予信徒的幸福生活!
因此,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由和谐的欢乐世界。庙里的和尚生活地自由自在、率性而为就不复赘言了,就是当地的居民也处在一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中。英子一家,温馨无忧、恬淡淳朴地生活着:赵大伯是个能干的“全把式”,什么活都能干,人又很和气:赵大娘勤劳能干,精神好,他们男耕女织,快乐劳动,自给自足;大英子许了的人家人很敦厚,家道殷实:小英子率真、可爱,保存着最为自然的本性,快乐地成长,该恋爱的时候就和明海拥有一段纯真的情爱,没有父母的阻拦,没有不许早恋的警告,人性如深山中的溪水一样自然流淌,蹦跃着欢乐的水花.围绕小英子一家交往的人们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在插秧割稻子的忙碌季节里,排好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着一起做农活,干活时,还“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这完全是一幅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看不到苦恼,看不到困难,看不到黑暗,点点的优伤似乎都没有,纯乎西方的极乐净土。
《受戒》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欢乐和温情,体验恬淡自如的生活方式,充满俗世的美。在强大的人性力量面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意味荡然无存。没有佛教的清规戒律,平淡地生活,享受生活,构建了“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美好世界。这是汪曾棋对佛教文化的理性思考,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主流,橘道佛教精神共同构成的艺术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