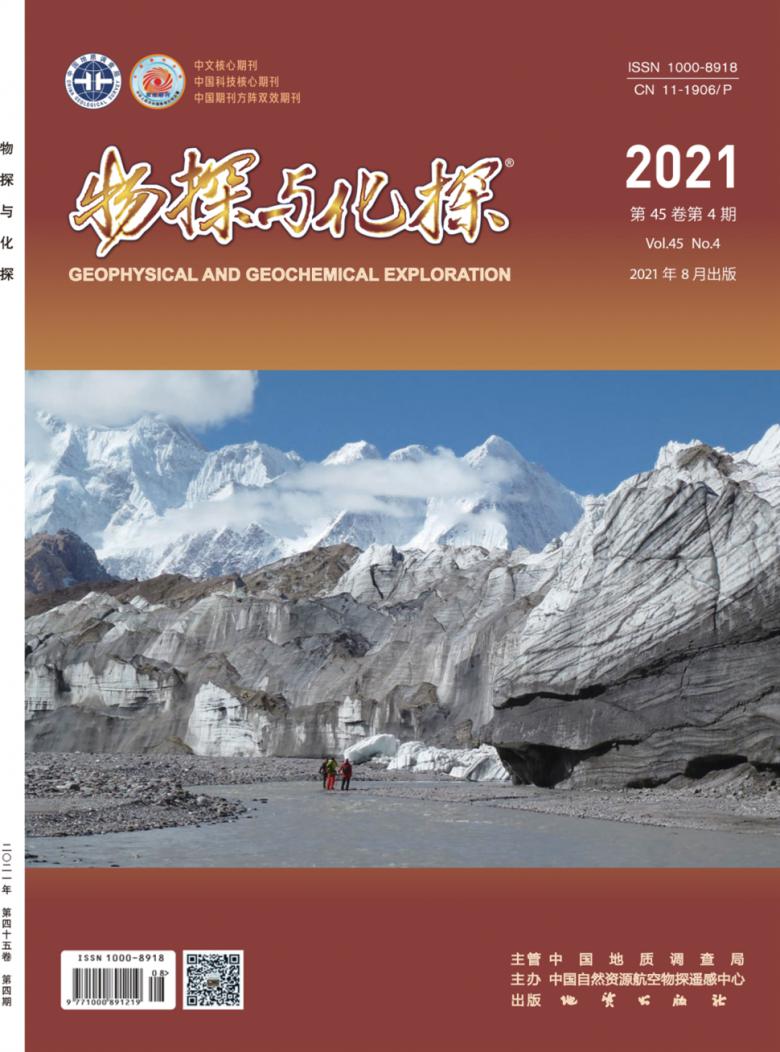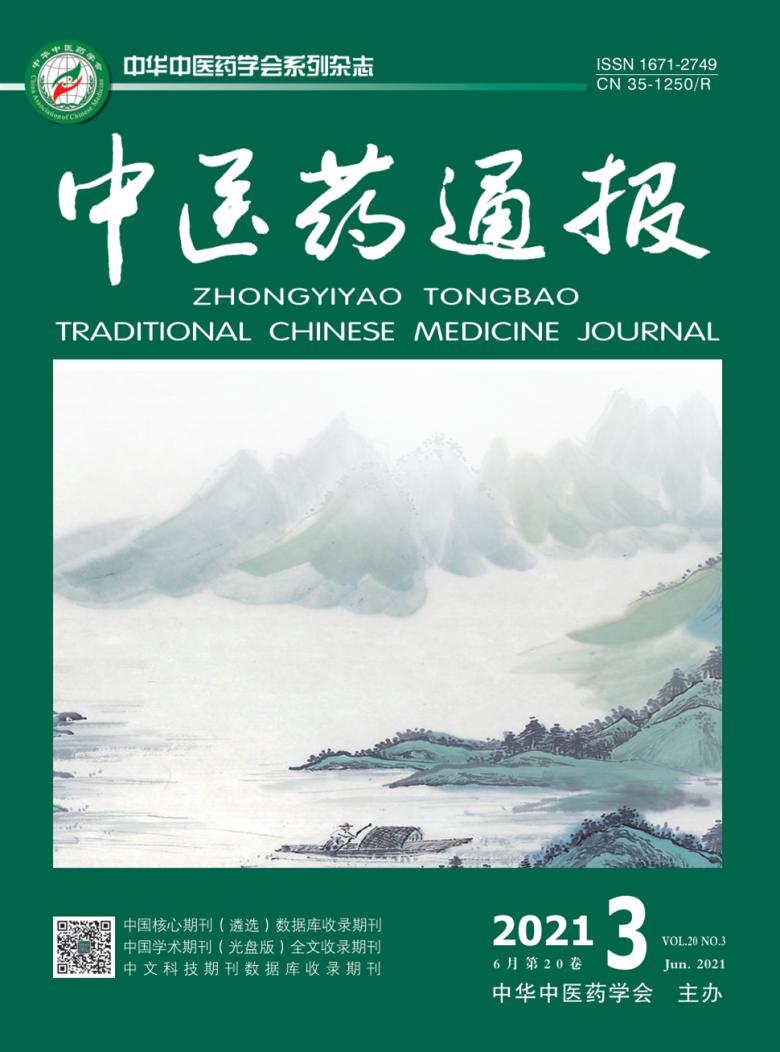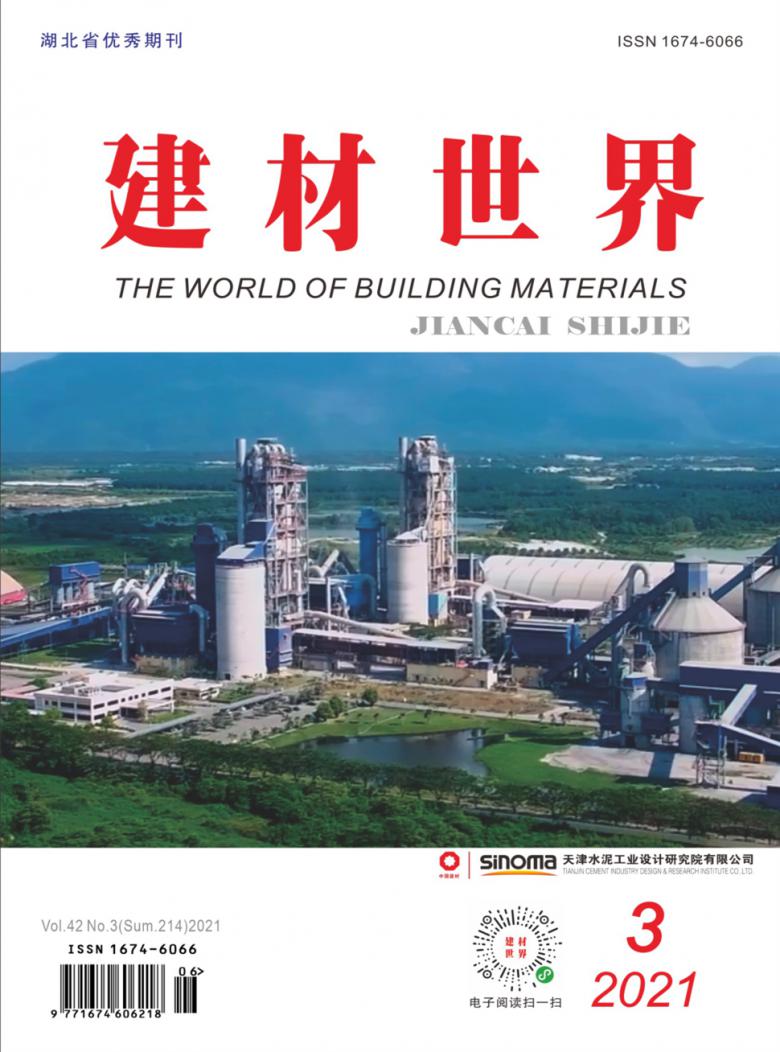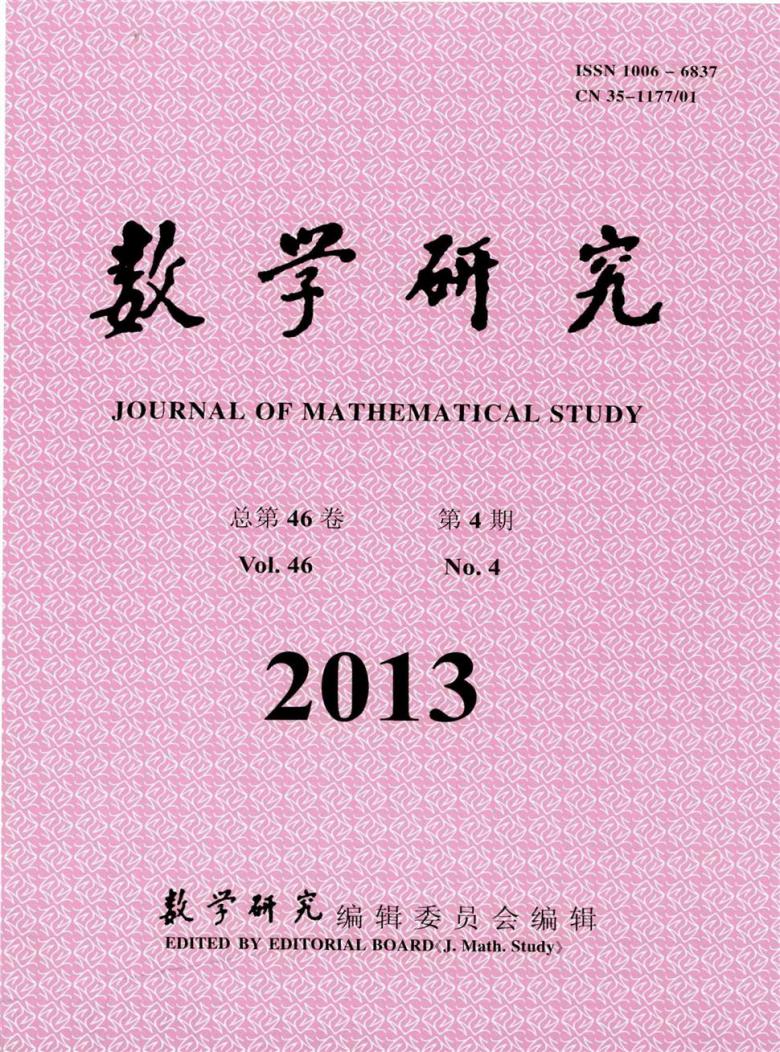浅谈当代教育伦理学的发展趋向
程亮 2011-05-15
论文关键词:教育伦理学;伦理学;发展趋向
论文摘要:在当代语境下,教育伦理学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在研究问题上从“教以道德”走向“道德地教”,在研究动力上从“专业主义”走向“实践主义”,在研究重心上从“道德规约”走向“实践反思”,在研究路径上从“伦理应用”走向“教育返观”。
作为一种分析教育与道德关系的“知识体”,教育伦理学是在伦理学与教育学的相互激荡中逐渐形成的:伦理学在探讨道德问题时,往往诉诸教育的力量,促进道德的进步;教育学在讨论教育问题时,常常追究道德的前提,巩固教育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沿着杜威、纳托普等人开创的路线,教育伦理学不断丰富论域、拓宽视角、更新范式,逐渐成为教育学(或伦理学)家族中的重要分支,甚至在大学里形成了初步的学术建制。本文试图立足当代的语境,勾勒教育伦理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趋向,以为反思和参酌。.
一、研究问题:从“教以道德”走向“道德地教”
单从渊源上说,教育伦理学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派,他们宣称可以教人以道德;在中国也可以返回到先秦诸家,他们主张以道德人格为教育的目的。首先从理性的层面对道德的“可教性”(或者说教育完成道德目的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的,当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是,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从昆体良到夸美纽斯,从洛克、卢梭到康德,往往将这一前提问题“悬置”起来,直接将道德作为教育的目的或内容提出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成,以往有关道德作为教育目的或内容的强调,逐渐使人们意识到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例如,赫尔巴特从“目的一手段”结构出发,依据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不仅确立了道德之于教育的最高目的,而且奠定了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新康德学派的纳托普也按照康德的批判哲学,以教育为达成真、善、美目的的手段,建立了教育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的架构;此外,还有贝内克、施莱尔马赫、罗森克兰茨、拉伊等,都将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知识来源。由此,教育与道德的关系,逐渐摆脱了纯粹经验的直觉或感悟,进而获得了伦理理论的理性辩护。总体来说,这些思想家或哲学家集中关注的仍然是“教以道德”的问题,具体涉及“道德是否可以教”、“教育应该达到何种道德目的或传递何种道德内容”两类问题。
然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教育伦理学在论域上逐渐有了新的拓展,即从“教以道德”到“道德地教”。这种拓展与杜威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教育伦理学”课程,形成了“教育伦理学”著作(Educational Ethics: Syl-labus of Course of Six Lecture-Studies ),更为重要的是将伦理的视角从教育的目的(或内容)层面转向教育的程序或制度层面。他认为,学校的道德目的不能仅仅通过直接的道德教学来实现,而必须依托一种更加广泛、间接、生动的方式,即将学校自身、教学方法、课程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在半个世纪以后,彼得斯(Peters R.S.)在《伦理学与教育》(EtI11CS and Education )中通过“教育”概念的语言分析,提出“教育”本身就意味着“道德”,旨在“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向学生传递某种有价值的内容”。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杜威的余绪,直接将“道德”纳人教育的“标准”,即一种能称得上“教育”的活动至少应该满足两个道德上的标准:一是传递的内容应该是“有价值的”;二是传递的方式应该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索尔蒂斯(Solos J.F. )、斯特赖克(Strike K.A. )、古德莱德(Goodlad J.)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有关“道德地教”的分析在主题上更加丰富,有的探讨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项事业或实践的道德性质,有的分析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伦理要求(主要是“教师专业伦理,’),还有的关注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承担的道德角色、遭遇的伦理困境、采取的伦理反思等。显然,这些分析直接指向的不是学生的道德发展,而是教师及其实践的道德维度,乃至作为教育(或教学)外部条件的政策或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说“教以道德”重在“道德的教育”,那么“道德地教”则偏向“教育的道德”,关涉的是教育的“正当性”问题。就此而言,当代教育伦理学不仅与道德教育理论殊异,而且不限于教师伦理问题的分析。
二、研究动力:从“专业主义”走向“实践主义”
早期有关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是由教育的道德目的或性质所激发的,常常诉诸教师道德人格的养成和教师行为的道德规约。这些研究一般将教师作为“道德主体”或“道德教育主体”,但是未能明确从教育专业的特性出发,阐明教育伦理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区别及其在实践层面的意义。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推进,教育作为专业实践、教师作为专业人员,不仅在制度层面得到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确认,而且在理论上引起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在这种“专业化”的诉求下,“教育专业伦理”或“教师专业伦理”概念逐渐成为教育伦理学关注的“中心”。这些研究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条路径是“社会学式的”,即从专业社会学的立场出发,以社会中相对成熟的专业(如医生或律师的工作)为参照,认为教育(或教学)要想成为一门专业,不仅要以坚实的知识或技能作为基础,而且还要履行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提供独特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中,专业人员(主要是教师)与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之间并非自愿或对等的关系:前者通常居于支配地位,后者往往处在受动的位置;这意味着专业人员必须承担起对服务对象的道德责任,以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权益和维护专业人员的社会形象。另一条路径是“教育学式的”,即以教育(或教学)专业中专业人员(教师)与服务对象(学生)之间的具体关系为基点,分析教师伦理的专业特性: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不同,教师并不是去维持与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和社会距离,而是与学生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惠式的关系。不管采取哪条路径,这些研究的动力或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专业化”及其“专业主义”的诉求,其目的都在于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品质和专业地位。
然而,这种“专业主义”的诉求,不仅在理论上容易遭到洁难(特别是“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预设),而且在实践上容易滑向“技术主义”,因为它强调的仍然是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专化。在这种“主义”看来,教育(或教学)是一个工具化、操作化或技术化的过程,因此教育(或教学)的问题不过是技术的问题,可以通过知识的提供、技术的改进予以解决。然而,“实践的”问题毕竟不是“技术的”问题:“技术问题着眼于在既定的目的(价值和准则)的情况下手段目的的理性的组织,以及在不同的手段之间的理性选择。相反,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我们可以据理支持或反对行为规范的公认的要求)。”这意味着,需要将教育(或教学)从“技术”的梗桔中解放出来,重新淦释为“实践”,进而凸显其“规范”或“道德”的维度。这里也有两条路线:一是直接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运用“实践智慧"(phrone-sis )概念,否认有关教育(或教学)的工具化、操作化或技术化理解,强调教育(或教学)在道德上的复杂性;二是从麦金泰尔的“实践”( practice)概念出发,认为教育(或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协作活动,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利益”或“卓越标准”的实践,而这种“内在利益”或“卓越标准”就是满足或促进他人的学习,要实现这种“内在利益”,就需要教师拥有某种德性。总体说来,这些研究试图超越“技术主义”的限制,恢复教育(或教学)作为实践的内在品性,重建教师作为实践者的主体价值。 三、研究重心:从“道德规约”走向“实践反思”
不管人们如何定位,教育伦理学都是以“伦理学”为理论渊源的。伦理学的传统乃至分歧,也常常会在教育伦理学的架构中进一步具体化。长期以来,“规范伦理”在伦理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教育伦理学最初也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教育(或教学)的“道德规约”上,或针对教育(或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的道德问题或困境,或从教育(或教学)所内含的道德品性、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出发,着力探讨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中教育(或教学)应该遵循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或道德规则,以及将这些理想、原则或规则内化为教师个人修养、制度内在品性的可能条件。因此,制定规约教育的优良道德规范,就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首要任务。
然而,这种“规范”的立场常常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除了一些激进的怀疑甚至否认道德规范普遍性的观点之外,更多的批评聚焦在道德规范的实践层面:即便是最优良、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也不足以提高个体在教育情境中的道德判断,不足以应对教育情境中的道德困境或冲突,不足以保证个体在教育情境中的合理选择;相反,教条化地悟守某些道德规范,可能会阻碍个体在实践中的道德成熟,甚至可能造成某种“反道德的”结果,如以忠诚的名义滥用职权。索尔蒂斯也警告说,教育伦理准则( code of ethics)并不能为其蕴含的基本伦理原则提供辩护;如果这些规范在实践中相互冲突,或者需要为一个人行动的理由进行辩护,那么教育者只是了解准则,就可能对情境做出不当的处理。因此,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伦理的实践最终还有赖于实践者个人的“德性”或“实践智慧”,而要获得这种“德性”或“实践智慧”,又有赖于实践者的“实践反思”。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道德规范在教育实践中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不是。仅有“规范”不足以产生“道德的实践”,但是失去“规范”,就无从确认“实践的道德”。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规范”,而是“在实践中如何应用规范”。一般而言,“应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应用,将道德规范看作是普遍的、自足的、超越情境的,关注个体对这些规范的严格遵循;一种是“实践”意义上的应用,认为道德规范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的合理性取决于实践的情境,有赖于个体的实践智慧,即将一般性的规范与具体化的情境结合起来的能力,因此规范不是用来“照搬”或“套用”的,而是为个体实践提供分析的工具,为个体判断提供参照的基点。当代教育伦理学尽管也在不断提出或完善教育的伦理原则,但是也充分意识到这些原则的实践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从业者的实践反思或实践智慧。
四、研究路径:从“伦理应用”走向“教育返观”
这里的“研究路径”,主要涉及“立场”( stand-point)和“方式,"(approach)两个维度。就研究立场而言,教育伦理学也从“伦理学的教育应用”走向“教育的伦理返观”。教育伦理学显然离不开伦理学,需要伦理学提供的概念和命题、理论和方法,但是这种“需要”并不意味着教育伦理学只是伦理学的简单应用或逻辑推演,或者说教育伦理学只存在与伦理学的单向关系。事实上,从杜威、彼得斯以至当今的诸多教育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教育作为一个实践领域的独特性,以及由这种独特性所引发的教育伦理学之于伦理学的“反哺”关系。这种“反哺”可以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为伦理学的已有理论提供新的证据;二是补充或修正伦理学的原有概念、命题或理论;三是提出新的伦理概念、命题或理论;四是形成新的伦理探究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伦理学的建构不能只是从伦理学到教育的“演绎”,还应包括从教育到伦理学的“返观”。
“研究立场”的转换往往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调整。当代教育伦理学也不满足于“规范的”研究传统,不限于价值的辩护和规范的引领。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语言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开辟了教育伦理学的新方向。特别是在谢夫勒、彼得斯等人的探索下,直接从“教育”、“教”、“训练”、“灌输”等概念的“日常用法”中,离析出“教育”或“教”所内含的道德维度,从而使伦理的要求成为“教育”或“教”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在教育的语境中,“分析的”方法可以澄清概念使用的某些混乱,但仍然难以回避价值或规范的问题。这意味着,“规范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存在互补的可能。因此,索尔蒂斯、斯特赖克等人又将教育伦理学引向了“实践的”道路:以道德两难教例为分析对象,结合伦理学的经典辩护理论(结果论和非结果论),探寻教育伦理准则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应对这种困境的可能选择。这应该是一条更加综合的道路。
以上仅从四个方面粗线条地呈现当代教育伦理学的“走向”。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走向”并不意味着教育伦理学原有道路的消解,而只是表明当代教育伦理学呈现出的一些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