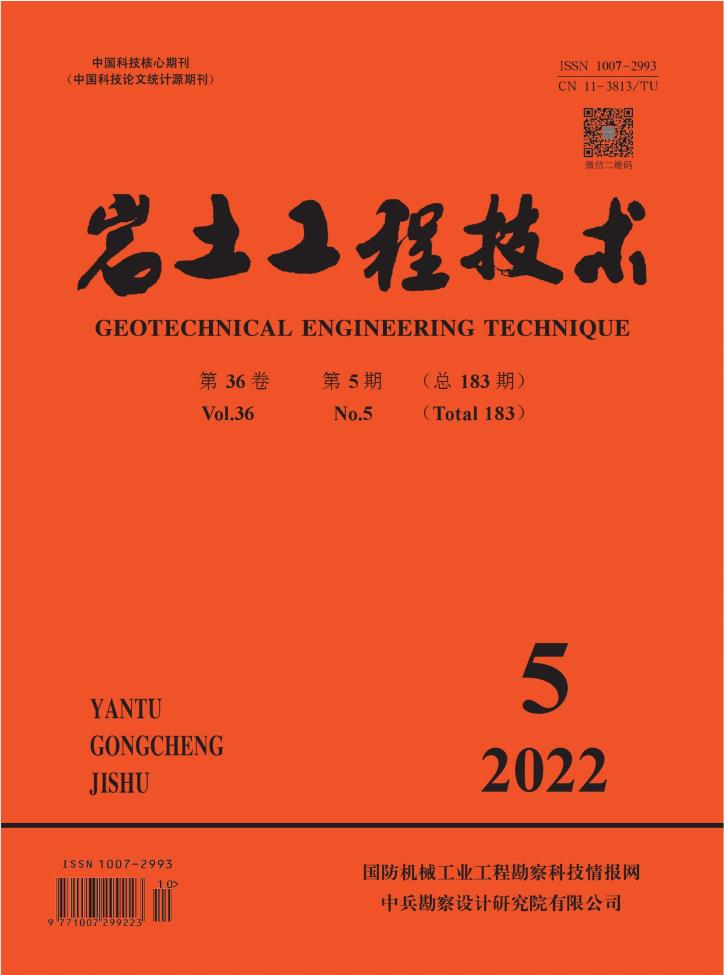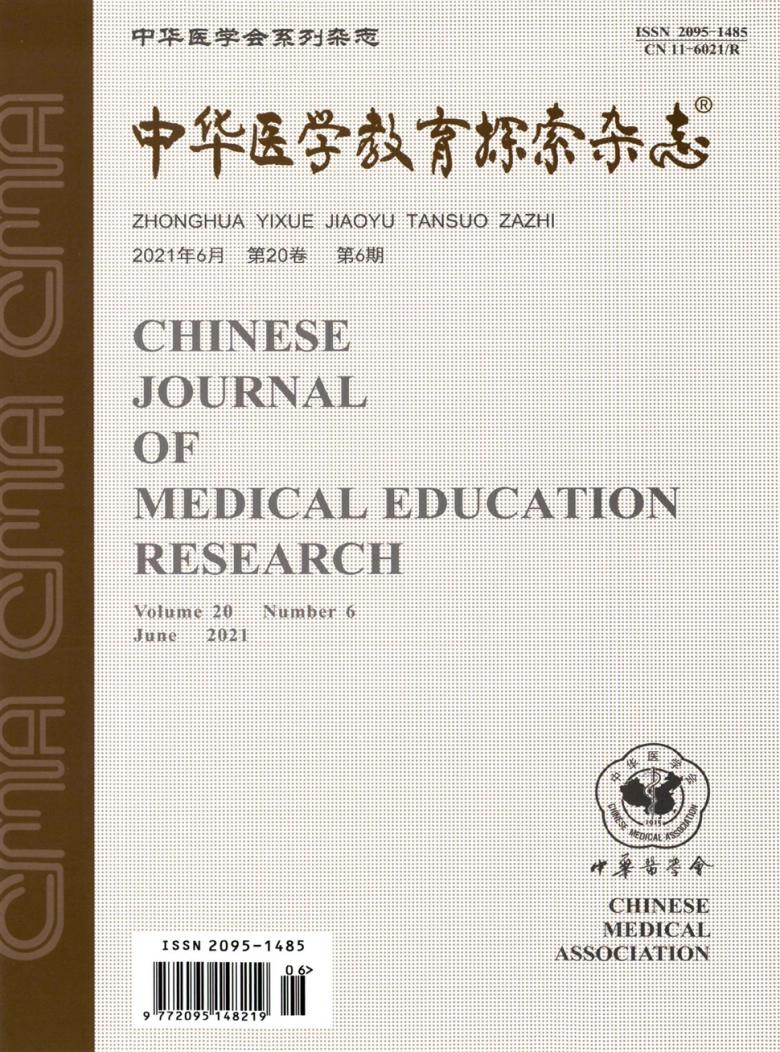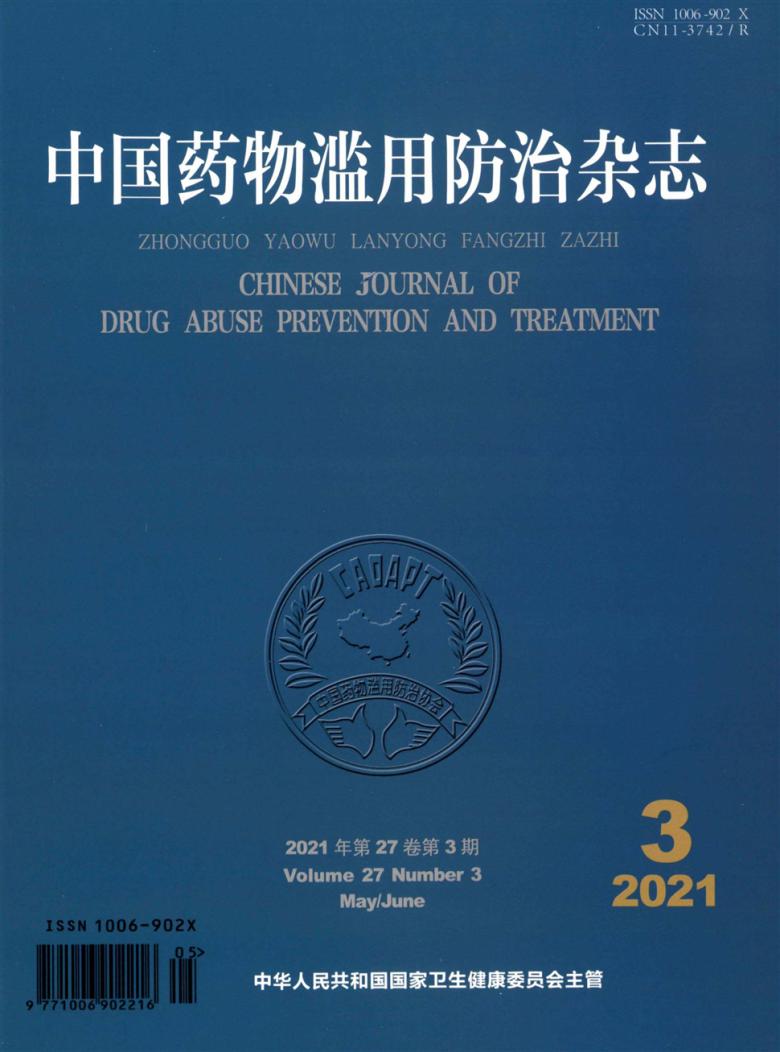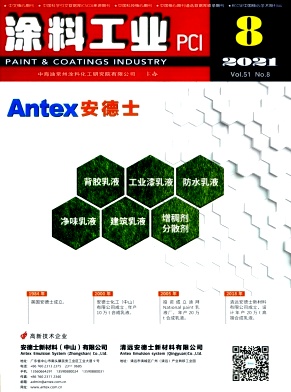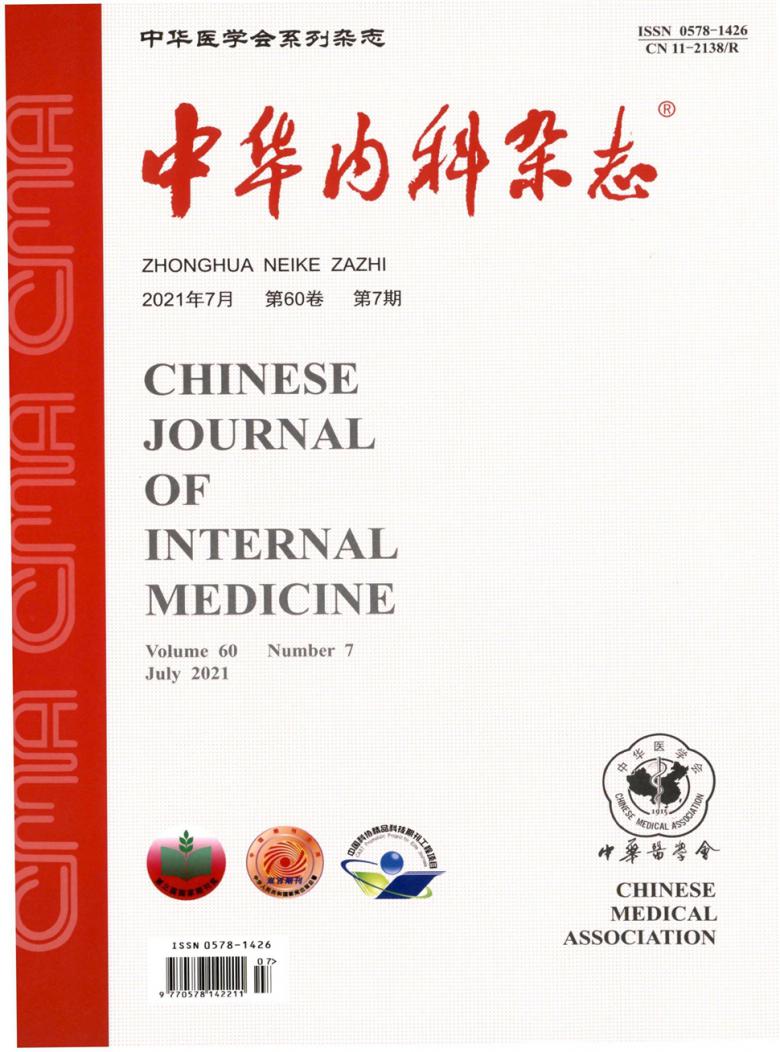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佚名 2006-01-11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原因造成的长期无法解决的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产生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最终使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因此,三农问题隐含的实质是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
关键词:三农问题 社会公正 社会排斥
农业、农村、农民,一个天大的“农”字,成了绕不开的难题。“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头等大事。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和农业曾经引领制度创新、改革之先,农村社会生活一度欣欣向荣。但是进入90年代后,农村和农业在体制改革上不仅没有大的突破,反而因为旧体制的延续逐渐桎梏了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的提高停滞不前的同时,农村的社会危机开始浮现,而危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和社会排斥。
一、当前三农问题呈现的新特点:主要社会群体的总体弱势化
首先是农村的日益贫困化趋势。虽然经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90年代初的8000万下降到90年代末的3000万(按人年均收入625元计),但是还有约2000万人处在温饱线的边缘,若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计算(相当于农村年人均收入的水平),贫困人口则更多。而且,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在90年代迅速增加,成为目前农村贫困化的主要问题。以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若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全国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就已达0.456。如果后者更符合这些年贫富差距扩大的实际感觉,以此为参照,农村的基尼系数应该超过0.5的官方警戒线了。农村的相对贫困化的加剧,还体现在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和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加速,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农业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2]而以城乡居民储蓄为例来看,8万亿左右的储蓄余额中,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只占约1万亿。若以居民享有的水电、道路、通信、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差距来看,城乡间的差距要比上个世纪70年代末更加扩大。
其次,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一方面,由于农村县乡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结果不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贫困化,而且导致统治形态趋于暴力化,农民实际日常生存条件恶化。也正因为此,基层干部队伍出现债权人化,日益异化基层政府的性质和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导致干群关系恶化。[3]同时因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他们原本已很有限的合法权益也因此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在贫困地区,农村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村级自治基本上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因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继续支撑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这等于强迫农民仅仅依赖人均有限的土地,在承担种植成本、口粮和各种税费摊派后,还要内部化所有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生命风险。反观小农经济时代,如果风调雨顺、租佃关系稳定、捐税合理,农民或可温饱。然而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不断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均缺乏适当的法律制度保护,同时农民教育、医疗支出上升等社会生存条件逐步恶化。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就已经开发过度、负荷过重的土地还能为农民提供什么保障呢?这就使得农村社会危机更加动荡。
因为危机的加剧,农民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农村出现的悲剧性个案越来越多。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近几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并且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三十三,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作为农村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她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之巨可见一斑。同时,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危机的深化,危机效应也随之扩散。社会各界、海内外正在对三农问题投入强烈关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和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两本书的个案分别从不同角度一再证实了内地农村的社会危机之严重和基层政权制度的极端不适应。对于农村的社会问题,现行的农村治理体制既无法从个案上逐一疏导,又难以从根本制度上予以缓解,进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1999-2000年因为自下而上的抵制,安徽省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遭遇挫折,个中沉疴锢疾与九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时所面对的困难竟如此相似。并且,农村的社会危机势必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李昌平所描述全面的三农危机:农村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底层贫困问题转化为社会治理危机、两极分化问题转化为阶级对立问题等。[4]
第三,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农民生产生活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历史。加上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面临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压力。最近,国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是很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是由于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和动员能力大不如从前,很多地方的农业基础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抗灾功能退化严重。以至于正常年景也灾害频繁发生,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日益凸现。农村教育虽然教学楼比过去高了,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公共品不复存在,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家庭收入的36%);据卫生部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医疗支出户均500元,在农村生病住院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现在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中学、公路等基础设施都由国家出资建设已经转入地方负责,而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已无力承担这些基础设施的安排。农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中西部的乡镇企业也因为农村市场的萎缩而难以为继,留念故土不再是新一代的农民观念,这也预示了城市的无秩序化时代的开始。
加上近年除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有所增加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不仅不对农业投入,相反,市、县、乡(镇)政府迫于数千亿债负(仅乡一级就高达2300多亿)和数百万超编人员的吃饭压力,还层层截留中央对农业的投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每年动员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但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再也组织不起“人海战役”了。投资和投劳的大幅下降,导致农村生存和生态环境状况日益严峻,过去已消灭的各种疾病在农村又重新泛滥起来,艾滋病等新的疾病来势迅猛,威胁人畜的生命安全和生产安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由短缺实现了向过剩的跨越,但农业的成本上升,农民的生存成本上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增产不增收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加入WTO后,国外的农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内大城市市场,导致很多生产与进口农产品相同农户的商品量越来越少,不少农户更加小农化、面临自给自足化的压力。
第四,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部门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现在,中央政府对农村的相关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逐步被地方政府异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政府的很多部门都因为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在执行其职能的过程中,部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假如中央财政拿出一个亿的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不仅不能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相反还有可能加重学生家长几千万元的负担。农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基层政府和部门“靠权吃民”的现象有泛滥之势。近几年中央以极大的力量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治理乱收费现在,但不少地方上半年“合费并税”,下半年又“税外加费”,并且这种现在有普遍化的趋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少地方政府和党的基层组织不同程度的“异化党和中央政府在农村政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总之,正是上述问题的长期存在和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成为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这一总体趋势。
二、三农危机的实质: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5]
三农问题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原因造成的长期无法解决的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产生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最终使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公正问题。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
社会排斥简单定义为由于社会公正失衡导致的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由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概念具有以上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有力的概念分析工具。它可以描述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揭示出将他们排斥出社会的推动者和施动者以及其中的机制和过程。这样也就能更好地说明社会公正失衡与其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关系。我国的社会公正问题导致的社会排斥表现在:
第一,公正失衡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排斥,即个人、家庭和贫困地区或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排斥把农民排斥出正常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务工限制、户籍壁垒等)、收入贫穷和消费市场之外。劳动力市场排斥指两种情况:失业或排斥出劳动力市场(exclusion from labour market)及劳动力市场内部排斥(exclusion within labour market)。鲍格姆将人们的就业状况由失业/就业二分法扩展为五分法:没有风险的固定工作(两年内没有失去工作的风险)、有风险的固定工作(两年内有失去工作的风险)、不固定的工作、短期失业(不超过两年)和长期失业(超过两年)。也既是说,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也和失业一样会导致人们被社会排斥,排斥的可能性随着就业不稳定性(occupational precariousness)的上升而增大。阿特金森也指出,从事不稳定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marginal job),并不能保证人们融入社会。[6]从事不稳定的工作或边缘工作的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或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但可以说是遭受了劳动力市场的内部排斥,而这种排斥同样可以引发其他维度的社会排斥。收入贫穷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贫穷线。消费市场排斥指两种情况:一是个人和家庭买不起或因经济拮据而限制使用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由于贫困和购买力低使得弱势人群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社会消费,他们就成为所谓的“被排斥的消费者”(exclude consumer)——排斥于社会主流的消费方式之外。经济排斥理论可以解释我国当前经济领域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分配不公和弱势群体等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更反映出农民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城市里的“三无农民”就是被排斥出了城市社会系统又被排斥出农村社会系统的一群。
第二,公正失衡把弱势群体排斥出正常的政治生活,即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disempowerment or powerlessness)、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政治排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和团体因为没有政治权利而遭受排斥。但政治排斥不仅涉及到是否拥有政治权利,而且还要看在法律上拥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是否能在现实中运用它们。第二类是指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未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排斥的指标主要包括:未参加选举,以及未参加政党、工会和社区性组织等。列宁说“文盲是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弱势人群缺乏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也缺乏政治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因而所谓的政治权利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实际意义,也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系统。 第三,公正失衡导致对弱势人群的社会关系排斥,即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豪斯等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存在(existence)或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其次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密度(density)、同构型(homo—geneity)、多样性(multi-plexity)或分布(dispersion)。第三是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依据以上框架,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当前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和社会交往能力的不公正,及其获得社会支持机会的不公境遇。
第四,公正失衡将弱势人群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识系统,包括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1ifeorientation)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文化知识排斥还应指处于少数的个人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所以,完整的文化排斥概念应该包含上述两层含义。以少数民族为例,当他们不能保留自身文化传统时,他们就遭受了文化排斥;当他们希望以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而又没有这种可能性时,他们同样遭受了文化排斥。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那么即使给予相应的文化权利,他们也无法正常地参与到主流文化知识系统中来。
第五,公正失衡也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各种制度之外,包括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包括社会救助制度)而无法获得公正的国民待遇。此外制度排斥还包括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只能保障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有基本保障,长期失业者将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7];而从未工作过或缴纳过社会保险金的人也同样会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这种情况一样在中国非常普遍。制度排斥使得弱势群体无法得到起码的制度公正和保护,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
社会公正失衡造成的社会排斥及其带来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除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外还会造成利益受损者处于多重的社会弱势之中,如导致社会贫穷、社会的对抗与排斥的“马太效应”,甚至由于社会公正失衡直接排斥了弱势阶层进入正常的消费市场、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网络分割、并被排斥出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之外,由于长期的社会公正失衡和社会排斥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人为的与制度性的社会断裂,造成更多低下阶层(underclass)的不应该出现,从而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8]与政治认同。其后果就是破坏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造成了政治合法性认同的严重流失,也就严重削弱了共产党执政的功能及其有效性。也正是社会公正的缺失,成为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对当前我们执政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主要参考文献
李昌平:《防止三农问题转化成革命问题》,中国农村网。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黄洪、李剑明:《困局、排斥和出路:香港 “边缘劳工”质性研究》,香港乐施会,2001年。
王永慈:《社会排除:贫穷概念的再诠释》,《社区发展季刊》2001年第95期。
Bakke, E. Wight 1969, Citizens without Work: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upon the Workers’ Social Relations and Practice, Hamden: Archon Books.
Berghman, Jos 1995,“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olicy Contex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Room (ed.)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Bittman, Michael 2002,“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The Money and Time Costs of Leisure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