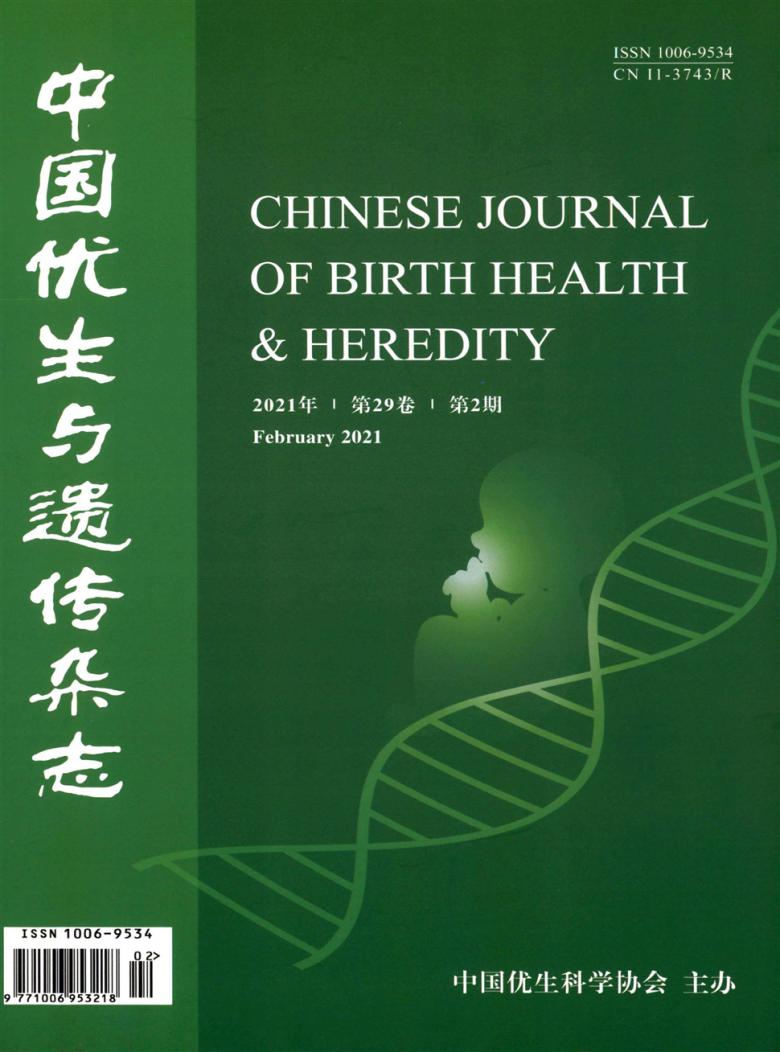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
金 鹏
【英文标题】Agricultural Surplus: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v in the Late Oing Dvnastv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命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加以考察。通过对晚清的农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形态也无法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化。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巨性是结构性的。
【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As the issue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m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be approached from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ide enough agricultural surplu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political rule could not afford necessarv government support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tion. The difficulty in sta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structural.
【关 键 词】农业剩余/现代化
agricultural surplus/modernization
一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常常因为过分的比附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者会遭遇理论框架及其解释能力双重匮乏的局面。我们尝试解答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难性的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加以检讨是一个必需的前提。笔者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需处身于"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eh)的立场,即将眼光放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1-p135]之上。
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启动问题的厘清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内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结构,及其自生的变迁动向。因为,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体形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引入中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偶性因素是已然确定的。所以,在这一题域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没有设问和解释效力。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即使冲击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对中国的现代结构之形成过程及其特征的分析,仍需从中国的自在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去提问。所以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方向性含混,重要的不是就中国近代化提出马克思式或韦伯式的分析,而是提出建立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之上的分析。这一历史经验表现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情境……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1-p173-174]
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转型,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其最重要的表征,在经济形态上它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菲雷对法国的近代化作过准确描述:"旧体制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将此工作完成。"[2]对中国情境的分析则体现为另一反题:旧体制将中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依旧举步维艰。
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中古经济革命"(注: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1973)中用以描述中国前近代经济变化的重要概念。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宋代已有重大变革,并且此一变化提出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之后,中国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此后一些令人鼓舞的历史迹象(类似于中国明清之际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等)常常被一些史家援引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的结论。然而,中国农村经济从未突破旧体制的框架,生成中国社会近代转置的动力因素。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是存在的,因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命题就是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农业剩余成为此际的关键,并构成为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中剧情主线的最有力抓手和极重要的分析范畴。因为,现代结构的生成即便在西方历史中呈现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但就社会形态的层面上观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却有着巨大的断裂。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的经济形态在其功能承担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用来维持社会的再生,而是向社会提供"潜在剩余"(注:保罗·巴兰:《关于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Baran,Paul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uth, New York:Monthly Review 1957)中提出资本形成的过程应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转化为社会的有效积累,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农业剩余"在中国现代化启动中的突出地位,那么问题就作了如下的转换:一、农村经济发展是否创造了足够的农业剩余;二,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换为社会有效积累?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表现为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是缠绕在一起的。下面细而论之。
二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第一个命题。许多研究者以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得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粗放式"(注:莫尔德:Japan,China,and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1660 to ca·191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在此书中,莫尔德把商业化区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两种,后者的标志是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消灭较快,交换关系对生产起较大支配。这种分类对于认清明清农业商业化的属性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商业化过程四处扩散等等,似乎一种将传统社会推向近代社会经济成长的突破性变化即可发生。然而,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现象亟需更深入的探讨。
不言而喻,晚清及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都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形式经济学在阐明人口增长对中国农业所起的作用时,作出了突出贡献。(注:有关人口压力造成的中国经济变化,何炳棣通过中国历代田赋和人口资料的分析,取得建设性成果,可见何著《中国人口的研究》(Studies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59.)另,德怀特·帕金斯在其著作《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中也有大规模的量性研究。)在 1792年雍正帝实行摊丁入田的税收政策后,人口的繁殖获得了最大的鼓励。就传统农业而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产量的增长几乎是具有同等含义的。在人口扩张之初,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能力赶上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鼓励农民垦荒、允许地区间移民、在新开发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作物,将更多的人力用于种双季稻必须的精耕细作之中,这些既使原有的农业部门有效地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农业产出的增加也一定意义上化解了人口压力。农业经济中持续的赢余和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生产和富余的大量人口在其最初并未显示太多的问题,然而,这里却隐藏了十九世纪后中国发展的诸多危机。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据考察,每个劳动力可耕地15至30亩[3]。但人口巨大增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从当时人均拥有可耕地的数量来看,整个19世纪都在1.75亩至2.3亩之间徘徊。所以单从平均亩产来看,这时期中国农村的发展已达到传统技术的极限,平均亩产量到达367市斤。然而和亩产量提高这一过程并行的却是单人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明代每个生产力年产粮4027市斤,到了清代,却下降到了2262市斤[4],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资源的增长,中国农业经济也就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在人均土地占有量与实际可耕种能力之间的差距之间隐含了劳动力的巨大剩余的实情。为缓解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的压力,土地经营出现了两个全新特征:一是农民已不可能追求经济效益,首要的是去安置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所谓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e involution)(注:"农业内卷化"是吉尔茨对爪哇水稻农作中生产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的一个特别名称。此概念用于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农业经营也同样适用。吉尔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e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Califomia Univ. Press,1963.))已然发生;二是中国农业陷入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5],大量的劳力投入虽将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这对农业生产中的新式投资、新的技术采用,却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新的投资与技术意味单位土地可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减少,而传统社会其它生产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人口,除了维护旧有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别无它途。由此可见,我门所见到的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它的增长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6]。
从另一方面看,农村的商业化程度在明清时期确有长足的发展。在中期帝国时代,国家放弃了直接管理市场事务的企图,宋代以后,国家简化了对经济管理,宁愿放弃直接控制,而改由其它办法去影响日益持之于私人之手的经济。明清之际,全国性、地区性的市场网络初具规模,大批新兴市镇涌现,农村基层市场蓬勃发育(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施坚雅的估计,到20世纪初,地方集市已有6.3万个。),这是由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所带动的。然而,我们不应对农民参与商品交换的程度及其后果作出过高的估计。小农家庭卷入市场经济运作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必然,市场以其有效的调节功能--时间上的季节调节、空间上的地区调节、品种上的有无调节,成为小农家庭再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和外部依存条件。参与商品交换的目的才是考察经济行为本质的关键,在传统中国,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的,甚至当农户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卷入市场与货币关系之中并为商业资本生产剩余品时,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仍不过是一个使用价值生产者的行为。这是其消费利益所赋予的特征,并就其整体而言,其生产耗费与保障家庭人口的生存相适应。所以它并不具备现代经济的含义。
经济作物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也不尽如此,中国经济作物发展是与劳动生产率的衰落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作物与封建政权强有力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经济作物适于集约经营,具有在较小的面积内创造出较大经济价值的特点。随着人均占地的减少,农民可以借此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产出,以缓解人口压力。但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权国家对这部分收入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于是推出一系列赏罚、限定和辅助措施给予保证。这种政治因素的干预,自是有助于经济作物的推广、农业基础的扩大;另一方面,它也造成推广和扩大的脆弱性。所以前近代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并不太快。在清代,经济作物大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而90%左右仍旧用于粮食生产。[7]经济作物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农户自身消费或用于交纳沉重赋税,提供给市场的只占一小部分,出口更是有限,而且也不能获得合理的价格。自乾隆以来,粮食价格上升较快,经济作物的利益反而下降了。
而农家从事手工业生产,首先也是为了自身消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身消费从一开始就与纳税完租,换钱易票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和租赋双重压迫使千万个农户投入这个营生。在手工业发展的背后存在的是一个灰色的事实:土地和粮食收入当时已不能维持农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农民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在生活和重赋高压下的男耕女织,一方面必须求助于织机,一方面又始终抓住土地不放,耕织结合不过是求得生存的最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增加投资、积累个人财富,实无从谈起,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生产方式受到严重限制是不言而喻的。依靠手工业来取得农业剩余是不可能的。
综上可知,所谓的农村商业化完全不是在农副产品充分剩余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可以在对前近代中国农民的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储蓄的估算中得到进一步证实。黄庆春的研究成功显示:鸦片战争前后,江浙地区农户的收入主要包括耕织两方面。首先是粮食收入,中等农户一年产粮2.2石(米1.5石,小麦0.75石,相当于1941公斤),可折合银26.0两;其次是纺织收入,一年大约织布18匹左右,折合银6.0两;每户农家一年中直接消费部分包括地租、口粮、穿衣和生产性支出,合计约银29.85两。进入市场的部分,主要是农户所织棉布除去自用后的剩余部分约15匹,合银4.5两。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农民家庭平均银32两的总收入中直接消费(29.85两)和进入市场部分(4.5两)相差悬殊;也就是说,农户农产品的90%以上都不经过市场而直接消费或转为实物地租,商品率仅为14%,剩余值为2.15两,表明储蓄率约为6.7%,这是颇为微弱的。[8]而且这部分剩余往往在农户婚嫁、殡丧等非经常性支出中消耗殆尽。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江浙地区在当时是农业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农村商业化的发展是在糊口农业的条件下进行的,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此微弱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是无法冲破凝结了两千多年封建自然经济,而建构起新的商品经济结构。言及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为依据论证中国近代化自生的可能性,条件其实并不充足。
三
第二个命题则显得更为复杂,它涉及政府能力与角色的问题,在"农业剩余"转化为社会积累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便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完成近代突破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将此普遍逻辑当作解释中国的底线时,如同美国学者琼斯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注:E.琼斯:《增长再现: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变化》(Growth Recurring: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在这里,琼斯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则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社会进步起否决作用。另见霍尔·约翰《权力和自由:西方兴起的原因和后果》(Power and Liberit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Lodon; Basil Black well 1985.));然而,琼斯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过于强大,以致于对社会进步起否决作用。这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揭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集权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为提取足以维持统治的资源,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队伍。在此前提下,广大农村的稳定安全是第一要义,集权国家因而全然没有现时代的经济观念。"政府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另:萦林格(Solinger)的研究表明,明清官员十分担忧农业产量的不够,并觉得如果人人都去经商赚钱,就没有人愿留下来种田。参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商业》(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mial Press.P.273。)另一方面,由于维护集权国家统治所需要的资源数量超过传统农业的承受限度,"一般来说,在农业经济的条件下维持统治,周期性地损耗的社会经济资源"[9],农业剩余总是十分有限的。当为了应付接踵而至的内外部挑战时,集权国家尝试更深地介入农村社会以便于从农业中提取更多剩余,促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受制于旧有的社会结构形式和行政控制能力的缺乏,这种努力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
对此题域的分析,应当着力于双重命题:其一,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中是否已然隐含了近代经济突破所必需的政府能力并不具备的实情;其二,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在清代以何种制度形式凸显,而这些制度对中国其后的近代化尝试发生怎样的影响。前者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化遭遇的可能困难;后者表现得更为具体,它参与塑造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面相。
我们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需强调集权国家的资源集中方式。中国集权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注:中国社会的许多特殊性实际上可归于一点,即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拥有一个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官僚体系,我们将此称为国家的早熟现象。),与集权国家相伴随的是不成熟和组织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这些都决定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必须采取政治而非经济手段。这种情况从中国原始国家的产生伊始便是如此。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地主-佃户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旨在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并使之转化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文明形态。"[10]然而,这种统治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政治技术的产物,"其资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11]
传统农业可能积累的剩余资源是有限的,这与集权国家所要求的程度相去甚远,"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12]上述的因素设定了中国传统国家与乡村的一般关系和王朝循环的普遍逻辑。由于可用资源的缺乏,传统中国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程度,根本不能同现代意义的集权国家相比,"虽然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制,但是它充分允许了地方社区的自主性。"[13]魏特夫在强调东方国家的集权特征的同时,运用普遍性的行政递减原则,认为中国集权国家的管理程度已经超过了效益的最高值,只能实现所谓的"部分管理"[14-p105-110]。集权国家政权的触角只伸及县一级,以此来减少中央政府的行政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资源压力。这样,传统中国就形成了集权国家及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乡村社会的相对自治共存的局面,国家依靠官僚队伍同广大的乡村社会打交道。
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的这种形构对中国历史展示的王朝循环的特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自始至终面临着可用资源不足的窘境,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国家不可能开辟集中资源的新途径,只能完全依靠农业剩余。因此"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15]而政府一旦尝试扩大自身的能力,以改善资源不足的局面,就会遇上两个巨大的障碍:首先,在儒家正统的统治意识支配下,国家应当崇尚轻徭薄赋,不该过分地触动乡村社会原有的自在结构,这是政权合法性在民间获得意识形态上支持的必要前提;其次,中国集权国家的早熟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国家机构的规模,致使有效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与行政技术的粗疏性之间存在极大的落差,试图改进行政的技术能力以获取更多资源,官僚机构的扩张,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支持,这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矛盾。因此,任何王朝最初的统治理念往往倾向于对农业剩余作适量的提取,小自耕农队伍的维护再生对政权的维持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乡村社会持有独立的姿态完全是为国家所允许的。然而,这种国家与乡村社会处于良性共生的"间架性设计"(注:"间架性设计"是黄仁宇用以分析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意指集权国家在社会不成熟和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为维持一定程度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做法,即国家在社会不发展和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人为的臆造社会结构。详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却忽视了早熟的集权国家的另一层矛盾:国家总是通过官僚系统进行社会治理的,既然国家可从社会提取的资源有限,国家可分配给官员,尤其是下级官吏(此处需注意的是,与乡村社会打交道的总是这一批人)的官俸就很少,它不足以满足官吏及其幕僚过体面生活所需。集权国家在资源上的窘迫,是官僚政治走向消极一端的重要原因,制度性的官僚腐败成为国家经久不愈的痼疾。(注:费正清提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变态现象之一,就是俸禄微薄所引发的官员制度性腐败。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同上,第91页。)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一旦上任,就立即学会如何区别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美好理想和谨严的行政现实了"。[14-p109]集权型体制和不完备的技术手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使得政府所设定的体制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行条件之间,存在一种很明显的偏差。这样,尽管集权国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相当高,几乎没有其他社会力量可以有实质意义地介入这个过程,但在政策实际运作中表现为变通方式普遍运用,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变通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与原政策目标看似一致,但变通后的实际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很可能与原目标背道而驰或互不相关。这种变通在很多时侯被中央政府所默许,它在一定的时期可以缓解早熟集权国家资源不足的问题,怛其最终的结果,却彻底破坏了国家--社会的均衡关系,而导致王朝的更迭。我们简要地归纳中国历史上各朝统治瓦解的经验,大抵都遵循以下的相对一致的路径:当新朝初建,百废待兴之际,国家一般对土地资源作新的分配并附以轻徭薄赋的政策,在减少资源提取的前提下使社会资源和国家力量形成良性的循环。及至中世,相对有效的管理造成的暂时繁荣引发官僚机构和王室的骄奢淫逸,这造成资源的巨大缺口,国家往往加大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小自耕农队伍日益削弱,土地兼并集中日趋严重,农村经济日渐凋敝,资源提取日愈不足。为维持自身的利益,官员依靠多种变通手法进一步压榨农村剩余,国家--社会的良性关系被摧毁。在末世,农业剩余被挤压殆尽,民不聊生,革命骤起,王朝土崩瓦解。这般的王朝循环的景观如梦魇一般缠绕在中国早熟集权国家的历史之中。
四
言至清代,上述的问题一样彰显。我们仍以集权国家资源提取入手加以分析,前清在制度的层面,与资源提取最相关的当属它的财政体制,所以这里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清朝政府对田赋地丁的处理方面。影响清代赋税政策的统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朝统治者关于赋税的政策目标的认识,一是统治者关于多种赋税关系处理原则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直接影响着清朝政府赋税制度的内容和政策调整的方向。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对满清贵族来说,建立完善的赋税征收体制和掌握熟练的理财本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式,最迫切的需要是保证税收,而保证税收最为稳妥的政策是尊重万历年间各地的田赋原额。顺治年间清政权致力于赋税征收的秩序化,但面对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朝政府财政不平衡的情况十分严重。战争形势下的财政缺口,突出地反映在各地官将上疏中所反复陈述的欠饷问题上,例如福建巡抚徐永祯论及福建存在的严重欠饷问题时称,自顺治十二年起至十七年止,奉拨各省未协拨的欠饷达1491453两,"有一分之钱粮即有一分之需用,缺一分之解额,即缺一分之供需。实缘外解不前,以致将节年起解内帑钱粮用过。"[16]为解决这一难题,清政权改变顺治元年免除三饷加派的决定,并用预征田赋的措施,清初的赋税征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经济的特征,这里值得充分关注的是,类似的措施在晚清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时,亦得到采用,其影响在后文详述。及至康熙,整个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在赋税方面,从发展生产培植税源,减少开支以惜国用出发,形成了以满足国用为目标的不加赋思想,概而言之,它表现为国用已足,钱粮蠲免。自康熙元年直至四四年,共蠲免钱粮9000万两,[17]相当于这44年正项钱粮总额的1/12,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则达6221万两,相当于这15年间正项钱粮收入的近1/6。[18]康熙的宽仁之政,导致了其后期官吏贪污风气的泛滥,雍正帝即位时面临的是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局面。雍正通过解决官侵吏蚀,加强赋税征收管理来保证国库的充裕,在赋税征收额度上,仍继承康熙时期的原额。雍正二年的摊丁入亩的改革,使清朝赋税制度趋于完备,它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影响而言,是把赋税额度固定下来。此期另一重要改革是在财政上实行耗羡(注:"耗羡"制度是集权国家为解决资源不足而采取的重要的措施,它旨在解决地方各级政权公私之用不敷之处的经费问题,事实上是一种加赋行为,使耗羡成为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重要财力。在吏治混乱时期,地方官员往往借此额外盘剥农民。雍正尚能正视这一问题,将它与钱粮正项相区别,他指出:"若将耗羡银两,俱比照正项具题报销,相沿已久,或有不肖官员指耗羡为正项。而于耗羡之外,又事苛求,以致贻累小民。此风断不可长",见《清世宗实录》,卷43。)归公的措施,其实意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随意加额征收,免除对农业剩余的过分收取。摊丁入亩的措施意味着,要取得赋税征收额度的增加,在不改变赋税科则的情况下,惟有赖于土地亩数的增加,在雍正厉行垦荒政策下,地方官为了追求垦荒成绩虚报田亩,使田土数加大,进而导致赋税的增加。这种做法必然地加重农民的负担。乾隆帝杜绝了因提倡开垦谎报地亩形成加赋的现象,在政策上以稳定地亩数为基础。当然,随着实际垦辟的扩大,出现新增田亩,这自然会使得赋税相应增加,这是合理的加增。新增部分地亩是否可以加派丁银呢?乾隆帝从人口增加和土地有限之间存在的矛盾出发,决定不以新垦民屯地亩上随年摊纳丁银。至此,清朝乾隆政府从地和丁两方面所制定的相应政策,使得清朝不加赋税收格局基本形成,一直到鸦片战争,固定的税率加上长期以来几乎固定化的土地数额,使清代的土地税收甚至政府的收入几乎成为固定不变的,定额化赋税征收体现了清王朝统治理念中的一般原则。但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如果以土地的价值或收入来估定税额,土地税将会随着土地价值或生产力的升降而增减,税额的调整便可跟上经济的变化;恒是清代土地税的征收既然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并采用级差税率体系,它除非提高税率,否则当通货膨胀和土地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时候(这在清代是最突出的经济现象),税收是不会增加的,在相反的情况下,它也不会减轻。为了配合不具备伸缩性的土地税政策,财政管理体制的呆板也是显见的。清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所确立的范围是由财政经制(注:所谓"经制",是指国家每年正常的财政收支都有相对固定的额度,并由《会典》、《则例》等法典式文献予以规定。)来体现的,是所谓"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19]。政府的各类开支均由法规详加规定,开支项目和特定的款额一经规定,历数百年而无变动。这是一种静止性的预算,但其结果却可能是对最基本的开支都不复维持。事实上,这种经制所限定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额度,并未完全为中央和地方各项事务的经常性用度提供充足财力保证。中央和地方许多行政事务的经常性开支都被排除在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之外,这种未列入财政支出的部分在实际开支中,只能谋求财政外的其他途径来解决。这种不因事设费、存在支出缺口的财政,我们称之谓不完全财政。不完全财政对清朝政府的行政来说,造成这方面的后果。首先,由于薪俸低微,地方公费缺乏和军事供给不足等财政缺口的存在,地方官将为了完成职守应付多方面而谋求更大非法的经费筹措途径,对中央政府法律条规形成冲击。由于有效正当的理由,他们的私自征取对中央形成倒逼之势,使清廷在政策执行和管理上被迫放松。其次,由于地方官将自行加派征收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地丁的额赋税的征足和完纳,造成清廷赋税征收的失控。再次,由于薪俸有限,促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外苛索,非法的提取农业剩余形成惯例,它将进一步破坏国家--社会的均衡关系。概而言之,在清代的不完全财政体制中可发现集权国家王朝循环的根本症状,按照既往的历史逻辑,清王朝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等待的是一个新朝的诞生。
上述的分析表明,把农民的温饱与帝国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政治逻辑,在王朝循环的历史中一向很明确。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作,维持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精致而微妙的平衡。即使两者之间发生不可抵抗的冲突,通常也是用改朝换代的形式予以化解,它阻碍着社会结构的全面革新的发生可能。因此,传统中国的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样式与现代要求之间有着本质的断裂,如此羸弱的政府能力,根本无法有效地汲取"农业剩余",并将此转化为现代化启动的必要动力,因为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20]。
在农本社会中,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率的增长才能使工商业的发展、政治形态和科学文化发达成为可能,近代社会的产生无非是这种剩余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发生质变时才出现的。前面的分析表明,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并不是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的,在这种生产状况下,农业剩余也不可能大量涌现。所以,一些学者(例如王国斌)尽管对此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乐观评价,但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类增长不过是"斯密型动力"(注:"斯密型动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明,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由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类经济扩张的动力,受制于人口的节奏和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王国斌借此概念系统地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前近代时期的经济状况,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详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方面,受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影响,以及清政府为解决上述问题而采用的政策,所导致的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的制约,中国农业部门无法承担起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本就不充裕的资源被进一步掠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无法获得足够的动力,而对于这一点,本文不作遑论。既无充分的农业剩余,又无强大的政府能力,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已然证明。
[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135
[2]菲雷.法国革命阐释.Franc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Maison des Sciences de I'Homme and the Cambridge Unic. Press(Cambridge 1981).PP.8-9.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1986,164-166.
[4]许纪霖、陈凯达.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1页.
[5]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M].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6]亚当·斯密.国富论[M].(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Random House. 1937.PP.137.
[7]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人民出版社1995.第一卷.214.
[8]马克圭编.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学林出版社1997.120-123.
[9]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82.
[1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商务印书馆1987.142.
[1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1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华夏出版社.1987.135.
[13]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7.176.
[14]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M].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5-110.
[1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47.
[16]车克等户部残题本.明清史料.已编下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199.
[17]清圣祖实录[M]卷223.
[18]曹月堂.谈康熙钱朝的钱粮蠲免[J].南开史学.1982.第1期.
[19]程含章.岭南集.《论理财书》[A].清经世文编.上册.650.
[20]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