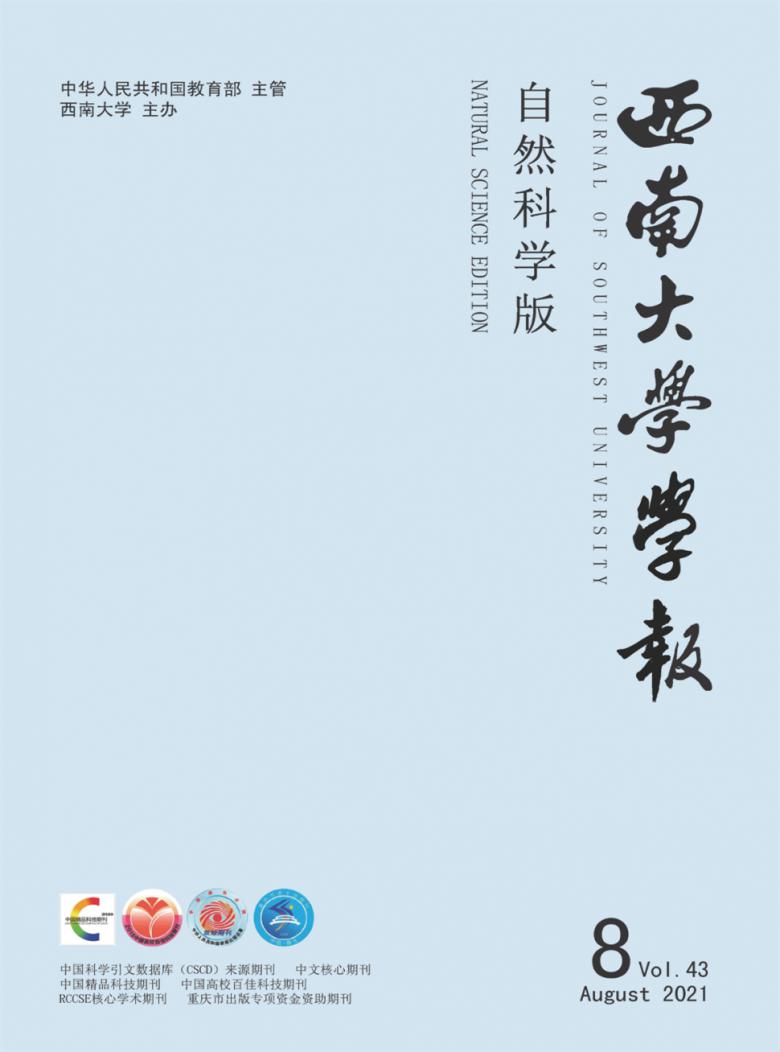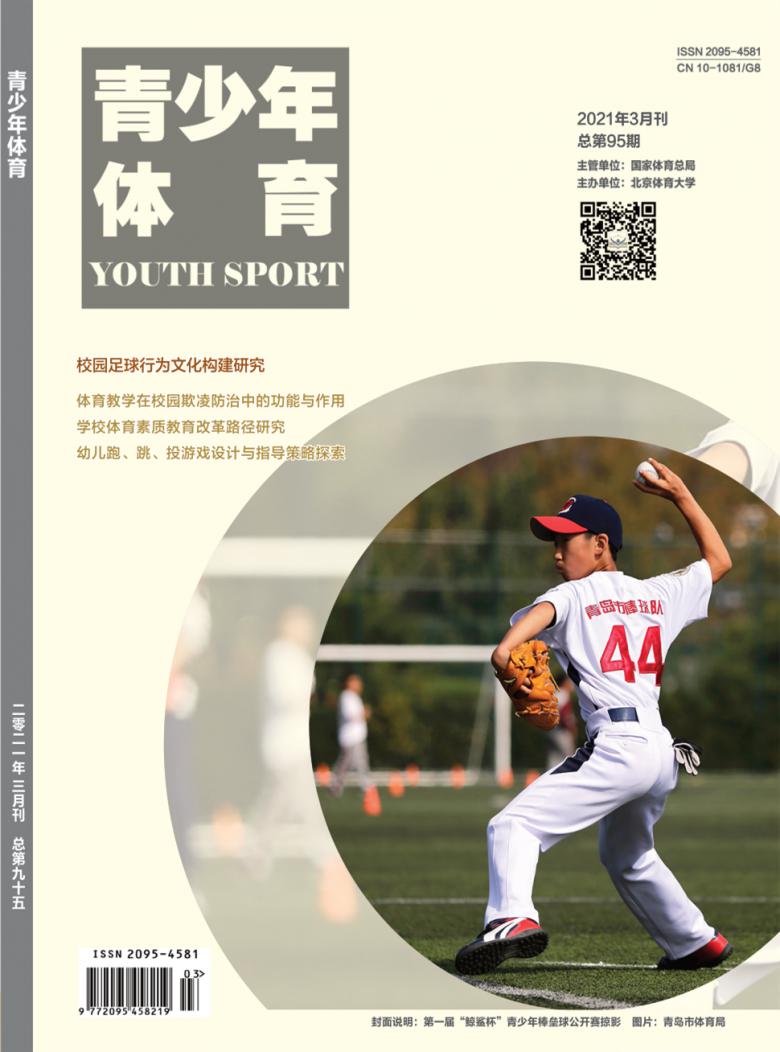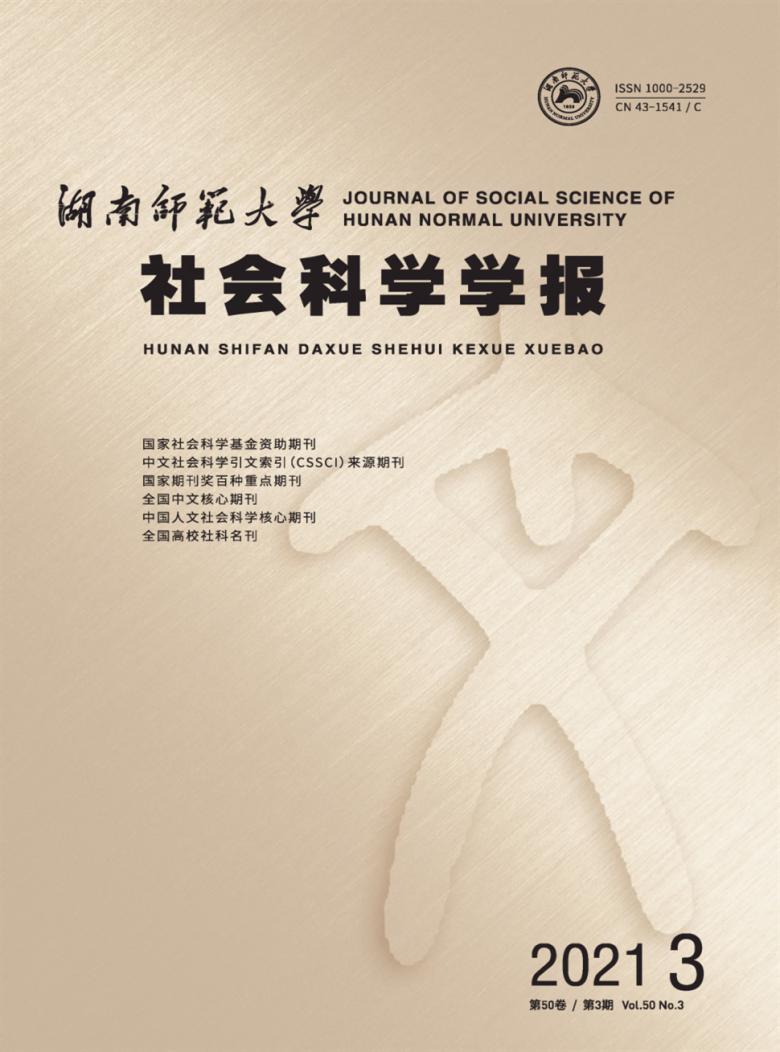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姜 铎 2006-04-26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第七届会议于1994年12月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包括台湾省的国内学者70多人到会,另有韩国和日本学者,故称之为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提交论文共50余篇。第八届会议预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我们几个和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人,在长春会议上曾达成下列默契:不成立正式研究组织,在每次会后,酝酿下届会议的主持人,大体上两年开一次。16年来便是这样过来的。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个刊物,既是洋务运动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两刊的编辑部又是洋务运动研究的促进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除以上正式会议以外,还就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人物、单位和事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例如左宗棠的研讨会便开了两次,1984年在苏州大学,1985年在长沙。1988年10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1994年11月,江苏省政协和常州市政协,在常州召开了盛宣怀150周年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曾国藩家乡,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关于丁日昌和刘铭传也分别召开了研讨会,刘铭传的研讨会开了两次,1995年11月的刘铭传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1995年江南造船厂庆祝建厂130周年时,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近代工业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1984年和1995年在山东威海连续举行两次中日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都很盛大,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像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专题,能够如此经久不衰、持续地召开那么多的学术研讨会,把它称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张吧。
最后说新成果。据粗略估算,这16年中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在1000篇以上,专著和资料近50部,堪称硕果累累。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专著和资料的出版情况。综合性的洋务运动专著共有3部。第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因成书较早,该书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全面否定论。第二种是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该书的指导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论。第三部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作者自称的“发展论”。三部综合性专著的共同特点是以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为中心,加以系统详尽的论述,张著只限于这一范围,后二者则兼及国防、教育等洋务运动的全面措施。这三部专著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另外,杜为德、林庆元、郭金彬合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介乎专著与专题之间的著作。关于洋务企业的专著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铎主编的《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有关企业史的专著,大都汇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洋务企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洋务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专著,更是五彩缤纷,主要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芦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董守义的《恭亲王奕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宝成关的《奕欣慈禧政争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徐彻的《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仅就甲午战争而言,戚其章陆续出版了《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还有几部翻译出版的外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的著作,例如陈绛译校,美国刘广京、朱昌峻合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下两册,近200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1000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500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共30册,约1500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2000万言的皇皇巨著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5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
(四)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给曾国藩扣上“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五)台湾地区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台湾地区史学界尚无专人从事洋务运动研究,亦未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但一些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玉法、吕实强等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洋务运动称之为“自强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洋务派主要人物奕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同样是基本肯定的。在发表的文章和会议研讨中,并未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一点与大陆学者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只举行了两次,一次是1987年8月召开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另一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兹将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个研讨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会期8月21—23日,出席中外学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学者近20人,令人遗憾的是大陆学者未被邀请。提交的论文共34篇,内容包括洋务与内政、西法与传统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层面,以及中外的研究与比较。举行了12次全体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上下两册论文集。
论文和研讨的内容要点是: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很高。“清季自强运动起于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讫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历时三十余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不仅是国人谋求对所谓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所作有效因应求自强的开始,也是百余年来中国进行现代化所作种种努力的起步。”(吴大猷开幕词)。“我们应该说:自强运动是很成功,但又是失败了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是主要的事实……从清中叶(或从十九世纪早期)的观点看来,自强运动是很成功的……自强运动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长远的影响”(刘广京:《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人我认为是相当消极的,只要能维持国家的生存就够了,满清政府不灭亡,中国能够存下去,这个就是自强运动的目标。我想,如果降低到这个层次,自强运动是成功的。中国没有灭亡,满清政府灭亡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就会肯定当时的努力,当时的建设,当时的奋斗。”(会议主席张玉法的总结发言)
第二,对曾国藩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兴办团练,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终能荡平发捻,芟刈大难,成为清代中兴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进,文武兼资,无论学问修养,治道军谋,伦理德业,皆是为天下法……曾氏亟谋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图因应,故不仅为传统的经世学者,而倡导自强运动,尤不遗余力,诚承先启后之人物。其领袖群伦,图新求变,殆无可置疑焉。”(王韦均:《从日记书信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和自强思想》)。“曾国藩的丰功伟业,道德学问,久为当时与后世之人所肯定。”(吕实强:《曾国藩的中庸之道》)
第三,对大陆洋务运动研究作了详尽的评价,但其中不免有误解和偏见。吴安家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长文,内容很详尽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议论并有独创之处,特别对近年来论争的评介尤为深透,但亦有误解的地方。吴先生在大量引用黄逸峰和笔者两点论观点以后,作出了下述结论性的批评:“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姜铎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认为洋务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后来却说它是反动和卖国。笔者怀疑这些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极左观点作为讨论的依据。从后来中共期刊和报纸上刊登出的文章可以看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提及他们两人的观点。严格说来,姜铎和黄逸峰两人的观点,只是范文澜和胡绳等人的看法的延续和发展。由于这些意见仍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框框影响下的产物,反对者众。反对者认为这个运动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卖国。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驳姜铎等人的看法。”他的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如说我们的观点是范、胡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后不一致等等。但偏见太深,不了解大陆论争的内情和我所坚持的两点论的本义,特别是无端怀疑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就未免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了。还是评论者吕实强先生说得对:“所以我认为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头,也应该稍微把他们这种隐含的内心状态提出来,而不使大陆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良心道德全然为我们所忽略。”
第四,“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下面是吕实强先生在评论上述吴安家文章中说的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毛泽东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①g]
在上述回顾以后,我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全文的结束。首先,希望预定的天津第八届洋务运动研讨会,能如期顺利召开。原有的倡导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编辑部,就近加以大力协助。其次,筹建一个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再次,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用适当的方式,同台湾学者协商,两岸互推几位熟悉洋务自强运动的学者,举行平心静气的交流座谈,力求能达成一个初步共识。最后,建议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我愿意捐资万元,作为提倡。竭诚希望研究洋务运动的同仁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社会各界热心资助学术研究的人士,广为劝募,以便积少成多,为今后洋务运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a 这段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b 上述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及《饮冰室合集》等书。
①c 此段引文均摘自《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c 《清史稿》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c 《清史稿》卷一九八。
④c 《清史稿》卷一九九。
①d 这段关于瞿秋白的引文转引自杨劲华《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d③d 《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5—36、59页。
①e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4月版,第648—649页。
②e 《清代通史》,第826页。
①f 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31—35页。
②f 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①g 以上有关引文均据《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