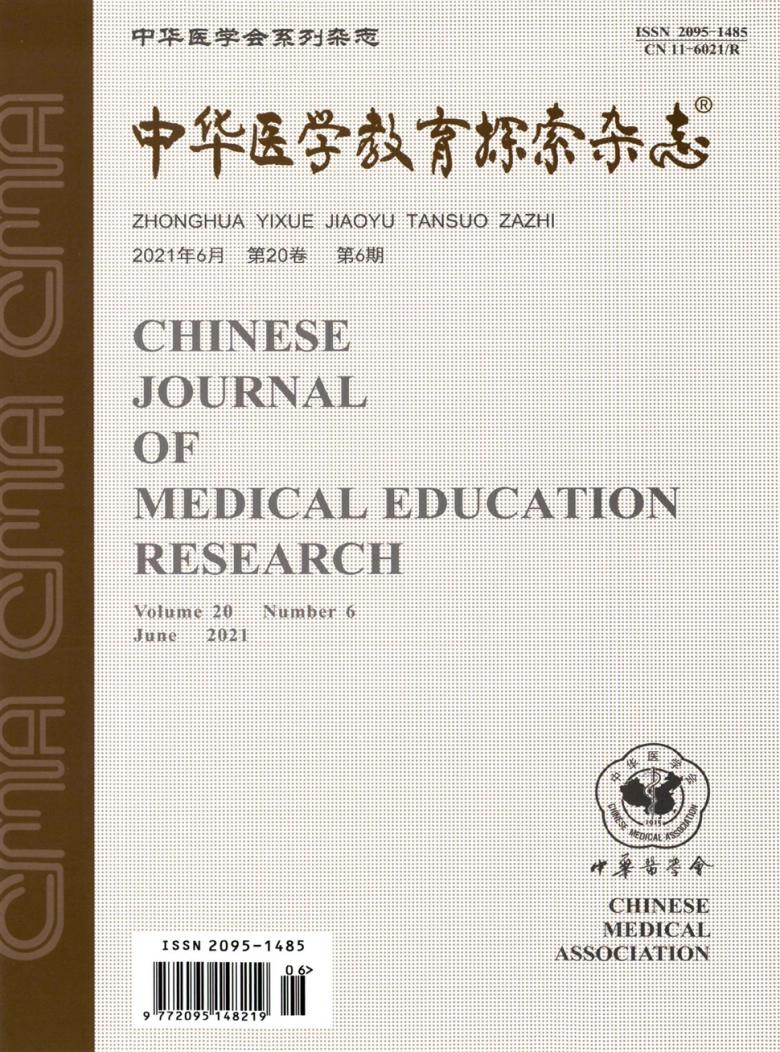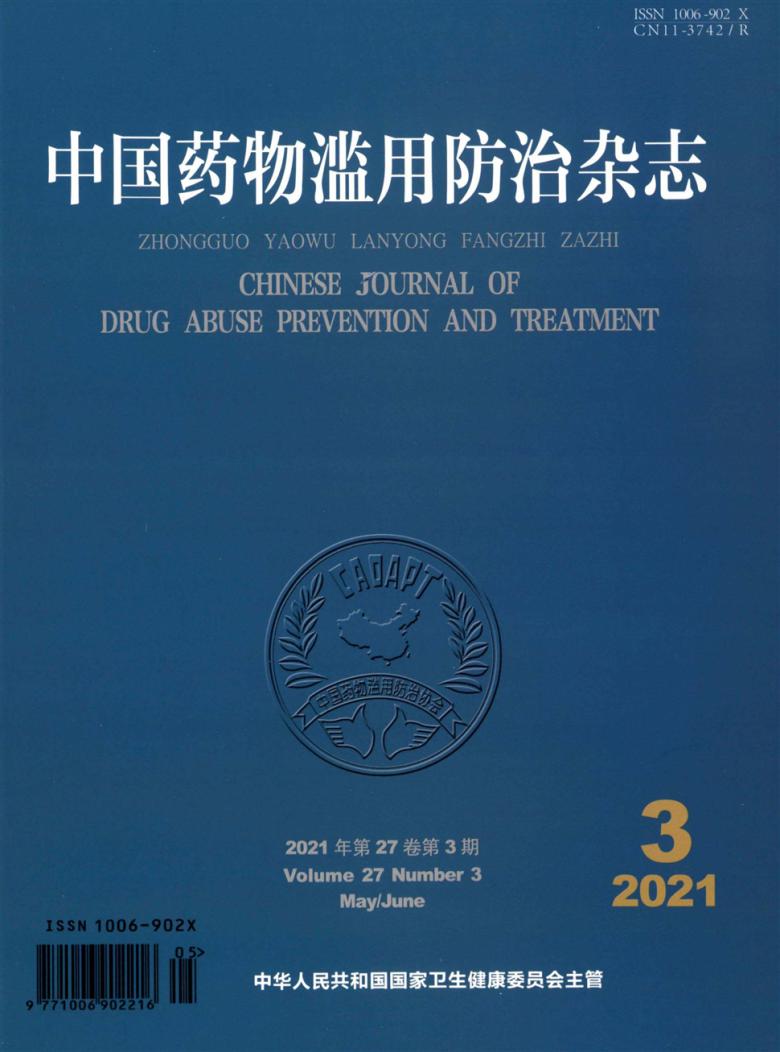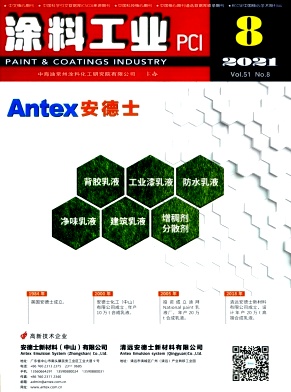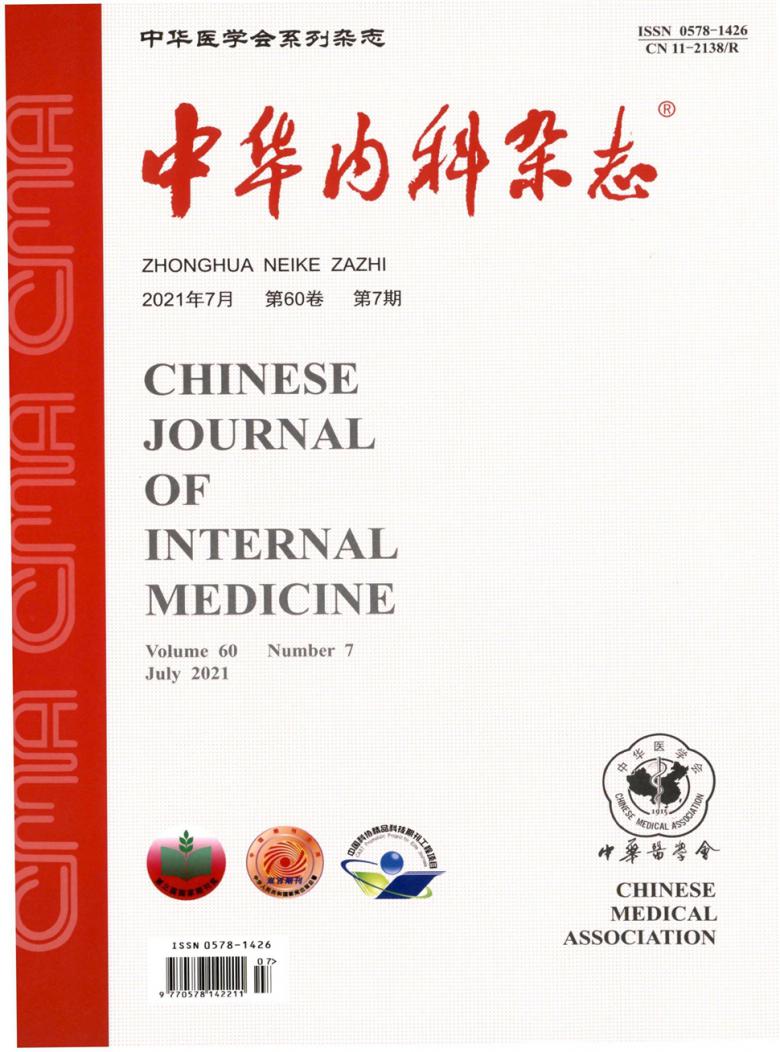华夏民族“是非”价值观念是何以可能的?——汉语原初“是”的语义结构分析
肖娅曼 黄玉顺 2006-04-05
语言学界通常认为,汉语“是”出现之初就是一个纯粹的指代词,可是却很少注意:“是”为什么能与其它指代词长期并存?为什么后来是“是”而不是别的指代词发展为系词?它为什么同时又发展为“是非”观念?
以当代哲学的观点看,作为科学建构前提的知识论和作为道德建构前提的价值论,都奠基于作为纯粹哲学存在论的形而上学[1];但形而上学本身,却又奠基于更源始的前哲学的观念。就西方哲学来看,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亚里士多德语)问题,或者说关于“是”(古希腊语einai;英语to be)或者“存在”(德语Sein)的问题。例如海德格尔(M. Heiddeger)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建立始于古希腊雅典哲学,那时人们开始遗忘了“存在”(Sein)本身或“是”(ist)本身,即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das Seiende),并专注于这样的存在者,将它对象化、专题化。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西方的知识论及科学建构、价值论及道德建构。然而此后人们虽然遗忘了存在,但存在或“是”本身始终是一切观念的真正源始的基础。那么,“是”在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就哲学界的情况来看,人们对西语to be的研究近年来颇为热烈,但对汉语“是”却谈不上研究;再就语言学界来看,对“是”的研究也不过几十年,而且仅限于语法学方面,然而据我们的研究,对汉语原初“是”的揭示关键在语义的揭示。我们曾指出:汉语“是”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之间的关联同样是本质性的;原初的“是”类似于古希腊语einai 。[1] 显而易见,对汉语原初“是”的研究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没有哲学的参与,语言学很难关注到“是”的语义问题 [2] 及其观念奠基性;而如果没有语言学的参与,哲学很难发现汉语“是”与西语to be之间的本然的对应性。
本文意在从中国的价值论观念方面切入,来探索这个问题:作为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的“是非”观念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属于形而上学建构的“是非”观念,与汉语原初“是”之间是什么关系?
早期汉语“是”是一个指代词,这在语言学界从来没有争议。例如在“惟命是从”这样的表达中,“是”作为指代词,复指其前置宾语“命”,“是从”即“从是”,即“从命”。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是”最初并不是“此”“斯”那样的一般性的指代词,而是神圣性的指代词;而且它一开始就隐含着系词性,后来才可能发展为系词。这里的“系词性”不等于“系词”;“是”最初不是系词,但有系词性。“是”后来之所以发展为系词,正是因为它原初具有的系词性。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它隐含的系词性乃是它的指代性的基础,因为正是这种系词性给出了所指代的事物的存在性、在场性。“是”的指代性乃是这种标示存在的系词性的存在者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一般存在论的最后“根据”。而“是”的指代神圣性也是这种存在者化的更进一步的结果,这样它才能成为价值论的最后“准则”。
汉语“是”成为形而上学价值论的基本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即是在属于中国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春秋战国时代,其经典表述是孟子的名言:“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2] 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是非”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们必须追溯到轴心时期之前的原初的“是”。但我们注意到,“是”字的出现较晚:“是”不见于甲骨文,最早的确凿材料见于西周早期金文。这似乎带来一个疑问:“是”真的算得上是我们的原初观念吗?对此,我们作出三点陈述:第一,“是”字最初写作它的同音字“时”,而“时”字的产生比“是”早得多(“时”甲骨文中就有,早期文献如《诗经》《尚书》等,“是”多作“时”),我们探索原初的“是”,理应包括探索原初的“时”。[3][3] 第二,即便就“是”而言,文字是滞后于实际语言的,“是”这个字晚于“是”这个词,这就是说,“是”这个词必定是产生于周代之前的。西方最早的完整古文献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已有einai用作系词。但是汉语原初“是”远比《伊利亚特》中的einai更为古老:从时代上看,《伊利亚特》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而汉语“是”或“时”字从公元前10世纪起就已经出现在西周金文和《易经》《尚书》《诗经》等古老文献中。第三,“是”或“时”之足以作为中国人原始的存在观念,因为它们产生的时代是在轴心时期(春秋战国)之前。
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形而上学是奠基于源始的本真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的;这样的“原始经验”,就存在于对“是”(存在)的领会之中。华夏民族亦然,原初的“是”(“时”)的用法正是我们祖先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后来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整个的传统观念,均基于此。汉语“是”(“时”)大致经历了下表所列的演变历程:
字词
语义
语法
层次
时代
时 / 是
存在
隐含系词性
源始生存领会
前轴心期
时 / 是
存在者
指代词
存在论
轴心时期
是
正确
形容词
价值论
是
判断
系词
语法标志
后轴心期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从语言学角度看,早期的“是”不过是一组指代词中的一个;但从哲学角度看,它却是殷周时代的根本观念的语言形式,如同古希腊语的einai 。应该说,西方的形而上学观念和中华的形而上学观念之间有相当的一致性。参照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即严格区分“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s)的思想,我们可以分析如下:源始的to be和原初的“是”都不是说的任何存在者,而是存在之为存在本身;唯其如此,它才能保证所有其它存在者的存在(在场性),而表现为判断。例如西语“Man is animal”、汉语“人是动物”这样的判断之所以能成立,首先是因为“Man is”或“人是(存在)”,即首先是因为“is”或“是”保证了“Man”或“人”这样的存在者的存在(在场性)。而“is”或“是”本身却不是任何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但是,当人们去思考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Grund)时,人们把“to be”或“是”思考为这样的终极根据,即思考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它保证了其它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它就是理念(柏拉图)、我思(笛卡儿),或道(道家)、性(儒家),等等。于是,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得以发生。但是前形而上学的“to be”或“是”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
汉语原初“是”与“时”的意义就是如此:虽然“是”与“时”均从“日”,但“是”与“时”显然不是在说天上那个作为自然物的太阳,因为那个太阳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者,人们因此可以问“太阳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此时,太阳的存在或在场性已经先行被给出——太阳因为“是(存在着)”,所以才能“是什么”。那么,太阳的存在是如何被先行给出的?正是由原初的“是”(“时”)给出的,其意义就是源始的生存之领会与解释,它更确切的表述就是更早出现的“时”,亦即华夏先民对其“生”(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的“时间性”(Zeitlichkeit)的领悟。“时”的原初意义是“四时”,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农耕生活的源始的生存境域。所有存在者“共在”于这个境域之中,而这个源始境域正是由“时”或“是”来表达的。此时之“日”还不是一个对象物,即还没有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者,然而似乎所有存在者的“共在”都由这个“日”照亮了;正是在这片光明中,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才得以敞现出来,它们也才成其为存在者。人们正是由此而感悟到时间性的“生”:这就是华夏先民的源始的生活感悟,即“生生之谓易”(《系辞传》)[4]。
但到了轴心时代,当华夏先民思考所有存在者之最后根据时,由于“时”“是”的时间性与“日”的天然关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日”理解为这样的终极存在者。“日”这样的终极存在者,其地位如创世的上帝。于是,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观念得以出现。例如在“日,则也”(详后)这个判断中,太阳就已经被理解为一个终极的存在者了。于是,不是存在本身给出了太阳的在场性,倒是太阳给出了所有存在者的在场性。太阳这个唯一存在者保证了其它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它便成为了最后的尺度。而在这个时候的文献中,“是”字也开始逐渐取代“时”字,意味着生存的时间性境域开始被遮蔽,作为终极存在者的“日”的神圣性开始被突显出来。
汉语“是”与西语“to be”的对应关系,可以由下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西语to be 包含的基本观念,是以不同的形态表示的;而汉语是孤立语,不是形态语,所以没有这样的形态变化。这就是说,汉语原初“是”所蕴涵的基本观念,都是以“是”或“时”不变的形态出现的,语法上出现于同一语法位置,语义上体现为同一义项的义素构成关系。而义素构成作为语义结构,只能通过语义分析来揭示。
转变
语种
存在
存在者化
存在本身
在场
终极存在者
存在者
印欧语
to be
(系词原形)
is / are / am
(系词形态)
Being
(动名词)
being(s)
(名词)
汉语
时
(系词性的指代)
时 / 是
(指代的系词性)
时 / 是
(神圣性指代)
是
(一般性指代)
表中揭示了:正是“时”或“是”所隐含的源始的系词性(不是系词,而是标示存在性的系词性)、亦即存在本身保证了存在者的在场性;而这种在场性的体现就是指代性,它指示着“此(这一个)”存在者的在场:早期“是”只指代神圣性的在场者,后来才逐渐可指代一般性的在场者。
现在我们具体看看“是”是如何指代神圣性的存在者的。“是”与“此”之类虽然都是指代词,然而“是”指示的存在者不是“此”之类指示的存在者;“是”所指示的存在者,是具有神圣性的在场者。换句话说,最初作为指代词的“是”,与“此”之类的其它指代词之间,存在着语义上的分工。这就是汉语原初“是”的语义与西语to be 的语义之间的重要差异:汉语的“是”观念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价值论特征。
指代词一般的特征是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由它所指代的对象赋予,因此指代词本身是无所谓褒贬或神圣的。但是,“是”却非常不同,它有特定的指代对象,这种特定的指代对象决定于它的语义结构。
首先,原初“是”不指代价值论意义上的否定者。西周春秋金文中无一例“是”指代否定者,却有“之”指代否定者,例如:“勿有不義訅之於不啻。”(者氵刀鍾)[5][4];《诗经》的《颂》中共有“是”39例,也无一例指代否定者,而其三例“此”中,就有一例指代否定者,如:“顺彼长道,屈此群丑。”[6](《鲁颂·泮水》)。《大雅》中“此”指代否定者的例子更多,例如: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诗·大雅·桑柔》)
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大雅·桑柔》)
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大雅·瞻卬》)
其它指代词也都可以指代否定性事物,例如:“蠢兹有苗,昏迷不恭。”[7](大禹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大雅·抑》)
其次,“是”只指代神圣者。西周春秋金文中,指代词“之”出现率很高,用它同“是”作对比,能清楚看出二者的差异。青铜器铭文无论长短,总有一句话总括铸器意愿,如祭祖祈福、勉励告戒等,“是”“之”往往出现于此。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是”“之”都是指代词,作受事宾语,只是“是”处于动词前,构成O+V 结构;“之”处于动词后,构成V+O结构。[5]《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8]、《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9]、《殷周金文集錄》[10] 所收集的西周春秋金文中,“是”共出现26次,其中“是”“之”句式相对的分别为:“是”19次、“之”58次。下面据“是”“之”前后词语的类型进行分类。由于再现金文的字型在技术上很困难,材料的文字将据上述三部金文研究著作释文的简体录出,括符内为同类形式出现次数:[6]
永保是尚。(3) 永保用之。(24)
永宝是尚。(1) 永宝用之。(10)
子孙是若。(2) 永寿用之。(5)
永保是从。(2) 永用之享。(1)
天命是匡。(1) 子孙用之。(1)
民俱是嚮。(1) 永用之。 (4)
是用寿考。(1) 永保鼓之。(6)
是用左王。(1) 秦 为之。(5)
先人是言五。(2) 永保之。 (2)
万世是宝。(1)
邾邦是保。(1)
分器是寺。(1)[7]
子孙是利。(2)
西方功能语法学派提出的“搭配”(collocation)理论指出,常常搭配使用的词语之间,意义密切相关。根据这一理论考察“是”和“之”所搭配的动词,会发现它们各自搭配的动词很不相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指代的对象不同。58个“之”,只与用、鼓、为、保4个动词搭配,4个动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使用之词(用、鼓、为),与它们搭配的“之”共56个,占96.55%;第二类为保持之词(保),与它们搭配的“之”共2个,占3.45%。从搭配的动词看,“之”被当作使用对象,即“之”指代的是青铜器这一物品。然而19个“是”,搭配的动词有11个:尚、若、从、匡、嚮、利、宝、保、寺、用、语。这些动词也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虔敬、祈福之词(尚、若、从、匡、嚮、用、利、语)[8],与它们搭配的“是”共16个,占84.21%;第二类为保有之词(宝、保、寺),与它们搭配的“是”共3个,占15.79%。从这种搭配关系不难看出,“是”虽然也指代被铸造的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却不是作为器物拿来用的,而是作为神明、祖先的化身,能荫庇铸器者和后世子孙的神器,因而,这19例“是”的指代对象都具有神性,即都包含“日”内涵。对西周春秋金文所有“是”“之”的考察与前面考察结果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出现时专用于指代神圣者。
不仅金文是这样,原初所有的“是”都一致表现出其指代的专用性——专用于祭神颂祖,即指代的都是神或合神意者。《诗经》的《颂》《大雅》所有“O是V”式中的“是”,指代的都是虔敬尊崇的对象——神灵、神物、天时。[9] 神灵包括天神、国君(在上古观念中,国君与天神有血亲关系);神物包括宗庙、祭品、供品和帝王的赏赐物;天时包括自然现象时节和时运等。以下材料按时代先后顺序列出:[10]
指代神灵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诗经·周颂·执竞》)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诗经·周颂·有瞽》)
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经·商颂·长发》)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诗经·鲁颂·閟宫》)
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诗经·鲁颂·閟宫》)
指代神物
杀时犉牡,有捄其角。(《诗经·周颂·良耜》)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诗经·商颂·玄鸟》)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诗经·商颂·玄鸟》)
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诗经·商颂·长发》)
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诗经·商颂·长发》)
是断是迁,方斲是虔。(《诗经·商颂·殷武》)
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诗经·鲁颂·閟宫》)
指代时运
保彼东方,鲁邦是常。(《诗经·鲁颂·閟宫》)
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诗经·鲁颂·閟宫》)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诗经·周颂·赉》)[11]
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诗经·周颂·般》)[12]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
“是”(“时”)最初主要成类出现于“O是V”句式,这些“是”(“时”)都用于指代神圣者。上古“此”“兹”“斯”等指代词常处于主语位置,而“是”(“时”)处于主语位置的极其罕见,但在《诗经·大雅》中就有2例作主语的“时”,它们表面看来与其它指代词无异,实则不然: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6](《大雅·生民》)
关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郑玄笺:“时,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时维后稷”郑玄笺:“是为后稷”。两个“时”分别指代姜嫄和后稷。诗中写周族始祖姜嫄履上帝之迹生后稷,后稷承天意而生之后虽被弃,但“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13] 这两例“是”(“时”)看上去不过是起了指代词作主语的作用,别无深意。但对此稍微留心就可注意到:上古有“是”“此”“兹”“斯”“之”一组指代词,为什么诗中两次指代不同的人,都用了同一个指代词“是”(“时”)而不用别的指代词?我们注意到,这里“是”(“时”)指代的都是周之始祖,与神有关,或者说他们就是神。
总之,原初“是”只指代神圣者,或者说只指代“是”者,不指代“非”者:作主语、宾语时,都指代的虔敬尊颂者;作状语(代副词)时,都指代的神圣正义的行为活动;作定语时,也大多指示令人崇敬的神或合神意之事。这就是说,“神圣”为原初“是”的语义结构中的重要构分。下文我们将会看到,汉语“是”观念的价值论特性正是基于原初“是”的这种指代的神圣性。
早期“是”指代的范围都与神有关,这不正与《说文解字》的说法一致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根据字形来考察汉字本义之书。“是”,《说文》说“从日”,亦即在他看来,“是”最初的意义与“日”有重要关系。而与“日”有关则意味着与神有关:自然现象之“日”被神化,这是人类早期的普遍现象,“日者,太阳之精,至尊之物”[6][14]。所以,通神的筮术称为“日”,而通神的筮人称为“日者”:“日谓日者卜筮掌日之术也”[11][15];“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12][16]。但是上文已经指出,这个“日”已经被存在者化了,它已不是原初的“时”(“是”)的观念。过去语言学家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文献中找不到“是”与“日”直接联系的证据,原因在于:语言学家所理解的“日”首先是一个存在者,其次是“太阳”这一个存在者。而“是”原作“时”,并不是指的太阳“这一个”存在者,而是指的“四时”,即源始的生存境域;当“是”被存在者化以后,它才成为“太阳神”。它使所有存在者得以分别开来、彰显出来:“日之为言,节也,开度立节,使物咸别”[13][17];“日者,万物由之已煦,万象由之以显”[14][18]。这个“神”隐含于指代(存在者)中,并规定着指代的语义指向,即这个指代的实现隐含着一个判断。所以,当我们尝试用“此”“兹”“斯”“之”去替换《大雅·生民》中那两个“时”时,便发现它们是不能替换的。作为上古祭祀文体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诗经》的《雅》《颂》,都是专用于祭神颂祖的,在这些成书于西周或春秋早期、亦即中国的轴心时期的文献所用的语言中,无论指代神灵、祭祀的神器,还是指代时运,这些“是”(“时”)归根结底指代的都是作为终极存在者的“日”,而这些指代神圣者的“是”(时)都不能被其它指代词替换。不仅如此,在这些文献中,除“是”(“时”)外,没有其它作主语或宾语的指代词(如“此”“兹”“斯”)是与“日”、神圣者有关的,它们甚至很少在这些祭神颂祖的文献中出现。
只有这样的作为“日”的神圣至尊的“是”,才能充当价值论意义上的“准则”。上古“是”除《说文》之说外,还有《尔雅》之说:“是,则也。”《尔雅》以汉初语言解释周代语言,它去古未远,对“是”的注说是很好的根据。“则”即准则,是一个价值论概念。但是语言学家却怎么也不能在上古文献中发现“则”与“是”的直接联系。然而显然,《尔雅》的“则”就是对《说文》的“日”的更进一步的解说。周代的“则”为“常”和“法”之意,“常”和“法”即不变的规律、准则;而“日”因为其运行极有规律而成为这样的准则。其实这个形而上学观念的来源仍然是前形而上学的“是”即“时”:对华夏先民来说,没有什么比收获更重要的了,收获关系到部落邦国的生死存亡,而收获须据“日”而行,“日”成为“生民之道”[15][19] 的唯一准则,因此“日”就是“则”。然而准则之为尺度,进而尺度之为尺度,首先因为它也是一个物、即一个存在者。准则作为度量标准,不过是用来度量一个物的另一个物。就价值论来说,被度量物的正当性来自于度量物的正当性;而这个度量物本身的正当性,则来自它的神圣性。
以“日”为“则”,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包含着判断义素,因为指代是否合乎“日”这一准则,必定要经过判断。而判断性就表现为系词性,这就意味着,“是”的价值论性质同样是基于其源始的系词性的。但是,这个判断义素如同“日”义素一样,最初也隐含在指代词“是”中,并未占据语法上的判断词位置,因此难以被发现。正因为“是”的判断义素的隐蔽性,大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为了解释“是”为什么竟然由指代词变成了判断词的原因而伤透了脑筋。
源自原始系词性的判断性、后来神圣性的指代性,这两者是“是”充当作为价值论范畴的“是非”观念的基础:前者保证了“是非”乃是判断,而后者则保证了“是非”乃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
西语to be 也表示肯定判断,不过这种肯定仅仅是一种存在性肯定,并无价值论的意味。也就是说,to be的源头古希腊语einai,即使是陈述邪恶者,也同样用einai。而我们已经看到,汉语早期“是”不用于价值否定性事物。由于“是”的这种肯定性植根于原初义,因而根深蒂固,当它出现约一千年后、已经发展为系词,仍然不能接受否定副词“不”的修饰。而在哈姆雷特的“to be,or not to be”中,“to be”用“是”表达,而“not to be”也必须用“是”表达;后者在汉语中却不用“是”、而用“非”表达,就像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16]那样。这说明,在早期汉语中,即使不涉及价值判断内涵,即使是表达单纯的存在性判断,“是”仍然不用于否定性的事物。至于后来“是”可以接受否定副词的修饰,而构成“不是”结构,已是晚唐至宋初之时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发展为系词的“是”是在近一千年以后,其价值肯定性才消失;而如果从它产生时算起,“是”约有二千年之久是与价值肯定性不可分割的。后轴心期的西语的to be 仅仅意味着存在论之“存在者”,而汉语的“是”不仅意味着存在论之“存在者”,更意味着价值论范畴的“善者”。华夏民族的“哲学”之所以带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或许与“是”的这种价值论特征有关?
总之,在汉语“是”与西语“to be”之间,既有对应性,又有差异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是非”观念,来源于作为形而上学观念的早期“是”的存在者化的神圣指代性;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是”观念,又来源于前形而上学的更为原始的“是”“时”的标示存在本身的系词性;这种原始的“是”“时”观念,乃是华夏先民的源始的生存之领会与解释。
[1] 肖娅曼:《汉语系词“是”的形而上之谜——“是”为什么发展为判断词?》,《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
[2]《孟子》:《十三经注疏》本。
[3] 肖娅曼:《中华民族的“是”观念来源于“时”——上古汉语“是”与“时”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周易》:《十三经注疏》本。
[5]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
[6]《诗经》:《十三经注疏》本。
[7]《尚书》:《十三经注疏》本。
[8]《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台湾大通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年三月。
[9] 唐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
[10] 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殷周金文集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大戴礼记》: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皇清经解》本。
[12]《史记》:中华书局?。
[13]《广雅》:?
[14]《管子》: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本。
[15]《左传》:《十三经注疏》本。
[16]《论语》:《十三经注疏》本。
--------------------------------------------------------------------------------
[1] 这里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不是传统教科书里的用法,而是西语固有的用法,意指哲学的纯粹部分,即存在论(旧译为本体论)部分。因此,本文的“形而上学”没有任何褒贬的意味。
[2] 这有两个原因:其一,20世纪的语言学以科学主义为特征,语义因其无形式标志被认为无客观依据,研究将缺乏科学性,因而被搁置起来;其二,在语言学看来,“是”一出现就是一个指代词,后来变成了系词,而无论指代词还是系词都没有实义。因此,语言学很难自己去关注“是”的语义问题。
[3] 语言学界一致认为,上古“时”“是”为异体字(“时”表示时间除外),即为同一个词的不同文字形式。笔者认为“时”为“是”的母体,“是”从“时”分化而来。
[4]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注:“訅,谋也。”
[5] O+V 即宾语+动词,V+O 即动词+宾语。
[6] “之”的出处略去,“是”的出处从上到下依次为(含同类者):者減钟、陈公子甗、徐音尹钲、伯亚臣缶霝、徐王鼎、申鼎、攻×戕孫編鐘(甲)、臧孙钟、蔡侯编鎛、曾子伯斿鼎、毛公旅鼎、虢季子白盤、攻敔王夫差剑(甲)、余義鍾、欒書缶、邾公华钟、邾公牼钟、晋姜鼎、王子午鼎。
[7] 全句为:“台嘉者(诸)士,至于万年,分器是寺。”(邾公牼钟 《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寺,持也。”)
[8] 金文中“匡”、“嚮”、“利”、“语”(娱)都是表示虔敬尊崇的动词。
[9]“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閟宫》)“是”不是代名词作主语,而是代谓词作状语,表示合乎神意地,正义的态度、方式等。
[10] 金文材料来自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马承源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
[11] 全句为:“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诗经·周颂·赉》)“时周之命,于绎思”郑玄笺:“劳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朱熹《诗集传》:“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复商之旧矣。”
[12]《诗经·周颂·般》郑笺:“裒,众。对,配也。遍天之下众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13]《诗·大雅·生民》毛传:“腓,辟。字,爱也。”
[14]《诗·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孔颖达疏。
[15]《大戴礼记·千乘》“日厤巫祝”王聘珍解诂。
[16]《史记·日者列传》裴駰集解。
[17]《广雅·释言》“日节也”王念孙疏证引《开元占经·日占篇》引《春秋元命包》。
[18]《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尹知章注。
[19]《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与於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origin of the values of ‘Rights and Wrongs’ in Chines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shi (是)’ and ‘shi (时)’. The are both corresponde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shi (是)’ in Chinese and ‘to be’ in western languages. The idea ‘Rights and Wrongs’ as values stemmed from the holy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shi (是)’ as demonstrative pronoun, which had been taken as Seiendes as metaphysical idea. Again the metaphysical idea ‘shi (是)’ stemm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pula of the more original ‘shi (是)’, which was a pre-metaphysical idea as Sein itself. And again the most original idea ‘shi (是)’ or ‘shi (时)’ was Chinese nation’s original ‘comprehension and explanation of existence’.
Key Words:Time; Beings; Rights and Wrongs; Existence; Sein; Values;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