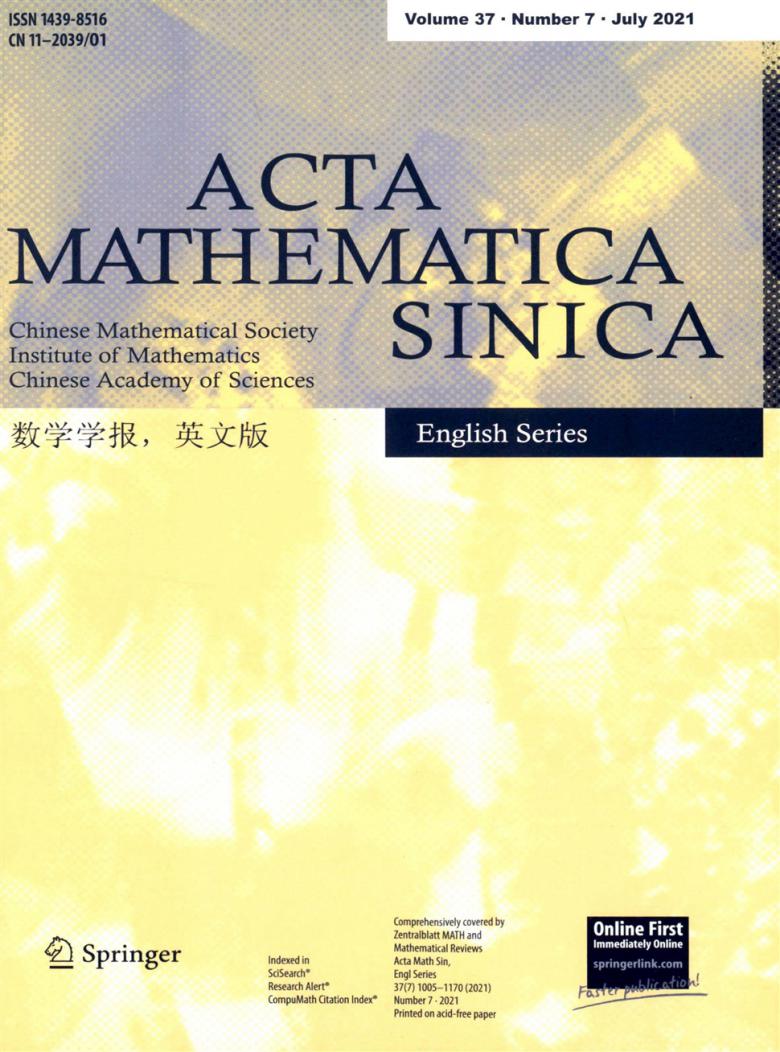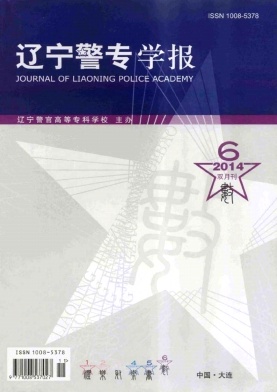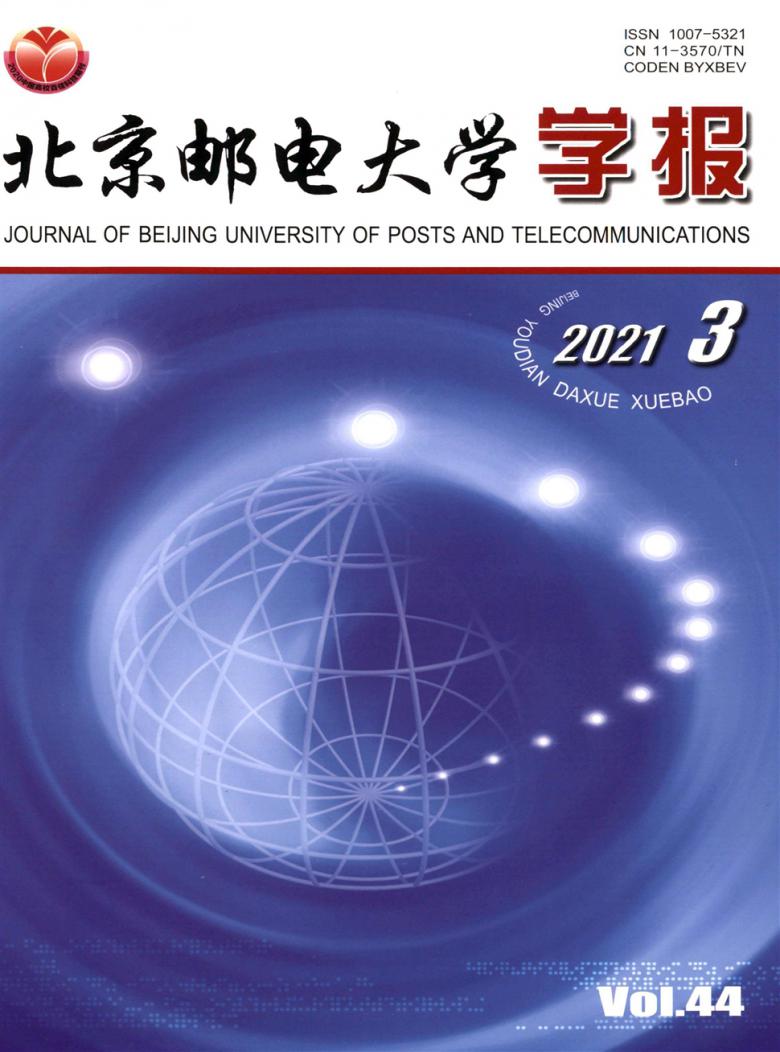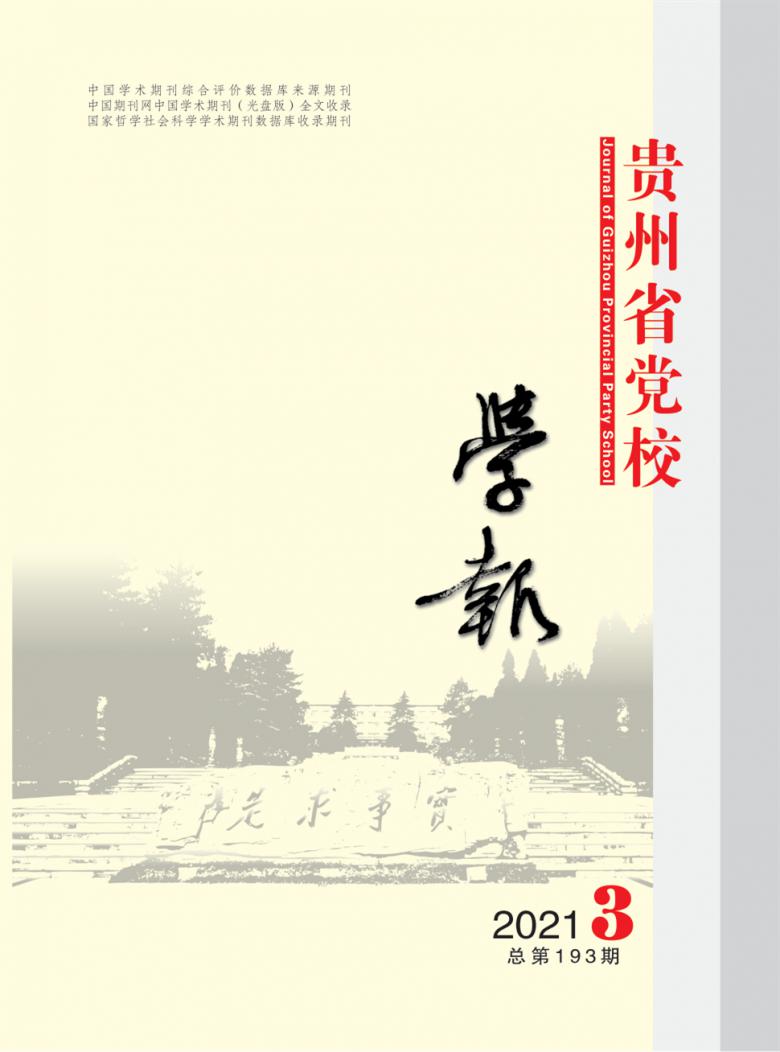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卢毅 2008-07-29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辛亥前后的民俗学研究
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他曾在《訄书·序种姓上》一篇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上古史。他说:“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讬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原注,‘图腾’一词音译——引者按)。……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鸟名,禹之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1]在此,章太炎利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崇拜等事例来解释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尽管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师的谬解,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方法的运用。
在章太炎的潜移默化下,同时受到西方学者安得路朗等人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与周作人也对民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起着手收集有关的书籍。1907年,鲁迅买到了一本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便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2]同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安得路朗合著的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内容的《红星佚史》。在此基础上,鲁迅在1908年撰写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就开始运用西方民俗学理论,深刻阐明了神话起源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驳斥了漠视神话者的浅薄无知。他说:“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并提出:“矧欧西艺文,多蒙其译,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3]由是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了神话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归国后,鲁迅又在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笑话。他还收集了各地儿歌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并将周作人所收集的歌谣推荐到《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4]1913年12月,鲁迅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编纂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5]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论者认为,后来的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自于鲁迅的上述主张。[6]
客观地看来,鲁迅之所以研究民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7]。这说明他研究民俗,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事实上,鲁迅并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以英国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为例,阐明其研究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8]。而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则更为系统,同时也更具有学术意味。
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9],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学者盖莱(Gayley)撰写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一书,此后他自己又先后购买了安得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表明他对民俗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出发,周作人开始对民俗学展开初步研究。1908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便呼吁说:“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10]这种对“谣歌俗曲”的高度评价,无疑极大地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回国后,周作人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儿歌童谣中去。1912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1914年1月,他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经过他的一番精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11],这可以说从实践上开启了北大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而且在这则启示中,周作人还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一词,并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是第一次。此外,周作人还具体制定了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也带有明显的科学性。
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此期间还撰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阐述了“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的看法,而且还分别论述了童话的起源、分类、历史、特点等问题,第一次将童话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在1913年11月15日发表的《童话略说》一文中,他更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俗学”一词:“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12],从而正式奠定了“民俗学”形成一门近代学科的基础。
二、“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客观看来,尽管鲁迅与周作人早在辛亥前后就已经开始收集歌谣,并从民俗学角度对神话展开了一些尝试性研究,但这项工作在当时毕竟仍然较为零星片断,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所以“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它到底是属于‘前史’或‘原史’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部门的中国歌谣学,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夜”[13]。
目前学者大都认为“民俗学运动”首先从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开始,而事实上这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密不可分。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白话文提倡者也逐渐认识到除了胡适一再表彰的几部古典小说外,白话文的根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各地歌谣。周作人便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14]他并且明确表示:“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15],“做新诗创作的参考”[16]。沈兼士也说:“‘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是这个决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话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17]。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认识,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由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规定了关于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同时宣布成立歌谣征集处,“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这显然意味着在这场“民俗学运动”揭幕战中,章门弟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集歌谣之进行》一文写道:“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这说明周作人此时已参加了“歌谣征集处”的工作。至1920年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发表《歌谣征集处启事》宣布:“顷因刘教授留学欧洲,所有本处事务已移交周作人教授接管”,这更表明了章门弟子对“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作用。
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三人联名《发起歌谣研究会征集委员》的启事,决定发起歌谣研究会。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宣告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8]。相较而言,歌谣研究会“从名称上看比‘歌谣征集处’提格了,成为了一个正规化的学术团体;领导班子加强了,并且发展了委员”。[19]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沈兼士担任主任,歌谣研究会也划归国学门,由周作人一人主任其事。该年12月17日,周作人等人还创办了歌谣研究会机关刊物——《歌谣》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民俗学研究刊物,被视为当时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20]。此后《歌谣》周刊运行三年,先后出版97期,增刊1期,发表歌谣2千多首,文章近3百篇,直至1925年6月28日合并入《国学门周刊》。
除了创办研究机构与刊物之外,章门弟子还从诸多方面对“民俗学运动”予以积极的理论指导,促使其不断趋于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初步探索并逐渐完善了民歌分类等理论问题。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点,民歌是民俗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而关于民歌的分类在当时却始终未能确定。鉴于此,沈兼士于1920年12月16日提出:“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我主张把这两种民谣分作两类,所以示区别,明限制”[21]。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民歌进行分类,虽不免有些笼统模糊,沈兼士自己后来也承认这种分类尽管在“原理上”还有几分成立的理由,而在实践中却“有时不能断定其为自然或假作”,但这毕竟反映了他积极探索的精神。
1922年4月3日,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也尝试对民歌加以分类。他主张将歌谣分为六大类:1、情歌2、生活歌3、滑稽歌4、叙事歌5、仪式歌6、儿歌(事物歌、游戏歌)。[22]这种分类标准基本上是依据歌曲的思想内容,同时又兼顾其特定功能及服务对象,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自清在后来编写的《中国歌谣》一书中,列举了十五种古今中外不同的分类法,最后还是采用了周作人的分类法。而作为全国第一部民俗学统编教材,1980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仍然大体沿用了这种分类法。这说明周作人对民歌的分类是较为完善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此外,周作人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如《论猥亵》、《谈<目莲戏>》、《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方言标音实例——绍兴音》、《读<各省童谣集>》、《儿歌之研究》、《中国民歌的价值》、《猥亵的歌谣》、《关于猥亵的歌谣》、《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歌谣与妇女>序》、《蛮女的情歌》、《<初夜权>序言》、《<海外民歌>序》、《<潮州畲歌集>序》等。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精辟介绍了国外民俗学理论,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途径。
第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扩大了歌谣征集的范围。在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对征集范围有这样一项规定:“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这在周作人看来,明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主张要撤废”。[23]在他的这一倡议下,《歌谣》周刊创刊时就修订章程,其中鲜明指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24]周作人本人也在《发刊词》中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周作人在后来相关回忆文章中,对这项贡献也屡屡津津乐道,由此可见他对猥亵歌谣研究是如何的看重了。
当然,由于当时社会观念仍较保守,所以这方面歌谣的收集依旧是困难重重。有鉴于此,周作人在1923年12月又撰写了《猥亵的歌谣》一文,刊登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上,对此进一步加以呼吁。1925年10月,他又约集钱玄同、常惠共同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其中写道:“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专门搜集这类猥亵的歌谣等,希望大家加以帮助,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来。”该文还将猥亵歌谣的价值归纳为二方面:其一,它们“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其二,“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他又列举了目前希望做成的两件事:“(1)搜集猥亵的谣谚谜语等编为《猥亵歌谣集》,(2)搜集古语方言等编为《猥亵语汇》。”[25]从效果上看,这一次征集的成绩颇为可观,仅周作人“所收到的部分便很不少,足有一抽斗之多”[26]。今天看来,周作人这种观念和举动在当时民俗学界不啻是一场石破天惊的革命,充分体现了他开放的学术心态和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
第三,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将歌谣运动进一步提升为“民俗学运动”。早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周作人便宣布:“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这说明在创刊之初,周作人便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从而将《歌谣》周刊的旨趣定位于整个民俗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纯歌谣。无独有偶,鲁迅也曾对《歌谣周刊》发表过重要的意见,他说:“《歌谣周刊》的范围狭窄了,要放宽,群众生活中流传下来的民俗、文艺作品都要整理研究。”[27]在他们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歌谣》扩充了刊物内容,同时发表文章声明本会收集范围,从歌谣扩大到各地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28],并说明:“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都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论长短都特别欢迎。”[29]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歌谣运动,将之提升到更加开阔的民俗学范围,容肇祖就回顾说:“《歌谣》周刊自四十九号起,虽未曾改名,而实在是民俗周刊了。”[30]
在此期间,周作人还对民俗学中的神话故事予以了特别关注。鉴于当时学术界对神话故事普遍存在着误解,他不得不一再澄清:“近来时常有人说起神话,但是他们用了科学的知识,不作历史的研究,却去下法律的判断,以为神话都是荒唐无稽的话,不但没有研究的价值,而且还有排斥的必要。这样的意见,实在不得不说是错误的”[31],“神话是什么?有些人以为是荒唐无稽之言,不但莫有研究它的价值而且有排斥它的必要,这种思想我认为实是错误”[32]。他并且还强调:“假使是民间的俗信,例如什么神什么鬼什么禁忌,那各有社会文化背景,值得了解与探讨。”[33]这无疑从学理层面澄清了人们的认识,为神话研究进一步扫除了障碍,极大地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范围。
第四,以平等的眼光,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积极倡导民俗学的建立。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创建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居功甚伟。早在1919年3月,朱希祖就明确提出:“一概须平等看待。高文典册,与夫歌谣小说,一样的重要”[34]。他并且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提议风俗调查会应采取“由近及远”的方法,先筹设京兆风俗陈列馆,以示模范。[35]而曾长期担任北大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后来也总结说:“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开一新途径。”[36]在就任厦大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演讲中,他又宣布:“本院于研究考古学之外,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37]这显然是将民俗学作为与近代考古学相同的一门学科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它的学科意义。
这一时期,周作人更是极力呼吁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他曾引章太炎的观点论证说:“章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38],这无疑是将民俗学视为一门基础学科。他还曾坦言:“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39]这更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强调民俗学学科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研究机构与刊物的创办,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章门弟子都积极开拓,勇于创新,为“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注释:
[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2] 周作人:《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3]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4]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5]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第49页。
[6] 常惠:《民间文学史话》,《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
[7] 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8] 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8页。
[9] [日]直江广治:《中国的民俗学》,转引自李扬:《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述评》,《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10]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3年,第330页。
[11] 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12] 周作人:《童话略说》,《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1912年11月15日。
[13] 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14] 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第31期,1923年11月4日。
[15] 周作人:《发刊词》,《歌谣》第1期,1922年12月17日。
[16] 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17] 沈兼士:《吴歌序》,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27页。
[18] 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5、16期合刊。
[19]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192页。
[20] 胡适:《歌谣·复刊词》,《歌谣》第2卷第1期,1935年4月4日。
[21] 沈兼士:《一封讨论歌谣的信》,《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6页。
[22] 周作人:《歌谣》,《晨报副刊》1922年4月13日。
[23] 周启明:《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4] 《歌谣研究会章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6日。
[25] 周作人:《征求猥亵的歌谣启》,《语丝》第48期,1925年10月12日。
[2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27] 王文宝:《编辑<歌谣周刊>的常惠先生》,《民间文学》1984年第8期。
[28] 《本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歌谣》第45期,1924年3月2日。
[29] 《本会启事》,《歌谣》第46期,1924年3月9日。
[30] 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5、16期合刊。
[31] 周作人:《神话与传说》,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2] 周作人:《神话的趣味》,《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2页。
[33] 周作人:《读旧书(二)》,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25页。
[34]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
[35] 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69页。
[36] 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43页。
[37]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38] 周作人:《女学一席话》,《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39] 周作人:《十堂笔谈》,《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