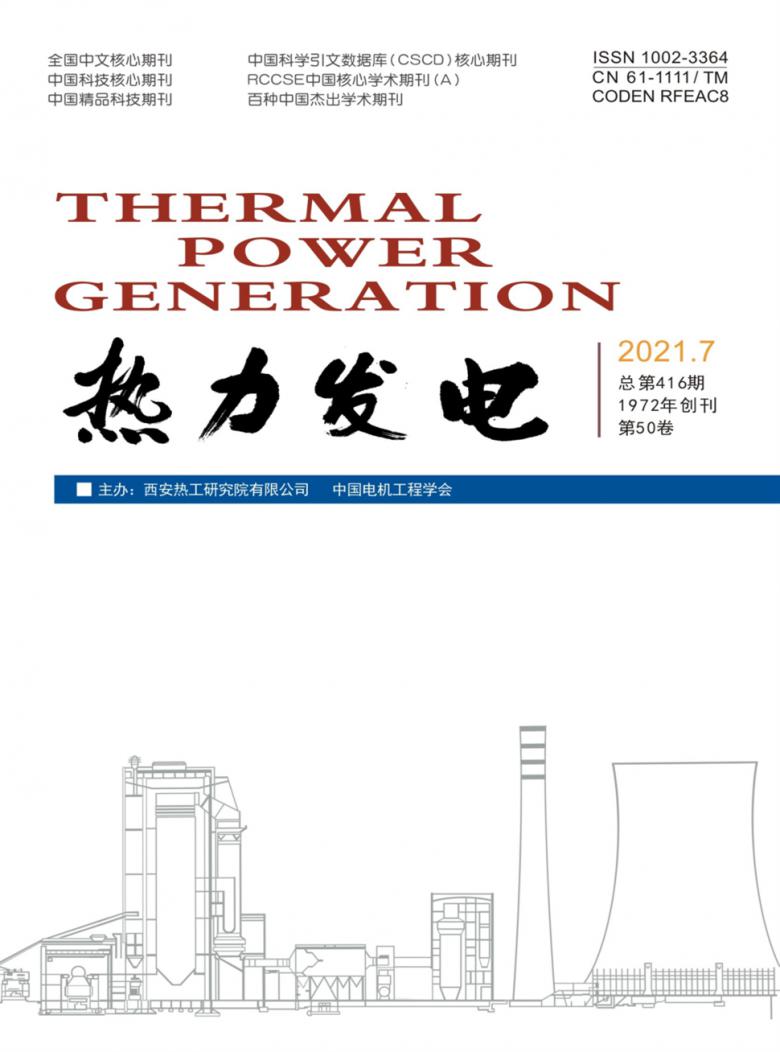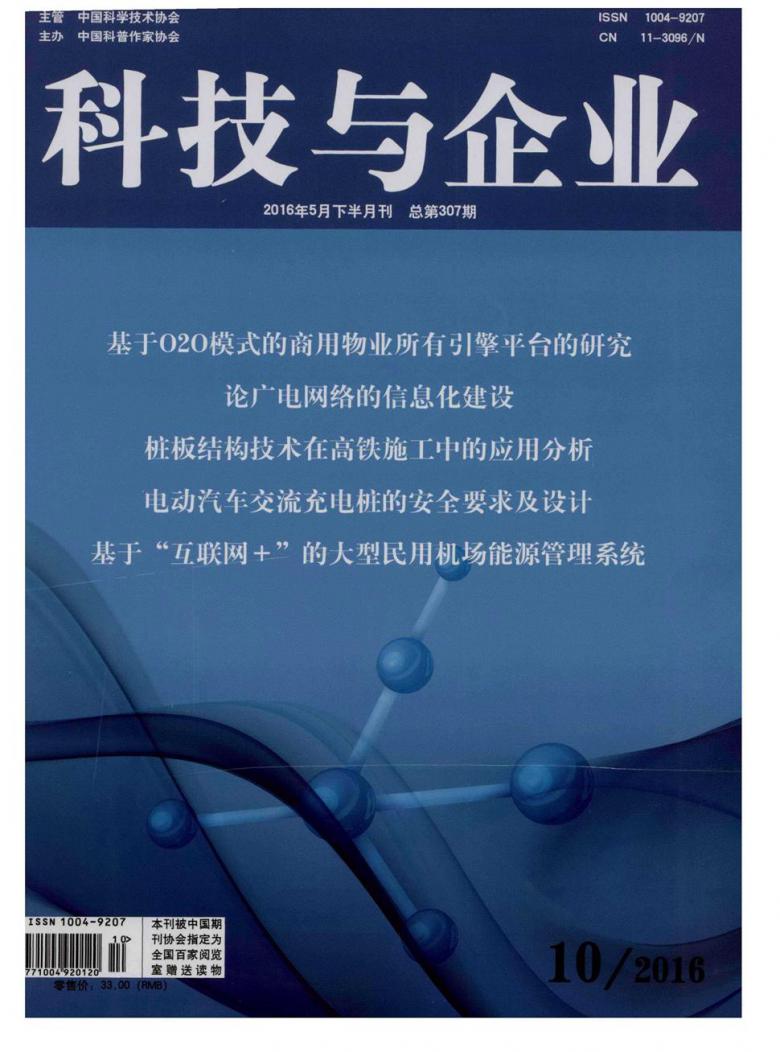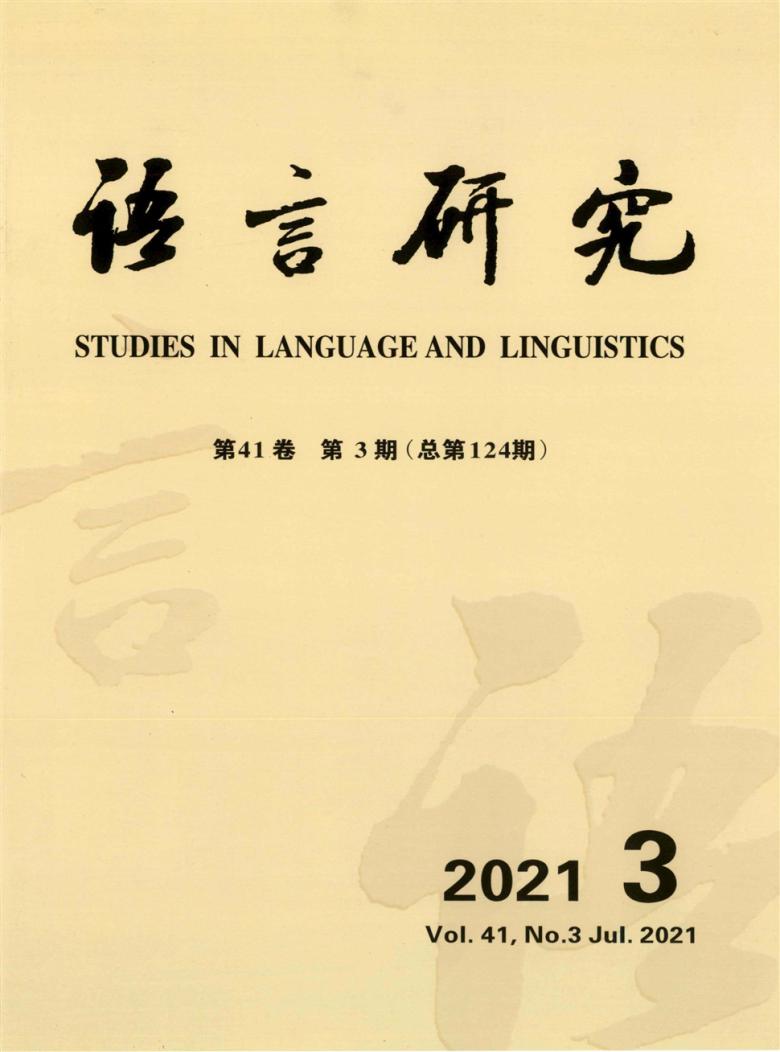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彭 华 2006-04-10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它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它所包举的范围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笔者认为,“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环视宇内,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中国文化亦然。中国文化如何直面“全球化”,本文提出了三点“对策”:(1)借鉴历史,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业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2)调整心态,稳健应对,从容裕如;(3)政府发挥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最后,笔者指出,未来“全球化”局面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文化 界说 探讨 展望
公元2001年12月11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随即,WTO成为中国人切切关心的一个话题,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作为一名中国人,自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话题,笔者向来颇为关心。因此,我仅在略陈几点浅见,算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参与或介入。
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其根本而言,是一个既具有时间概念、同时又具有空间概念的术语(英文和汉文都反映了这两个层面的意思)。
关于“全球化”出现的时间,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议。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三说。第一说认为,早在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此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诚如马克思所言,哥伦布之“发现”美洲,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之一即是使人类的历史由“地区(区域)史”走向“世界史”;但当时尚不具备“全球化”的规模和效果。第二说将“全球化”的时间界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的纷纷出台。该说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所界定的时间也堪称慧眼独具,但其时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套用李慎之的话说,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①]。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致辞中只用了“全球性”一词,“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三说直指九十年代末期,同时在参照系中置入了中国。九十年代末期的全球化,上承九十年代初、下启本世纪初,业已具备成熟的规模和特定的效果。因此,该说最为可取,最具可操作性,也最为贴近中国国情;并且在拙文的“话语体系”中,也最具可行性。故而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一项界说。
就“全球化”的外延而言,它所包举的范围相当广袤,几乎是全方位的,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其涵摄的范围。当然,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但还有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等等(甚至垃圾的处理也成了全球性的问题)[②]。拿WTO来说,它虽然主要是贸易层面的,但它也涉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方面。王蒙敏锐地指出,“外国的东西,虽然你看着非常技术性,但往往和他们整个的文化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③]。可以这样说,加入WTO虽然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全球化的影响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二项界说。
对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另外一个词语“全球主义”,也有必要在此略做区分。所谓“全球化”,其实并不应当拒斥国家的民族性、经济的多元性和文化的个性(后文有论述);但与之相反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后者是把前者单一化(例如只强调全球化的经济面向)、意识形态化(例如只讲全球化的“好处”),而掩盖全球化过程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变得更边缘化,区域化,其实是如何把他们排除出去。而我所理解、所展望的“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详见后文)。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三项界说。
一、汹涌的潮流: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无须否认,“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④]。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全球化”业已来临,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虽然说常常是指经济(产品、资本)的全球化,另外再加上信息和技术的全球化。诚如前文所言,这并非“全球化”的全部内涵和外延;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它们也带来了新的时尚、风气、品位,新的生话方式。这些新的生话方式,不但会与“后发社会”和“边缘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拒绝“接轨”的群体)发中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区域文化”(如中国文化,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此论旨推向极至。降而言之,即使是像可日可乐、麦当劳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固然是源于美国本土,代表了“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它们己经不能简单地“还原”(revert)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出现了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益相关的群体,其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而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买办。
就本文论旨而言,“全球化”的面向或层面包含了全新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虽然“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经济”。面对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中国文化,其实也是无处遁逃——中国文化,必须直面“全球化”。
二、中国文化的界说: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特有的人文关怀
文化(culture),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别离了文化,其实人类无处附丽;所以,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人”特有的存在样式。
某一“民族文化”区别于另一“民族文化”的标志,就在于其作为核心部分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念。任何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显示出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方式。虽然说某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作为某一“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基本的永恒的价值观念,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identity)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形象地说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及特质,前贤大德、时下才俊多有评说,本处仅择其大义与要旨而言。(1)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这恐怕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钱穆说,“中国文化,简言之,乃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⑤],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有生命性之文化”[⑥]。(2)作为颇具人文色彩的中国文化,其最为注重者恐莫过于道德精神。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特重于道德之文化,亦可谓道德精神,乃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主要特点。”[⑦]在《中国历史精神》的演讲中,他又再次申述此旨,“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之道德的精神”。这在儒学上表现得最明显,钱穆用了一个“善”字来概括[⑧]。(3)中国文化又颇重伦理纲常。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⑨]。(4)就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融摄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之融摄和包容外来文化,主要有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至于中国文化的其他特质,在此不再赘述。
三、历史的借鉴: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
中国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其实不乏现实借鉴意义。与中国文化相关涉的外来文化,主要有两大宗,一是汉魏以降的佛教,二是明清以降的西学。前一项业已告一段落,而后一项则仍在进行之中。
相对于汉朝以前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而言,佛教其实是一种非常“异质”的文化,所以佛教之东渐中土,堪称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先是有所谓“格义”之学,之后又有“沙门不敬王者论”,再后来才稍微顺畅,并最终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之进入中国文化,应该说还是颇为成功,究其因缘,陈寅恪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⑩]。进而言之,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定的自信心有关,我自巍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
明清以降的西学,直至1840年以前几乎没有成就多少气候;但随着1840年西方“坚船利炮”的滚滚而来,国门为之洞开,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文化似乎岌岌可危。陈寅恪明言,“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11]。
与前一次佛教入渐中土相比,这次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不再是积极的主动的自信的“纳入”,而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卑的“学习”。先是有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物质层面),再有康、梁的“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后来则演变为“全盘西化”(文化层面),反文化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如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干将,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诚如闻一多所言,“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现代英国诗人·序》)。他们似乎“预设”(presuppose)了一个前提,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似乎就可以融入“世界化”的潮流;而目下有些人,再顺杆而上,进而认为,如此就可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是由于文化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危机。但其危害甚深,因为全盘弃绝传统,不仅意味着连根拔除人所特有的人文理念,而且还意味着否定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否定历史经验的参照意义;全面拒绝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将摧毁文化的价值理念,也为向怀疑否定科学理性的功能的非理性主义暗转埋下了伏笔。近代的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一论,怪诞而嚣张、离奇而肤浅,殊不足取。
中国文化在近代确实是“生病”了,需要救治,需要复兴,“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12]。当然,保有传统、发扬传统,并不是说要拒斥西方、拒绝“全球化”。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钱穆就说过:“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3]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14]。此论不可谓不精当。
四、心态的调整:稳健应对,从容裕如
两相对照,就可以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前后两次面对外来文化,但前后两次的心态却截然相反。汉唐之时的无比自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得支离破碎;汉唐之时的宽广胸襟,已经被“欧风美雨”吹得荡然无存。对于国人前后截然相反的心态,鲁迅有过精彩的评说。而心态背后隐藏的东西,无疑就是国力与国运。其实,我们在直面如今的“全球化”时,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大可坦然面对;但前提是国力的提升与国运的昌盛。
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王国维当年曾经讥讽过只知国学而不知西学的“一孔之陋儒”,并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15]。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16]。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年兴者”(《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的论述,虽是事过境迁,但至今看来,仍然不失其睿智洞见与指导意义。中学西学,密不可分,如果加以互相勘照,互相借鉴,自当会有更多的发明与创见;但援引西学绝非生搬硬套西学,简单的套用与单一的比附,只会贻笑大方。“橘逾淮而枳”,即是明证。援引西学以为我所用之前,必须做具体的可行性上的检讨与验证[17]。王国维注重与西人学术的“暗合”,陈寅恪注重“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也许正因为如此,吴宓将陈寅恪的文化观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本位论)[18]。就中国思想史而言,玄奘的忠实输入唯实学,就是一个典型,“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根据陈寅恪的看法,“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9]。就此而言,任何“削足适履”和“削履适足”都不可取[20]。亦即,在建构中华文化时,既要有“放眼看世界”的文化气魄,也要有中华文化必将振复的文化自信。
五、政府的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
顾炎武当年非常睿智地区分了“国”与“天下”,所谓“亡国”乃“易姓改号”(如王朝更替),而“亡天下”则直接关涉到文化命脉,“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他高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进而言之,文化兴亡,非但匹夫有责,国家也有责焉。质而言之,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亦需要国家的“积极引导”,这是国家与政府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
就这一层面而言,法国政府的应战战略不无借鉴意义。比如电影产业,在好莱坞的全球攻略背景下,法国电影数十年屹立不倒,法国电影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生产水准,本国电影票房一直稳定在市场份额的30%以上。法国的电影产业政策,其最重要的一环是以财政收入来支持电影艺术创作。据统计,90年代以来,法国的电影扶持资金总额一直保持在每年12亿—17亿法郎之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人投资法国电影的积极性,目前法国电影的集资渠道已形成了本土制作人投资、电视台投资、外国投资等三条渠道。由于法国实行了积极引导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为法国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上的支持,使得法国电影在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竞争力,保证了电影的稳定生产,法国电影民族产业不仅没有被吞食,而且始终保持了元气[21]。更何况,就本质而言,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其实还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直接来自法国文化。因此,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抗还仅仅“资本主义文化”范围内的对抗。而中国文化与美国则不然,二者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其冲突与对抗势必更为激烈而猛烈,所遭遇的问题也势必更为。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信心百倍地面对“全球化”;国家与政府也有信心、有能力、积极地引导我们中国人直面“全球化”。如此而为,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关于“全球化”的展望,中外论说者甚伙。我仅在此强调一点:就“文化”一端而言,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
身处春秋时期的孔子,曾经精辟地区分过“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朱熹《四书集注》)。孔子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伦理学的层面,而同时期史伯的区分则主要集中在哲学的层面,“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显然,所谓“和”并不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同”则反之。因此,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
具体而言,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产业,虽然他们还不是非常成熟,但他们无疑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群一直到每个个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个性,所以融入“全球化”并不等于失却自我、失却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反而会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爱惜自己的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和消化,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半坡村的“半坡文化”很纯粹,埃及的卡纳克神殿,它的金字塔文化、木乃伊文化和圣殿文化很纯粹,但是古埃及人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所有活的文化都是充分利用开放和杂交的优势,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当中发展,所以王蒙认为“纯洁性的提法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提法”[22]。
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这毫无疑问应当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当务之急),恐怕应当是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壮大精品文化产业(行话叫“做大”、“做强”)。比如,当今国际业已有五大唱片公司,它们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规模宏大;而我国虽然有290多家音像公司,但它们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注册资金都只在40亿元人民币,整个产业规模偏小,加起来还不如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这五大唱片公司全部进来,我们自己的唱片业肯定没有生存余地。因此,奋发图强,发扬壮大的神圣使命,又严峻地摆在国人的面前。当然,“做大”、“做强”并不是通过单一的并购以达到简单的外形膨胀,因为“简单的外形膨胀”最终还只是“纸老虎”一个,最终未必能经受得住人家的冲击。
话也说回来,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不等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要努力,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比如,作为1994年中国第一部引进的外国大片《亡命天涯》,成为中国国产电影“亡命天涯”的一个象征;但是,五年之后,“外语”大片票房的整体滑坡和“华语”电影借《卧虎藏龙》之势的整体向好,昭示了国产电影在“休克”疗法下的复活可能。
[①]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②]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③]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3日。
[④]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⑤]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331页。
[⑥]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08页。
[⑦]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192页。
[⑧]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78页。
[⑨]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⑩]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10、11页。
[11]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11页。
[12] 唐君毅、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张祥浩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
[1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5页。
[14]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3日。
[15]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科大学文学科章程书后》,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
[16]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同上。
[17]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上海),1997年2月6日第三版。
[18]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关于陈寅恪对文化的看法,可详细参看拙作《陈寅恪的文化史观》,《史学理论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
[1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20]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上海),1997年2月6日第二版。
[21] 万千:《当资本来到你面前:法国政府应战策略》,《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3日。
[22]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