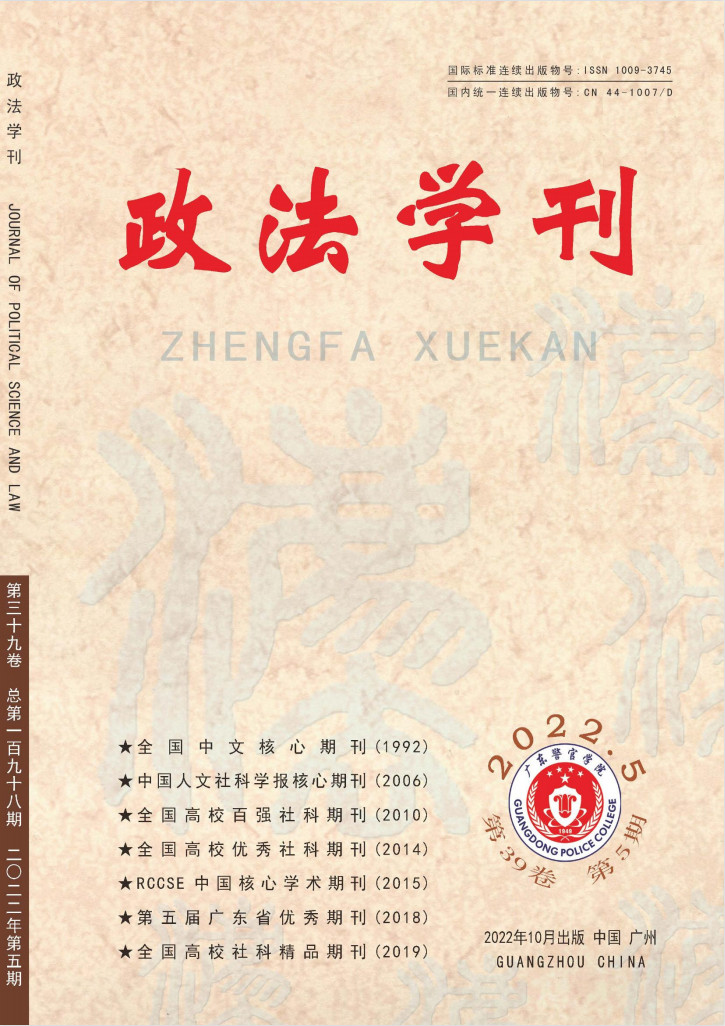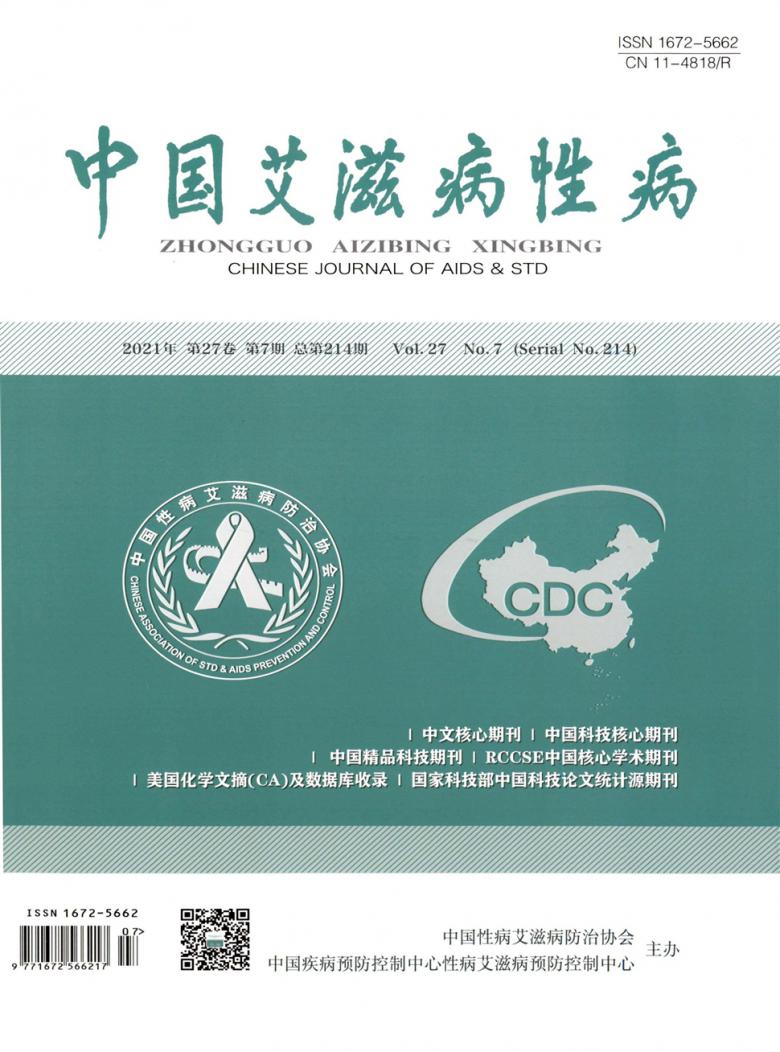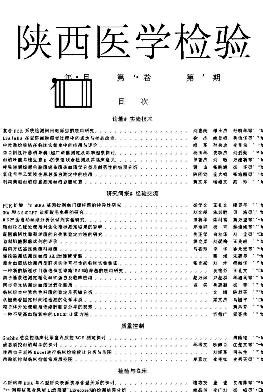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佚名 2003-06-07
亚洲风暴已经逐步扩散全球。继俄罗斯之后,拉美的巴西正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对冲基金LTCM在美国政府牵头拯救下才免于破产,暂时避免了在发达国家即时爆发金融危机。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金融危机日益繁密,而且日益严重。在发达国家,80年代美国用于拯救存贷银行的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挪威是4%,瑞典6%,芬兰8%,西班牙17%。在1980~1996年,有三分之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经历过信用制度的灾难。在家,灾难程度比发达国深远得多。自1980年以来,有5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系统损失了一半以上资金,有十多个国家使用了10%以上的GDP来拯救银行危机,数额达到7500亿美元。有些国家甚至要使用GDP的25%来解决金融危机。如今,亚洲金融风暴又一次打破纪录。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70年代以来至少三次。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90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90年代的新情况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不稳定性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4%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五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三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三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
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亨伍德在《华尔街》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衍生工具大部分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分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八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亨伍德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80及90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20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20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在1981及1997年之间,多起兼并收购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
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学家的: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 -7810法国 -880意大利 -1090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德国 +2030英国 230共计 -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
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增长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50、60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 1972~1980年 1981~1990年
南韩 39.7 27.7 16.9
日本 48.2 22.9 14.4
美国 28.4 17.4 12.6
欧洲 16.4 12.7 13.4
来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41页。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撤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业)都多。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现在已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七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90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装进自己口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所造成的损害就由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搭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五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90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主要资料:
1、"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London.
2、"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by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No.229, 1998, London.
3、"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London, 1998.
4、"IMF/World Bank/WTO-Free Market Fiasco", edited by Eric Touss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