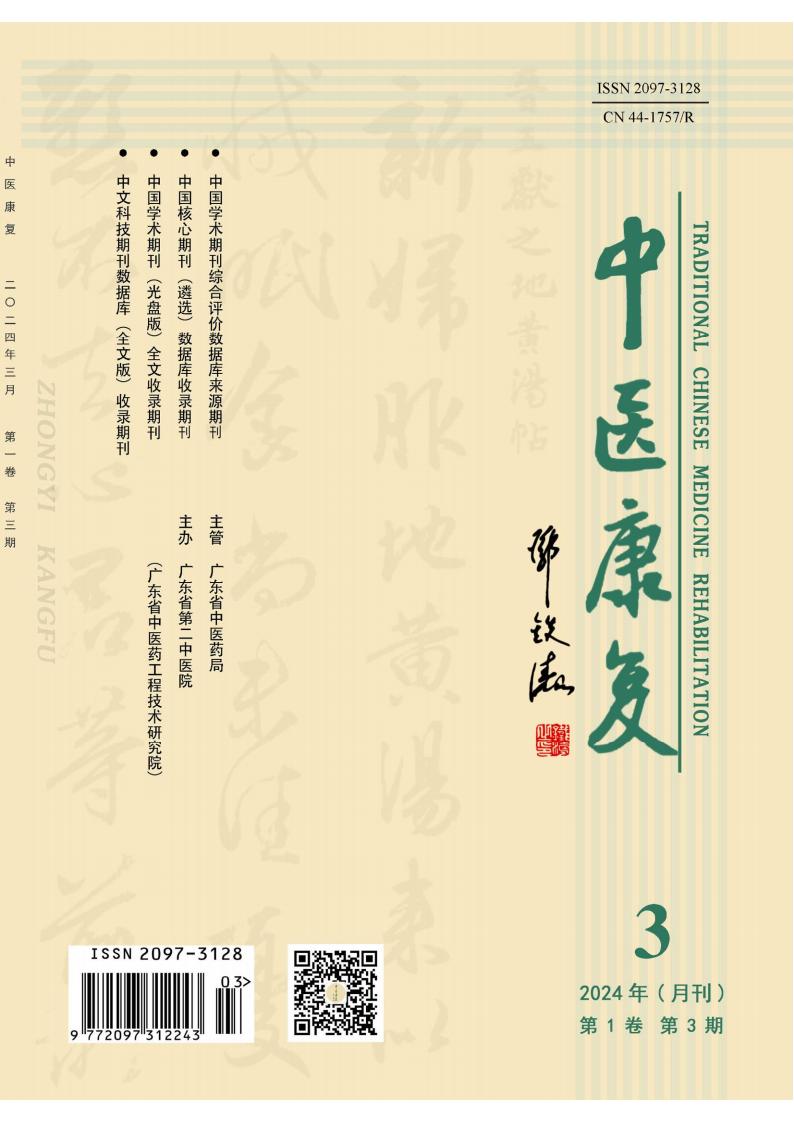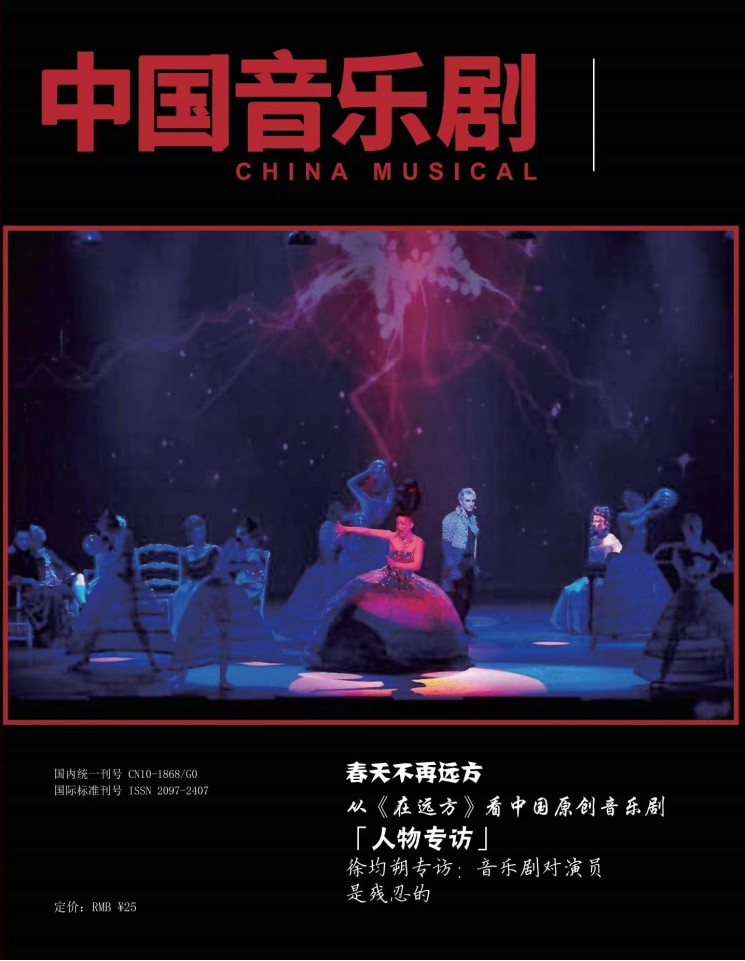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发展理论视野中发展观的几次深刻转折
沈 杰
内容摘要: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人类发展观和发展实践进程中,经历了从唯经济指数独尊的时代,到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指数的时代,再步入一个强调人文指数的时代。这些转折不仅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对发展实践一种反思结果的发展观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反映在有关发展理论和发展决策的学科角色上,则是表现为从经济学主导的时代过渡到综合性学科的时代,而且正进入一个人文学科大显身手的时代。
作为发展理论语境中的发展观,本身则是发展理论内涵的高度体现,它是涉及到发展哲学、发展原则、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诸方面的一种理论体系和实践策略。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发展观,不仅体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现代化实践认识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都表现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决策的有关学科角色上。作为发展观的一种集中而具体的表现形式,便是发展指标及其体系的制定。
20世纪中叶,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在西方,它的兴起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作为一种最为迫切的实践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且也成为联合国国际事务的关注重点。从60年代开始,联合国大会先后通过了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国际发展规划。而进入90年代之后,联合国又推出了许多发展研究项目,并制定了大量发展规划。
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尽管在现代化理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变迁理论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理论,但最确切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则是自现代化理论形成之后开始的,因为现代化被视为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发展理论则是对有计划社会变迁的关注形式和思考成果。然而,由于现代化理论在其产生不久之后便受到批评,因此,学者们更愿意采用发展理论这一称谓来与现代化理论相区别,而后来的现代化理论也即狭义上的发展理论。所以,发展理论从内涵和外延上要比现代化理论更宽泛,但在实际研究领域和方法上则又与现代化理论有着紧密关联。
一、从“GDP崇拜”到强调综合指数:独尊效率转向兼顾公平
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观以“GDP崇拜”为其特征,实质上反映了当时对于现代化的一种简单化理解。由于这种发展观把发展主要看作一种经济现象,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单维度的物质财富增长过程,因此,按此逻辑的发展理念是: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经济指数的增长。体现这种发展观的典型例子,可以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规划中看到。这一规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应达到5%的目标。可见,这种发展观所强调的只是经济指数,而没有注意社会指数和其他方面的指数。
这种发展观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它在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得以最充分体现的原因在于: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情势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确立的发展战略都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可以说,“GDP崇拜”[1]成为一种普遍情结。“GDP崇拜”的实质就是唯效率崇拜。
经由这种发展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速的加快。到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在总体上达到了联合国发展规划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5%的目标。然而,这种发展观所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甚至还带来了种种非意图性的不良后果,具体而言,这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不久便带来了许多严重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有: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如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被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从而导致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结果。正是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并未呈现正相关、甚至还出现负相关的现象,促使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对以往发展观进行反思。于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出现了各种“替代性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无疑是以另一种不同的发展观为基础的。
正是基于对以独尊经济指数或“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的检讨,发展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放弃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而倡导一种综合取向的发展观,强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这种综合发展观的基本理念认为,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应看作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之间综合、协调进步的成效。
从比较的角度,可以把与“GDP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发展观不同的综合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阐述如下。
首先,在发展取向方面。传统发展观强调发展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综合发展观则强调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固然不容置疑,但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至高无上,而社会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联合国的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规划中便开始给予强调: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同快速的经济增长相同步,而且要切实减少现存的地区、部门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这些目标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发展的最终结果,因而它们被视为同一过程的综合物。[2]可以看到,不再是单一地强调效率,公正的重要性已经被注意到。
其次,在发展机制方面。传统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具有单一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特征。而综合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则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整体性的特征。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表现出“时空压缩”特征,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的高科技化,由于信息、资源的引进与输入频度加大,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类,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几率空前地增加,由此导致各国的发展环境之间从未像现在这样息息相关。因此,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到资源短缺、人口过剩、失业严重、移民浪潮……。这一切都从反向角度表现出当今世界在发展特征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整体性。
再次,在发展内容方面。传统发展观主要注重的是物质层面的发展,而综合发展观则更加注重多个层面的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
最后,在发展原则方面。在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时期,实际上是只重视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而综合发展观则注意到在追求经济效率时要兼顾社会公平。
如果概括地表述,传统发展观所理解的发展,其特征表现为:以独尊经济指数为取向,因此必然依赖单一性的机制,奉行效率优先的原则,最终则以物作为发展的中心目标。而综合发展观所理解的发展,其特征表现为:是以综合指数为取向,因而必然依赖复杂性的机制,奉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最终则是以人作为发展的中心目标。
从传统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体现了发展理论对发展本质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刻转折。首先,它丰富了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反映在发展指标上则表现为发展指标体系越来越复杂,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3]中,只是把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PPP)计算的人均GDP当作参考指标之一,另外3个指标分别是:出生时预期寿命、成年人识字率、从小学到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一份由该机构委托独立的专家组所撰写的“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成为比较国别之间人民生活真实状况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主要“从人本身出发”,尽量全方位地反映人民生活,而不是像GDP一样仅反映了经济发展方面的状况。
其次,这次转折重新定位了发展的目的与发展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实质上是把物作为发展的目的,而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而综合发展观则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而把物作为发展的手段。因此,传统发展观在发展的目的与发展的手段上是本末倒置的,综合发展观将两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正确地加以定位。
二、幸福指数关怀:发展观演进中的人本化取向
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形式之一就是发展指标的制定,因此,发展观的转变也必然体现在发展指标及其体系的变革方面。与发展观演变进程相一致的是,发展指标的变革同样经历了几个相应的阶段:从独尊经济指标阶段,到强调综合指标阶段,再进入关注人文指标阶段。
在综合发展观中,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心目标。然而,人的发展又是分层次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人的发展指标体现出来。换言之,强调人的发展的指标,可分为几个不断上升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关心人的生存条件层面(衣食住行、预期寿命等);第二层次是关心人的发展条件层面(职业素养、流动机会等);第三个层次是关心人的心理感受层面(满意程度、幸福感受等)。
在人的发展方面,如果说强调综合发展的指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初级层面的话,那么,倡导“以人为本”的目标则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高级层面,换言之,在“以人为中心”阶段,发展理念向更高的层面上升。“以人为本”具体化在发展指标方面则表现为对“人文指数”的关注,这种人文指数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变成具体的发展指标。而生活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指数”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了发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中对心理感受给予了高度重视。可以说,作为发展研究一个重要领域的发展指标,在60年代以前涉及的几乎都是客观层面的内容。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综合发展观的影响,生活质量研究也逐步向更广泛、深入的领域扩展,主观层面的内容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其中以测量个体维度主观层面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指标研究,在当时美国兴起的“社会指标运动”中出现了。此后,“主观幸福感”等较具代表性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在生活质量研究和测量中日益扮演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
将幸福感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哲学家、心理学家的推动,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内含有认知成分,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因而带有很多理性色彩,同时也内含有情感成分,表现内在体验的性质,因而具有很多情绪色彩。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实际上,可以认为,幸福感是一种高度的或极其强烈的生活满意状态。总之,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感受。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无论如何,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上体现了发展观进入“以人为中心”阶段之后,向着“以人为本”的更高层次的提升。具体而言,发展目标从“以物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是发展观的一次重要转折,而进入“以人为中心”的阶段之后,从以人的生活条件为中心进入到以人的生活感受为中心,则是发展观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似乎可称作以幸福指数为核心的人文取向的发展观。这种人文取向的发展观的出现,除了受到社会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以及人的需求上升规律的支配作用之外,也是由于一些关于人的幸福感的研究成果所推动。
在传统的经济学视野里,财富的增加是提升人的幸福程度的最有力手段,因此,财富增加似乎就意味着幸福增加。但是,心理学科对于财富数量与幸福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些值得注目的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4]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幸福感受之间的相关度非常紧密,但是,一旦超过了这种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所有变量中,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受的比例不会超过2%。追踪性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人们的幸福感受程度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相反,压力感受却有所增加。
对现实情况的研究分析表明,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而心理学科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之,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阈:只有当GDP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的追求;而只有当GDP超过特定界阈之后,幸福指数才会呈现增加,换言之,GDP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作为解释人们幸福感受的物质基础,可是,在突破一定界线之后,它对幸福程度的解释力似乎就变得很弱。因此,GDP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程度的根本性指标,但决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幸福程度的根本性指标。
正由于幸福感已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独特尺度,幸福指数成为说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于是,一向以研究客观层面著称的经济学,近年来也更多地关注主观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幸福感这个长期以来属于心理学范畴的研究课题进行了特别耐人寻味的探讨。而以往更多地沉浸于纯学术兴趣的心理学,随着对发展研究介入程度的加深,对于幸福感的关注程度也正在增加。于是,当今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交叉之势。如果说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概念而对人类幸福做出过一种特殊贡献的话,那么,心理学家则应该最有能力丰富“幸福指数”概念而对人类幸福做出另一种特殊贡献。
值得提及的是,幸福感及其幸福指数研究日益倍受企业和政府方面的重视。政府研究幸福感的意图也许表现在:近几十年来,以GDP衡量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十分显著,但人们的幸福感似乎没有太多增加,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GDP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相关度已不再像以往一定时期那样显著的话,那么,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有关社会政策时,只追求GDP高增长的单一取向应被放弃,而更合理的策略是,将幸福指数与GDP有机结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
三、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至今已呈现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最早的现代化属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自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之后的现代化皆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存在某种赶超情结,表现为制定赶超发展战略、提出超越式发展构想等等。赶超情结在常规情况下是巨大的行动动力,但在偏激化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一种“后发劣势”,其后果的一种典型形式就是,为了急切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滋生“GDP崇拜”,从深层上看,这是对工具理性或效率的极端追求所致。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历程中曾经一度出现过这种情形,引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后果。因此,正基于经济增长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进步的深刻认识,提升出了经济与社会之间必须协调发展的重要理念。
人类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事实冲击着“GDP崇拜”,这深刻而有力地说明,GDP的增长不仅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进步,而且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幸福增加。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增加人民幸福,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不仅应该了解人们仍然缺少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人们将会需要什么,从而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了解人们仍然缺乏什么,这是经济学等学科的硬指标能够发挥特长的领域,而了解人们将会需要什么,则是心理学等学科的软指标能够大有作为的领域。主观层面的指标在评估生活质量时,不仅不可或缺,而且作用重大,尤其是在对生活质量做出评估并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信息导向时,仅仅依靠客观层面的指标就显得不够全面。[5]而当今的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首先了解哪些客观条件因素与主观满意程度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推出相关政策来改善这些客观条件因素,从而促进人们幸福感受程度的提高。
这一切导致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指标研究领域,有关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相应变化:在独尊经济指数或“GDP崇拜”的传统发展观阶段,表现为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进入以强调多重指数为特征的综合发展观阶段,则表现为多学科共同发挥作用的时期,不仅经济学仍表现出其重要性,而且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也显得日趋重要;而步入幸福指数关怀的人文取向发展观阶段,则会是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大有作为的时期,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其他学科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而从追求效率至上的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到表现人文关怀的心理学大显身手的时期,是发展观发生深刻转折所带来的发展研究学科格局呈现出的新态势。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型现代化,晚发型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资源就是“后发优势”,其突出特点就在于能够充分吸取早发型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潜在的“陷阱”。
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后发优势”:站在一个崭新历史高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进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道路和远景。而重视幸福感这一人文指标的重要意义,就是这种“后发优势”在发展理论上的一种必然体现。
当社会发展进程迈上一定台阶之后,追求幸福感及其最大化,是由人的需求上升规律所决定的。人本化生活的最重要目标应该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财富。因此,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本原则,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目的。所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在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国家,尽管谋求经济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但是,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仅只是一种手段。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诸多其他因素,如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对于人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的高低、财产的多少等经济因素。因此,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政策意义就表现在:幸福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个人生活样态的“晴雨表”,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风向标”,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
因此,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以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GDP的预期目标,而且也确定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
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能够落实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有效方式。它把自古代以来哲学家们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思辩变成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际操作化并可以具体测量的方法体系,这正是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最深刻、最丰厚的内涵之所在。
由此也将带来政府工作职能的新变化。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是政府工作的传统职能。在人文取向发展观的要求下,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把确保人民幸福的增加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促进人民幸福的最大化成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职能,也是最高层次的工作目标。总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都只是增加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人民幸福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追求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及其可持续化,应该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最重要课题。
鲍宗豪主编:《当代社会发展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王凯、周长城:《生活质量研究的新发展:主观指标的建构与运用》,《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邢占军:《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周长城等:《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美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林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C. P·欧曼、G·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吴正章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锆、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法]F·佩鲁:《发展新概念》,郭春林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幸福指数将成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3月2日。
《“幸福指数”颠覆传统发展观》,中国旅游营销网(http://www.yfzs.gov.cn)2004年10月1日。
Dennis Rapael, Rebecca Renwick, Ivan Brown, and Irving Rootman,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nd Health: Current
States and Emerging Conception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 65-88, 1996.
Ed. Diener, “A Value Based Index for Measuring National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6:107-127,1995.
Philip Seed and Greg Lloyd, Quality of Life,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1997.
[1]本文中使用“GDP崇拜”这个术语的目的,主要在于概括性地表述那种独尊经济指数或效率主义的传统发展观的核心特征。
[2] 1982年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把第六个“五年计划”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中加进了“社会发展”的概念。强调经济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把社会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这种综合发展观的一种体现。
[3] HDI,即Human Development Index,又译为“民生发展指数”。
[4] 以1981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本标准,大约是在3000美元左右。
[5]虽然主观指标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无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指标都不能单一地测量并说明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质量的内容,从而为相应的社会政策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对生活质量涉及的具体内容分别从主观维度上和客观维度上加以测量,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对于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