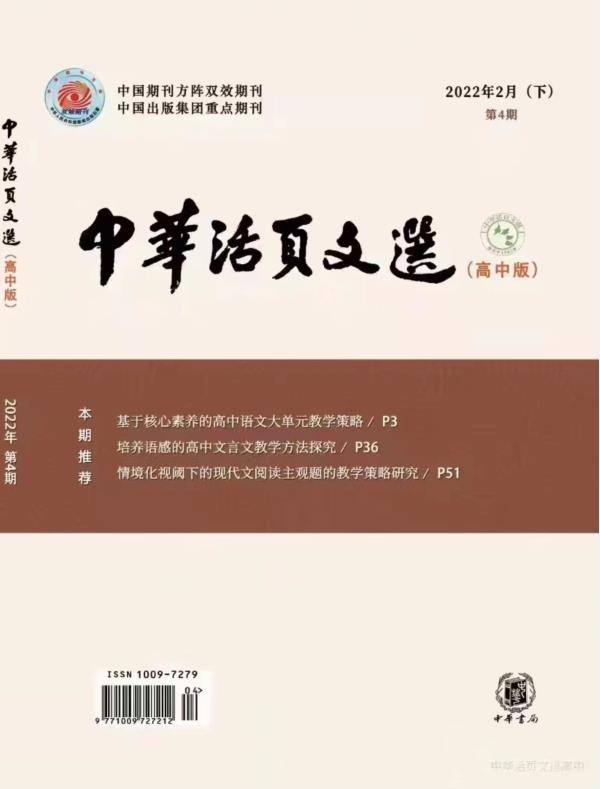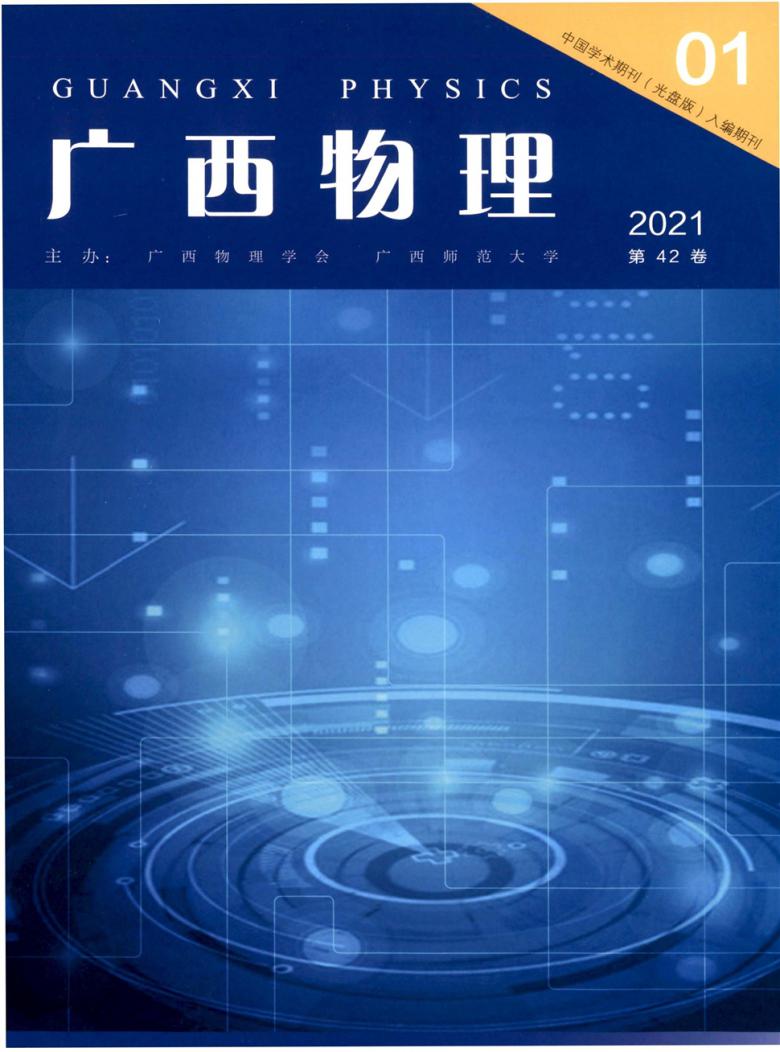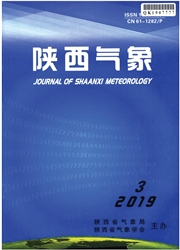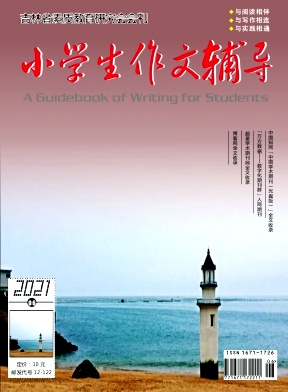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下)
黄宗智 2006-04-30
人口史
现在我们来讨论中国人口史这一论题,以及相关的溺杀女婴问题,看看它们对发展与内卷能够说明什么。按照彭慕兰的观点,溺杀女婴是他想给长江三角洲勾勒的画面的一个关键部分:又一次与18世纪欧洲相同,因为溺女婴实际属于“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其结果是生育率比欧洲还低,人口压力也不比英国更为严重。这与彭的总体看法相呼应,即较之英国,长江三角洲并没有经历更高程度的内卷。这一部分的论证,他主要依赖的是李中清(James Lee)的著作。
(一) 彭慕兰和李中清的论证及数据
首先,李中清(以及不少其他学者)论证了溺杀女婴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在分别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王丰合写的著作中,李的讨论以东北辽宁的道义社区1774—1873年间12000个农民的有关记录中男、女婴的不同死亡率为基础。李推测大约1/3的新生男婴和2/3的新生女婴从未登记入册,如果我们假设未注册婴孩的死亡率和有记录的相同,那么可能有“1/5到1/4的女性死于故意的溺杀”。[1] 李还使用了特别完整的皇族户籍册,一个1700—1830年间的总计33000人的样本,并提出“1/10的女婴多半在生命最初几天就被溺杀。”[2] 。彭慕兰引李中清为证,提出在中国有25%的新生女婴被溺杀(第38页)。
这里姑且不论到底有多少女婴被杀的问题。李中清对道义的估计既得自人口数据也得自猜测。准确可靠的估计尚有待于将来的研究。实际溺杀率无疑因时间地点不同而各异,并且可能比李的估计要低得多。这里只集中讨论他们如何使用自己拟定的数字。
李中清和彭慕兰告诉我们,溺杀女婴实际上是一种“产后堕胎”。与其说它来源于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意义上的生存压力——即在人口/土地挤压下,因粮食生产难以跟上人口的增长,以致粮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营养不良乃至饥饿和死亡——倒不如说它恰好表明了这一压力的不存在。它是类似于欧洲晚婚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3] 李、彭以及王国斌、李伯重[4] 等人想要论证的是,中国的人口历史与欧洲相同,其人口模式一如欧洲,即主要是由“预防性抑制”形成的“生育驱动”(fertility dri8ven)而非“马尔萨斯神话”曾经揭示的那样,是由“现实性抑制”构成的“死亡驱动”(mortality driven)。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后堕胎”的概念。如果被溺杀的婴儿即使已经出生了还可以被看作是“堕掉”的话,那他们就不应该被计算在死亡率中,从而也不应该出现在预期寿命的计算当中。[5] 因此,李中清在对辽宁道义与欧洲基于教会出生登记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只把道义的“6个月大”而不是新生的婴儿计算在内。[6] 如此一来,道义的预期寿命为29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李、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与欧洲人大致相当。
但如果李的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7]
除了把被溺杀的女婴排除出死亡率数据之外,将溺杀女婴视为“产后堕胎”也将那些婴儿从“总和已婚生育率”中排除了出来。再一次,如果被溺杀婴儿系被“堕掉”而不算出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在生育数据当中。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计算道义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时没有就溺杀女婴做任何修正。他如实指出,他只是在对未登记男婴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对未注册人口做了修正,而没有去考虑更多的未登记女婴。[8] 于是,他(和彭慕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婚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出人意料地低(第41页),其“总和已婚生育率”为6个,从而中国人的生育率,比1550—1850年间西欧的7.5—9个还要低得多。[9]
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早些时候在他为一部有关中国人口会议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记录中的数字一般应该在考虑到溺杀女婴的前提下向上修正25%。譬如,刘翠溶基于“华南”地区5个族谱提出的数据应该加以修正,因为族谱主要关注儿子,而对夭折的或者被杀弃的女婴不做记载。[10] 与李中清不同,泰德·塔尔弗德(Ted Telford)依据1520——1661年间桐城县(在长江三角洲之邻的安徽省)的39个族谱共计11804人的记录,通过预设25%中等女婴死亡率对其数据进行修正,做出8—10个孩子的总和已婚生育率估计。[11] 此外,依据1906—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海山地区非常可靠的数据、1980—1981年对最初为卜凯所研究的中国7个地方580位妇女所做的回访以及1931年乔启明在长江三角洲的江阴县搜集的高质量数据,武雅士(Arthur Wolf)得出7.5个孩子的估计。[12]
实际上,如果把他自己估计的25%的被溺杀女婴算入出生婴儿当中的话,李中清的数字就会跟武雅士以及塔尔弗德的相差无几。这样一来,李的数据就会非常不同,也就得不出他的结论,即中国的数据显示了比西欧还低的生育率。[13]
总之,李中清(以及彭慕兰)把溺杀女婴解释为“产后堕胎”并因此而排除在生育率和死亡率之外 ,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其两个基本论点的关键所在:即中国人的死亡率(或者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以及中国“预防性抑制”的施行甚至超过欧洲。如果对溺杀女婴做不同的解释,而且将其算在出生和死亡人数当中的话,采用他们自己的数据和估计就可以得出一幅与他们所论证的非常不同的画面。
不仅如此,武雅士在其对李中清著作的谨慎评论中还证明:即使接受李得出的那些数字,我们也可以找到比有计划的生育控制——即“晚开始,早停止,长间隔”加上“产后堕胎”——更为合理的其他解释。他指出,早婚和经期相对较晚可以解释为什么较晚开始生育。而且早婚(以致年龄不大婚龄却较高,房事频率亦相应较低)或者因健康问题或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较早停经,则能够说明较早停止生育的现象。最后,生育的长间隔,也可以被营养不良以及穷人迫于生计而外出佣工等因素所解释。武提供了通过深入访谈得到的直接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低婚姻生育率本身就得用贫困及生存压力来解释,而不能当做没有生存压力的证据。[14]
(二)一个不同的观点
回到溺杀女婴的问题。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15] 。可是,光是性别偏重就会促成一个人溺杀其女婴吗?还是由于有其他压力首先导致了杀婴,其后对男孩的文化偏重才促成溺杀女婴的选择?而且,考虑到中国各地几乎都为婴儿庆祝满月这一事实,一岁以下的孩子果真还未被当做是完全的人吗?
要充分探讨这一论题,我们需要有更多区别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中国人口行为分析,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启示性的端倪。根据长江三角洲萧山县(浙江省)的三个族谱——1240—1904年间的资料,哈勒尔指出地位较高(即持有功名者,也就是可以认为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有更多的孩子。这是由于富人比较早婚,而且可以纳小妾。[16] 武雅士在比较可靠的台湾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并拓展了哈勒尔的看法,他展示了富裕农民家庭(不仅仅是持有功名的“士绅”家庭)具有更高的婚后生育率。[17] 最后,周其仁重建了日本满铁研究者系统调查过的三个村庄的人口历史,并指出富裕农民因为有抚养能力而有比较多的儿子,但贫农也有较多儿子,这是因为他们老年不得不靠儿子的出雇收入来维持生活。[18] 综合起来,这些成果提示:溺杀女婴可能主要是那些为生计所迫的贫农力争有更多儿子的一项行为。
帝国晚期的一些观察者明确地将女婴溺杀主要归咎于贫困以及昂贵的嫁妆,而且政府官员敦促设立孤儿院来处理这一问题。[19] 1583—1610年间生活并供职于明朝廷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年)讲得特别明白:
这里更为严惩的一宗罪恶习就是某些省份的溺婴行为,其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供养他们并已彻底绝望了。有时候那些并不怎么穷的人家也会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他们无力供养这些孩子的日子会到来,到那时他们就只好把孩子卖给陌生的或者残酷的奴隶主。[20]
只有少量土地的贫农和没有土地的雇农夫妇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可以依据农村习俗保留一份养老地藉以养老,而他们却不能。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儿子,法律和习俗都要求儿子出雇以赡养父母。[21] 女儿不能这样。而且,即使他们勉力把女儿抚养成人,到头来恐怕还是得把她卖出去。在那样的生存状况下,溺杀女婴的事情比较可以理解。
我这里并不是想争论只有穷人才会溺杀女婴,而是说他们多半构成了这类行为的主体部分。即使是李中清也承认:“过去的中国父母减少生育或者杀婴是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反应。”[22] 在他原来和康文林合写的著作中,李实际上把溺杀女婴置于马尔萨斯式“现实性抑制”的范围,而不是他后来主张的“预防性抑制”。[23] 但那一认识,在其后来对“马尔萨斯神话”进行激烈批评以论证其“生育驱动”而非“死亡驱动”的中国人口体系时,已丧失殆尽。
李中清自己的数据实际上表明了贫困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上面已经提到,他的皇族数据表明溺杀女婴的比率为10%。李运用这一数字争论说,既然女婴溺杀甚至出现在富裕家庭里,那么该行为就必定是全社会范围的而不仅仅是贫困所致。然而这些数据彰显出另一条不同的逻辑:即使他自己的数据也表明,那些大多已贫困化了的“低等贵族”比“上等贵族”更倾向于溺杀女婴。[24]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假设所有33000皇族成员都还相当宽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群体10%的溺女婴与道义农民25%的比率之间的差别。道义至少3/5的被溺杀女婴是否可以用贫困来解释?
李中清(与彭慕兰)提出的解释,其动机似乎主要还是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这把他引向另一个关于中国人口历史的可疑论述。正如曹树基和陈意新[25] 指出的,李决心依照欧洲“生育驱动”模式来重写中国人史,促使他把19世纪中期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因此,他得出了一条1700—1950年期间直线型中国人口转变模式,以与其希望证实的“生育驱动体系”保持一致,而不是与死亡危机激发的体系相一致的具有陡然下降的曲线。[26] 他从而抹掉了19世纪中期南方长江三角洲地区太平天国战争、西北的回民起义以及华北大旱灾所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曹树基的最新研究在详尽使用方志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了各府人口的总数和变化,结果认为,1850—1877年间这些灾难所造成的死亡达到惊人的1.18亿之多。[27] 对其估算的详细评论有待其他学者,但即使他估算的误差达到50%,还是有6000万人的死亡损失,也就是当时总人口的1/7。
当然,19世纪中期并不是第一个大灾难发生的时期,伴随王朝更迭的灾难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在我看来,历史记载表明了一部由死亡强有力地塑造的人口史,即使不是严格的和狭隘的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现实性抑制”。这一体系不应该与马尔萨斯就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而构造的生育驱动的“预防性抑制”模式等同起来,更不能把溺杀女婴和没有生存压力等同起来。
(三)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
在19世纪中叶的灾难时期达到巅峰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否就是溺杀女婴的社会情境?最近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表明,溺杀女婴背后的同一生存压力导致了广泛的买卖妻女。这类现象如此泛滥,以致《大清律例》增加了足足16条新例专门处治此类行为。这些新例大都颁布于乾隆年间(1736—1796年)。[28] 而对法庭案件档案的考察也显示妇女买卖非常普遍,此类“交易”引发的诉讼大约占到地方法庭处理的“民事”案件的10%。我们知道,清法律系统虽然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开放,但仍然被普通老百姓视为令人生畏之地,大多数人只有迫不得已才会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做这样的考虑可能是合理的,即在所有妇女买卖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最后诉诸公堂。如果我们取5%这一数字的话,也就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65000宗这样的“交易”。如果取1%,那就有825000多宗。[29] 无论精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赤贫人家买卖妻女的现象如此泛滥,以致清刑部起码在1818年已经决定对这样的人不予惩罚。其理由是,那些迫于生存压力而出卖自己的穷人应该受到同情,而不应该被惩治。[30]
另外一个相关的社会现象是未婚的单身“光棍”人口的形成,它是贫困(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完婚而独身的男人)和溺杀女婴引发的性比例失衡共同造成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征候导致了法律对处理“犯奸”行为(illicit sex)的一些重要的改变。[31] 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清代关于“光棍”以及相联的“棍徒”和“匪徒”的一系列立法,表明在当时政府的眼中,这已经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与处理买卖妻女问题一样,清政府颁布了足足18条新例来对付这一新的社会问题。[32]
上至乾隆帝,下至地方官员和文人,18世纪的人们注意到了这些长期趋势的某些征候。[33] 后者中最著名的当是洪亮吉(1746—1809年),他由于其1793年所作“治平”和“生计”两篇名文而被一些人(不完全恰当地)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出身贫寒的他对穷苦人的方方面面都至为敏感。而且他游历甚广,编纂了许多方志,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当明了。在洪亮吉看来由于近百年的太平,人口大幅度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和生存资料的扩增。物价陡升,工资剧跌,贫富分化拉大,失业人口激增,对社会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结果,穷人是饥寒、饥荒、洪水和瘟疫的首批受害者。除了这两篇论著,洪还留给后世较多的诗作。其中有不少基于实地观察,表达了他对饥荒受害者和贫寒人士的深切同情。他特别加以描述和评论的饥荒,是长江三角洲以北淮安地区(位于江苏省北部)1774年大旱以及随之在长江三角洲西部以句容县为中心的18个县发生的水灾。30年后,他于1804—1806年间又记述了长江三角洲以北扬州地区的特大洪灾,以及次年在三角洲内他的家乡常州地区发生的饥荒和干旱。这次他不仅为救灾捐赠了相当的经费,还亲自负责该地区的赈灾救济工作。[34]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洪亮吉的观察仅仅适用于18世纪末期,我还想简要地引述一下罗威廉的关于18世纪杰出官员陈宏谋(1696—1771年)的最新大部头研究。罗引述了陈在1744年前后写就的一封信,信中申明太平之世人口剧增所引起的问题。陈指出,虽然最近添加了不少由围垦沼泽和开发山地而得到的耕地,但他十分担心人口增长速度远超过耕地的扩增。陈认为这个问题是所有官员都必须注意的。[35] 另外,在1742年呈交乾隆皇帝的奏折中,陈强调在(用罗威廉的话)“巨大的人口压力下”近年来百姓“生计”的下降。罗威廉基于这些以及大量其他证据有力地指出:“我认为,这(食物)……是清帝国最重要的施政领域,起码在西方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文化威胁之前是如此。”而且,罗进而指出:“在陈宏谋的时代里,……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所有官员都首先关注这个问题[人口对资源的压力]。”[36]
罗威廉的观察很大程度上跟我自己对清法律的研究相吻合。我提出,清代的民事法律展示了一种“生存伦理”,这与民国民事法律借自德国1900年民法典的契约和牟利伦理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法律保证那些由于生存压力所迫而出卖土地的农民可以以十分有利的条件回赎他们的土地;它禁止放债人向那些被迫借钱维持生存的农民放高利贷;它维护那些离家开垦沼泽或山地农民的永佃权;它禁止牟利商贩买卖穷人妇女,而同时指示其法庭不要惩罚那些迫于生存压力出卖自己的穷人。1929—1930年颁布的(经过三次草案修改的)新民法典结果在实践性条例中掺入了这些规定的很大部分,尽管在组织逻辑上仍然保存了原来的德国蓝图。[37]
上述那些趋势和观察有助于我们了解18世纪以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这里我所谓“社会危机”,并非意指纯粹由人口压力造成的生存危机这一简单的马尔萨斯式观念,而是如我在几年前所提出的,清代是一个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交汇的时期。在华北地区,尽管商品化为一些人提供了致富的可能,然而却致使很多其他人——承担了市场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人——贫困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蚕桑栽培所代表的内卷型商品化使农村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此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人口压力与社会不平等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尽管不一定是占总人口更高比例的)“贫农”“阶级”的形成,包括佃农、兼打短工的贫农以及无地的雇农。在贫农阶级的底端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结婚的单身汉,其中不少人变成由无业者和乞丐组成的“游民”的一部分。自18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持久的特征。[38]
我认为,溺杀女婴是这个庞大的社会危机的许多征候之一。它表明穷人中生存压力的加剧,而不是李中清和彭慕兰所主张的没有如此压力。同样,买卖妇女表明了赤贫阶层经受的压力,而不是没有这种压力,也不是市场刺激下的资源的理性配置。彭慕兰将溺杀女婴作为把中国与欧洲等同起来的重要依据。他在借仗了李中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和结论以后,很容易就得出了他的最终结论:1800年前的中国在人口压力方面并不比英国/欧洲经济的处境更为恶劣。反之,英国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这两个地区同处于今后既可内卷也可发展的状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大分岔直至1800年以后才出现。 是因为煤炭?
至于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最后要看他关于煤炭的讨论。他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瑞格里有力地论证了“有机经济”,即前工业的农业体系与“以矿藏为基础的能源经济”,也就是主要基于煤炭(和蒸汽)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能源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力畜力,最终基于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的能源则主要依靠远为丰富的煤炭供应——一个男子每年可以开采大约200吨煤,这是他所消耗能量的许许多多倍。在瑞格里看来,正是这一差别使单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区分工业经济与前工业经济的标志。[39]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英国偶然地得益于煤炭的丰富资源及较早的发展。根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40]
瑞格里强调煤炭,意在论证英国工业化中偶然因素,从而驳斥了过于目的论的“一体化”的“现代化”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凸出英国工业化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仅作凭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更不用说只用煤炭来解释。这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它们的差异加十分关键。在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及其推动的城市化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以后,强调煤炭的重要性是对经济变迁的动力提出一个相当深奥的论点。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41] 这个论点完全不同于简单的机遇论,或煤炭单一因素论。实际上,瑞格里在这本书中论述“农业革命”(“发达的有机经济”)花费的大量篇幅,绝不亚于他关于煤炭早期发展(“矿藏基础的能源经济”)的论述。在瑞格里看来,这两者都揭示了英国很早就出现的特点。
彭慕兰是这样来运用瑞格里的论断及资料的。他先是指出英国在煤炭资源上占了有利位置;与此相反,他断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由于西北地区煤矿所产难以运输而受到阻滞(第57、59、64—65页)。然而后来他仍坚持,尽管长江三角洲“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但还是要“到19世纪才变得比欧洲(包括英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第229页)。这一观察促成了他有关“生态缓解”的论断:他认为煤炭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生态缓解”,而长江三角洲却无此幸运(第274—278页)。彭特别提到了新大陆提供的糖,不然英国就得耗费310万英亩土地来生产糖以满足供给(第275页);其次是棉花,否则在1815年就会占用900万英亩土地,到1830年则将达到2300万英亩;最后还有不可或缺的煤炭,要满足当时的供给,英国除非再奇迹般得到1500万英亩的森林(第276页)。[42] 他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煤炭与新大陆供给英国的原料总量超过英国耕地所能出产的总和。因此,正是“煤炭和殖民地”(coal and colonies)的历史机遇,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区别开来。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彭慕兰对瑞格里论点的扭曲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他对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的使用。
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43] 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44] 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45] 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最后,瑞格里本人可能给予人们一种夸大了矿产能源对于农业的意义的印象。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表明,当机械与化学革命降临到一个已经高度密集化、内卷化的农业体系之上时,其所带来的只是总产量的有限提高,即仅仅增长了三四倍而不是更多,远不如工业部门,而且(中国的情形)还是伴随着极端的劳动密集化才得来的。即使投入了现代能源,土地的生产力终归相当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 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倍增长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可能要比瑞格里本人认为的还要重要。
两种比照鲜明的经济
我这里要强调,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
彭慕兰选择了1800年前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比较,以求证实其中国与欧洲此前并无经济差异的论断。然而我们看到,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实际上是贯穿欧洲与中国之间从发展到内卷这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就英国的农业而言,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比长江三角洲低得多,其平均农场规模是后者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其单位劳动生产率高出很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较多的畜力、畜肥投入,这一农业经济在18世纪经历了毋庸置疑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进而,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后者为许多人提供了独立于农业的替代性生活来源,足以支持人口扩张与迅速的城市化。此外,家庭收入有实质性提高,消费型式也有大的转变,这些都推动了城乡贸易的扩展。最后,煤炭生产较早得到发展。综合的结果就是,英国在1800年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备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迥异于此。在这里,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卷可以说已经达到全球极高程度。在前工业时代,水稻、棉花及蚕桑栽培显然是比较最为劳动密集的生产体系。它们彰显了我所说的内卷式增长,即单位劳动以报酬递减为代价的绝对产出的增加。内卷式增长使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体现在单位面积的产出及其支持复杂的城市网络、发达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精英文化的能力。但这种发达的状况是靠单位面积上极度的劳动密集化以及单位劳动的低度资本化和单位工作日的较低报酬而实现的。农村家庭工业几乎仍然完全维系于旧式的家庭农场经济,二者都是生存的必要支撑,缺一不可。这样一种内卷式增长与发生在英国的那类转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就英格兰的经济而言,我们可以列出五大变化(革命),再加上矿业(煤)的早期发展;而长江三角洲呢?这其中一项都没有。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人口或者农业(和家庭工业)可以单独解释现代工业的发展与未发展,在此它和其他因素相似,哪怕是市场交换(及劳动分工)或生产关系,或是资本积累、产权制度、技术、消费需求以及煤炭。中、英比较诚然凸显出农业及家庭手工业中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化以及内卷式报酬的差异,但是现代工业革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被理解为多因素巧合而非单一因素的事件。18世纪英国的经历提示了那些至少在起因上是半独立的多重趋势相互巧合的重要性,尽管其中的一些显然也是彼此关联的,即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新型人口模式、新型城市化、新的消费型式以及大量的煤炭产出。但所有这些在18世纪的中国或长江三角洲都没有出现。这里所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源头,而是19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附录:度量衡
中国度量衡按地区和时代多有不同。此文所用“斤”全指“市斤”,等于1.1英磅。“石”是容量,1石米重约160斤,即176磅。
此文水稻产量全指米,与稻谷比例约7比10。
棉花产量全指皮棉。布“匹”所指是标准土布,重1.0914公斤,相当于1.32市斤,3.6337方码,32.7方尺。皮棉成布过程中,弹花损失约4%,上浆加重给5%。因此,布匹重量与所用皮棉大致相当。 注释
[1] J. Lee , C.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 En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70;J . Lee,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1.
[2] J. Lee , C. Campbell前引书,第49页。
[3] Pomeranz前引书,第38页;J.Lee , C. Campbell 前引书,第70页;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61页。
[4] Wong 前引书,第22—27页;李伯重:《堕胎、避孕与节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1卷第1辑(2000年)。
[5] 曹树基、陈意新在《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2001年4月的原稿中首先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没有提出确切的例证。文章正式发表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未提此点。
[6] 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55页,表4.2。彭慕兰误将李中清的数字引作“1年”大的孩子,而李的数字实际上指的是1岁——这是中国式的计算方法,李、王将之约等于6个(Pomeranz前引书,第37页;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55页。)
[7] Schofield 前引文,第67页以下。
[8] 在J. Lee , C. Campbell前引文第90页注10;但在J. Lee, Wang Feng 前引文第85—86页处没有提及。
[9] J. Lee , Wang Feng 前引书,第8页;Pomeranz前引书,第41页。
[10] S. Harrell, The Rich Get Children: Segment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 1550—1850. In Arthur P. Wolf and Susan B. Hanley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Liu Ts’ui-jung , A Comparison of Lineage Populations in Sorth China , ca. 1300—1900.In Stevan Harrell (ed . ),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94—120。
[11] T.Telford,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Lineages of a Tongcheng County, 1520—1661. In Stevan Harrell 编前引书(1995年),第48—93页。
[12] A. Wolf , 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Rural China . In A. Wolf , S. Hanley,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54—185。
[13] 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6章, 特别是第90页;另参J. Lee, C. Campbell前引书第92页。
[14] A. Wolf ,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7, no. 1 (March 2001):133—154.
[15] 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 第60—61页。
[16] S. Harrell, The Rich Get Chileren: Segment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 1550—1850. In A. Wolf , S. Hanley 编前引书。
[17] A. Wolf , 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Rural China. In A. A Wolf , S. Hanley 编前引书,第182—183页。
[18] Zhou Qiren, Population Pressure on Land in China : The Origins at the Village and Household Level, 1990—1950. Ph. D. dissertation , UCLA , 2000。
[19] Ho Ping-ti ,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 1368—1953.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58—62; A. Waltner, Infanticide and Dowry in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C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pp. 193—218。
[20] 引自Waltner 前引文第200页。
[21]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8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2] 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100页。
[23] J. Lee, C. Campbell 前引书第4章。
[24] J. Lee, Wang Feng前引书,第58页。
[25] 曹树基前引书,第455—689页。
[26] J. Lee, Wang Feng前引书,第28页。
[27] 曹树基前引书,第455—689页。
[28] 薛允升:《读例存疑》,黄静嘉编校,卷5,(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1905]年,例275—3到275—18。
[29] 在我们从四川县,河北宝坻县(清顺天府)及台湾的淡水(分府)、新竹(县)收集的清代1760—1909年间628宗“土地、债务、婚姻及继承”案件中,总计有68宗案件,亦即超过10%的案件,处理的是妇女买卖(P. Huang , Code ,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 [以下简称Code , Custom ,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7, 225—226; P. Huang ,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c gh tuj tqi Civil Justice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 240;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待刊),表9.1)。如果使用我的研究中提出的估计——“民事”案件占地方衙门处理案件总数的1/3,地方衙门平均每县每年处理150宗案件——的话,则每县每年就有总计5宗这样的案件(Huang , Civil Justice, pp. 173—181;Huang , Code ,Custom , Practice, pp. 163—172)。 假定诉诸公堂的案件占此类交易总数的5%,那么每县每年就有100宗此类交易,亦即就全国范围(清代有1651个县、厅、州)而言就有165100宗。如果假定诉论案件占此类交易的1%,则总数就要高4倍,即825000宗。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猜测。要做出更为可靠的估计,(如果可行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案件数量和县的数量都比较大的样本才行。
[30] Huang , Code , Custom, Practice , pp. 157, 168—169。
[31] M. Sommer , Sex, Law ,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2] 薛允升前引书,例273—7到273—24。
[33] 严明:《洪亮吉评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
[34] 何炳棣在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 1368—1953(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第271页中概述了洪亮吉两篇论述的内容,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理论化口吻而非实际观察的语气。这里我相应地稍做修正。关于洪亮吉的贫寒出身和对穷人的同情,参见陈金陵《洪亮吉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关于他编纂的许多地方志,参见严明前引书第130—148页。
[35] W。 Rowe , Saving the World :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6.
[36] Rowe前引书,第155—156页, 第188页注13。
[37] Huang , Code , Custom , Practice ;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38] Huang , North China ; 黄宗智:《华北》; 亦见Huang , Yangzi Delta, 与黄宗智《长江》。孔飞力在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2章中有出色的讨论;亦见其他著作。
[39] E. Wrigley ,Continuity , Chance and Change :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77页及各处。
[40] Wrigley 前引书(1988年), 第54页, 引M. flin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vol . II, 1700—1830(Oxford, Englan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4), vol. 2, p. 26.
[41] Wrigley前引书,第115页。
[42] Pomersanz 引Wrigley 前引书(1988年)第54—55页。
[43] T. 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 1895—1947.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 17.
[44] Wright 前引书,第10—12页情1、2、3,第195页。
[45] J.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Wen Lineage in Pingxiang County , Jiangxi . Modern China , 27.2 (April 2001), pp. 20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