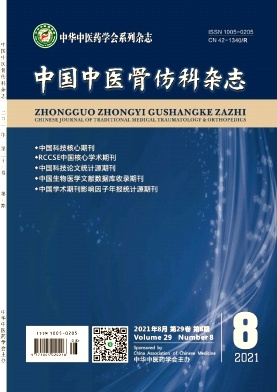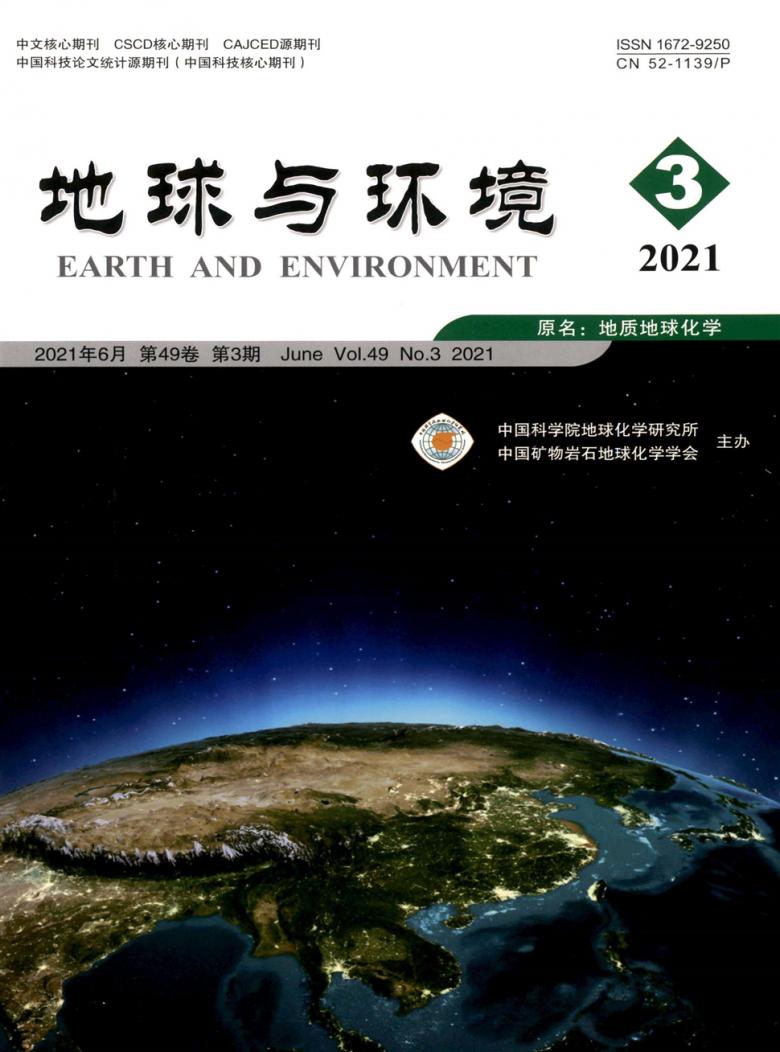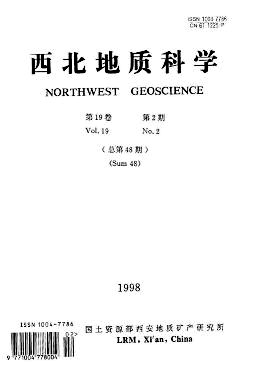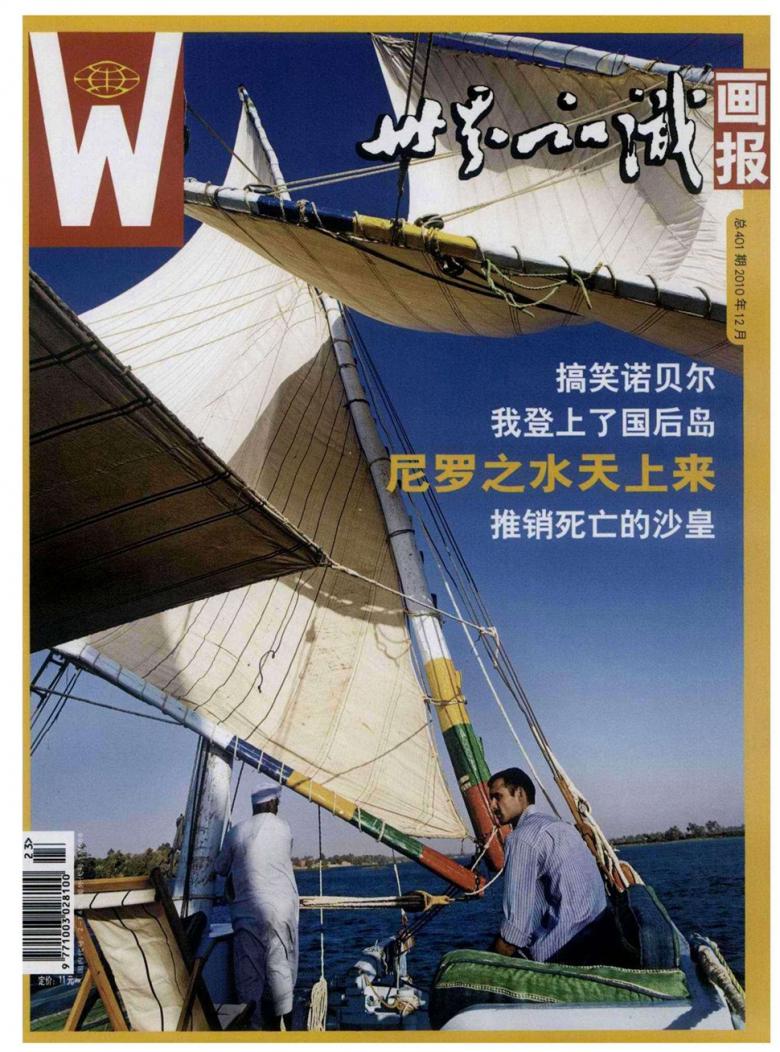“普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 (一)
许章润 2011-01-28
晚近二十多年的“普法运动”,推导自官方,流行于社会,蔚为一种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似乎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涵育过程,而恰成一场“运动”,一种不同于二十世纪中国人记忆深处任何“政治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今天回头来看,因有将近三十年的纵深,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作出阶段性评判。总括来看,这场“运动”的本意在于灌输选择性的法制意识,以守法公民作为最终期待产品,旨在营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忽略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义追问,也无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当性考量做出切实回应,特别是着意回避了有关政制与政体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因而,对于本予回应的重大问题,便采取了选择性回答,或者,悬置起来,不去触碰,诉诸“延迟战略”。在此,仅就“守法”一项举例而言,则大致的追问包括:为何需要“守法”?遵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是否可能、应当和值得遵守?以及,法律本身是否存在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究属何种关系,又有何层面与境界之别?进而,公民是否具有不服从乃至于积极反抗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不经意间,“普法运动”却在一般社会阶层,特别是普罗大众中间,引领出一种自然法式的法权意识,催生出全体国民比较视野下对于法治境界的深情憧憬和强烈向往,促发了遍地开花的“公民维权运动”,唤起了中国语境下关于法律正义、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全民性思考热情,甚而改变或者有望改变政府的行政方式。进而,它呈现出促进中国政制转型、培育中国政治的现实可能性。[1] 凡此种种,所为何来,欲将何往?其间呈现出何种消长起伏的态势?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着何种正负两面的影响?置身其间,当事人已然、应当与可能采行何种措置?此时此刻,“普法运动”实际上已然走到尽头,不可能再有和作为,法制和法治既非其所能旦夕恪尽其功,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自有轨辙,亦非其独力即可傅粉施朱,而曾经喧嚣的一切,似乎“由绚烂而归于平静”,因而,瞻前顾后,吾人职责所系,正需予以事实梳理,慎予深切的理论反思。 一、一个时代的记忆:用法制敲动政治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普法运动”必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载述着运用法制铺展“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努力,以及由此展现的国家理性涵育过程中的重重纠结。 法权时代降临的全民加冕典礼 首先,“普法运动”为中国法权时代的降临举行了一场全民加冕典礼。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换言之,它的出现本身就已说明,当下政制真切地意识到专权擅断、“无法无天”的治理秩序已然走到了尽头,早晚必定收场,提醒我们法律文明秩序之终将登场,而预为梳理,有所因应。至少,经由此番修理,可以暂时制止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而为正当性的再造另辟蹊径。毕竟,提供秩序、规范和安全等公共产品,是政制存在的理由,更是政治诞生的前提,如果政制和政治刻意延祚,就必须正视这一自我必然性,兑现历史预期。而且,在政治发展和文明转型的历史视野下,一个基本清晰的脉络是,自宗教文明、伦理文明而转型于法律文明秩序,是晚近世界的大势,一种世界性强势主流文明主导下的秩序格局,虽“国情”而不能免,起初可能概属“不得不然”,其后必然转而“有以然哉”。“普法”的应运而生,不过是在不自觉间接应着这一时代,将至晚启自清末变法更张的这一中国文明秩序转型,以大张旗鼓的方式更作渲染而已。 在此语境下,可以看出,当年倡行“普法运动”,主导者“选择性”的立意可能首先源自“文革”教训,溯自秩序失范的惨痛记忆,不排除旨在着意于训育人民,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起步,而以加强专政、巩固政制为归依。但是,曾几何时,法治本身的固有内涵终究非言词所能刻意遮蔽,必将顺流而下,排挞而出。尤有甚者,反倒可能因其歪曲性解说而愈益不屈彰显。一旦将法制或者法治从笼中放出,则其自我必然性终究要转换为现实性,这既为当年法制在欧美登场的历史所早已证实,亦为今日眼面前的中国进程所一再映现,说明理一相殊,万物总有其源流。无他,上述三大文明秩序递次转型的发生,源于世道变了,政道和治道因而随之转圜而已,法治及其自我必然性之步入历史进程,正属于“有以然哉”。君不见,当今中国,迄而至今,浸淫既久,蔓延已广,“法治”蔚成全体国民的时代意识,虽既得利益曲意诿饰,终究难登台面。试想,当今之世,至少在理念层面,舍祛“法制”或者“法治”的支撑,任何权力均会失去其合法性,更无正当性,本不是什么尚需证说的大道理;同时,如同下文将要举列的,虽然公权力“带头违法”不曾稍息,可一旦曝光,必招致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弹、齐声讨伐,从而最终可能迫使前者作出正面回应,哪怕是有限回应,也说明“普法”造成的法治观念之深入人心,而成浩浩荡荡之时代诉求也。“普法”因应其间,迎接这一时代,为这一时代张本,也使自己汇入了这一时代。 的确,经此洗礼,亿万中国民众油然而生对于法治的向往、期待与评判,并进而在应然的意义上生发出关于经由法律治理而构筑一种惬意的秩序格局与规范世界的制度想象。在社会心理层面,一般民众悉认法制或者法治才是开放社会与良善生活的不二法门,也是小民百姓赖以自保的起码前提,更是经邦治国的天下公器。正是在此,“普法运动”催生了国人有关经由法制而营造惬意社会的功能期待,提示了他们托庇于法治而实现良善生活的价值托付,唤醒了他们有关良善生活的自觉自为,鼓荡着他们对于人间秩序的阶段性美好憧憬。因此,至少在理念层面,自官学两界而至引车卖浆者流,藉由“法治”或者“法制”这一修辞,他们寄寓着自己关于公平正义和良善生活的美好憧憬,申说着对于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制度想象。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体平权,罪刑法定与罪刑相应,政府和百姓都要依法办事,公权力必须接受制约,官员及其权责均须纳入问责体制,而法律本身应当源自正当立法程序、符合公义,以及以公道为正道,等等,等等,成为刻下一般民众和不少官员的共识。细而言之,一般而言的“同命同价”、节假日加班须付双薪诉求等等,均不外其附带产品。实际上,可以这样说,第三次“改革开放”以来,[2] 鉴于市场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状态,价值多元导致的离心化倾向,若非对于“法制”或者“法治”所表征的规则之治的一意憧憬凝聚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最低限度的同盟关系,维系了这个社会的俗世存续,而蔚为三十年里中国民族最具主导性的政治意志,则中国社会早已土崩瓦解了。同时,这也就说明,当下治道所能祭出的正当性大旗,除开经济发展“将蛋糕继续做大做强”,概非民主法治不可,而彰显出中国文明建设自家现代性政治文化之时不我待。“普法”在此不啻为一场全民现代性弥撒,更是政制得以攀缘上政治的捷径。如果说“政治是理性的女儿和法律的母亲”的话,[3]那么,就中国三十年来的进程来看,不仅法制导源于政治,而且,可能通达至、催逼出政治,而接续以下列“权力与法权的辩证法”这一主题。 权力与法权的辩证法 “普法运动”昭示了一种现代政治关于法权与权力的辩证法,而为政治体制转型和新型政治的诞生,预作思想操练。权力的正当性本质在于法权,一种源于民主体制和公开立法程序的公共权力意志,展现为法权的效力;而法权的现实性力量源自权力,一种凭依垄断性使用暴力而获秉的贯彻公共意志的权能,表见为权力的实效。没有权力作为支撑,法权必定软弱无力,而失去了法权这一内涵的规范和导引,权力则可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因而,法律、法制并非限制权力,更非破坏或者废置权力,而是旨在限制滥权,即经由对于权力本身的妥适安排,来制约强权,防范暴力,阻遏暴政。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之上,即终究而言,权力不是法律所能限制得了的,相反,法律的本质是权力,一种获秉正当性的权力,适成权威,其施行亦有赖于权力为之张本。事实上,权力只能以另外一种权力来限制,正如“以野心制约野心”,利益只能以另外一种利益来抗衡。法律不过是它们的别名,法制则为一套将它们化转为公开较量的程序性体制,旨在提供角力规则,而将约制与抗衡导入按理出牌的套路,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最低限度的和平共处。反过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律的终止之地,便是暴政的起步之处。经由此道,现代政治下的权力本质上例属法权,而且,只有将自己转圜为法权,才能获秉正当性。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辗转其间,在提供将权力变成法权的机制之际,进而昭示天下,一切权力只有使自己变成法权,才能获秉效力,并可能具有实效,更主要的是,才具有正当性,恰成权威。而所谓的政权,不过是采取了法权形式的一般性权力而已。说是“一般性”,就在于权力总是特殊性的,隶属于掌权者,表见为诸如政党等特定的公民团结形式之“执政”,而政权则恒具普遍性、一般性与开放性,等待着受托人来执掌。所谓“稳定”,主要不在权力是否更迭,而在政权能否保全。进而,所谓“维稳”,枢机应当在此,而非在彼。同样正是在此,“普法”所揭示的现代政治关于政权、权力和法权的一般原理,为我们省视中国可能有与应当有的政治生活方式,撕开了一方觇孔。 历史而言,法国大革命以还的晚近人类政治故事,一个基本套路是,大凡“革命”之际,多率性伸言权力就是暴力,如毛泽东所言,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摧枯拉朽,而非“请客吃饭、绣花绘画”。这是因革当口,或者,政制草创、未及矫饰之际的表达,也是真切上演的实践,更是基于“解放哲学”的理念宣泄。但是,事过境迁,倘若一切走向常态,则多尽速自我正当化,制礼作乐,“盛世修典”也。此时,政治为政制而登场,法权随之翩然降临,为政治缝制晚礼服。大率而言,现代政治提供的正当性赋予机制,不外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由权利授予权力。因此,无论是法权还是权力,其合法性均在于权利的授权,而且,是一种严格循沿程序、附着于一定仪式的实现合法性的授受活动。具有这一特质的机制不是别的,就是民主。晚礼服若非以权利为质料,则权力的肉身难得脱胎为法权。倘若一切顺利,则人民作为选民,由此登场,“芸芸众生”的市民和国民在此一转身成为公民,而只有公民,不是什么前政治的“群众”,才是一种政治存在,一种摆脱私性存在属性的公共性存在,也才可能有望免于任人宰割的命运。[4] 以此观之,则“普法运动”的最大功德,就在于不期然间演绎出了这一现代法理,将此现代政治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成为人人不言自明之理,浅层次地进行了一场全民政治心智操练,为可能刻下正在积蓄力量、即将登场的新型政制及其政治预予思想准备。经此洗礼,使得一切无此程序和仪式的权力形态,在顿时遭临空前巨大的合法性质问与正当性压力的同时,根本上失去了一切自我辩解的可能性,只好硬挺。而硬挺,既非政治之福,更非国族之福,实际导致了僵局。化解僵局,除非不得已遭临“宪法时刻”,在尊重社会生活自我演生的同时,最好的流程还是启动法权程序。正是在此,“普法”讲述的常态政制流程与追求的公共事务进程,向全体国民,尤其是她的年轻一代,提示了这一依赖于法权程序的现代治道的可欲性。——实际上,它是以“再启蒙”的方式,恢复这个民族有关此种可欲性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基于公共协商、程序理性和实用理性的现代法权,不仅其用在有裨于化解僵局,落实政道,而且,更在于增益政制的有效性,修正政治的正当性,进而,于实现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与政制的和解、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与政治的沟通之际,可望为缔造公共空间提供最低限度的共识及其制度凭藉。“依法维权”蔚为思潮,见诸神州大地的公民实践;依法行政成为全体国民的政治期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而向往就是压力;立法听证虽说流于形式,但有形式总是强于连形式也无。凡此种种,不过为此法权意识推导出来的实践例证而已,并进一步推展为下述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和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 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与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 “普法运动”渐次揭示的现代法制及其法意,向全体国民彰显了一种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宣示着关于生活伦理的现代法权立场。本来,启蒙的政治经济学消隐,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彰显,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其实是晚近三数个世纪间逐渐推演的全球性世俗化进程的中国版本,而于此时此刻,中国百年社会历史转型的收尾时段,翩然登场而已。就市民的政治经济学而言,安宁有序的俗世生活,“小康”社会的市民憧憬,厘定产权关系与获享经营自由的康乐愿景,对于自己的一生保有大致有所预期和预设的可能性,均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来看,举凡人道博爱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与公平正义、礼仪廉耻与温良恭俭、良善生活与美好社会,凡此诸项,经由“文革”后文化复兴式的“平凡昭雪”,以及市场经济的正反两面淬砺,已然成为考量社会的可欲性,进而成为追究政制的正当性的指标,并随着法制的逐步走向健全,特别是私法规则的慢慢缝缀和细密化,而落实于生活伦理的法权化过程之中,演绎为一己“私人”的私德判准,人际互动的“关系”伦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换言之,传统的义利之辨由此可得换形为“一准于法”的权利得失,所谓“依法办事”也。经此转折,现代法权在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的同时,提供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市民生活的新型平台,也不妨说就是一种新型伦理。在此,“普法运动”对于私权进行的躲躲闪闪而又不可回避的现代法权宣谕,特别是对于“私产入宪”式的政制德绩的媒体渲染,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整体合法性叙事的登场,私法理念之渐次进入生活层面,而广为流布,深入人心,蔚成一种“法教”式的现代市民心性启蒙。 颇为吊诡的是,经此一役,个人于此实现了“脱政治化”,固守的却是“私人”属性,而形成了与前述使自己成为“公共性存在”这一趋向相向而行、二元并存的格局。此种人格形态,不是别的,恰恰是现代工商社会法制统治下的造化,例属所谓的“现代法制”对于“人类形象”的预设和预期,[5]包裹着市场与技术的双重期待。如果说法治和政治造就公民,那么,在法制和政制的一统天下,庸常个体,踯躅于市场、辖制于技术、俯仰于欲望并耽溺于娱乐,其市民人格极致,充其量只能是“私人”,一种常态社会下保全并满足于食色心性的庸常人类。也就因此,这里的“脱政治化”,不仅意指摆脱旧日“政治运动”铺天盖地时代个人被迫遭遇的泛政治属性,一种被迫充应、提线木偶式、前政治的政治炮灰势能,而且是指与上述作为公民、因而例属一种公共性存在的政治属性之区隔,以保有人人作为血肉之躯、食色之体的市民康乐本性之定位。 凡此种种,历经三十年的社会变迁,特别是数场有关公私界限的法权厘定的全民讨论,每天都在上演的诉讼活剧及其“全民网议”,以及相应的立法规定,逐渐渗透于国民心智,特别是“80后”们的“平淡”生活方式之中。终于,以“80后”们为典型标本的“私人”及其“公共性存在”并存的人格形态,一种将市民和公民两种人格糅合一体、却又井然分际的新型国民,初现于国中。——它不是别的,即“私人”也。“私人”以自然个体为本,首先自认洒扫应对的市民位格,其次不拘于国民身份,是否用脚投票端看利益取舍,再次欣然于公民担当,不过却淡定处之。因而,他们是真正无可奈何的人,便也就是通情达理的人,进而,他们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所能养育的最为正常的人。“私人”的诞生,是三十年里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新型国民的典范,展现了文化转型烙于人格特征的代际转换的有限实现,同时表明,中国时间中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世间,即将过去,终将过去。 是呀,想一想“陕西黄碟案”对于公权边界的巨大昭示意义,看一看“重庆钉子户案”有关公民私有合法财产的予取关系的法权演示,[6]看一看志愿者们应招而起、却又并不太当真的从容淡定,再思考一番遍于国中的浮世享乐之合法化,所谓的自由个体追求幸福的冲动及其满足等等之堂皇大词蔚为自由主义的魂幡,则托庇于“普法”宣谕,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与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之有望渐成国民心智,一切皆在不言之中矣。[7] 二、固有的内在紧张 前文曾经指出,这场延绵二十年的“普法运动”先天带病,病在忽略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义追问,也无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当性考量做出切实回应,特别是着意回避了有关政制与政体的政治经济学思考。虽说如此,但却造成了上述阵势,这便抖搂出了这场“运动”先天存在的诸般内在紧张了。 选择性内容与固有内涵的紧张 首先,综观全程,一个显明的事实是,对于法制内容和法治意识的选择性灌输,与现代法治固有内涵的要求之间,先天存在着内在紧张。普天之下,并无一种作为绝对摹本的“现代法治固有内涵”,实际上,当今之世,举目所见,至少就有所谓的欧陆式法治、普通法的宪政主义乃至于东亚型法治等等,说明法制也好,法治也罢,的确都不过是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创造出来的规范世界而已。但是,这不等于说法治本身没有自己的真际,更不意味着凡此生活世界和规范世界没有自己相应的意义世界,正是这一“真际”和“意义世界”,使得不同类型的法治之间分享了得以沟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种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现代制度空间、实践形式和人间秩序,法治具有自己确凿无疑的理念、规范与实践形态,以及在不同文明时空中的多元表现。由此,才有所谓的法制和法治,进而才有关于它们的法意及其论争,中国关于“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及其全民普及运动亦且才有根据,也才有意义。姑且不论法治在自己的流布过程中是否烙有哪一种特定文明的印记,但是,它们各自均围绕着自己所认定并可分享的基本理念、价值和准则展开,则是确定无疑的。[8] 也就因此,对于法治的非本质主义的多元现代性开放态度,并不妨碍现代人类分享着有关法律之治的共同的、普适的基本理念、价值和准则。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此种“紧张”何所由来,将欲何往。 自1970年代末以还,最高当局重申法制,先期的法制十六字诀,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虽非法治的严整表述,但却基本穷尽了法制的主要内涵。逮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出台,仅从学理而言,反倒自此原本不错的脚线退步,适成不伦不类,适足加剧了本然就有的内在紧张。东拉西扯,左支右绌,不免前言不搭后语,说明意识形态贫乏,“理论创新”走进了死胡同。与此相反,近些年来,随着法理学对于相关问题的阐释愈明,“固有内涵”在民间流布既广,所获认同愈深,“选择性的”宣教愈加不攻自破。体现在理念层面,就是百姓的市民性成长,不再认可公权对于私域的随意侵犯的合法性;国民的公民意识崛起,要求兑现自家公民身份的冲动强烈。表现为实践形态,则市民消遣的道德性无需听凭公权的界说,洒家自有主张,而各种“公民维权行动”,其中一些表述为官方口径的“群体性事件”,启蒙于法治理念,如星火燎原。可能是感觉到事涉关口,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遂图穷匕见,已然顾不得理论逻辑的周延了,因而才有诸如上述“法治理念”及其宣教这等下策,反将二者的紧张更形于外,有以然哉。 的确,综观各类官方主导的“法制宣传”材料,包括“劝世文”式的街道法制文宣材料,不难看出,其主导立意着重于下述三点,表现着并造成了“普法运动”的诸般悖论。 一是片面强调“守法”。守法不仅是义务,而且是美德,更是政治忠诚的标志,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教义,也是现代法治的内涵。但是,仅取一端,置国民的“义务性”存在远甚于其“权利性”存在定位,就不免其心殊异,而另有盘算了。毕竟,当下中国,作为“历史三峡”的一阶段一环节,不仅是一个需要转换义务观念、训育责任意识的时代,更是一个摆脱旧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秩序旨意,以寻求新型公民权利形态的“权利时代”。——工商经济主宰的现代法治社会,将自然和社会层面的人欲,几经转圜,变身为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权利,并以此奠立权力的合法性,形成二者的制衡之势,庶几乎得保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蔚为一大发明呢!因而,置此情势下,此种关于“权利”的申说,如果说对于早已渡过“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现今西方福利社会未必十分急迫,可能,也未必急切需要的话,那么,对于昨天刚刚摆脱帝制专权和左派极权体制的中国来说,可是时代急务,而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应有之义呀!可能,正是昧于此点,或者,有意回避此点,才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大凡官式“普法”材料,均了无有关使得市民成为公民,以及国民必须臻境于公民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本质的内容,好像也无遑着意于此。相反,充斥篇章的多为“守法光荣,违法可耻”式的片面宣示,以及某某“落网”后的现身说法及其惨状的直观展示,而凸显的无一不是国家威权的无所不在,旨在唤起听众/观众敬畏之心的孜孜用意,以及在这一切背后,那个政体的英明伟大之不言自明。因而,一般的法制宣教以最具“斗争性”的刑事法为主,而就最为突出的刑事法宣教本身来看,主要讲述的是“假设如何,将会如何”的惩罚式罪刑关系,昭示“违法犯罪”的“下场”云云,却缺乏孤立的个人面对强大公权时如何救济的切实内容,而这才是现代意识,一种启蒙后的民权主义法理,也是法政安排的德性之所在。正是在此整体语境下,即便是一些“普法材料”对于公民权利信誓旦旦的举列,譬如排比条陈诸种政治权利,因为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言者缈缈,听者昏昏,也使得凡此作为顿成秀场,当下制造了一种自我反讽气氛,似乎反而加剧了一般民众的被剥夺感,以及对于应予信守的法制和政制的疑惑。如此这般,此时此刻,“法制宣传”只有青蝇吊客,“法律信仰”云乎哉!
政制与政治的紧张 如同法制与法治之别,“政制”与“政治”二位一体,在层次、境界、准则和修习次第上,既彼此牵连顾盼,又各有自家畛域。换言之,但凡搭建起民族国家框架,摆脱“无法无天”状况,基本能够维持法律、秩序和公共生活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体制,即为一种法制和政制,甚至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法制和政制,而不论其政体形态,更不对它作什么自然法式的省视和政治正义追问。其反面是所谓的“弱国家”与“失败国家”,不仅难言经济社会发展和建构优良政体,而且,连基本秩序也无,国家能力羸弱,行政效能严重不足,多数时候处于失范状态,公共生活自无保障,法律和规范亦且形同虚设。海地大地震后的饿殍载道,索马里的盗贼蜂起,阿富汗之四分五裂,可为其例。这其间,自“弱国家”、“失败国家”至“成功国家”,至少存在“失范”、“基本治理”、“有效治理”和“善治”等层次,展示出人类政治秩序与政治智慧的地方性差别。[18] 正如笔者一再指陈的,百年中国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至少包含四个方面,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它们连贯一体,旨在贯通“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指向的理想愿景是强有力的现代民主国家。[19] 具体说,前两项的落脚点是有效治理的“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当下中国基本恪尽其功。不仅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渐次发育、居民生活水准和国民素质大幅提高,而且,经由清末以还五、六代人的接续奋斗,表征和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法律、政制框架早已搭建完毕,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终于呈现出大国初兴的繁华景象。当然,说“基本恪尽其功”,就意味着尚未大功告成。其中,撇开海峡两岸四地在政制、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之有待整合、从而蔚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不论,仅就社会而言,其之不见成长,允为症结。时至今日,不仅缺乏一个自觉自为的中间阶级以为缓冲,国家直面原子化的“群众”的状况无所改善,而且,政府直接下海主导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长,反而导致社会空间的进一步萎缩,一般民众对于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倚赖。就后两项来看,重在使得“民族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进而恪臻善治,实现政治成熟和伦理圆善。就此而言,则百年之间,兴革继替,一言难尽,有待努力处尚多;今日政治改革似乎走到了“瓶颈”,建设现代政体的进程颇多顿挫,而且,有陷入“勃列日列夫现象”的趋向。总括来看,上述四项,均有所成,而无一不尚有待于继续努力,但相较而言,后两项尚需努力处更多,也更为艰难曲折,也许,于现实的法制和政制而言,“风险”更大。 如果说上述四项任务表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所孜孜追求的不外是“富强、民主和文明”,因而,大体循沿着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向“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和“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路径递次挺进的话,那么,上述第一、二项对应的大致为“富强”这一目标,完成的是“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的建设,并为“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的开展提供法律时空和政治边界,而应当和必须进境于“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即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所谓优良政体者也。二者同德,辐辏用力,有可能导引向“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国家建构的最高境界,所谓意义秩序者也。凡此境界,对应于“富强、民主和文明”这一总括性政治憧憬与秩序图景,说明现代国家是权势国家、宪政国家和文明国家的综合体,现代政治不是别的,乃为权力政治、宪法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三位一体,而分别因应着“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的纷繁世像。[20] 然而,正是在此,刻下精英心志畏缩,心气委琐,推展乏力。一方面,政制无法容涵政治的成长,使得政制自身无法转换为一种公共存在;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发育所造成的公共性需求,客观上要求政制为政治提供更为灵活的用度与广阔的空间,而政制雅不愿为此献身。这样,二者遂紧绷绷的,并出现相互削弱的自我悖反效应,却最终诉诸时刻提心吊胆的“维稳”来打发之,令人浩叹。 在此,“中国问题”的当下症结在于,一方面,现有政制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持民族国家格局的体制保障,过往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家间政治”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在相当时段内与时俱进,具有自我更新、应对外部环境的强劲能力。特别是近年来应对自然灾害所展现的强劲国家动员能力,史无前例,蔚为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国家百年奋斗的一大善果,已然不能单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概括。与此同时,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还即已切身历练的“大国博弈”,使得中国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调处,愈益表现出大度与成熟,颇有气象,说明了这一政制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面前,对于“国家理性”具有相当的自觉。但是,另一方面,自“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的递进,换言之,以民主为核心标志的现代政治在中华大地之诞生,一种“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状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早晚要来的事,人心所向,势所必然,对此同样应当抱持高度自觉,而这进而意味着这一体制本身必须做出重大转型,一种根本性变革,如此方能满足“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以“民主国家”为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才能获秉强健的国家能力,国民在此基于公民的自我体认,可得奉献一己忠诚;而在“民族国家”时空内上演的“民主国家”,才能蔚为贴心的家园,国民于此返身自顾,在市民的定位中,方会认同其为惬意居所。如此,“中国”这一浩瀚时空,既高扬公民理想,努力成为一种公共政治空间,又慰藉民族理想,蔚为国民空间。假以时日,土壤细流,其所成就的将会是“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的恢弘气象。 因而,如果此一政制希望延祚,并保持应变的活力,则需向政治挺进,以后者的公共性内涵来救济正当性的不足,从而有望在维持自身存续的同时,与后者一同成长。但是,如若以政治为理想境界,则需对于自身做出重大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调整,于价值理念和制度操作两方面做出切实因应,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于自身的否定,以否定求得肯定。宋儒曾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借用这一说法,不妨说政制是“以法把持天下”,而政治才是“以道治天下”。当今之世,所谓道者,核心内容即现代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也。然而,也正是在此,这一体制的犹豫不决和迟迟未能做出适应性选择,面对渴盼打开政治公共性之门的汹涌民情,这一体制对于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之口惠而实不至,使得人们对于其适应能力、更新动力和政治诚意,均生发出了多重疑问。同样,恰恰在此,“普法”所揭示的法制与法治、民族与民主、政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刻下“有法不依”所反映的法制未获恪守、法治不见成长的窘境,以及这一“发展的瓶颈”所反衬出的政治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均在在说明政制对于政治处处掣肘,已然到了非冲决不可之际。可是,情形似乎是,愈是如此,政制的自我危机感便愈为深重,因而愈发不愿迈步,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此种急迫性。现有体制整合功能之工具理性与强化此一功能必得诉诸政治公共性的价值理性的纽结,导致了一种二者相互削弱效应,造成了时刻必须诉诸“维稳”的政治态势。如果破解这一“发展的瓶颈”?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是否能够破解之?对此,理论逻辑无法代替实践逻辑,但是,理论逻辑至少可以提供的一点解释就是,它说明中国的发展所遭遇的政体选择,要求“政治决断”登场,启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幡的民主化进程,实为刻不容缓。每再拖宕一天,就难免遭遇缺乏政治诚意的质问,使得存在于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政制与政治的紧张”愈加展露无遗,进而连同上述诸项紧张关系一起,造成了下述三大后果。
政制与政治的紧张 如同法制与法治之别,“政制”与“政治”二位一体,在层次、境界、准则和修习次第上,既彼此牵连顾盼,又各有自家畛域。换言之,但凡搭建起民族国家框架,摆脱“无法无天”状况,基本能够维持法律、秩序和公共生活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体制,即为一种法制和政制,甚至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法制和政制,而不论其政体形态,更不对它作什么自然法式的省视和政治正义追问。其反面是所谓的“弱国家”与“失败国家”,不仅难言经济社会发展和建构优良政体,而且,连基本秩序也无,国家能力羸弱,行政效能严重不足,多数时候处于失范状态,公共生活自无保障,法律和规范亦且形同虚设。海地大地震后的饿殍载道,索马里的盗贼蜂起,阿富汗之四分五裂,可为其例。这其间,自“弱国家”、“失败国家”至“成功国家”,至少存在“失范”、“基本治理”、“有效治理”和“善治”等层次,展示出人类政治秩序与政治智慧的地方性差别。[18] 正如笔者一再指陈的,百年中国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至少包含四个方面,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它们连贯一体,旨在贯通“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指向的理想愿景是强有力的现代民主国家。[19] 具体说,前两项的落脚点是有效治理的“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当下中国基本恪尽其功。不仅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渐次发育、居民生活水准和国民素质大幅提高,而且,经由清末以还五、六代人的接续奋斗,表征和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法律、政制框架早已搭建完毕,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终于呈现出大国初兴的繁华景象。当然,说“基本恪尽其功”,就意味着尚未大功告成。其中,撇开海峡两岸四地在政制、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之有待整合、从而蔚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不论,仅就社会而言,其之不见成长,允为症结。时至今日,不仅缺乏一个自觉自为的中间阶级以为缓冲,国家直面原子化的“群众”的状况无所改善,而且,政府直接下海主导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长,反而导致社会空间的进一步萎缩,一般民众对于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倚赖。就后两项来看,重在使得“民族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进而恪臻善治,实现政治成熟和伦理圆善。就此而言,则百年之间,兴革继替,一言难尽,有待努力处尚多;今日政治改革似乎走到了“瓶颈”,建设现代政体的进程颇多顿挫,而且,有陷入“勃列日列夫现象”的趋向。总括来看,上述四项,均有所成,而无一不尚有待于继续努力,但相较而言,后两项尚需努力处更多,也更为艰难曲折,也许,于现实的法制和政制而言,“风险”更大。 如果说上述四项任务表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所孜孜追求的不外是“富强、民主和文明”,因而,大体循沿着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向“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和“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路径递次挺进的话,那么,上述第一、二项对应的大致为“富强”这一目标,完成的是“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的建设,并为“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的开展提供法律时空和政治边界,而应当和必须进境于“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即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所谓优良政体者也。二者同德,辐辏用力,有可能导引向“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国家建构的最高境界,所谓意义秩序者也。凡此境界,对应于“富强、民主和文明”这一总括性政治憧憬与秩序图景,说明现代国家是权势国家、宪政国家和文明国家的综合体,现代政治不是别的,乃为权力政治、宪法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三位一体,而分别因应着“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的纷繁世像。[20] 然而,正是在此,刻下精英心志畏缩,心气委琐,推展乏力。一方面,政制无法容涵政治的成长,使得政制自身无法转换为一种公共存在;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发育所造成的公共性需求,客观上要求政制为政治提供更为灵活的用度与广阔的空间,而政制雅不愿为此献身。这样,二者遂紧绷绷的,并出现相互削弱的自我悖反效应,却最终诉诸时刻提心吊胆的“维稳”来打发之,令人浩叹。 在此,“中国问题”的当下症结在于,一方面,现有政制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持民族国家格局的体制保障,过往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家间政治”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在相当时段内与时俱进,具有自我更新、应对外部环境的强劲能力。特别是近年来应对自然灾害所展现的强劲国家动员能力,史无前例,蔚为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国家百年奋斗的一大善果,已然不能单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概括。与此同时,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还即已切身历练的“大国博弈”,使得中国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调处,愈益表现出大度与成熟,颇有气象,说明了这一政制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面前,对于“国家理性”具有相当的自觉。但是,另一方面,自“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的递进,换言之,以民主为核心标志的现代政治在中华大地之诞生,一种“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状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早晚要来的事,人心所向,势所必然,对此同样应当抱持高度自觉,而这进而意味着这一体制本身必须做出重大转型,一种根本性变革,如此方能满足“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以“民主国家”为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才能获秉强健的国家能力,国民在此基于公民的自我体认,可得奉献一己忠诚;而在“民族国家”时空内上演的“民主国家”,才能蔚为贴心的家园,国民于此返身自顾,在市民的定位中,方会认同其为惬意居所。如此,“中国”这一浩瀚时空,既高扬公民理想,努力成为一种公共政治空间,又慰藉民族理想,蔚为国民空间。假以时日,土壤细流,其所成就的将会是“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的恢弘气象。 因而,如果此一政制希望延祚,并保持应变的活力,则需向政治挺进,以后者的公共性内涵来救济正当性的不足,从而有望在维持自身存续的同时,与后者一同成长。但是,如若以政治为理想境界,则需对于自身做出重大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调整,于价值理念和制度操作两方面做出切实因应,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于自身的否定,以否定求得肯定。宋儒曾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借用这一说法,不妨说政制是“以法把持天下”,而政治才是“以道治天下”。当今之世,所谓道者,核心内容即现代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也。然而,也正是在此,这一体制的犹豫不决和迟迟未能做出适应性选择,面对渴盼打开政治公共性之门的汹涌民情,这一体制对于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之口惠而实不至,使得人们对于其适应能力、更新动力和政治诚意,均生发出了多重疑问。同样,恰恰在此,“普法”所揭示的法制与法治、民族与民主、政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刻下“有法不依”所反映的法制未获恪守、法治不见成长的窘境,以及这一“发展的瓶颈”所反衬出的政治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均在在说明政制对于政治处处掣肘,已然到了非冲决不可之际。可是,情形似乎是,愈是如此,政制的自我危机感便愈为深重,因而愈发不愿迈步,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此种急迫性。现有体制整合功能之工具理性与强化此一功能必得诉诸政治公共性的价值理性的纽结,导致了一种二者相互削弱效应,造成了时刻必须诉诸“维稳”的政治态势。如果破解这一“发展的瓶颈”?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是否能够破解之?对此,理论逻辑无法代替实践逻辑,但是,理论逻辑至少可以提供的一点解释就是,它说明中国的发展所遭遇的政体选择,要求“政治决断”登场,启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幡的民主化进程,实为刻不容缓。每再拖宕一天,就难免遭遇缺乏政治诚意的质问,使得存在于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政制与政治的紧张”愈加展露无遗,进而连同上述诸项紧张关系一起,造成了下述三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