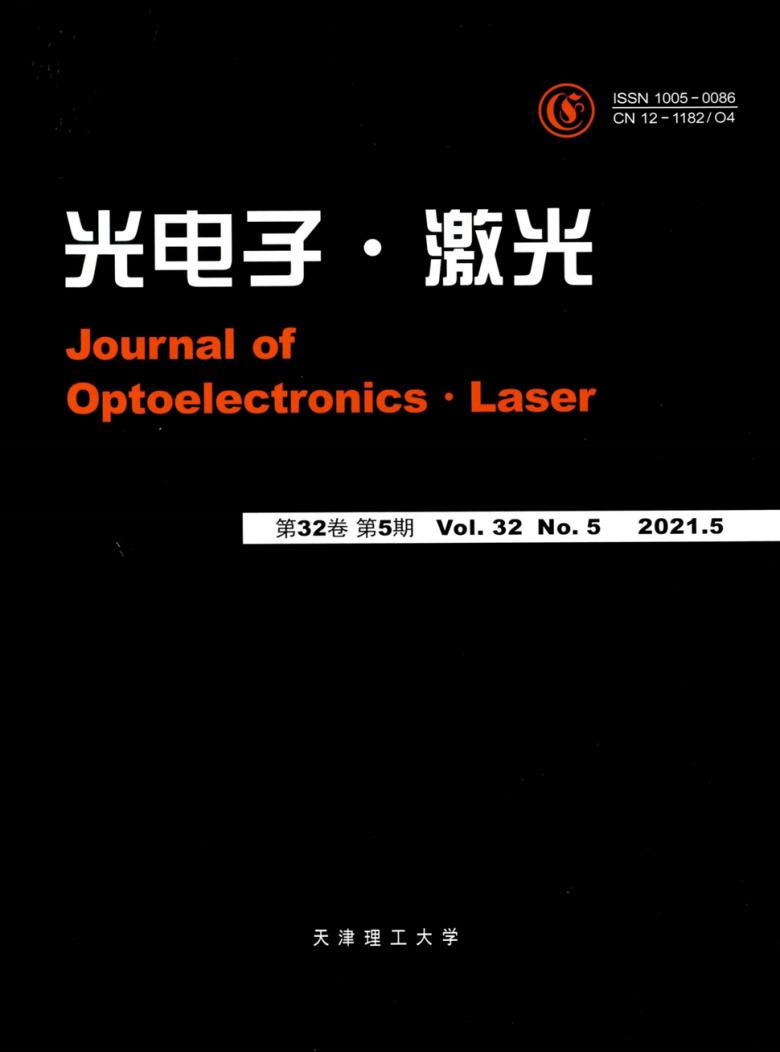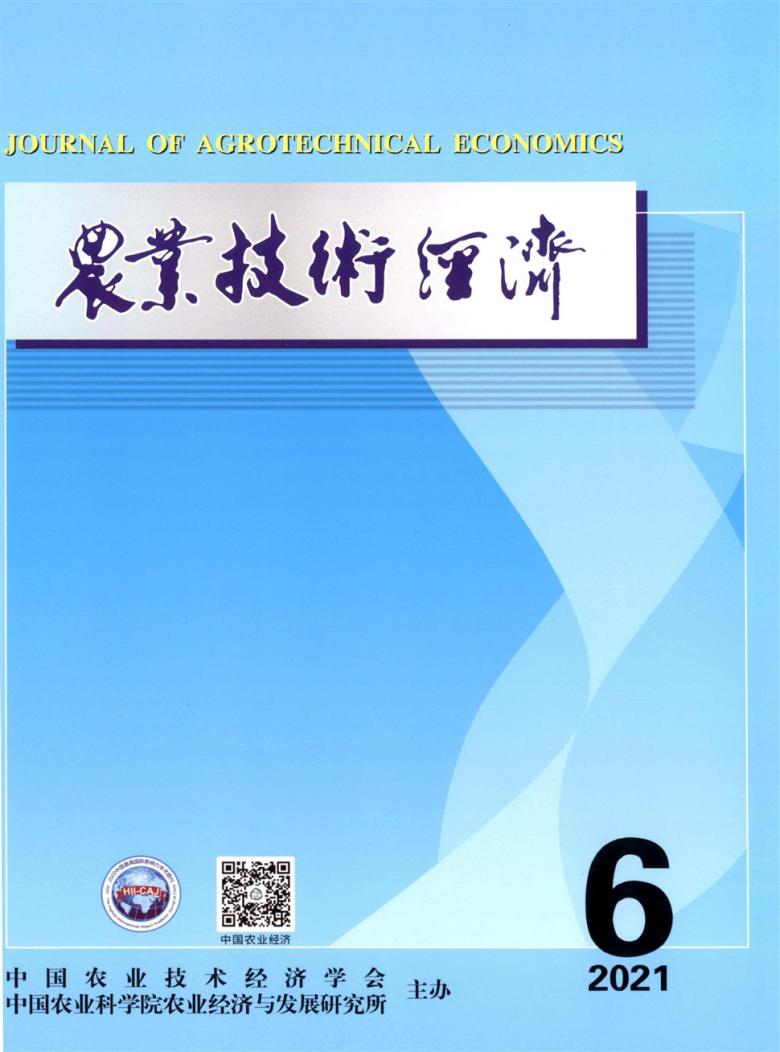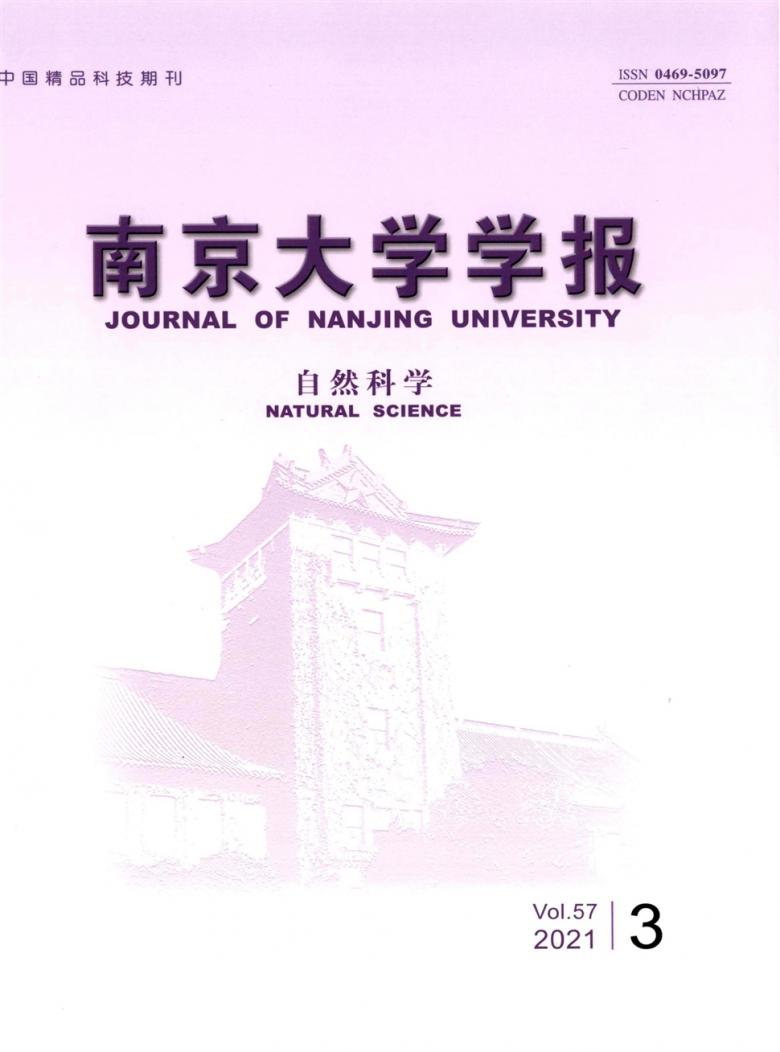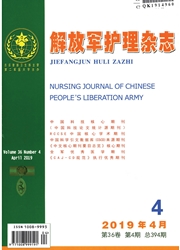“公安三袁”与李贽文学思想的渊源
张树俊 2009-02-06
摘 要:李贽是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在明末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李贽继承了自王艮以来的泰州学派反道学的传统,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学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把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发展史等问题上李贽坚决反对“假言”、“师古”的文风,主张文学创作要出自真心,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由于“公安三袁”与李贽有着某种特殊的渊源关系,所以“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与李贽具有颇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反古;率性;倡俗
李贽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平民哲学学派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大师。李贽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从某种意思上说,李贽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仅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精神,其文学作品也是“战火纷飞”,直指传统腐朽的观念和封建统治。由于“公安三袁”与李贽有着一定的师承关系,所以他们的文学风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不同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公安三袁又与李贽有所区别。本文试作一些初步的比较,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
李贽[1527—1602]初名载,号卓吾、宏甫、温陵居士,又号龙湖叟,晋江(今福州晋江)人,杰出的思想家,泰州学派的第三代传人。
据史料记载,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贽开始辞去官职,离开姚安,由滇入川,而后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北黄安,开始了他归隐著述、讲学的生活。至黄安后,李贽先是住在天嵩书院,教授耿家[耿定理]的子弟,并开始致力于史籍的阅读和研究。不久,李贽与理学家耿定向发生尖锐矛盾,李贽决定离开耿家。之后,李贽写了大量的书信来揭露批判耿定向的假道学,这使耿定向十分恼怒。有一次,李贽游武昌黄鹤楼,耿定向指使徒众进行围攻。但这并没有使李贽屈服,相反,却扩大了他的声望。当时在武昌任湖广左布政使的刘东星,把李贽邀到自己的官署加以保护。湖北“公安三袁”,也是在这时和李贽密切交往起来的。
“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及袁中道兄弟三人,他们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由于他们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有《白苏斋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有《袁中郎全集》。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有《珂雪斋集》。他们之中袁宏道成就最大,他自称“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兔,捣钝贼之巢穴”,是在反复的斗争中是一员主将。据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记载,衰宏道文学主张的建立是受了李贽的深刻影响的:“先生[袁宏道]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
实际上,公安派与泰州学派本是一派。公安派名义上是一个地方派,而从渊源来看,公安派也是泰州学派的一个支派,公安派的“三袁”是泰州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因为焦骇和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袁宏道是焦豌的学生,焦竑与李贽又是知己朋友,袁宏道对泰州学派的李贽很崇拜,自称是李贽的弟子。他在一首《送焦弱侯老师使梁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的诗中说:“自笑两家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而李贽在《九日至报东寺闻中郎且至因喜而赋》的诗中也说:“世道由来不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亦自认袁宏道是他的学生。李贽非常赏识轰宏道,说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汉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一首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对袁宏道期望甚为殷切,称其为“英灵男子”,是想衰宏道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焦蛇和李贽是泰州学派同代知己,袁宏道正是在两位大师门下执弟子礼,接受他们的教诲,因而深受他们的启蒙文学思想的影响。袁宏道和李贽常有书信往来,把李贽著作放在床头经常阅读。他说:“幸有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错可以醒眼,甚得力。”
除袁宏道外,公安派袁氏三兄弟都是李贽的弟子,都受李贽深刻的影响。据史料载,万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袁宏道兄弟三人先后两次到麻城向李贽求教,第二次时间最长,共达三月有余,袁宗道说:“不读他人文学觉懑懑,读翁[李贽]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热乎。”袁中道在一首诗中也说:“我有兄弟皆慕道,君多任侠独伶予。”钱谦益在谈到袁氏兄弟与李贽关系时说:“袁氏中郎,小修皆卓如之徒,其指实卓吾发之。稚圭与小修具龙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学于稚圭,其师友渊源如此。故其诗文之大指可得而考也。
“公安三衰”的思想与李贽是一脉相传的,他们都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公安三袁”基本继承了李贽反封建的叛道思想和斗争精神。李贽反封建传统、反对道学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正如他自称:“余自幼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李贽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与封建道学作不屈斗争的一生。在明末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李贽继承了自王艮以来的泰州学派反道学的传统,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学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开启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先河,并把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安三袁继承了李贽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如袁宏道在《与张给谏》的信中说,“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他还说:“大丈夫当独来独往,自舒其翼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终耳。”咻现了他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这些思想精神和愿望都与李贽如出一辙的。
二
由于“公安三袁”直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与李贽在文学思想方面有着极大的相近性。
首先表现为他们有一致的文学发展观。在李贽的时代,八股文风盛行,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主张。当时文坛上王世贞、李攀龙等“前七子”极力提倡复古,造成文坛笼罩着一片“拟古”、“复古”之恶劣风气。李贽对这一复古浪潮进行了批判。李贽认为,文章的好坏,“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并非愈古愈好,文学在变化和发展中不断地出现好作品。李贽的这一文学发展观与他辩证发展的是非观是分不开的。他说:“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历史是前进的,现实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起变化,所以文学作品也不应“执一”,更不应抱古。
“公安三袁”在李贽的影响下,也提出了和复古派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有力地驳斥了复古派的种种谬论。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不应该厚古薄今。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说:“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 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他在好多文章里反复阐述这一论点,发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呼声。
李贽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是唯心的,把好的文学作品都看成是“童心”的产物。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所谓“童心”,据他讲就是“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种理论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哲学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李贽要求作家“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有了童心就能写出好作品,用不着什么“道”,“吾因是百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啐贽对道学大力攻击,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由此,李贽主张文学创作必须“发于陸情,由乎自然”,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在《读律肤说》一文申明确指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李贽以为创作的冲动源于作家的真实情感,所以作品中感情的流露应当是完全自然的,如果矫揉造作,不真实,就不能写出好作品,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李贽一再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根于心,发于言”。他在《司马迁传论》中说:“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有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李贽还认为,作家的不同个性,决定了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作家只要顺着自己的性格去进行创作,真正做到“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就会使自己的作品产生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效果,如果强求达到某种自然,倒反而会失去真实,最终也得不到好的艺术效果。所以他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
“公安三袁”关于文学的基本主张主要出于他们的“性灵说”,这种“性灵说”实际上是由李贽的“童心说”变化而来的。公安三袁提出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所定下的种种清规戒律。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文学有表达多种多样个性的权利,所以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肯定了诗可以“若哭若骂”,可以怨而伤,可以写得很露骨。“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这种提法对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一种反抗。
在文学创作上公安派反对摹拟。既然文学是随着时代而发展,那么就完全不必要摹拟古人。袁宏道在《与江进之》的信里谈出了他们的见解:“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音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他猛然攻击了文人中的复古之风,指出复古事实上就是抄袭,“剽窃成风,万口一响”,“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袁宗道在《论文》中说得好:“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复古派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自己的见解,文章的内容空洞无物,不得不借助于古人词句来装点门面。由此可见,“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与李贽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在反复古和文学发展观、文学创造的基本主张方面,“公安三袁”与李贽一致外,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如李贽反对复古派盲目崇古时矫枉过正,把八股文的地位抬高了,袁宏道也跟着如此。李贽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浅近明白,几乎不用典故,不装腔作势,并且采用民间俗语,在复古之风很盛的时候显得非常突出,公安派也主张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文学语言来写作,不用什么典故,采用大量俗语,“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他们都对通俗文学十分推崇。李贽敢于打破历来传统文人的偏见,肯定新生事物,把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记》和《水浒传》同列于“古今至文”。他说:“降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公安派也非常推崇通俗文学,袁宏道对《水浒传》也评价很高,他说在《水浒传》的相形之下,“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并把关汉卿、罗贯中和司马迁并列为“识见极度高”之人。李贽大胆进行小说评点。他是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人,曾评点过《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多种戏曲、长篇小说。这种对戏曲、长篇小说的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新的样式。“公安三袁”也对小说、戏曲进行过评点。如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离骚》、写、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仇校,肌劈理分,时出新意。”总之在文学思想上“公安三袁”继承了李贽的基本思想。 三
“公安三袁”和李贽的文学思想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公安三袁”与李贽的文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李贽比公安派有更强的创作激情和斗争勇气,李贽主张创作要有激情。他说写作要“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贽正是以其锋芒毕露的文字,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对他“切齿咬牙,欲杀欲割,”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贽的文章特色还在于见解大胆,敢于反对封建社会传统的教条,对道学家的攻击火力甚强,揭露出他们丑恶的灵魂,文字泼辣。痛快淋漓,有鼓动的力量。比如李贽在《因记往事》一文里,他称赞当时横行闽广海上的林道乾。说他“称王称霸。众愿附之,不肯北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并且指出这些人物产生的社会原因:“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在《五死》一文里,他把楚国的伍子胥和汉朝晁错的死,看着“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在《又与焦弱侯》的信里,他对那些道学气的知识分子作了无情的揭露:“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发表这些意见,在封建社会里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而公安派虽然作品中也时见愤懑之语。如衰宏道的七言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第二首:“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曲与栽花市。新诗曰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但总的来说,“公安三袁”在文学的创作激情和斗争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在当时宦官擅权、政治腐败、朝内党派剧烈的环境中,他们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既不敢参加斗争,又不愿同流合污,想置身于是非之外,于是退守田园,忘情山水,以此来麻醉自己。袁宏道在给他的老师妈琢庵的信里就曾说过:“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李贽的惨死,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他们更加畏缩了。袁中道在为李贽而写的《李温陵传》中说:“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有一条是“公[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爷。”看来这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也是公安派作家普遍的思想弱点。
其次,李贽认为文学应该充分地反映现实。李贽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抒发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不平,反对无病呻吟。他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而公安派的“性灵说”虽然是“童心说”的变化和发展,但“性灵说”把文学不是看作表现现实生活,而是看作表现抽象的“性灵”。公安派的作家江进之在为袁宏道的《敝箧集》所作的序上,把创作方法说得非常神秘:“灵窍于心,寓于境。境自所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宛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他一味强调作者的主观方面,即所谓“心”,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称赞袁宏道的功绩,说是在他影响下,“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把创作之源归之于“心灵”,“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这是唯心的观点。在它的指导下,文学的题材越来越狭小,作家的灵感越来越枯竭。终于不得不求助于所谓“韵”和“趣”,走上了魔道。事实确是这样。公安三袁除少数作品[如《李逋赋》、《猛虎行》、《竹枝词》]等而外,公安派中最有名望的作家袁宏道的确如他所自称的“诗中无一忧‘民’字”。他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大多缺泛深厚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及身边琐事,抒发“文人雅士”的情怀,表现地主阶级文人的闲情逸致。比较好的是那些反对作官、反对道学气的文字以及一些清丽的小品。袁宏道在这方面成就较高。当然,他们也有极少数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袁宏道十分厌恶作官,甚至认为“官实能害我性命”。固然这对官场生活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从个人出发。如他在《戏题斋壁》诗中说:“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膻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数鼠猫,身似近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
此外,李贽擅长杂文形式。尽管他在题目上还标着“论”、“序”、“跋”、“记”,甚至是书信的形式,可实质上它们的内容已符合我们现代“杂文”的概念。李贽亲手编写《焚书》时,将这些文字[书信除外]均列入“杂述”一类。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往往是由一两件事情引起感想,进而阐发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有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悍的随笔。而公安派则以诗和散文见长。尤其是散文清新活泼,解放了文体,“一扫王李云雾”,打垮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死气沉沉的统治,特别是袁宏道的游记具有相当高的描写能力,文笔秀逸。像《初至西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虎丘》、《天池》、《五三世》、《天目》、《满井游记》等篇,都是写得好的散文。可以说“公安三袁”对散文的发展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他们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丰富了表现的方式。
总而言之,公安派与泰州学派本为一脉。泰州学派李贽等重要传人的思想和文学主张给“公安三袁”以极大的影响。“公安三袁”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文学思想,并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见解和实践,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对后来启蒙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