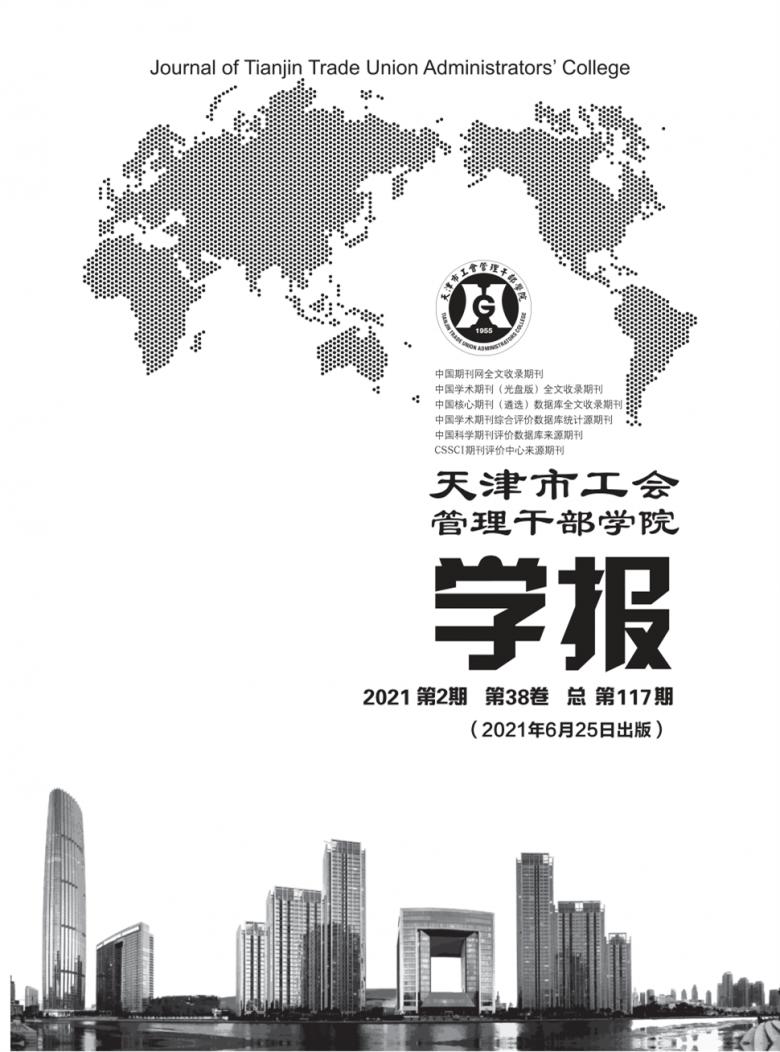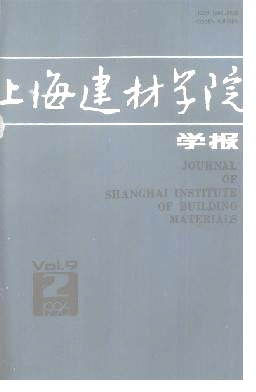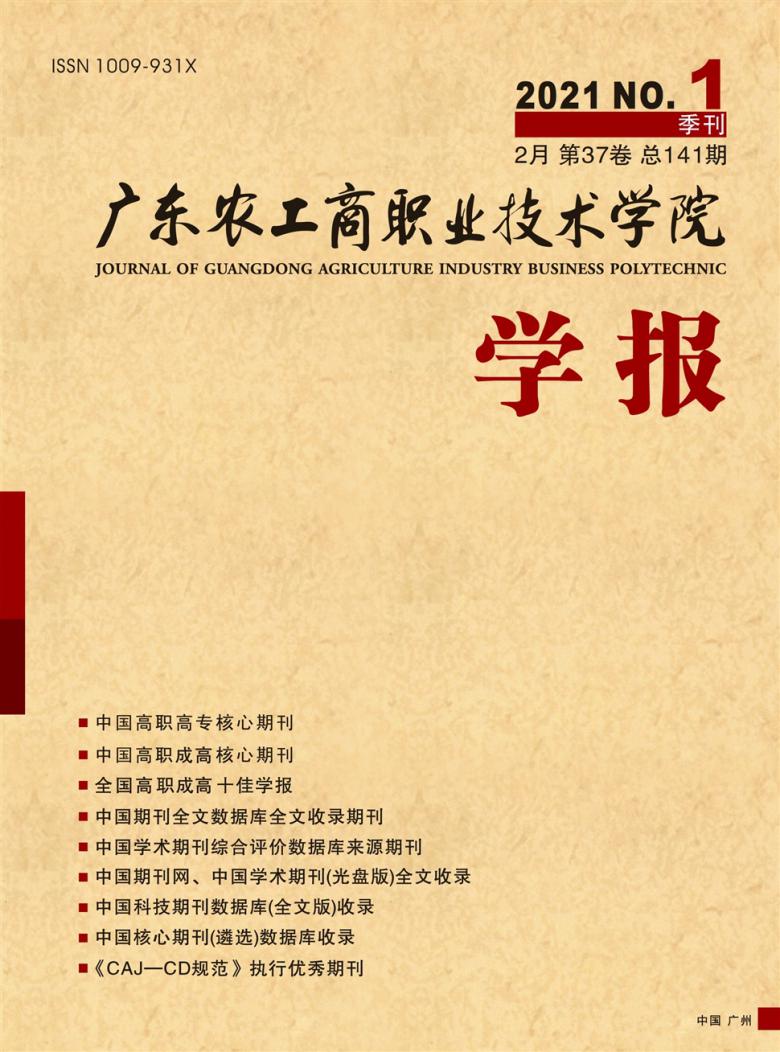关于浅论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李卓
〔论文关键词〕决策理论判断问题性质理性决策决策机制研究政治心理学
〔论文摘要〕判断问题性质,是一个实践中常见而理论探讨中少见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此后从三种外交决策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决策机制研究、政治心理学)引申各自对“判断问题性质”的不同解释。作者最后认为三种外交决策理论在荃本假设、哲学基础的差异,使得可以较好的描述“判断问题性质”的综合决策理论难以产生。
一、对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
外交决策是从一系列政策预案中,选择出某个方案以解决外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所谓问题往往既指一种客观事态的变化,也指一种主观认知的变化。它相对于某标准而言,这个标准在外交决策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表现为决策主体对某个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相符状态的认识与认同,“问题性质”即相对于这一标准发生变化的事态的特性。“判断”则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特性的认识和对这一认识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有两个特点,时间上的连续性与事态上的变化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是这样一个过程:决策主体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个命题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该命题的内容为决策主体对相对于某一个标准发生变化的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认识。因此“判断问题性质”有两个阶段性成果—针对某种变化的认识,对这种认识的认同。这两者不仅在“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也将影响外交决策这一过程的其余部分。
有时候决策主体即使对“某种事态的特性”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会制定、实施相应方案,这并不是因为认识、认同发生改变,而是因为其它限制因素的影响,如外交目标与决策主体的其他目标的冲突或“决策主体与决策执行者的认知不同”作为一个限制变量也介入到决策主体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现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即“判断问题性质”不必然决定决策成果。
但缺失“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的外交决策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以决策的本质是“选择”为思维起点,则若无法“判断问题的性质”,就无法使用某种标准对方案与目标进行选择。如果以决策是一个“过程”为逻辑起点,则若没有“判断问题的性质”的过程,则整个决策“过程”的起点,就无法进行有效分析该“决策”,也无法针对此“决策”制定和采取对应决策。因此,“判断问题性质”必然存在于整个决策过程中。
二、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有关外交决策的理论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以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由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衍生出的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关注于官僚机构与组织过程的决策机制研究、以及关注于决策者心理过程的政治心理学。不同的学派虽然都承认外交决策是做出选择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不同。
本章主要介绍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理性国家是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对外交政策的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决策过程可以用理性选择模型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主要指主体知道他的选择内容,对未知的事物形成预期,具有明确的偏好,并在经过一些最优化过程后审慎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外交决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必要修正,如决策主体不追求最优,而是满意:维持最稳定的状态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为中的决策者选择;政治收益有特殊性。
在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形成一个对事态变化的认识的命题与对这个命题的认同是连贯的,其原因是对事态的认识是基于现实主义安全观、国家利益观;对这个命题的认同也基于同样的观念,单一决策主体和一贯的现实主义利益观是使得该过程如此连贯的原因。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者的思维存在一种“泛安全问题化”、“泛国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倾向,即存在“不知问题性质却己将其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最终服务于形成某一可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即存在以下过程:对国家利益可能的变化进行程度区分—不同变化程度对应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方案维护在一个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或一个政治利益低限上的不同政治利益),而这种目的可能扭曲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或致使不同环节中的理性互相冲突,最终导致整个过程可能出现行为体以理性为目的的行为不够理性的荒谬。因此,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不一定能够体现客观事态发生变化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够确保最终对策可维护国家利益。
三、决策机制研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与现实主义者相反,决策机制研究者反对将国家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决策机制(决策背后的政治制度、体制、机构乃至规章制度)约束了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正如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对外决策的根源必须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国内需要与要求中寻找。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订的总的框框里去理解。”决策机制研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决策机制的理解—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前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基于组织内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是各种组织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平衡结果。国家决策者常为官僚机器所左右,决策部门缺乏多种选择,面临政府部门利益的激烈争斗,难以解决政策的执行问题等。后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国家政府成员间讨价还价的产物,根据这一模式,关键者是总统、总理、高级行政和立法部门领导,当然,政府外成员(如利益集团)有时也起重要作用.该模式强调三点,其一是谁参与决策。其二是决策参与者同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三是决策成员间如何调整相互关系。决策机制研究认为,决策参与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定和执行最佳政策,关心的是对自己而言的最佳政治利益和影响,因而常会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标不明。
决策机制研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主体是居于决策机制核心的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僚。部门或官僚对问题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门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区别,是寻找问题的特殊性。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特点是,部门或官僚的特殊性,而不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即客观事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面对事态和事态牵涉到谁的利益。由于对事态变化的定性将极大地约束与部门、官僚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则部门、官僚需要协商出“问题的性质”,使决策内容符合部门、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对它们的利益构成根本威胁。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并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协商”—对预期中的利益的分配过程。此外,客观事态变化并不重要,而各部门、官僚自身的利益变化才是对决策主体而言的事态。而客观事态也并非“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中的认同的对象,各个决策主体之间的可能的利益妥协的结果才是他们对自己视野中的有关自己未来利益变化的事态的认同对象。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部门或者官僚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维持“团结”—不同决策部门、官僚所共同组成的决策主体的最终意见一致。但也存在与这种前提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当决策机制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达成意见一致的能力时。这种情况中的决策主体的“判断问题性质”较为特殊,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依然与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客观事态无关,而与部门或官僚对决策系统的依赖性有关,即部门或官僚的利益面对可能导致决策机制崩溃的威胁时,参与决策的各主体愿意迅速达成一致意见以“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依然被扭曲,能否达成“意见一致”比能否符合“问题”本来面貌,对于各决策主体来说更重要。这时的“判断问题性质”实质上是在寻找各方认识的交集,而不单纯是利益的分配,同样与客观事态变化的特性不相关。
在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内,形成认识与形成认同的区别非常明显:在形成认识中,由于自身利益特殊性,多个决策主体对于某种事态对自身利益产生何种影响的认识明显不同,在形成认同中,多个决策主体以利益分配或追求共同认识为目的进行协商,其结果即为“判断问题性质”的成果。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与理性国家行为体的“判断问题性质”的区别是:决策主体的数量不同、国家利益在最终结果形成中的地位不同。这种区别的根源是—决策主体是关注国家利益的单一理性国家行为体还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决策机制中的官僚或部门?
四、政治心理学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最终做出决策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策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决策者倾向于从内向外看问题。“判断问题性质”则是形成一个对所面对的问题的基本看法的过程。对此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及与认知结构相关的信仰、价值观、个性、兴趣等心理特质。性质与其说是被判断出,不如说是被建构出。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与决策机制研究,都包含一个假设,即决策主体的利益是外界给定的,参与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益或保护利益。但利益不是一个定量,外交决策的互动乃至外交决策制定过程本身,都会使利益发生变化。决策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心理特性也对决策者的利益有影响,利益因此成为一个有无限内涵的符合决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决策者认知.
政治心理学将判断问题性质看成是建构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乃至认同的过程,突出了决策者认知结构的作用。但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被什么改变,是一个难以衡量、估计甚至难以察觉的问题。如果决策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最终对策来源于认知结构的碰撞,则即使了解每个决策者的对“客观事态”的认识,也无法推测出最终的决策内容,整个“判断问题性质”将变得异常复杂。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对国家主体的“黑箱假设”,但本文认为与其说打开了黑箱,不如说告诉我们有无数个黑箱,且不存在打开每个黑箱的通用办法,且只有打开每个黑箱才有可能了解某个决策的本质,因此政治心理学很难对现实中的决策难题提供有效建议。
外交是互动性的,一方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对方的行为。若一方对另一方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无法做出一个基本的把握,则前者的“判断问题性质”就无法得出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态的特性、后者行为的意图、后者对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动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命题集合。形不成这样的命题集合,一个被决策者认同的具体方案就难以形成,从而致使外交互动难以保证。政治心理学的分析让人意识到了决策的复杂性,因此交涉双方采用一些通用假设会使得决策过程,尤其是“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变得清晰并保证外交互动顺利进行。
五、结语
任何一个外交决策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判断问题性质”中,这些局限性都较为明显,现实主义者过于强调某项决策的必然性与应然性,其追逐国家利益的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强假设,其逻辑内部的“不知问题性质却己将其定性”的倾向使得“判断问题性质”受到干扰。因此该理论对“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描述与建议都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而决策机制中的官僚与组织决策模型,描绘出了不关心客观事态本身,只考虑自身利益得失的决策者形象,描述决策实践却提不出对决策机制的改进意见。政治心理学者的研究与决策者距离最近,但在难以描述“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同时,也无法对其提供改进建议。三种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都不能单独提供对实际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清晰描述和可行建议,似乎三种理论的融合可能帮助我们对该问题有更好的认识。
但遗憾的是,三种外交决策理论对“判断问题性质”的相互矛盾的理解,根源于其不可通约的理论假设(决策主体与决策主体偏好),则建立一种有关外交决策的综合理论不够可行。在哲学层面上,现实主义决策理论是本体论先于认识论的,政治心理学则是认识论先于本体论,机制研究中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还不是很确定,所以三种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也难以协调。因此本文认为在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理论从多个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避免狭隘的视角,但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关“判断问题性质”的外交决策理论,似乎并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