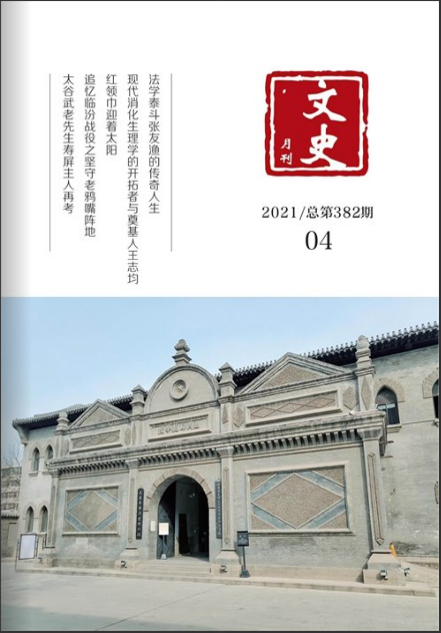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未知 2006-10-06
关键词: 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倍,达917.8万人。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 “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
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 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 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被现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区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内在的力量和逻辑。当《北京晚报》炮制着类似小靳庄诗歌那样歌颂美好生活的新民谣时,北京市民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从未停止。一种是贫嘴张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贱的传统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无奈。另一种是艺术家张大力式的,他用“把脸画在墙上”的先锋行为,向这个喧嚣而沉闷的社会作出一个怪诞的姿态,发出一个奇异的声响。而游历西藏达十年之久的自由电视人温普林,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温普林《茫茫转经路》,2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北京市开始兴建的又一条通衢大道,使发现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引发了知识分子新的抗议浪潮。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尘暴、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凸显了北京作为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危急地位。人们公开和私下议论的问题是:北京会被迫迁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