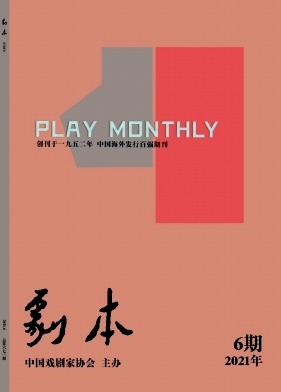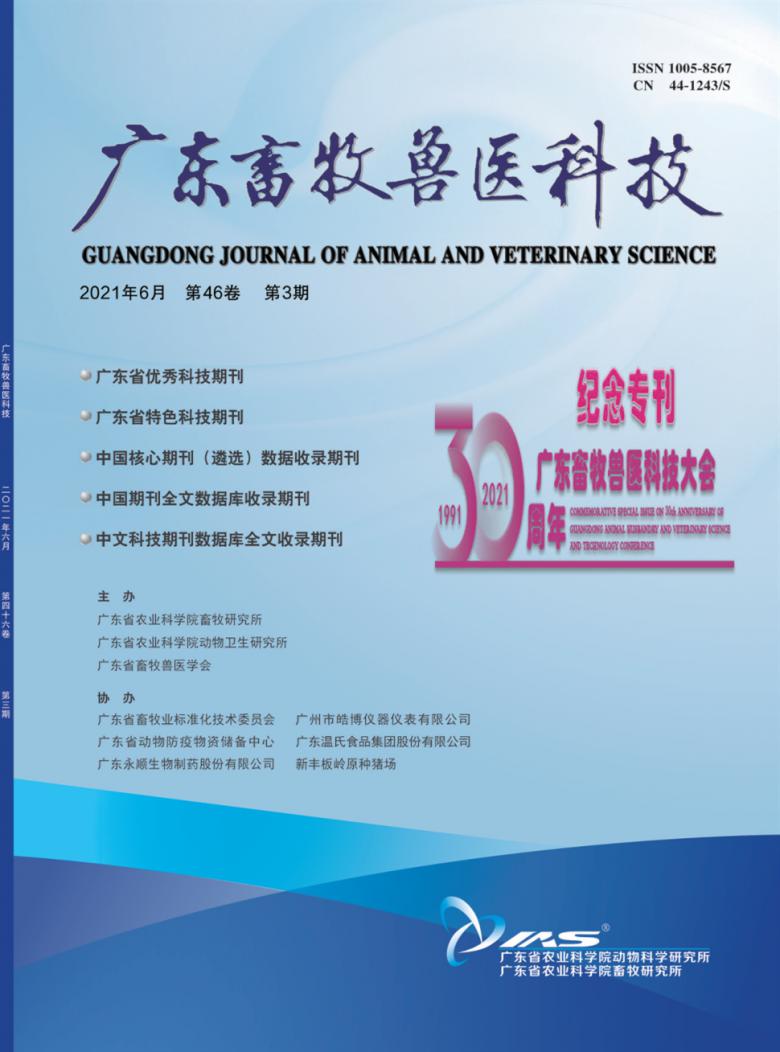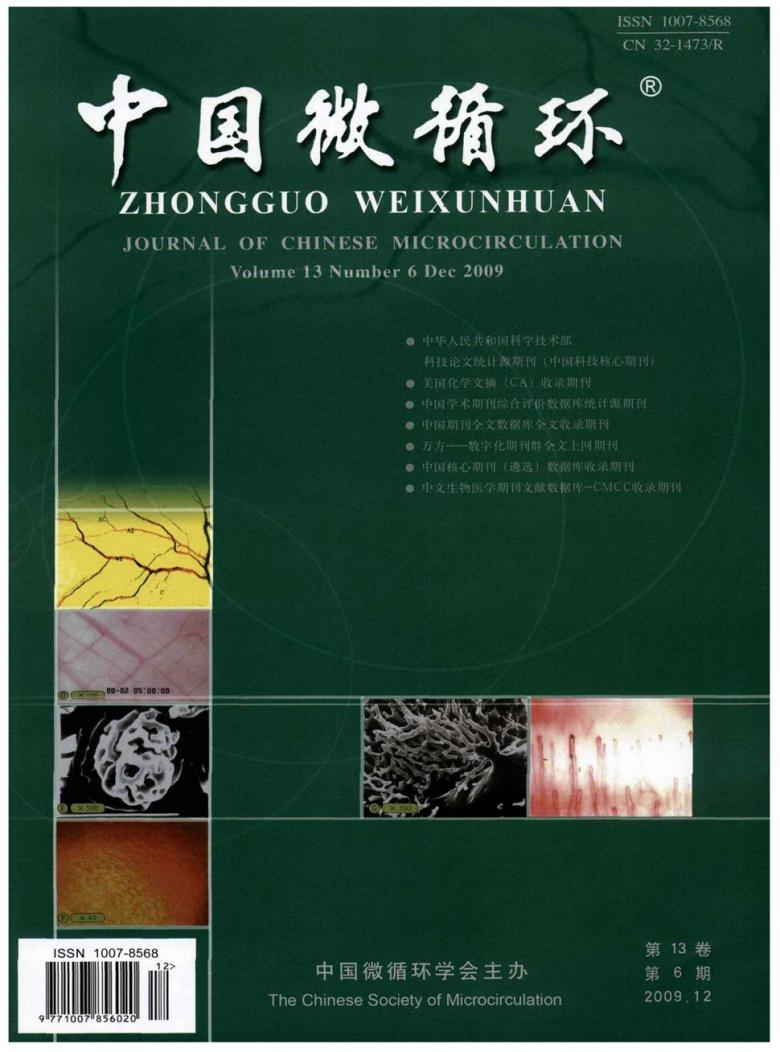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的现实旨归
曾雅云 2010-02-21
论文关键词 :吴承恩 西游记 文本 形象 塑造 现实 旨趣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细读文本,从主人公的转变、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及人物形象塑造的人性化、世俗化三方面来阐述《西游记》的现实旨趣。
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因与现实的无 比契合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身份 ,因此,我们研读的文本就像一本神秘 的密码本,解开了密码 ,文本产生当时的社会真实情状就会一览无遗地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文学和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严密而不可分的整体。吴承恩的《西游记》也可遵循这个原理来解读。
吴承恩之前的取经故事中,唐僧一直是主角。最早记录玄 奘西行的典籍是其弟子慧立所作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着意彰显的是西行求法的艰苦卓绝和唐僧的虔敬坚韧,特别是唐僧的超众智慧与学识。在《诗话》与杂剧中,虽然 出现了护法的孙行者 ,且地位 日趋重要 ,但主角仍是圣僧唐三藏 ,凸显的还是作为圣僧 的唐三藏的坚定意志和超然智慧。而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当仁不让地成了最鲜 明的人物。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隐恶扬善、全始全终降妖除魔的孙行者,看到 了一个睿智仗义、武艺超群 的孙行者个乐 观幽默、聪 明机智 的孙 行者 ,一个 战天斗地 、不畏强权的孙行者 。这个行者光芒四射 ,有着张扬的个性和恣肆 的风格 ,他睥 睨神佛 ,无 视尊卑 ,他不贪图名利财色,只追求个体价值的认同。而圣僧唐三藏呢,意志坚定却不免胆小怯弱,慈悲善良却不免迂腐 固执 ,尤其突出的是他 的糊涂 昏庸不辨是非真假。在这里 ,二人的性格刻画发 生了质的变化,二人 的地位也发生 了根本 的扭转 。孙悟空与唐僧主从地位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作者吴承恩与前人在价值认同方面的不同,是吴承恩的创造。也就是说,之所以会有这一根本性 、创造性的变化 ,完全是取决于作者吴承恩的生平经历、才性气质与美学取向。
吴承恩少时即以文名之于淮,天启《淮安府志》说他“性敏而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然此英才在科举一途却命运多舛,终其一生“仅为邑臣以老”。扭这等才情与遭遇必然造就他愤世嫉俗的性格。这是其一。其二 ,他的父亲吴锐虽为商人 ,却喜爱读书,喜论时政,尤其崇拜陶渊明,自号菊翁,个性淡泊正直,吴承恩深受其父影响 ,任职八品县臣也以安贫乐道的原宪、拙于征赋的阳城自比,淡泊名位 ,耻于折腰 ,其倔强不同流俗的个性可见一斑。其三,吴承恩生活的时代 ,王阳明的心学已广为流布。心学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潮流,心学强调对主体意识 、独立人格的肯定,对主体意识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 :弘扬 自由人性 ,尊重个体价值 ,肯定人的物欲合理。在心学浪潮的冲击下,理学家所设定的各种陈腐规范和风格就都被打破了。而据当代学者考证 ,与吴承恩交往的密友、文友 、同乡及各方面人士几乎有 80%以上与心学人物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吴承恩本人更是与诸多重要心学人物如万表、徐阶、李春芳 、胡宗宪等有过直接接触,这就使吴承恩能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心学思想,从青少年到晚年都处于浓厚的心学氛围之中,从而为他的创作烙下心学思想 的深刻 印迹 ,而他的生平经历和他的个性气质又使他更易与心学思想契合 。这样,无拘无束任性 自在、战天斗地无所畏惧的孙悟空脱颖而出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之前的取经故事把弘扬佛理放在首位 ,意坚志诚、性理通彻的唐三藏 自然是礼赞的对象。可见,没有心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及对人性解放 的呼吁,没有心学浪潮对吴承恩的冲击,孙悟空的形象只怕也很难横空出世了。
再看吴承恩的西游 中孙悟空形象的塑造。 今天,西游记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在一般人的接受视野里,《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讲述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辛到西天求取真经 的故事,电视剧<西游记》一播再播,是假期档必播节目,孩子们也是一看再看,百看不厌,可是,看着看着,孩子们就会问,孙悟空不是齐天大圣吗?不是最厉害的吗?怎么又打不过妖怪呢?这个 问题看似简单 ,实则意义非凡,可以说是解读《西游记》的鲜明分界线 :《西游记》因此从纯粹的娱乐功能中剥离出来,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由此得以直接逼近其复杂内涵。
细读作品,孙悟空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美猴王到孙行者的转变。大闹天宫时的美猴王,上天入地下海所向披靡 ,失手被擒之后任凭刀砍剑刺、火烧雷打,不 曾损动分毫 ,八卦炉神火锻炼 ,反炼就了他 的火眼金睛、铜头铁臂。可在保护唐僧取经途中,却屡屡受挫,原因何在?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为什么就降伏不了那些妖怪?是创作上的前后矛盾还是另有深意?作者创造了那么一个豪放不羁、无所不能的英雄 ,却为什么又要把他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我认为,孙悟空形象塑造上的前后反差不是作者创作上的疏漏,而是基于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对当时广大士子命运的清醒认识。
孙悟空输给如来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后,欲求难脱 ,只得皈依佛法 ,保护取经人往西方拜佛,修功正果。入彼法门,修持正法 ,只有苦练邪魔 、尽心修悟 ,方能寂灭成真 ,信心正果,所 以悟空经历的万千磨折只不过是归真正果的必经劫数。花果山的美猴王无欲无求,是不伏天地管辖的混元天真 ,他 自由自在翻天搅海无所不能 ,而护法的孙行者则要求功德圆满,如此一来,事事便都不同。佛门佛门的规矩 ,以前可以欺天诳上,随心所欲现在头上有金箍,稍有不尊教令 ,就有人收管,跟前是师父唐僧时时以紧箍咒相挟,远者有菩萨、如来以功果相诱。如果图自在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就是 自毁前程 ,“到底也只能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第 l4回),至此,孙行者想要折回花果山却是再也不能了。就像观音说的,从一开始就 只有 紧箍 的咒 ,“无甚 么松 箍儿 咒”。(第57回)
而像作者一般的读书人 ,命运和孙悟空又有何异?不走仕途倒可清闲 自在 ,可也进入不了社会的主流,满腔抱负也无 由实现,可一旦踏上科举入仕之途,命运便如牵线风筝不能 自主。科举仕宦体制 自有他运行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织就 了一张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网,束缚着读书人 的身体、意志、思想。想要忤逆不顺,就有人念动咒语,让你生死不能;想要挣脱解放,“前程”二字让你首鼠两端,欲罢不能;想要有所作为,盘根错节的人事网总是多方掣肘 ,让你无所作为。《西游记》中孙悟空降妖除魔的经历就是现实环境里那些位卑志远的英雄们有志难伸、有恨难平的真实写照。
书中黄风岭用三味神风吹得悟空眼不能开,身不能近的是灵山脚下一只得道老鼠。棒杀吃人尸魔,唐僧听信谗言大念紧箍咒不说,还怒写贬书将悟空逐回花果山。把悟空压在三山之下,使山神土地为奴当值的平顶山金角银角怪乃太上老君的守炉童子,据说是观音求来托化妖怪考验唐僧师徒真心的(果真如此?观其行径不像,还觊觎唐僧 肉)。乌鸡 国推王下井,侵夺江山的是佛旨差来的文殊 坐骑青 毛狮 子,占黑水河神府、伤众 多水族、要蒸吃唐僧肉的河妖是西海龙王的外甥 ,陈庄吃童男童女的通天河妖是观音莲花池里一尾浮头听经的金鱼。金兜洞 的独角兕来历神秘、神通广大,悟空并一干天神罗汉无人能伏 ,原来是无上仙宫太上老君栏中的青牛。毒敌山琵琶洞的母蝎子精只不过曾经在雷音寺听佛谈经 ,就令悟空发怵,菩萨也不 能近身 (此怪 大概算如来 的私淑 弟子吧)。弥勒佛祖跟前司磬的黄眉童儿化身黄眉老怪,在小西天假充佛祖 ,他法力无边 ,金铙罩悟空,一个布搭包儿可 以囊括一切,任你是能耐通天 的神兵神将,也概莫能逃。比丘国妖言惑主,谋取千名小儿心肝的妖道是寿星的脚力 白鹿。唐僧昏昧不明执意救下来的老鼠精供奉着义父李天王义兄哪吒的长生牌位。将唐僧师徒并玉华王父子一并衔去 ,将悟空捆打无数的九灵元圣是太 乙救苦天尊坐下的九头狮子。摄藏天竺公主,假合真形,欲破唐僧元阳的是蟾宫玉兔。
凡此种种 ,或因命定的劫数,或因唐 僧的昏昧,或因妖魔 的来历不凡——与上界仙佛们不是沾亲带故,就是门生僮仆,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水火不侵的孙行者受伤 、吃亏或是无功而返那都是可以理解的了。而降伏了的妖魔 ,就算他们伤生害命、犯下滔天的杀孽,他们的主人至多就是呵斥两句,不说死罪,活罪也都要饶过,悟空想要彻底剿杀是万万不能 ,连薄施惩戒主人都会求情,最后悟空能做 的也就是收拾一下洞里那群小妖,一切罪孽都 由他们顶了。这就是悟空的困境:明明是降妖除害 ,却每每蒙冤受屈,受昏庸无能的唐僧的辖管;明明是私下凡尘为害作孽 ,非要说 “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明明是吃人无数的凶魔狠怪,只要在主人面前温顺 听训 ,一切罪孽都烟消云散。而悟空的这诸般 困境,正是作者 审视 当时黑 暗政治现实环境后的无力与无奈,也是当时无数仁人志士的无力与无奈。“不专纪鬼,时纪人间变异 ,亦微有鉴戒寓焉”,可见,作者创作《禹鼎志》时的意图在创作《西游记》时更为明确了:假托神魔来演绎现实故事。
有指证现实的诉求 ,就决定 了《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人性化和世俗化,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人性化和世俗化 ,又使得吴承恩的《西游记》在指证现实时更入木三分。 唐僧师徒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灵山,拜求真经,如来吩咐传经 ,手下尊者阿傩、迦叶竟公然索要人事 ,索贿不成就传白本经书,悟空告到如来座前,如来却说经不可轻传空取,否则,叫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进而强辩 白本乃无字真经,反诬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如来此举 ,一则是罔顾是非,颠倒黑白,一则是挟经取利,违逆佛家教旨,很像是人世间卖官鬻爵、渔民取利、昏聩不 明、是非不辨的君王的作为。有这样的如来撑腰,二尊者当然不思悔改 ,竟能二度索要人事。唐僧只得把吃饭的紫金钵盂奉上,阿傩被宝 阁的力士 、庖 丁、尊者们羞得脸皮都皱了,手中还是拿着紫金钵盂不放。就这一细节,所谓神佛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神圣庄严之相 立时轰然坍塌,而其罔顾廉耻的贪婪却跃然纸上,分明是人世间贪官的面貌。
再看吃尽狮驼 国一国人众的大鹏金雕 ,凶五百年,无人问津,更有甚者,他“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王曾与他为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罗以兄弟相称 ,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这是为何?不知道他的罪孽?不是 ,只因天界 、佛界都知他与如来有亲 ,如来算来还只是他的外甥。最后如来亲来收服 ,那魔 头仍不悚惧 ,还想杀如 来 ,夺雷音宝刹。受 困之后不思悔罪还敢叫嚣不止 :“你那里持斋把素 ,极贫极苦 ;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衍。”如此狂妄嚣张,如来不仅不加 申斥 ,反是许诺 ,“我管 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 ,凡做好事 ,我教他先祭汝 口。”
这不是愚弄欺 害天下信众吗!从骄横 凶残、恣意妄为的大鹏金雕 ,我们看到的是人世间那些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横行无忌的皇亲贵眷们的画像 ,对金雕的滔天罪行不仅视若无睹还曲意相交的神佛们又何异于人世间那些明哲保身、罔顾正义 、曲意奉承的大小官吏?众生瞻仰、大慈大悲的如来对如此罪孽不但不闻不问,不施惩处 ,反而许 以美馔 ,还让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 ,这不正是人间那些昏昧不明、颠倒处事、漠视生灵的昏庸之君吗? 与此相反的是 ,监观万天、浮游三界的玉皇大帝因凤阳郡郡侯无意推翻斋天素供 ,触犯天尊这一小节,就不管那郡侯是如何 的清正贤 良、重爱黎民,也 不论 全郡百姓的无辜 ,严令凤 阳郡连年亢旱 ,累岁干荒,闹得民不聊生 ,百姓吃人顾命 。
两相比较,哪有什么天 理?哪有 什么慈悲?哪里有善恶,哪里有正义?众生顶礼膜拜的如来、玉帝、神佛们都是如此作为,又如何会有 朗朗乾坤、清明世界?拂去祥云瑞霭的极乐世界 ,实际也是个你欺我害的现实世界,诚如唐僧所说:“徒弟呀 ,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隐去头上神秘光环的神佛们,长的也是追名逐利、斤斤计较的凡人心肠。神佛们虽高居天上,可作者给他们画的相是人间的相,和世间凡人 的面貌脾性一般无二;所行之事也是人间之事,和凡人思想行径并无二致 。作者给我们描画的不再是高高在上、远离人问烟火的神佛,而是 一个个有 着真切性情的人。
而所谓取经的圣僧,抛开那金蝉子转世 的喙头,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凡夫俗子。胆小懦弱、专断易怒 、昏聩无能、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一见山高林密,就惶恐悚惧;每逢遇险遭难 ,必垂泪悲啼 ;徒弟行事稍有差池 ,立生怨怼;《多心经》时时念诵在口,万千恐惧却常挂碍在心。悟空尽心除害,他却昏乱胡信,一任八戒谗言撺唆;肉眼凡胎不识妖邪,还每每嗔怪悟空惫懒无 良善之心。悟空打杀打家截道 、杀人放火的贼寇 ,他狠心念咒驱徒 ,不为慈悲,只为悟空杀生害命,妨碍他积功累德;狮驼岭误认悟空丧命,他跌脚拳胸,不为师徒情义 ,只痛惜西天拜佛他们弟子同众的功劳化作了尘土。这样的唐僧,经历干蛰万魔之后虽正果成佛,也不过脱却了肉身凡胎罢了,心还是凡心一颗。 在这一从神佛到人从圣僧到人 的还 原过程中,一切世俗本相皆清晰在目。所以鲁迅先生 、胡适先生认为《西游记》有游戏之意,有滑稽谐趣之旨,也不无道理。因为所谓上界事就是身边事 ,所谓佛圣僧就是身边人,虚幻的神魔世界处处可见现实世界的投影,如此 ,读者对神的虔诚敬畏在这一还原过程中便被不知不觉地消解了。身边的人和事常常是不可随意论说的,神佛们 的龌龊卑怯作者却可以借着悟空、八戒嚷破,并加以揶揄嘲弄,读者读来怎能不觉得轻松有趣? 但笔者认为 ,作者的创作又不纯粹只为游戏、谐趣。
考据西游 的成书,现存《西游记》最早刻本— —金陵世德堂本上有陈元之于万历二十五年写的序 ,由此可以确定西游成书于万历二十五之前,作者应该是生活在嘉靖和万历年间。明朝中叶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腐败 、动荡不安在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明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暗于用人,昏于行事 ,以致宦官奸佞擅权索贿,特务肆虐,民不聊生;明世宗则迷信道教,一心只求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父子长期把持朝政,贪赃枉法,弄得吏贪官横,民生凋敝;穆宗神宗两朝皇帝也都是昏惰朝政,耽于逸乐,史书更称神宗是“以金钱珠玉为命脉”的人。当此之时,任何美好的社会理想都会破灭,心怀正直的人必定碰壁。对这一切,一生仕途坎坷的吴承恩是深有体会 ,感愤在心。《西游记》中描摹了两个世界,一是神魔世界 ,如前所述,这个世界并非清明世界;二是凡人世界,这个世界作者借如来之口也有备述:“天高地厚 ,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 ,多欺多诈;不尊佛教 ,不向善缘 ,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 ,害命杀生 ,罪盈恶满”。这两个世界虽判然有别,实为一体,二者的构筑可以说就是在为现实世界绘影图形。所以,在游戏、谐趣之余,作者更多的是要向我们传达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观察与针砭。
特里 ·伊格尔顿在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兴起时指出,文学的学者们占据 的是更受珍视的感情与经验的领域,而谁的经验和什么样的感情,则意味着会产生不同的问题。那么 ,当我们解读吴承恩的西游时,我们就不能不去考察作者现实的经历和他的思想情感;《西游记》所具有的浓厚的神魔色彩可以归之于作者大胆自由的想象,而这想象搭乘的翅膀却是作者的深切的人生体验。
伊格尔顿还谈到 ,“经验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故土,是它扎根最深的地方,而且以其文学的形式还是一种想象的经验的自我实现”。¨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想象来补足实际经验的贫乏,实现对理想的渴望。那么,孙悟空这一形象则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作者对自由理想、个体价值的热切追求和他正视现实的妥协与折 中;反映了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不为修心正道,不为游戏 ,现实批判是其思想旨趣。
[1][2][3]刘怀玉.吴承恩诗文集笺校·附录[M].原刘修业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