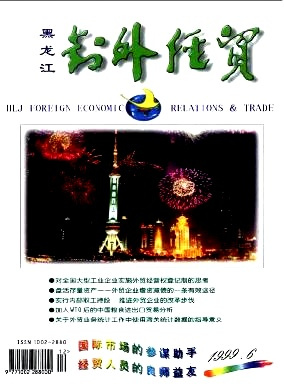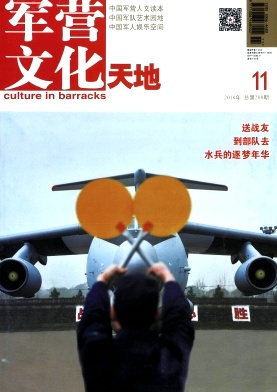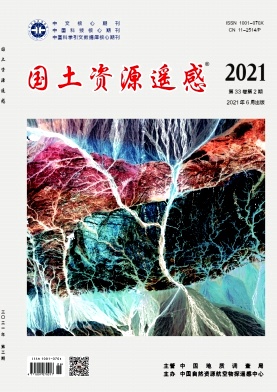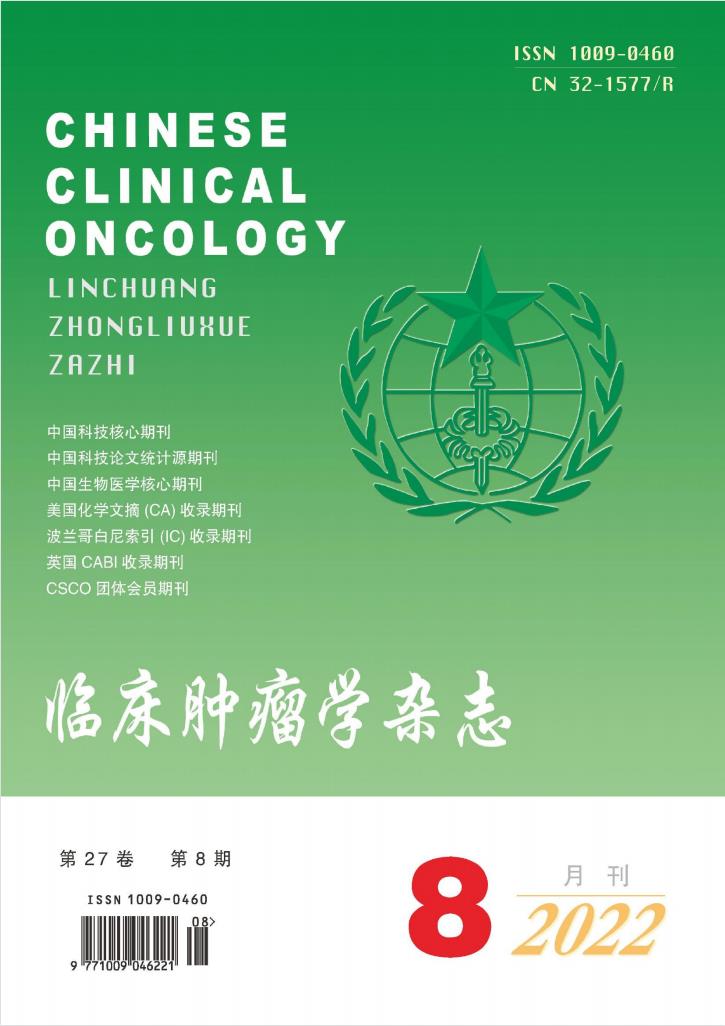文学鉴赏的主观性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性———读《古诗赏鉴四题》兼与彭运生教授商榷
佚名 2008-12-08
《名作欣赏》二零零六年六月号上半月刊刊发的彭运生教授的《古诗赏鉴四题》,在阐发了自己对四首古诗(或其中名句)的独特理解的同时,也对某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发出了质疑。读过该文,感慨良多,禁不住也要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发表点个人的看法,并与彭先生商榷。
一
读过彭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对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特点又有了鲜明而深刻的体认。
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单纯来自于作家的赋予,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为我们所熟知的名言正道出了文学鉴赏活动的主观性特点。而这并非只是经验之谈,二十世纪西方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斯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无论是接受美学的理论,还是文学鉴赏活动的实际都表明,每个读者在文学鉴赏活动中,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性情气质、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艺术观等方面出发去看待作品的。面对以语言符号构筑的文学形象和意境,读者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丰富的想象、联想能力,融入深邃的情绪情感体验,借助敏锐的感悟能力和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通过对作品符号的解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体验、理解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渗入自己的情感、思想、性情气质和人格精神,对原有的艺术形象和意境进行开拓、补充和再创造,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从而使作品的意义“溢出”了作者原来设定的意义框架,产生出作者所意想不到的意义来。这就是对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的原因。
彭先生在文章中,分别就四首古诗(或其中名句)质疑了同时代的其他几位论者的理解和阐释。如认为郭应德、过常宝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对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的解释是“顺着天然信仰说出来的话与科学无关”;认为张世英先生在《新哲学讲演录》中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的“艺术上的考证既不必要,也不合法”;认为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中讲解杜甫的《蜀相》时“所言‘诗人不禁热泪涟涟’,不仅言之无据,而且似乎意味着此诗是诗人悲伤、无望心情的产物”。与此同时,彭先生以“在我看来”为引领,分别出示了自己对这几首古诗或其中名句的理解与阐释。然而,在笔者看来,彭先生的解释亦不过是体现了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的一家之言而已,并未真正实现其所追求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其对《早发白帝城》的“妙处”的阐释,尽管颇有逻辑性和哲理性,但仍不免使人困惑:“此诗内在雄辩地暗示了象征着‘高度’的‘白帝城’的价值”,这一结论从何而来?言之所据又在哪里呢?所以,尽管彭先生从“科学”出发“断然拒绝”考证和想象、联想这类“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时的本能反应”,但事实却是,拒绝了考证的彭先生,却无意识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想象的陷阱,其充满个人主观性的作品意义阐释,最终让我们也只能把它当成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而已。
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特点,认识到“不同的读者在作品中投入不同的情与理,就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接受和意义阐释,⋯⋯但任何一种阐释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有其合理性”(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年版,第347 页),,谁也不能说自己对某一作品的欣赏才是最正确的体验和最完美的解释(当然彭先生也并未如此说),而且正是不同的解释使作品的意义宽泛深远起来。
二
然而,肯定文学欣赏的主观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为,建立在文学鉴赏活动基础上的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学鉴赏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审美享受为目的,富于主观性、感受性和个人倾向性;文学批评以对作品意义和价值的审美理解、审美判断为旨归,要求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不带个人好恶的公正性。而要保证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公正性,科学的批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在此仅对彭先生文章中所涉及到的考证法和文本分析法做些必要的探讨。
关于文学批评活动中的考证法,彭先生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艺术上的考证既不必要,也不合法”。在他看来,“这样的考证,实质上是想到日常人生中去寻找艺术的本质”,这说明他不认为艺术的本质与日常人生有什么联系;可紧接着他又说:“而实际上,我们更多地只能通过艺术而理解人生的实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艺术的本质与日常人生无关,那么为什么我们又“更多地只能通过艺术而理解人生的实质”呢?从这自相矛盾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彭先生在艺术本质与日常人生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还不甚明了,而这恰恰影响了其对考证法在文学批评中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的认识。
其实,无论是艺术发生学的研究还是艺术生产(创造)的研究都表明了,艺术从根本上讲来源于生活又超越了生活。作为文学艺术体裁之一的诗歌,其本质就在于或抒情言志,或阐发事理。而诗人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释之理,既来自于日常人生经验的激发,又显示出超越日常人生经验的努力和追求。关于诗歌的这一本质,并非“人类的一种天然信仰”,而是被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事实、真理。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进行诗歌批评时,便可以采用考证法,即由孟子提出、后被广为运用的“知人论世”法。当我们了解了作者的性格、志趣、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就会对作品中的“情”“志”“理”的内涵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例如,当我们了解了杜甫一生由开元盛世的读书、壮游到奸臣当道求仕不得的十载长安困守、安史之乱爆发后的陷贼逃难与为官遭贬及至生命最后十余年的漂泊西南客死舟中的命运遭际,了解了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内心情感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就不难理解其在《蜀相》中借对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命运遭际的慨叹而抒发的自身壮志未酬的悲愤了,也就不会再发出“所谓‘诗人不禁热泪涟涟’又是从何得知的信息?难道诗中的‘英雄’是诗人的自指?”这样的疑问了。拒绝考证,拒绝“自由任意的想象”和“只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出到作品之外”的联想的彭先生,在对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时,也显示出了一定的问题。比如,他在反对其他论者对《滁州西涧》的分析时说:“所谓‘独处’和‘自由’、‘幽冷’和‘孤寂’以及‘诗人内心的凄怨和忧郁’,郭应德先生又是怎么知道它们的存在的呢?它们不是天然信念支配下的无意识虚构或捕风捉影吗?它们不就是批评家对诗中‘独’和‘幽’等字眼儿见了风就是雨的结果吗?”这里姑且不论他所批评的郭应德先生的见解是否正确,仅以他对文本语言批评(即他所谓的就作品中的某些字眼儿“见了风就是雨”的“捕风捉影”的分析)方法的反对而言,笔者是不能苟同的。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为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人正是靠着对语词的精心选择和组织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旨趣的。因此,我们应该也完全可能通过对文学作品语言符号辞面与辞里意义的解码,来探寻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进而发掘出超出作品原来意义框架的“言外之意”。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注重炼字炼句,因此,采用“咬文嚼字”法或英美“新批评”家所谓的“细读”法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如果脱离了蕴涵着作家的情感、思想的文本语言而大谈特谈作品的意义,岂不真正成了“无意识虚构”或“自由任意的想象”?
另外,彭先生在分析《滁州西涧》一诗时说:“这首诗共有四句,但后两句本身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并就“小舟缘何偏‘自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其在方法上犯了断章取义、肢解整体的错误。任何文学作品,不管是一首小诗还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作为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个由各个构成要素有机统一而成的整体,作品的意义、价值也正存在于这有机统一的整体之中,如果将这一整体割裂开来,抽取其中的某一部分,并不顾其与整体中其他构成要素的内在联系而单纯地片面地加以分析和引申,所得出的结论便不会是作为整体的原作本身应有之义,而文学批评却要求我们尽可能客观、公正、科学地分析作品本身原有的内涵,并正确地指出其艺术价值和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因此,如果以文学鉴赏而论,彭先生采用“摘句”法对“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所做的“妙处在于创造出了需要救助的弱者以及诱使弱者接受救助”的解释,还是可以作为体现了彭先生个人的性情、人格、思想、情感的一家之言而被我们玩味一番的(尽管我们可能也可以不表示赞同),但是,如果上升到彭先生极力倡导的“科学”的文学批评的高度来
看,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断章取义的批评方法,就只能因其“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与作品应有之义相去甚远而引起我们的不满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彭先生在其文章中多少混淆了具有主观性的文学鉴赏与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文学批评的界限。其文章名为《古诗赏鉴四题》,这意味着此文是文学鉴赏活动的成果。然而,作者在文章中又多是在批评了其他论者的解析不是“科学”的文学批评的前提下来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这就暗示了彭先生本人的解释才应是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标准的文学批评。但事实是,我们从中并未看到多少有科学根据的分析和结论,而且有些结论,如把《蜀相》一诗的“灵魂”归结为“对于死亡的厌恶”,说“此诗的妙处(即所谓悠长余兴)在于它内在的雄辩,具体说在于它对于死亡的消极价值作出的反复的隐秘论证”,不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或许笔者过于愚钝,不能明了彭先生文章中“隐秘的论证或者内在的雄辩”,甚至对彭先生之文多有误解?那就只能深表遗憾和歉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