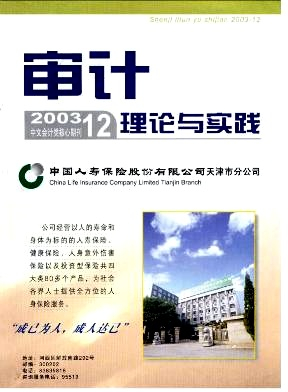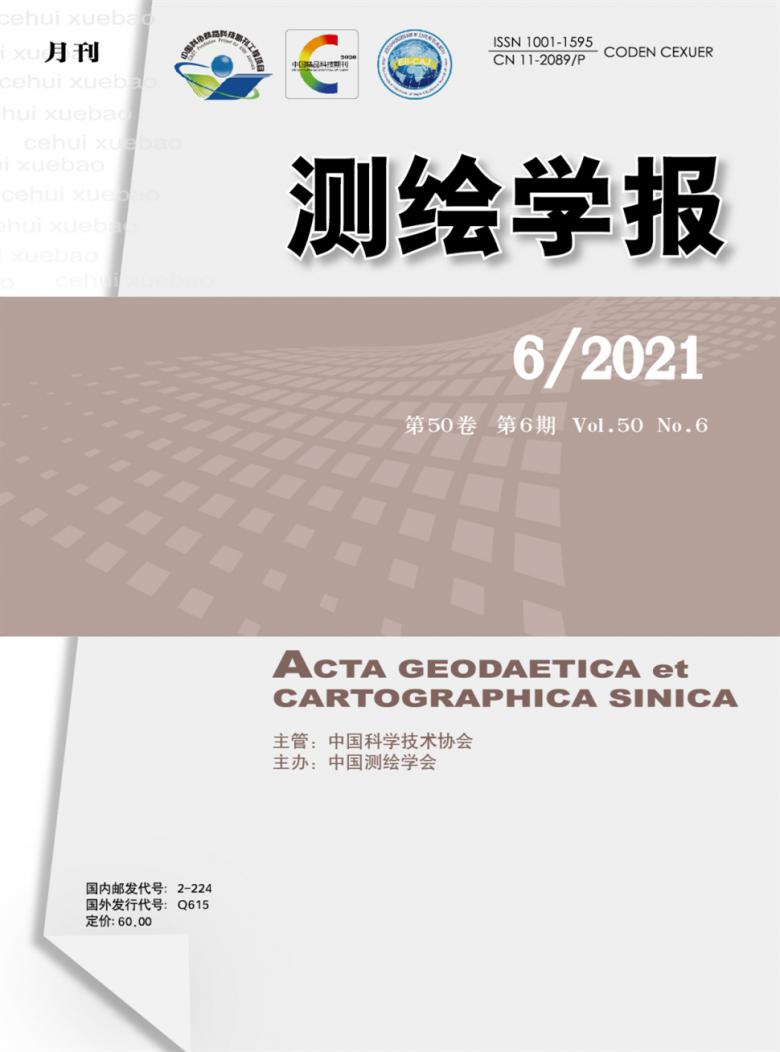论作为“立法”策略的孔子诗学
李春青
提要: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士人思想家是以“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在彼时的文化领域的。孔子是其代表。他的思想学说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士人思想家这种“立法者”的特殊身份。孔子的诗学思想与他的“立法”活动密切相关,或者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其“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合法性 立法 诗 自我神圣化
一
士人思想家的立法冲动首先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崩乐坏”不仅仅是指西周的典章制度受到破坏,而更主要的是表明了在三百年的西周贵族社会中形成的那套曾经是极为有效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这就出现了“价值真空”的局面。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不再相信任何普适性的道德和信仰的价值规范。韩非所说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i]正是指这种情形而言。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都奉行实力政策,全副精神用于兼并或反兼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根本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的建设。于是那些处于在野地位的士人思想家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建构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为天下立法的伟大使命。
那么士人思想家为自己的立法行为所采取的策略和价值取向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主要看儒家的情况:
如前所述,西周礼乐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儒家士人。表面看来,儒家士人是士人阶层中最为保守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与主张彻底抛弃礼乐文化的道家以及主张用夏礼的墨家并无根本性区别,他们都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乌托邦,目的是为社会制定法则。区别仅在于:儒家是要在废墟的基础上,利用原有的材料来建构这个乌托邦,而道家、墨家则是要重新选择地址来建构它。所以儒家也不是什么复古主义,他们同样是要建构乌托邦。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就必然要对那些原有的建筑材料——西周的文化遗存进行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功能;又因为他们毕竟是借助了原有的建筑材料,所以他们的乌托邦也就必然留有旧建筑的痕迹。这两个方面都在儒家关于诗歌功能的新阐发中得到表现。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理解与诗歌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实际功能已然相去甚远。例如颂诗和二雅的一部分原本是在各种祭祀仪式中用来“告于神明”的乐舞歌辞,这可以说是诗歌在西周官方意识形态中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了。但是声称“吾从周。”的孔子却对诗的这种重要功能视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在孔子的时代诗歌原有的那种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已经随着西周贵族制度的轰毁而荡然无存了。而孔子的言说立场也不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立场,而是处于民间地位的士人立场。在西周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诗歌作为人神关系中的言说方式实际上负载着强化既定社会秩序、使贵族等级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使命。而对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士人来说,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而不是强化已有的社会秩序。
但是对于诗歌原有的沟通君臣关系的功能孔子却十分重视。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ii]诗如何可以“事君”呢?这里主要是靠其“怨”的功能。孔子将“怨”规定为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对西周之末、东周之初产生的那些以“怨刺”为主旨的“变风变雅”之作的肯定。“怨”不是一般地发牢骚,而是向着君主表达对政事不满的方式,目的是引起当政者重视而有所改变。所以,孔安国认为“怨”是指“怨刺上政”,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朱熹将其释为“怨而不怒”就明显隔了一层。“怨刺上政”并不是单方面地发泄不满情绪,而是要通过“怨”来达到影响“上政”的目的。这样才符合“事君”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西周至春秋中叶之前,在贵族阶层之中,特别是君臣之间的确存在着以诗的方式规劝讽谏的风气。《毛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或许并不是想当然的说法,而是对古代贵族社会内部某种制度化的沟通方式的描述——诗歌被确定为一种合法的言说方式,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即使错了也不可以定罪。
所以孔子对诗歌“怨”的功能的强调并不是赋予诗歌新的功能,而是对诗歌原有功能的认同。孔子虽然已经是以在野的布衣之士的身份言说,但是他的目的却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所以对于西周文明中某些方面还是要有选择的保留的。
诗歌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那种独特的作用即“赋诗明志”,大约是西周时期贵族内部某种以诗歌来沟通人际关系的言说方式的泛化。根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在聘问交接之时通过赋诗来表达意愿并通过对方的赋诗来了解其意志甚至国情成了普遍的、甚至程式化的行为。赋诗的恰当与否有时竟成为决定外交、政治、军事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尽管“赋诗明志”的文化现象与孔子的价值取向并无内在一致性,但是对于诗歌这样实际存在的特殊功能孔子却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他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iii]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iv]这里“无以言”的“言”,显然即是“专对”之义,指外交场合的“赋诗明志”。孔子这里提倡的是诗歌的实用功能,与儒家精神无涉。所以随着诗歌的这种实用功能的失去,孔子之后的儒家如子思、孟子、荀子等人那里再也无人提及它了。
二
孔子毕竟是新兴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对诗歌的功能自然会有新的阐发。他之所以不肯放弃对诗的重视是因为儒家的基本立法策略是在原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建构而不是另开炉灶;而他之所以要赋予诗歌新的功能是因为他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或者说赋予诗歌新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将诗歌当作修身的重要手段上。《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中的一句,是说鲁僖公养了很多肥壮的战马,这是很好的事情。这里并不带有任何的道德评价的意味。但是在孔子这里却被理解为“无邪思”之义。朱熹说:“‘思无邪’,《鲁颂·駉》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如此之名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v]这里当然有宋儒的倾向,但是大体上是符合孔子本意的。这可由其他关于诗的论述来印证。其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儒包咸注“兴于诗”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vi]朱熹注云:“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可知汉儒、宋儒持论相近,都是认为孔子将诗歌作为修身的必要手段。孔子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vii]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学习了《周南》、《召南》才会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才会做人,否则就会寸步难行。同样是将诗歌作为修身的手段。在孔子看来,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美善人性的表现,而不在于其外在形式。所以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viii]按照孔子的逻辑也完全可以说:“诗云诗云,文字云乎哉?”——诗歌的意义不在于文辞的美妙,而在于其所蕴涵的道德价值。
由此可见,原本或是祭祀活动中仪式化的乐舞歌辞,或是君臣上下沟通方式,或是民间歌谣的诗歌在孔子这里被阐发为修身的必要手段。诗歌原本具有的那些功能: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使既定社会秩序合法化以及沟通上下关系、聘问交接场合的外交辞令等,在孔子的“立法活动”或价值重构工程中都让位于道德修养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将修身视为诗歌的首要功能呢?这是一个极有追问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与孔子所代表的那个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直接相关,同时也是一种“立法”的策略。对此我们在这里略做探讨。
孔子所代表的这个被称为(亦自称为)“士”的知识阶层是很独特的一群人。依照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属于“民”的范畴,没有俸禄,没有职位,不像春秋以前的作为贵族的“士”那样有“世卿世禄”的特权。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唯一的依据就是拥有文化知识。此外他们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是这个阶层却极为关心天下之事,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这或许是他们秉承的文化资源即西周的王官文化所决定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生存在那样一个战乱不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希望靠关心天下之事、解决社会问题来寻求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管什么原因,这个阶层的思想代表们——诸子百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都试图为这个濒于死亡的世界秩序提供疗救的良药。
诸子百家之学本质上都是救世的药方。那么如何才能救世呢?
首先就是为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制定法则。所以诸子百家实际上人人都在扮演立法者的角色。如果说老庄之学的主旨是要将自然法则实现于人世间,即以自然为人世立法,那么儒家学说则是要在西周文化遗留的基础上改造原有的社会法则。在充当立法者这一点上老庄孔孟以及其他诸家并无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是立法者呢?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将自己塑造为立法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
儒家的策略是自我神圣化。我们知道,儒家是在继承西周文化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学说的,商人尊鬼神,周人重德行,所以他们就抓住了一个“德”字来为自己的立法者角色确立合法性。看西周典籍如《周书》以及《周易》、《周颂》、《周官》等,周人的确处处讲“德”。如《洪范》讲“三德”、《康诰》讲“明德慎罚”、《酒诰》讲“德馨香祀”、《周礼》讲“六德”、《周颂·维天之命》讲“文王之德之纯”等等。这都说明周人确实是将“德”当作一种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观看待的。周人的所谓“德”是指人的美德,也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恭敬、正直、勤勉、勇毅、善良的品质。盖西周政治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所以要维持贵族内部的和谐团结就必须有一种统一的、人人自觉遵守的伦理规范。“德”就是这种伦理规范的总体称谓。孔子对周人遵奉的伦理规范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细密、系统,从而建构起一种理想化的圣贤人格。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素质。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孔子教授弟子的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也是儒家士人自我神圣化的主要手段。例如“君子”本来是对男性贵族的统称,例如《诗经·魏风·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谓就是指贵族而言。但是到了孔子这里“君子”就成了一种道德人格:有修养、有操守的人称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例如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ix]孔子要求他的弟子都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君子、小人之分暗含着对立法权的诉求:我是君子,所以我有权为天下制定法则。
所以孔子对圣贤人格或君子人格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就是证明自己立法活动之合法性的过程。而且这种君子人格所包含的价值内涵实际上也就是孔子所欲立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立法活动与证明立法权之合理性的活动就统一起来了。这真是极为高明的文化建构策略。然而无论孔子的策略如何高明,在当时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他的立法活动都是无效的,因为除了儒家士人内部之外他再也没有倾听者了。他的价值观念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获得合法性。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话语系统,孔子的思想在后世得到了最为广泛、最为长久的普遍认同,同时孔子本人也被后世儒者继续神圣化,直至成为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最高权威。这正是孔子特别强调诗歌的修身功能根本原因之所在。
孔子在为天下立法过程中建构起的话语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精英文化。孔子及其追随者为了维护这种精英文化的纯洁性,极力压制、贬低产生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因为只有在与下层文化的对比中方能凸现出精英文化的“精英”性来。这一点在孔子对“雅乐”的维护与对“郑声”即“新乐”的极力排斥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x]这里所谓“雅乐”是指西周流传下来的贵族乐舞,其歌辞便是《诗经》中的作品。这类诗乐的特点按孔子的说法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是可以感发人的意志,引导人向善的。“郑声”则是产生于郑地的民间新乐,其特点是“淫”,即过分渲染感情的。
孔子通过对“雅乐”与“郑声”的一扬一抑、一褒一贬确立了儒家关于诗歌评论的基本原则,凸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根本差异,并确立了精英文化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如果“郑声”仅仅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化孔子恐怕也没有兴趣去理睬它。看当时的情形,“郑声”这种民间艺术似乎颇有向上层渗透的趋势,甚至有不少诸侯国的君主都明确表示自己喜欢“新声”,而不喜欢“雅乐”。也就是说,“新声”以其审美方面的新奇与刺激大有取代“雅乐”的趋势。孔子是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为了维护精英文化的合法性,就必然会贬抑民间文化,这里并不完全是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孔子凸显精英文化之独特性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与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及民间文化区分开来,以便充分体现儒家学说作为“中间人”的文化角色,如此方可代天下立言。
三
下面让我们来看在孔子对《诗》的理解中是如何贯穿这种文化角色以及这种文化角色是如何影响到孔子的诗学观念的。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因为影响了孔子的诗学观念也就等于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诗学。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经将原有的三千多首诗作“去其重”,编订为后来《诗经》的规模。于是便有了历代相传的孔子删诗的说法。自清代以来,疑者蜂起。不管孔子是否真的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都丝毫不影响他在诗学观念上的伟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对诗歌功能做出全面、深刻阐述的思想家。但是,孔子的诗学观念又是十分复杂的,以往人们对这种复杂性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深入理解了。在我看来,孔子诗学的这种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他对诗歌功能的认定乃是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或者说,是出于对诗歌在历史流变中呈现出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政治文化功能的兼收并蓄。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则是对《诗》充当“中间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坚持。还是先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是如何论及诗歌功能的吧!
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
2、“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3、“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4、“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5、“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以上五条是孔子对于《诗》的功能的基本看法。我们如果稍稍进行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功能实际上并不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它们并不是同一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简单说,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形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孔子对诗歌在实际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之作用的概括总结,还是他寄予诗歌的一种期望?是他个人对诗歌功能的理解,还是当时普遍的观念?
上引1、2两条毫无疑问是讲修身的。对于“兴于诗”,朱熹注云:“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xi]朱熹的意思是由于《诗》是人的本性的呈现,所以具有激发人们道德意识的功能。关于第2条,历代注家皆以为“不为《周南》、《召南》”,即意味着不能自觉进行道德修养,因此就像面墙而立一样,寸步难行。然而考之史籍,修身实非诗歌的固有功能。据《周礼》、《礼记》记载,诗歌的确是周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西周,诗与乐结合,同为祭祀、朝觐、聘问、燕享时仪式的组成部分,属于贵族身份性标志的重要方面。而在春秋之时,诗则演化为一种独特的外交辞令,更不具有修身的意义。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修身功能乃是他自己确定的教育纲领,当然也是他授徒讲学的实践活动所遵从的基本原则。因此孔子关于诗歌修身功能的言说可以说是他与弟子们构成的私学文化语境的产物,在当时是没有普遍性的。根据孔子的道德观念与人格理想,他的修身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人改造成为能够自觉承担沟通上下、整合社会、使天下有序化的意识形态的人:在君主,要做到仁民爱物、博施济众;在士君子,要做到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教化百姓;在百姓,则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师长。
总之,孔子基于“修身”的道德目的来理解《诗》,就必然使他的“理解”成为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无论一首诗的本义如何,在孔子的阐释下都会具有道德的价值——这正是后来儒家《诗经》阐释学的基本准则。
第3、4条是讲诗歌的政治功能。看看《左传》、《国语》我们就知道,这是春秋时普遍存在的“赋诗言志”现象的反映。《左传》一书记载的“赋诗”活动大约有六十余次,其中最晚的一次是定公四年(前506年)楚国的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为赋《无衣》。这一年孔子已经45岁。这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赋诗言志”依然是贵族的一项受到尊重的并具有普遍性的才能。尽管在论语中没有孔子赋诗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见,在他周游列国的漫长经历中,一定也像晋公子重耳那样,所到之处,与各国君主、大夫交接之时常常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的。这样,孔子对诗的“言”或“专对”功能的肯定就是彼时大的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具有某种必然性。倘若在孟子或荀子那里依然强调诗歌的这一功能,那就显得莫名其妙了。对于这种对《诗》的工具主义的使用,按照孔子的思想逻辑,是不会予以太大的关注的,因为他历来主张“辞,达而已矣”,并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是由于在他生活的时代利用诗歌来巧妙地表情达意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贵族身份的标志,所以他也不能不对诗歌的这种功能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
第5条是孔子关于诗歌功能的最重要的观点,其产生的文化语境也最为复杂。关于“兴”,孔安国说是“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以理度之,朱说近是。此与“兴于诗”之“兴”同义,是讲修身(激发道德意识)的作用。关于“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为“考见得失”,二说并无根本区别,只是侧重不同而已。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功能。关于“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二说亦无根本差异,只是朱注略有引申,而这种引申非常符合孔子本意。孔子尝云:“君子衿而不争,群而不党”朱熹注云:“和以处众曰群。”[xii]可见这个“群”具有和睦人际关系之意。这是讲诗歌的沟通交往功能。关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朱熹注为“怨而不怒”。意近。这也是讲诗歌的政治功能。
如此看来,“兴、观、群、怨”涉及到诗的三个方面的功能。关于修身功能已如前述,不赘。关于沟通、交往功能则《荀子·乐论》有一段关于音乐功能的言说堪为注脚。其云: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xiii]
这里所说的“乐”是包含着“诗”在内的。
关于政治功能,孔子是从两个角度说的:一是执政者的角度,即所谓“观”,也就是从各地的诗歌之中观察民风民俗以及人们对时政的态度。在《孔子诗论》中有“《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也。”[xiv]之说,可以看作是对“兴、观、群、怨”之“观”的展开。二是民的角度,即所谓“怨”,亦即人民对当政者有所不满,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孔子诗论》云:“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xv]这是对“怨”的具体阐释。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诗歌这种“怨”的功能十分重视,并且认为“怨”的产生乃是“上下不和”所致。而“怨”的目的正是欲使“上”知道“下”的不满,从而调整政策,最终达到“和”的理想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兴、观、群、怨”说的内在联系。
这样看来,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确认共有四个方面:修身、言辞、交往、政治。这四种功能显然是不同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是《诗经》作品在漫长的收集、整理、传承、使用过程中渐次表现出的不同面目的概括总结。这种对诗歌功能的兼容并举态度,是与孔子本人的文化身份直接相关的。如前所述,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他本人也曾在鲁国做过官,有着大夫的身份,他晚年也受到鲁国执政者的尊重,被尊为“国老”。这些都使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说话。但是,他毕竟又是春秋末年兴起的民间知识阶层(即士阶层)的代表,具有在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与自由精神,同时他作为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者、整理者,作为最为博学的西周文化的专家,对先在的文化遗产怀有无比虔诚的敬意。这样三重身份就决定了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理解和主张是十分复杂的。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对在当时普遍存在于政治、外交、甚至日常交往场合的“赋诗”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所以他强调诗的言说功能;作为新兴的在野士人阶层的思想家,他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提升十分重视,深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道理,故而时时处处将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对于长期存在于贵族教育系统中的《诗》三百,孔子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它成为引导士人们修身的手段。而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也必然使其对诗歌的“怨刺”功能予以充分的重视。最后,作为西周文化的专家和仰慕者,孔子对《诗》三百在西周政治文化生活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当然心向往之。而沟通君臣、父子、兄弟乃至贵族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可以和睦相处,使社会安定有序正是诗乐曾经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xvi]。因此对于诗歌沟通、交往功能的强调对孔子来说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在“兴、观、群、怨”四项功能之中,后三者最突出地表现了孔子对《诗》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观”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要他们通过诗歌来了解民情,从而在施政中有所依据,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与利益。“怨”是对人民表达意愿的权利的肯定,是鼓励人民用合法的方式对执政者提出批评。至于“群”,则更集中地体现了意识形态“中间人”的独特功能,是对于合睦、有序的人际关系的吁求。
孔子将《诗经》作品在不同文化历史语境中曾经有过或者可能具有的功能熔于一炉,其目的主要是使之在当时价值秩序开始崩坏的历史情境中,承担起重新整合人们的思想、沟通上下关系,建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将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某些文化文本的重新获得有效性之上——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的乌托邦精神之体现。所以对于《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孔子都是作为现实的政治手段来看待的。他说: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xvii]
包咸注云:“‘先进’、‘后进’,谓仕先后辈。礼乐因世损益,‘后进’与礼乐,俱得时之中,斯君子矣。‘先进’有古风,斯野人也。”[xviii]朱熹注云:“‘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程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xix]
根据这些注文我们可以知道,孔子之所以“从”被时人视为野人的“先进”,根本上是因为其奉行之礼乐质重于文,亦即重视实用而轻视形式。而“君子”的礼乐则相反,过于重视形式而忽视了实用。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月云月云,钟鼓云乎哉?”[xx]也正是强调礼乐的实用功能。孔子天真地以为,只要西周的文化典籍得以真正传承,那么西周的政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复。实际上,尽管这些典籍曾经就是现实的政治制度,可是到了孔子时代早已经成为纯粹的文化文本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产生相应的文化文本,而流传下来的文化文本却不能反推出它当初赖以产生、现在已经崩坏的经济、政治制度。这是先秦的儒家思想家所无法意识到的,也是先秦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xxi]
注释:
[i] 韩非子:《五蠹》,见《韩非子》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ii] 《论语·阳货》,《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iii] 《论语·季氏》,《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iv] 《论语·子路》,《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v] 《论语·为政》注,《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vi] 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九引,《诸子集成》本。
[vii] 《论语·阳货》,《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viii] 《论语·阳货》,《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ix] 《论语·里仁》,《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x] 《论语·阳货》,《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标点本1988年版。
[xi] 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泰伯》
[xii] 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卫灵公》
[xiii] 《荀子·乐论》
[xiv] 李学勤释文,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2001年3月版,第60页。
[xv] 王志平释文,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2001年3月版,第211页。
[xvi] 对于诗歌的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在后面将有深入探讨,这里暂不展开。
[xvii] 《论语·先进》
[xviii] 见焦循:《论语正义·先进》,《诸子集成》本
[xix] 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岳麓书社标点本
[xx] 《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