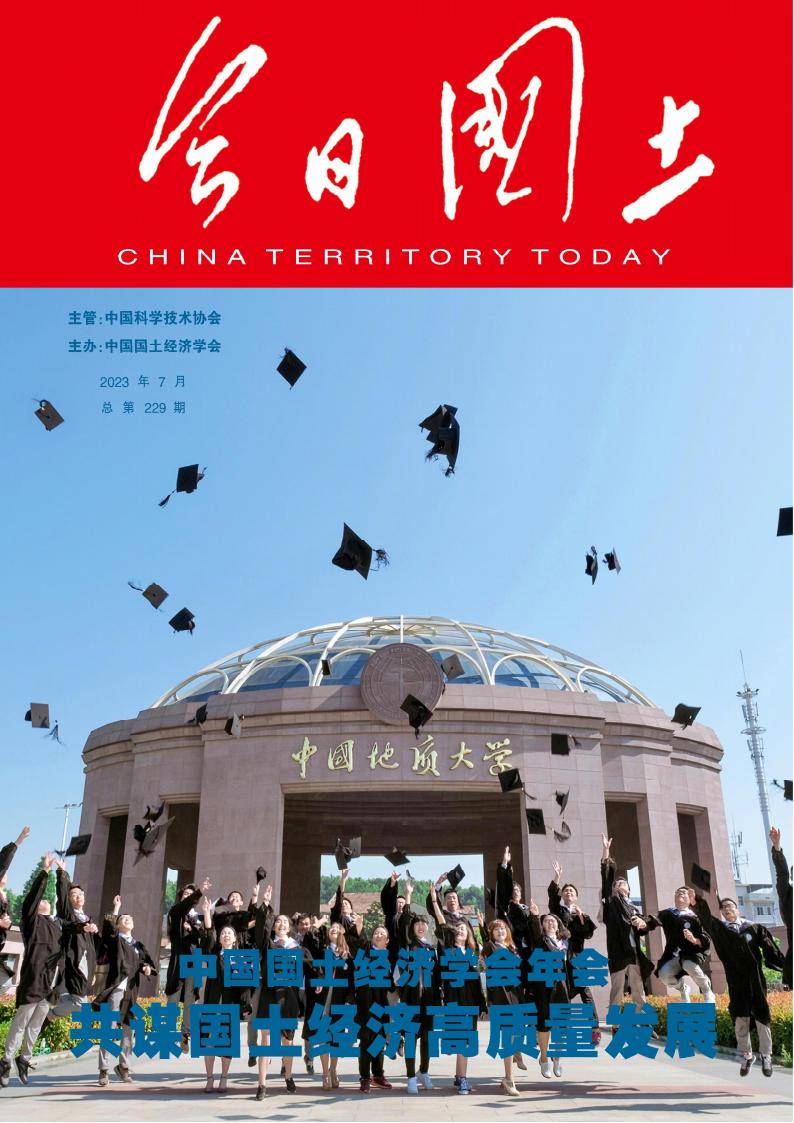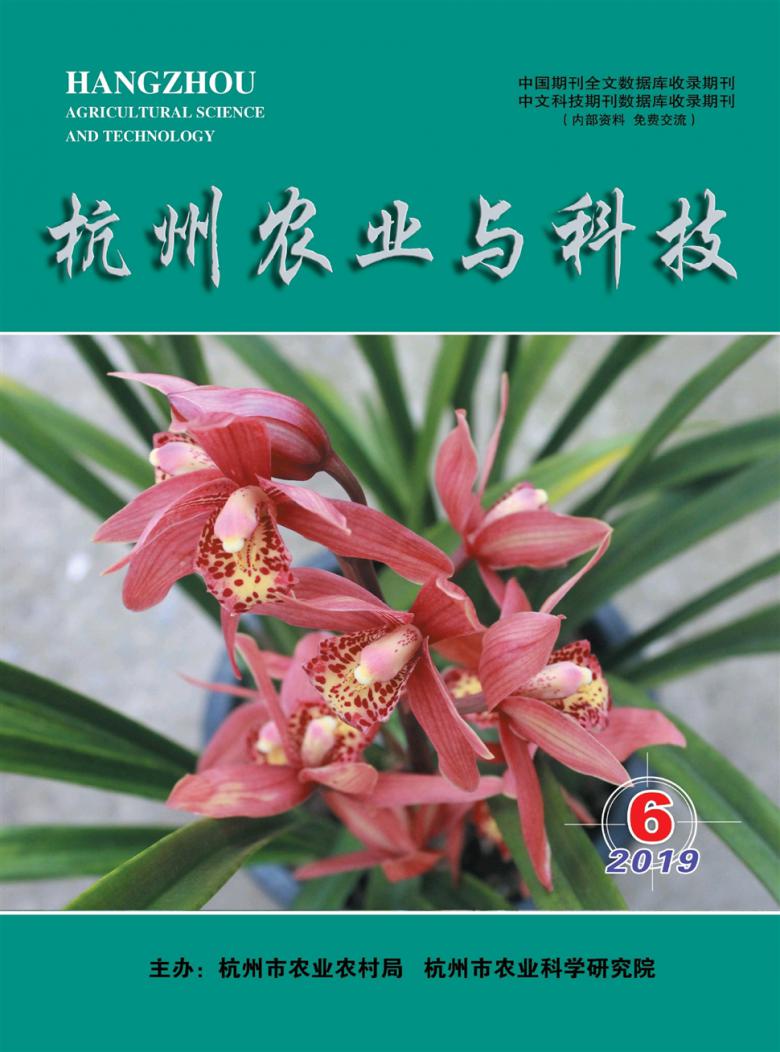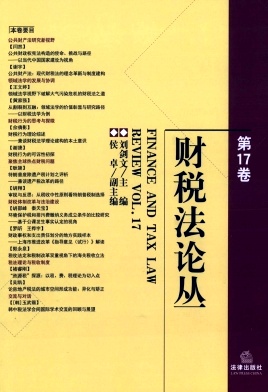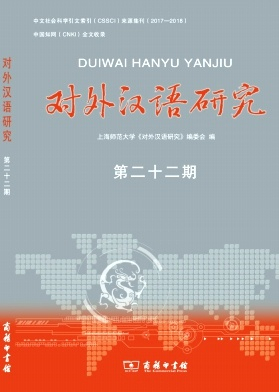关于浅论明中期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别支”
佚名 2011-11-30
摘要:在明中期前七子文复秦汉说风靡的背景下,祝允明从与经文的源流关系和经文文质对举、风格兼备的角度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提出“文之本体”的概念;其文统观对六朝论的阐述表现出对传统悬绝汉魏高古、指斥陈隋绮靡做法的反感,反之以平览十代和否定四家六家说的开放、多元精神,将备受质疑的六朝文纳入了复古的统绪之中;又以创作实践展示出对六朝文风的偏爱;在前七子派有限容纳六朝文、反“靡丽”说意义向度的对比下,其晚年对六朝文的极力推崇显得有别时流,并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祝允明;六朝论;《祝子罪知录》;文复秦汉
明弘治末,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事,倡导诗文复古,尤其是其激进派将“文必秦汉”奉为圭臬,一时文坛为之一变。吴中名士祝允明亦应时力倡古文辞,其部分作品古邃奇奥,甚者诘屈聱牙,不能成句,是未入七子阵营而复古意识最强烈的吴中派文人。然综观祝氏着作,尤其是《祝子罪知录》,在其文统观“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所展开的长长的复古线上,除以六经(秦汉文)为旨归,要求学者自唐而上溯乎六籍,极力强调六经为文章之至外,他还将备受传统质疑的六朝文以六经之支流的正统地位引入其文章复古统绪中,文质对举,并提出“文之本体”的文学观念,以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在前七子派“文复秦汉”学说风靡的大背景下,祝允明对六朝文的辩护突出强调了文学的艺术特征,是对明前期台阁体、性气诗及理学家诗文理论的极大否定和批驳,对于提高文学的独立价值有着及时和重大的意义,其“文之本体”概念的提出亦将文学审美主义补充进了明中期的文学批评史中。
然而对祝氏的六朝观问题,除黄卓越先生在吴中派文学研究中有所涉及之外,学界鲜有关注。台湾学者简锦松先生虽在探讨北学与苏州文学关系时发出吴人学古宗尚之问,然其回答亦仅徘徊在汉魏、唐宋之间,并未提及六朝,并以此论曲折、非片言可尽草草收场。本文旨在前贤基础上专论祝氏对六朝文、文质观的看法,及对文章拟古对象的选择、态度和方法等。
一、主六朝的理论依据
(一)六朝文乃经文之支流
关于经文的创作动机,祝允明遵循《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发生论。《罪知录》卷八认为,人身含灵结秀,包藏着心、情、理、气,人只要心动就会有表达感情的冲动,由此而发的言也必将理气相谐。上古言、文互指,从言到文无须修饰,其不同的文章风格完全来源于理足气茂之后的自然发声,言之或沉实或藻丽取自发声之内容与意图,即符合一定的“体”,概言之即为修辞立诚、尚体贵达。这与其《答张天赋秀才书》中强调的“心奴耳目”以自遂、自得的主张相似,是吴中文人自适、自惬心理在文章创作中的反映,由此亦可看出祝氏对于古文的效习并非亦步亦趋地纯粹摹拟,仍然重视由内而外地真诚抒发,即刘勰所谓的为情造文。祝氏认为经文并非诸子骋奇而作,而皆为君臣、士庶、妇稚心动后有感而发,这些胶轕混淆的自然之音经孔子芟刈之后便成六籍。由于创作主体的群体性和创作动机的自发性,经文态貌咸备,各体自殊,有齐停整截、句句平铺者,亦有纾迟婉约、风调窈窕者,有庄重亦有葩丽,有至简亦有至繁,囊括了后世之文的所有文体和风格,后世之文均可从六经中溯源。所以作为绮靡绚丽的风格之一种,六朝文自然囊括于经文的不同风格之中,只是作为经文的支流,无法与经文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相比拟。
(二)由经文文质关系肯定六朝文“文之本体”的地位
作者理着气达,故经文搞文被质、文质相谐。篇、旬、字有情有旨,道广理充,气厚情实,便为文章之至。祝允明举根直而叶敷、花艳之木(多“文”)与枸株(少“文”)为木的不同种类、乾坤不谓“健顺”(无“文”)、元首股肱不谓头脚(无“文”)等为例,认为“文”为文之本体,又举士、女均须修饰以成士、女为例,说明“文”之必不可少。在祝氏看来,风格多样、迥异的经文中不乏鲜采华绚、艳丽妍媚的文章,然均能达到文质彬彬,且为其自然而然所呈现的态貌,并非有意作异。祝氏以经文风格多样、文质相谐的事实驳斥了近时以奥涩枯瘠、“尽削鈆黄”为文之本体的做法,由此看出祝氏针对现实而来的反思性文学理论;又以后世之文均拟诸经文而出,为长期受到指斥的六朝文予以了申辩,将魏晋之浸衰、陈隋之绮靡归结为“理局气猥”的原因,把“过文之罪”从六朝文上卸了下来。由此,一方面将六朝文放诸经文之流的脉系中肯定了其地位;另一方面,由“转嫁”原因肯定六朝文而将“文之本体”的地位保留了下来。后世之文不能兼顾文质,便会流于整比堆垛、纤细艳丽。六朝文之弊正是在于此,且由汉至六朝愈演愈烈,于是从唐以后,由初唐四杰到张籍、皇浦浞、李翱、崔詹等振起矫弊,虽其人其作“固亦为然”,然仍劣于武德至天复之际的晚唐作者。祝氏并不同意后人以晚唐作家尚未涤尽六朝脂粉陷于绮靡而次于初盛唐作家的评价,反而对近时作家的“途目仗耳、党污徇浅、猥腐可嗤”甚为不满。他又从文质关系上历评了秦汉至近代之文,认为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代之文均本于五经,皆随意赋形,无偏于质,属于文质相谐之作,只有近代(宋、元、明)之文“一于枯瘠,弗黩于文”,将唐前与宋后之文在文质关系对比中作出了区分。再进一步将心情理气与耳目口鼻比之于施受、“主”“用”的关系,详细地解析了其所谓“文”之意蕴,即“文”应当兼顾耳目口鼻所感之声、色、香、味四体,而非仅声之一道。为将“文之本体”的论证推向极致,祝氏在《罪知录》卷八“系论”部分又引《易经》内容探析了文德关系,认为“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引王克之言论述“文”之重要性,如“人无文则为仆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物以文为基,人以文为表”,等等。
另外,“吴中文章藻丽为天下冠”,吴俗好奢靡及成弘间吴中滋蔓的竞习词华的风气也使吴中文人对六朝文有着天然的偏好,尤以祝允明为着。他习六朝、效齐梁之体,为文“芳腴融于心极,雕绩畅于辞锋”。其大量游记散文、赋作及《罪知录》里的论说文字均呈现出典型的六朝风格,这些作品除具相当的艺术价值之外,亦带动了吴中文人的竞习之风。由于祝氏的创作活动要早于理论撰述,由创作实践显现出来的对于六朝文的天然偏爱可看作祝氏将六朝文引入文统观、并极力为其辩护的源动力。 概言之,《罪知录》卷八“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一条几乎整篇都贯穿着为“文”辩护的意图,无论是从举六经而衍生出的文质相谐为文之本然的解析,即对十代之文尤其是六朝文风格的肯定,还是对宋后近时之文枯瘠文风的指摘,抑或是之后对四家六家说的批判,凝聚的同一个核心
的辩护、肯定甚至极度张扬,以至于在文质相谐的命题中过分关注到对偏质的否定和对过文的包容而忽略了二者的平衡。揣摩作者文字背后的意蕴,在举六经的标目下,祝允明并未投人多少文墨来论证六籍经文之至的地位,其不容辩驳的权威地位亦较为容易被接受。故由此可认为,祝氏将经文定位文章之至的目的只是为对六朝文(或“文”)的容肯找到合理而无可辩驳的理论根基,因为只须将六朝文纳入六籍的流脉中,其与六籍在本质上便只是微殊而非迥别了,即六朝文并未度越六籍三史、尽捐故习,与六籍之本背道而驰,于此在肯定六朝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对“文”的全面辩护。
二、根本乎五经、平览乎十代与刺四家六家说
《罪知录》中,祝允明从文学发生论出发,指出经文是理足气茂而成之言,成文之后自然搞文披质。六经之后,百家迭出,如先秦庄屈、两汉班马、魏晋、六朝、唐等,虽千姿百态,但都无越于六籍、拟诸六经而出。这里,祝氏提到几个问题:其一是后人所谓魏晋浸衰、陈隋极靡的文进入文统的问题。祝氏认为魏晋、六朝文也是拟诸六经而出,并未背驰文之本体,问题出在“理局气猥”之上,而非“过文”的过错。对于六朝“文”之过错的认定会导致对单一枯瘠文风的潜在默许和推动,而这与貌态咸备的经文是相左的,更与祝氏根本五经,平览十代(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的多元化风格追求相矛盾,这便是第二个问题:开放性、多元化是祝氏思想多处可显现的一贯性思维。如前所述,经文产生的方式使多样化风格成为本然状态,祝氏在文中详细列出了后世由经文衍生出的数种文风实例,换言之,后世任何风格的文章都能从经文中找到源头,都是经文之根所生出的枝叶,都应给予肯定。六朝文风由于偏文,并过渡发展而偏废失全,从两汉到六朝变本加厉,最终导致繁靡稚弱。初唐四杰振起救弊,元白、李杜等续接其后,其标准和创作都在六籍三史的范围之内,均得到了祝氏的容肯。在文论方面,祝氏对六朝的陆机、刘勰均表示赞许,而反对唐后对六朝及唐代文人荡涤不尽六朝脂粉的评价,他对宋人诗论尤其反感:“夫文出乎天造,而主于明道,谁则不知?何必攀援河洛,于引天地,动辄凌驾世道,自炫高远,及至究其归止,竟逐目睫耳轮之接,止于孟韩以下数人而已。腐颊烂吻,触目可憎,噫嘻!何哉?吾且窃哂之。”(《罪知录》)言辞激烈,感情激愤。从其批评的方式和内容来看,祝氏除从经文发展的角度为“文”辩护而对宋人评论不满之外,还流露出对以孟韩为归止的理学式评论方式的反感,对故弄玄虚、妄标道学的理学家的不务实际、徒尸其名的学风的愤慨,这构成祝氏反宋学、理学的又一个诉诸点。而这些恰巧就是明代学子文人的问题所在:“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就使自成语录,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试夺千魁,竟亦何用?呜呼!以是谓学,诚所不解”(《答张天赋秀才书》);“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较礼,附丽经师,或猎琐浮尖,依俙文苑。”(《西洋朝贡典录序》)换言之,祝氏对宋理学的指摘恰是由对明代文风的反思而来,理学、举业对古学、古文创作之挤压所造成的文坛浮陋之风,一方面隐约触痛了祝氏屡试不第(五次乡试、七次会试)的伤口,早年即以古文写作名起吴中的名士却始终徘徊于举业场上、进士门外,对于时文、举业“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不平衡心理不时以曲折的方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又直接触及祝氏醉心古文的真性情,他敏感地表现出对于完全无益于古文推动的浮陋学风的清醒认识和忧虑。由此反推,祝允明对于宋学的批判也是带着某种个性和充分的现实针对性的,而非空洞浮泛地为反理学而反理学,更不是跟风似的人云亦云,其务实、反思的思维特性也由此得到印证。第三个问题是文统止于唐的问题。祝氏认为,唐后开始出现“异谈”,“异谈”即指四家六家(韩柳欧苏/曾王)之说。四家六家说起于苏轼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来,祝氏回顾了唐后古文三次变革历程:第一次变革为韩愈首倡,柳宗元附和,就八代之文偏堕绮弱、过华而矫之,由过而矫至中庸;然经其后学孙樵、罗隐、陶秀实、徐鼎臣、穆修、尹洙、张景、柳开、石介等推波助澜,遂而致于改形易度,以成二变;第三次是欧苏曾王接续韩柳,竞为趋逐,而终过矫堕偏,导致文风枯瘠刻削,远离中庸。因此,宋人文统观的失误及失误导致的唐后枯瘠刻削的文风是祝氏将文统观止于唐的直接原因。另外,六家受举业影响,为文涣漫儇浮,与经文篇、句、字皆有情旨相背离,功苟易办的速成作文法与祝氏学充才广的古学崇尚也相左。
祝允明在完成刺四家六家说的叙述中涉及这样几个角度:首先,由于韩愈首发的文章变革起于拯弊八代绮靡文风,因此四家六家说问题实际又回归到上文的六朝文问题上来。也就是说,对于四家六家说的批判实由为六朝文的辩护而来,恰如清初王士禛一语道破:“允明作《罪知录》,历诋韩、欧、苏、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内,不遗余力……乃其大旨,则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实。”一四家六家合称,其作者横跨唐宋两代,而以上文统观的叙述是“底乎唐”,由唐而上,平览乎十代中也包含唐。这样,六家中韩柳二家被“刺”与“底乎唐”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矛盾。事实上,单从文学的层面上来说,祝氏对唐文也多持肯定态度,如《祝子罪知录》同篇叙述:“(文章)所称王杨卢骆、燕许陈梁、权吕元白、四李(华、翰、观、邕)、独孤之徒、又如称李杜、又如称籍、浞、翱、詹等,凡其标而出之,固亦为然。”祝氏自己读书也是“十年汉晋十年唐”(《口号三首》),并认为:“唐人为稗虞之册,各征见闻,不事剽袭,宋之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窃掠复迭多有可厌。”(《约斋闲录序》)又如其《侍御成公纪行集》云:“唐英之语盖博参焉,故其它多与杜异,而竞不尝违唐,又与后来媚宋者不同。”将唐宋文直接置诸对比之中,“轶宋窥唐”之见甚为明显。由此看来,对于韩柳的刺夺应偏重于其二人的文统观和首倡古文改革的始作俑者之身份,故在祝氏的评判体系中柳高韩低就不足为怪了。依此类推,祝氏对于六家高低的评判与各位荡涤六朝脂粉的程度及对古文革命的贡献成反比,因此由于只是古文运动的附和者,柳宗元在六家中也是祝氏评价最高的一位文人。
第二个角度是:反对四家六家说直承祝允明的反对文化垄断、单一立标的学术思想而来。他举出,近来八龄三尺之童不知何为典籍之时,便以知六家取笑只知四家者之寡陋;接触《文选》、《文萃》之后,便从四家六家之说,赞秦汉之高古,斥六代之绮靡,对于这些传统评论,“只应千古守辄,终生服膺而已。呜呼!……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日苏黄,评画就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若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罪知录》)祝氏对于文化垄断的反诘理足气茂,并及经、史、子、集各个学科,可见对于这种垄断和促成垄断的方方面面,祝氏憎恶之深。此时, 点便是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