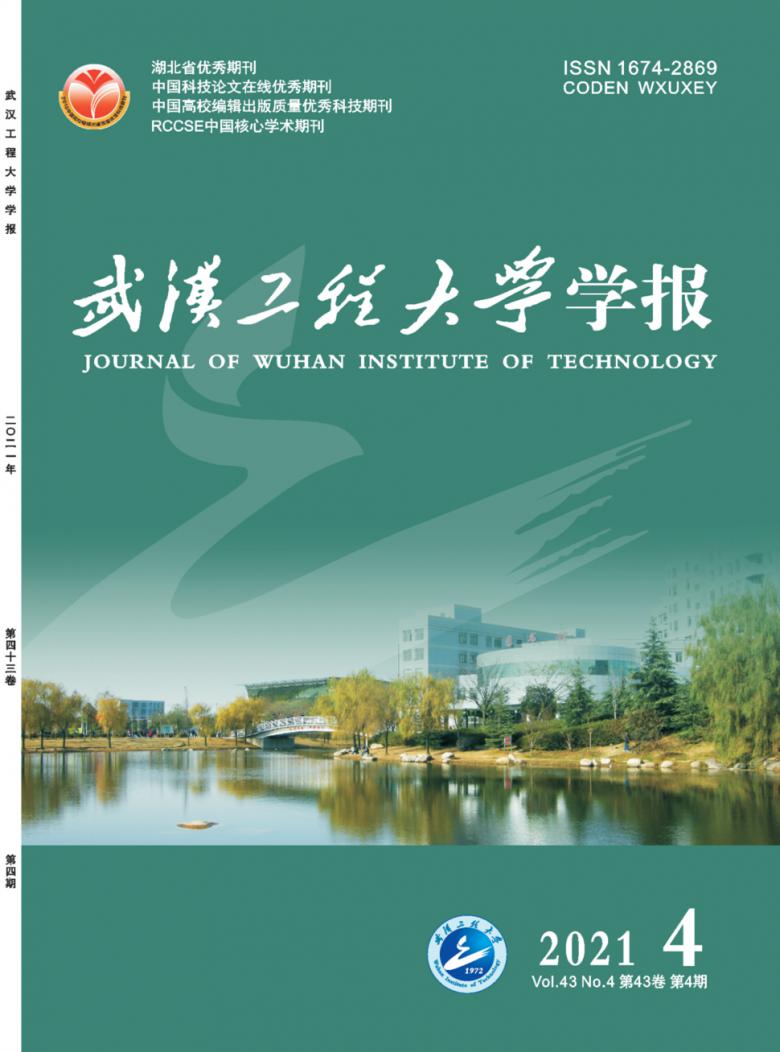关于从崔莺莺、杜十娘、李香君看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历程
聂玮 2009-04-23
[论文关键词]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主体价值
[论文摘要]元明清文学中女性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戏曲作品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爱情观的变化体现了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从她们各自阶段的个性意识出发,勾勒出女性觉醒的总体轮廓是递进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人性觉醒是元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反映,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尤为突出。而元明清戏曲中三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爱情观的变化则揭示了元明清文学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发展轨迹。三位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关于元明清文学中反映出的女性觉醒,妇女主体观念的增强,以前的研究者在评论单个作家作品时也多有提及。但都没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女性的觉醒作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从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纵向比较中,从三位女性对理想爱情追求的不同层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历史性的宏观结论。
《西厢记》(元王实甫作)、《牡丹亭》(明汤显祖作)、《桃花扇》(清孔尚任作)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之作。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里仅就三位女主人公对幸福爱情的理解和追求的层次及深度,来分析她们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西厢记》的女主人崔莺莺是相府千金,婚事早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恒,但她与青年书生张君瑞一见钟情。这是人在自然天性基础上表现出的男女之间的爱悦,是对人性美追求的自觉反映。处在重重禁锢中的莺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礼教的束缚,一方面是青春的苦闷和对自由人性的渴望。所以在行动上她采取了“隔墙酬韵”、“月下听琴”等隐蔽方式倾诉爱恋。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内心热烈,外表冷静;夜间热情,白天“规矩”。以至红娘责备莺莺“假意儿”,但莺莺这支“出墙红杏”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战胜封建礼教,与张生结为美满夫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莺莺性格中表现了一种新的爱情观念。
首先,是对“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突破,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确认。
其次,是莺莺在追求理想爱情时,对虚名的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中两个莺莺作一比较。在送张生赴京赶考离别时,董本《西厢记》中的莺莺说道:“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被”。可以明显看出莺莺的功名心理。而王本《西厢记》的莺莺却嘱咐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还抱怨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又千叮咛万嘱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表现了莺莺只重爱情、不重功名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崔莺莺的爱情理想仍是“才子配佳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在爱情的追求上,莺莺并非处在与张生平等的地位上。在与张生私下结合时,莺莺说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表达了男女之间在爱情上的不平等。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的矜持、犹豫、顾虑也都反映了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封建妇女觉醒历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所以说,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表现了女性觉醒的萌芽状态,是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朴素肯定,是基于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以莺莺的反礼教思想为起点,掀起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狂涛巨澜。
和崔莺莺相比,《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要坚决得多,对生命的感悟也深刻得多。青春的觉醒、人性的觉醒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
在《牡丹亭》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戏中,集中体现了杜丽娘人性的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对生命的感悟。“惊梦”中表现了她对生命感悟的两个层次: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香闺”是束缚杜丽娘人身的樊笼。久居香闺,像笼中的鸟,不能自由。杜丽娘从空间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约束。“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牡丹虽好,却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开,美景常在。借花自况,表达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时间感悟。对生命的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引发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萌发了强烈的青春欲望,并且为实现爱情理想,开始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崔莺莺所没有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主动、强烈、持久,直至后来以身殉情,死后她仍在寻找梦中情人,终于还魂结为夫妇。从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怀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这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著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理想爱情的斗争中,她不像崔莺莺那样只是被动地承受,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是把自己摆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像男子那样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对自然天性的追求,体现了人的原始生命现象。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价值观念上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
所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在女性觉醒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对爱情的追求,则表现了女性觉醒的又一高度。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相爱。他们的爱情除了色、艺、才、情外,共同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香君自觉地把命运、爱情和政治相联系。把婚姻的幸福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使爱情蒙上了政治色彩,视野更为开阔。在《却奁》中,她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表明她坚贞的人格。
李香君对幸福爱情的追求,自始至终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从《却奁》开始,她被卷入了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对爱情的坚贞和执著追求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奸党得势,逼香君再嫁,香君坚决不从,以致洒血溅扇,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心志,也表明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独立的、自主自由的人的意志。当香君被捉去充当歌妓,她在筵席上痛骂马、阮奸党:“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说明她对侯生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志向与爱情兼容的基础之上。李香君所追求的不只是人身自由,爱情幸福,还进一步追求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命运的捍卫和关心。和崔莺莺、杜丽娘相比,李香君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时代感,表现了女性觉醒的更高层次。
如果说崔莺莺传达了女性觉醒的朦胧意识,杜丽娘弘扬了青年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抗斗争精神,而李香君则把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她们应该说都达到了各自时代的高峰,标志着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
女性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除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而存在外,被剥夺的有话语权和自我存在。女性的觉醒就是把女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法律或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复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地位。元明清文学中所体现的这一觉醒历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体现了女性觉醒历程中的三个阶段:崔莺莺的觉醒属于第一个阶段——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就是对自己作为人的直觉的自我意识的朴素肯定。杜丽娘的觉醒属于第二个阶段——主体自我能力的自觉探索,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追求。李香君的觉醒属于第三个阶段——主体自我地位具体的、辩证的肯定,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递进发展,体现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主要脉络和总体轮廓。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也更加突出。而这其中,时代环境之变迁当是重要因素。蒙古族人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旧有的思想和风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礼教磐石也随之动摇,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而《西厢记》所描绘的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驳,崔莺莺的形象因被注入了时代因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牡丹亭》产生的明代后期,社会矛盾非常复杂,思想界的斗争也格外尖锐。一方面,封建卫道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礼崩乐坏的局面,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精神和肉体层面受到禁锢和迫害更加深重。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文人士子就反对封建专制与皇权的绝对性,思考人的主体意识。属于王学左派的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也在继承李贽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同时,明代后期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时。杜丽娘的“至情”,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外,更多的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这已经超出了爱情的范畴,表现出突破禁欲、对活生生的人的体认和尊重。杜丽娘的形象对于封建制度的冲击,对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比一般的追求自由爱情要强烈得多。她所包含的人性复苏、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精神,表明了晚明时期对人性内涵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大范围的肯定。
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促使学人们用历史批判精神来反思明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政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大胆批判揭露至高无上的君主。顾炎武认为,要保全天下,则须依靠天下匹夫的责任心,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王朝的易姓改号与兴衰存亡只是与君臣统治者的升降沉浮有关,与天下百姓的切身利益无关。而保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这才是正义人士和民众应尽的责任”。这些杰出的思想家的进步言论,对很多作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家们淡漠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充分肯定女性的价值,强调女性的独立和尊严,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李香君热爱生活、珍惜感情,更重要的是她注重名节,是非分明。以国事为重,表现了女性心胸和思想境界的重要变化,由此也达到了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最高峰。
可以说,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无不蕴涵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映射着时代进步文化的痕迹,是广大民众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这一社会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爱情问题、女性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