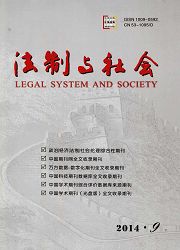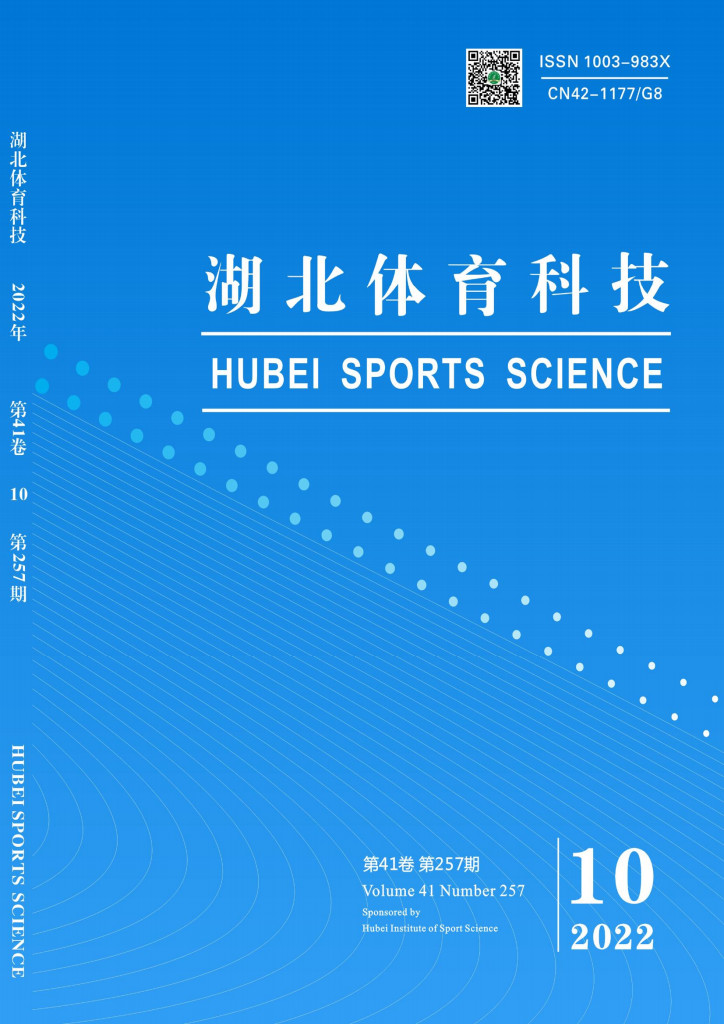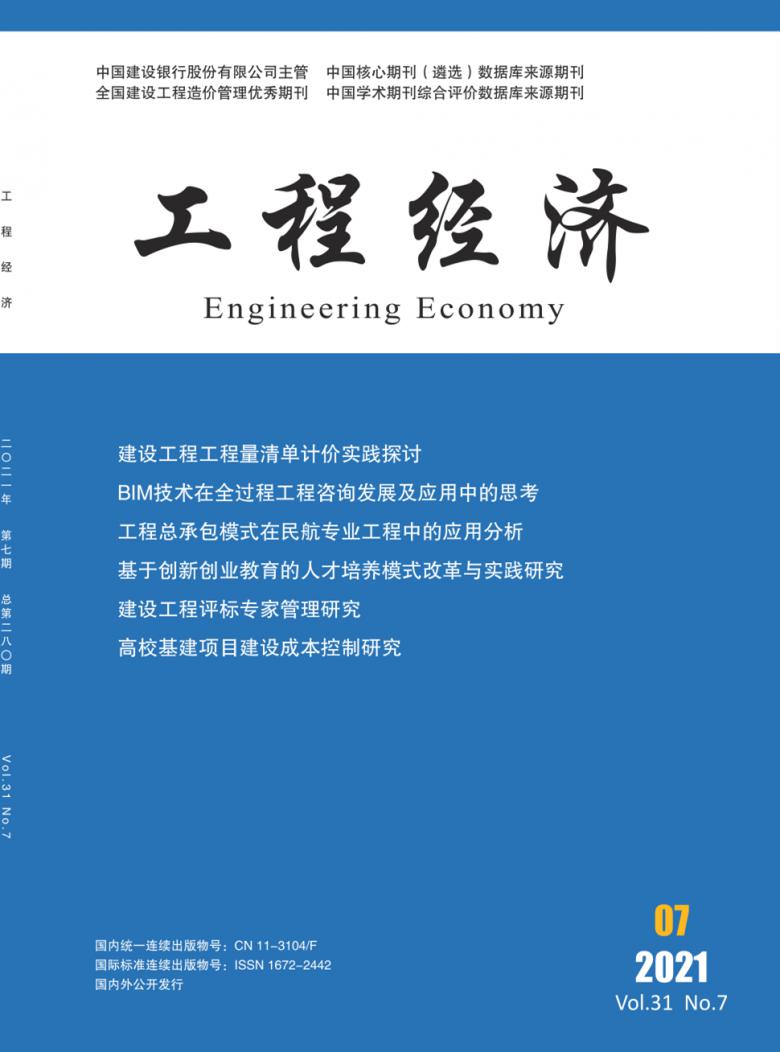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上)
陈改玲 2008-07-22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新中国第一套现代作家选集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出版缘起,“组织化”的编选方式,以及旨在传布新文学史知识的“编辑凡例”。以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为个案,展示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理解。通过分析“新文学选集”序言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作家对旧作的“过滤”和“修改”等典型景观,来展现在新的文艺政策规范下,编选者(作家)对作家形象的塑造和新文学传统的打造。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正 文】 一、传播“新文学史知识”
开国伊始,读者热爱解放区作品,开明书店面临稿荒,经营颇为困难。此时,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开明书店股东胡愈之,萌发了编选“新文学选集”的念头。当时市面上正在热销“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明书店要想寻找卖点,就得另辟蹊径,结合开明书店悠久的出版新文学作品的历史,胡愈之把目光转向了1942年以前的新文学作品,提议出版“新文学选集”,得到茅盾、叶圣陶、丁玲等人的呼应,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委会。 “新文学选集”的《编辑凡例》中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显而易见,“新文学选集”的拟想读者首先是青年,其编选目的是使青年读者可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新文学的发展,获得基本的认识。编委会又是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的呢?《编辑凡例》中有这样的描述: 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会被称为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会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编委会把“现实主义”命名为新文学主流,这是左翼文学界长期以来强化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结果。第一次文代会开幕那天,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讲话,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倾向,但是它的主流,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始终是同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相联系的。”这种把新文学主流与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相联系的思路在三十年代左翼理论家的文章中就有所凸显。但是,作为新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又是如何同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建立内在的联系呢?评价“新文学选集”的《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注:冷火:《新文学光辉的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1951年9月20日《文汇报》第4版。)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新文学选集”的意义,指出“新文学选集的本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纪程碑。而这纪程碑所昭示的大道,便是从旧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一条大道。我们今天得以明辨这条路向,就必须感谢死去的先烈和继续在努力工作的文艺作家。”至于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是否对应于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新的现实主义)有何区别,这正是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新文学选集”既然是以丛书形式来确立新文学权威、排列作家队伍、形成新文学史的看法的,丛书的人选也就至关重要。从入选作家来看,“新文学选集”基本上兼顾到了1942年以前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其中,鲁迅、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闻一多、洪深、田汉等人均在第一个十年登上文坛,除瞿秋白外,他们的作品均被选入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剩下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茅盾、丁玲、巴金、老舍、曹禺、蒋光慈、柔石、胡也频、殷夫、洪灵菲、艾青、张天翼等人,都在第二个十年开始展现创作才华的。用当年流行的观念来看,除叶圣陶、朱自清、许地山、闻一多、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外,其余的占入选人数近四分之三的都是左翼作家,“新文学选集”把众多的自由主义作家排斥在外,这昭示出编委会意图建构以左翼文学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史的设想。为了突出鲁迅与郭沫若高于其他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鲁迅与郭沫若入选作品的数量多于其他作家,《鲁迅选集》有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为上下两册,其他作家均各一册。 这套选集分为“健在者”与“已故者”两辑。健在作家中茅盾身份特殊(注: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1981年4月11日胡耀邦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人都是党员作家,占人选者的二分之一。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都比较亲近,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注:茅盾在《关于目前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中称十年来国统区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与“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注:冷火:《新文学光辉的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健在者”建国后都担任了领导职务,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而把“已故者”列为“第一辑”,这寄寓了编委会在享受建国的“大欢乐”时,对牺牲者的深切缅怀和纪念,意识形态的色彩浓重。 在已故作家中,鲁迅与瞿秋白为“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人都是革命作家。虽说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号召“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新文学选集”编委会在《编辑凡例》中特别强调了要出版烈士作家的作品,并说这次只是初步编选了十二种,“二十余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收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新文学选集”突出已故作家的革命烈士身份,再次彰显了新文学史与革命史重叠的文学史观念。
二、编选方式的“组织化”
“新文学选集”编委会对于人选和选目都极为慎重。叶圣陶1950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说: 上午治杂事。午后两点半至文化部,雁冰邀开新文学选集之编辑会议。编委缺席者多,仅余与雁冰、杨晦、丁玲四人会谈而已。此选集选五四以来作者二十余人,老解放区(注:建国初期,把延安等地称为“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各选其文为一集,印行传世。余之一集,原定自选,余以不愿重览己文,请灿然代定之。今各册目录已大致交到,故开会商讨。即按诸目逐一检览,或略表意见,或无异议。决定再由编委分册重看一过,以示郑重。此书将交开明出版也。(注:《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从叶圣陶日记来看,丛书最初的数目大致为“二十余本”,很有可能并不一定全是最终选定的二十四本。 “新文学选集”中,健在作家的作品一般由作家自己编选,也有请人代选的,如《叶圣陶选集》就由出版总署秘书长金灿然编选。已故作家的选集,编委会约请他人代为编选。编选者多为作者同时代人,与作者有过直接往来或更亲密的关系,对作者的创作和为人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比如,编选《洪灵菲选集》的孟超与洪灵菲同为太阳社成员,编选《胡也频选集》的是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对于编选者提交的作品选目,编委会反复讨论,认真把关。《鲁迅选集》的编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拿它与四十年代由文协总会组织作家编选的“现代作家文丛”(注:1947年,为打击盗版书,捍卫作家利益,文协总会出面组织作家自选文集,1948年9月开始出版,这就是“现代作家文丛”,由梅林主编,上海春明书店出版,共12种。依次为《鲁迅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郁达夫文集》、《叶圣陶文集》、《巴金文集》、《老舍文集》、《丁玲文集》、《张天翼文集》、《雪峰文集》、《胡风文集》、《梅林文集》。)中的《鲁迅文集》作比较。《鲁迅文集》,选录了37篇小说和杂文。书局排好清样后请许广平撰写后记,许广平对选目颇为不满,在《后记》中说: 这本集子共收三十七篇,分四类:小说有《药》、《故乡》、《阿Q正传》,取自《呐喊》、《祝福》、《在酒楼上》则采自《彷徨》,而《奔月》、《非攻》、《老子》乃从《故事新编》所选。随感录有十篇,除末篇《文学和出汗》,原在《而已集》内,其余九篇都取自《热风》,演讲仅二篇,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也是从《而已集》选出来。杂文共十七篇,在这文集内占的分量比较多,那是无足为奇的,因为鲁迅先生写杂文实在不少,拿他的全部杂文比起来,反而觉得并不算多了。这里前六篇选自《南腔北调》集,后九篇取于《准风月谈》,末两篇则由《全集补遗》中选出。
三、《田汉选集》和《瞿秋白选集》的缺席
1951年7月,“新文学选集”开始出版。最早的出版广告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进步青年》(第238期)上。随着出版的进度,《进步青年》、《语文学习》,甚至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封四上都有“新文学选集”的出版广告。所刊载的广告中,《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都标有“在排印中”的字样,这样的标示给人的感觉是选集已经编定了,正在“排印”。其实,《田汉选集》就没有编,或者说没有编成。1955年田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 当一九五○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以往的作品难以查寻,并不是“延搁”的理由。在“新文学选集”中,烈士遗作在收集方面最为困难,丁玲曾感叹收集到的殷夫作品仅限于二十六篇(注:丁玲:《序——读了殷夫同志的诗》,《殷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黄药眠也恳请蒋光慈的友好提供蒋光慈的材料(注:黄药眠:《蒋光慈小传》,《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可最终编选者经过多方努力,即便材料不那么齐全也还是出版了烈士选集。田汉的选集没能编出来,主要的还是他心怀“惶恐”,觉得以往的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拿不出去。以新的人民文艺为标准来衡量以往的作品,对旧作极度不满,这种心态在入选这套丛书的其他老作家那里也很普遍,他们也都在选集序言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瞿秋白选集》没能出版,也是有原因的。建国后《瞿秋白全集》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50年2月2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到他与杨之华见面的事, 杨之华说正在收集整理《瞿秋白全集》的材料,不久可以付排(注: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6页。),可见瞿秋白的材料收集是比较齐全的。为何没有出《瞿秋白选集》,有可能是在编选中遇到了困难。瞿秋白是文学家,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中,有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的话语。“新文学选集”的主编茅盾,以及其他编委在瞿秋白评价问题上当然是敏感的。1949年纪念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茅盾撰写了《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一文,谈到瞿秋白对文艺批评上的贡献时,茅盾说: 他首先提出了“大众语”问题,发表了卓越的主张;他又不遗余力地抨击那非驴非马的“五四文腔”,给写一个嘉名:骡子文学。他对于“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的成就评价过低,当时朋友们中颇有几位不赞同他这意见。记得《学阀万岁》的初稿,有几个朋友就认为不能发表,退还了秋白;后来经过他自己稍稍修改,这才发表了出来(这些事发生在“左联”还存在的时期)。有一天,在某处遇到他,我就问他:难道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的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的多了。 茅盾就瞿秋白对新文学的评价过低的观点作了解释,认为那是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接着又说: 二十年前,文艺理论上若干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那时候,一般的理论水平都不见得太高,所以,秋白在那时候的文艺评论在若干论点上有时不免有点偏向,我们正不必为他讳;但是,值得我们钦佩,而且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是他的决不固执己见的态度。(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五十年代为了确立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凸显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基本上都采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五四”新文化是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取得的,对“五四”以后的文学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文艺界领导者之一的茅盾怎能不郑重指出瞿秋白的“文艺评论在若干论点上”有“偏向”呢!1953—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瞿秋白文集》,冯雪峰在《序》中申述了同样的观点:“作者在个别论点上有偏向”(注:冯雪峰:《〈瞿秋白文集〉序》,《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因为《瞿秋白选集》涉及的问题太敏感了,即便茅盾、叶圣陶这些瞿秋白的挚友也不敢大意。八十年代出版《瞿秋白全集》时,出版署有明文规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过中央审批。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瞿秋白的作品也要经过相当层次的审批。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瞿秋白选集》没能及时编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