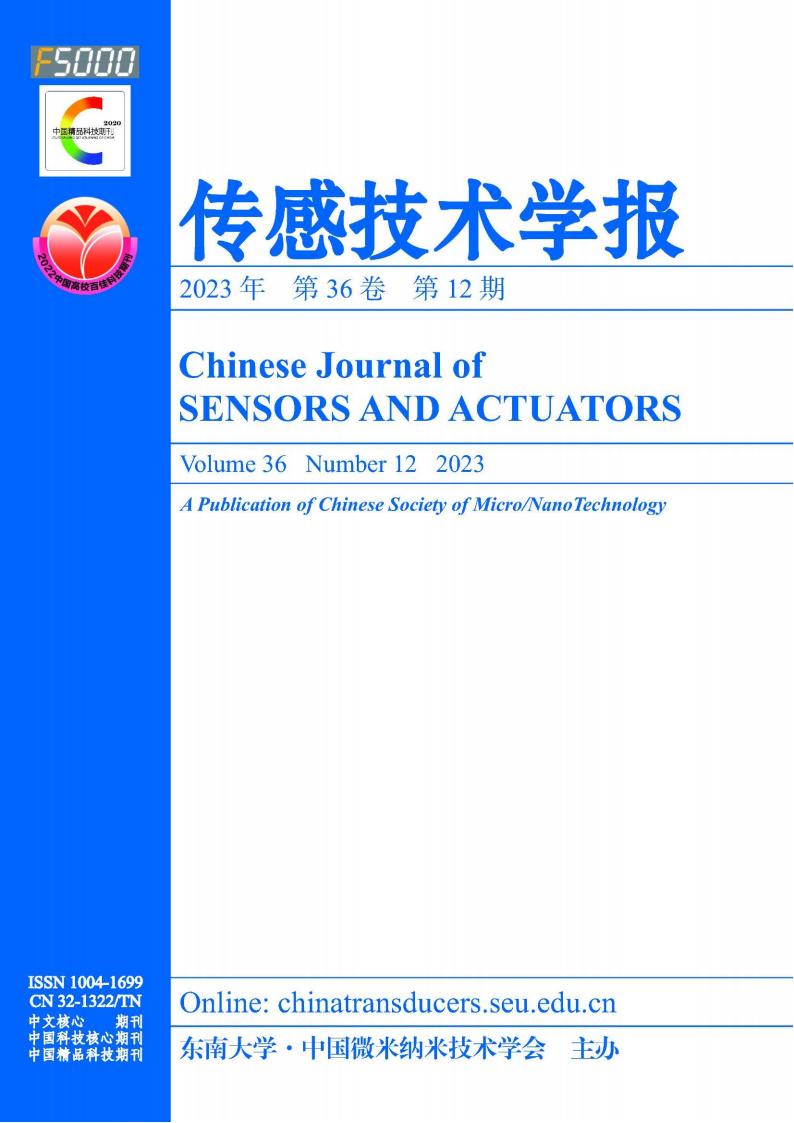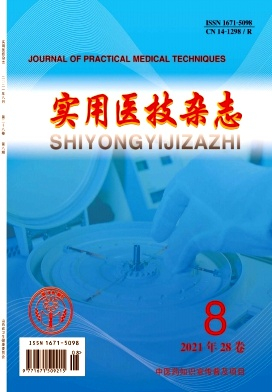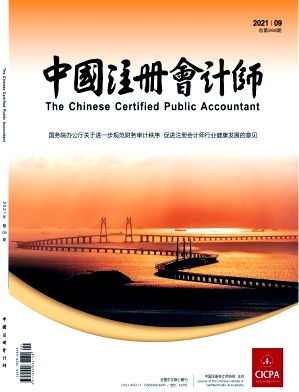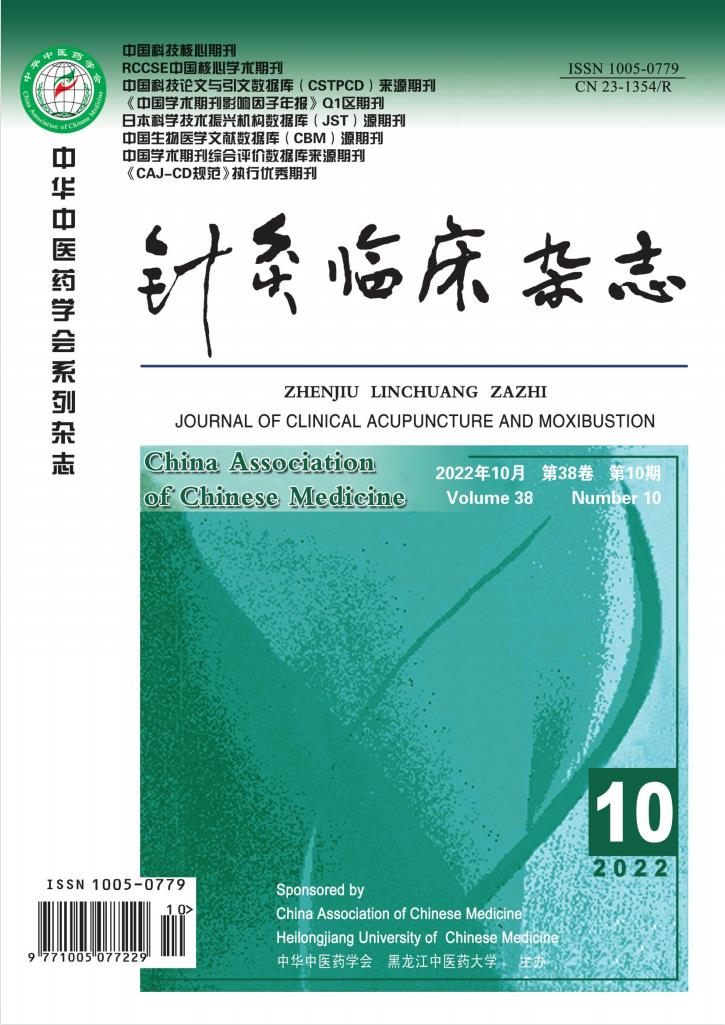明中后期市民文学中的价值变异与消费观念
毛德富 2006-04-19
【内容提要】明中后期市民阶层及市民文学反映出的变泰发迹心理与现世享乐的消费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社会风尚,也不仅是一种市民的消费心态,在这种消费观念背后,裹挟着对人生、命运、享乐、欲念等的沉湎与留恋、把握与追求;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发现与思考,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和生活态度。这种新的内容,使得“消费人生”具有了复杂的意义,受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念的引导和影响,明中后期的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但是,这种消费观念与追求变泰发迹的心理,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其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价值变异/变泰发迹/消费观念
【 正 文】
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开始了重新对人进行全面的思考,试图对人的困惑、人的价值作出全新的诠释,以此建立哲学的新思维;明中后叶则在消费人生的现实洪流中,裹挟着对人生、命运、享乐、欲念等的沉湎与留恋、把握与追求;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再次发现、思索,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与生活态度。
正因有了这种新的内容,使得“消费人生”具有了复杂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人生颓废和意志消沉。
正因有了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念的引导和影响,使得明中后叶这一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
…………
觉醒:人的发现与价值变动
程朱理学的著名论点是“存天理,灭人欲”,把“理”与“欲”的冲突与对立极端化,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注:《朱子语类》卷十三)把封建主义、禁欲主义、等级制度视为“天理”、“性命”,当作封建统治的规范、秩序、法规来强加于人。
王阳明的著名观点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把问题全部集中在身、心、知、意这种种没法脱离生理上的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个人意志上。尽管本意也是想把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内化为一种心理意志,或称心理的伦理化,但结论正相反,由于心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个人意志,逻辑的发展是王阳明的“心学”本能地否定了用外在抽象的、伦理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压抑心灵的“理学”,他认为: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谓百姓日用即道,……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
并进一步指出“理学”并非“圣之学”,“圣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不仅感受到人性被理学长期“捆缚”的“苦楚”,而且斥责道学是在装模作样。刘宗周也认为“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刘宗周的学生陈乾初认为:“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注:《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79年版,第461页,第468页)本是反对道学而承认人欲、人性,却无意中喊出了对程朱理学禁锢与压抑人性的不满。
当然,从哲学上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批判最有力的是李贽。为了从根本上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他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尊奉的祖师爷孔孟。不仅对孔孟不恭敬而且大胆地反对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他认为愚夫愚妇不能干的事,虽是圣人也一定不能干。况且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孔子的话怎么能成为“万世之至论”呢?他的不少言论像投向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
在呼唤个性解放的同时,李贽对个性的束缚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控诉了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种种清规戒律对人的约束和禁锢:
……即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第183—184页)
一生一世把人死死限制在一个既定框子之中,这种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李贽实在不能忍受,并自嘲自己的前半生: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注:《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第347页)
这不正是那些虽崇信儒教而不知儒教为何物的芸芸举子,朦腾儒生的自画像吗?李贽一旦清醒过来,不仅不愿作吠声之犬,而且要睁了眼看,用了心思,对历史、人生与社会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李贽非常庆幸自己“天生我大胆”,乐于承认自己是“异端之尤”,并为争取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甘愿“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甘愿被封建卫道者诬为“妖人”,“妖怪之物”,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李贽的一生,从理论著述到实践行动,不仅充满着个性解放,人人平等,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色彩,而且还把统治阶级给“道”抹上的一层层神秘色彩,毫不留情地刷去,让“道”从天上回到人间。李贽公然宣称饥来吃饭困来眠的生存欲望,趋利避害的自私欲望,好美色乐享受的快乐欲望,是“吾人禀赋之自然”。“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注:《明灯道古录》卷上。)那么,黎民百姓“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注:《焚书》卷一《答邓明府》,第39页)这有什么可鄙薄的呢?人类的种种欲望是自然本性,无论圣人或者凡人,礼教不应禁止、抑制,而应该顺从、支持。从千万人之心中、之自然欲望中流露出来的便是礼。为了一种其它目的,人为地给人外加进去一种规则则非礼。(注:《焚书》卷三《四勿说》)李贽在将封建礼教世俗化的同时,将“礼”消融在世俗生活之中,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地稀释和溶解,为个人主义鸣锣开道。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的全面复归的呼唤,在明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到了明末王夫之那里,完全把“礼教”消融在人欲之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认为只有人人平等、自由、博爱,互相尊重,这才是天理,否则便不是天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到了清初思想家戴震那里,仍然抑制不住对礼教吃人、杀人的愤慨。(注:《戴震集》下编《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75页)
随着对旧道德、旧风习、旧传统、旧价值的破坏与对抗,李贽等人的怀疑论哲学思潮的张扬与鼓荡,在那种人性禁锢和个性失落的黑暗年代,尽管犹如空谷足音,但毕竟在一批与市民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识之士当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唤醒了一批士人的觉醒。在新与旧的界碑中,出现了一大批狂人形象:
李中麓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继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贤。中麓每日或按乐,或与童子蹴毬,或斗棋,客至则命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
(杨)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王九思《答王德征》云:“九思者,当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为吏部;吏部获罪,左迁寿州;寿州不可,罢归田里……”(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吴中张幼予奇士也。……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堂庑间挂十数牌,署曰:“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士人·张幼予”。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2页)
“狂人”似乎是每一转折时代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狂人”作为旧时代的送葬人,新时代的先行者,不仅常常被统治者恨之入骨,而且常常被世俗不理解。李贽笑纳之余,又以“异端”自谓。至于李贽落发为僧,仍出言无忌,狂行狷介,并敢于和统治者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决一死战,(注:《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第295页)不正表现了一个斗士的性格吗?何心隐同样以惊世骇俗为快意,以“一言行即为人所怕”相标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妖”,却被李贽赞为“英雄汉子”。徐渭“疏纵不为儒缚”,“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注: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佯狂到残害自身,践踏自己性命的程度。袁中道重“狂狷”而鄙“乡愿”,袁宏道公开宣称,追求人生的“五大快活”,王思任专以嘲谑“达官大吏”为快事,(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575页)卢柟“为人跅跎,好使酒骂坐。”(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25页) 在这个狂人家族中,有的狂放,有的狂狷,有的狂傲,人的狂猱……虽狂情不一,但狂心相通。他们既执著地追求理想,又痛苦地感到理想之虚无缥缈,云遮雾罩;既大胆地批判现实,又清醒地觉得现实之无法脱离,无法理解。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感到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停止探索、追求。如对禁锢人性的控诉和反叛,对人性复苏的期冀和追求,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也要为市民解放运动狂飙的兴起摇旗呐喊,鼓波作浪。
以文艺为武器,向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冲锋陷阵的主力仍是李贽。当然李贽之前已有汤显祖对真情至性的辩护,徐文长对“己之所自得”的提倡,李贽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狂飙。他的“童心说”不仅是对当时矫揉造作的文坛的当头棒喝,而且是对虚假矫情的道学在文坛流毒的控诉。因此,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因此他认为童心之失,在于“道理闻见日以益多”故也,而“道理闻见”又是“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注:《焚书》卷三《童心说》,第98页)
正是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想引发下,公安三袁提出了“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语)。仍是要求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对个性的宏扬,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号称全能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更是奉李氏之学为蓍蔡,而凌濛初又是步冯氏后尘。“三言二拍”的编纂不正是对李贽等进步思想家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吗?“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它用文学的形式体现了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或加入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洪流中去。是否可以这么说,当时进步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相互融合、牵引、催化,共同弹奏出一曲人的觉醒的赞歌。
挣钱:变泰发迹“白日梦”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人地位、商品意识的变化,引起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消费意识的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所显示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又引起整个社会心理——重商、重利、重财的变化。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说: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
这种不顾一切追求财利的风气,不仅在市民阶层蔓延,而且一直扩散到官僚士大夫之家,如有的就广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注:《谷山笔尘》卷四)为了趋利谋财,不仅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而且还绞尽脑汁去赚大钱赢大利,在金钱财利的冲击下,清高不值一文钱。
明代市民小说,便是在这种社会现实引发下真实地描绘出一个商人的天下、市井的世界。在这里,商人是扬眉吐气,还是垂头丧气,完全要看他的得利多少而定。
于是有一种心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变泰发迹,转眼暴富。
虽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但它却是那些万分渴望富有的人的正常心理。
它像罪恶的墨菲斯托菲里斯,引诱着浮士德。它像一股强劲的飓风刮到晚明的城镇和乡村,刮到市民那欲壑难平的内心——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诞生、具有现代消费意识的风行,引诱着人们的希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一句话:对金钱的追求,是他们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原本是“宁静”、“恬适”的内心世界,从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为了达到对金钱的占有,私欲无限膨胀,结果“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歙县风土论》)商场成了战场,同行成了冤家。面对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动,价值转变,或许有的人会惊诧、迷茫、躁动、不安,但对金钱的追求,对“变泰发迹”的热切向往,成了人们——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白日梦”。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环境中的市民阶层,作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获取利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无可厚非。 然在不发达的共同体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在占有金钱心态的驱使下,常常靠侵占和欺诈的手段来获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4页)
如在商业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商品商业资本”中经常遇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的现象,第二种形式“货币商业资本”中的会票行业与高利贷资本在明中后叶是非常活跃的商品经营形式。如在第一种形式中,当时有许多自耕农或佃农依赖副业生产的补偿维持生计,可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果实常被商人用欺诈行为并吞。当时从事丝织与棉织业的农民,常被牙行商人用大秤盘剥。在石门县丝行牙侩所造大秤高达二十余两。(注:参看《石门县志》卷十二)有时牙行用掺假银的方式剥削农民。(注:参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六册)在第二种形式中,典型的是严嵩,把钱寄在工商店铺,典当以生息,而“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注:《明史》卷三○八《奸臣传·严嵩》)
商人经商,目的获利,却是天下一切商人的追求。因而,“变泰发迹”也成为众多商人梦寐以求的梦想,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笔记或方志中均有反映。
文若虚经商屡遭挫折,在心灰意冷之时,偶然乘了走海贩货的船到海外观光,无意间因一筐洞庭红桔和海滩上捡来的龟壳而暴富(初刻一)。王生行商两番遭劫,后又在婶母的鼓励下,坚信“必有发迹之日”,结果也是“遂成大富之家”(初刻八)。故事虽说有点荒诞不经,市民变泰发迹的心态却真实可信。文若虚倒楣时,“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听说北京扇子紧俏,等到他把扇子运到北京,京城却阴雨连绵,直到箱子里的扇子霉烂也没见个好天气。等他时来运转时,随便买筐桔子,也值几百两纹银,拾个龟壳,便是稀世珍宝。我们透过这怪诞不经、神秘莫测的帷幕,不难看到贩货行商,竞争激烈,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不是命运捉弄人,而是人对市场规律各种因素未能把握。如文若虚只知暑天人们需要扇子,却未知过热的北京后来的天气变化。人投身商场,对商场的各种信息、行情、规律把握不了,难免有“时也”、“命也”之叹。
《叠居奇程客得助》写程氏兄弟,经商折本,无颜见江东父老,困居异乡,后得海神相助,又屡屡得手,“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上面罩一海神,似乎程氏兄弟否极泰来是神力,其实这是一个囤积居奇而致富的故事。因囤积居奇在中国是商业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借神力以掩饰。当然,我们无意对程氏囤积居奇而致富作什么谴责,我们知道程氏家乡的风俗:“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家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程氏兄弟既皆落寞,羞惭惨沮,乡井无望,遂受用他商,为之掌计以餬口。” (注:吴曾祺《旧小说》戊集一)一个时代,一方乡土对发财致富的迷狂心理,而演变为浇薄人情,势利心态。
作为一种时代崇尚,变泰发迹的美梦并不仅仅商人有,它实际已渗透到市民的各个阶层,甚而至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三言二拍”,地下挖出金银而飞黄腾达的“掘藏发迹”故事不乏其例,上厕所捡到大包的银子也屡见不鲜,甚至,大仲马笔下邓蒂斯式的“基督山遇宝”也出现了(《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在市井的世界中,市民对突然暴富津津乐道,对飞来横财受之不惊,像小业主施复在街上偶然捡到一包六两白银之后的心理活动及后来举动,只能说他是一个刚刚脱胎于封建农民的小手工业主,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身上既有市民的发财梦想,又有农民的忠厚本分。施复的行为,对于那些狂热追求金钱,一心渴望发迹的某些市民来说,虽是一个反映,是一个刺激,更是忠厚品性在新兴市民那里的一个遗响。
从现实对变泰发迹的渴望,到对历史上的故事传说的津津玩味,显然是在经商暴富的大道之外,又开辟了一条人生际遇中的穷通之道,作为对经商中的变泰发迹故事的补偿,如《喻世明言》中的《穷马周遭际卖槌媪》、《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等,皆叙述主人公开始穷困潦倒,后来一朝发迹的故事。将这么多变泰发迹的历史人物故事加以铺排演说,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的背后隐藏的仍是明代市民阶层对荣华富贵的深情呼唤。尽管故事中间也有对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批判与嘲讽,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则是对金钱、名利、富贵荣华的艳羡与渴望。流风所及,影响士林。何良俊讲他生活的时代,举子中进士后,厌见故旧,厌谈文论道,相反,“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正俗一”)
对金钱的崇拜和狂热追求直接影响着人情世态。换言之,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被金钱无情地撕破了。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这无异是丑恶的,卑鄙的。然而——
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
明代的金钱崇拜当作如是观。对市民来说,追求金钱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的职业本性规定了他们的道德原则。
事实上,尽管对金钱的崇拜影响了人情世态,但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对封建礼法纲常的猛烈冲击。为了金钱,刘氏把失散多年的侄儿棒打出门(初刻三十三),吕宝趁哥哥外出数年未归,便将嫂子卖了(《警世通言》卷五),开酒店的李方哥垂涎于“白白送来”的十两银子,竟劝说“有几分姿色”的妻子和一老翁拼作一夜欢(《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正是在充满“铜臭”,人耻言之的“黄白之物”面前,封建伦常被冲了个七零八落。恰如晚明一首叫做《题钱》的民歌所唱:
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
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分明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人为你生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他丧了。(注:《林石逸兴》卷五)
找乐:衣食住行尚奢靡
中国人向以勤俭素朴、吃苦耐劳闻名于世。曾几何时,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得人为的等级贵贱受到震撼,使得因出身地位的特权受到限制。因而,人们愈要实现个人价值,愈要发挥个人所长,表现在人际交往上的礼节和排场,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和豪华,逐渐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标。遂演为一种专尚“儇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注:王士性《广志绎》)之风习。张瀚在《松窗梦语·风俗纪》中记载北京、杭州的风俗:
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则观风问俗,所系良重矣。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士,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脉脉,思欲挽之,其道无由,因记闻以训后人。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龚炜在《巢林笔谈》卷五记吴地风俗:
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
明中叶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有一文人李乐站在正统立场上描述当时风气:“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者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注:《续见闻杂记》卷十一)整个社会对饮食肴馔的消费标准是酒必名酒,茶必佳品;点心杂食,目迷五色;欢宴便餐,山珍海味。当时的方志、笔记、小说有大量记载,以致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专门的饮食文化。
中上层阶级的住宅与其说是休息安居的需要,毋宁说是风尚趋使的结果,建筑风格的典雅古朴、和谐宁静,无疑已属于艺术的范畴。明中后叶的江南民家,稍有积蓄便思建楼盖房,大型建筑园林化更是贵族一雅,如钱谦益将废园改建后,园内设有“玉蕊轩”、“留仙别馆”胜景,如留仙别馆,“树绿沈几,山翠湿牖,烟霞澄鲜,云物靓深,过者感叹尝以为灵区别馆也。”(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五(《留仙馆记》))江南园林,闻名中外,又岂是“不喜治第,而多畜田”(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的北人所能比拟的。至于夏言家中“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在当时的贵族之家,并不鲜见。(注:焦竑《玉堂丛语》卷八“汰侈”)
服饰式样的争新斗奇,衣着首饰换金去银,笔记小说中屡有表现:“有以千金为妇饰者”,(注:《肇域志》“山西”)有用三十两银子买一顶帽子的。(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明中后叶那样讲究服装、重视豪华,没有一个时代像明中叶那样将历代统治者视为“贵贱不相逾”的“士女服饰皆有定制”的律令在实际生活中废弃了。就连大户婢女、官府皂隶也追求大红大紫、丝绸绫缎。御史大夫王大参总督蓟辽时,“奢淫汰恣,帐下纪纲卒数百人,后堂曳罗绮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猎,骏骑连翩,妖童执丝簧,少女控弓弩,服饰诡丽,照耀数里。”(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兵部·边材”)而工部“徐渔浦冏卿,时为工部郎, 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杼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吏部·士大夫华”)龚炜说吴地情况:“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下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注: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从道学家痛心疾首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切等级、秩序几乎都被打破了。
陈设用具的精巧别致、堂皇豪华、婚丧寿诞的大操大办,四时八节的消费竞赛,收藏古玩的雅趣嗜好……
中国有丰富灿烂的饮食文化,历代的美食家功不可没。不仅是豪门民家“炮凤烹龙”,“山珍海错”,即使在一般市民中间,吃请之风也非常盛行:
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厌心。(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
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京正德前后风俗的变化:妇女服饰由朴素而华丽,宴会由菜四碗、六碗到菜八碗、十二碗甚至十六碗等。联系西门庆家的多次宴席,可知当时吃喝风之盛行、之奢侈了。
中国人爱面子,讲排场,为爱面子,常常摆架子。下面几则资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淆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4页)
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禂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6页) 进而发展到官僚在家庭和家乡也要摆在衙门的架子: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8页)
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昔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众人因之,尽乘轿矣。……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20页)
流风所及,衙门之间公款请客,大肆铺张,成为当时衙门一条特别风景线: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宴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0页)
难怪当时有一高僧感叹说:洪武间的秀才做官,吃苦受怕,到头来,如有过犯,轻者充军,重者刑戮。那时的士大夫无负国家,而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像是还债的。现在的士大夫,为朝廷出力不多,又有多少好受用,真是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的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的。(注:陆容《菽园杂记》卷二)还债讨债之说是佛家语,但从一个侧面见出当时的士风、官风。对这种追求现世享乐的奢靡之风,当时的人们也有评价:
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娇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注:《博平县志》)
当然,文人站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所谓“贵贱不相逾”的封建秩序的立场上对“奢靡”、“浮薄”之风日烈,“敦厚俭朴”之风渐佚,痛心疾首,严厉斥责,我们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在看到这种现象所包含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认识到这种奢靡之风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消费心理。或者说是泡沫经济中的一种虚假消费能力(虚假消费能力即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那一部分消费能力),今天也有叫做超前消费的。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有人“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的“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有的“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注:王士性《广志绎》)有的“乐岁则尽数出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携妻子逃徙趁食”(注:王士性《广志绎》)。
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可知盛行于当时社会的是一种超前的高消费,这种超前的高消费并非物质丰厚,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而是畸形的商品经济倒映的虚假繁荣而导致的病态的消费特征。
病态的消费特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病态的消费心理,病态的消费心理反过来又与病态的消费特征相为激荡,它虽无益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在本文论列,兹略),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观察这种病态的消费心理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和风气驱使下,明中后叶直至清初,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更其风雅,康对山(海)与妓女同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705页)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 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臧循因与娈童“游乐”罢官回乡,这种丑闻在健康的社会恐怕羞与外人道也。岂不知在当时不但不是丑闻,而且当作文坛佳话,“艺林至今以为美谈”(钱谦益语),所以汤显祖把此事略加渲染点缀写诗为朋友送行。屠隆整日和妓女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好交游,蓄声妓”,(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45页) 且因与人纵淫,身患花柳病,在当时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故而汤显祖在诗中戏称“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家间大有童男子,尽捧莲花当药王。”(注:汤显祖赠臧晋叔诗见《汤显祖诗文集·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卷七,汤赠屠诗见同书卷十五《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抗清英雄陈子龙在不富裕的家境中纳妾三人,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皆当时佳话。即如商人,稍有资产,诸事悭吝,惟宿妓纳妾,挥金如土。(注:谢肇@⑩《王杂俎》卷四)致使晚明士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颂而不已。 ”(注:屠隆《鸿苞节录》卷二)
这种快乐舒适的生活情趣与纵欲佻荡的人生方式携手共和,固然对禁欲主义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客观上起着张扬个性、重视情感的进步作用,但也必须指出,这里面同时还夹杂着整个社会病态疯狂和世纪末情绪。
正是从这一特殊层面上,当时的消费风气不仅是一种消费心态的映现,同时又导致了消费心态的膨胀,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并动,人情世态的扭曲。从消费心态到整个人情世态,是一个合逻辑的发展。人情世态正是社会风气的重要方面。社会风气和当时进步思潮相汇集,吃喝玩乐的消费心理和“好货”、“好色”是人本性的哲学观点相结合,出现了一幅奇妙的现实景观:奢侈淫佚的社会风气不仅是对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冲击破坏,也不仅是对传统生活观念的转换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进行了一次矫枉过正。
社会风气的奢侈淫逸,进步思潮的鼓风扬波,在世纪末情绪的笼罩下,产生了一个时代的怪胎:沉湎酒色的堕落和消费人生的颓败,流露出一个时代的焦灼、狂躁、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情绪……
这,不仅王阳明没想到,而李贽也会吃一惊的。
把人物场景拉回到今天——一个健康向上、稳步发展的社会,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如果说“变泰发迹”是一种可以理解但并非健全的生活理想的话,那么“现世享乐”则是一种不思进取只图快活的人生追求。它犹如一面双刃剑,它犹如一只潘多拉的箱子,如果不可能把它锁起来,也必须及时地发出警告:
这只不祥的箱子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