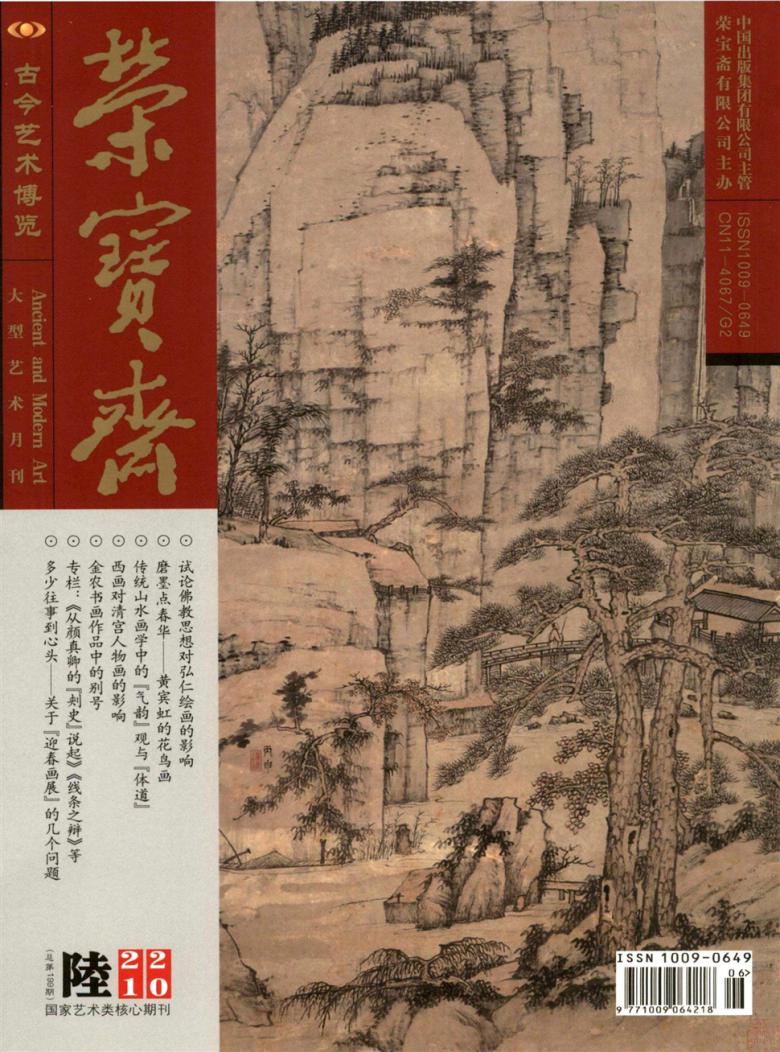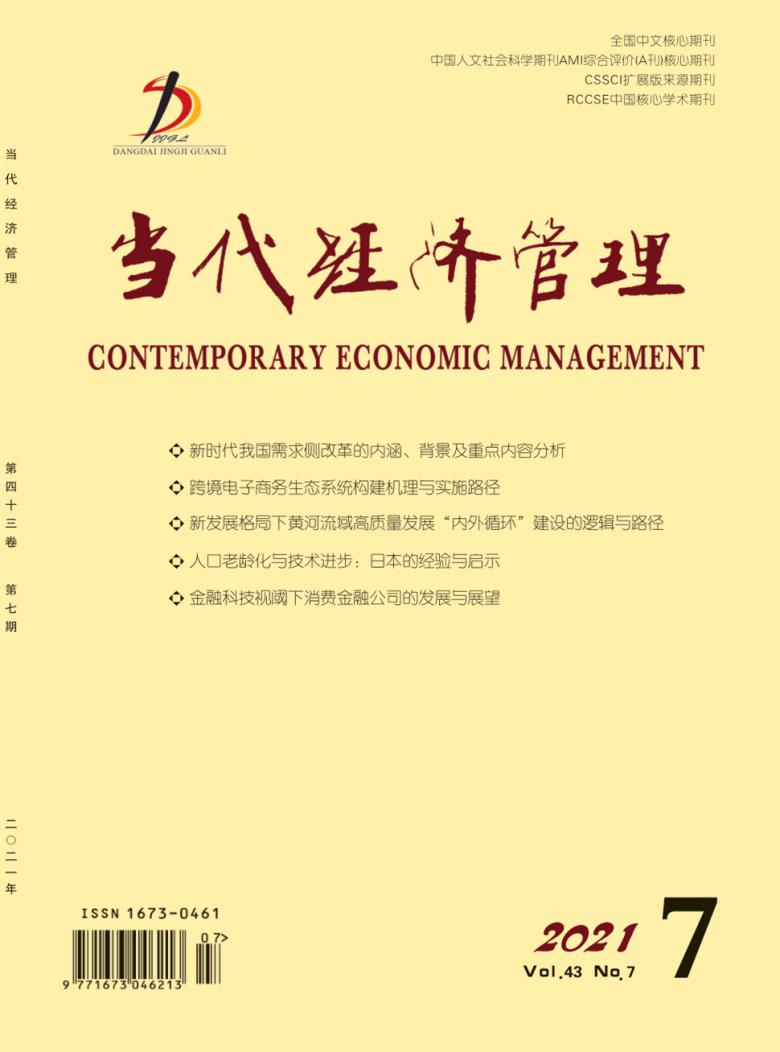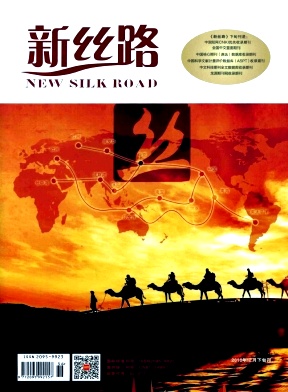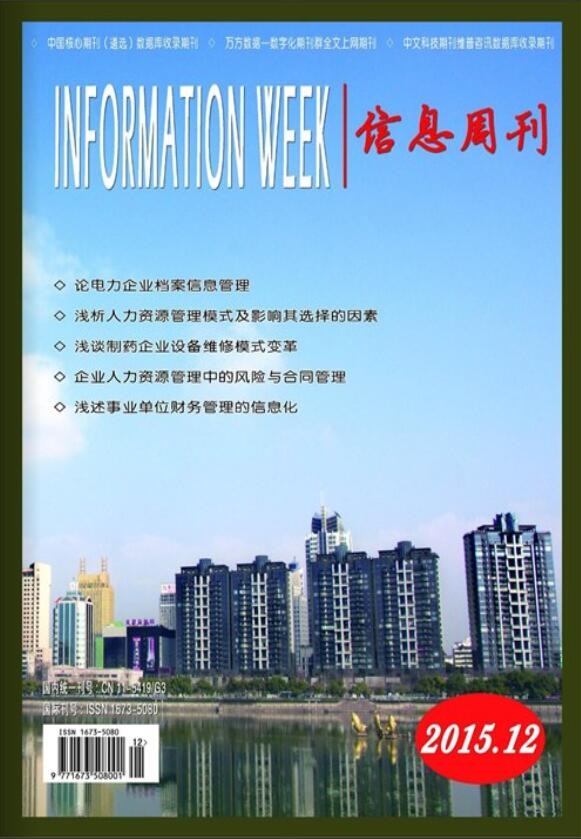探索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的功能分析
佚名 2013-02-05
一、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及其表现
所谓全球化,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整合的综合过程,也可说是这些模式或特征在全球范围移动的过程。全球化推倒国家疆界,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globalizati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全球化的社会语言现象,其二是为了研究这种新现象所需的新理论。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的新视野下,全球化是有关社会语言的;语言内在于全球化过程。因此,用诸如“语言与全球化”这样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不适宜的,似乎将二者割裂了开来。关于作为理论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我们在其他著述中有较充分的论述(Blommaert 2010)。本文简要考察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特征,进而讨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移动性”,联系中国/汉语情境,阐述移动性研究的两大课题。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有三个主要表现。
首先是全球化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因特网的兴起形成了重要的社会语境,使新的话语类型或模式、新的实践、新的认同迅速发展;语言变化随着网络活动而发生,例如采用拉丁化的词语形式而非母语形式;各种英语变体通过新的力量传播到全球;嘻哈(hip hop)音乐等流行文化在全球的盛行推动了这些新变体的传播。
第二个方面是全球化对移民模式和移民社群的影响。难民和短时民工改变了世界范围大城市的面貌,导致了“超多元性”(superpersity)(Vertovec 2006),即城市中原居民与移民的混居,移民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组织形式。这其中包括全球实践共同体构成的网络取代了传统的“言语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Castells 1996)。城市移民的语言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手机、网络视频等技术使移民可以(用母语)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同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少数人群体的多语模式正在变化,语言保持和丧失面临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英语等全球性语言的传播改变了语言的层级秩序,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方言面临窘境。语言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和丧失成为凸显的课题。“大”语言变得更“大”,“小”语言变得更“小”。然而全球性语言的使用,也形成了新的多语模式,创造着新的语言保持机会(Mufwene 2008)。
与以上三个方面相联系的,还有对全球化的怀疑和批评。出于自己的经历和期待,一些群体对能否成功参与全球化过程表示严重怀疑,由此对全球层面的活动和全球化语言说不,转向地区层面及其语言变体。一些人周游全球,跟踪并批判各国政府商议的全球化举措,形成反全球化运动的话语。在欧洲曾发起运动,要求地区语言在法律保护下得到承认。
社会语言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对以上现象作出探索。例如,De Swaan(2001)和Calvet(2006)试图概括全球化时代语言关系的一般特征;Fairclough(2006)探讨了全球化对话语模式的影响;Pennycook(2007)考察了英语在全球化流行文化中的新角色。然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整体面貌尚不明确,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情境。这反映了学术世界的不平等,以及研究西方之外地区的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需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全球化进程发生且影响着语言的结构、选择、使用和相关认同的形成。当今中国便是这样的语境。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全球化的超级事件带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旅游业的繁荣发展。这些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社会语言面貌,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华语圈的社会语言面貌。
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三个特征
2.1影响的广泛性
全球化对社会语言学语境的影响是全方位而非局部的,它引起社会语言学语境的总体重组。“全球化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超出了全球化实际发生的范围”(Hobsbawm 2007:4)。即使它的直接影响仅限于少数人,间接影响也会涉及每个人,包括表面上没有被“全球化”的人。
以因特网和手机的普及对社会交际模式的影响为例。随着信息交流新标准的建立,各机构在日常实践中转而依赖新技术,如银行业务和各种申请手续的电子化。这些机制转型不仅影响到新技术的使用者,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使用或没有机会使用它们的人。在学术领域,当今主要国际期刊的投稿正向电子化发展,投稿人必须通过因特网,稿件须在电脑上做成PDF格式。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到熟练使用电子技术的学者,而且也影响到所有希望参与到学术信息交流中来的学者,例如那些没有或仅有极少相关资源的学者。资源在学术共同体中被重新分布了。同样,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传播影响也极广泛。许多国际学术刊物有明确政策:只接受英文投稿。如果承认其他语言的地位,刊物立刻就会降低档次。不仅论文限于英语,而且必须是“好”英语,即美式或英式标准英语,而非尼日利亚英语。刊物会建议母语不是英语的学者向英语本族语者求助,修改论文。“仅限英语”政策影响到学科范围中希望参与信息交流的所有人。差异不在于影响的有无,而仅在于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而已。
2.2群体和语言变体的不平等
在全球化这一影响所有人的活动中,有输家也有赢家。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扩大了个人、群体、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Hobsbawm(2007:3)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目前流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在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二者都同时发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对全球化影响感受最深的,是从中获益最少的人。”
例如,随着各种机构服务的电子化转型,某些群体获得了方便和效率,而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当电子邮件、QQ、网络视频成为交流的主要方式得到年轻人的宠爱,传统书信往来方式逐渐退出时,依赖纸笔书信进行异地交流的老年人变得更加孤独,甚至被遗忘。当电子投稿成为学术规范时,一些人得到极大的方便,缺少相关资源和技术的学者则被排除在外,非洲许多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仅限英语”的发表政策造成了学术圈的信息传播不平等。已经用其他语言发表的研究,如果想重新用英语向国际刊物投稿,则面临“重复发表”、“自我剽窃”的危险。许多扎根本土的研究不为国际同行所了解(Wen & Gao 2009)。
2.3权力资源的多元性
在制造不平等的同时,全球化也预示着集权时代的结束。虽然国家仍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但它必须与各种民间机构、私人机构分享文化市场。这是由于全球化改变了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价值取向在社会中得以复制的工具形式。例如,国家教育系统的文化霸权被打破,政府须与私有机构分担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如新东方学校、疯狂英语等私人培训机构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全球化的媒体极大地影响着各国的流行文化。学习不再局限于学校课堂,从网络下载外国影视剧、玩跨国电脑游戏、模仿英文歌曲等,成为英语学习的重要部分。这些非正式学习情境易于接触,并且非常丰富,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对文化认同、价值和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Gao&Xiu 2008)。尽管官方可能将英语的膨胀视为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威胁,但年轻学生可能将此视为创造机会、释放个性的活动。
三、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新概念:移动性
3.1移动性及两大相关课题
社会语言学者面临艰巨的挑战,即如何更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全球化的社会语言现象。以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是以静态的“言语社区”为常态,在此基础上去谈“接触”等问题的。而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需要新的以“移动”为常态的范式(Blommaert & Dong 2010)。Blommaert(2007a、2007b、2009、2010)已对部分新概念进行了阐述。这组概念的核心是“移动性”(mobility),即人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以及移动的能力或潜力。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必须是有关移动性的社会语言学。“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被默认为是移动的,语言向人提供或剥夺移动的可能性。人们学习某种语言,是因为它提供了移动的潜势。另一方面,语言和图像等符号本身也可以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social indexicality)而移动,并改变形态。例如指向社会底层阶级的黑人英语,通过说唱乐(Rap)形式进入流行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当中,成为时尚、“酷”的标志。
移动性有两大相关课题。其一是语言的移动潜势,即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为人们提供了怎样的移动潜势,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潜势是否有很大区别;其二是移动的人、移动的语言,即人们是怎样通过使用自己能够具有的语言,获得或丧失移动性,语言如何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而移动,产生新的移动潜势。前者强调社会语言学“结构”的一面,即社会结构对“移动”的影响和限制;后者则既可以是“结构”的,也可以是“建构”的(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2008),它可以揭示人是如何在结构影响下移动或被束缚的,也可以揭示个体或群体的人如何发挥主体性,创造“符号机会”(semiotic opportunity)而移动于社会空间,建构新认同。就“结构”与“建构”而言,移动性研究侧重的是经常被忽略的“结构”的一面。
下面我们联系中国/汉语情境探讨这两大课题。中国学者已经在相关领域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描写性调查,获得了宝贵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在以移动性为核心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同时,也还有更多现象、问题和领域有待探索。 3.2语言的移动潜势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不再锁定于某个空间,人们很容易搬迁至异地,或者坐在办公桌前、网吧里通过网络跨越广阔空间与他人交流。中国内部大量移民带着自己的方言和语言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国家的“边缘”移动到“中心”,在城市形成了新的社会多语环境(参见Dong & Blommaert 2009)。这些中心具有多元混杂的都市特征: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真正的“本地人”只是少数。中国国内移民也是全球化过程的体现,与其相联系的是新精英阶层的形成、部分劳动阶层贫困化的加剧、当地和局部区域的社会语言秩序重组。在此背景下,需要考察哪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什么?普通话是不是国内移动潜势最大的语言,其地位受到何种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竞争和挑战?强势和弱势汉语方言的地位和移动潜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有何改变,是否能在多元混杂的情境中生存?
3.2.1英语传播如何为中国的语言格局洗牌?随着新兴全球精英阶层的形成,英语的全球移动潜势迅速增强。据大样本调查统计推算,中国约有4.7亿人学过英语(魏日宁、苏金智2008)。过去普通话是移动潜势最强的语言,而现在随着人口社会异质化的增强,出现了更复杂的格局。对部分人来说,英语成为提供全球移动潜势的语言。它不仅提供在虚拟空间移动的可能性,而且提供在物理空间移动于全球范围的可能性。懂英语的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全球各地旅游、经商、生活。英语为精英阶层提供的移动潜势几乎是无限的。具有话语特征的新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如雅皮士、波波族等(Wang 2005)。
即便对普通人来说,英语移动潜势的吸引力也很大。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从贫穷的农家孩子变为百万富翁、“出国教父”的故事广为人知,成为英语改变命运、成功爬至社会上层的象征。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英语,连旅游点的许多小商贩亦能用英语交流。另一方面,对英语学习的投资彰显了贫富差距,不同经济水平家庭在孩子英语学习上的投资差异很大(邹为诚等2006)。这种投资差距是否会增加语言资源分布的不平等性,英语究竟是供所有人向上攀爬移动的“梯子”,还是资源获得过程中的社会阶层“滤网”,还有待深入考察。英语学习对民族认同影响的复杂性,也有待深入探索(高一虹等2004,陈新仁主编2008,Lo Bianco等2009)。
3.2.2汉语在大中华地区、世界华人圈和全球范围的地位。在英语称雄全球的状况下,汉语的移动潜势定位于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世界范围的华人社区。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出现了“汉语热”,来华留学生剧增,对外汉语教学的市场也在国际上逐渐扩大。据统计,2001-2008年来华留学生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09年留学生总数突破22万(崔希亮2010),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4000万①。汉语正在成为次强势的全球化语言,逐渐进入其他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外语和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日本、泰国的第二大外语(郑梦娟2006)。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也相应处于上升势头。那么,汉语的兴盛是否、如何悄然改变着全球的社会语言格局?在与英语等语言的竞争中,汉语的移动潜势如何,其发展方向是什么?
3.2.3中国国内社会语言秩序的改变。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强化了英语的移动潜势,社会精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消费英语文化产品,出租司机等服务行业人员也被要求学习英语,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的交际效益。那么,英语水平不高的人是否感觉无力或权力的丧失?少数民族语言和大多数汉语方言的移动潜势相对很低,功能领地局限于所在地区和相关群体,有些正在消亡(戴庆厦2004,曹志耘2006),理想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道布2010)面临多元性锐减的局面。然而,这些语言和方言能与占主导地位的普通话共存的事实,是否也预示着它们有相当大的活力和自我保持能力?强势方言粤语有扩张趋势,群体有强烈的语言权利意识并诉诸“挺粤语”的集体表达②,这将对语言政策带来什么挑战?是否会引起过度敏感和语言问题政治化,进而强化普通话相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上下层级关系?是否会影响其他群体的语言保护和保持意识?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萎缩的同时,它们与普通话的混合变体也不断产生,一些方言借由流行文化得以传播(如流行歌曲中的粤语、小品中的东北方言),这些现象在中国的整体社会语言格局中是否占有、占有何种地位?
3.3移动的人、移动的语言
在重组的社会语言格局中,人们怎样通过语言使用获得或丧失移动性?他们是否主动采取措施,以选择、保护、发展其语言或语言变体?他们是否、如何创造和利用符号机会,建构新的认同?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和挑战?语言和语言变体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是否也发生了移动,其社会指向产生了什么变化?
3.3.1内部移民语言及变体研究。国内移民可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考察。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3亿,比上年增加1.9%③。农民工涌入城市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语言格局(曾炜2006)。对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汉语方言格局总体变化(苏金智2008)、农民工在城市中与不同群体交流采用不同变体的状况(夏历2007,刘玉屏2010),已有定量描写和分析。施旭、冯冰(2008)在对中国公共话语的考察中,关注到农民工等群体在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董洁(Dong 2009)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农民工语言,揭示了更为建构的一面。她基于层级(scale)概念,将认同建构分为人际、元语用、机构话语三个层面,呈现了农民工在北京混合使用家乡方言和普通话,建构多元认同的状况。
3.3.2海外留学生、侨民的语言使用、保持和丧失。中国有大量留学生、移民和侨民短期或长期居住海外。汉语及方言在他们居住地的使用分布是怎样的(张力2008,张东波、李柳2010)?汉语及方言在不同代的华人移民中是怎样保持、转用或丧失的,其原因何在(郭熙2003,王晓梅、邹嘉彦2006)?他们采用了哪些母语保持策略,成效如何?以上问题和调查材料可以放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中考察。海外人士返乡后,对国内交际环境的适应状况如何,感受和态度是怎样的?那些以频繁往返中外乃至周游全球为生活常态的人,其语言使用、交际策略和语言认同又是怎样的?
3.3.3在中国的外国人共同体研究。在中国的“老外”数量在增长,且形成聚居共同体。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长,有家属陪伴。他们享受专门开设或主要面向他们的学校、商店、酒吧、医院等一系列机构、场所和服务;在当地发展出一些与中外人士交流的常规活动形式和社交圈,如英语戏剧演出、家庭音乐演奏会;通过新的交流技术用母语与故乡亲友保持通畅的联系。“老外”的言语库是怎样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如何,以什么为具体目标(经商、购物、教育等),满足双语家庭需要,或者仅仅是对居住国文化的尊重?他们怎样用英语与本地人互动,这种互动又怎样建构了当地人的言语库、言语特征、语域(高建平2008)?跨国婚姻形成了双语双文化家庭,这也是全球化的特征,但相关研究还很少。中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发展势头,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低层外国工人(如保姆、低薪合同工)来此工作,这些群体的语言使用也值得关注。
3.3.4英语的“非标准”、“非常规”使用。中国人的英语使用产生了各种新的语言变体和特征,如“中国英语”、语码混合、语言或语用错误。政府和社会做出努力使公共语言环境“优化、净化、国际化”(周庆生2007),如奥运会前北京曾开展市民为公共标识中的英语挑错活动;学者基于调查为相关部门提供对策(周庆生2007)和规范文本(杨永林2010)。政府对非常规的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处理,体现了中国城市国际化的努力。但个人和群体有可能放任不规范形式自由发展,这可能意味着对某种文化时尚和价值的追求、认同的维护或扩展。例如,大学生用英语为自己取名,是通过符号的创造建构理想个人认同(Gao, Xiu & Kuang 2010)。一些大学生认同中国口音的英语(Bian 2009),志愿者在奥运场馆贴出不适宜的标语“Wespeak and the world will listen”(Gao 2010),中国网民在网上用欠规范的英语对国际事件发表看法,都是自发地用全球化符号来表达民族认同。具有本土特色的新话语还广泛出现于广告等话语类型中,构成“全球本土化”的新风景(Wu 2008)。在国家、机构和个人层面,民族认同何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藉由语言的使用得以保持和强化?在“另类”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新的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
四、结语
全球化的特征是移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是移动的社会语言学。目前中国本土出现的社会语言学现象,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本文简述了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特征,着重讨论了这种现象的核心概念“移动性”及两大相关课题——语言的移动潜势,移动的人和语言,并举例说明了值得探索的问题。中国学者已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还需要更多地为国际同行了解,所报告的材料也可在“移动性”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下获得更充分的解释。这一视角能使我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到现象在总体格局中的位置、受系统结构的制约,并反过来分析或预测现象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该视角向我们强调和警示结构的限制,揭示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移动资源的巨大不平等性,同时也启发我们不要忽略语言使用者的主体能动性,应注意考察新的符号机会和移动潜势的创造。
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整体而非部分的,它改变整体社会语言学版图。由于这一整体性特征,相关研究需要社会语言学者的跨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