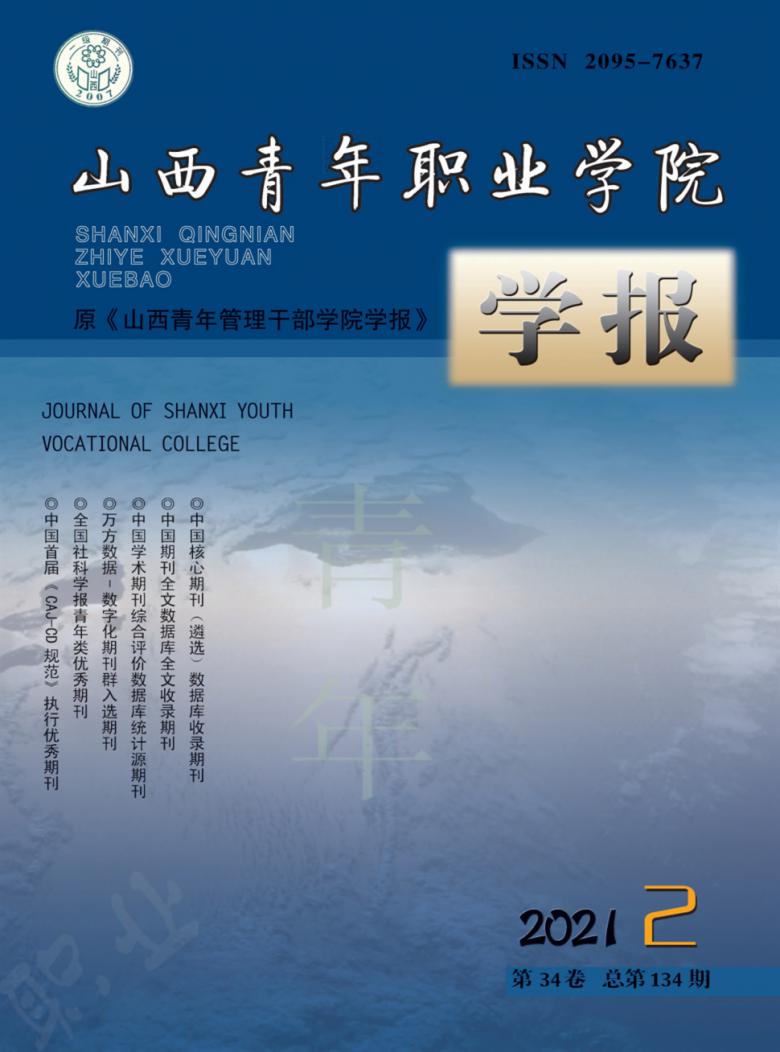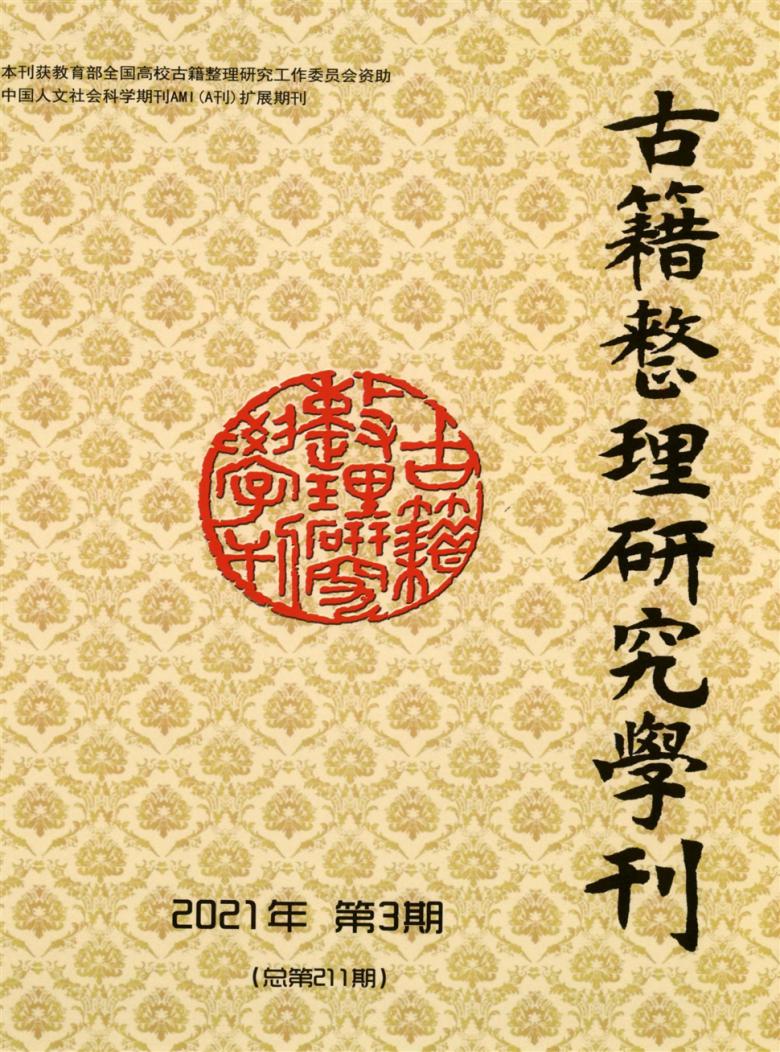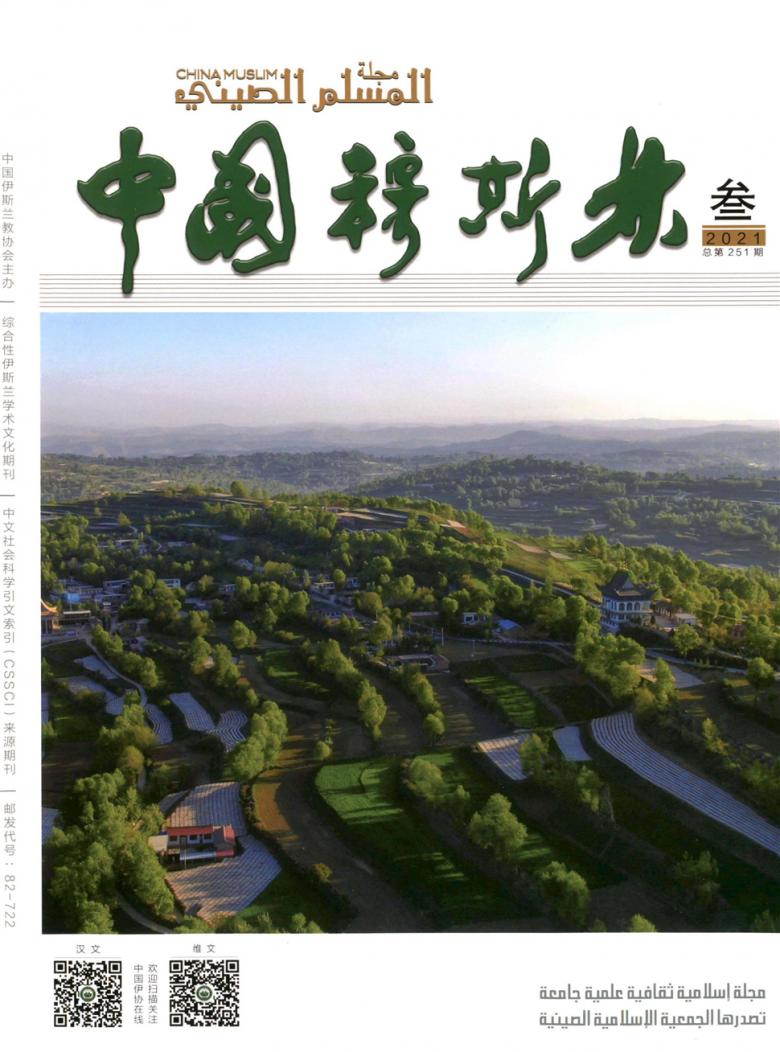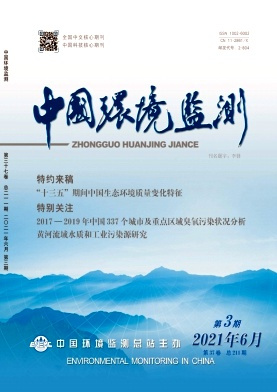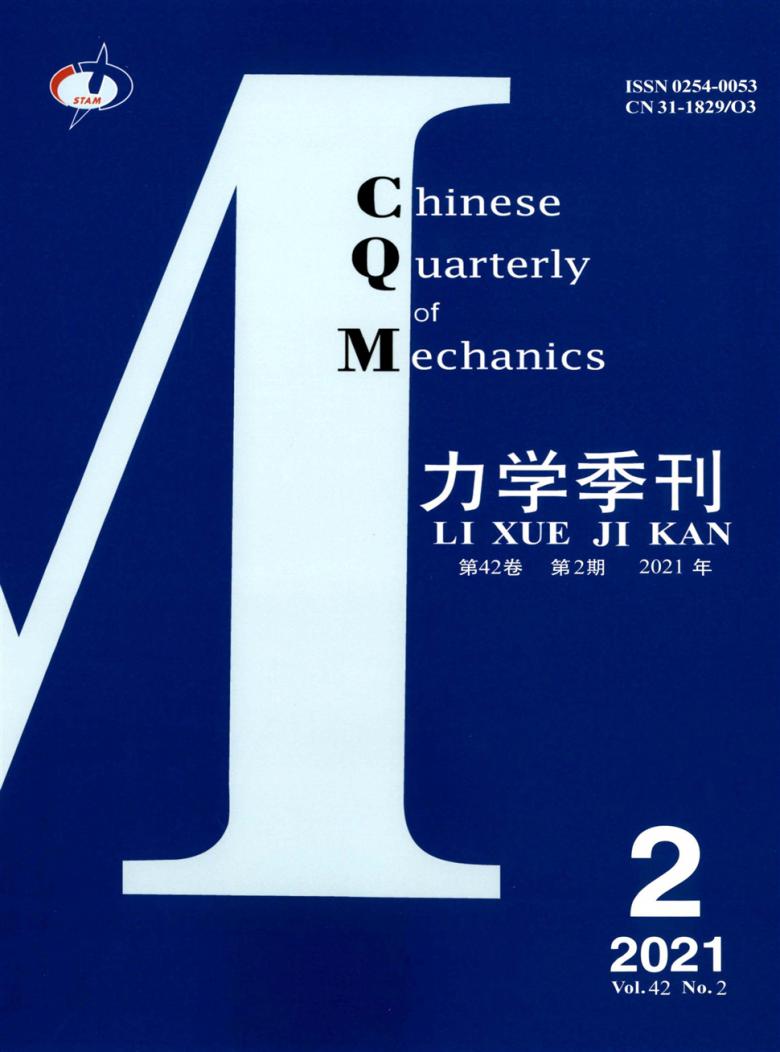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探究
王海燕 2011-10-10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二、互文性、互文本。“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