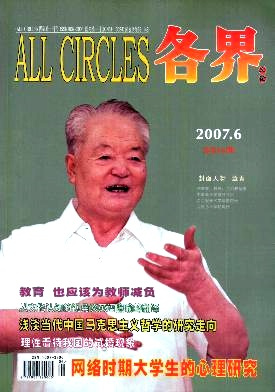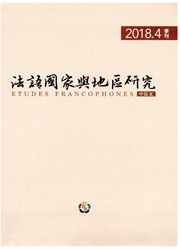关于浅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徐小丹 2011-06-13
论文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伦理思想死亡意识鬼气
论文摘要: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来自他生命本体的矛盾、深刻和复杂,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如何看待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
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的先驱,鲁迅“五四”期间是以彻底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他不仅借小说人物之口揭示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而且在杂文中一次次发出痛切的呼唤:
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人把鲁迅看作是新文化运动中全面、彻底地反传统的典型代表。的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所在,但是却不能全然概括鲁迅的态度。它忽视了鲁迅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是出于一种文化策略。鲁迅是深知中国传统社会和国民性格心理的,他在《无声的中国》做了生动的表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为了打开新路,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甚至是过分的批判态度,以达到动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现实效应,无暇顾及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达了他们对旧文化、对旧社会的真实情感。事实上,鲁迅所表现出的激烈而坚决地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割断了自身与传统的联系。这一点,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已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这种深刻的矛盾使得鲁迅对旧文化极为厌恶又不无留恋,笔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旧文化情怀。
鲁迅多次强调自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知识分子”,这表明他是把自己放在传统之中的,在整体上感受到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又与传统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其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鲁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种儒学的氛围中,不能不受到这一传统的精神价值的熏陶。比如,孔子哲学思想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精神,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等有益的格言,均为鲁迅所赞赏并奉行的。再如孟子强调“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上的主观努力,与鲁迅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显然相通。而孟子所主张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也不能说对鲁迅刚正不阿的人生观毫无影响。事实上,鲁迅反传统的历史行为,也不无包含着儒家的人世精神。他青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相呼应。
此外,鲁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认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笔下,墨子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和平战士,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他奔波劳碌于楚国和宋国之间,止楚攻宋,消洱杀戮,维护了正义。反观鲁迅本身,不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吗?他极其反对,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徐寿裳曾说鲁迅写的《非攻》在描写墨子的伟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这话是不假的。其“爱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爱”思想的影响。另外,鲁迅的复仇意识中还可以找到墨侠精神的痕迹。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墨子之徒是侠”,轻生死、行侠仗义、睦毗必报、扶危济难是其基本的精神写照。而这些墨侠精神在鲁迅的大量文本中(如(铸剑》《非攻》(女吊》《无花的蔷薇之二》等)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鲁迅一度赞扬墨子临危赴难的品质,都可以看出他与墨侠精神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
鲁迅也曾说过,在他的思想中有庄周的“毒”,说明了庄子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虽然对庄子哲学所提倡的人生观、社会观持批判态度,但对其瑰丽的想象、丰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怀却赞赏有加。关于这点,郭沫若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他指出“鲁迅爱用庄子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庄子的反映”。的确,鲁迅最为推崇的就是庄子和魏晋的文章,喜爱庄子的说理以驳难,常含讥讽的笔调,其《故事新编》和《野草》的创作就深受影响。此外,庄子的个性解放思想对鲁迅也有很大的启发。他主张“任其性命之情”,反对一切有损于性命之情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倡扬个体生命的自我冲决和超越能力。而鲁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个性精神绝对自由,提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对一切对个人精神自由的束缚与压制有一种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识。
再综观鲁迅创作的大量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触目的题材—“死亡”。“死”是鲁迅热衷的主题,其大半生不停地写着“死”。夏济安先生对此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作为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鲁迅的死亡意识显得矛盾而复杂。首先,鲁迅身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现实残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随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割舍的启蒙使命感,坚决地批判传统文化。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儒家是从生命的起点和过程来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进取。因此,儒家将“死”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求转换到现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价值,以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理想与功利思想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也不例外。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随的一生。家庭的变故,社会的黑暗,个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扰,死亡时时威胁着他。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然而,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被压倒,以生来对抗死,反对轻死,贬斥苟活。他明确表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人类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积极参与现实,以个体生命去肉搏着空虚中的黑暗,在抗争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人类的进步,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抗争精神显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人生精神的强烈浸染,与儒家“尽人事”的进取态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鲁迅“死”的话语中,他又多次说到自己是“死的随便党”。给友人的信中曾出现“往往自视亦如轻尘”、“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等等类似的话。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可见鲁迅不害怕死,把死视为自然、必然的结果。这种死亡意识与道家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终极价值,生死与之相比,不过是道的自然表现。“死“就是让生命融于自然,应该顺应自然,对死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鲁迅与传统文化联系本身并非单一和纯粹的性质。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他曾有这样的表述:“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孙郁先生认为这黑暗便是某种鬼气。而所谓鬼气,一方面是对存在的虚无的揭示,是实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鲁迅自己内心绝望的心绪,与佛教中的苦难感交织在一起。自然,这与鲁迅的生活经历相关。鲁迅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亲去世。在这种状况下,他经历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态炎凉。因此,对生活中种种丑恶与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对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叹:“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使鲁迅的作品充满了阴深恐怖的“鬼气”,常常缠绕着魔鬼的阴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没在这一长影中的挣扎。正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并向虚无主义转移。我们都很清楚,鲁迅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无可否认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着悲观绝望、虚无厌世的一面。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被虚妄所压倒,在虚妄面前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见,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用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做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的确,鲁迅仍具有传统文人的内质,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冲破一切传统的同时,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旧文化情结,形成了鲁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与痛苦,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