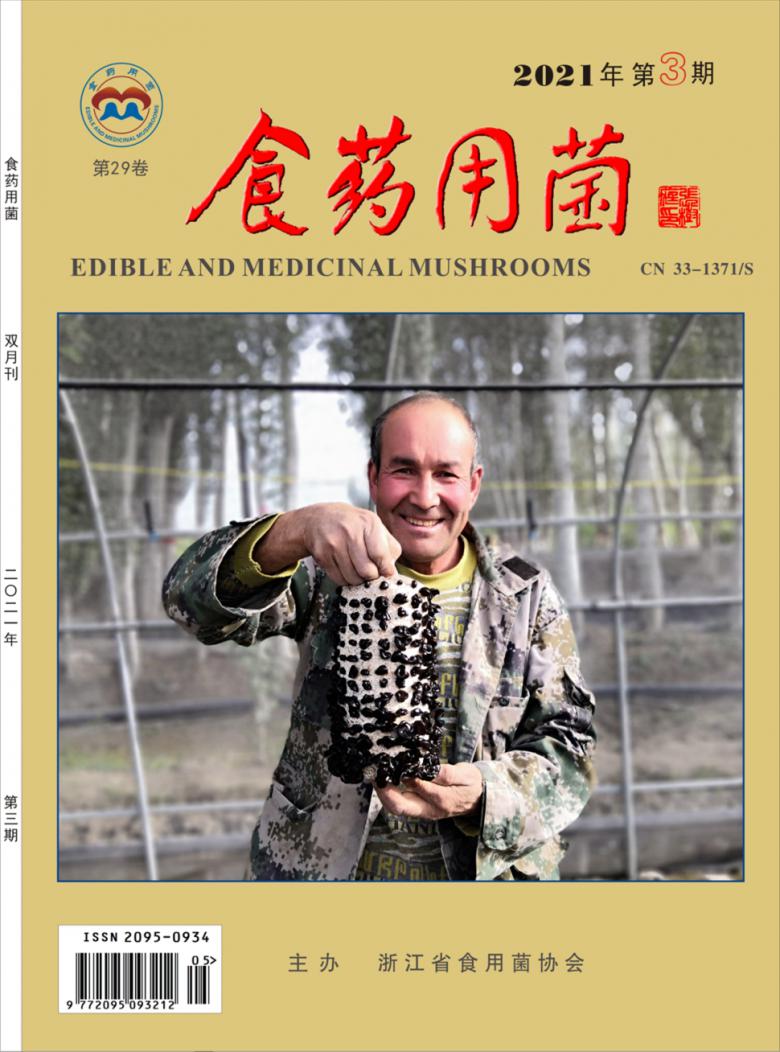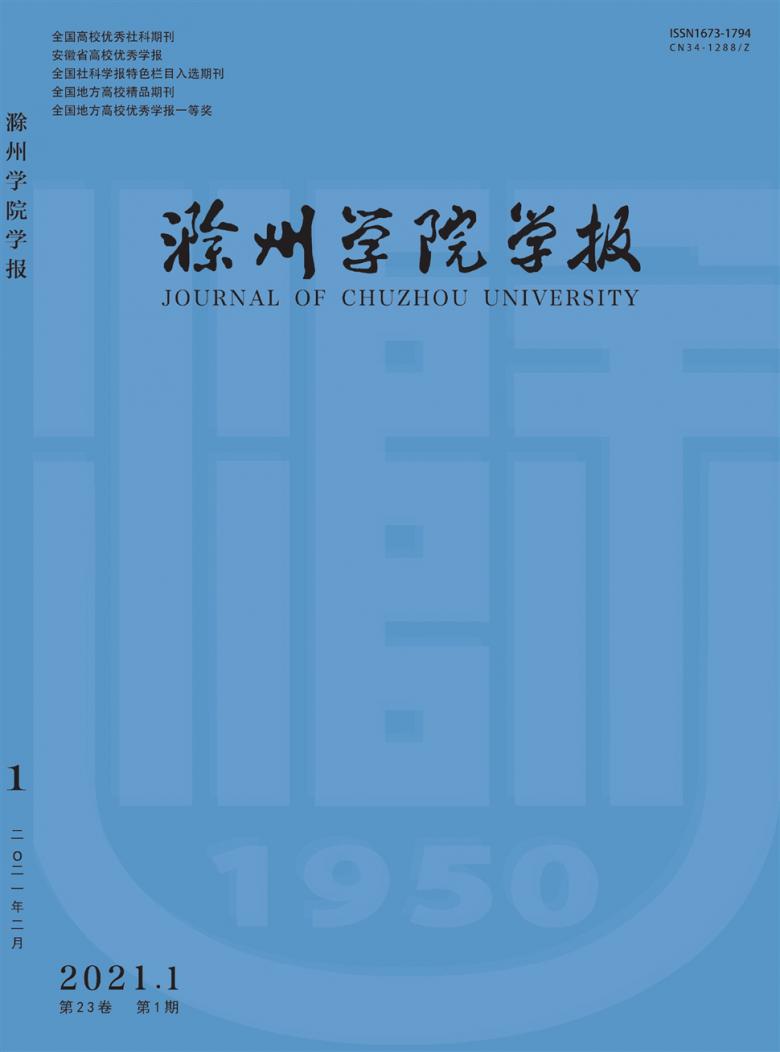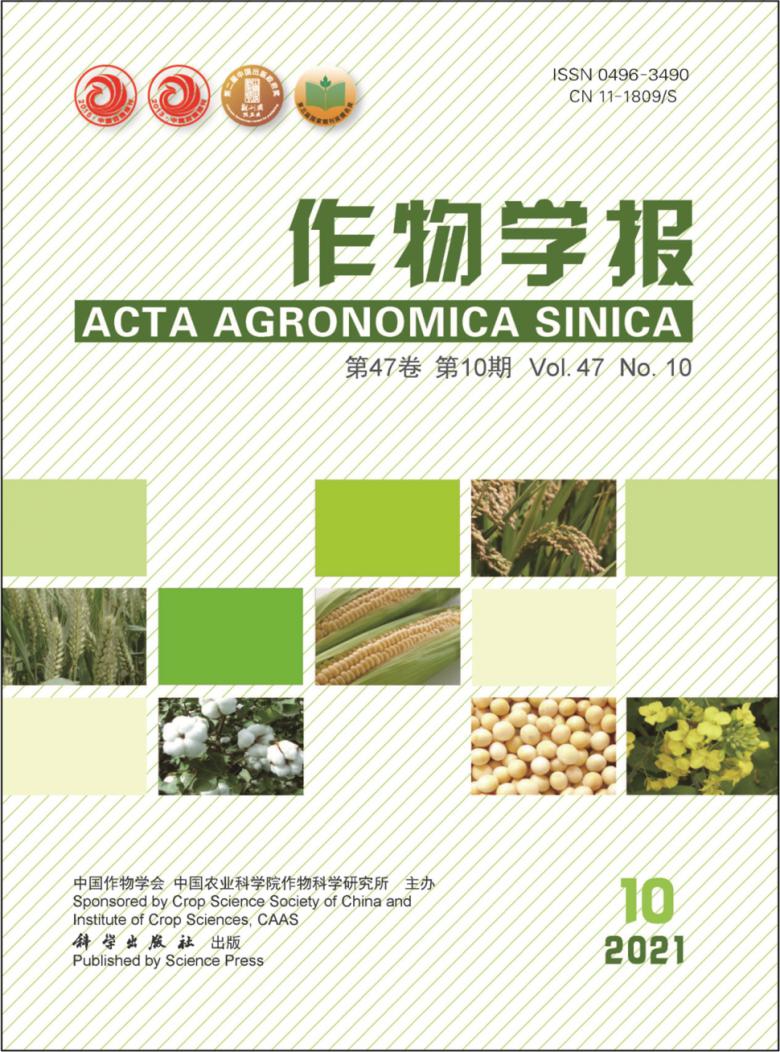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女性文化批判
王海梅 2010-12-05
论文关键词:鲁迅 夫权 女性角色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中国长期以来的“父子型”文化模式下,女性作为文化存在,其生存是艰窘而悲惨的。鲁迅通过祥林嫂、子君、爱姑三个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女性悲剧生成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自身原因,以此来实现他对女性文化的批判。
五四时期,对旧道德、旧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讨伐,妇女问题在这次思想大震荡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对妇女的讨论出现了空前的高涨。鲁迅小说里、杂文里曾经多次表现妇女的生活,描写妇女的遭遇,控诉妇女的命运,《祝福》、《伤逝》、《离婚》便是其反映妇女问题的力作。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自己的小说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主意。”显然,对病态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在病态文化濡染下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女性生存惨相的展示,始终贯穿在其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以此揭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运演的是“父子型”文化模式,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都处在“被人看”、“被人用”的角色地位,她们仅仅作为人妻、人母、或“玩物”、“附属品”等角色进人父系制的家庭秩序,以绝对服从以尽其工具意义上的角色职能,以倍守封建的父权文化和封建礼教的“规范”作为自己的职志。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领域处在无权的被人摆布的地位。自从儒教宗师孔子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男尊女卑思想后,一代又一代儒家文人都在注释、扩充和强化这一思想,使得女子在这一强大的父权文化覆盖下渐渐迷失了自我,女性被制度化、道德化地全面剥夺了人权,他们的卑屈地位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是维系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鲁迅正是站在反封建文化的高度,以“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美学追求,塑造了祥林嫂、子君、爱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此表现父权文化栽害、濡染、重压下的女性屈辱、悲惨的悲剧命运。
对于理解父权文化下女性“非人”化的生存惨相,《祝福》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和认识价值的。《祝福》讲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南农村一位劳动妇女祥林嫂命运多并的故事。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祥林嫂所受封建父权文化的重压及其濡染是至深的。父权文化规定下的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和父权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其他精神枷锁在其身上都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她对社会把女性角色固定为‘、女儿—妻子—母亲”三重复合的理想女性标准视为天经地义,对封建的父权文化意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的“从一而终”的节烈思想深信不疑。作品正是通过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揭示了父权文化毒害因袭下的不觉醒农村妇女丧失既定角色后的走投无路。
同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祥林嫂一向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尽其女人的角色职能获得妇女最起码、最“正常”的生活,但因命运的多并,使她最终丧失了其固定的角色地位,这是祥林嫂的第一重悲剧。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缺乏“人”的观念的理性自觉,对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反而无意识的维护,并着意以封建礼教的标准塑造自己,但依然不被社会所承认,这是第二重悲剧。祥林嫂最初是被迫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在父权支配下她承认了这个不合理的婚姻。但不久丈夫死去,使她第一次失去了“人妻”的角色地位。在那个时代,出了嫁的女人永远是丈夫的附属品,即是男人死了也还是他遗留下来的附属品,所以她本想格守礼教的规范而守寡,“扎着白头绳”,愿意为丈夫守孝。她的出逃,固然是对“严厉的婆婆”的逃避,也是对自身不幸环境的逃避,她在鲁家“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固然是勤劳能干,但也是失意后孤独感的寄托。所以,尽管丈夫的死,谈不上对她有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但“寡妇”的身份无疑使其心理蒙受浓重的阴影。“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抵死反抗再嫁,但最终还是给夫家捆绑回去,像一头牲口似的被卖到山坳里。祥林嫂再嫁贺老六后,尽管有违初衷,但一切都已注定,于是慢慢对其第二个丈夫有了好感。对自己的骨肉、精神寄托—阿毛有了感情。可以说,这是的祥林嫂又一次获得了自己作为女人的角色,重建了心理上的平衡。但不幸的是,第二个丈夫又死于伤寒,儿子阿毛又被狼衔去。阿毛的死对她是致命的一击,这种浸透骨髓的悲哀,使她变得精神失常。因为她担着“失节”的罪名而获得的生活希望彻底成为泡影。她反复述说阿毛的故事,表露出对自己也曾和别的女人一样“有过儿子,做过母亲”的自豪和失子的负疚自责,当然更是心灵受到重创后心理变态的“失语”。
对于祥林嫂而言,再嫁、丧夫、失子使她丧失了封建文化对女人规定好了的角色职能和理想存在样式。妻子、母亲、“好女人”做不成,但终究还要生存下去,夫家赶她出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重回鲁家“作稳了奴隶”,尽其“被人用”、“被人奴役”的角色,以求得蔽体裹腹之需。但在渗透着浓厚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环境中,她这种地位也不能保住,因为她被视为“不干净的女人”。尽管她顺从于封建文化的戒规条律,试图用“捐门槛”赎罪,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在礼教和神权的束缚下,最低层次上的愿望也不能得到满足。这次打击,使其精神彻底崩溃。各种角色丧失后的祥林嫂“百无聊赖”、既没有了人身归属,又没有了精神寄托,走投无路,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希望“与家人见面”,在阴间继续其角色职能,把人间未竟的希望寄托与虚无。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漫长的中国历史下的女性文化存在的畸形作了有力抨击,对女性因受封建礼教的因袭濡染的生存惨状作了深刻分析。《祝福》其实就是其思想的形象写照。正如鲁迅其他作品揭示腐朽文化因袭下的“国民性”一样,《祝福》揭示的是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因袭心理状态下的惰性,意在“揭除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透过祥林嫂悲剧的一生看出,封建社会的女性存在本是“非人”化的,但广大的妇女们却缺乏自我意识,不对父权文化进行反抗,而恰恰是把封建礼教、封建的女性观和性别角色定位内化为自己的义务,以当时的社会道德为道德,以当时的普遍观念为观念,这正是祥林嫂悲剧意义的深刻所在。
在五四时期或五四高潮和落潮时期,知识女性是文学中数量最多、影响较大的一类形象,这类形象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暴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表现了知识女性“自我观念”的觉醒。但是鲁迅的《伤逝》却是借助子君“梦醒后无路可走”的“人生最大的悲剧”,表现了女性生存的艰窘和惨象。
无疑,子君是“自我观念”觉醒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不顾封建文化濡染下的遗老遗少老东西小东西之流的敌视和狠裹的目光,不顾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的干涉和反对,甚至不顾和家庭断绝关系,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鲜明的带有冲决封建文化约束的“五四”时代的色彩。这是被“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思想唤醒了的年轻知识女性向传统的父权文化发出的挑战,是意识到自我价值和尊严、认识到“女性也是人”的表现。
但是,在这种男权文化氛围相当浓重的社会里,女性没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能力,女性即使觉醒,命运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她除了觉醒的心,还带了什么去?”的确,五四运动以后,社会部分职业向妇女开放,农村妇女由于经济破产流亡到城市,被工厂主雇用,为的是她们工资低,少数知识女性则被当作“广告”、“花瓶”,以迎合男子一贯玩弄女性的卑鄙心理。中国妇女仍然在被歧视、被损害、被侮辱的生活中挣扎。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她们从闺阁中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他们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所以“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既然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政治生活中,女性没有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在经济生活中,女性没有与男子同样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女性就不可能真正的有路可走。所以“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因为如此,始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觉醒”了的子君,也只能在达此目标后而止步,从而使她虽冲破旧的束缚,却走向了另一种依附。她和许多犯了时代病的“五四”青年一样,并未将反封建、反传统的理性觉悟内化到心理深层中去,真正成为价值规范,传统的女子治内的思想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附意识还影响着她。所以她心满意足地承担了家务劳动,并为此“倾住着全力”,把所有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涓生身上,把涓生的怀抱视为生命的港口,在小家庭的金丝笼里“麻痹了翅膀,忘却了飞翔”。这种“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生活的依附性无疑给她的命运播下了悲剧的种子,所以当涓生面临失业时,她变得异常的怯弱和消沉,最终还是在生活的压力下,重回父亲家里而孤独的死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娜拉走后,“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在《伤逝》中正是怀着无限爱护和惋惜的心情,以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反映了父权文化下男女不平等社会中“觉醒”女性无路可走的悲剧命运,更批判了父权文化影响下女性的思想中因袭的传统重负、封建奴性和弱者意识,以此揭示出时代转型期女性悲剧生成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自身原因,以及女性解放的举步维艰。
四
鲁迅谈到《离婚》时说:“这里的爱姑,本来也富有反抗性,是能够都记下的,可是和《伤逝》里的子君那样,还没有长大,就被黑暗势力压坏了。”;’〕如果说子君的悲剧是在揭示父权文化濡染下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复归依附的话,那么《离婚》所揭示的就是女性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尊严而向父权斗争的失败。
男权社会里,婚姻历来便是男权至上。男子拥有选择、占有直至抛弃的权利,女性从属于男人、受制于男人,男人掌握着“休妻”的权利,而女性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任男人摆布而忍辱负重地以男人的意志为中心活着,倘若男人有了新欢,一纸休书便能将旧人扫地出门,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多听到弃妇们悲悲切切的哀婉之声,多看到女性生存的沉重与惨痛。
同是农村妇女,爱姑的性格不同于祥林嫂。她泼辣能干,具有反抗性。她要求妇女有独立人格,与丈夫平起平坐,她不能忍受妻子的地位被剥夺,反对丈夫纳妾或与人饼居。丈夫与小寡妇私通,她就骂丈夫是“小畜生”;公爹偏袒丈夫,她就斥之为“老畜生”;并且表示“我一定要给他们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她把夫家闹得鸡犬不宁;地主慰老爷出面调停,她也拒绝接受;连七大人也不放在眼里。她的反抗的确给人耳目一新、酣畅淋漓之感,使我们看到中国女性反抗封建夫权的精神气概。但最终还是在浸染着浓厚父权意识的“七大人”们的压力下被迫屈从,宣告了女性为命运而抗争的失败。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不是一纸休书便可以结束一次婚姻的时代了,但是封建的父权意识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女人依然处于卑贱、被人摆布的地位,毫无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尽管表面看来,爱姑的离婚是那样的“公正”而“堂皇”,最后夫家再加十元钱,爱姑也愿意,双方和和气气分手。但十块钱里却透着爱姑的屈辱和无奈,包含着“七大人”们对妇女地位、人格和尊严的践踏。因为爱姑的离婚,说到底不是自由离婚,而是买卖离婚。
对爱姑来说,离婚是不幸的,在贞操节烈思想依然深重的社会现实中,女性被抛弃,实际上等于生命的终结。因为女子还依赖男子生活,女子再嫁还受社会鄙笑:男子可以另求新欢,逞其“自由”,而女子只有屈辱和苦痛。作品正是通过爱姑抗争的失败,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夫权制度的罪恶,反映了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同时我们也看到,爱姑反抗的失败,也是其骨子里的奴隶心态所导致。因受父权文化的濡染,因依然被“传统”深深禁锢着,她的反抗自始至终是那么苍白无力。她用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教条为思想武器来反抗男权社会,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啊!那么容易吗?”而且自从嫁进夫家后,“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可见其反抗父权文化的理论依据还是封建礼教,并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主体自觉。她反抗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住“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纽带的婚姻家庭关系,其结局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在旧中国,妇女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从妇女角度人手,更能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罪恶。《祝福》、《伤逝》、《离婚》先后从三个层面上表现了女性在父权文化濡染下的生存惨相,以此指明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