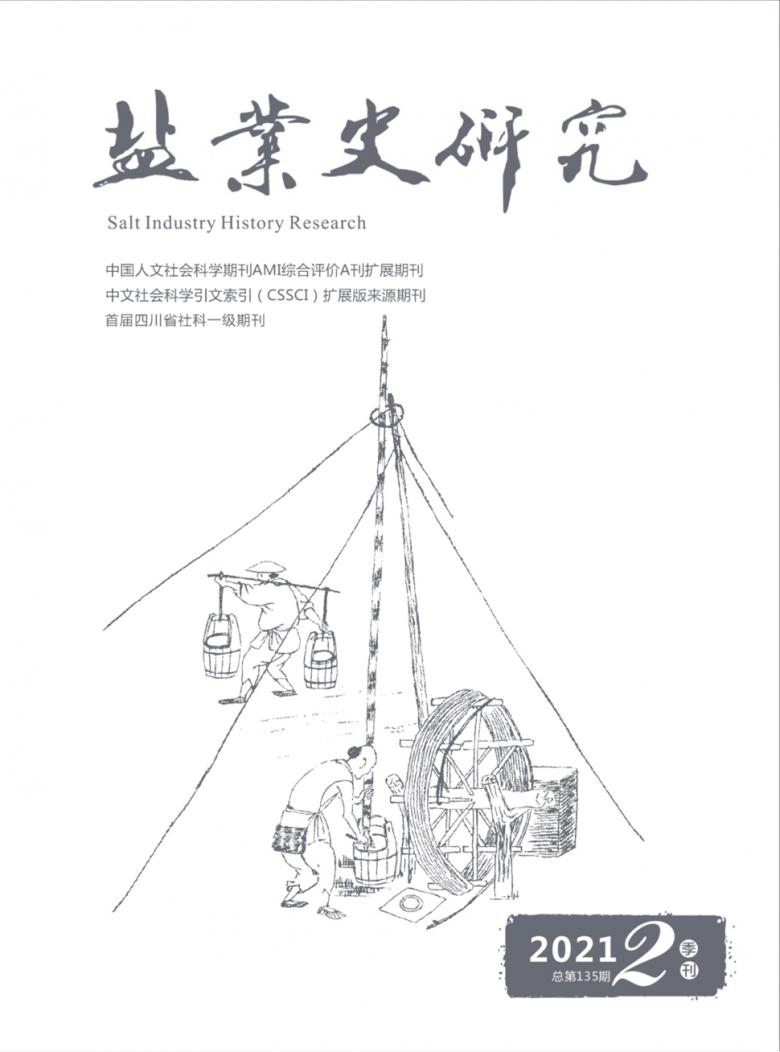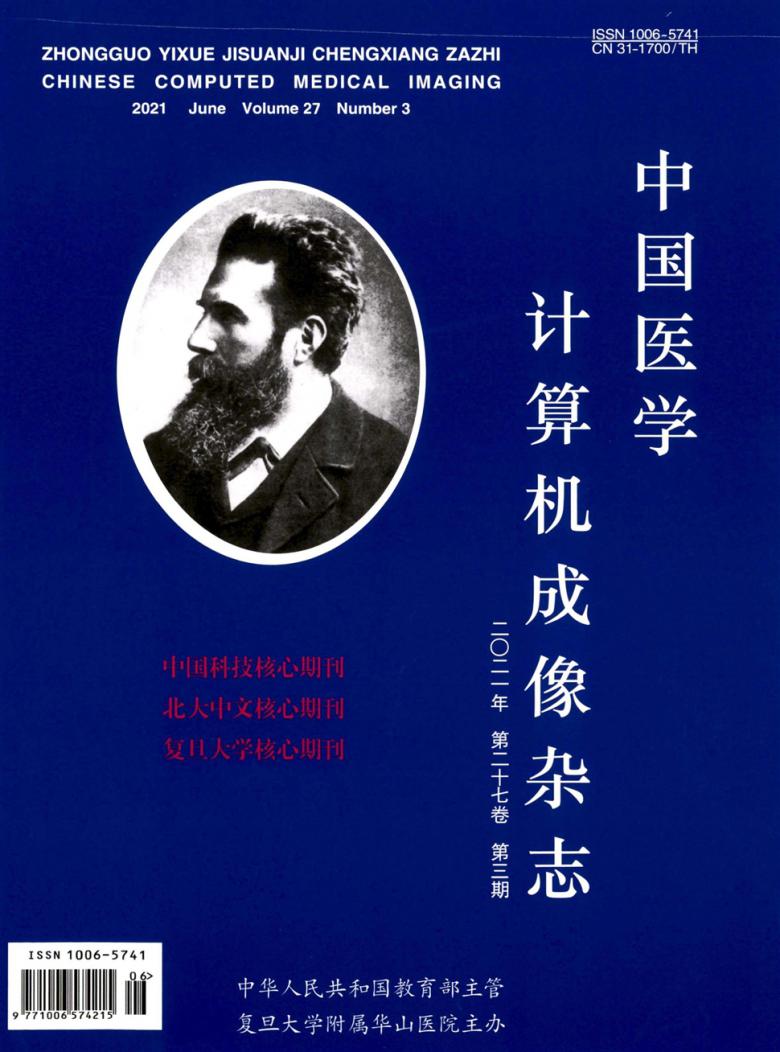浅谈人性透视与文化批判:鲁迅、钱钟书小说主题之比较
赵庆超 2010-12-02
论文关键词:鲁迅钱钟书现代小说人性透视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在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上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们的小说均以苛刻的标准过滤传统和现代视域中的人生百相,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其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能够提升文学彰显人性和世界的审美品格。
鲁迅和钱钟书分属于不同的现代文学史阶段,其各自创作的小说数量都不是太多,但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审美意蕴和生命体验却是同时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敏锐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学养积淀为他们提供了观察世界、表现人生的独特视角,这种厚积而薄发的创作范式是他们的小说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笔者试从对比分析的角度研究两人小说在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方面的异同性,并试图揭示造成这些异同表现的时代文化症候和文学启示。
一、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
鲁迅和钱钟书以一种苛刻的眼光过滤现实与历史、本土与异域的复杂文化现象,在冷静的审视中揭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惰性对个体生命的无情吞噬和有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发掘沐浴在自由之光中的现代人深陷新的人生困境的深层原因,指出部分不自知的人们沉醉于黑暗大泽而不挣扎、不觉醒的劣根习性和悲剧命运。两人都在小说中揭示传统文化麻醉人、毒害人的负面作用,批判经过几千年积淀而占据国民精神高地的文化劣根性。这种积习深重的传统思维定势被国民奉为圭臬,以极大的排他性对相异的精神向度进行挤压与吞噬,对异己分子的精神与肉体进行双重虐杀。对于这种在传统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惰性文化因子,鲁迅和钱钟书都进行形象的刻画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指出它们滋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不管是鲁迅小说中的闰土、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乡间底层人物形象,还是钱钟书笔下的方逐翁、董斜川、爱默的公公与父亲等遗老形象,都拖着长长的传统文化暗影,他们或愚昧不堪,或顽固不化,或狡诈蛮横,或老实无用,或忍辱负重,或自欺欺人,在“看”与“被看”的人生舞台上既拒绝给予别人以幸福与安慰,又被人赏鉴着自己的悲欢与苦欣,小心地维护和修补着“老例”。对他们身上顽固不化的国民劣根性,鲁迅和钱钟书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从文化的视角去深挖导致精神劣根滋生的传统温床,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刻画他们愚昧麻木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风貌,或在喜剧式的嘲讽中戳穿他们虚伪、迂腐的真实面目,或在不动声色的冷静观照中昭示他们固守过时的人生信条而不自知反而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错位意识和时代幻觉,从而使人性批判在文化层面上达到旁人难以触及的深度和广度。
在展示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鲁迅和钱钟书所创设的文学场域却有着重大的差异。鲁迅在其小说中描绘一个老中国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仿佛与时间的流逝无关,几乎封闭式地保存着传统的生存状态,自给自足地繁衍生息。鲁迅以“挖祖坟”、“清旧帐”的彻底性集中批判了传统阴魂不散的乡土世界里国民的愚昧、麻木或狡诈的生命本相,他们好像摆脱不了历史轮回的宿命,在现实的时空中重复着历史的生存之梦,时光的流逝只不过为其增加好奇的谈资和消遣的话题,而随后消融在古老历史记忆的图像里。在这片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乡土世界里,传统意识对现代精神的警觉是自发的、不约而同的,吉光屯的阔亭们对想要灭灯的疯子是那样的恐惧与残忍,大哥与赵贵翁们对狂人的戒备连眼神都是相像的。这种吃人的真相只不过是传统老例的一种延伸,“四千文明古国古”的旧账上记载着如此类似的把戏,既有血淋淋的肉体残害,也有阴森冷酷的精神虐杀。鲁迅直指国人积习深重的心灵暗影,批判他们身上遗留已久的主奴根性、面子膨胀、精神胜利法等劣根习性,以求唤起沉睡的人们,摆脱传统暗夜的束缚,走上决绝的新生之路。钱钟书的小说主要展示现代背景下的传统城镇生活,他让生活在城镇里的遗老们在嬉笑怒骂中粉墨登场,不管是方鸿渐的父亲方逐翁,还是爱默的公公和父亲,还是“同光体”诗人董斜川,都在现代城镇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坚持传统宗法社会的人生信条,做着现代社会里落伍的遗民之梦。方逐翁迂腐守旧得像家中的那座祖传老钟一样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却抱守着古老迂腐的传统信条并时时炫耀它们的高明。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这些遗老们或以历史守旧的眼光衡量事物,或以传统的守旧心理定位自我,成为现代社会中别样的类群,与鲁迅老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与互补。在这种对照互补中,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反思显示出深广的文化通透感,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群体进行冷静观照,使得两人的批判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蕴含着鲜明的主体精神。
二、透视和质疑现代文明的种种假象
鲁迅和钱钟书是现代社会的启蒙者,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关注并不是盲目地只唱赞歌,而是以苛刻的眼光去发现新的压迫、新的不平等、新的精神奴役和创伤,从而揭示现代人物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危机。两人既批判传统思维定势对现代人性萌芽的扼杀与围攻,也指出现代精神枝条的稚嫩与脆弱。两人都不回避现实世界的矛盾和悖论,在冷静的审视中直面和揭示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不全面,处处存在人类自造或他设的陷阱,批判不自知的人类的浪漫主义、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天真和自恋癖,戳穿现代文明外衣下的种种人生和生活的假象。他们在小说中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在解构的同时也微微透露些许生命的亮色,暗示通向美好未来世界的诸种可能性,如《狂人日记》里的孩子、《药》里夏瑜坟上的花圈、《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里坦然走路的“我”,以及《围城》中的唐晓芙等都暗示了对令人窒息的现实人生的突围力量。这些事物或人物身上既有对难以驱除的历史阴影的清理,又有对新的生命征程的踏入与迈进,象征着现实世界中蕴含理想色彩的审美内容,它们可能会蒙上新的污垢,在新的起点中可能会遇上新的歧路,但毕竟预示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可能性。但也应该指出,两人由于过于关注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批判和人性剖析,认识到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漫长,感到重建理想未来的艰难,所以其小说主要进行的是对历史传统与现实人生的清理和反省,而没有致力于描绘未来世界的理想图景。
鲁迅所揭示和批判的现实世界多是过去时间的一种延伸,由于现实世界中不断袭来的精神暗箭和感受现实世界时层层淤积的心灵创伤,由于童年世界里的阴郁记忆下意识地不断涌现,由于发现现实与历史之间总是惊人的相似甚至仿佛完全叠加在一起,鲁迅常把现实作为历史悲剧的循环影像,现实并没有标示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仿佛陷入荒谬的轮回之中,所以鲁迅对现实同样不满并执著地予以批判。《药》表现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双向隔膜,《肥皂》、《高老夫子》讽刺了伪知识分子好色、猎奇的虚伪本性,《兄弟》揭示现代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阴暗、自私心理,《在酒楼上》、《孤独者》写出知识分子在追求个性解放道路上的软弱与偏激,《伤逝》写出现代爱情在遭受旧有纲常伦理的围攻和现代人格不能承受之轻的困境下而走向寂灭的真相。另外,鲁迅还深刻地揭示所谓的一些“新”的名目其实不过是旧的把戏的排演,骨子里散发出演过无数遍的旧戏的气味。《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们的革命只不过是在玩一种投机的把戏,而革命后的县城掌权者没变,只不过换了一下称谓而已;《离婚》中的爱姑看起来是一个摆脱封建淑女品性、追求女性独立的新人形象,但她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封建夫权所抛弃之后想依附而不可得的女性悲剧;《风波》中被剪去辫子的七斤不仅没感到进入民国时代的轻松与喜悦,反而因张勋复辟而在赵七爷的威吓下感到自己末日的降临。正如汪晖所指出的那样:“鲁迅抑制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作眼下的事情来体验,以至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确的界线,面前的人与事似乎不过是一段早该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过去而已。”
钱钟书对现实的解构和批判更为底,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把现实看作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从人类根性的基点上对现实世界中人们难以改变的精神缺陷进行揭示和批判。在《围城》中,他几乎解构了一切合目的性的结局和世俗的进步,方鸿渐既没有花好月圆、良辰美景般的婚恋结局,也没有出人头地报效祖国的事业成功,虽然他曾求学于中西文化,有着较为广博的人生视野,但仍身陷归国后的灰色生活之流而不能自拔,最终成为一个无根飘浮的现代人。小说中的其他“新儒林”人物也基本如此,他们常常浪漫地怀旧,这种虚幻的怀旧为他们的现在争回了一些面子,精神胜利似的填补了现实的虚空、无聊和不能逃脱的困境。汪处厚常向人们吹嘘自己战争中失落在南京房子里的无数古玩,陆子潇不断描述战前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的盛况,李梅亭也在脑海里建构了一所被日本人烧掉的上海闸北的洋房,连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乡老宅在意念里放大了好几倍而到处吹嘘自己家曾经如何富有……。现代人自欺欺人的劣根性成为他们身陷现实泥淖的重要原因,他们既不能正视现实,也不能认识自我,因此常常造成现实与自我的错位。《人·兽·鬼》暗示出现代人由于不自知而常常事与愿违的现象,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爱默在听到丈夫另有新欢的消息后马上露出了女人软弱可怜的本相,而作为丈夫的李建侯在婚外情满足之后的心境也像火车上看到的向后退的黄土那样干枯憔悴;渴望婚外情的曼倩在和丈夫的表弟天健切切实实发生了肉体关系之后,却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不管是钱钟书把现代人看作孤岛上的人、围城内外的进城者或出城者,还是比喻为鸟笼内外的鸟、想吃葡萄的猴子等等,都显示他对现代人生困境的独到发现。不管社会如何进步发展,现代人仍然会被新的问题和矛盾所困扰,人性的劣根也会像猴子尾巴一样总有露出来的时候,这种发现劣根性并使其形象地展示出来进行批判的意向寓指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具有普泛性的文化色彩。 不管是以民族现实为考察基点,还是着眼于人类根性的揭示,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都通过对个体形象的塑造深入到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层面,对现代文明进行冷峻的透视和质疑。两人都有着宽广的理论视野,但他们的小说并没有因此抽象化和教条化,而是在审美层面上包蕴着对生命个体的终极思考,他们的小说在现代生命哲学的高度扩充了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展现力度,加深了对人性世界的认识与揭示。
三、风格形成原因和启示探析
在2O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最关注的不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弱小民族的生存危机问题,是中华民族的自救、自新问题。作为一个现实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鲁迅思考问题的起点还是以对国民性的考察为基点,以救国、立国的愿望为缘起。他考察了近代以来器物救国、制度救国的发展历程,但避免了它们的狭隘性和急进功利性,注重精神启蒙和反思性的文化批判。因此,这种启蒙主义意图进入创作实践的建构过程之后,那种救国、立国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退居幕后,而关于人的本能欲望和生命力的现实思考和文化批判则被置于小说主题的前台,构成他审视社会和人生的文化视点。虽然他的小说画面和人物语言都带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这种深广的文化批判却暗合整个人类的灵魂世界,阿Q形象接受的世界性影响已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最初在民族传统的思考基点上展开的人性和文化批判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钱钟书是在民族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的年代进行小说创作的,但炮火连天、风起云涌的战争氛围并没有影响他的小说创作,他冷静地避开政治意味日益加重的时代主潮,在战争的缝隙里找到安放心灵的宁静书斋,进行中西文化的冷静观照和深刻剖析,揭露长期被忽视的人类“根性”,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这种文化观照的通透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的文化批判的延续,只不过鲁迅把批判与揭示的重点放到传统与历史上,而钱钟书的重点则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文化批判都抓住了人的最深层次的“根”,即精神和灵魂的更新与蜕变,这是人们摆脱奴隶时代向“第三样时代”迈进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只有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面貌和灵魂痼疾发生根本改变,真正的“人国”才会出现。所以说,他们在小说中所进行的文化祛魅(消除文化负面性的影响)和人性透视是深刻而必要的。
鲁迅和钱钟书小说中深刻的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代性的神话,显示了现代性自身的悖论性特征,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视角。两人在小说中肯定现代制度和现代精神,看到时代进步、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孕育了现代文明、现代精神。不管是夏瑜的革命行为,还是方鸿渐的求学西洋,都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思想影响、推动的结果。同时,他们又在小说中描绘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产生的新的陷阱及其对个体生命造成的新的束缚和压迫。吕纬甫、子君和魏连殳无法远行,成了“折翅鸟”,方鸿渐、曼倩、爱默也身陷难以逃脱的现代围城.成为失乐园里无家可归的游子。因此,两人的小说在讽刺和刻画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同时,也揭示进步理性观念和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新的异化、拜物化、工具化状态。这种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通透认识反映两人认识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它是在宏观把握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带着丰富的体验作出的清醒反省,这对丧失独立立场、膺服某种理论或梦想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参照。不管是革命化的历史叙事,还是欲望化的情欲叙事,还有粗鄙化的物质叙事,都试图取消人文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赖以存在的价值前提——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自觉的理性批判精神,献身或依附到某一思想或潮流中,无条件地服从于某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观念,不是用理性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不关注它们的历史过程性和有限性缺失,而是为之制造大量终极性的结论。鲁迅和钱钟书的文化批判显示着长久的生命力,它告别了现代文化的幼稚病,没有把批判指向绝望的虚无主义,而是在对世界的不满足中暗示生命前行的诸种可能性,在韧性的文化批判中暗含着人文主义的温情关怀,在感悟世界的大彻大悟中深味人间的悲凉与无奈,从向内与向外的双重视点来寻找深层的文化症结,从而确立彻底的文化批判姿态,这种永不满足的探寻和求索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有机性。鲁迅和钱钟书的文化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寻找或拯救自我心灵的参照,那是一种对自我和社会的深层文化意识的自觉把握与沉省,一种既不自大亦不自轻的清醒冷静的主体意识,一种虽悲观却不彻底绝望的人生观照情怀。
鲁迅和钱钟书被称为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他们的小说所进行的人性和文化批判,既与其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密不可分,也与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思想穿透力密切相关。他们都注重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连接与融合,不管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还是对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的刻画,都与他们宏阔的文化观照视野相关联,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具备厚积而薄发的创作优势,正是这种严肃的艺术创作态度与深厚的文化素养相结合,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品位。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文学,都应该具备发人深省的内涵、暗示真相的启悟和通向高远境界的审美导引力,这样的作品才会成为经典性的厚重之作,鲁迅和钱钟书小说中深广的人性和文化批判精神可为之提供丰富的借鉴和启示。
总之,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都在理性审视世界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进行深刻揭示,都从形象的层面上升到寓言或哲理的层面,形成对世界和人性的特殊体验和认识,完成从形而下向形而上层面的拓深和升华,这也是它们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深层原因。在整个2O世纪中国文学中,具有这种品格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多,有的还长期被排挤到文学主流话语的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深化鲁迅和钱钟书小说中的这种人性和文化批判精神,彰显和提升这种深邃的文学品格,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