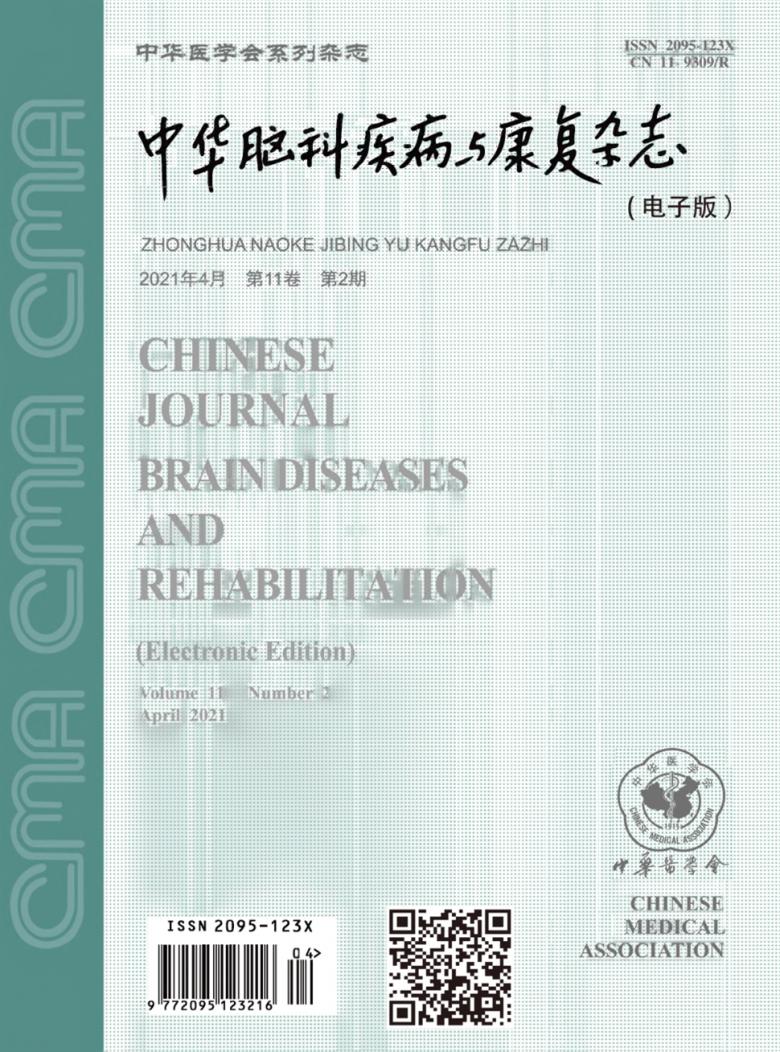浅议三重缘:诗与书法及华文文学(评论)
佚名 2011-11-29
时间是无法贮存的,但记忆的水纹能把蒙尘的岁月展开……
本来,应杨际岚先生和刘小新兄的催促,笔者构思了一个名为“建构或整合———刘登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启示”的标题,拟从诸多视角切入来谈谈刘登翰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生与文学、生命与学术的别样理解,尤其是作为一代学者为我们对当下的语境和姿态所留下的深刻启示和意义,来进行一番描述和阐释。
一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难忘的大学时光,因为爱诗写诗的缘故,笔者有幸结识了当时部分在当代诗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诗评家和学者,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写作者,自然是莫大的荣幸。就在那时笔者认识了时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着名诗人刘登翰先生,而我主持的当时在全国高校中颇具声势的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特别聘请他为首席顾问。之后我们常有往来,还时常携带着每期刚出版的诗报《南风》或诗歌习作,与其他诗友结伴登门拜访。他曾以文学讲座和具体指导等方式为诗社的顺利开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至今依然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里,刘登翰先生既是一位沉静而明智、文艺修养颇为深厚的长者,又是一位谦谦而恂恂的儒雅之士。他待人谦和诚恳,无论你的地位是高是低;他说话犹带鲜明的闽南乡音,判断问题力求公正客观,从不锋芒毕露,呈现出一种信达雅的气度。他首先应该是一位诗人、作家,然后才是一位学者、批评家。临出国留学前,笔者为配合参与主编的《名城诗报》所策划的“福建诗人散文诗人推介”专栏,曾撰写过一篇《我观福建诗坛》的诗歌评论,有一段描述这样写着:
令人惋惜的是,曾在学生时代就以诗歌而显露自己横溢才华的诗人孙绍振、刘登翰两位学者,由于近几年来皆致力文艺美学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无暇于诗的创作,可他们依然认定诗是人生的一部分,是青春的艺术。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勇于跟自己挑战,他们一旦认定要做的都干得很出色,甚至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孙先生的诗歌评论、文艺美学,刘先生的台港诗歌研究和评介等,视野宏阔深邃、标新立异,各领风骚,无疑地给贫乏而脆弱的诗歌理论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且颇具权威性。他们挥写并留下许多华彩的篇章,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和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推动了当代新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备受海内外瞩目!
旧事重提,旧话重述,此中真意,不言而喻。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使许多富有才华和良知的、跟孙、刘二先生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其曲折而坎坷的命运遭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战乱与艰难,青年时代的热血、激情和理想主义,中年时代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直至进入晚年之后,生命才呈现出一片秋高气爽的缤纷胜景。而今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和经营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一些前辈在生命追寻的历程里,保存着许多具有超前意识的、且又做到了忠实于心灵感受、忠实于文学本质的具有恒久价值和意义的篇章。沿着刘先生个人的心灵地图所指示的方向,我们或许多少能挖掘出其中潜在的精神价值和意义。
旁白之一:刘登翰最早痴迷于诗歌。他自我如是说:“诗曾经是我生命的一大部分。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工作性质的改变,它渐渐变得轻淡和间接。但诗确实曾占有我很长一段人生,像一种魔,至死无法解脱。”(《瞬间》后记)这份特殊的情结,使他欲罢不能。于是,他语词中的瞬间世界,乃是由灵活的、易变的、在瞬间生成的词语所构成。它们是山海、土地、季节、梅雨、岁月、月色、故乡、妈祖、闽江、阳台、木棉等等意象生发的“纯粹或不纯粹”的歌,以及那些梦幻般的日常事物和气息,在“瞬间”体验的余温里呈示出各自孵化的含义、结晶和形式,又仿佛是词语通向经验之源的一种溶解。“所有丢失的春天/都在这一瞬间归来/所有花都盛开,果实熟落/所有大地都海潮澎湃//生命曾是一盆温吞的炭火/突然喷发神异的光彩/每个日子都因这一瞬间充满意义/所有痛苦等待都不再难挨//像云,携一个梦,款款走近/像星,凝两颗泪,灿灿绽开/生命在这一瞬间进入永恒/世界因这一瞬间真实存在”(《瞬间》)。
对于人们而言,瞬间似乎什么也不是。日常生活世界,总是表现为瞬间的枯竭,这与人的内心生活贫乏且枯竭有关。就生活、劳动、事件的长度来说,瞬间是难以构成什么可言说的内涵。与之相反,刘登翰诗歌却揭示了瞬间丰富的蕴藏。在他的笔下,“瞬息”的故土是在一种特殊回味气息中呈现的,“崚嶒起伏在一片苍茫里/以飞鸟的卧姿/一副瘦嶙嶙的肩胛/撑高远蓝的天/这个叫做诗山的/故乡呐//海在很远的地方/蓝给母亲看/在母亲/飞出去就回不来的眼睛里/泪给儿子看/欲归的心无处停泊/才把故乡唤做/码头//只有垂下眼睑的母亲才这样回答/你出产什么//游子”。在不足20行的、长短错落、灵活变化的句式中,质朴的话语充满诗意的张力空间。诗人面对时间的现在与过去之间、空间的起伏(山)与遥远(海)之间无法逾越的苍茫的里程,让优美的动感画面在节奏自然流转中油然而生旋律的感染,让引发的想象与回忆闪现出冷隽抒情的辉光。“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和怀想,惟有从母亲垂下的眼睑获得了答案。诗人以敏感而通明的内心唤醒瞬间的感受,在瞬息颖悟中构成为诗歌走向心灵世界的一个丰润的感动。诚如诗人的自我表白:“人生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但凝定在历史里的瞬间也将永存。……面对逝去的瞬间,珍惜是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时代过渡的这一代人感情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则也相信,昨日是校正今天和明天的历史坐标。”(出处同上)笔者以为,这种通向无限的瞬间之“秘道”,如同一个可以辨认的标志,也可视为一个趋于成熟的诗人的气味或风格。
海德格尔说过,诗的建立是“在奉献与赞美的意义上设立。”而诗作为歌唱的仪式,在历史上就是一座由神秘的符号构筑的语言的神殿。为何需要一种奉献与赞美意义上的设立?诗所设立的应是什么?作为言语之“寺”的建立,诗其实就是敞开了一个世界,并使我们看到的都充满祝福。而赞美即是通过为万物赋名,语言将存在者引入世界,以奉献给它们的存在。“东方地平线上/凉飕飕的早春黎明/一个农民,一个/佝偻的身影/什么也不曾顾虑/就把种子,默默地/播进大地,播进/历史的进程里,一个/民族的坚韧”(《三月》),这首写于1980年的诗作,在今日读来依然意味隽永,盖其源在于诗人透过特定的历史语境表达了对于大地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存在于歌唱中的那个时代的灵魂,依旧凭着万物而存在。对于诗人而言,这种歌声既是一种感情的呼唤,又是一种心灵的声音,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回应。然而,在蒙尘的历史中,文化同样残缺不全,人很容易患上营养不良症或文化偏至症。诗人对此具有自我的清醒意识。继而,他曾在一段时间里调整“转型”,写散文写报告文学。通过散文,他修补了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的“裂痕”走向和谐,去“寻找生命的庄严”;通过报告文学,他寻找某种时代精神和社会信息的“输出”通道,去感受人生哲理与历史意蕴的生成。
或许因为自身在感知生活、传达情感等创作实践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考和经验,刘登翰把笔触逐渐伸向了对于诗歌的理论批评,而且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分析,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因素。早在1958年,即在北大中文系深造时,由于深受着名诗人、当时主持《诗刊》工作的徐迟先生的倡仪和鼓动,他便与如今在中国文坛诗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着名学者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等前后届学友一道,接受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尽管“难产”了。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初,面对新诗潮汹涌而至,他主动参与其中,热情地把舒婷等一批新锐青年诗人推上诗坛。之后,面对海峡对岸蓬勃生长的台湾现代诗率先予以大力推介、展开评论。无论是以新诗思潮和诗人个案研究相结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与洪子诚合着),还是另一部与人合作的(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都有其鲜明风格和研究特色。一部当代新诗史,作为具有拓荒式和建设性的着述,的确令人刮目。这是对20世纪50—90年代中国新诗状况的精心梳理和评述,既有就新诗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推动与制约下整体衍变轨迹的勾勒,又有对不同时期新诗在表现对象、表达方式、创作方法等艺术领域上的特征和嬗变的描述;既有对诗歌潮流、生成秩序及构成条件和方式的观察与思考,又有对具体诗人的写作和重要诗歌流派和群体的研究。尤为难得的创见是把台港澳与中国大陆即两岸三地的新诗采取带有“整合”视野的尝试处理和互动链接,尽管这是写作当代中国新诗史的一大“难度”,却明显地呈现了着作者的智慧、勇气和创新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在新诗的生长史、发展史、写作史和活动史乃至诗人心灵史的背后,是对一代学人精神历程的深度揭示,是对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下的真、善、美的重新发现与修复,是对被时间的尘埃所遮蔽的、任生活风雨侵袭的本真诗性的呼唤、寻求和擦拭,也是对一个渐渐远去的时代背景和诗歌真相的描画和再现。诚如哲人爱默生所言:“破译每个时代的谜语,总会发现它自己的谜底。” 二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在许多人的感觉里,可能如印象中的故乡一样,走在路上已渐行渐远,甚至觉得早已成为“已故”的梦乡,尤其是在电脑化时代,更多的从事写作的人甚至已脱离手中之笔。但我庆幸并且欣慰,即便以毛笔为工具的书写在日常和实用领域几乎已濒临绝迹的当下,书法的文化传统依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日趋多元的当代社会,书法显然已失去了固有的尊荣而走向边缘,只能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依愚浅见,这恰恰正是书法作为纯粹艺术的时代真正揭开序幕……
旁白之二:走向书法,走向作为艺术的书法,只有智者,才能把犀利的目光投向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发掘与探索中,才会以鲜活灵动的意象凝定于铺开的宣纸,才会以抽象的艺术线条铸造美的造型,然后把那些属于古朴的灵魂和时代的精神气象,氤氲流淌在历史文化的河道中……
书法犹如人在跳舞。文字,属于人的语言符号;书法,属于人的情感符号。如果说诗歌是生命的旋律,那么书法则是心灵的舞蹈。是故,诗与书,素来都是中国传统文人修心养性的最佳选择。因为,诗歌使人联想飘逸,直指艺术之内核;书法则让人情感清雅,追求平和与高尚。甚而可以说,书法艺术之于人生,无论是益智、健体、审美、养心和博学等都有着无法言喻的妙处。
纵观刘登翰的书法,文意清淳,流利多情;秀丽风雅如南方山水,飘逸自如中尤见法度。在当代诗人、作家和学者群体中,其书法庶几趋近于上乘,如此笔情墨趣,也是其书法一直让不少人心向往之的缘由。在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部分诗人、作家和学者拥有书法艺术的天赋,又以文学底蕴的支撑使书法变得更为丰富和立体。这种从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文化声音,是复合性的才艺体现,多重性的精神交响。刘登翰深谙其中三味。从他切入书法艺术的领地加以观照,他似乎注定要走文人化之路,追求一种精致圆融又不乏神采性灵之气,玲珑清隽而不乏清刚爽健之格的风韵。我像读诗一样读他的字,从一撇一捺、一波一磔中去感受书者的心境。其书的苍与稚、立与依、逸与沉、润与枯,皆尽可让人心领意会。这种从心中涌流而出的线痕墨色,显露其真性情,似是能听能品,其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息也随之在书作中洋溢,这是一种人书合一的人文对应结构。由是可见,那种鼓翼振动式的逸致驱使他拨动了艺术的触须,那种“空梁落燕泥”式的清雅则使他获得了人生的天籁,既潇洒大方,又自然秀雅。
人之性情常常是先天之铸就,又凭后天之积累。一个艺术家总是要从自身出发,并在不断探求和历练中加以修行。然而,文(诗)心绝非一日可以养成,需要一种沉潜和坚守。刘先生深悟到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一种传统文化的维护。失去了它的传统和源流,即失去了这门艺术。在这种意念的统摄下,他追踪先贤书家的墨迹神韵。二王、苏轼、鲜于枢、文征明诸大家及唐宋元明时代为我们留下的帖学经典固然是他心仪和竭力追摹的,但他只在于性相投契,即一切服从于他心目中与自己追寻的美学范式相关的逻辑。于是,他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作为一个非专业书家,他不仅逐渐形成了独具的书艺风貌,而且做到了丰盈而不杂驳,腾挪而不失序,仿佛是理性的歌声弥漫于他敞开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门艺术,书法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蕴,总是深藏于创作者的心中,而非刻意追求罗列的表层之物。
三
诚如书法也好、诗歌也罢,都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达,人生也有太多的东西必须加以面对,你别无选择。
旁白之三: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里,刘登翰可谓开国内学术界之先河,而且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一路探索一路垦荒一路收获。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扩大华文文学在海内外学术界乃至世界性的影响,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构成,对于人们关注、走近和理解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进程中的价值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一种突破性的贡献和开拓性的意义。
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与张扬,也由于华文文学本身蕴含着丰富内容、文化信息和心灵密码,华文文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已然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有益于中华文化重构的重要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推进堪称迅猛异常。然而,伴随华文文学研究空间的渐次推展和深拓,置身于其中的研究者和学术界,却遭遇了一个学科命名、定位、归属以及学科理论构建等诸多问题的尴尬局势。面对开放的华文文学,如何让其自身在生长壮大中获得合理的依据和定位呢?对此,刘登翰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自审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窒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面对华文文学世界这个巨大而庞杂的空间,随时都有可能需要一个研究者在学术意识与理论建构思路上进行适时调整,方能更好地把握和确定华文文学的存在价值并就关键性问题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因而,保持开放而前瞻的意识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在刘登翰看来,无论华侨、华人和华裔的文学,其主要文字媒介是华文,一般情况下称之为华文文学。但华文文学并不能涵括华人和华裔作家用其它语种创作的文学,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华裔的英语文学受到包括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广泛关注。其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沟通和改造,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历史之间文化融汇的重要现象和亟待深入探讨的新鲜命题,而且随着华人对所在国社会的参与和融入程度日益加深,华人的异语种书写已渐成一种普遍现象。对此,他表示赞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超越语种的局限而立足于族性和文化之上的学术主张。同样的,他又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气势,从目前全球化语境影响学科体系的一些新变动来拓展华文文学诗学体系的学术思考空间。近年来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既有宏观的透视,又有微观的剖析,学术视野开阔,内容有的放矢,锐气不减当年,堪称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一文,则从华文文学形态的某种特殊性出发,针对有的学者以“一体化”和“多中心”来建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和思路提出大胆的质疑,这不仅是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深入而透彻的思考,也是对处于流动性状态的、跨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态势的清醒认识和极大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华文文学诗学体系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应该说,刘登翰的学术个性,在于他能把宏阔敏捷的文化视野和缜思求实的研究品格加以结合,从而开辟了自己的研究疆域。从他早期率先提出一个必须面对的文学现实,即文学的“分流与整合”的理论阐释所揭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必将从分流走向整合的必然趋势,到他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去考察和研究台湾文学,并在《台湾文学史》一书里得到的集中体现;从他对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的多元构成和大视角的全方位描述和观照,乃至于对东南亚华文文学、海外新移民文学、尤其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思考和研究,以及对诸多重要现象与问题的审察和清理,等等,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其声音,可以看到他富有创建性的论述,不仅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同样的为当代华文文学世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富有价值作用的理论导引、实践范式和诗学体系建构模式。
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是人们在谈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时经常提起的话题。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从许多文学家的身上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恕勿赘言。有人这样描述过,作为学者,刘登翰起步于多元的文学创作;作为作家,他又在文学研究的领地找到归宿,从而展示了一代文人的特殊风采。我想,读者诸君只要走近刘登翰,走向他为生活、时代和文学所思考而凝聚及留下的文字结晶与构筑的精神大厦,自然会有“所见略同”之感,并且,可能获得更多的感染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