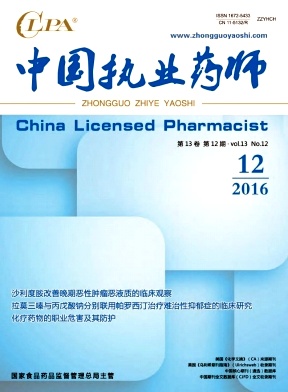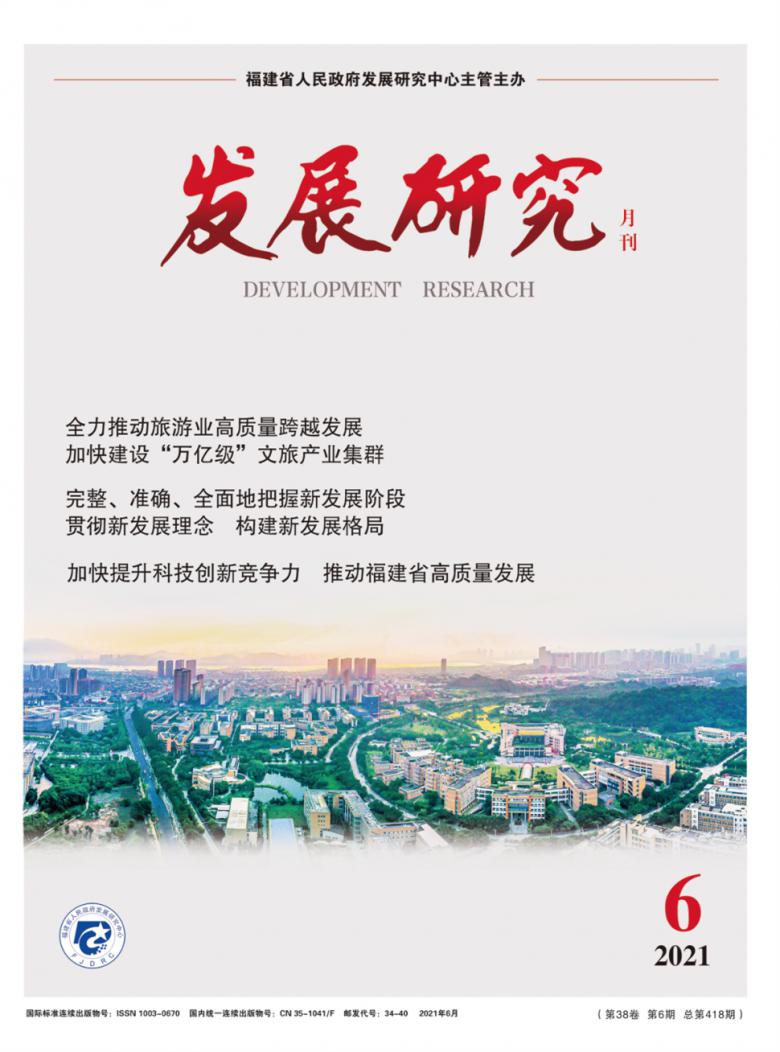关于从“天葬”所感悟到的中国画艺术心态
高民利 2012-01-12
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对于我来说,它是我心中永远的圣地,它给予了我多少生命的启迪和感悟,给予了我丰富的灵感和美的享受,那里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的圣洁和神秘,那里的沟沟壑壑是那么的博大和深邃,我庆幸自己作为一名画家,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里给予我的一切启示和震撼。
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我就被她那种辽阔和深远的地域风情所深深吸引,这是和大都市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一名画家,而是一个异乡人怀着虔诚的心灵终于寻找到自己梦想中的第二故乡。我是来朝圣的,在大昭寺,看万盏酥油灯长明,记录着朝圣者永不止息的足迹,也记录了岁月的永恒。在巴松措,看着绿色的湖水纯净如玉,心中的烦恼不由荡涤一清。在藏南,我试图和藏民打成一片,为的是把我的心变得更加纯净。来到天葬台,我有幸参加了西藏人的天葬。在这里,我分明感悟到生死轮回过程中,万物与宇宙一体、共融共化的感觉,感到生命是神的恩赐,没有神祗的恩赐,生命不会往生。没有奉献精神,生命更不会永生。因为佛陀转生,以肉身饲鹰。
我看到天葬师把死体背到空旷的高台上,远处是死者的亲朋好友,他们在虔诚的看着天葬师在高台上模糊的身影,在为一个亡灵超度,他们虔诚的祈祷,那种感觉真是肃穆、庄严,竟然感觉不到一点恐怖和恶心。我想,这也许就是生命的轮回。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
我翻阅资料,看到在中国古书中就有关于天葬的记载。例如,“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出自《周易•系辞传》),“盖上也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蚊嘬之。”(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在现代社会的一些地区的人群中天葬仪式依然存在。例如在西藏,天葬师把尸体背朝着天,折断四肢,在尸体中央和两肩用力撕开皮肤露出肌肉,然后退开,苍鹰铺天盖地而下竞争啄食。天葬台上剩下骷髅时天葬师用石头将骷髅敲成骨酱揉成一团,秃鹫再次铺天盖地而下,食尽散去,周围的人开始长跪顶礼。又如生活在非洲东部地区的马塞族人,他们死后将死者的全身用水洗干净之后,细细地涂上一层奶油,放在屋内中央位置,亲属们默跪在遗体四周做一天的祈祷,随后村中长老引路,众人抬着遗体来到荒郊野外,将遗体放在那里,任野兽吞食,飞鸟叼啄,借此表示马赛人死也不同土地结缘。
关于天葬,藏传佛教认为,点燃桑烟是铺上五彩路,恭请空行母到天葬台,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逝者在世时的罪孽,请诸神把其灵魂带到天界。天葬台上桑烟引来的鹰鹫,除吃人尸体外,不伤害任何动物,藏人称之为“神鸟”。据说,如此葬法是效仿佛祖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行为,所以西藏至今仍流行天葬。
对于天葬,我们汉人恐怕无法接受,汉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其实无论是天葬还是入土为安,对于生命来说都是一种形式,汉人讲究的是投胎转世,藏人讲究的是生死轮回,在西藏人眼里,天葬是圣洁、高贵的。他们是一种生死的轮回,是从感知界通向往生界的一种途径。在天葬的过程中,听着法号长长的余音在空谷中回荡,我对于生命的感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体验。仿佛这种声音把我们和未来连接起来。
这样那幅《天葬》也应运而生了,我只希望我自己能用手中的画笔把这种感受深切地记录下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庄严。
带着这种感觉,我发现,西藏的神奇与博大,并不在于他的宽广、厚重、离天很近,而在于她内里蕴含的虔诚之心和自然淳朴的态度。在西藏,自然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正正常常,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即使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的,它是一种轮回,一种通过轮回而使灵魂涅槃的圣地。在这种地方,感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心去体味那里的一切,用心去在寺庙千年的香火中,感受那独特的充满人文的美感。
西藏带给我的感受,也让我在创作中,充满了艺术的灵感,我明白,这种灵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对心灵的体悟和对西藏风情的理解,来打通一个境界与一个境界的联通。就像天葬,人本是自然中人,那最终是要回归自然的。人的生态,就如佛祖以肉身饲鹰,让自己的躯体有所价值。人的价值,在生前创造了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在死后,也应该回归自然,回报自然。这也许是天葬给予我的最大启示。
在创作中,我发现感觉最重要,没有感受,就没有激情。没有感受便没有好的创作。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既要有感受,也要有生活。我喜欢以泼墨大写意表现藏民的形象,表现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象。
事实上,我想从艺术的本质——创造这一体认的角度,进行我的认知,从而在认知层面,以独特的感觉,在西藏人物画的创作上,进行新的构成。毕竟,要写意出富有时代精神的画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要表现一个对于我来说还很陌生的民族之魂更是不容易,我只能更加用心地深入这片土地,用心体会。
我选择西藏风情并在反复皴擦渲染的同时依旧坚持以“线”造型,强调人物的线性节奏与韵律。同时,线条的质量和笔墨的皴染也非常重要。在同一画面中,既要注重线条的质量,又要设计笔墨的成分。务必使线条流畅自然而又毫不浮滑,凝练概括而又不乏笔墨的丰富变化,再加之淡淡的背景渲染,将藏族人物天性飒爽却又略带羞涩之气的精神情状非常委婉地表现了出来。使整个画面给人以强烈的浪漫主义抒情韵味。
其次,就表现技法来看,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西藏的民族服饰明显带有比较“厚重”质感,但艺术家要表现这种“厚重”,就非得借助于光影,通过画体积块面才能实现。有些画家的西藏人物画的的确很厚实,明暗关系也很突出,但那与中国画之间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在我看来,画家表现西藏人物,就造型上来讲,应该关注的是其身上依然存在的线性之美,而不是他“厚重”的质感及“浓艳”的色彩。再者,这种厚重感同样可以通过“厚重”的笔力来传达。但在我的画中,我非常注重写的语言,在写的恣肆随意中,调动我的感受,以笔墨的行笔线路,来在画面的构成上,寻找新的突破。我想用笔铿锵有力,沉着稳健,或是大笔横扫,势如破竹,最能体现我的个性。所以我的情感表达,是快意的,是坚韧不屈的。我知道在我的感觉中,对佛那种无休止的虔诚精神,虽然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于事无补,但是对于藏民族与恶劣自然的条件抗争的心境,我是非常的震撼。
在多年的西藏生活中,我觉得艺术创作,既要甘于寂寞,又要胸怀开阔,在西藏广漠阗寂的生活中,远离尘嚣,埋头钻研,不断的汲取营养,慢慢体会创作灵感与激情。因此,我在不断的追求个性中,不急于定格,而是清醒的认识到一个成功的画家,其作品必须体现个性,更要有自己的风格。但是这个风格是在艰苦的摸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近几年来,我经过反复尝试,找到了一种以笔墨为主调,在皴擦过程中,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西藏人物的形象上进行深刻写意,因此,我以气运笔,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使中国画更具神韵和气魄。这是我在西藏人物画创作领域的一点点心得和体会,我相信通过不断的艺术探索,我的人物画创作将会再攀新的高峰。
面对他们不屈不挠地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英雄一般的坚韧精神——也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焕发出了这种苦涩的美感——现实的苦涩与沧桑令人们充满同情与怜悯,而生命的坚毅与神奇更令我们钦佩不已!
因此,在我的艺术理念中:“情感大于任何形式,没有情感的形式像失去生命的贝壳”,我坚信独特的情感会产生独特的艺术形式,拒绝惯性思维与无聊的笔墨游戏。同时,关怀苦涩的生命、赞美圣洁的灵魂、讴歌这一伟大的民族又是我艺术作品永远的精神追求。我相信,真实地再现藏人的生活场景不如凝练地表现他们的精神状态更有价值。这也是我从天葬台上得到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