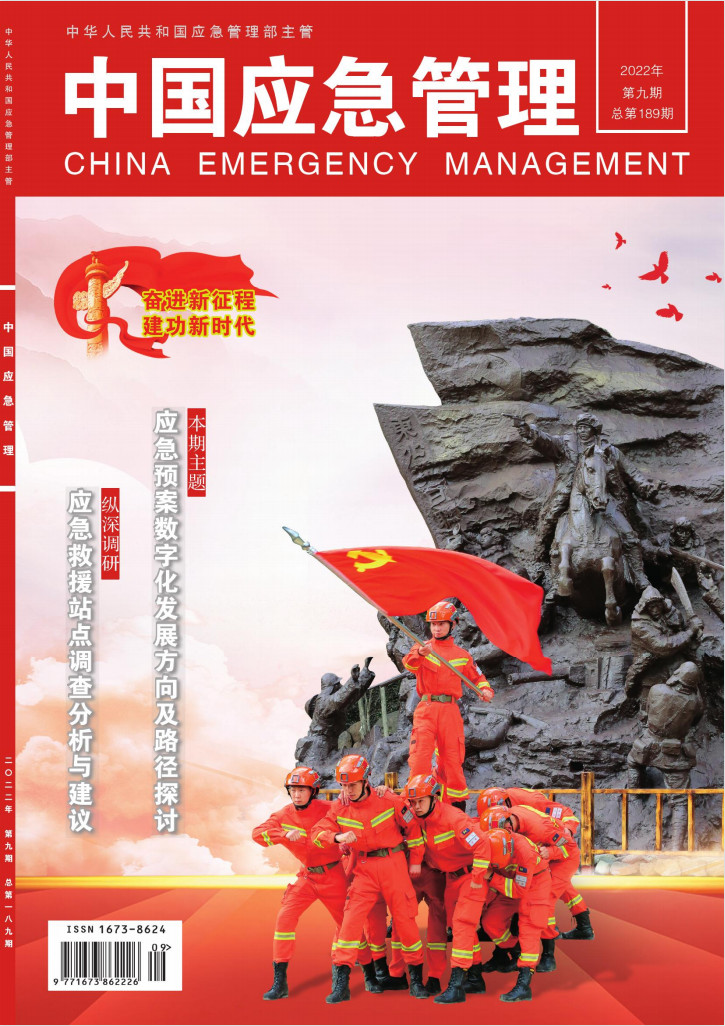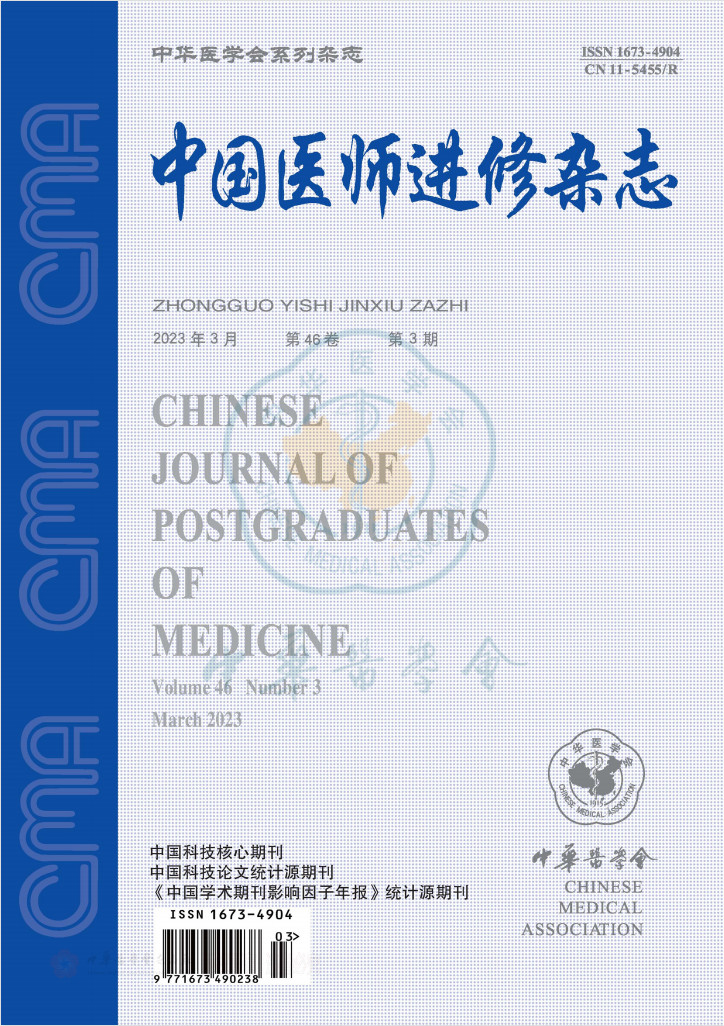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的分茶研究
关剑平 2006-04-29
一.研究背景
分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烹点茶的方法,但是随着末茶的消亡,今人之于分茶,知其名者已经是凤毛麟角,更谈不上具体内容。而且由于现代中国的饮茶高度物质化,与生活态度基本无关,以及史学研究侧重于政治、经济等传统学科等内外原因,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茶文化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反,在日本,由于茶道的刺激与启发,茶文化研究尽管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但是作为史学家的“副业”,尤其是为了满足茶道爱好者提高修养的需要,仍有一定数量的论著问世。因为日本茶道对于中国茶文化有着传承关系,为溯本求源,日本的茶文化研究不时涉及中国,汉学研究京都学派领袖之一的青木正儿先生曾致力于中国茶文化研究,并在1962年出版了《中华茶书》,其中就提出分茶的原意是在大型容器里点茶之后再分盛到小碗里饮用,宋徽宗《大观茶论》所介绍的就是分茶。[i]然而至今已超过40年,除了其子中村乔先生在二十多年后重新注释《大观茶论》时指出分茶法始见于陆羽《茶经》之外,[ii]没有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宣化辽墓中有五幅清晰、精美的饮茶壁画,本文拟从研究张世卿墓后室西壁和张世古墓后室西南壁上的两幅壁画出发,印证以文献史料,比照以出土文物,探讨分茶的烹点方法,在解明分茶这一古代生活技术的同时,也为现代末茶的复兴提供技术依据和历史经验。
二.分茶的沿革和基本程式
“分茶”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岸说“晋臣爱客,才有分茶”,[iii]在他看来分茶从晋代开始。晋代的史料如何呢?杜育在《猶赋》里说“酌之以匏”,[iv]即使用瓢斟酌茶汤;在《神异记》中,丹丘子向虞洪祈讨茶时使用了“瓯牺之余”的说法,“牺,木杓也。”[v]在中国茶史上,匏、牺之类的杓子是分茶的专用工具,这意味着晋代确实存在分茶。汉魏画像砖所描绘的宴饮场面,在比较显目的位置上画一个甚至多个大型容器,容器里还放着一把杓子,分茶的斟酌方式就源于这种斟酒方法,就是在宣化辽墓壁画里也有同样的画面。杜育说“式取公刘”,[vi]不仅表明他以酒器为基准选择茶器,还是对晋代饮茶以饮酒为基本模式加以模仿的状况的真实写照,这是中国饮茶在形成的时期就具备了完整的形式与充实的内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说都是分茶,各个时代还是有相当的差别,烹茶法与点茶法的使用就是唐宋分茶的主要区别之一。
《茶经》所介绍的分茶是烹茶法,一面加热,一面制作茶汤。“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左卤,右臽)(*左卤,右监)而钟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策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左饣,右孛)均。”[vii]即当水初沸时,先加盐调味;二沸时取出一瓢水,一边用筷子激烈搅拌开水中心,一边用则舀取适量末茶放入釜的中心。等到开水剧烈沸腾,再到入事先取出的那瓢水,阻止开水沸腾,养育茶汤的泡沫。最后把茶汤分盛小碗,尤其要注意泡沫的均匀,然后供饮。
《大观茶论》所介绍的分茶是点茶法,把已经烧开的水倒入盏盂里加工茶汤。赵佶根据加开水的次数,把整个点茶过程分成七个部分(七汤)。
头汤“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愈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一次加入的水量要视茶末的数量而定,目的是把茶末调成胶糊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能直接冲入茶末之上。使用茶筅搅拌时也有严格的技术要求,由此奠定点茶的基础。
“第二汤自茶而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第二次注入开水要求来回成一直线,块注快停。
“第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第三次注入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至此为止茶汤的颜色大半已成定局。
“四汤尚啬,筅欲转梢宽而勿速,其真精华采既已焕然,轻云渐生。”第四次注入开水的量要少,茶筅的搅拌频率也要低一些。
“五汤乃可稍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然后结霭凝雪,香气尽矣。”第五次注入开水时要视至此为止茶汤的状况而决定击拂方法。
“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然则以筅著居,缓绕拂动而已。”第六次注入开水时如果泡沫已经勃然而生,只要缓慢搅拌即可。
“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第七次注入开水主要看茶汤的厚薄程度,如果达到要求,点茶就完成了。
点完之后的茶汤分盛入小碗供饮,除了要求各碗的茶汤分舀均等,还要注意浮在茶汤表面的泡沫也要均匀,即“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viii]
三.分茶茶器
分茶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还更加形象地反映在绘画作品里,张世卿葬于1116年,张世古葬于1117年,他们的墓里各有一幅点茶图,描绘的内容就是点茶法的分茶,下面就以这两幅壁画为中心,探讨茶器的形制以及作用。
1. 茶碗
两幅壁画里都绘有斗笠形的茶碗,[ix]至今为止出土了很多唐宋时代的斗笠形茶碗,最广为人知的是法门寺的玻璃茶碗。曹昭解释其合理性道:“古人吃茶汤具用(*上敝,下瓦),取其易干不留津。”[x]不仅这两幅点茶壁画上的茶碗,所有壁画上的碗全都是白色,所以因为绘画色彩的局限,这些瓷碗除了白瓷,青瓷等淡色瓷器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事实上也从辽墓出土了大量青白瓷碗。
早在晋代杜育就宣称“器泽陶简,出自东隅”,[xi]虽没有明言是以今浙江绍兴、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还是温州一带的瓯窑,但是当时浙江不仅是东方,甚至是全国的代表性陶瓷产地,尤以青瓷著称,因此杜育选择浙江的青瓷碗饮茶。到了唐代,继承杜育选择茶器基准的陆羽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崇越窑青瓷: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州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百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xii]
陆羽针对社会上推崇白磁茶碗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越窑青瓷优于邢窑白瓷。这至少可以说明青瓷、白瓷是唐人优先选择的茶碗。晋唐以来的这一选择基准也同样影响着宋代,余襄公“越瓯新试雪交加”说的是越窑茶瓯中的白泡沫,[xiii]苏东坡“酡颜玉盌捧纤纤”说的是用青白茶碗饮小龙团茶,[xiv]范仲淹“碧玉瓯中翠涛起”[xv]说的是斗茶的青瓷绿茶汤,梅尧臣“纹柘冰瓯作精具”[xvi]说的是以白瓷为茶器,林景熙“冰瓯雪碗建溪茶”[xvii]以冰雪形容白瓷茶碗并用于饮建茶。
以上这些史料说明各种茶、各种饮用法都广泛使用青白等淡色茶碗,但是仍给后人留下宋人对兔毫盏等黑色系统的茶碗情有独钟的深刻印象。宋初陶谷在《清异录》里就说:“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xviii]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杯微厚,火脅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xix]欧阳修在《和梅公仪尝茶》诗里写道:“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xx]《茶具图赞》也选择了它。由此可见有宋一代多么推重黑盏,尤其是建安建阳窑烧制的兔毫盏。
宋代茶书所记载的对象都是建茶,所推重的茶碗也是建窑的兔毫盏,除了反映审美观之外,还有像蔡襄等所强调的建茶配建盏的意蕴。然而不仅蔡襄、赵佶之流,就是陆羽也没能为茶界制造出一个“标准”,再加上蔡襄也只是说在斗茶时不使用这些青白色的茶碗而已,所以茶碗的实际使用状况是尽管黑盏得到茶书作者的竭力推荐,各色茶碗仍然使用于包括建茶乃至斗茶在内的各种茶的饮用中,廖保秀所谓“斗试家皆只用黑釉茶盏”[xxi]言之过分。
2. 茶托
两幅壁画上的茶托分别是黑色和红色,当是漆器,《茶具图赞》所收录的茶托名为“漆雕秘阁”,强调使用的是漆雕工艺,实物见于大英博物馆。人们对于盏托的起源非常感兴趣,早在唐代就有相关记载:
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宁之女以茶盅无衬,病其烫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盅倾,乃以腊环楪子之央,其盅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致百状焉。〔原注:贞元(785-804年)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xxii]
李匡乂为澄清茶托并非起源于贞元初的青郓地区而讲述了崔宁之女的故事,其实盏托由托盘演化而来,汉代已经普遍使用。在晋代,当饮茶习俗日趋普及时,盏托被吸收进了茶器,在湖南长沙沙子塘东晋墓里就出土了青瓷茶托。这条史料提供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是,在唐代已经使用各种素材制造各种造型的茶托。宋代茶托的丰富多彩,更有文物作无言的证明。金属茶托如四川德阳孝泉镇窖藏出土的银质茶托,河南洛阳安乐出土的铜质茶托。各大名窑也烧制瓷器茶托,在江苏镇江发现了章岷墓(前文曾引用过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其中出土了景德镇湖田窑的影青茶盏和茶托。此外,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北宋定窑的牙白茶托,等等。周密在《齐东野语》里说:“凡居丧者,举茶不用讬,虽曰俗礼,然莫晓其义。或谓昔人讬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据”。[xxiii]可见盏、托配套使用是饮茶的一般规范,至少在一段时期里,红色漆器茶托的使用非常普遍,而各色漆器茶托的考古发现同样是不一而足,如江苏宜兴和桥宋墓出土的褐漆茶托,在湖北武汉十里铺北宋墓出土的花瓣盘口漆茶托等。
3. 都蓝
其他点茶的绘画作品往往还画有许多茶器散放在桌上,而这两幅壁画的画面异常简洁,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桌上分别有一个红色方箱和黑色圆盒,质地应该也是漆器。
在据称是元代钱舜举所作的《品茶图》里,右侧中间一人手里捧着与张世卿墓壁画大小、色泽、图案相仿的漆器圆盒,里面排放着各色器皿。由此类推壁画里的箱盒是茶器盒,所有的茶器都放在了这两个箱盒里。同样性质的茶器在《茶具图赞》里被戏称为“苇鸿胪”,顾名思义是用苇编制的。不过在一般场合多沿用陆羽所起名称——“都蓝”,梅尧臣在《尝茶和公仪》诗中写道:“都蓝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xxiv]晏殊的《煮茶》诗也说:“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筠笼(一作都蓝)煮惠泉。”[xxv]都是说提着都蓝烹点茶。
都蓝的形制在《茶经》中有明确记载:
都蓝以悉设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双阔者经之,以单纤者缚之,递压双经作方眼,使玲珑。高一尺五寸,底阔一尺,高二寸,长二尺四寸,阔二尺。[xxvi]
与壁画上的都蓝相比,《茶经》的都蓝要大得多。都蓝的尺寸因所容茶器数量、种类而异,所以难以一律。即便是陆羽也需要不同尺寸的都蓝,因为以上的都蓝是针对《茶经·四之器》所提到的茶器而设定的,而陆羽同时为外游饮茶准备了简式茶器组合,收纳这些茶器时就不能使用上述的大型都蓝了。不同饮茶方法造成茶器的差异,再加上审美情趣因人而异,从而造成了都蓝在形制上的区别。
4. 茶盂
在两幅壁画的桌子上还放着两个比较大型的白瓷茶盂,这是一个关系到茶的烹点方法的关键性茶器,而至今为止的研究都对它避而不谈,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于分茶没有基本的认识。在唐代,因为直接在釜里烹茶,所以《茶经》里没有这种茶器的记载。宋代用执壶煮水,在这种茶盂里点茶,所以说这是一种主要使用于宋代的茶器。
研究这种分茶时使用的茶盂的困难首先来自它似没有专用名称,与饮茶用的茶碗一样,也被称作盏,因为宋代也使用茶碗直接点茶,所以茶碗与茶盂不仅有同样的名称,甚至有重叠的功能,没有相当完整、具体的记载,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而饮茶史料恰好就往往是只言片语。《大观茶论》所记载的盏是点茶用的茶盂: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xxvii]
宋代也直接使用茶碗点茶,为什么说《大观茶论》在这里所说的盏是分茶时点茶用的器皿呢?除了书中记载了分茶方法以外,直接的根据是赵佶强调大小不同规格的茶盏的选择要视点茶的多少而定。如果仅仅点一人饮用的一碗茶,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这个茶盏直接用来点茶,并且与茶碗一样,也以建窑兔毫盏为首选。与茶碗不同的是造型,前面已经提到唐宋普遍使用斗笠形的茶碗,而这里的茶盏比较深,考虑到运用茶筅需要一定的空间,底部比较宽大,即便内收,也不会达到斗笠形茶碗的程度,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茶碗。与宋代斗笠形的茶碗相比,日本茶碗不仅规格比较大,而且碗壁垂直高耸。茶筅是日本茶道唯一的搅拌茶汤的工具,所以促使这种与《大观茶论》要求一致的茶碗应运而生,由此可见促使这种宽底茶碗产生的原因是茶筅的应用。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赵佶所说的茶盏选择原则推理,为一个人点一碗茶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小型宽底碗,并且就使用这个点茶的茶盏直接饮用,分茶法自然而然地消逝了,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分茶与现在仍在日本使用的以单碗为单位的点茶形式的连接点。回过头来再看曹昭对于斗笠形茶碗易于喝干“不留渣”的评价。在原则上茶末是不溶于水的,仅仅是与水搅拌均匀而已,所以有沉淀物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日本茶道里,为了尽可能干净地喝完茶汤,允许出声啜饮,这是对点茶与饮茶的碗盏一体化所造成的后果的补救措施。
5. 鱼尾柄杓
在壁画上的茶盂里各放着一把鱼尾柄杓,与茶盂一样,也是分茶的标志性器具。因为没有把茶器与点茶法结合起来研究,以至至今无法理解《大观茶论》里的“杓”的功用,廖宝秀就说:
徽宗所指杓的作用与唐代煎茶法,以瓢自釜中舀茶入盏的用法相同,但点茶法由茶瓶直接注汤入盏,不需茶杓的。《大观茶论》茶器中列了茶瓶,但未提及煎茶的釜、鼎,却又列出茶杓,实不免矛盾,亦令人困惑不解。徽宗所称的茶杓与今日日本末茶道所使用柄杓,其容水量亦大致相符,柄杓大小亦约可容一碗汤量,然酌汤入杓,不取满量,仅取其四分至六分之间而已。由徽宗杓条的说明,似乎宋代的煎茶法仅在釜中煎汤而不煎茶,击拂仍与点茶相同,于盏内进行击拂(酌汤至盏击拂),由于宋书没有详述煎茶法的程序,这只有待专家学者更多的研究论述了。[xxviii]
廖宝秀对于宋代茶器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具体的研究,并且也注意到联系烹点方法展开研究的必要性,可惜对于茶的烹点方法更多的是总结概括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至无法解读茶杓的功用。相比之下,沈冬梅的研究更令人扼腕,她在提出与廖宝秀相同的困惑之后进一步指出:
(《大观茶论·杓》)表明用杓取的是点试用的开水。水杓与汤瓶的功用不相协调,这在主要论述点茶法的《大观茶论》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南宋刘松年《撵茶图》画面内容可供参考,画面中的桌子上放著一只水盆,水盆中有一只水杓,桌边站立一男子,右手持汤瓶,正往左手所持的茶碗中注汤(从方向上看象是在往水盆中注水,但这在事理上说不同),炉上又烧著一只水铫,说明水杓用来取冷水而非热水。[xxix]
沈冬梅的《宋代茶文化》是最系统的宋代茶文化研究专著,而且她已经注意到了刘松年《撵茶图》的分茶场面,可惜因为对于分茶方法的认识问题,而与茶盂、茶杓的解读失之交臂。
前面已经提到杜育在《猶赋》中强调使用瓢,《神异记》则说使用木杓的牺斟酌茶汤。他们的选择以及审美情趣对于后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陆羽在《茶经》中就说:“瓢,一曰牺杓,剖匏为之,或刊木为之。”[xxx]并引用了《猶赋》和《神异记》的记载。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宋代还是一脉相承,南宋的《茶具图赞》收录了瓢,并戏称为“胡员外”。在《大观茶论》里则有“杓”的条目:“杓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为量,过一盏则必归其余,不及则必取其不足。倾杓烦数,茶必冰矣。”[xxxi]即杓的大小一定要适中,否则就要反复斟酌,导致茶汤变凉,影响味感。
6. 瓶
张世卿墓壁画里有两把黄色执壶,张世古墓壁画里有一把白色瓜棱执壶,都是陶瓷的,文物考古界所说的执壶在茶界被称为瓶或汤瓶、茶瓶、茗瓶。
陆羽使用釜来煮水烹茶,而略晚一些的苏(*广字头下,異)在《汤品》里评比各种茶瓶:“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炫豪臭公子道。”与贵重的金银,低廉的铜铁相比,竭力倡导使用瓷瓶,其审美意识又与杜育、陆羽不谋而合。同时他也反对使用不施釉的陶器,因为这样的茶瓶会严重影响茶汤的质量:“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左钅,右夸)宸缄,且将败德销声。谚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xxxii]从西安王明哲墓出土的青釉茶瓶就是这一时代的文物。贯休在《桐江闲居作》中写道:“深炉烧铁瓶”[xxxiii],反映了各种质地的茶瓶的使用状况。
到了宋代,赵佶在《大观茶论》里对于瓶作了比较具体的记述: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xxxiv]
蔡襄、赵佶都强调使用黄金汤瓶,反映了不同于杜育、陆羽乃至苏(*广字头下,異)的审美情调。在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黄金汤瓶,不过在四川德阳县孝泉镇出土了银质执壶,而在景德镇近郊出土的影青瓜棱执壶不仅与《茶具图赞》,就是与壁画中的白色瓜棱执壶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黄金汤瓶价格昂贵,它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普遍使用其他质地的汤瓶,就像蔡襄所说的:“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xxxv]出土文物就是这种使用状况的真实写照。
各种质地的汤瓶的使用也同样反映在诗文里,杨亿《陆羽井》说;“金瓶垂素绠”,[xxxvi]苏轼《试院煎茶》说:“银瓶泻汤夸第二”,[xxxvii]惠洪《无学点茶乞诗》说:“银瓶瑟瑟过风雨”[xxxviii]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说:“无锡铜瓶手自持”,[xxxix]苏轼《题方子明道人东窗》说:“客到催茶磨,泉声响石瓶”,[xl]朱熹则在《按唐仲友第四状》里提到铁质汤瓶。[xli]
7. 火盆
陆羽在他特制的火炉上,不仅刻上了八卦,而且在刻写纪年时专门强调“圣唐灭胡明年”[xlii],即平定安史之乱的次年,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壁画上所描绘的火炉是五足盆状,似为铁质。在张世古墓里出土了陶质的冥器火盆。火盆是一种使用频繁的炉子,其它辽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类似火盆。
8. 渣斗
两幅壁画上分别绘有黄色和白色渣斗,当是瓷器。渣斗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被广泛使用,流传至今的文物数量也很大,在同一墓群的张文藻墓里就出土了黄瓷渣斗。辽代茶器中的渣斗是盛放渣滓的器皿,其功用相当于唐代茶器中的“滓方”:“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xliii]
9. 棒状器
梅尧臣《以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银瓶煎汤银梗打,粟粒铺面人惊嗟。”[xliv]说的是使用银质汤瓶煎汤,使用银质的梗棒击搅,使得茶汤的表面漂浮其如同小米粒儿般的泡沫。北宋前期的史料表明当时使用着匙箸等工具击搅茶汤。蔡襄在《茶录》中就介绍了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xlv]在宋代建茶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丁谓则在《煎茶》诗中写道:“罗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花随僧箸破,云逐客瓯圆。”[xlvi]即与陆羽一样,使用竹策——筷子搅拌茶汤。“竹策或以桃柳蒲葵木为之,或以柿心木为之,长一尺,银裹两头。”[xlvii]而到了北宋末期,茶筅异军突起,不仅《大观茶论》作了详细记载,还开始频繁出现在诗文里,南宋的《茶具图赞》甚至把它作为典型的搅拌工具加以收录,名之曰“竹副帅”。
然而从张世卿墓壁画中只能看出手持细小棍状器具,从梅尧臣的诗来看,筷子类的工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在《得雷大简自制蒙顶茶》诗中再次使用了“细梗”和“鞭”两词:“初分翰林公,岂数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以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与鞭,二物诚不幸。我贫事事无,得之似赘瘿。”[xlviii]明代以后,叶茶成为中国茶的主流,而分茶所使用的末茶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明清时代的人无法理解其烹点方法,朱昆田就在《碧川以岕茶见贻走笔赋谢》中把“银梗”作为嘲笑的对象之一:“因笑唐宋人,纷纷贵团饼。研须倚石臼,打或藉银梗。”[xlix]
四.小结——兼论茶器的文化内涵
分茶是末茶的烹点方法之一,就壁画所描绘的茶器而言,其点茶的基本程式是:在火盆上煮开水,从都蓝里取出茶器,开始点茶。在茶盂里放入适量的茶末后,一手持装有开水的汤瓶,一手持搅拌茶汤的银梗,一面逐渐注入开水,一面搅拌茶汤,待茶汤浓度适中,并搅拌出泡沫后,用瓢或木杓把茶汤分别斟酌进斗笠形的茶碗里,放在漆器茶托上,以供饮用。同时还要准备渣斗,以盛装剩余的渣滓。
中国从来就有“美食不如美器”的传统,这一点在茶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茶器不时用坐相互馈赠的礼物,黄庭坚就曾接受过茶瓶,并为此作诗谢答:“短喙可候煎,枵腹不停尘。蟹眼时探穴,龙文巳碎身。茗椀有何好,煮瓶被宠珍。石交谅如此,湔祓长日新。”[l]器具的意义不仅在物质层面上,还具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郑玄解释使用匏来酌酒的含义是“俭且质也”,即瓢的使用象征着节俭、质朴,因为“匏是自然之物”(孔颖达疏)。[li]孔颖达在解释《礼记》中使用陶匏为祭器时说:“‘器用陶匏尚礼然也’者,谓共牢之时,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贵尚古之礼自然也。陶是无饰之物,匏非人功所为,皆是天质而自然也。”[lii]班固也把“器用陶匏”作为“昭节俭,示太素”的手段。[liii]无论是晋代的杜育,还是唐代的陆羽,都选择使用了陶瓷器皿和瓢。桓温、陆纳等也以茶示“俭素”,标榜自己的生活态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素,每宴惟下七奠(*左木,右半)茶果而已。”[liv]由此看来,在晋代,无论是分茶的基本程式,还是俭素的文化精神都已经形成。
在中国,因为末茶文化的失传,所以在既不明了烹点茶的具体方法,也没有明确的茶器传世的情况下,对于文献记载的茶器的研究非常肤浅。以往的考古文物性质的茶器研究,除非异常特殊的造型或伴随着文字出土,否则难以确认究竟是否是茶器。壁画等图像资料里所描绘的茶器具体明确,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确认茶器的线索,为进而解明茶器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切实的证据,刺激了茶器研究。但是因为割裂了与茶的烹点方法的协同研究,仍然限制了茶器研究的深度。本文与其说是要彻底解明分茶的烹点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茶器,还不如说是想向方法论单调、问题意识贫瘠的茶文化研究现状中,抛入一块引玉的砖瓦。
--------------------------------------------------------------------------------
[i] (日)青木正儿:《中华茶书》,《青木正儿全集》第8卷,春秋社,1984年,199页。
[ii] (日)布目潮恭、中村乔编译《中国的茶书》,平凡社,1985年,218页。
[iii] (唐)韩岸:《为田神玉谢茶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44,中华书局,1983年。
[iv] (晋)杜育:《猶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2《草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v] (唐)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百川学海本。
[vi] 《猶赋》,《艺文类聚》卷82《草部下》。
[vii] 《茶经》卷下《五之煮》。
[viii] (宋)赵佶《大观茶论·点》,说郛本。
[ix] 茶碗是唯一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茶器,请参考(日)水上和则《宋代茶碗考——关于辽墓出土的斗笠形青瓷碗》,高桥忠彦编《东洋的茶》,淡交社,2000年,141-180页。
[x]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下《古无器皿》,四库全书。
[xi] 《猶赋》,《艺文类聚》卷82《草部下》。
[xii] 《茶经》卷中《四之器》。
[xiii]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18《茶类·和伯恭自造新茶》,黄山书社,1994年。
[xiv] (宋)苏轼:《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6《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余梦中为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余花唾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也,乃续之为二绝句云》,四部丛刊初编。
[xv]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四部丛刊初编。
[xvi] (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36《晏成绩太祝颐双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诗六十篇,因以为谢》,《四部丛刊》初编。
[xvii] (宋)林景熙:《林霁山集》卷3《书陆放翁诗卷后》,四库全书。
[xviii] (宋)陶谷:《清异录》卷4《茗猶》,百部丛书集成。
[xix] (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盏》,(明)喻政《茶书》万历壬子序刊本。
[xx] (宋)欧阳修:《居士集》卷12,《欧阳文忠公文集》10,四部丛刊初编。
[xxi] 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74页。
[xxii] (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茶托子》,百部丛书集成。“建中”原作“建始中”。唐代无建始年号,据《旧、新唐书》《崔宁传》改。
[xxiii]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9《有丧不举茶讬》,中华书局,1983年。
[xxiv] 《宛陵先生集》卷51。
[xxv] (宋)陈思辑《两宋名贤小集》卷110,四库全书。
[xxvi] 《茶经》卷中《四之器》。
[xxvii] 《大观茶论·盏》。
[xxviii] 《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89页。
[xxix]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学海出版社,1999年,84-85页。
[xxx] 《茶经》卷中《四之器》。
[xxxi] 《大观茶论·杓》。
[xxxii] (唐)苏(*广字头下,異):《汤品》,(明)喻政《茶书》万历壬子序刊本。
[xxxiii] (唐)贯休:《禅月集》卷10,四部丛刊初编。
[xxxiv] 《大观茶论·瓶》。
[xxxv] 《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瓶》。
[xxxvi]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4,四库全书
[xxxvii]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11。
[xxxviii] (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8,四部丛刊初编。
[xxxix] (宋)苏辙:《栾城集》卷6,四库全书。
[xl] (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2,四部丛刊初编。
[xli] (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奏状》,四部丛刊初编。
[xlii] 《茶经》卷中《四之器》。
[xliii] 《茶经》卷中《四之器》。
[xliv] 《宛陵先生集》卷56。
[xlv] 《茶录》下篇《论茶器·茶匙》。
[xlvi] 《瀛奎律髓》卷18《茶类》。
[xlvii] 《茶经》卷中《四之器》。
[xlviii] 《宛陵先生集卷》第55。
[xlix] (清)朱昆田:《笛漁小稾》卷10,四部丛刊初编。
[l] (宋)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8《谢曹子方惠二物二首·煎茶瓶》,四部丛刊初编。
[li] 《毛诗正义》卷17《大雅·公刘》。
[lii] 《礼记注疏》卷26《郊特牲》。
[liii] 《东都赋》,《文选》卷1。
[liv] (晋)王隐《晋书》,《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茗》。“七奠(*左木,右半)”原作“漆喇扑”,据《太平御览》卷976《菜部·菜》和《晋书》卷98《桓温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