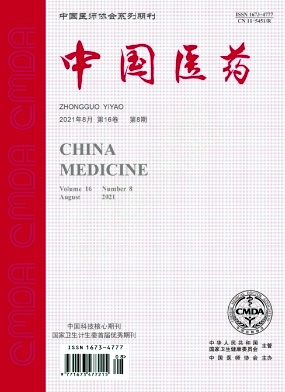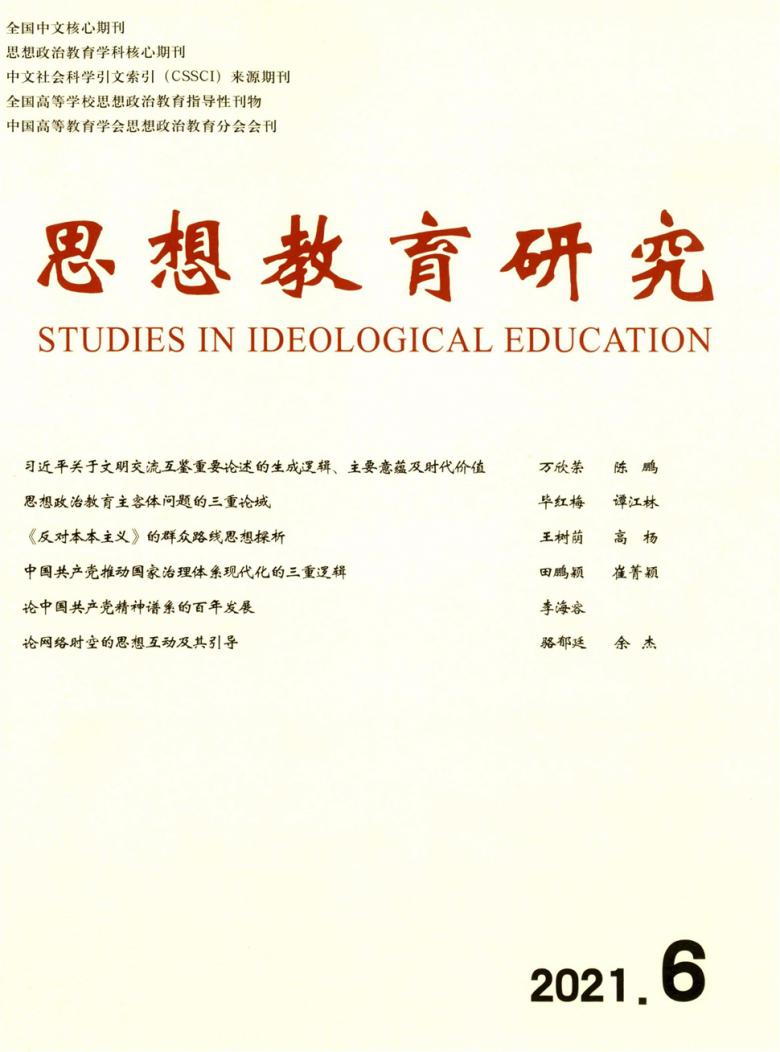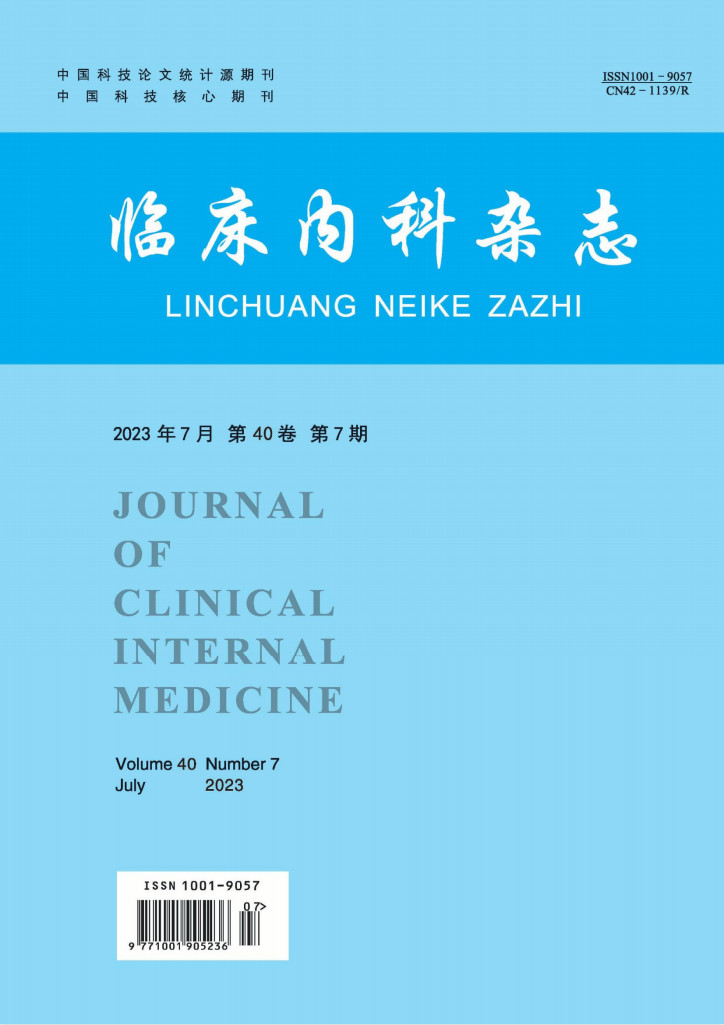现实主义艺术发展与精神分析
王军强 2021-02-01
摘要:现实主义艺术兴起于19 世纪的欧洲,其艺术表现形式是“如实”描绘现实可触世界的艺术,既指艺术的创作方法,也指艺术的写实手法。其具有批判性或揭露性,是对社会现实的同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关切,是没有夸饰、没有扭曲,平静、沉着的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的出现是对学院新古典主义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的反驳,这意味着艺术家更注重揭示现实主义原本的面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民众精神状态。
关键词: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图像复制
在当下的艺术语汇中,现实主义似乎已成为一个艺术史上的名词。作为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与创作手段的称谓,它逐渐淡出了当代艺术的话语圈。然而,我们对现实主义的陌生化,实在出于我们对这个语汇的种种偏狭隘的理解,而非其自身的自律性与活力的消失。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曾经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从“85 ”新潮到今天,30 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美术经历了狂飙式的变革和突进。30 余年的时间,在艺术史的编年中,不能算是一个过于短暂的时间刻度。在饱尝了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禁果”之后,我们的艺术家们对待现实主义艺术的态度已不像当年那样激进。多重的参照体系和经历了变革之后的冷静,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重新审视其艺术本体价值。
一、“现实”的由来
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个专门的艺术文学词汇,其艺术史上的概念始于19 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对学院新古典主义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的反驳。而其意义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摹仿”的理论。在古希腊,艺术(tekhne)是手艺的通称,其偏重于技艺、行动方面。即便如菲迪亚斯这样的大雕塑家,在当时也只被看作一个手艺人。柏拉图认为,画家对现实事物的视觉再现,只是一种用形象而不是用实在事物进行摹仿的低级活动。理念是世间万物的源头与范式,艺术家所做的,只是对理念的映射的再摹仿,因而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1]。在他之后,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存在从普遍的共相(Eidos)(等同于柏拉图的Idea)拉回到个体的实存。他把“摹仿”艺术看作是摹仿者对摹仿对象的能动反映。这种摹仿具有能够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偶然表现必然,实现可能与可信的统一。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用创造的规律去再现现实,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机械“摹仿”、镜子式的反映。史诗、悲剧等叙事性作品是摹仿的艺术,绘画、音乐、舞蹈等也是摹仿的艺术,“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例如,绘画用颜色来摹仿,音乐用音调和节奏来摹仿,诗用语言、音调、姿势来摹仿。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摹仿的本能,每个人能从摹仿的成功中得到快感。在亚氏那里,艺术的正当性得到了肯定,并且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它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还蕴涵了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因而,艺术也就具有了很好的认识作用。在中世纪,艺术的认识作用一直是被肯定的,甚至是其存在的唯一正当性理由。图像作为认知的工具,能够向目不识丁的人们传播基督教教义,可以将教堂装饰得如同天国般辉煌。在这段时期内,艺术虽然都在以人物组成的画面来进行叙事,但其所指向的,却是最不具有现实感的宗教故事和精神世界;图像作为彼岸世界的载体,接受人们的膜拜。画面表面上呈现出的现实性与其所指的宗教世界的超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对“现实”的画面本身意义的破坏。不过在这时,图像中的叙事单位并不追求形态上的逼真,人与物形象的符号示意性缓解了这种张力。但我们应该留意这种张力,因为在后面的艺术史上,它对现实主义艺术造成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在15 世纪的欧洲北部的艺术中,现实画面内部意义的张力达到了一个高峰。通常,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中间阶段;同时,这时的人们也对现实的世俗世界抱有最强烈的宗教热情和幻想。这个时期的绘画风格精于将画面内的所有的事物都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从人物衣着到室内摆设,每一样都画得一丝不苟,其细节的逼真程度令人惊叹。然而,这绝非可以被简单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因为画面中隐含的宗教含义甚至超过了有史以来任何时期的绘画。扬・凡・埃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幅名作,画面如同一张见证了二人婚姻的照片,让观者犹如置身于夫妇俩的房间之内,所看到的是画面上呈现出的实景(如图1 所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整个场景与其说是画家绘其所见,不如说是绘其所知。几乎室内的每一件陈设,都是按当时15 世纪尼德兰地区的习俗,程式化地安排在画面中的。从面前的小狗、左下方的拖鞋,上方唯一的一根蜡烛,到床上被单的颜色,再到新娘隆起的腹部,无一没有特定的宗教含义。对于当时当地的人们来说,这幅画充满了象征的意味[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绝没有摄影的概念,一幅看似逼真的画面,绝非一定按照实景绘制。而在摄影图像泛滥的今天,我们总会在潜意识中以观看摄影的眼光来解读一幅画面,特别是当一个画面呈现出逼真写实的状物描绘,即一种物理上的“现实主义”倾向的时候。这种诱惑会让我们简单地认为我们看到的就是画家所看到的,甚至于“所见即真实”。这种心理所导致的危险,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而且在历史上,它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在同时期的欧洲南部,主要是意大利地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已经悄然开始。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以“窗户”理论重新开始挖掘描绘现实的价值。“画面就是向这个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这就意味着,画家应该把画面描绘成如同从一个固定的视点看出去,在视网膜上所得到的视像一样。艺术家们开始了一场竞赛,痴迷于透视法和缩短法的实验,努力在画面上造成三维空间的视错觉效果。莱昂那多・达・芬奇总结绘画经验时说:“画家应该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用这种办法,他的心就会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然而在这里,追求视觉的真实(real)仍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Realism)。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宗教的影响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旧的神学思想与新兴的人文思想相交汇,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以新柏拉图主义的面貌融合在一起。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继承了柏拉图的看法,认为现实事物只是最高存在的投影,人的灵魂也是受着上帝之光的吸引;世间美好的事物是上帝爱的创造,人类通过对美的追求激发对上帝的爱,以求接近上帝。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赞助人洛伦佐・梅迪奇周围的文人圈子里,菲奇诺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在他的传播之下,波提切利、莱昂那多、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一批大师都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深刻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雕像,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视觉结晶;即便是表现世俗题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其中也深深蕴涵着超越于现实的神学思想。
二、“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
西方艺术的两大思想来源―――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这两者本身都不会产生出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如上文所说,要到19 世纪方能成为一种明确的艺术指导思想。而其客观条件,即是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影响的式微,以及人们对古典艺术兴趣的消退。到了19 世纪初,民族国家在欧洲纷纷形成并成长,特别是欧洲大陆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洗礼。对世俗权利争夺的关注,对现实生活的投入,使得人们走出了以前那种以宗教为中心的生活状态。在新古典主义艺术受到了浪漫主义艺术的挑战之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人们对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了反思。此外,19 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也在观念层面上催生了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僵化的新古典主义和主观理想化的、追求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都已不能满足当时人的精神需求。此时,现实主义的思潮现出了端倪。1789 年4 月27 日,席勒在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第一次在近当代文艺理论的层面上,运用了“现实主义”这一说法。而据波兰现代美学家符・塔达基维奇考证:“现实主义”概念最先出现在1821 年一篇题为《19 世纪的墨丘利》的佚名文章中。文章称“忠实地摹仿显示提供的原型”的原则“可以称作是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内涵基本上还保留在古典“摹仿说”的框架内。法国画家库尔贝标志了现实主义的真正兴起。1955 年,库尔贝正式打出了“写实主义”的旗号。这一年,他的作品在由拿破仑三世所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落选,库尔贝便在博览会旁边举办个人作品展览,以丽水学院学报示抗议。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画室》。库尔贝的名言“我没见过天使,所以我不会画它”,表明了他与通过绘画体现理想价值观的整个传统的决裂[3]。在他的名作《打石工》《筛麦妇女》《库尔贝先生,您好》(如图2 所示)中,都以巨大的尺幅,庄严的构图,严谨的技法表现现实生活里中下层平民的生活状态,其中《库尔贝先生,您好》的构图,可能来自当时法国流行的民间版画的图式。在库尔贝的这些作品中,观看者看不到任何画面之外的、象征式的形而上的存在与理想价值,生活即是生活本身。这里既没有形而上的玄思,也没有过分夸张的形象与情感。只是把现实呈现在观看者眼前,而让人沉浸到现象所显现出的种种意味之中。然而通过在这之后的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看似最简单的再现,却需要最沉静的心灵、最独立的思考和最大的勇气。在当时,人们为这样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欢欣,继而对其提出了社会价值判断方面的要求,包括现实主义艺术应具有批判性或揭露性,应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现象,以及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平等地位。在这一方面,杜米埃是一位卓越的漫画大师。另一方面,柯罗、米勒和巴比松画派的画家来到郊外和农村,进行户外写生,描绘农民和农村的生活。他们的手法或质朴、或轻快,而他们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对写生的重视,使他们的艺术都得以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样的局面维持到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以印象主义的兴起而告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库尔贝就没有马奈,没有柯罗就没有莫奈,在法国,现实主义艺术很自然地发展到了印象主义。印象主义给现代艺术的洪流打开了闸门,而撬开这扇闸门的,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它既是古艺术的终结,亦是现代艺术的滥觞。然而现实主义艺术并未完结。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它得以保持并继续发展,终对中国20 世纪的艺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俄国的巡回画派那里,现实主义精神与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悲剧性气质相融合,并借助于正处于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精神,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列宾、苏里柯夫的作品里,满目尽是对社会现实的同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关切。然而在后来的苏联,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使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主义”术语进入马恩文艺理论文献是在19 世纪50 年代,1859 年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运用于文艺领域,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认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将现实主义与艺术典型相联系。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现实主义从此被笼罩上了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色彩,这与它最初关注个体的出发点相比已经开始出现了紧张。应该说,最初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中就已经潜伏着这种紧张。艺术不仅是对现实世界外形的摹仿,而且能从对个体的描绘达到对共相的揭示,也就是揭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在苏联,这种现实主义的外延被放大到了极致,导致了对其本身的背离。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面貌出现,成为统治者满足政治需要的文艺宣传工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基本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到了“文革”时期,现实主义的“超现实化”达到了高峰,美术作品表现手法相对单一,从构图到人物形象相对程式化。这种情形与前面所说的中世纪的宗教图像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类似。而“所见即真实”的视知觉心理,使民众在潜意识中对这些图像产生了信赖,继而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化的半催眠状态中对图像进行膜拜。但就“现实主义”艺术本身来说,它的确在那个时代被极大程度地扭曲和破坏了。这种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艺术本身的特质所导致的。以个体反映一般,以典型揭示普遍和必然的“摹仿论”基础使它容易成为被意识形态利用的政治工具,而“现实”(real)画面给观看者造成的错觉,使人将作为载体的画面内容与其指向的象征或理想意义混为一谈。现实主义艺术经此破坏,面目全非。这就造成了“85 ”新潮之后,非官方艺术对现实主义偏见式的否定和排斥。但在这之外,“现实主义”在中国20 世纪的美术中仍然结出了累累硕果。从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政治漫画,到延安的木刻版画,从蒋兆和的《流民图》(如图3 所示),到罗中立的《父亲》,在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中,现实主义启示了很多艺术家创作出真正深入生活,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民众精神状态的杰作。在这个图像被大量复制、泛滥的时代,传统的架上绘画的存在正当性被无数次的质问。从摄影术、现代印刷术之后的机械复制,到当下电脑、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统治下的数码技术复制,绘画何以成为一门仍然具有独立性的、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形式?影像技术可以把观看者直接带入现场,进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全方位复制,在物理的逼真性上完全超过了传统绘画。现实主义之真实(real)何以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空间?本雅明认为,他所说的“灵晕”(aura)已经从绘画作品上褪去了,绘画从膜拜价值被贬为消遣价值。然而,复制图像的泛滥造成了人们对它们的轻视,而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珍视和崇拜,正是得益于它是由人运用最直接的工具,以不可复制的历时性的过程完成的实物存在。影像之真,在于物理性的逼肖,但影像的表面真实有时却遮蔽了生活的真相。数字技术的运用,在丰富了影像表现力的同时也贬低了影像的真实可靠性。真实的影像在现代生活中似乎是最唾手可得的,但生活和人生的真相却在包围着我们的影像中幻灭。我们在精神上对真实的渴求在日益加深。应此,当代现实主义的真实,在于以画家的心和手记录下对象之后,再以作品去打动观看者。即实现“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两个方面的统一。我们周围的影像,大半都带有表演的性质,而我们亦对此心知肚明。但我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绘画则来不得半点表演,画家以心运手,写生造像,这个历时性过程本身就是在寻求和表现一种具有恒定性、持久性的内在真实。这样没有夸饰、没有扭曲,平静、沉着的艺术在当下也就显得尤为可贵,当下的艺术也需要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现实主义艺术,就应当回到它的原点,展现出应有的面貌和气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某个艺术思潮和观点,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主流艺术样式,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揭示现实主义原本的面貌,让这个“最熟悉”的风格流派,去除长期以来历史和政治赋予它的“浪漫色彩”,在中国整个艺术教育体系下具有现实意义,这将有助于艺术实践和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1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7.
[2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 :243.
[3 ]邵大箴.图式与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