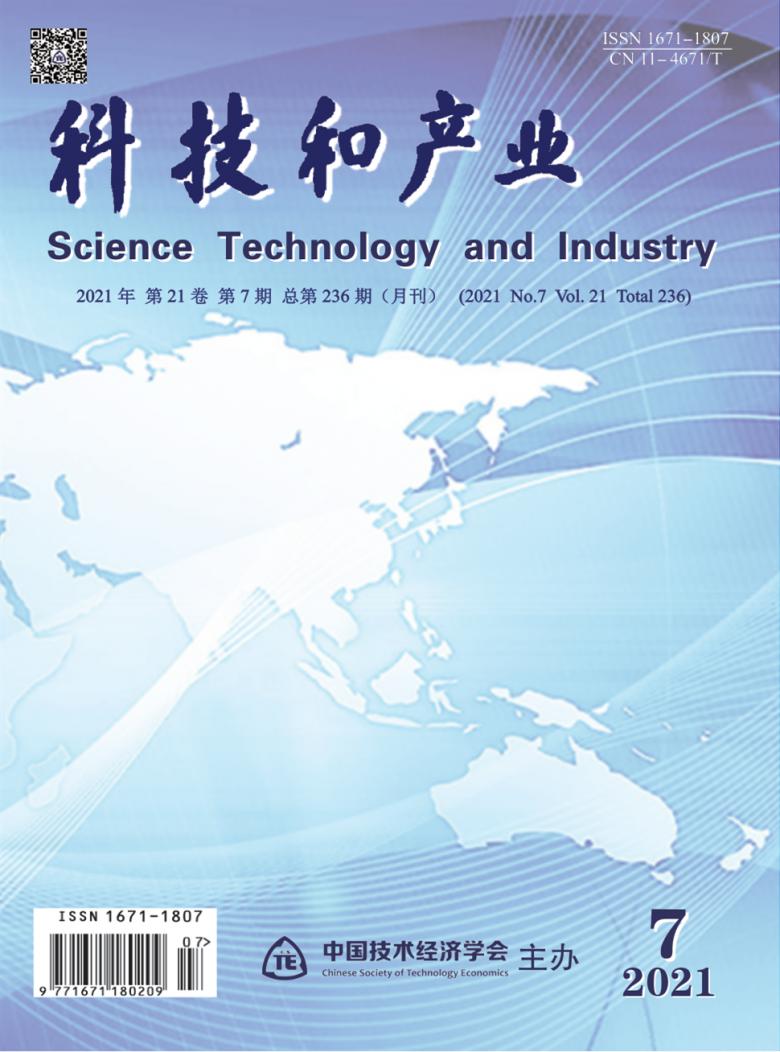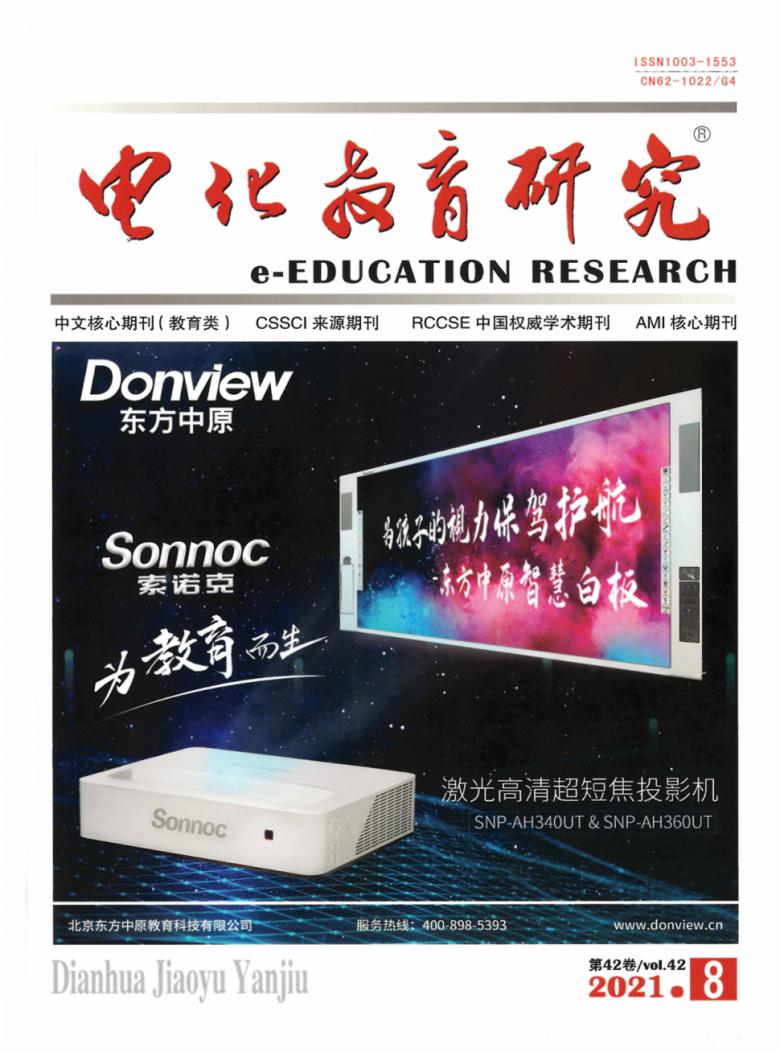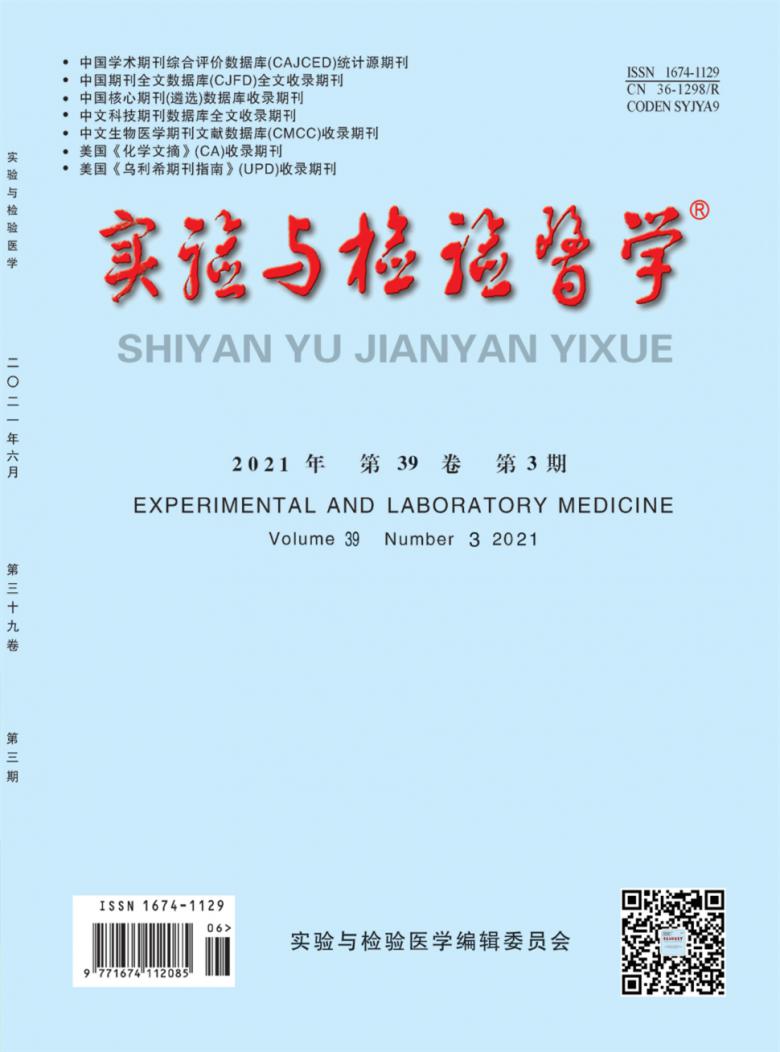“祛魅后的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
季广茂 2007-01-08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雷蒙·阿隆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世事如棋,人生如弈,面对沧桑巨变,不知他会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雷蒙·阿隆生活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人们常拿他与萨特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出生于1905年,都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都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会顺理成章地参加高校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并在大学任教。他虽然不是中国人,没有听过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演讲,还是远走他乡,加盟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建立的法国抵抗组织。
二战结束后,他从伦敦返回巴黎,曾在安德烈·马尔罗的战后新闻部短期任职。任职时间虽然不长,却立志以新闻采访和政治评论为终身之职。他1954年开始在索邦讲授社会学,同时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HESS)任教,197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83年逝世时,有人说他“不仅是法国大学中伟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国大学中最伟大的教授”。因为“死者为大”,所以即使这话有些水分,也没有多少人深究。
阿隆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哲学,博士论文主攻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但纵观其一生,他的学术旨趣是主要是社会学,他大多围绕着社会思想、产业社会等问题“大放厥词”。他兴趣广泛,涉猎的领域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史、军事理论、比较政治学等。而且在这些领域,他都是公认的国际权威。可以说,他不仅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而且是兴趣极广泛的学者;不仅是兴趣极广泛的学者,而且是矢志不渝的思想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既是大力介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勇于对公共事件指手画脚,同时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家。虽然法国有这样的传统,但在他那个时代,能同时演好这两种角色并不容易。
广泛的兴趣和丰硕的成果,使他成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但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他有明显的过人之处:猜不透的果子他不吃——他只守望自己熟悉的领域,谈论自己关切的话题;没有味道的果子也不吃——绝不像中国今天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上了趟厕所,因为多交了三五角钱,也要仰天长叹:“中国,一个小便也不免费的国家!”
在那代知识分子中,雷蒙·阿隆属于特立独行之士,他总是不合时宜,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尽管他最初同情左翼人士,并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一道创办了著名的左翼文化杂志《现代》,但在冷战时期,他却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指点江山。这的确够“出格”的,因为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同情共产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阿隆还常有惊人之论。比如,他认为,超级大国不可能为所欲为;同样,阻止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核武器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令人不寒而栗,但核武器并不等于一切,过分夸大核武器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作用,有自欺欺人之嫌。这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核武万能论”颇不合拍。
在那代知识分子中,只有阿隆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抗拒极权主义的巨大诱惑,无论这诱惑是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此外,他还透过独特的法国视角来观察政治事务、进行政治评论。这些特点的奇妙混合,使得他的著述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卓然独立,以至于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他的著述之所以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还有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阿隆认为,他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是那个时代使然,因为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原子时代。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任何接受过精致的古典教育的法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包括萨特在内的其他知识分子也经历了这些事件,为什么只有阿隆抛开了抽象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效忠,保持了独立自由的人格?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阿隆最重要的著述发表(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那是他的黄金岁月。他关心的较为重要的话题包括冷战及冷战中超级大国、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这些都是对公共事务的反思。当然阿隆不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他也没有先见之明,无法得知美苏之间的对抗将以何种形式收场,不会预料到在他去世后的几年之内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变,不会知道如此巨变对于世界说来是何等重要。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因为在面对不可确定的历史难题时,他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阿隆在政治上冷静客观、慎思明辨,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阿隆毕业后曾在魏玛共和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目睹了民主政治的崩溃和专制主义的崛起。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法国同胞,莱茵河两岸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后果有多么严重。可悲的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狼来了”的呐喊,反而觉得他在极力“危言耸听”,以为他在“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他亲历了法国第三共和的衰微,目睹了政治的腐败是如何导致了贝当在纳粹军队入侵法国后的上台。自由政治何以如此不堪一击?何以时时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威胁?阿隆对此甚感兴趣,甚至是极其着迷。他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因此和他的同代人分庭抗礼。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忧虑,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政客和知识分子面对希特勒的大屠杀茫然四顾之时,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事件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忧虑,他才能对战后法国出现的各种危机(包括1968年五月运动)做出积极而审慎的回应。阿隆一再强调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呼吁法国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和的公共争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介入不仅一种重要的生活态度,而且是改进社会的主要方式。因为在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里,仅仅观察和纪录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充当了“人类罪恶与灾难的观察者”而沾沾自喜。
当然,这并不说明观察并不重要。相反,与抽象的理论相比,观察和经验更有价值。阿隆一直关心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公民秩序(civil order)和公共自由(public liberties)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能把这三者融为一体的是经验和观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这方面,阿隆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大有惺惺相惜之势。这三者间的关系彰显出他对于自由的思考,以及对于日益崛起的极权主义的忧虑。在阿隆那里,“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涵盖各种专制现象的理论范畴,而是伸手可及的种种社会现象与生活经验。
阿隆对于极权主义的思考源于他对于极权主义的对立物的关切,即对于自由社会的关切。自由社会总是不完美的,时时遭受形形色色的外在限制和威胁。比如,极权主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自由社会即使偶尔出现轻微虐待战俘之类的事件,也会被某些人大肆渲染,上纲上线。尽管如此,自由自有自由的价值。在全球冲突的年代里,即使有人选择美国式的社会制度,那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社会有多么美好,美国人的生活有多么幸福,而是因为,美国是公共自由的坚强卫士。
因此可以说,虽然自由和民主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自由和民主是脆弱的,因为要想保护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任何社会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自由和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社会上存在着某种种种缺陷,甚至是丑恶现象。依据健全的常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有一个笑话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妈妈对孩子抱怨说,我年轻时貌美如花,没想到嫁给了你爸爸,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孩子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插在牛粪上?妈妈叹口气,答曰:唉,牛粪也不好找呀。这时,妈妈面临的选择无非两种:或者有牛粪插,或者无牛粪插。插在牛粪上,固然不雅,但聊胜于无,也算差强人意了。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须知,如果没有婚姻,爱情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吃不到的苦比吃到的苦更苦”,的确如此,吃苦,固然不好,但总强于无苦可吃,无事可做,饿肚子。
因为追求“最好”而沦入“最坏”之境地的,古今中外,俯拾即是。用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说就是,“试图通往天堂的路,却导致了地狱”,或许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也是历史或理性的一大诡计。但总是有这样一些人(有时甚至是一些老好人),他们在建设最美好、最纯净、最强大、最本真的社会的名义下,要推翻、瓦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就是拼命抵抗这种诱惑,保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使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阿隆蔑视那些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人,特别是以暴力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人。“暴力”的别名就是“革命”。阿隆反对革命,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过,革命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集团运用暴力,冷酷压迫其反对者,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政府,同时梦想着改变整个国家结构。对于以暴力(“革命”)为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嗜好,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火硝烟有关。
是呀,革命可是一件大事情,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目的在于摧毁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革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这正如J.F.肯尼迪所言,因为不允许人们进行和平进化,所以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暴力革命。如果情形许可,如果和平进化还有可能,暴力革命就永远没有合法性。即使暴力革命是合法的,按照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三思——总不能像陈胜吴广那样一怒之下“揭竿而起”。厚黑教主李宗吾对此有个极其有趣的比喻,他说所谓革命就像一帮人合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房子里,其中有几个人没有征求全体合住人的意见,就决定拆了重建。这时问题就来了:这房子虽然破败不堪,但总是聊胜于无吧,你不经合住人同意就拆了重建,这是强奸民意;而且,万一拆了旧的又建不起新的,咱们何处栖身?“边设计,边施工”?怕是有点玄。建房是否有图纸,设计是否合理,需要多少材料,要造多少预算,一切是否像你讲得那么句句是实,绝无浮泛之词?万一你收了回扣,弄了个“豆腐渣”、“王八蛋”工程而无法入住,你有什么后续手段?即使没有收回扣也没有弄什么“豆腐渣”、“王八蛋”工程,可建了个半截子就用完了工程款,然后你钻进了预先分给自己的套房,来他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只好风餐露宿,那我们冤不冤?革命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不然就会沦于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地——失败时居多,胜利了也只是少数人的胜利——建了一半钻进自己的套间,便宣告一切完事。
阿隆之所以有这样的惊人之论,是因为阿隆信奉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祛魅后的现实主义”(disenchanted realism)。众所周知,个人自由和法律秩序是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两大遗产,但它们在20世纪一直遭受致命的威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深受理想主义的蛊惑,甚至陷于“不要更好,只要最好”的理想主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这方面,“祛魅后的现实主义”可谓一剂良药。阿隆认为,我们在审视世界时,首先要看到它已然的、现实的一面,而不是它应然的、理想的一面。无论是社会评论家、社会科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要首先关注世界的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理想的未来。阿隆对于马克斯·韦伯大加赞赏,因为韦伯“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回答下列问题(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全部的业余政客打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是一位内阁部长,你怎么办?’”阿隆曾经为此扪心自问:“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通过提出下列问题来制约自己的批判:‘处在他们(内阁部长们)的位置上,我又能怎么办?’”
或许正是为了扮好“影子内阁部长”的角色,阿隆开始涉猎年轻时不曾涉猎的学科。早在1937年他就说过,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你也不会随时得到这样的机会——以真理反抗谬误,甚至为此英勇献身。知识分子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一己之见,就必须涉足经济、外交和政治等众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但在这样做时,有些人总是把太多的道德评价倾注于自己的社会分析,任由道德激情淹没理性的分析,甚至以此为得意。阿隆对此颇为不以为然。即使碰上二战时期的傀儡政权这样浇灌了太多的道德染料的敏感话题,阿隆也主张冷静、冷静、再冷静,理智、理智、再理智。在他看来,维希傀儡政权犯下的与其说是罪恶,不如说是过错,因为那也仅仅是政治判断失误的结果而已。事后诸葛亮式的“明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式的“功利”,只是徒然搅乱了历史的混水,有利于某些人浑水摸鱼而已。同样,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东西方缓和的局势,他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甚至对当时四处弥漫的狂热感到厌倦。他更喜欢与希特勒媾和的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使得在两次战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幻想破灭了。这幻想便是, “能否实现和平,取决于言词,而不取决于勇气和力量均衡。”事情恰恰相反,世界能否和平,并不取决于“话语”,而是取决于勇气和力量均衡。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错把梦想当现实”,因为一旦苏联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它会毫不犹豫地退回到以前的铁幕时代。
由此可见,“祛魅后的现实主义”依然魅力十足。当然,阿隆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我们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指的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或先验的判断,准确地预测各种可能性,精确地预测未来的成败得失的“指数”,并据此制定决策,采取行动。这只是一种“理论现实主义”,一旦付诸实践,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一想“囚徒的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吧,我们从中除了得到“人算不如天算”的感叹,还会得到什么?再想一想那位精明至极的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吧,他自以为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和《英德宣言》是高明之举,会给英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以为“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英国民众也把张伯伦视为“英国人民的大救星”,狂呼“张伯伦万岁”。结果呢,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竹篮打水一场空。张伯伦在慕尼黑做出的决策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就像马其诺防线,看起来固若金汤,打起来不堪一击。阿隆对于这种精于算计的“算死草”式的现实主义不屑一顾。
与“理论现实主义”不同,“祛魅后的现实主义”强调观念和理想的重要性。自亨利·基辛格以来,当代“现实主义者”大多对观念和理想敬而远之,对于抽象的目标和伦理的雄心更是疑虑重重。在这些“现实主义者”看来,观念、理想之类的东西在政治话语中毫无价值。往好处说,它们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说教,在进行事关生死的政治抉择时,一定要将其置之度外;在更多的情形下,它们也只是一些托辞,是某些人在采取与其不相关的行动时披着的画皮。“祛魅后的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不仅包括了利益和权力,还包括观念和信仰。阿隆认为,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人们未必具有统一的信仰,但人人都有其信仰,并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和军事部署、生产方式一样,观念和信仰也是现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忽视了道德判断,忽视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利益,“现实主义”就不再“现实”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与当时的苏联问题专家做出的“现实主义”观察相比,在苏联的走向这一问题上,阿隆的现实主义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和更精确的预测,表现出极强的洞察力。举例说吧,早在20世纪40年代,阿隆就用“双轨制”解释苏联将要采取的国际战略:苏联会持续不断地追寻自己确立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有两种,一种是结盟,一种是对抗。此论当时振聋发聩,不料进入70年代后,“双轨制”已经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街头智慧”(street wisdom)。
阿隆之所以对苏联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耿耿于怀。苏联与传统的强权国家大相径庭,因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阿隆终其一生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他比许多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博学。他对马克思的兴趣始于早年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但后来,他对19世纪社会思想史的持久关注,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论争,都维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阿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俗宗教”,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面。他认为,各种极端主义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或者极力求助于自由政治,或者大力危及自由政治,总之都要与自由政治结成某种关联。
阿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种看法时,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特点再次暴露无遗,也再次证明他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美国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更喜欢使用功能性术语(functional terms)研究马克思主义政体,强调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隆的做法感到不可以思议,因为他使用的是他们的术语,却不采纳他们的观念。与当时的欧洲左翼人士不同,阿隆可不想四处“寻找为他们[欧洲左翼人士]的上帝建造金字塔的人”。
因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现实主义”,阿隆对于社会、政治、历史的看法从来都不是“昂扬向上”的。他对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政治革命、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都无法改善人类的生存境遇。但这并不意味着阿隆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对未来毫无信心可言。他也常常表现出乐观之意,但那乐观也只是“谨慎的乐观”、“怀疑的乐观”而已。比如,对于现实的透彻了解使他早在1947年就认识到,永久的和平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暂时的和平却是可以期许的,战争也是可以暂时停止的。阿隆相信,持续不断地警惕、缩小东西方对抗带来的风险和破坏力,是全人类共同肩负的责任。这种看法与当时的主流看法颇为不同。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的目标就是终结一切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走向美好的明天”。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要么是制造核武僵局,要么是和平对话,要么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他反对把苏联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他相信,苏联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全世界推向战争、死亡的边缘,它会通过对抗与妥协这两种方式,持续地追寻自己的目标。
因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现实主义”,阿隆对于任何一种“体制”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既憎恨信奉一元论学说的左翼人士,也厌恶抓住那只“看不见的手”死死不放的右翼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这样的立场无异于自拔坟墓,他也一度使陷入“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尴尬境地。但是现在,和另一位政治多元论、思想多元论的卫士伯林(Isaiah Berlin)一样,他也终于在去世后不久苦尽苦来,得到了他早该得到的荣誉。
他把自己描述为“介入的观察者”(le spectateur engage)。他自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不群不党,其意见先是得罪这一方,然后又得罪那一方;其人更是不堪忍受,因为他把自己的中庸思想推向了极端,把激情隐藏在冷峻的论点之下。”
事实证明,阿隆的中庸态度和世俗智慧的完美融合,不仅能使我们精确地洞察世事,而且使我们在面对种种复杂的世界局势时端正姿态,摆正心态,避免“愤青综合症”的爆发和“鸵鸟政策”的泛滥。冷战结束了,世界依然不尽如人意,恐怖主义的肆虐依然是令全世界头痛不已的首要难题。冷静、理智、克制依然是面对世界局势时的首要姿态。用阿隆的话说就是,“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观察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带着冲天的狂热和满腔的义愤。”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Raymond Aron, 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from a Witnes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Edited by Yair Rei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ony Jud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Tony Judt,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