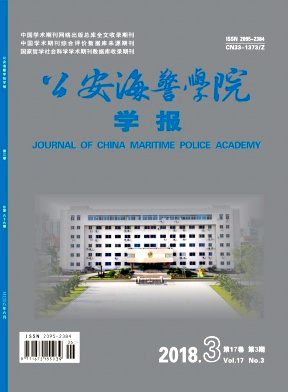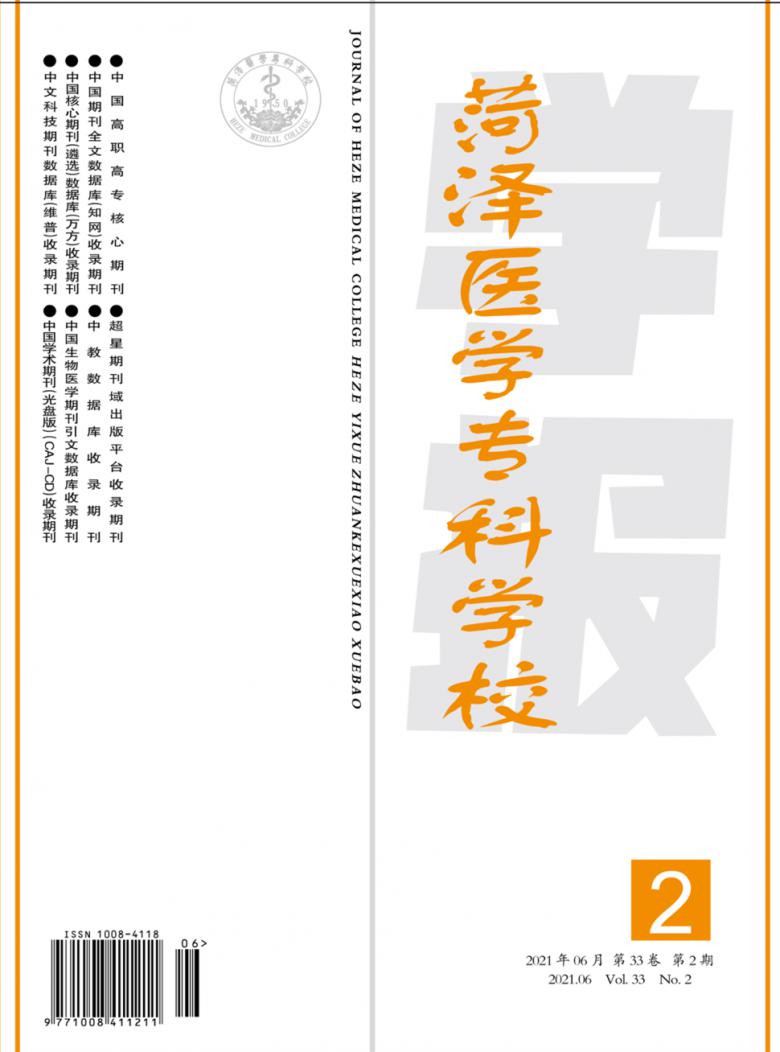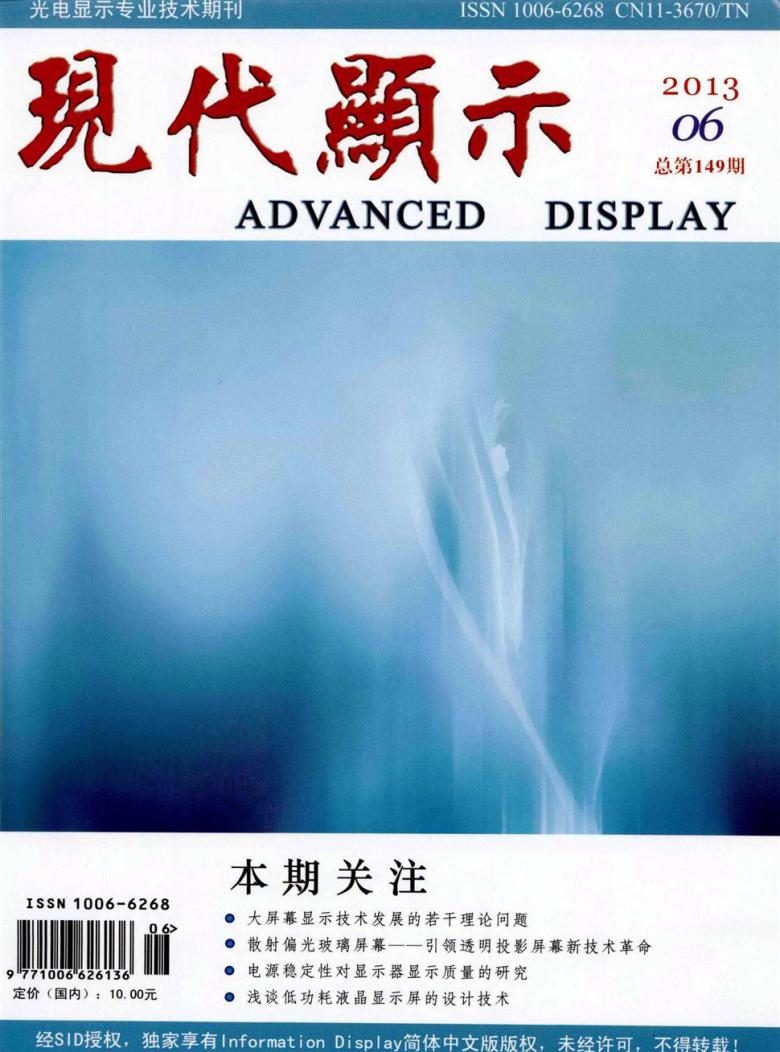试论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艺术品格的差异性
何孟霞
论文关键词:文学影视媒介受众表现手法
论文摘要:文学创作和影视传播是隶属于同一文化河流的两条不同分支,它们带给人类相同的心灵滋养和精神愉悦,但作为文化的不同分支,二者的艺术品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的媒介和受众的参与性不同;其次,二者的表现手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最后,它们被解读的时空与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也不相同。
文学创作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化类别,千百年来,它以抽象的语言文字、概念思维为人类的精神领域提供着重要的精神食粮,而影视传播则是近百年来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光影声幻化技术的出现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改变着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类别。它们二者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影视艺术作品是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创作者的共同产物,但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影视艺术文本(即文学创作),那么高水准的影视艺术传播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特别鲜明,因而研究二者的差异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的艺术品格的差异性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文化媒介和受众的参与性不同
文学创作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描述对象的艺术门类。语言文字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抽象、概括的反映,“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以及文字)的符号系统中,基本的、占绝大多数的符号本身都是没有形象性的。它所代表的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命题与推理,因而不像感觉、知觉那样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它是一个以声音(或线条)来表示的符号系统,是客观事物的抽象的、概括的反映;从人的心理活动上来说,属于第二号系统,虽然语言本身没有形象性,却具有唤起人们形象感的功能。文学语言不同于一般的科技语言和日常语言,它往往突破语法结构和逻辑要求,强调个人的感情色彩和风格,采用隐喻、暗喻、转喻、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来反映外部世界,表达主题情思,有时甚至刻意追求阻拒性语言。因此,文学作品中言语的指涉意义往往不是一眼看穿的。例如,杜甫的“恶竹应须斩万竿”中的“恶竹”,李商隐的“寒梅最堪恨”中的“寒梅”,彭斯的“红红的玫瑰”中的“玫瑰”、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中的“露”“风”等等。都不能理解为实际的竹、梅、玫瑰、露和风,这些事物都是一种象征,“恶竹”象征“小人”,“寒梅”象征不得志或生不逢时者,“玫瑰”象征爱人或恋人,“露”与“风”象征恶劣的政治氛围等。
影视艺术是以视觉为主的视听艺术,它首先必须通过影视画面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阐述哲理。每一部影片的内容和意蕴,都必须通过画面造型表现出来,即使是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也必须通过可见的人物造型、环境和摄影造型在银幕上体现出来。
影视艺术还需采用光,光既是摄影的基础,又是人们视觉感觉的基础,银幕或荧屏画面上的影像的形状、轮廓、结构、色彩、明暗、情调等等,无一不受到光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更是使得“光”成为影视艺术中具有巨大潜力的艺术元素。声音亦是影视艺术的不可或缺之处。例如,日本影片《生死恋》的结尾,男主人公在网球场外,心中思念死去的女友,球场上空无一人,画外音却出现了从前两人一起打球时的碰撞声和女友的欢笑声,声画分离造成了时空的错位,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
由于影视将文学作品中的概念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因而受众的参与性较低。影视传播的受众,即观众,他的位置始终是在银幕下,是一个被动的观看者,电影给什么就只能看什么。影片《楚门的世界》就很好地诊释了这一点,楚门虽然生活在无数的探头之下,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看到他的真实“演出”。但是,他与女朋友在卧室内的亲密镜头却从来没有被直播,吹起了风,放起了音乐,镜头转换到飘动的窗帘。
二、两者的表现手法不同
影视传播以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为主,辅之以特写以及不同时空的跳跃、衔接等。影视传播的任何一个情节或一组画面,都要从影片表达的内容出发来处理节奏间题,这就需要镜头的衔接与跳跃。比如,在一个宁静祥和的环境里需要使用慢节奏的镜头转换,否则,就会使得观众觉得突兀。然而在一些节奏强烈、激荡人心的场面中,就应该考虑到种种冲击因素,使镜头的变化速率与观众的心理要求一致,以增强审美效果。警匪片《江湖告急》运用“跳跃”的手法来拍摄,一场戏一个情节刚发展到一个顶点便戛然停止,立刻转换到下一段戏,使影片显出一分异常的简练干脆,给人留下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通过特写,电影让人看到只有在最近距离内才能看到的极其微小的世界。同时,特写也是展示影片人物心理和戏剧含义最有力的手段。
文学的表现手法主要体现在对语言文字的操作运用上。表现手法的选择与运用,应该服从于总体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意图,服从于不同的体裁样式的要求。文学创作中的基本表现手法,有描写、叙事、抒情、议论等。
描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造型手段。它要求在语言运用上要绘形绘貌、绘声绘色,特征表现要历历在目,神韵传达要栩栩如生。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中,对祥子做了这样的肖像描写:“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作家既活灵活现地写出了人物的面目,也透露出了年轻祥子的淳朴性格。 文学创作中也采用叙述的表现手法。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顺叙方式最为常见。就拿《三国演义》来说,第一回从“建宁二年四月观日”皇宫出现妖孽、蔡琶上书、十常侍作乱开始,引出黄巾军,然后是桃园三结义……叙述就这样沿着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推进。在第一回的末尾讲道刘备等三人救了董卓却受到怠慢,张飞大怒,要提刀杀董卓,然后说“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回一开始,便接着上一回结束时的内容讲道刘备和关羽劝阻张飞。倒叙也是叙事的一种,往往采用事件当事人事后回忆的形式展开。这种叙事方式,首先将事件的结局突出醒目地加以呈现,使其得到有效的强调,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力量和强烈的悬念感。如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梅里美的小说《卡门》,鲁迅的小说《祝福》《伤逝》等,都是运用了倒叙的手法。还有插叙的方式可以对主要情节起到补充交代、扩大容量、丰富完善的作用,并可以调节叙事的进展节奏,使情节的发展更加完整,更加合理。
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必然要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不管作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情感的抒发都会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推动艺术想象,并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文学创作也就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外化或形式化。作为表现手法的抒情,则特指作家自觉而集中地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一种写作方式。它要求作家创造性地运用文学语言,把真挚而丰富的情绪感受准确、充分地传达出来。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小诗《自由、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短短四句,直写情怀,掷地有声,感人至深。像读杜甫《登高》中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悲凉之感不觉溢于言表;读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的诗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欢愉之情自然扑面而来。
三、解读的时空与反映的文化内涵均不同
文学作品在阅读过程中,因其是静态的东西,时间、空间不受限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对文本的阅读时间,甚至反复阅读,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深刻理解。然而影视阐述出的心理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文字描述的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影视是声化艺术,心理活动难以从人物对白中直接体现。依靠演员的面目表情、肢体动作来展示是很好的手段,但总嫌不彻底、不明了;独白、旁白似乎更为直接,但不宜更多插入,否则会影响影片的美学价值。影视传播在解读的过程中,因为是动态的事物,转瞬即逝,观众不能自行调整观看的时间。由于影视往往借助鲜明的画面、人物的对白加强观赏效果,因受时空的限制,表现的思想内涵较之文学文本则显得简单、直观。
影视文学同文学作品比,其表现抽象事物的能力也有待提高,在揭示更为复杂、深刻的主题方面也往往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鲁迅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桥南的信中提到关干小说《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问题:“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信中提及“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似乎暗含着以后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彼刻明星便可能表现了。然而,事隔半个多世纪,198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岑范导演、严顺开主演),尽管编导及演员以严肃的艺术态度和强烈的责任心来演绎影片,但就播出效果来看,多数观众依然将其作为娱乐笑谈或哀怜对象,并未看到深潜其中的主题。如何领会原著的思想主题及心理内涵,并通过影视剧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能消除影视改编所带来的阐释异义,这是影视工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艺术相同一样,它们归根结底各自都是独立的,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本性。文学语言为文字符号,读者须基于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将其转化为文学意象和意境。文学表现方式极为自由,不受时空限制,“笼天地于形内,措万物于笔端。”影视表现为具体可感的影像和声音,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表达方式随科学的发展日益丰富多样,观赏性、娱乐性更强,更符合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其在商业社会大行其道奠定基础。一百多年来,文学和影视这一对姊妹艺术互相滋养,互相给予。影视离不开文学的哺育,而文学作品也在电影的冲击和影响下,不断蜕变,增添新质。在图像霸权文化符号地位日益稳固的今天,充分认识二者的不同审美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鉴别两种不同艺术的特质,使其相得益彰,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