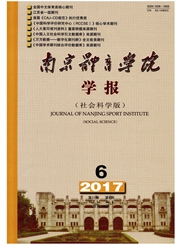从《四艳记》看晚明才子佳人戏曲的基本走向
傅湘龙 2008-07-23
【内容提要】才子佳人戏曲的发展模式在晚明实现了某些突破,《四艳记》就是通过“传诗递简”、“幽期密约”的缩减与在“好事多磨”过程的增强来率先完成的,并成为一时创作的典范文本。而它的问世也深深地打上了当时文化思潮、社会风尚的烙印。
【关 键 词】四艳记/晚明/才子佳人戏曲/基本走向
【正 文】 自从《西厢记》确立才子佳人戏曲“四部曲”模式以来,这类题材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都入其牢笼而难以突破。晚明剧作家叶宪祖受当时文化思潮、社会风尚的影响而创作的《四艳记》有意对这传统模式的某些环节如“传诗递简”、“幽期密约”进行修正,通过“好事多磨”过程的增强而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从而奠定了《四艳记》在晚明才子佳人戏曲文本中的典范意义,引领着晚明才子佳人戏曲创作的基本走向。
一
在《四艳记》之《碧莲绣符》中,章斌与碧莲一见钟情,不堪忍受隔离之苦而欲委身为秦家记室,作品在此为才子佳人传诗递简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平台,然而情节的推进却没有因循这一传统的模式。自第3折开始, 文本围绕章斌如何受聘掌管书记进行。第5折更是游离这才子佳人戏曲模式之外, 详叙章斌如何替秦公子解除学院按临扬州所举行考试的烦恼,也就是这一折,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通过考试展示了章斌作为才子所应具备的吟诗作赋才能,从而将剧本纳入才子佳人戏曲的范畴提供了基本条件,作者用此环节来代替“传诗递简”过程。其次,由于章斌为秦公子排忧解难,秦公子思量“图报答,谢思私,指挥百事凭君志”,为下文秦公子舍身为章斌婚姻之事向秦夫人求情埋下伏笔,作了强有力的铺垫。此外,考试过程中秦公子央人代考之事被人告发,又因他与主考官略叙家门而得以平息,从而增强了剧本起伏曲折的态势。至第6折, 当章斌“特地央(青)奴送写(绣符)先讨个佳缘约定”时,碧莲才“依稀犹记,年少一书生,他两载淹留空系情”,这表明对于素梅来说,两人最初的一见钟情只是萌动了她求一可意之人的心愿, 并未对章斌有着如何牵肠挂肚的思念,更不消说如何进行传诗递简了。在第8 折老夫人的宾白亦可佐证两人关系的生疏,“自从把碧莲交付青奴拘管,果然终日在房中闷坐,不敢半步闲行”,以至碧莲“生憎拂镜,日伤孤影,苦摧残自甘凄冷;水阁波光,凉亭风景,怕行游偏添闷萦。”可见秦夫人管束之严,给两人传诗递简的可能性没有留下任何时空缝隙。文本是如何舍弃“传诗递简”与“幽期密约”2个环节而过渡到“洞房花烛”的结局呢?这就得力于绣符之类信物的绾合与秦公子等人所给予的支持或创造的条件,青木正儿评之:“一以物件维系姻缘事,此派盖出《荆钗记》,至叶宪祖诸作造其极矣。”[1] 这种情况在晚明才子佳人戏曲中屡见不鲜,《灵犀佩》、《鲛绡记》、《钗钏记》等无不以此信物为媒介使得才子佳人得偿宿愿,而类似秦公子式的人物也俯拾即是,如《夭桃纨扇》中刘令公闻知才子与佳人订盟,便智劝才子努力功名以免使佳人有白头之叹,有意识地寻求自主婚姻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间的和谐统一。在第8折中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可怜不得刘郎管, 多少流波衬落花。”他们充当了红娘的角色,对于才子佳人的团圆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一见钟情后,在第3折立即展开“传诗递简”环节:两人于月朗风清的夜晚隔墙吟诗,在进行容貌审美之后旋即展开才能考核;在第2 本中因老夫人赖婚,张生又通过弹奏《凤求凰》来倾诉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通过这高雅举动来互通情愫;红娘受命来探望病情,张生又央其附送简贴,“寄与蒲东窈窕娘”,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迹;莺莺在赖简之后,获悉张生病重,托红娘递送“药方”,至此才走至“幽期密约”环节。剧本在情节推进中反复穿插“传诗递简”达4次之多。也就是从《西厢记》开始, “传诗递简”成为才子佳人戏曲模式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
至嘉靖前期,以郑若庸《玉玦记》为代表的文词派正式形成,“热衷于爱情题材创作,旨在认同风流浪漫文人历史传统,借助于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典雅工丽的文辞实现自我娱乐。”[2] 作者未能考虑人物身份,一味自逞才情,即便是有着些许文化素养的人阅读文本,如不加以阐释,也如堕五里雾中。由于文词派作品“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3],因而招致戏曲理论家的广泛批评。沈德符指责《玉合记》道:“梅禹金《玉合记》最为时所尚,然宾白尽用骈语,饾饤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承《西厢记》之余风,文词派在向重情的创作传统靠拢时,尽管在“传诗递简”环节表现得不那么热衷,但由于刻意追求骈四俪六的形式美感,竟至视传奇为骈赋,乖违音律者甚多,根本不适合舞台演出。即使勉强搬上舞台,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未能产生广泛影响。如何使戏曲文学适合舞台演出,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将戏曲由“案头之曲”引入“场上之曲”,叶宪祖作了积极的探索,减少文本中的曲辞,加大宾白的比重以增强戏剧的叙事性;在语言上将文采与朴淡熔于一炉,力求“音律精严,才情秀爽”。
二
在《丹桂钿合》中,权次卿“叨中探花,官居学士”,“断弦而未续”,集才华与品行于一身,具备礼乐教化中陶冶出来的温文儒雅,“宦情甚淡”,因情僭礼,淡漠功名。徐丹桂“生来一貌倾城,青春无伴苦伶仃,身依慈母畔,矢志守坚贞”,兼具外在美艳容貌与内在慧性才情。尽管两人具备了才子佳人的基本特质, 但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而始终未能进入幽期密约环节。权次卿于月波庵窥见丹桂绝色,愈深思慕,遂假以钿盒冒认白氏侄儿取得合法身份。剧本第3 折中丹桂闻知“表兄从京中远来,今日欲图一会,只得强起梳粧”,按此推理,两人见面后彼此倾慕, 距离“幽期密约”只一步之遥。然而作者别出心裁,有意避免堕入窠臼,让徐母忽得心疼来冲散两人的见面。当权次卿携定神丹入堂问疾时,见丹桂闺门未锁, 欲“闪将进去……,霎时相见诉衷肠,将他搂定休轻放,准备如天色胆强”,无奈“深闺寂寞掩疏窗,一段风情空自狂”,这也只是他自我妄想的念头而已。生旦2 人在徐母房内第一次见面时,基于各自出众的容貌与气质,权次卿认为“越把我情肠牢缚,几时得桂影近嫦娥”,而丹桂也觉得“表兄这般俊雅”,“当不得俊眼偷睃,抽身去么,纵无情怎生抛得情哥”,以至发展到“霎时相傍姻缘大,挽着花枝肯放过”,“且商量琴瑟调和”。试想,如果不是徐母的突然惊醒,2 颗炽热的心早已碰撞在一起了。作者清醒地把握着一条底线,即生旦在“洞房花烛”之前没有任何“幽期密约”的机会。
比较而言,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却频频展示柳梦梅与杜丽娘的幽期密约过程:其一,柳梦梅名字由来,是由于有美人于梅花树下召唤(第2出)。其二, 杜丽娘游春感伤,梦中与柳生相见得以共赴云雨(第10出)。其三,柳生于梅花观展画把玩,“高声低叫,……声音哀楚,动俺心魄”,杜丽娘前来相会(第28出)。在第30、32出亦如此展示两人相约过程,直至36出完成“洞房花烛”环节。应该说, 以上所举关目关于两人相会都可视为“幽期密约”过程, 只是汤显祖不时将具体化的“幽期密约”过程以梦、人鬼相会的形式进行替换,以突出其所倡导的具有超越生死的男女爱情力量,即其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四艳记》中其余3 剧如《夭桃纨扇》由于任夭桃身份的特殊性而可忽略“幽期密约”过程,《素梅玉蟾》中凤来仪与素梅也只一次亲密的接触,然连这也要被突如其来的偶然性因素所冲断。叶宪祖如此执着地删减“传诗递简”与“幽期密约”环节,其目的在于:在无法超越具有“令人魂销肠断”情感力度的《牡丹亭》与《西厢记》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另辟蹊径,但又不屑于令人掩耳不忍闻的文词派创作。李渔在《闲情偶寄·窠臼》中说:“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5] 如何变旧为新,在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爱情题材上作文章?受杂剧体制所限,叶宪祖已敏锐地觉察出此前诸剧在形式上的创新如《四声猿》等,采用合4个故事于一剧的做法。 同时在各剧中均用一道具来连缀故事如玉蟾、钿盒等,使之在戏曲中时隐时现,穿梭自如,这在当时杂剧传奇中已成一时风气,如汤显祖《紫箫记》、《紫钗记》,许自昌《灵犀佩》等。最引人注目的要数4 剧中所采用新奇的情节结构所造就的波澜诡谲的喜剧效果。
三
李渔在《闲情偶寄》关于“变旧为新”中指出:“又须择其可增者增,当改者改,万勿故作知音,强为解事,令观者当场喷饭”。[6] 叶宪祖煞费苦心构置的情节模式是“好事多磨”,这成为晚明才子佳人戏曲的典范之作,产生深远影响。凌濛初《二刻》卷3《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明未张琦的《金钿盒》传奇、磊道人与癯先生合编的《撮盒圆》传奇、傅一臣的《钿盒奇姻》杂剧均与《丹桂钿合》相仿佛。《二刻》卷9《莽儿郎惊散新莺燕龙香女认合玉蟾蜍》、傅一臣《蟾蜍佳偶》亦与《素梅玉蟾》情节类似,有可能以此为各小说戏剧之故事本源。 “好事多磨”是创作主体立足于文本体制,别出心裁设置情境,运用错认、巧合、误会等结构手法,造成情节的起伏曲折,以达到给观众读者可惊可愕的新奇感受。所谓巧合,就是纯粹以偶然性因素促成事件的发生。在戏曲里采用“巧合”手法,《素梅玉蟾》是典型的例证。小生凤来仪瞥见杨素梅“惊若天人”,遂以玉蟾蜍央人寄去以求佳期,素梅亦见凤生“天然俊雅,不觉动情”,在文本第2 折中即许下与之今宵相会,两人自一见钟情发展到幽期密约,接下来的过程则是由巧合所牵引:正当两人卿卿我我把盟设誓之际, 忽有不知趣的窦氏二兄弟破门而入强拉凤生话寂寥,无奈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散我一场惊搅,云笼雨盖,霎时间雾释冰消”。待到东方晓白,凤生醉酒而归,欲与素梅结秦晋之好,却惊讶发现门锁已开,素梅已被前来道贺的龙香接走。面对人去楼空的悲凉景象,凤生呼天抢地哭诉:“天杀的窦二,兀的不害杀我也。天,这段姻缘,小生费尽了千思万想才得成就。一场到手的买卖,平白地拆开去了。”如果没有侍儿龙香偶尔到来的情境,凤生与素梅亦有可能制造既成事实。此后生旦又指望再叙欢悦,把衷情诉说,忽有冯氏到来,因担忧素梅“年纪长成,姻缘未偶,特接你到我家去”,且“今日黄道大吉”,片刻不能停留,即日便将素梅移居异地,使得凤生盼望连朝,杳无音耗。本是速配姻缘,只因各种偶然性因素的介入使两人从此饱受别鹤离鸾之苦, 再续携手洞房之事就无从谈及了。本是各拟双飞的才子佳人,最后却被阴差阳错撮合在一起,“须知天缘宿世,算今朝会合偏奇,好似惊弦宿鸟,竟遂于飞”。只亏那玉蟾有意,巧作良媒,凤生所聘之妻正是素梅,有情人终成眷属。
叶宪祖在有限的篇幅里以巧合来安排叙事,剧情的推进在经历迂回曲折之后往往又“曲终奏雅”,避免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而导致结构散漫的弊病。黄宗羲评叶氏剧作“古淡本色,街谈巷语,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直迫元人,与之上下”[7],对于叶氏戏剧创作成就给予很高评价。受其影响,晚明才子佳人戏曲家在戏剧中普遍采用这种喜剧手法,构成悬念和期待以引起观众的审美注意和审美兴趣。据《康熙浙江通志》载“宪祖长于填词,古淡本色,街谈巷语亦化为神奇,吴炳、袁令昭词家名手,皆从其指授为弟子。”[8] 阮大铖《石巢四种传奇》精于用误会等手法来增强戏曲的戏剧性,如《春灯谜》设置了所谓“十错认”,极尽离奇曲折之能事:“男入女舟,女入男舟,一也;兄娶次女,弟娶长女,二也;以媳为女,三也;以父为岳,四也;以韦女为尹生,五也;以春樱为宇文生,六也;义改李文义,七也;彥改卢更生,八也;兄豁弟之罪案,九也;师以仇为门生,而为媒己女,十也。”[9] 王思任评《春灯谜》云:“文笋斗缝,巧轴转美,石破天来,峰穷境出。”[10] 虽头绪纷繁,但作者能凭其娴熟的叙事技巧使之意趣各异,令人叹为观止。其他剧曲家如范文若之《花筵赚》、袁于令《西楼记》、吴炳《粲花斋五种曲》都能步武叶氏,选择传统的才子佳人题材而不守矩矱,达到“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的境界。据统计,吴炳戏剧中的曲折态势,《绿牡丹》9个,《画中人》、《疗妒羹》各8个,《西园记》、《情邮记》7个,吴梅评《情邮记》云:“吕药庵读此记,比诸武夷山九曲,盖就剧中结构言之。余谓此剧用意,实以剥蕉抽茧,愈转愈隽,不独九曲而已”[11],如此之多的跌宕起伏,使得无论是读者在阅读戏剧文本或观众在观舞台演出都能处于紧张兴奋状态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叶宪祖在借助于叙事操作的灵活性以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娱乐观众的前提下并没有走至媚俗的极端,仍保持其寄寓情爱理想的雅文化品格,达到一种雅与俗的自然融合。相比之下,吕天成《缠夜帐》却以某些观众曾经有过的狭邪经历为题材,极尽其中乐趣。祁彪佳评之为:“以俊僕狎小鬟,生出许多情致,写至刻露之私,无乃伤雅!”其另一剧作《二淫记》“暴二淫之私,乃至使人耻,耻则思惩矣”[12],此种创作初衷与淫秽小说的作者广造舆论为色情小说辨解的行为殊途同归,可以说是吕氏早期从事《绣榻野史》创作对戏剧创作的影响,沈璟在《致鬰蓝生书》云:“二淫记,纵述秽亵,足压五关,似一幅白描春意图。”[13] 戏剧领域的媚俗程度因受体裁所限而终究有限,泛滥成灾的色情小说此刻就不可等量齐观了,“纸之为贵,无翼飞,不胫走”[14],即是描绘当时淫秽小说的出版情况。它专注于生理层面的铺陈,细致入微地描绘当事人肆无忌惮的淫乱,满足于对动物本能的渲染与放纵行为的激赏,如托名唐寅的摭拾流行的小说中有关僧尼淫行内容汇辑为一册的《僧尼孽海》、专叙男性同性恋的《龙阳逸史》。醉西湖心月主人更是接连炮制《宜春香质》与《弁而钗》,在描摹亵状宣泄低级趣味的同时借此以牟取高额利润,而这些小说又往往以劝世讽戒为幌子以争取其在社会上流传的合理性,如《肉蒲团》中第1回所宣称:“凡移风易俗之法”, “要因其势而利寻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自我鼓吹是淫秽小说的惯常作法。 色情小说的传播伤风败俗,危害极大。它“使观者魂摇色夺,毁笥易心,若夫幼男童女,血气未定,见此等词说,必致凿破混沌,抛金躯命,小则灭身,大则灭家。”[15] 此类题材的创作,更助长了晚明社会本已人欲横流的非理性的社会风气,世风之颓丧日益严重。晚明戏曲家乐此不疲地选择才子佳人戏曲题材,通过“旧处翻新,板处做活,真擅巧思而,新人耳目者”的同时又保持其应用雅文化品格。
从文化背景来看,自王守仁肯定戏剧“与古乐意思相近”,强调“今要民俗返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民俗返朴还浮,取令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6] 提倡利用民众所容易接受的通俗文学来进行道德教化。王守仁认识到,与其苦口婆心宣讲较为抽象道德理论,还不如通过敷演可歌可泣的忠臣孝子故事,使观众如临其境,效果立竿见影,从而使通俗戏曲小说的创作有了理论支撑。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进而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17] 针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偏激观点而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显然会得到有着自我意识的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表现在通俗文学创作中,则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贴近百姓日常生活。色情小说着意选取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铺叙,《绣榻野史》篇末有“因此上有好事的,依了他的话儿做了一部通俗小说”之语,即作者是在据实事进行创作。剧曲家首先要考虑的也应该是观众接受问题。风雨飘摇的晚明社会使得创作时事剧容易走向作者自我满腹牢骚的情感渲泄而偏离观众,极尽温柔缠绵的才子佳人剧既投观众所好,亦可使作者逃避烽烟四起的现实而得到慰藉,而大家都去染指的传统题材容易陈陈相因,这就迫使剧曲家在叙事操作上挖空心思以别开新路。
在戏剧领域,才情奇绝的沈璟在昆曲音律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影响深远。其《南九宫谱》、《南词韵选》、《唱曲当知》等戏曲音乐理论著作成为当时剧作家必读的教科书。“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曲,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自谓得沈吏部九宫正音之秘。”在创作实践上,沈璟的早期剧作《红蕖记》有着“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韵,句句有移宫换羽之工”之称。从《埋剑记》开始寻思戏曲语言通俗化的道路,至《博笑记》曲辞宾白就明白如话了。沈璟在戏曲“本色”方面所作的努力得到当时剧曲家的认可,王骥德推崇说:“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滥机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设。”[18] 但由于绌词就律,剧作内容有时就显得过于枯涩无味,“如老教师登场,板眼场处,略无破绽,然不能使人喝彩。”这也为后来追随他的剧作家叶宪祖等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此相关的汤、沈之争的展开引发晚明剧坛的轩然大波,诸多戏曲理论家被卷入漩涡,但他们并未盲目附和汤、沈,而是持中庸调和的态度。剧曲家站在客观的立场审视汤、沈理论主张的优劣得失,进而提出了“合之双美”主张。如吕天成虽为沈璟弟子,然不为一家之见所囿,认为“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硎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乎?”“合之双美”说激起了剧曲家如王骥德、冯梦龙、孟称舜、祁彪佳等人的屡屡回应,从而使晚明戏曲家在创作才子佳人戏剧以娱乐观众的同时又保持其应有的雅文化品格,终究有些才情曲律双美的文人之作如《四艳记》的产生,掀起了才子佳人戏剧在晚明的创作高峰。 总之,叶宪祖《四艳记》通过在“传诗递简”、“幽期密约”环节的缩减与在“好事多磨”过程的增强,有别于《西厢记》的典范模式。它既对文词派填塞学问的创作方式予以摈弃,又与同期的色情文艺创作划清了界限。凭借其在华美的文辞、谐和的音律、灵活的叙事技巧,使得它在才子佳人戏曲创作的转型期中具有突出的典范意义。它的问世,既是作家通过汤、沈之争对戏曲本体论有着较为清晰认识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风尚在戏剧领域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