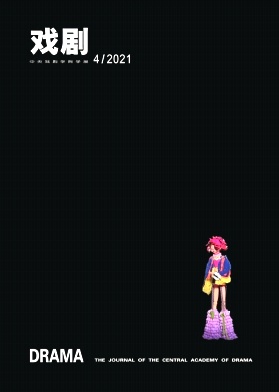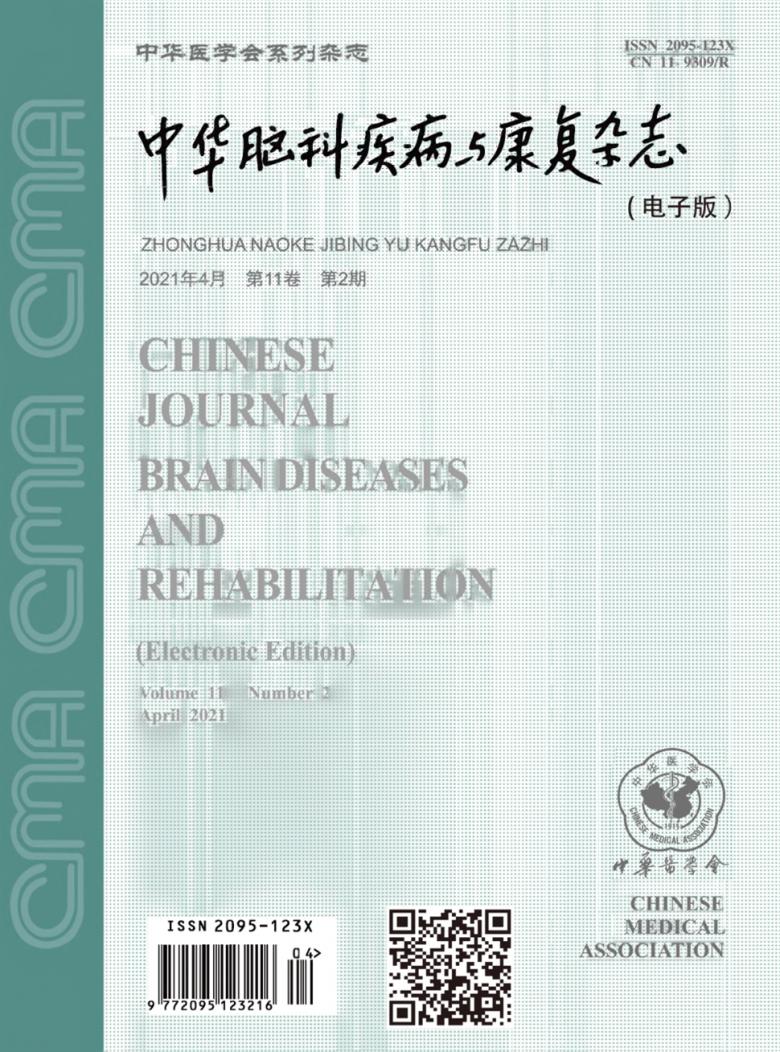唐蕃宗教文化交流
陈崇凯
一、概述
1、初传时期
大体从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止。此期唐朝佛教文化早期输入吐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两位公主远嫁吐蕃时带入;二是派遣使者赴唐求取佛教文献;三是邀请汉僧进入吐蕃译经。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
2、吐蕃佛教创建时期
约指从桑耶寺筹建到剃度蕃人僧人出家时期。此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特点有五:首先是依靠汉人桑喜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作准备;二是命桑喜等卦五台山参观学习汉地寺院形制;三是派塞囊和桑喜赴内地学习佛教教戒,为吐蕃剃度僧人出家作准备;四是请汉地僧人入藏,为译经作准备;五是赤松德赞从学习汉地佛教知识入手,形成在吐蕃正式创建佛教的思想。
3、吐蕃佛教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从赤松德赞中年起,到热巴坚赞普时止。此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特点是:一是发展初期,所请汉地僧人更多《莲花生传》载,当时被迎至吐蕃从事译经等翻译工作的汉人有:帕桑、和尚玛哈热咱、和尚德哇、和尚摩诃衍、汉地学者哈热纳波、和尚玛哈苏扎以及毕洁赞巴。(见该书,本版,146页下)。此外还有汉地学者桑西。二是成果更突出,数量大出现了系统的《丹喀尔目录》,在所译六七百佛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31种。(《丹喀尔目录》日本影印大藏经,卷145、145、146、149页)三是自公元781年后,吐蕃从汉地吸取佛教成果的地点集于敦煌,吐蕃既在敦煌当地充分利用汉藏等族僧人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同时又把汉地佛教和名僧中的精华部分和人物迎入吐蕃。755年以后敦煌所出的禅宗经典和语录,约有二十部左右,诸如《顿悟无生般若颂》《顿悟真宗金刚般卷(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最上乘顿悟法门》等等。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涉及汉藏佛教禅宗交流的一本书,即《顿悟大乘正理诀》,此书大约成书于792__794年,作者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 又称“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他给吐蕃赞普上书时自称“破落外臣”。王锡在敦煌陷于吐蕃后留居敦煌,可能出家或为居士,故自称“破落外臣”。该书详细记载了赞普赤松德赞请敦煌汉僧等三人赴吐蕃辩论佛经之事,其中之一即是王锡。①四是汉地禅宗传入吐蕃,其代表人物就是大禅师摩诃衍那,从而引出吐蕃佛教历史上的“顿渐之诤”。五是在吐蕃佛教发展晚期,出现了敦煌译经讲经的高潮,其突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高僧法成,他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 (法)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18页及附录。
二、文成、金城公主与佛教入藏译经的关系
唐朝佛教同吐蕃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吐蕃佛教的初传、创立和发展均与唐朝佛教有关。黄灏说:“吐蕃多元文化的两个源头--汉地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两者相比较,汉地中原文化影响远比印度文化为深、为早。……文成公主入藏为汉藏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这不仅在《贤者喜宴》及《西藏王统记》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有实物为证。玉树州巴塘乡勒巴沟的寺院及佛像崖刻,昌都乍丫石刻等姑且不论,最生动的体现就是大昭寺供奉至今的释迦牟尼佛像,此圣像是由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的,此像被藏族人民视为“幸福的源泉”,受到藏族人民的话千百年来的顶礼膜拜。藏文史料说,文成公主奉像入藏,历尽艰辛,这一路是传播佛教文化之路,也是释迦佛像为吐蕃人民不断加持之路。整个吐蕃时期,大量的译经今日已无从得见,但此释迦镏金佛像却独存至今,佛光普照,香火不绝。”②
初传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上指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期,是佛教开始传入吐蕃时期。其间,唐朝佛教是其极重要的渠道。
1、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有两件佛教文物:一是释迦牟尼佛像,另是三百六十部佛经,其中释佛像即今日仍供于大昭寺者,是向为藏族人民最为崇拜的佛像。而三百六十部佛经的具体情况则已不可考,然而带去佛经应属可信。
文成公主除带去佛像和佛经外,还传入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规。小昭寺是文成公主设计建造;大昭寺虽系泥婆罗公主具体施工而成,但是寺址的选择勘察及寺院型制的设计,却是出自文成公主之手,对此,藏史多有记载。两寺均留存至今。小昭寺后来成为黄教的下密院。而大昭寺则因内供释迦佛像及其精美的建筑而亨有盛名。据《玛尼宝训》载,文成公主还将汉地之“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传入吐蕃。
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松赞干布聘请汉地大寿天和尚至吐蕃请他和吐蕃人拉拢多吉贝负责翻译汉地佛经,而文成公主则是他们的“施主”。藏史又载,文成公主还亲自参加译经。《玛尼宝训》载,文成公主随松赞干布译经达13年之久,“汉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译师是文成公主本人及拉垄多吉贝……请汉地堪布(摩诃衍那)翻译历算、药物及医疗法等等。松赞干布……赐给每人一升金粉及一个曼陀罗……此后译经持续十三年之久。”①文成公主已会藏语文可信,但能亲自译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文成公主关心和支持翻译汉地佛经一事,则母庸怀疑。
据上可以看出,文成公主对吐蕃早期传入佛教是有特殊贡献的。她的崇佛影响了松赞干布的信仰佛教。进而松赞干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从事佛事,由是汉地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及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有了佛教的萌芽。对此,《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亦有记载:“(文成公主)将六百侍从带至赤面国(按:即吐蕃),此公主极信佛法,大具福德,赤面国王(按:即松赞干布)亦大净信过于先代,广兴正法。”《于阗国教史》亦载:“其时,吐蕃赞普(按:即松赞干布)与唐皇帝成为甥舅(之好),文成公主被圣神赞普(按:即松赞干布)迎娶。公主在吐蕃建大寺院一座,鉴于此因,所有僧侣亦来此地,公主均予以资助,乃于吐蕃广宏大乘佛法。十二年间僧侣与一般俗人均奉行佛教。”上述正是对汉地佛教影响吐蕃的极好概括。
2、金城公主
在吐蕃佛教初传时期,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和墀德祖赞对引进汉地佛教亦有所贡献,虽效果不及文成公主之时,但有其特点,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即“谒佛之供”及“七期祭祀” ②。前者是将文成公主死后藏在大昭寺南门中的汉地释迦佛像迎供于大昭寺,是为拉萨大昭寺朝佛活动之始。后者是关于在吐蕃推行追悼亡臣的佛事。此外,金城公主同文成公主一样,在吐蕃也建造了一座寺院,名为“九顶正慧木屋寺”。但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藏文写卷《于阗教法史》、《于阗授国记》和《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这三个文献在记述墀德祖赞时期一批于阗僧人前来吐蕃地区从事佛教活动的史实中,却均提到了金城公主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对这段史实,敦煌藏文写卷P.T.960《于阗教法史》有如下记载:
最后,于阗圣教毁灭时,上部四座城市之比丘们全都来到于阗会集。此时,于阗人为魔所诱,不信圣教,不敬比丘,且凌辱之,抢劫他们财物,将三宝财物与比丘之粮食,寺庙之土地、奴仆、牲畜等全都抢走。比丘们在于阗无法再安住下去。在此情况下,全体比兵只好出走,汇集在杂尔玛寺庙,商议说:‘于阗之地已无法再住,往何处出走为好?’此时,因吐蕃赞普笃信圣教,敬重比丘,大施供养,于是,一致同意前往吐蕃。当时,……全体比丘从杂尔玛出走,到卓帝尔。在卓帝尔,有一自然形成的地藏菩萨寺庙。其上,有一座不大的小山。此时,自然开裂,从其中得到一升珍珠。乃用它维持了三个月生活。到了春季孟春之月出发,到迈斯噶尔。迈斯噶尔之北方天王与吉祥仙女,化为人身,维持他们春季三个月生活。后来,剩下的财物全部用完,初夏四月到了吐蕃。及至此时,有许多僧人还俗,有许多人在路上饿死。正在这时,吐蕃赞普和汉地君王结成甥舅,文成公主降嫁吐蕃赞普。公主在吐蕃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寺庙,给寺庙献上土地与奴隶、牲畜。全体比丘来到这里,生活均由公主供养,吐蕃之地大乘教法更加宏扬光大。十二年之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幸福。正在那时,由于群魔侵扰,带来黑痘等各种疾病。文成公主由于沾染黑痘之症,痘毒攻心而死。于是,俗人们对佛教顿起疑心,云:‘黑痘等各种疾病流行是由于比丘僧团来到吐蕃的报应。’谓‘不能让一个比丘留在吐蕃。’要把他们赶回各自住地。于是,全体比丘只好来到印度犍陀罗①。
在以上引文中,译者将原文中的“汉公主”(rgya—kong—jo)译为“文成公主”。事实上,从这段史实的背景及有关记载来看,文中的“汉公主”实际应是指金城公主。因为文中明确提到于阗僧人逃往吐蕃之时,“吐蕃赞普和汉地君王甥舅”。唐、蕃虽两度联姻,但唐蕃以“甥舅”(dbon-zhang)相称却是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后方才出现的。在金城公主入藏以前唐蕃间未见有“甥舅”相称的记载。从此迹象看,文中的汉公主实应为金城公主。关于此点,尚可从《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中的记载得到证实:
于阗国也被纳入吐蕃国王统治之下。这以后,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此时,于阗国之佛教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王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王报告,此赭面国王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并问:“还有比丘吗?”比丘之堪布说:“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还有许多比丘。”于是王妃将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请来,安置在寺庙之中,很好地供养了三四年。此时,公主染上痘症去世,其它人也病死很多。吐蕃的大臣们商议后说:这是因为召请这些蛮邦游方比丘而得到的报应。’把他们和请他们来的汉人僧侣统统向西方驱赶②。
以上引文明确记载于阗僧人逃往吐蕃并获得供养的时间是“在赭面国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以松赞干布算起,墀德祖赞应为吐蕃的第五代赞普。若以后弘期藏文史籍所载的佛教传入之始的拉脱脱日年赞算起,墀德祖赞则应为第十任赞普。这显然与《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所说“赭面国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均不相吻合。这是否为记载之误,抑或是于阗僧人对吐蕃国的无知而造成的错误,目前尚难以确定。不过从上文所载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而不是第一代国王之时,我们已大体可推知文中所言的汉地公主,显然应是指金城公主。
② 黄灏《吐蕃文化略述》,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① 《玛尼宝训》第282页下,转自黄灏《贤者喜宴》择译注(二)注15)。
② 《贤者喜宴》,第七卷,71页上至72页下。
① 《西藏王臣记》,北京第1957年排印本,第67页。
② 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60页。 三、墀德祖赞、墀松德赞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1、墀德祖赞派人求取汉地佛经
他是派吐蕃使者亲卦汉地取经的首创者,他派以汉人之子桑希为首的四名吐蕃使者亲赴唐长安,向皇帝请赐佛经,唐皇将用金液写在瓷青纸上的佛经一千部,赐给桑希等人。如果“一千部佛经”属实,应是汉经输入吐蕃最多的一次。此后,汉地佛经《金光明经》及《律差别论》之传入吐蕃亦始于此时。
盖言之,在吐蕃佛教初传时期,汉地佛教中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营造、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虽远不及桑耶寺建成之后那样,但对吐蕃社会中出现佛教来说,汉地佛教无疑起了重大影响,并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地佛教紧密相关。
2、墀松德赞派桑希等入唐求取汉经
吐蕃佛教创建时期。这一时期约指从桑耶寺筹建到剃度僧人出家之际主要是墀松德赞执政时期。这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特点有五,首先依靠汉人桑希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做准备。其次,命桑希等赴内地五台山,参观学习汉地寺院型制,为建桑耶寺做准备。第三,派拔赛囊及桑希赴内地学习佛教教诫,为吐蕃剃度僧人做准备。第四,请汉僧入藏为有计划地翻译汉经做准备。第五,墀松德赞从学习汉地佛教知识入手,并萌发和坚信佛教,进而形成在吐蕃正式创建佛教的思想。
上述五项特点,是在吐蕃佛教创立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突出表现。
墀松德赞信佛思想的形成是因直接受汉人和汉地佛教的影响。此赞普自幼就有两位汉人相伴随,此即贾珠嘎勘①及桑希。贾珠嘎勘和桑希均先后给墀松德赞讲过汉地之《十善经》,②赞普“甚喜”。桑希还特为赞普讲读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和《佛说稻竿经》,赞普因之“生起大信心,由是笃信佛法”③。此后,墀松德赞继其父之志,又派桑希等吐蕃使者赴内地,他们此次完成两项重大任务,即参观五台山寺院,将寺院型制“铭记在心,奉为楷模”④。这是吐蕃人首次访五台山,成为824年吐蕃向唐“求五台山图”之先导⑤。另一任务是见到了汉僧金和尚,并从汉僧处获得汉经三部⑥。墀松德赞了解了汉经内容之后,随即不顾有人反对,着令请来的汉僧梅果、印僧阿年达及精通汉语的吐蕃人翻译这些汉文佛经⑦。此外,为了学得汉地佛教有关教诫之规,墀松德赞又派阐藏热、拔赛囊及桑希等30人的大型使团赴内地,他们在唐皇的支持下,从汉僧学得了“修行教诫”。并得到唐皇所赐汉纸100秤。
总的看,在桑耶寺建成前,吐蕃从汉地得到了上述五种佛教知识和实物,为桑耶寺筹建和此后之正式创建佛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一切,均源于墀松德赞从汉地佛教中所生起的崇佛之坚定信念。
3、桑希等赴唐地求取“十善法”及金字佛经入藏的经过
据《贤者喜宴》和《拔协》记载,桑希一行被墀德祖赞派往汉地求取佛经,他们顺利抵达长安,曾受到唐朝皇帝的接见,被赐予佛经千部和大量礼物。此后桑希一行返藏时途经一个名叫埃曲(grong-khyed-aeg-chu)的城市,遇见了一位名叫金吉雅的颇具神通的汉地和尚,又从金和尚那里得到关于如何“修行经教的教导”和三部佛经。此时,桑希等人已得知赞普墀德祖赞薨逝和反佛大臣禁佛的消息,并向金和尚寻求了指点。此外,还记载桑希等人曾到唐地代县之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并取得了文殊菩萨佛殿之图样。当桑希一行返回吐蕃时,由于反佛大臣掌政和实施禁佛,而墀松德赞尚未成年,故只好将从内地取来的佛经藏到了秦浦(mchims-phu)的岩洞中。但《布顿佛教史》称,桑希返藏时还带回一汉地和尚,因当时吐蕃禁佛,汉地和尚遂返回①。从这一情节看,桑希一行显然应是在返回后才知道禁佛的,故这与《贤者喜宴》、《拔协》、中关于其从金和尚口中得知禁佛的记载不合。
下面择引《拔协》中关于桑希汉地求取佛经的经过②:
(金城公主卯年生的)王子四岁时,住在翁布园宫中。这时唐朝皇帝派使臣马窦给国王献厚礼。使臣有个孩子叫甲楚噶堪的,献给王子做游伴。桑喜“的父亲是唐朝皇帝派往吐蕃向赞普献礼的使臣,名叫巴都,后来在吐蕃安了家。”
(有一次甲楚噶堪在陪王子游玩时,发现一些红虫子要杀死),甲楚说:“中原有部叫《乎儿加》的经典说,如果杀死这些虫子,是极大的罪孽。”王子问道:“《乎儿加经》里都说些什幺了?”甲楚噶堪桑喜对王子说:“《乎儿加经》里说的是十善法。”以后,他们便经常谈论十善法的事,大家听见了,都愿意修行此法。由于王子说:喜欢十善佛法,国王便派桑喜和另外四人作为使臣携带信函,到中原去求取汉族经典,并对他们说:“如果遵令完成使命,定当重赏;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杀头!”
于是,使臣等五人启程前往中原……(唐朝)皇帝马上派使者前去迎接,……吐蕃的五位使臣向卜者所说的一样如期到来,汉族和尚向他们敬礼后,遵照皇帝吩咐,把他们打法到皇帝驾前……使者向皇帝献上吐蕃赞普的信函。皇帝收下信函,看后答应按信中所请办理。之后,对桑喜说:“你本是汉人马窦的孩子,留在这里做我的内臣不好吗?”桑喜听了心想:我如果留在内地,今生虽然快活,但是,为了能在吐蕃传扬妙善佛法,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哪怕是一本佛教经书献到赞普手中。然后,再想法禀告赞普,返回中原。想毕禀道:“圣上赐我留在中原,我不胜感恩之至。但是,吐蕃赞普对我们下了严厉的命令,我如果不回去,父亲会因此被处死刑,那我会悲痛欲绝的。因此,还是请圣上开恩,让我返回吐蕃,和父亲商量后,再设法前来做陛下的臣属。”皇帝说:“我心中最喜爱你,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提出来!”使臣桑喜禀道:“若蒙赏赐,就请赐给一千部佛经。”皇帝说道:“你到(中原)达格吾柳隘口时,没有遇到扰害,反而受到敬奉,(我的)大臣布桑旺保(的卜者)说,‘你是菩提萨垂的化身’,有先知神通的和尚也向你敬礼;佛在授记中预言:‘在最后500年的浊世间,在红脸人的地区,将出现一个首倡宏扬佛法的善知识’。从你的高尚德行来看,佛的授记,定然指你无疑。让我来帮助你实现志愿吧!”于是,赏赐了一千部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还格外赐给了许多其它物品。
五位使者返回吐蕃……的途中,有一附着精灵的巨石挡路……在巨石附近的艾久镇里,有一个叫尼玛的和尚。他从肩胫到胸前套上绊胸索带在修行。他被委派当堪布,把巨石弄碎,并在该地修了一座寺庙。
这时,五位使者到来,向他学得修习的经教并问和尚道:“我还能和父亲相见吗?最后吐蕃能弘扬佛法吗?如果在吐蕃传扬佛法,吐蕃鬼神不会危害我的生命吗?赞普父子平安吗?”和尚以其先知神通观察后,答道:“赞普已经去世,王子尚未成年,信奉黑业(指反对佛教,信奉苯波教)的大臣们掌权,制定了反对佛教的‘布琼’法典,发起灭法,从跟儿拆毁了扎玛的真桑本尊佛堂。你回吐蕃后,要好好地侍奉王子。等王子成年后,他会和你谈起各种外道教法,那时,你可趁机向他宣讲我给你的这本经书,王子便会产生信仰。最后,你对他宣讲我给你的这第二本佛经,他的信仰会更加虔诚。最后,你对他宣讲这第三本佛经,王子便会决心推行佛法了。”说完,赠给桑喜三卷佛教经典。又说:“吐蕃是有佛法缘分的,最终教法定会昌盛兴隆。……”
桑喜听和尚说真桑佛堂被拆毁了,心理非常难过。为了将来重修佛寺,五位使臣便到五台山圣文殊菩萨的佛殿去求取图样。这座佛殿修建在山顶上……最后,只剩桑喜一人进入佛殿中。他向圣文殊菩萨等佛像行了礼,取了图样,……(桑喜将五台山寺院形制)铭记在心,奉为楷模.……五位使臣便返回了吐蕃。①
赛囊(被反佛势力逼迫避居到芒域)走后不久,桑喜一行五人完成了去内地的使命,回到了吐蕃。这时王子尚未成年,(反佛大臣掌政,不准传扬佛法,)桑喜只好把从内地取来的佛经藏到钦朴岩山的石洞中。
过了一段时间,王子长大成年,看到了父祖留下的文书,便和尚伦谈论说:“我父祖在文书中说:如果要使臣民安乐,须按汉地的《柳采姜》行事。照今天情况看,我父祖所说,好象是错误的。”大臣们问道:“父祖们对汉地的《柳采姜》是怎幺说的?”于是赞普让文书甲·梅果读了《柳采姜》一书。读完,赞普说:“从文书中看,我的父祖辈认为佛法是好的。”桑喜听了赞普的话后,心想:看来世间要出现善行了,汉族吉木和尚预言的该向国王说佛法的时机到了。想罢,对国王说:“若有汉地的佛法,父祖辈所说的《柳采姜》便显得不对而无用了。”赞普问道“那幺,你有没有汉地的妙善佛法的经典啊?”答道:“我去过汉地,所以有佛教经典。”于是从钦朴的岩山石洞中取出佛经,照吉木和尚的指点,首先对赞普宣读了《十善法经》。王子听后,对之产生了信仰。然后又宣讲《金刚经》,王子听后,产生了更大的信仰。最后,又宣讲了《佛说稻秆经》。王子听后,领悟到首先要正行,第二要有正见,最后要见行双修,于是坚信佛法,说道:“在我活着的时代,能得到这幺佳妙的佛法,实在是大地的慈悲,上天的慈悲!要向一切神献供养!赛囊曾对我说:‘不倡行佛法是不行的。’此话确实不错。我要赐给赛囊‘万’字白银章饰(告身)和大黄金章饰(告身);赐给桑喜你嵌花‘万’字章饰(告身)和小黄金章饰(告身)。现在你和甲·梅果、印度的阿难陀以及所有的学者,一起来翻译从内地和芒域取来的佛经吧!”桑喜遵命和梅果等三人便在亥保山的岩洞中开始翻译佛经。
后因反佛大臣达诺与尚·玛降的反对,国王与“大臣们商定,先派桑喜到象雄的窘隆地方去取‘魔洞宝藏。’”
为了学得汉地佛教有关教诫之规,赤松德赞又派阐臧热、拔塞囊及桑喜等三十人的大型使团赴内地,在唐皇帝的支持下,从汉僧学得了“修行教诫”。并得到唐皇所赐汉纸一百秤。
……执政的母舅尚·玛降冲巴解说道:“国王所以短命而死,都是奉行佛法的报应,实在不吉祥。佛法说来世可以转生,乃是骗人的谎言。为了消除今日灾难,应该信奉苯波教。谁若再行佛法,定将他孤零零地一个人流放到边荒地区去!从今以后,除苯波教外,一律不准信封洽谈教派。小招(9页)寺的释伽牟尼佛像是汉地的佛像,要送回汉地去!”说完,便命人将佛像套在用皮绳编制的网里拖到寺门口,再命三百人拉走。到了卡扎洞地方,怎幺也拉不动了,只好就地埋进沙坑里。拉萨一个管理佛像和经塔的庙祝老者(或称香灯师),是汉地和尚,也被驱逐回汉地。他走时,把一只靴子落(音注)在吐蕃了。他说:“这预兆着吐蕃佛法还会向星星之火一样,迅速燃烧兴旺起来!”
(此后吐蕃陷入黑暗),于是属民百姓和占卜者都说:“这是因为汉地的释迦牟尼佛像发怒”,又将佛像从坑中拉出,用两头骡子驮着送到芒域去了。
玛降死后,王臣又集合商议兴佛的事情。尚·聂桑禀道:“祖辈松赞干布倡兴佛法而国泰民安。他的圣裔、赞普您的父王赤德祖赞也奉行妙善佛法,后来遭到玛降破坏。……如今应该把那尊从汉地的佛像再从芒域请回来供奉。”……国王下令道:“……现在要把汉地的佛像再从芒域请回来供奉,我也要奉行佛法。大家看行吗?”大家一致同意倡兴佛法。
……随后,赞普又委任拔·赛囊为司库并派他的做特使(二次)赴汉地取经,并且说定,如果完成使命,便赐给他的长子以超等的大银字章饰(告身);还委任章·甲安诺勒思为取经的理财官,桑喜为总领,加上其它随员组成30人的取经使团跟随赛囊一起前往。……塞囊和桑喜晋见皇帝致敬礼,因为是唐皇派绸篷车迎来,汉人呼其为‘达尔康(意即绸屋)’。
塞囊要唐皇派和尚赴藏讲经…皇帝向赞普赐一万匹绸料,赐塞囊一只百两重的金翅鸟,十串蚕豆大的珍珠串,五百匹绸料。
……(取经使团)快到皇宫时,让其它人员留在一处,只请赛囊和桑喜二使者晋见皇帝致敬礼。……皇帝对赛囊说:“……汉族占卜者说要来菩萨化身的使者,画的和你一模一样。你是马鸣菩萨的化身吧!你想要什幺都赏赐给你。”赛囊说:“……无论如何请恩赐一位和尚,我们要向他学习经教。”皇帝准予所请,派塞等少数人骑马前去,并召来艾久城的和尚教他们佛法。在赛囊学了经教潜心修习期间,皇帝赐予赛囊一只百两重的金翅鸟、十串蚕豆大的珍珠串、五百匹绸料、一疋白泽汗锦缎等奖赏。
(赛囊将阿杂诺雅再次请回吐蕃后),大家商量说:“请大师住在哪儿好?”桑喜说:“暂时先修一所简单的住处吧!”于是在扎玛尔的真桑寺附近修了一处没有门的住所。住所里面的佛堂是照汉地五台山寺庙图样修造的。修好了,便请大师住在那里。
4、修建桑耶寺及翻译四地经书
桑耶寺之建亦与汉地佛教有关。寺址曾经流地卜算师所选定。而三层楼式之寺院主殿,其中层则系仿汉式建筑,中殿所塑之燃灯佛等九尊佛像亦为汉式。壁画中之喜吉祥及忿怒金刚二神像,亦以汉语“金刚”命名。寺中还建有专为汉僧参禅之用的“禅定菩提洲殿”及汉经译场妙吉祥注洲佛殿。此外,还有储藏汉经的专用经库。
桑耶寺的竣工是吐蕃在创建佛教中迈出的重大一步。继之就是剃度僧人出家,据载,最早出家的7人之中就有汉人桑希,也有的藏史说,不是桑希而是桑希之子热丹①。总之,首批出家的人中有汉人。这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第三件事就是大规模译经,首先翻译的就是汉地佛经②。负责译汉经的是汉藏两族僧人,即汉和尚玛果莱及藏译师阐卡莱贡、拉隆禄恭及琼波孜孜③。这里将翻译汉地佛经放在首位,再一次证明汉地佛教在吐蕃佛教中极受重视。所译佛经均专藏于寺中之汉经经库之中,据《五部遗教》载,藏有汉僧摩托车诃衍所译的经有12箱之多④。文中之摩诃衍,在《红史》中又被称为“和尚摩诃衍”,这人是当时被迎到吐蕃 的十二轨范师之一,似与“顿渐之诤”时的摩诃衍同名同人。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从佛教意义来说,吐蕃此时有了正规寺院,内有出家僧人和佛经、佛像,从此吐蕃创建了自己的佛教系统,可谓吐蕃佛教已初具规模。其间汉僧为此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①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3页下。“巴德武”即“汉人德武”。
② 《拔协》,第14至15页。又见《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8页上至第79页上。又此三部佛经,据载是汉地尼玛和尚所赠。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91页。
③ 同上。
④ 《拔协》,第8页。
⑤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20页。
⑥ 《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⑦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8页上至第79页上。
① 佟锦华等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正文第5页。
② 以下均择自佟锦华等译,《拔协》一书,不再一一注明。
① 注:唐穆宗长庆四年(842),“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页20)五台山自吐蕃起直至清季,向为藏族僧侣所敬仰,朝山拜佛者络绎不绝,赤松德赞时之吐蕃大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率两名弟访五台山,取得汉地医书而归。《老玉妥·云丹贡布传》120页上转引自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四)注66。
① 《五部遗教》第二函,31页上至31页下。
② 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27页,《西藏王统记》204页。
③ 《贤者喜宴》,第七卷,105页上至105页下。
④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05页上。 四、汉藏佛教的“顿渐之诤”
1、入蕃汉僧概况
吐蕃佛教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主要指从墀松德赞中年起,至热巴坚赞普时止。这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特点是,首先在发展初期阶段,从规模上看,所请汉地僧人更多。而成果更突出,出现了著名的包括许多汉经在内的《丹喀尔目录》。其次,自公元781年后,吐蕃从汉地吸取佛教成果的地点转而集中于敦煌,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敦煌几乎成了吐蕃佛教在东方的中心。吐蕃既在敦煌当地充分利用汉藏等族僧人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同时又把汉地佛教和名僧中的精华部分和名人迎入吐蕃,从而也就显示出此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第三个特点,即汉地禅宗传入吐蕃,其代表人物就是汉地大禅师摩诃衍,并引出吐蕃佛教史上的“顿渐之诤”。第四点,在吐蕃佛教的发展晚期,则出现了敦煌译经讲经高潮,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吐蕃高僧法成,他为汉藏佛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时入藏汉僧很多。公元781年,“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计时得,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①。《莲花生传》载,入吐蕃的译经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哇、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②。当时能精通汉藏语文的汉藏族僧人已相当多。这时所译佛经相当系统,数量也大,大部分可从《丹喀尔目录》的佛经目录中看出,在所译六、七百佛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三十二种③。
2、摩诃衍与汉地禅宗入藏
公元781吐蕃占领敦煌,此后“时近百年”,经吐蕃经营,敦煌佛教的大为发展,其间有大量的汉族僧尼与藏族僧人一起从事译经、讲经、听经等等佛事活动。此时汉地禅宗影响最大。
河陇地区佛教界,汉地禅宗有很大势力和影响。敦煌所出755年以后的禅宗经典和语录,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些经典大约有二十部左右,诸如《顿悟无生般若颂》、《顿悟真宗金刚般卷(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大乘开心显性顿悟法门真宗论》及《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最上乘顿悟法门》等等④。
这里应特别提到敦煌所出的一部涉及汉藏佛教禅宗交流的书,此书即《顿悟大乘正理诀》,此书大约成书于公元792—794年,作者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又称“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他给吐蕃赞普上书时又自称“破落外臣”,王锡在敦煌陷于吐蕃后即留居敦煌,此后可能出了家或为居士,故自称“外臣”。该书详载吐蕃赞普墀松德赞请敦煌“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赴吐蕃辩论佛经事,三人之一即是王锡。王锡将摩诃衍吐蕃之行记在他写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此书成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
吐蕃赞普正式延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入蕃,说明摩诃衍已是一位敦煌高僧,也是吐蕃赞普对他的敬重。摩诃衍等三人赴吐蕃,从此汉地禅宗和禅学开始传入吐蕃佛教界,成为吐蕃佛教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在我国佛教的禅宗史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摩诃衍(即大乘和尚)是将汉地禅学传入吐蕃的第一位僧人。他入藏的时间稍晚于神会(668—760,慧能弟子)弘扬顿悟派的时间。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 使者请唐朝派汉僧入蕃传法,“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行,二岁一更之。”①或许摩诃衍那就是此时从沙、瓜州请行吐蕃东部的。伯希和所藏吐蕃经卷中载:“原沙门摩诃衍言,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②而沙州于781年陷落,摩诃衍那当于此年抵达拉萨,后在拉萨、山南札玛一带传教。此前吐蕃尚不解禅宗,正如王锡所记,当时吐蕃正处于“禅宗莫测”的阶段,摩诃衍赴吐蕃传教,吐蕃始有禅宗流传,而且影响很大,传播极速,信徒颇众,连吐蕃王后也信从其教。《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卢氏一自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朗惑珠于情田,洞禅宗于定水……。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法大乘,皆一时出家矣”。《布顿佛教史》也说:“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所云,并学其道”,“汉地和尚摩诃衍之门徒广为发展。”由于吐蕃众僧多学摩诃衍的禅宗之道,致使桑耶寺都断绝了香火供养。足见汉地禅宗影响吐蕃佛教界及世俗之深广。为此,摩诃衍那还写了《禅眼论》、《禅答》、《现之面》、《百十部经源》等著作,以至于使印度佛教在吐蕃每况愈下,木才发了顿渐之诤。
3、顿渐之争
在藏族宗教发展历史上,顿渐之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渐门巴和顿门巴是个汉藏语复合词。渐门、顿门是汉语,“巴”是藏语,可理解为“派”。顿悟是汉传佛教禅宗慧能泊的中心思想。“禅”是观的意思,观的方法,称为禅法。禅宗又分南北两派,慧能所传为南派。主传方便法门(即五方便道),强调“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越三世”,以心为法身,即宽大无边,若以本意可超越三世,勿须渐积,一念即可实现,强调顿悟。
当时同在吐蕃传教的,还有“五天竺国”(印度)的“婆罗门僧三十人”,婆罗门僧主传莲花戒。在禅宗广为传播的情况下,莲花式学说难以推行。他们想借助赞普的力量制止禅宗流传,莲花戒僧人“奏言,流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而摩诃衍则提出“与小乘论议,商确是非”。于是双方展开辩论,这就是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诤”,即“顿门”与“渐门”的一次大辩论。
据藏史载,双方都做了辩论准备,摩诃衍等及其追随者约300人,在特为汉僧参禅用的桑耶寺禅定洲殿准备辩论,摩诃衍为此写了《修禅定可卧轮》、《修定者参禅问答》及《再答》、《论证见解之表象》、《引经为证八十经藏缘起》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概貌可见于《顿悟大乘正决》的后半部③。莲花戒僧也写了四部著作,即《修》初分、中分和末分三部以及《瑜伽恭修造诣》④,西藏大藏经留存下了这些著作。辨论“以月击年,搜索经义”,结果“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词穷”,败于禅宗。但印度僧人“遂复眩惑大臣,谋结用党”,企图借助某些大臣的强大政治压力来压服禅宗。因而奉信禅宗的一些吐蕃僧人被迫“为法捐躯”,“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皆深悟真理,同词面奏曰,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堑”①。可见吐蕃僧众信奉禅法,志坚不移。公元794年左右,吐蕃赞普“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②。这标志着汉僧摩诃衍在吐蕃传播禅宗的巨大胜利。
关于“顿渐之诤”,藏文亦有多种记载,如《贤者喜宴》和《拔协》等等,说法与《顿悟大乘正理决》不一。藏文记载,说摩诃衍辩论失败,返回汉地。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顿渐之诤后,摩诃衍虽然离开了西藏,但顿门巴的思想并没有随之而走,主要影响到后来年宁玛,噶举等藏传佛教的教派。藏文《五部遗教》中的《大臣遗教》记载“顿渐之诤”最详,而且主要记载摩诃衍派的辩论发言,其中有汉地禅师26人,藏族禅宗堪布及译师21人,他们的辩词具体而生动;其中也记载了渐门派的发言,并有摩诃衍的答辩。总之,这些都是罕见的有关“顿渐之诤”的珍贵文献。
4、法成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吐蕃名僧“法成”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法成”是他自己用的汉译名,其藏名音译为“桂·却楚”。
法盛大师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和佛学。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记载,他生活在公元833—859年左右。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是他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最大功业。他的这些译作留传至今,有些分别收在汉藏文两种大藏经中;其中有些汉文佛经已经丢失,不过这些佛经的法成藏译本却保存下来,而早期藏文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某些佛经,法成将其由汉文译为藏文,并收入藏文大藏经以得以存世,其功非小。
法成事绩无正史可考,只能从敦煌文献的某佛经题记和署名中知其略史。公元848年,吐蕃 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此前法成在敦煌佛经的汉文题记或署名中,他常自署名“大蕃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③,此后他的自署名则为“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④。此外有时也简署名为“沙门法成”⑤。法成在河西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沙州和甘州,时间在公元833年至859年。
法成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以及张掖县译经和集录佛经、讲经。他精通汉语文,他讲经时,许多汉僧诸如明照、法镜等等均耳聆笔录。他的佛经译着有藏译汉佛经和汉译藏佛经,此外,他还有讲经记录和他的佛经集录,总计有23部之多,恕不赘述。法成还对吐蕃在河西的汉译藏的佛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1978年以来,我国对现存敦煌所藏佛经进行了深入的事理研究,发现有大量的汉译藏佛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类手书经卷有三百多卷,其中有法成署名校勘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就有二十余处①。这反映法成在汉藏译经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的学者考证,敦煌文献中的《瑜迦论汉藏对照词汇》似即法成讲授《瑜迦师地论》时的词汇集。此外,还有《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伯字1257号汉藏对照佛学词汇》等汉藏对照词汇,这些都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旁证。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方面的交往,从佛教文化交流来说,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来说,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所共有,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族佛教文化的发展,无疑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份。自然,但是佛教在汉藏两族各自的文化发展以及汉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有益作用也是客观的历史潮流存在,不容低估。
①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页12。
② 《莲花生传》,108页上。
③ 《丹喀尔目录》日本影印西藏大藏经,卷145,146页,149页
④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之《敦煌写本的佛经》,第305至306页。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八0。
② 《伯希和劫经录》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③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14至116页。
④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①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② 《大臣遗教》,第20页上至第26页上。
③ 见《萨婆多宗五事论》伯字2073号。
④ 见《瑜伽论》,斯5309号,又见《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伯字136号。
⑤ 见《诸星母陀罗尼经》,斯1287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论文出庥》;《新编汉文大藏经总目》。
①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第59页,第61页。载1978年12月《文物》,又见作者之《河西吐蕃 经卷目录跋》第58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集;《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第88页,第99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1期。 五、道教与苯教文化的交流
1、苯教教祖辛绕与道教老君的关系
苯教教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三种说法:(1)出生在4000年前的大食(伊朗)俄莫隆仁;(2)出生时间与释迦牟尼同时代,出生地在象雄的俄莫隆仁,现在阿里札达县也确有一个俄莫隆乡;(3)“辛绕”是创造古藏文“达巴夭字”的始祖,降生在今阿坝州金川县巴底乡的“琼布”地方,该地有大片平坝叫“卧莫隆仁”,苯教祭坛遗址尚存。此外,有的人说他出生于吐蕃第八代赞普时期。这样就出现了大食、象雄、嘉绒三个均称作“俄莫隆仁”是象雄语,意思是“九朵莲花瓣”,这与老君生下来后脚采九朵莲花的传说,极为相似。“老君”从其母右胁下生出;辛绕从其母右胁用雍仲凿穿而出。联想到道教的祖师有“人老君”与“神老君”之说,苯教的祖师辛绕是否也有“人辛绕”和“神辛绕”之说呢?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后,苯佛斗争十分激烈。唐朝开国之初,道教处于十分优崇的地位,道教与苯教同时产生于各自地方的原始巫术,互相已有了长期的交流。吐蕃的苯教徒为了同传入的佛教作斗争,为了抬高苯教的地位,把“神老君”的一些神话移到“辛绕”身上。“辛绕”与“老君”不是一个人,而“神辛绕”和“神辛绕”与“人老君”的传说,倒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正表明后期苯教中有某些道教文化的影子。
2、对苯教师称“神仙”的探索
正如大家所知,“和尚求佛,道士求仙”的说法已沿习很久。道教又称神仙教,道士是追求成为“神仙”。苯教把学完苯教经律的苯教师称为“神仙”(帐松),直到现在仍然如此。“神仙”一词不见于早期“原始苯”的称谓,也不见于佛教徒的追求。苯教师称为“帐松”,正是道士求仙的说法。法国学者石泰安所著《西藏的文明》载:“吐蕃聂赤赞普后,……出现了‘神仙宗教’就是苯教”。这表明当时苯教中出现了一派追求成为“神仙”的。笨教经书《九乘》和第六乘,是专门讲“神仙乘”的。英国藏学者施耐尔格鲁夫在所着《苯教九乘导论》中说:“苯教徒使用‘仙人’一词是指受过全部戒律的人。这一乘所讲的戒律的整个精神是佛教的,但其中许多纲目甚至某些成条的素材显然不是佛教的。”既然不是佛教的,而早期“原始苯”也没有这种说法,这些内容正是当时苯教吸收了道教求仙戒条时,正是道教的教理。
《土观宗派源流》指出的汉语对贤人称为‘神仙’的‘仙’字,(可能)藏人错讹遂呼为‘辛’的说法,就容易理解了。藏文的“辛”除了诠释为“辛绕”和“辛氏族”外,再未见到有其它单独的字意解释。若半此字与其它字组词,则成了一种仪轨,或从事这种仪轨的有一定地位的人。“辛”同“苯”,既有同义的方面,也有区别。如“度辛”超度亡录的苯教师;“楚辛”本仪轨的苯教师;“色辛”殡葬仪轨的苯教师;“朗辛”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具有“神仙”的“仙”的意思,也许就是汉语“仙”的译音。
3、对藏文史籍中“价苯”就是“道士”的探索
噶尔美《苯教史(嘉言至宝)》一书引自《汉玛》说:“永恒苯教的太阳发出光芒。因为(这地方)被知识渊博的导师的光芒所充满,他们就是所谓学术世界的六位异人,即大食学者察托拉海,知识的五个分支,他都精通;拉达克学者阿卓,他粗通公开传授的知识;汉地的学者来当芒布,他精通秘传的知道……”。该书又引用《什续》说:“白乃古、高昌苯徒钦·白秀札木和价苯来当芒布”,这里的“价苯未当芒布”无疑就是指道教的道士。这两段文章还说明以下问题:(1)高昌是8世纪前西域四镇中一个小邦的国名。这里指的汉地是指当时吐蕃占领的河、陇地方和西域四镇的时期;(2)藏族把道教和道士称为“苯波”,至少在公元8世纪就开始了;(3)这位道士来当芒布传授的知识是秘传的知识,即道教在占卜、祈福、禳灾、镇邪、祭祀中的一些秘密仪轨。道教的部分教理、仪轨至少是这一时期为苯教徒所吸收。
《土观宗派源流》说:“苯教”其见解行持与诸乘的教理,是按照总摄苯教八万四千法门的《密咒关隘日庄严论》中所写的。此论是大食、汉地、天竺及藏地等众多成道大德在芒喀秘密苯窟中聚会时纂集的。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及芒喀在今何地?尚不清楚。但这段话表明苯教的见解、仪轨和“九乘”等教理,是在有汉地的成道大德(有名的道士)参与下纂集的。
4、关于藏文史籍中“天师”一词的探索
《奈巴班智达教法史》载:“印度班智达李敬受于阗尼天师和吐火罗译师罗生措的邀请前往汉地传教。”于阗,藏文称为尼域“天师”是道教中高层道士的尊称。正如前面所述,道教徒称其创立人张道临为张天师。这里所说的尼天师可能是当时于阗地方道教的高层人士。这表明公元4世纪前于阗地方已有了道教。当时于阗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信道上,中原的巫文化和道教文化也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商队传入了于阗地方。于阗与象雄的关系密切,道教文化也会波及到象雄。公元631年大羊同国部落(即象雄)遣使与唐通好。当时于阗也传入了佛教。正如前面所述,中原地方有一段时期曾出现过“道佛合流”的局面。所以道、佛两家都在于阗传播。
公元7世纪,唐朝的使节、朝圣者也通过唐蕃古道到达天竺,引起了印度对道教文化的兴趣。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说:当时“迦摩缕波(阿萨姆)的国王曾向他索求一尊老子的塑像,并要求送他一本《道德经》的译文”。可以想象道教文化的足迹不仅到达了青藏高原,而且通过唐蕃古道对当时印度的影响程度。 六、藏汉龙神信仰的关系①
龙是一种生活在地下的神,有精灵性质。藏文中的龙与汉文的“龙”,相互有某些联系,但区别也很多。汉文中的龙是具形体的,有鳞及须、五爪,可以兴云致雨,而藏籍中的龙所指较为模糊,仿佛泛指地下的,尤其是水中的动物,诸如鱼、蛙、蝌蚪、蛇等。
如同其它原始神录一样,在历史的发展中,藏族的龙神有其演化过程。
1、早期的龙神
早期的龙神不但形象模糊,而且居住地纷纷繁繁。霍夫曼在论述西藏的宗教时写道,这些龙的最初的住所是河和湖,甚至是些井;它们在水底有家,守卫着秘密的财富,这一点与汉地龙神相同。但又说“有一本苯教著作上说,龙住在一种奇怪的山尖上,在黑岩石上,它的峰顶像乌鸦在头一样,也住在像猪鼻子似的坟堆上,像卧牛的山上,也住在柏树桦树和云杉上,也住在双山、双石和双冰川上”,这又与汉地的龙神大为迥异。显然,这里的龙神不但是住在江河湖海溪井水泊,而且超出了与水有联系的处所,仿佛一种精怪的脚色,自然地模糊了自己的个性形象。霍氏还引用了“赎罪诗”:
龙王住在所有河流中,
年王住在所有的树上和岩石上,
土主住在五种土中,
人们说,那里就是土主、龙和年。
它们有什么眷属?
带有长刺的蝎子,
细腰的蚂蚁,
金色的青蛙,
松蕊石色的蝌蚪,
贻贝一样白的蝴蝶,
这些就是他们的眷属。
这段诗中,又肯定“龙王住所有的河流中”,与上文大相径庭。因此,此时的龙神的形象,既不仅涉及蛇、蛙、螃蟹,也不仅仅是鱼、蝌蚪诸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随时附身或者变为蛇、蛙、鱼、蟹的精灵,并且无时无处不在。它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因此它是人间424种疾病之源,瘟疫、梅毒、伤寒、天花、麻风病,无不与之有关系,实际上它是一种人在时时谨慎敬奉的疾病灾难的象征,与年神有等量齐观的作用,这似乎与汉地龙神观念相通。
2、中期的龙神
中期的龙神是以明确的分工的形式出现的,是已经归入系统体系中的神。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龙神之所以有清楚的分工,与社会的这种进步紧密相关。居住于东、南、西、北、中的龙神可分为嘉让、解让、莽让、章赛让、得巴让五类。这五类龙神又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嘉让善的龙神,它可以保护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莽让是恶的龙神,它可以给人间带来灾难祸害,诸如瘟疫、疾病、干旱,均为彼之所为;解让、章赛让、得巴让基本属于不好不坏、兼善兼恶的龙神,它们可能给人类带来祸乱,分别籍根性于神界、人界、非神非人界。当然,社会分工不是以本质的善恶美丑划分的,藏区的龙神们,也有自己的劳动分工。如恰布等龙神主司下雨、降雪、打闪,若天遇久旱不雨,当求它降雨;僧波等龙神主司各种龙病,若生癞子、疮疱、水痘等龙病,当求它免去灾病沉疴。也不能得罪、冒犯、触怒那些主司跌打摔伤、腿断骨折的汤哇等一些意外事端的龙神。却热等龙神主司人间饮食饥饿和战争冲突,人们吃不饱、或遇战争,是因这些龙神不高兴,等等。除了这些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职司外,也有主管精神领域的龙神,如嘎波、宁嘎等就是让人们存心善正直,不要生贪嗔、嫉妒之心的龙神。
藏族对龙神的供祀活动,一般都在近河、井、池、江、渠湖泊处进行,供祀食物主要也是鱼类家族所喜欢的藏红花、芝麻、畜肉、酥油、奶、芫荽等。其供养的形式亦据情而定,隆重的由巫士主持;一般的,在煨桑时将所用祭品烧入桑中,或将其直接投入泉、湖、江、河、池水中。在青海、甘肃藏区的调查中,屡见此种现象。
3、晚期的龙神
藏文曲籍中,有一些龙王、龙女的故事,如吐蕃第二十九代王没卢若娶龙族女为王后。此类说法与早期、中期的龙神的形象有悖,它已将泛化的龙神形体单一化,抹去了早期龙神不断害人的精怪性,使它成了善神。这可能是藏汉、藏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在汉族的神话传说中,龙源于蛇,后成为神,同样是与水有联系的神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至于汉族地区所说的四海龙王,为地道的水神形象,天之旱,天之涝,都与之有关。至今在一些农区,倘遇久旱不雨,便请龙王降雨,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后期藏区绘画、雕塑中的龙的形象与汉地无二。
印度和汉族的交往据有关专家考证,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龙源于印、源于汉尚不得知。季羡林教授说:“在文学方面,从公元5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学中生产了一类特殊的作品——鬼神志怪的书籍。这些书里面的故事有很多是从佛经抄来的。唐代(公元681年~907年)传奇小说盛极一时,在这一类的小说里,印度故事的影响也很显著,譬如里面常常出现的‘龙王’和‘龙女’就都起源于印度。”藏区有关“龙王”、“龙女”的传说是否也起源于佛经故事?这种可能性应该说很大。
从佛教传入藏土的具体情形分析,龙王龙女等神话传说在藏人中的传播,大约始于吐蕃王朝兴盛时期,尤其是自桑耶寺修成后建立大规模的译经场,大规模的译经给此类神话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从汉地传进此类神话传说的可能性。
① 参见丹珠昂奔著《藏族文化发展史》,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