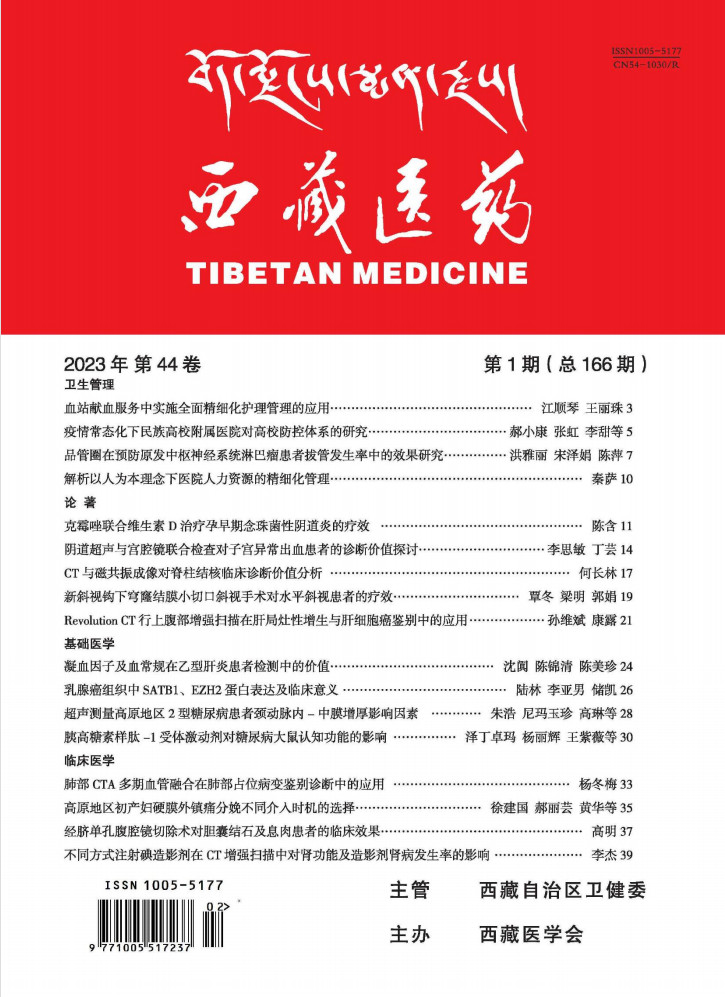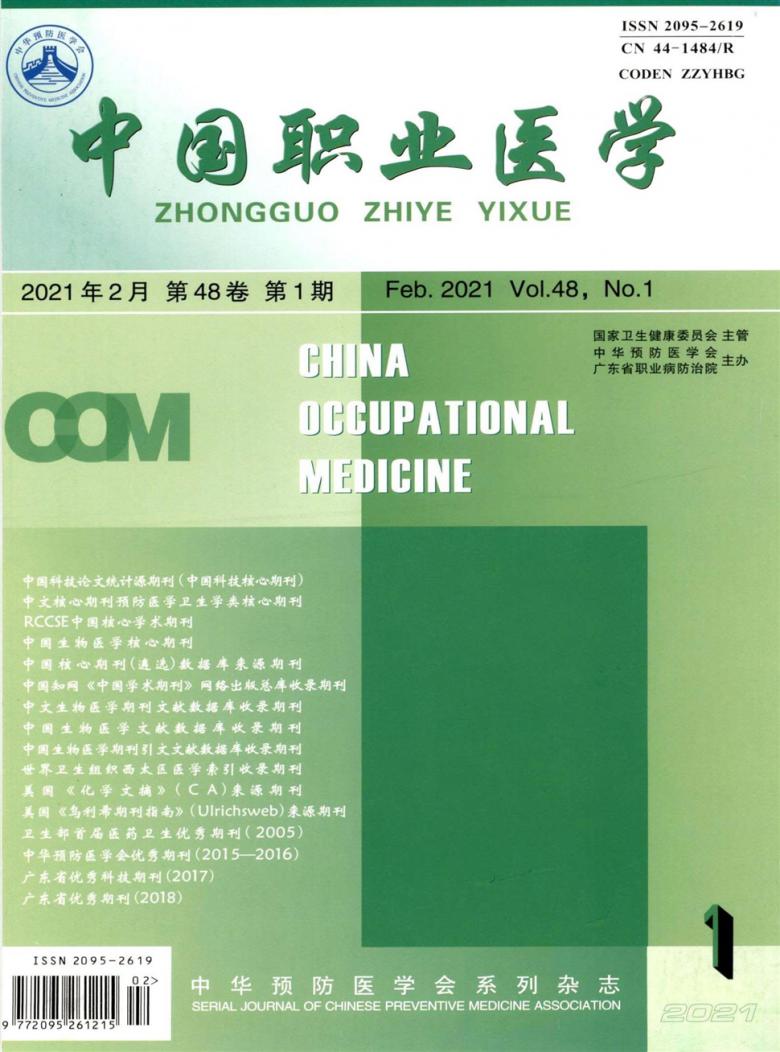环境伦理与东方情结
雷 毅
[摘 要]建立普适的环境伦理需要各种文化的参与,激进的环境主义试图寻求东方的帮助并不意味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东方转向”。当下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实质和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将东方传统生态智慧融入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可能性,而不是去做主观上有利于我们的错误判断。
[关键词]环境伦理;东方转向;深层生态学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ethics must take various cultures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ttempts to seek help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doesn’t mean the “Oriental turn” of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as a whole. What we should do at present is not to make incorrect judgments favorable to us,but rather to analyze carefully the different theories in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hen try to fin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the Orient into 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ethics;Oriental turn;deep ecology 近年来,“转向”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它从最初学科内部的“语言转向”、“实践转向”、“技术转向”、“人类学转向”逐渐蔓延到西方学术思想“东方转向”的讨论。有人甚至把“东方转向”看成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并断定这种整体的“转向”必然要影响到环境伦理学领域,进而提出了“为什么西方人研究生态伦理不能绕过东方”之类的问题[1]。然而,这类问题的讨论对于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究竟有无益处,需要我们认真分析。 一、西方何种生态伦理需要东方 “为什么西方人研究生态伦理不能绕过东方”之类的问题隐含着双重的含义:一是东方的思想对西方人研究生态(环境)伦理有重要意义;二是西方人若是忽视(或不重视)运用东方理论就不可能发展或变得完整。然而,若是仔细地分析起来,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伪问题)。西方的环境伦理研究,从仅仅要求经济改革到激进的众生平等,其间散布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伦理主张差异巨大。对于一个意识形态十分繁杂的研究领域,除非各种理论均有此倾向,否则,用整体的西方生态伦理来代替其中的某个主张显然不妥。因此,当谈论西方生态伦理不能绕过东方时,我们必须明确,究竟是整个西方的生态伦理学不能绕过东方,还是只有其中某个或某些伦理理论不能绕过东方。此外,我们还必须明确,东方传统中有哪些资源被西方生态伦理研究所利用或可能被利用,这又涉及我们对东方的生态资源究竟有多少认识的问题。可以设想,我们若是对东方生态资源的家底都不甚了解,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判断不出错呢? 就西方的环境保护思想而言,通常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阵营,而在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包含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整体论等主要思想流派,在这些主要流派之间还散布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学说,此外还有诸如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生物区域主义等等。事实上,各路流派除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这类基本要求之外还没有形成共同一致的主张,在西方传统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之前,是不会去寻求东方帮助的,然而,要认识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我们避开头绪繁多的各种理论,回到产生各种环境伦理(由于学科产生的特殊背景,西方学者通常称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而非生态伦理;在我国,生态伦理与环境伦理混用)最近的源头,用历史的线索来把握它的脉络,这种把握对于我们认识究竟西方何种环保思想需要求助东方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的环境保护思想,在源头上就始终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即资源保护路线和自然保护路线。这两条路线由美国人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和约翰·缪尔(John Muir)所分别开创,它们造就了今天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亦称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生态运动)。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一切的环境问题归结为我们现行经济规则的不合理,因而相信只要对经济规则和法律制度作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并严格遵循平肖提出的“科学管理,明智利用”原则,我们就可以避免环境问题的困扰。由于他们的社会改良要求并不涉及社会制度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因而也常常被称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到目前为止,以这种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是工业社会的主流。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的浅层生态运动是不需要求助东方的。它坚信,经济、法律和首先规则的改进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如果现有资源可以利用就不必回到传统,东方哲学整体上不能对西方有帮助并且可能是有害的。例如,人类中心主义代表人物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就认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良方只需从西方传统的人文资源中去寻找,无需东方的帮助。东方哲学所倡导的整体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相容,将其引入不仅会削弱西方的科学技术基础,还将从整体上危及西方的文明体制。因此对西方而言,宁可要一个污染的世界,也不要一个专制的世界。 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者的思维基本上是西方的,并且它们各自从西方传统的人文资源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立论基础和话语方式,至少目前从他们的论著中尚未见到他们对东方思想的兴趣。只有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整体论者才会试图寻求包括东方智慧在内的非西方的生态资源。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在于他们把一切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受技术支配的工业化社会体制,认为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使人在工业化道路上与自然愈加疏离,因而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文化的危机。他们反对生态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改良式的解决方式,在他们看来改良的做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打破这种体制不可能在内部找到出路,必须寻求外部的解决。能够从外部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范式产生颠覆作用的大概只有现代科学和东方的文化。因此,当我们说到西方生态伦理需要求助东方时,大概仅仅只能指深层生态学,若是把它理解为整个西方环境思想求助东方,那便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二、深层生态学对东方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如果把生态危机看成是文化和社会危机,那么,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办法便是对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然而,面对强大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打开缺口。因此,深层生态主义者大多是寻求外部的帮助来与工业文明对抗。对他们而言,现代科学(包括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生态学)和非西方的生态智慧是手中的重要工具,他们相信这两件工具就能够为颠覆工业社会的价值范式提供巨大帮助,最终建立起他们理想中的生态社会。 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生态学揭示了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科学,生态学提供了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其他学科中是缺乏的[2]85。生态学所揭示出来的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依赖性、系统整体的平衡性、有机性和整体性展示了一幅和工业社会机械论自然观迥然不同的图景。不仅如此,生态系统所表现出的整体性还孕育了一种强调互补、平等、关系和均衡的价值观。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便是以生态学为基础,发展了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论思想。也是基于对生态学中生态系统功能性特征的认识,深层生态学提出了它的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 然而,正如深层生态学的创立者阿伦·奈斯(Arne Naess)所说:“作为科学的一个门类,生态学并不考虑何种社会能最好地维持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类价值理论、政治、伦理问题。只要生态学家们狭隘地固守自己的领域,他们就不会过问这类问题。”[3]因此,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深入挖掘出生态学背后的形而上学含义。不过,生态学的现代表达虽然在观念的层面上对工业文明的价值与伦理提出了挑战,但仍不足以与强大的工业文明相抗衡。只有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与现代的生态观念相一致的根基,并将现代的生态观念置于传统的精神资源之中,通过协同的作用才能构成对工业文明的颠覆。然而,寻求传统精神资源的支持,仅仅着眼于西方传统是不够的,必须放眼于全部的人类传统。在寻求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东方的古老思想与生态学的新观念颇为契合。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物学鸿沟和道德鸿沟都荡然无存。东方文化强调以主客交融、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它追求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这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分离,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逾越形成鲜明对照。由于东方文化传统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与深层生态运动的基本理念有诸多相通之处,因而能够对西方环境运动由浅层向深层的转换提供帮助。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深层生态运动对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关注,主要在于它为现代生态学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表达。 深层生态学在建构它的理论体系时广泛借鉴了西方传统已有的各种精神资源(如西方哲学、西方科学和基督教思想)和其他民族的精神资源(如亚洲的道家、禅宗佛教、甘地的思想、印第安原居民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它的理论核心“自我实现”论中有很好的体现。尽管“自我实现”论最初是由奈斯个人提出的,但很快就得到了深层生态主义者(如德沃尔、塞欣斯等人)的普遍认可。有人认为这种“自我实现”论是在借鉴了儒家的大我观或天人一体观之基础上提出来的,并认定“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观已经超越了马斯洛等人自我实现理论,后者将自我实现主要局限在社会领域,尽管也主张忘我地体验自然。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生态的自我实现理论,几乎就是儒家思想的翻版”[4]。然而,从深层生态学对其理论结构的阐释(如图)就可以看到,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直接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哲学、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传统,而与儒家思想毫不相干,充其量只表明他们的思想与儒家相契合,此外不再有更多的含义[5]。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奈斯、德沃尔和塞欣斯等代表人物那里并没有表现出对儒家的热情,尽管奈斯对中国曾有过兴趣,但那仅限于对毛泽东的思想。 B=佛教的基本前提(Buddhist) C=基督教的基本前提(Christian) P=哲学前提(Philosophical) DEP=深层生态学纲领 不过,深层生态学阵营中的重要人物如史奈德(Gary Snyder)、罗西(Robert Roshi)等人曾在日本、印度和中国的西藏学习过禅宗佛教。奈斯“自我实现”中的自我是大写的自我(Self),意是指“生态自我”,这是一种不断扩展了的认同感,最终达到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它类似于佛教中的见性成佛(佛性的显现)。因此,如果说此处有东方情绪的话,那么,它的根源是在禅宗佛教而非其他。我们可以将儒家的生态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进行比较,发现共同性和相通性,但若是要寻找两者之间必然的关系,还需要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 就整个西方生态伦理领域而言,确实有过对东方生态智慧的热情,这有美国环境思想史家纳什(Roderick Nash)的表述为证,他说:“近几年来,人们对亚洲宗教的伦理意蕴的兴趣已成为促使宗教‘绿色化’的另一源泉。……一些美国人直截了当地用非基督教传统来激发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他人,特别是60年代那些为反主流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年轻人,则干脆放弃已丧失信誉的基督教,转而信仰亚洲宗教,如道教、耆那教、神道教、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印度教。”[6]注意,这里没有提及儒家,但绝不是疏忽,而是隐含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事实上,道家的哲学在自然观和人生观方面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有诸多的暗合。德沃尔(Bill Devall)和塞欣斯(George Sessions)曾说:“当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已经从道家经典《老子》和13世纪日本佛教大师道元(Dogen)的著作中发现了灵感。”[2]100奈斯则说得更明确:“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3]深层生态学在选择东方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会青睐道家?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理查德·塞文(Richard Sylvan旧译理查德·西尔万)和贝内特(David Bennett)在详细研究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的关系后,给出了答案。他们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7]因此,当我们在谈论东方转向时,必须弄清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究竟为什么需要东方思想,需要什么样的东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