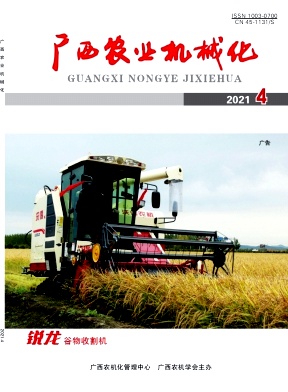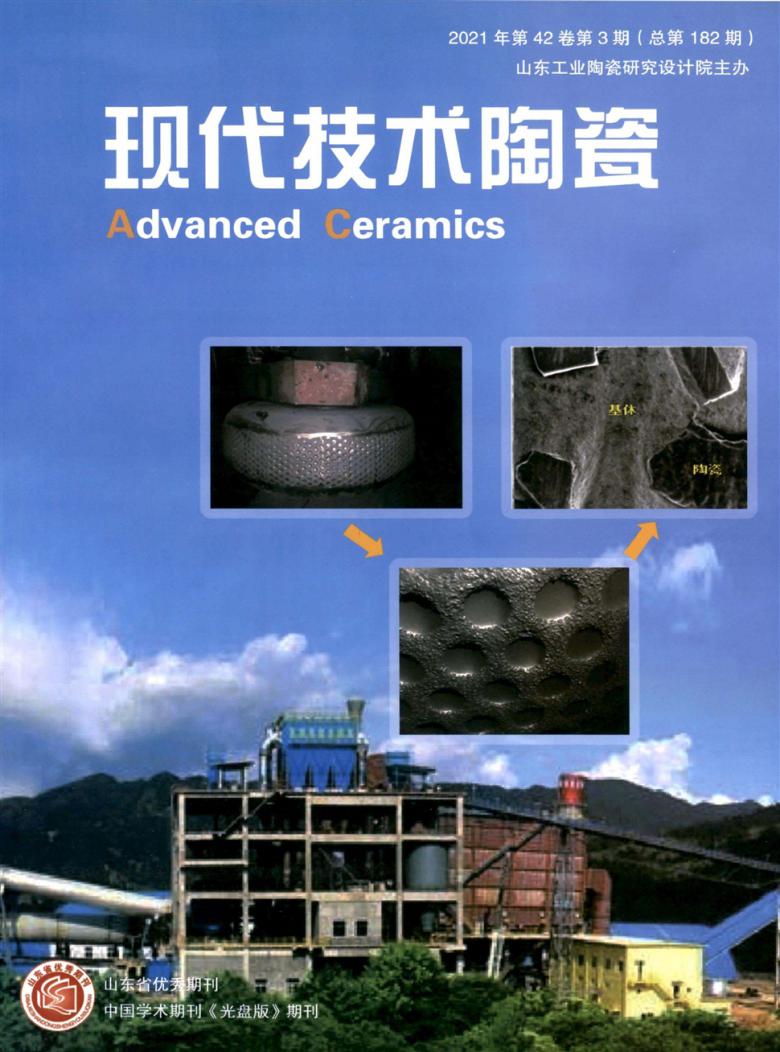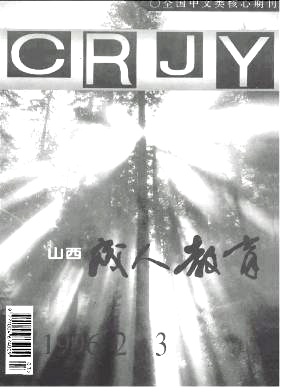张力冲突中的爱之诫命——论基督宗教伦理学的一个深度悖论
刘清平 2006-05-28
The Double Love Command in Tense Conflicts
--On an In-Depth Paradox of Christian Ethics
关键词:基督宗教 爱的诫命 伦理学 深度悖论
提要:耶稣提出的两条爱的诫命,集中体现了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的根本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在这两条诫命之间,既存在着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包含着张力冲突的一面,以致它们必然会在宗教伦理学上陷入一个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一方面,基督宗教把爱邻人建立在爱上帝的本原根据之上,试图以爱上帝为基础、实现普世性的爱邻人;另一方面,它又赋予爱上帝以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从而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主张以放弃派生从属的爱邻人为代价、来维护本根至上的爱上帝,乃至最终以爱上帝否定爱邻人。
基督宗教往往又被称作“爱的宗教”;最能体现它的这一根本特征的,当然就是耶稣提出的两条“爱的诫命”——“爱上帝”与“爱邻人”。不过,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在这两条内在相关的诫命之间,不仅存在着和谐统一的一面,而且存在着张力冲突的一面,以致基督宗教爱的观念最终必然会在宗教伦理学上陷入一个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一
众所周知,对于一位法利赛人律法师提出的问题“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的回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从语境关联的角度看,耶稣的这一回答似乎显得有些奇特。本来,那位律法师的问题很清楚,是要询问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最大;然而,耶稣在回答时却相继提出了“爱主你的神”与“爱人如己”两条诫命,并且十分清晰地将它们区分为“第一”和“其次”。从基督宗教神学的理论视角看,前一条诫命直接以神性的上帝为对象,关涉到人神关系的领域;后一条诫命直接以凡俗的邻人为对象,关涉到人际关系的领域。所以,无论在对象的性质方面、还是在地位的高低方面,它们之间都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不能够简单地合二为一。但进一步看,耶稣不仅明确肯定了它们之间彼此“相仿”,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两条诫命一起——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条诫命、甚至不仅仅是“爱上帝”这条“最大的”诫命自身——构成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耶稣的上述回答足以表明:他一方面的确是把“爱上帝”与“爱邻人”当作两条不同的诫命来看待的,另一方面又的确是把二者当作一个内在相关的统一整体来看待的。至于这两条诫命之间的具体关联,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这两条诫命虽然在意向性对象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点(一个指向神性的上帝,另一个指向凡俗的邻人),但在意向性活动方面又呈现出清晰的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极大地突显了“爱”在人神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根本意义,在这一点上无疑彼此“相仿”。
本来,旧约中摩西十诫的主要内容,也分别关涉到人神关系与人际关系两大领域。不过,在人神关系方面,它强调的首先还是对“独一的主”耶和华的崇信,因此特别要求人们不可信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神名;而在人际关系方面,除了主张人们应当孝敬父母之外,它突出的也依然是一些具有否定性内涵的律法禁忌,亦即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参见《申命记》5:6-21)诚然,旧约中也提出了爱上帝与爱邻人的诫命。不过,它们既没有直接包含在摩西十诫之中,也没有内在地联系起来,而是在两个地方分别陈述的;尤其是“爱邻人”的诫命,几乎只是附带性的提及,并没有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意义。(参见《申命记》6:5;《利未记》19:18)从这个角度看,在旧约中,无论人神关系、还是人际关系,主要还是具有否定性、被动性的意志内涵;所以,旧约才会特别要求人们“不可做这做那”,由此表现自己对上帝的坚定信仰。
相比之下,耶稣通过提出两条爱的诫命,显然就使人神关系与人际关系都经历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深刻转型,明确赋予了它们以肯定性、主动性的情感意蕴,特别要求人们“应当爱神爱人”、由此表现自己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保罗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不仅明确指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提摩太前书》1:5-10),由此突显了从义人心中生出来的“爱”与为不义之人设立的“律法”之间的微妙区别,而且还特别强调:“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罗马书》13:8-9),甚至宣布“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13)。就此而言,耶稣提出的两条爱的诫命,的确集中体现了基督宗教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异之处,尤其是集中体现了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在伦理方面的根本特征。
进一步看,与旧约只是提及“爱邻人”的诫命相比,耶稣明确主张两条诫命一起构成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求基督徒不仅应当爱上帝、而且还应当爱邻人,也极大地突显了“爱人如己”的人际之爱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基督宗教认同的灵性生活不再像犹太教那样主要限于崇信神性上帝的范围,而是更广泛地扩展到关爱世俗邻人的领域,乃至最终使“爱人如己”构成了基督宗教所谓“诚爱”(agape)的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就此而言,耶稣提出的爱的诫命,在继续坚持犹太教的神本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显然又比犹太教包含着更浓郁的人文主义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与犹太教崇信的上帝主要呈现出“公义”的特征相比,基督宗教崇信的上帝才会主要呈现出“爱”的特征。
其次,这两条诫命虽然在突显“爱”的意义方面彼此“相仿”,但由于它们的意向性对象毕竟分别指向了神性的上帝与凡俗的邻人,因此,二者在基督宗教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相对地位,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主次之别。耶稣的回答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种内在的差异:尽管两条诫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构成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但单就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而言,应该说只有爱上帝才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而爱邻人则只能说是“诫命中的第二”,因此必然要从属于第一条最大的诫命亦即爱上帝的诫命。
导致两条诫命出现这种主次之别的原因是很容易发现的。从基督宗教根本教义的视角看,既然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既然上帝不仅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人、而且出于自己的本性关爱人,人作为上帝的造物,当然应当首先去爱上帝,以此作为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同时,既然邻人就像自己一样也是上帝的造物、也享有上帝的关爱,作为爱上帝的一种体现或是扩展,人当然也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人,以此作为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换句话说,在基督宗教爱的观念中,既然爱上帝的诫命直接指向了本根至上的“独一的主”,对于爱邻人的诫命来说,它就不仅具有本原根据的源初意义,而且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相比之下,既然爱邻人的诫命只是直接指向了作为上帝造物的凡俗邻人,它不仅在根源上必然要派生于爱上帝的诫命,而且在地位上也必然要从属于爱上帝的诫命。新约文本对此也做出了清晰的说明:“凡爱生他的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约翰一书》5: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耶稣曾明确指出在所有的诫命中“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31),认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诫命相比始终是最大、最重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在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中,这两条诫命也可以同等地享有并列“最大”的地位。因为这一结论实际上等于是承认:神性的上帝与凡俗的邻人都同样是既本根、又至上的最高存在,从而把基督宗教变成一种二元性的信仰观念。很明显,坚持崇信“独一的主”的基督宗教当然不会同意这样一种主张。事实上,一方面,只有明确肯定爱上帝对爱邻人所具有的本根至上性,基督宗教才有可能在它的理论架构内把这两条诫命统一成一个整体、使它们一起构成“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另一方面,只有明确肯定爱邻人对爱上帝所具有的派生从属性,基督宗教才有可能把它的这种“爱人”观念与其他宗教体系或伦理学说的“爱人”观念(诸如希腊哲学的“爱若斯”、启蒙运动的“博爱”、儒家的“仁爱”或是佛教的“慈悲”等等)区别开来。20世纪基督宗教神学界有关“诚爱”观念的热烈讨论,就从比较伦理学的角度鲜明地指出了它与其他理论的“爱人”观念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异。
再次,虽然两条诫命之间存在着这种本根至上与派生从属的深刻差异,但由于它们毕竟都建立在“上帝造人并且爱人”这个终极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二者的关系中,无疑包含着和谐统一的一面。新约的许多论述,如“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4:12)、“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约翰一书》4:20)等,都清晰地体现了两条诫命之间的这种统一关系:既然一方面爱上帝是爱邻人的本原根据,另一方面爱邻人又是爱上帝的体现完成,那么,一个人只有出自真心地去爱创造世上万物的上帝,才有可能出自真心地去爱作为上帝造物的邻人;反之,一个人只有出自真心地去爱作为上帝造物的可见邻人,才有可能充分体现他对不可见的造物主——上帝的真心之爱。事实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神学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种和谐统一的一面,探讨和阐发两条爱的诫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论证和宣讲基督宗教爱的福音的。
同时,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两条诫命之间存在着这种和谐统一的内在关系,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也一直发挥着不容否认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对基督宗教世界的伦理道德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许许多多虔诚的基督徒正是遵照耶稣提出的这两条爱的诫命,在崇信和敬爱上帝的本根基础之上,进一步在“爱人如己”中热情、无私地关爱周围的邻人,乃至关爱作为上帝造物的全体人类,把这种对邻人的人际之爱视为对上帝的神性之爱的扩展完成和完美体现,尤其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对于包括非基督宗教世界在内的全人类做出种种富有意义的巨大贡献。我们在讨论基督宗教爱的观念的深度悖论时,当然不应该忽视或是否认这一事实。
二
不过,本文试图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两条爱的诫命都建立在“上帝造人并且爱人”这个终极的基础之上,但由于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本根至上与派生从属的深刻差异,因此,在二者的关系中,不仅包含着和谐统一的一面,而且包含着张力冲突的一面。这里我们不妨从分析爱邻人诫命的内涵入手,逐步深入地探讨它们之间的这种张力冲突。
众所周知,在基督宗教中,“爱邻人”在本质上是一条指向全人类的普遍性诫命。不错,在旧约中,“爱人如己”的诫命主要还是放在“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的文本关联中加以论及的(参见《利未记》19:18);然而,在新约中,耶稣以及保罗等却多次强调:“爱邻人”应该超出犹太民族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外邦人那里(参见《马太福音》8:5-13;《马可福音》16:15;《使徒行传》10:34-35,13:46-49,15:6-21)。 尤其在奥古斯丁明确主张“邻人”就是指每个人或一切人之后, 这条诫命更是无可争议地具有了普遍性的整全内涵,以致我们从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基督宗教倡导的“邻人之爱”,首先是一种指向全人类的“普世之爱”。并且,显而易见的是,在基督宗教的理论架构内,这种无所不包的普世性内涵,也是与上帝创造并且关爱全体人类的根本教义内在一致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倘若从这种普世整全的视角理解爱邻人的诫命,所谓的“邻人”就必然是既包括那些爱上帝的基督徒,也包括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于是,问题在于,在肯定爱上帝是本根至上的最大诫命的前提下实施爱邻人诫命的时候,基督徒甲是不是应当爱非基督徒乙?
本来,假如乙也是一位爱上帝的基督徒,从理想化的视点看,对此可以说没有任何疑问:既然乙不仅像甲一样也是上帝的造物,而且像甲一样也是爱上帝的基督徒,那么,即便甲与乙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彼此为敌,甲依然应当在爱上帝的同时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乙,因为乙与甲在遵守“爱上帝”这个最大的诫命方面,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两条爱的诫命似乎就可以保持完全和谐的统一状态了。不过,假如乙不是一位爱上帝的基督徒,两条爱的诫命之间却会立即出现某种严峻深刻的张力冲突,以致甲对乙的态度也势必会面临某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甲似乎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乙,因为乙毕竟像甲一样也是上帝的造物、具有上帝赋予的人的本性;但在另一方面,甲似乎又不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乙,因为乙毕竟不像甲一样是一位爱上帝的基督徒,而是悖逆天父旨意、不愿去爱上帝。其实,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不爱上帝”亦即“不信上帝”恰恰就是最大的不可饶恕之罪,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中一切世俗性的罪恶,因为它违背了所有诫命之中第一条最大的诫命,所以必然要受到上帝的公义惩罚,乃至最终会下地狱。所以,耶稣曾经断然指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6);“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8:24)既然如此,基督徒甲又怎么能够按照爱邻人的诫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非基督徒乙?
富有意味的是,我们可以从新约记述的耶稣教诲中,为两条诫命之间的这种张力冲突找到有力的文本证据。一方面,耶稣明确要求门徒:“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4-48)显然,根据这些教诲,既然上帝完全地爱所有的人,基督徒当然也就应当像他那样完全地爱所有的人,其中无疑包括那些在信仰上与自己敌对、甚至逼迫自己的非基督徒,因为这些不爱上帝的“歹人”、“不义的人”就像那些爱上帝的“好人”、“义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造物、享有上帝的关爱。但在另一方面,耶稣又反复强调:不但那些“亵渎圣灵”、“终不悔改”的十恶不赦之人,而且就连那些不信他的异能、不愿接待他的使徒的人,都必然要遭受超乎想象的严厉惩罚,乃至最终坠落地狱、经历永火永刑,“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参见《马太福音》10:14-15,11:20-24,12:31-32,25:41-46)。有一次他甚至宣布:“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马太福音》10:34-35)显然,根据这些教诲,如果邻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拒绝信仰上帝,基督徒就不能爱他们,而是应当与他们生疏乃至动刀兵,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这些人居然不愿去爱创造他们的上帝,以致本来是“完全”地爱每个人的上帝,最后也会“必不认”他们。
新约记述的使徒言论,同样清晰地体现了基督徒面临的这种两难境地。例如,一方面,保罗热情赞美耶稣:“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明确认为耶稣的爱遍及一切罪人,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断然指出:“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哥林多后书》6:14-15),公开主张爱上帝的“义人”不应当与不爱上帝的“不义之人”在相交、相通、相和、相干中——更不必提在相爱中——混为一体。再如,一方面,约翰热情赞美“上帝就是爱”,因为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并因此明确认为“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包括去爱耶稣同样为之作了挽回祭的“普天下人”(《约翰一书》2:2,4:8-11)。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断然指出:“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二书》10-11),公开主张信仰基督的人应当拒绝与不信基督的人来往,甚至不要问他们的安,否则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至于主张不爱上帝之人必将遭受严厉惩罚的话语,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哥林多前书》16:22)、“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彼得后书》3:7)、“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犹大书》5),在使徒的言论中当然也不罕见。《启示录》9:4-6甚至宣称,在末日审判前,天使将会这样吩咐蝗虫:“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种宁可保护“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却“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甚至要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求死不能境地的态度,无疑是与耶稣明确提倡的普世性“爱邻人”的诫命大相径庭的。
显然,新约记述的这些耶稣教诲和使徒言论,通过展示两条诫命之间的张力冲突以及基督徒面临的两难境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爱上帝与爱邻人之间内在蕴含的深度悖论:一方面,为了实现第一条最大的爱上帝诫命,基督徒应当去爱那些不爱上帝的邻人,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上帝的造物、同样具有上帝赋予的人的本性;但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为了实现第一条最大的爱上帝诫命,基督徒又不应当去爱那些不爱上帝的邻人,因为他们犯下了弃绝上帝的不可饶恕之罪,理应受到痛恨乃至严惩。结果,本来在起源上派生于爱上帝诫命的爱邻人诫命,就被它的这一具有至上意义的本原根据所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一些神学家虽然已经察觉到两条诫命之间的上述张力冲突,却似乎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深度悖论,反而从基督宗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这种一方面去爱作为“上帝造物”的非基督徒、另一方面去恨作为“不义罪人”的非基督徒的做法,在伦理上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奥古斯丁一方面主张:“谁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友,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真是幸福!”另一方面又宣布:“我真痛恨那些反对圣经的人们,为何你不用‘双刃的利剑’刺死他们,使他们不再敌视圣经。” 托马斯•阿奎那在回答基督徒是不是应当出于诚爱去爱罪人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则采取把所谓“罪人”的存在分解为二的方法,主张:就罪人也是上帝的造物、并且因此拥有达到神性至福的能力这一方面说,基督徒应当出于诚爱去爱他们;但就罪人不信上帝的罪行与上帝正相反对、并且因此构成达到神性至福的障碍这一方面说,按照《路加福音》14:26中记述的耶稣教诲,基督徒又不应当出于诚爱去爱他们,相反还应当出于诚爱去恨他们——哪怕他们原本是自己的父母或亲人。随后他又总结说:这样做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上帝的缘故、真正地出于诚爱去爱这些罪人。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依据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明确认同基督徒在面对非基督徒时可以而且应当坚持某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态度,却没有指出其中实际上蕴含着本根至上的爱上帝诫命必然否定派生从属的爱邻人诫命的深度悖论。
然而,这一悖论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被神学家们所察觉,就停止自身的存在。相反,在现实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它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不幸的是,有时候甚至是以令人震惊的极端方式——充分地展现自身。例如,16-19世纪基督宗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可以说便是上述悖论的典型例证。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运动的确是颇为真诚地想把基督宗教爱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因此,许多传教士在面对那些此前从未听说耶稣基督之名的非基督徒时,也的确是极力以那种类似于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博爱心理对待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充满关爱的仁慈举动,使他们领会基督之爱的无穷魅力,心甘情愿地接受爱的福音的灌注感化,最终皈依为爱上帝的基督徒,从不信之罪的苦海深渊中解脱出来、重获新生。但在另一方面,一旦这些人在屡屡感召之下依然冥顽不化、拒绝皈依基督信仰,尽管他们还是无可争议的“上帝造物”或“邻人”,尽管他们可能并未因为这种不信就失去他们那种淳朴率真的源初道德,他们却往往被转而视为执迷不悟、腐坏堕落的“不义罪人”,以致被取消丽日高照、甘霖普降的权利,受到“生疏”乃至“动刀兵”(并且常常是这些非基督徒此前闻所未闻的文明化了的“动刀兵”)的待遇,结果是不仅在话语中被诅咒着“下地狱”,而且还可能在现实中被驱赶着“下地狱”。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粗暴的态度往往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需要密切相关的;但在肯定这种关联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基督宗教爱的诫命的深度悖论,尤其是那种主张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罪无可赦、必须严惩的神学观念,在促成和加强这种粗暴态度方面的深层效应——这就正像我们在讨论许多基督徒对于全人类做出的巨大慈善贡献的时候,不应该把它们仅仅归结为这些基督徒个人的善良本性、而根本否认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在促成和加强他们的这种“爱人如己”态度方面的深层效应一样。
其实,在中世纪,一些教会机构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对于叛教分子、无神论者以及异教徒们实施的近乎残忍的严酷惩罚(而实施这类严酷惩罚的主要理由甚至惟一理由,便是这些人坚持不愿信仰上帝),已经足以使人怀疑“爱人如己”的诫命是怎样在这些“罪人”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面得到积极贯彻的,倒更容易让人觉得只有那种针对他们不信之罪的“疾恶如仇”态度才最终落到了可悲的实处。直到今天,依然还有一些神学家真诚地相信:“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只有信仰提出了爱的诫命的耶稣基督,才是世人获得神恩救赎的唯一途径;否则,仅仅由于“不信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一个人就有可能永远沉沦万劫不复的阴间地狱。所有这些显然可以表明:基督宗教爱的悖论所包含的那种厚重而又严峻的深度意蕴,不是神学家们的漠视态度就能够去除消解的。 三
上述分析或许很容易会受到一种批评,即认为它只是采取“非此即彼”的视点、而非采取“亦此亦彼”的视点考察爱上帝与爱邻人的关系,结果就把两条诫命简单地对立起来了。对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任何意图,想要否认在两条诫命之间存在着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如前所述,本文明确承认:耶稣本来的确是把两条诫命当作一个内在相联的有机整体来看待的,而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也的确是十分真诚地希望基督徒都能够在伦理生活中做到既爱上帝、又爱邻人。本文的目的只是试图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正如耶稣教诲、使徒言论、以及基督宗教的伦理实践从各个角度所表明的那样,在两条爱的诫命之间,不仅存在着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而且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张力冲突;而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在伦理方面所陷入的深度悖论,恰恰就来自这两者——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与非此即彼的张力冲突——在两条诫命关系之中的内在并存,以致本来是从爱上帝诫命中和谐统一地派生出来、并且被视为它的扩展完成的爱邻人诫命,反过来又会在张力冲突中受到爱上帝诫命的限制否定,从而无法真正实现自身。
尤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导致两条诫命之间必然出现张力冲突、乃至在伦理上陷入深度悖论的根本原因,并非源于某种外在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恰恰来自基督宗教始终坚持的下面这条本来是旨在确立两条诫命之间和谐统一的根本教义:“爱上帝”与“爱邻人”都建立在“上帝造人并且爱人”这一神性真理的终极基础之上,因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本根至上与派生从属的鲜明差异。实际上,由于基督宗教首先就把两条诫命置于上帝造人并且爱人的终极基础之上,其次又因此把爱上帝的诫命置于爱邻人的诫命之上,主张爱邻人不仅在起源上派生于爱上帝、而且在地位上也从属于爱上帝,这样,它提倡的对邻人的爱,在本质上便是一种充满神本意蕴的爱,而不是一种充满人本意蕴的爱。因为归根结底,这种爱并不是由于邻人是“人”而去爱邻人,乃是由于邻人是“上帝的造物”而去爱邻人。
从表面上看,既然基督宗教明确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这种区别似乎没有多大意义;然而,正是这一微妙的细小差异,造成了深刻的天壤之别。首先,这样一来,基督宗教认同的“人”,在本质上必然会受到其特异性神本主义立场的严格限定,具体表现在:依据基督宗教的有关教义,“人”不仅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的产物、具有上帝赋予的本性,而且由于这一原因,“人”本来就应当出自本性地顺从上帝的旨意、无条件地信仰和爱上帝,否则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扭曲了自己作为“人”的内在本性。 其次,这样一来,基督宗教认同的“爱邻人”,在本质上也不是为了邻人自身的缘故而去爱邻人,乃是为了上帝自身的缘故而去爱邻人,以致爱邻人最终可以并且应当还原为爱上帝。换句话说,即便在“爱邻人”这一诫命之中,邻人本身也并非爱的终极目的,只有上帝才是爱的终极目的。众所周知,这些正是基督宗教始终坚持、从未放弃的根本教义。例如,安德斯•尼格伦在讨论希腊哲学“爱若斯”观念与基督宗教“诚爱”观念的区别时就明确指出:“爱若斯必定总是把对人的爱视为对人之善的爱。……而诚爱却是与之正相反对的:上帝的爱是所有对人的爱的基础和样式。”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则强调:“基督宗教爱的诫命之所以要求我们去爱邻人,并不是因为邻人在可爱性方面与我们是平等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尊重人格’,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邻人。” 就连积极倡导“普世伦理”的孔汉思也依然宣称:基督宗教主张的“爱邻人”,“显然不是出于某种建立在普遍人性之上,源于抽象的、共同的人性哲学宇宙论。这种信仰并不能让我去爱所有的人。……爱敌人是因为神爱所有的人”。 然而,这样一来,尽管基督宗教的确十分真诚地希望“爱邻人”能够成为指向一切人的本真性普世之爱,它在本质上却必然会受到其特异性神本主义立场的严格限定,以致最终不可能成为那种为了人而指向一切人的本真性普世之爱,亦即那种由于人是人、并且为了人自身的缘故所产生的普世之爱。费尔巴哈曾因此明确指出:“对作为人的人的爱,只不过是属自然的爱。属基督的爱,乃是超自然的、洁净了的、神圣化了的爱;但是,属基督的爱也只爱属基督的东西。……宗教式的爱,只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爱人,因而只是似是而实非地爱人,实际上只爱上帝。”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为了爱上帝才去爱邻人的前提之下,一旦在爱上帝与爱邻人之间出现张力冲突(例如一旦邻人不愿爱上帝),那么,基督宗教就不得不为了维护本根至上的爱上帝,而不惜牺牲派生从属的爱邻人,结果只能是凭借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否定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
例如,耶稣在宣布他来是叫人与自己家里的人生疏之后,紧接着便指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6-37)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进一步主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不难看出,耶稣的这些教诲实际上已经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清晰地揭示了全部问题的奥秘所在:身为基督徒,必须把爱上帝无条件地凌驾于爱世人(包括爱自己的父母儿女)之上,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爱世人胜过爱上帝;因此,一旦世人违背了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不愿去爱上帝,基督徒就应当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而与他们生疏,乃至去恨他们、与他们动刀兵。否则的话,基督徒就是把爱世人凌驾于爱上帝之上,因此也就不配作耶稣的门徒了。结果,虽然耶稣的确曾经把两条爱的诫命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但正是他自己,同时却又凭借至高无上的“爱上帝”否定了派生从属的“爱邻人”,以致不惜在这里要求基督徒去恨不信上帝的非基督徒、乃至与他们动刀兵。
鉴于前面提及的种种悲剧性事件,人们——包括不少基督徒——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一方面基督宗教的爱邻人诫命在理论上具有如此整全的普世性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存在着大量仅仅出于纯粹宗教性的原因就去仇恨乃至迫害非基督徒的现象。其实,导致这种深度悖论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源,恰恰就在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自身之中。如上所述,正是基督宗教的这种根本教义,在肯定爱上帝与爱邻人和谐统一的同时,又以一种特异性神本主义的方式,把这两条诫命尖锐地对立起来了。换句话说,在耶稣教诲、使徒言论以及神学家们的理论论证始终如一地予以肯定的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之中,本来就潜藏着迫使我们在从“亦此亦彼”的视点考察两条诫命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不得不从“非此即彼”的视点考察这种关系的内在契机。归根结底,虽然基督宗教的确是十分真诚地希望基督徒都能够做到既爱上帝、又爱邻人,但它不仅把爱邻人归结为爱上帝、而且把爱上帝凌驾于爱邻人之上的基本立场一旦贯彻到底,势必会在本质上否定爱邻人的自律意义和独立地位,使其仅仅沦为爱上帝的附庸点缀,以致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最终把本来是“亦此亦彼”的既爱上帝、又爱邻人,变成“非此即彼”的只爱上帝、不爱邻人。
四
其实,假如基督宗教提倡的爱邻人在本质上是为了邻人的缘故而去爱邻人、或是由于邻人是“人”而去爱邻人,那么,只要邻人乙是“人”,无论乙是不是基督徒、爱不爱上帝,基督徒甲都应当遵循爱邻人的诫命,在“爱人如己”中像爱作为“人”的自己一样去爱作为“人”的乙。然而,由于基督宗教提倡的爱邻人在本质上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去爱邻人、或是由于邻人是“上帝的造物”而去爱邻人,结果,虽然基督徒甲的确可以遵循爱的诫命,在“爱人如己”中像爱作为“上帝造物”的自己一样去爱作为“上帝造物”的乙,但他却不可能在“爱人如己”中像爱作为“基督徒”的自己一样,去爱作为“非基督徒”的乙,因为就这一点而言,由于乙违背了爱上帝这条最重要的诫命、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成为所谓的“不义罪人”,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甲不但不应当去爱乙,反而应当去恨乙。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乙的邻人之爱便必然会受到甲对上帝的神性之爱的限制否定,从而无法真正成为那种为了人而指向一切人的本真性人际之爱。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假设有乙与丙两位邻人,他们除了在乙是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而丙是爱上帝的基督徒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之外,在其他方面——包括人格属性、道德品质、生活习俗、日常嗜好等——都是完全一样的。假如甲在本质上是为了邻人的缘故而去爱邻人、或是由于邻人是“人”而去爱邻人,那么,甲对乙的爱与甲对丙的爱本不应当存在什么差异。但是,既然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甲只能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去爱邻人、或是由于邻人是“上帝造物”而去爱邻人,结果,甲就必然会发现乙远远不如丙那样可爱、或是那样值得去爱,因为乙虽然也是“上帝的造物”,却又背离了上帝的旨意、居然不愿去爱上帝,以致成为“不义的罪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乙的爱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强度上,都必然会受到爱上帝诫命的限制否定,从而在本质上远远低于甲对丙的爱。
诚然,如果甲对没有同样信仰的乙只是怀有一般性的邻人之爱、而对具有同样信仰的丙怀有更强烈的教友之爱,这种做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基督宗教主张的一视同仁的普世关爱理想,但倘若从“爱有差等”的视角看,却也无可厚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情况并非仅仅如此。因为如上所述,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在这种情况下,甲不仅应当使自己对丙的教友之爱大于对乙的邻人之爱,而且还应当为了维护爱上帝诫命的本根至上性,进一步去恨不愿履行这一诫命、作为“不义罪人”的乙,仅仅由于“不爱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就与乙生疏乃至动刀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宗教爱的观念的深度悖论便会以一种戏剧性的反讽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这一观念原本是旨在要求基督徒甲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而去爱邻人——其中既包括非基督徒乙、也包括基督徒丙;但在另一方面,恰恰是、并且仅仅是为了爱上帝的缘故,甲却不得不在人生最重要的方面(亦即灵性生活的方面)富于信仰激情地对基督徒丙充满教友之爱的同时,又在同一个方面富于信仰激情地去恨非基督徒乙,尽管乙与丙除了在是否爱上帝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之外,在其他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一方面,基督徒甲只有出自真心地去爱作为上帝造物的一切邻人——其中既包括非基督徒乙、也包括基督徒丙,才有可能充分体现他对上帝的真心之爱;但在另一方面,基督徒甲只有在出自真心地去爱基督徒丙的同时、又出自真心地去恨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乙,才有可能充分体现他对上帝的真心之爱。然而,倘若我们从一种普遍性人本主义的视角考虑这个问题,很明显,虽然基督宗教几乎拥有一切正当的理由鼓励基督徒甲爱基督徒丙胜过爱非基督徒乙,但它却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鼓励基督徒甲仅仅出于“不爱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就去恨非基督徒乙。
因此,由于在伦理方面存在着上述悖论,虽然基督宗教爱的观念的确可以凭借甲与丙之间作为“基督徒”所发生的教友之爱,扩大加强甲与丙之间作为“人”所发生的人际之爱,甚至,虽然它也的确可以凭借甲与乙之间作为“上帝造物” 所发生的宗教之爱,扩大加强甲与乙之间作为“人” 所发生的人际之爱,但在另一方面,它同时却又几乎是“无中生有”地凭空增添了基督徒甲针对非基督徒乙的宗教仇恨,并且凭借这种宗教仇恨最终消解了甲与乙之间作为“上帝造物”所发生的宗教之爱、以及作为“人”所发生的人际之爱——而假如甲不是把爱上帝的诫命凌驾于爱邻人的诫命之上的话,这种宗教仇恨在甲与乙之间原本不会存在。实际上,当耶稣宣布“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的时候,他已经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悖论的深度意蕴:基督徒与其父母子女之间原本基于血缘关系能够自然实现的“血亲之爱”,可以并且应当仅仅由于“父母子女不爱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就受到基督徒与上帝之间至高无上的神性之爱的消解否定,以致最终转变成一种“血亲之恨”。正是根据耶稣的这段教诲,“梵二”会议的有关文献才会明确指出:“既然皈依者所信仰的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象征(参见《路加福音》2:34;《马太福音》10:34-39),那么,皈依者自己也会经历各种人际间的分离和决裂。不过,他同时也可以体验上帝赐予的无限喜乐。” 显然,从基督宗教根本教义的视角看,对于基督徒来说,为了体验上帝赐予的无限喜乐,这种人际分离和决裂其实是一种必要的、甚至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而全部问题就在于:从基督宗教根本教义的视角看,皈依者所信仰的主,恰恰又要求基督徒在爱上帝的同时爱邻人,亦即维系和巩固人际间的和谐和统一。
就此而言,如果说在引发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冲突战争方面,各大宗教在灵性生活中的深度信仰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仇恨始终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的话, 那么,具有极度反讽意味的是,在引发历史上基督宗教针对其他宗教所发动的宗教冲突战争方面,可能就连基督宗教爱的福音自身,也在伦理方面负有不容推卸的重要责任,因为它明确要求:基督徒应当仅仅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去恨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与他们生疏乃至动刀兵。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宗教提倡的“爱的福音”,其实并不是针对全人类的“福音”,而只是针对那些已经或者将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们的“福音”——“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以弗所书》6:24)对于那些弃绝上帝、终不悔改的非基督徒亦即“不义罪人”来说,它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一种“祸音”:“你有祸了!”(《马太福音》11:21)保罗在告诫门徒应当诚心爱人、不要以恶报恶时引用的旧约一段话语,或许可以充分体现“爱的福音”的这种黑色幽默意味:“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罗马书》12:20)毋庸细说,这一点当然足以表明:基督宗教主张的“亦此亦彼”的既爱上帝、又爱邻人,最终必然会在深度悖论中变成“非此即彼”的只爱上帝、不爱邻人。
五
进一步看,就连基督宗教提倡的那种对非基督徒作为“上帝造物”的邻人之爱,在本质上同样也不是出于非基督徒是“人”这一事实,而首先是出于非基督徒作为“上帝造物”依然拥有皈依基督信仰、达到神性至福的潜在能力这一理由。换句话说,基督宗教提倡的这种对非基督徒的邻人之爱,也不是为了他们作为邻人的缘故、把他们当作“人”来爱,而首先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把他们当作“上帝造物”、乃至当作所谓“天生的基督徒”(德尔图良语)、“潜在的基督徒”或是“匿名的基督徒” 来爱。
事实上,耶稣在一些教诲中体现的那种主张爱罪人可以胜过爱义人的倾向,只有基于这一点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他在回答自己为什么要和罪人一同吃饭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9:12-13)倘若这里所谓的“罪人”之“罪”仅仅是就基督宗教的信仰层面而言、亦即仅仅是就这些罪人“不爱上帝”而言,那么很明显,首先,耶稣并不会因为罪人是“人”而更爱他们,也不会因为罪人是“上帝的造物”而更爱他们,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罪人与义人之间并无二致;其次,耶稣同样也不会因为罪人不爱上帝而更爱他们,因为按照耶稣自己的有关教诲,这是这些罪人应当被“生疏”的直接原因。毋宁说,耶稣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出于凭借更大的爱而使这些罪人皈依基督宗教、成为爱上帝的基督徒、最终达到天国至福的动机,也就是他自己业已提到的“召”的动机。所以,在另一个地方,耶稣便清晰地宣布:“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7)至于耶稣主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倘若这里所谓的“仇敌”和“逼迫”仅仅是就基督宗教的信仰层面而言,也应该作如是解,亦即不是因为这些逼迫自己的仇敌是“人”,而是因为他们依然还有可能皈依基督宗教而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耶稣向曾经采取种种手段逼迫他的门徒的保罗显现,使其蒙召归属基督、到处传布福音,便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结果,即便这种对非基督徒的更大的爱,最终也还是被还原到对上帝的神性之爱那里。
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对非基督徒作为“上帝造物”的邻人之爱,最终只会导致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非基督徒由于被基督徒对他们怀有的这种更大的爱所感动而幡然猛醒,接受爱的福音,皈依基督信仰,摆脱迷失状态,成为也爱上帝的邻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或许不再有资格继续享受基督徒对非基督徒所怀有的那种更大的爱,却必然有资格开始享受基督徒对基督徒所怀有的教友之爱,并因此免除被“生疏”或是“动刀兵”的危险。第二种结局是:非基督徒尽管充分感受到了基督徒对他们所怀有的更大的爱,却依然执迷不悟,拒绝皈依基督宗教,坚持不愿去爱上帝,决心要在全无福音或是异教信仰的苦海深渊中沉沦下去、度过余生,也就是所谓的“终不悔改”。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非基督徒在天国里达到神性至福的可能性已经丧失殆尽,在基督宗教看来,他们当然也就会因此失去被基督徒继续爱下去的资格,以致只能等待着最终在地狱里遭受严厉的惩罚。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曾经以长时间不能结实的无花果树必然被砍掉作为比喻,公开宣布:“你们如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3)保罗也曾明确断言:“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20-22)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义人是否应当出于诚爱去爱罪人的问题时,同样断然指出:“在此岸生活中,有罪的人们依然具有获得永恒至福的可能性。不过,对于那些已经迷失在阴间地狱、因而在这方面与魔鬼处于同一状态的人们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情况究竟怎样,恐怕不难想象。上面提到的发生在传教运动中的那些悲剧事件,以及发生在宗教裁判所里的那些残酷现象,已经足以表明:即便在此岸生活中,那些坚持不愿抓住达到永恒至福的神性机遇、“终不悔改”的无神论者或是异教徒们,尤其是那些曾经一度怀有基督信仰、后来却又转而放弃这一神性机遇的叛教分子,也有可能被提前送进地狱,遭受严厉惩罚。换句话说,在第二种结局中,无论在此岸生活里、还是在彼岸生活中,基督宗教爱的观念所肯定的基督徒对于非基督徒作为“上帝造物”的邻人之爱,都必然会被基督徒对于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的神性之爱根本消解。
诚然,神学家们也许会辩解说: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在此岸生活里,基督徒应当始终坚持他们对于那些“终不悔改”的非基督徒的邻人之爱,因为作为“上帝造物”的基督徒自己,并没有权力“论断”或是“审判”非基督徒;只是在非基督徒由于“终不悔改”的缘故而受到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之后,他们才会在彼岸生活中遭受应有的惩罚。不过,这一辩解并不能够改变上述结论。这是因为,既然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彼岸生活同样也是真实的生活、甚至是比此岸生活更真实的生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邻人之爱,最终还是在更深度的灵性层面上被基督徒对上帝本身的神性之爱所否定。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尼采才会明确指出:“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应当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宗教之所以会具有特别强烈的传教动机,可能也与上述悖论内在相关。这是因为,从理想化的视点看,两条爱的诫命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绝对完美的和谐统一:一切人都成为基督徒、都能够爱上帝,从而每个人都可以既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上帝,又做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一切人,最终实现基督宗教十分推崇的普世之爱。就此而言,两千年来基督宗教不断展开一波又一波的传教运动,力图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世界各地,在使全人类都能爱上帝的基础上使基督宗教成为本真意义上的“普世教会”,其深层的心理动因之一,或许也就在于爱上帝与爱邻人之间的上述悖论在基督宗教的“集体潜意识”中所诱发的那种焦虑不安,那种想要消解其中的张力冲突、实现完美的和谐统一的急切渴望。(参见《哥林多前书》9:16-23;《彼得后书》3:9)
不过,严格说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爱的诫命深度悖论的最终消解,也仅仅是具有纯粹理想化的抽象可能性。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作为整体的基督宗教内部,始终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教派。这些教派的成员往往也会仅仅由于在爱上帝的具体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而无法在基督徒彼此之间做到爱人如己,亦即无法去爱那些采取其他方式爱上帝的基督徒,有时甚至还会因此造成彼此之间的深刻仇恨和严重冲突。换句话说,某些宁肯采取这种方式爱上帝的基督徒,不愿去爱那些宁肯采取另一种方式爱上帝的基督徒,有时候甚至还会因此在彼此之间“动刀兵”,因为他们坚持认为:采取其他方式爱上帝,就是不合上帝旨意、犯下异端之罪,就不可能真正获得救赎、达到神性至福。其实,在新约中,这一点已经初露端倪,因为保罗一方面明确要求基督徒们“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哥林多前书》1:10),另一方面却又郑重告诫他们:“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1:9)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导致基督宗教内部产生这些仇恨冲突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那些属于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们没有严格贯彻耶稣提出的两条爱的诫命;相反,恰恰正是由于他们严格贯彻了耶稣提出的两条爱的诫命,尤其是由于他们严格坚持把爱上帝的诫命置于爱邻人的诫命之上,才最终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彼此不能相爱。换句话说,导致基督宗教内部这种不爱邻人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基督徒们最终没有严格履行爱邻人这个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不如说是由于他们首先严格履行了爱上帝这个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这一事实当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表明:在爱上帝与爱邻人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爱上帝最终必然会压倒乃至否定爱邻人。 六
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在“爱是不可能命令的”意义上说,爱的诫命已经是一个深刻的悖论;而在对人来说它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个更深刻的悖论。 不过,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说,基督宗教爱的诫命在伦理方面所蕴含的最深刻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它明确主张爱上帝构成了爱邻人的本原根据,强调爱邻人是爱上帝的扩展完成,坚决要求基督徒应当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进一步去实现普世性的爱邻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坚持爱上帝的诫命对于爱邻人的诫命具有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它又不得不要求基督徒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爱上帝、而不惜放弃派生从属的爱邻人。至于这个深度悖论的反讽意味,我们可以从下面的陈述中略见一斑:一方面,基督宗教把爱上帝确立为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并且从中派生出爱邻人这个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基督宗教把爱上帝确立为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结果反而导致了爱邻人这个第二条次重要的诫命不可能真正实现。或者说,本来植根于爱上帝之中、甚至被认为是爱上帝的扩展完成的爱邻人,最终反而会被它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本原根据——爱上帝本身所否定。
毫不奇怪,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就像基督徒们一样,基督宗教崇信的上帝自身也会面临一个十分相似的深度悖论, 亦即西方一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所讨论的上帝的“爱”与“公义”之间的矛盾。 诚然,按照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而且“不偏待人”(《罗马书》2:11),以致他可以凭借他的全能一视同仁地去爱作为他的造物的所有的人。不过,问题在于:上帝是否可以像他爱那些爱他的基督徒那样,去爱那些不爱他的非基督徒?毕竟,上帝在本身就是“爱”的同时,还是无可否认的“公义”,乃至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17:31);甚至就连上帝的“爱”本身,也必然包含着这种“公义”,因为耶稣明确指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约翰福音》14:21)因此,按照基督宗教明确认同的这种“公义”,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孝父母、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撒谎、不贪婪,乃至可能要比某些基督徒具有更高尚、更优秀、更杰出的道德品格,也依然会仅仅因为在爱上帝这个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方面悖逆上帝旨意、背离上帝之道而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并且由于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而受到至高上帝的严厉惩罚。因此,《约翰福音》3:16-36明确指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说得也很明白:“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马书》2:3-5)奥古斯丁同样公开坦承:“如果我不爱你,你就对我发怒,并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 毕竟,即便上帝的无限怜悯,也只能指向那些虽然曾经犯下各种世俗罪行、最终却能顺应福音悔改、转而皈依基督信仰之人,而决不会丧失原则地指向那些在不爱上帝这一“罪行”方面“终不悔改”之人。否则,倘若全能的上帝完全放弃这种“公义”,毫无保留地宽恕原谅那些不爱上帝、终不悔改的非基督徒,从而像对待基督徒那样一视同仁地对于非基督徒普施关爱,作为一位“嫉妒”的上帝,他又该如何禁止世人跪拜偶像、崇信邪神,确立自己唯一至上的神性存在,并且维系世人对于自己作为“独一的主”的排他性信仰?
一些现代神学家曾试图以各种方式解答这个发生在上帝的爱与公义之间的深度悖论。例如,卡尔•巴特在论及那些以上帝为敌的人们时就明确指出:“上帝的爱也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燃烧,不过是作为消耗和摧毁他们的灰烬的火。” 保罗•蒂利希则从上帝就是爱自身的立场出发,强调上帝对那些违背“公义”的人们发出的“神谴”其实也是一种“爱”: “这种神谴不是爱的否定,而是爱的否定之否定。……审判是一种爱的行为,因为它让那些抗拒爱的造物归于自我毁灭。……当神性之爱终结时,存在也就终结了;神谴只能意味着造物被置于它自己所选择的非存在之中。……一个有限的存在可以疏离上帝;它可以无限期地拒绝与上帝和好;它可以被抛入自我毁灭和彻底绝望之中;但即便这种结果也是神性之爱的作为。” 无疑,按照这些解释,上帝对于所有世人(包括那些不爱上帝的非基督徒)的无限之爱,的确可以得到一以贯之的完美实现。不过,历史上那些仅仅由于“不爱上帝”这个纯粹宗教性的原因便被送上火刑柱的正直善良的叛教分子、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们,大概会觉得这种“爱”未免包含某些黑色幽默的冷酷意味。其实,倘若我们采取“换位思索”的方式想象一下,假如那些曾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或是仅仅因为信仰差异就残忍迫害正直善良的基督徒的人们以同样的口吻宣称:他们这样做,恰恰体现了他们崇信的上帝或神灵对于耶稣以及这些基督徒的神性之爱、以便在爱的否定之否定中使后者通过自我毁灭被置于后者自己所选择的非存在之中,不知这些神学家们又该作何感想?
其实,与上帝的爱和公义之间的深度悖论相比,基督宗教爱的诫命所包含的深度悖论,在本质上是一个更有现实意义、内涵也更为深刻的悖论。归根结底,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宗教信仰领域的理论上的悖论,而首先是一个涉及人际道德领域的实践中的悖论;因此,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神性的上帝将会如何在彼岸世界中对待非基督徒的神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涉及到作为人的基督徒应当如何在此岸世界中对待同样作为人的非基督徒的伦理问题。就此而言,这个深度悖论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更直接、更密切的关注。
这里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包含着上述深度悖论,以致它提倡的爱邻人诫命在与爱上帝诫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就仅仅是强调爱上帝、而完全不强调爱邻人。相反,正如新约文本和众多神学家的理论阐述所表明的那样,基督宗教的确十分强调爱邻人——包括爱那些身为非基督徒的邻人——在灵性生活的层面上对于基督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而且,与某些思想家提出的批评相反, 基督宗教对于爱邻人的这种强调,就其本意而言也不是一种虚伪造作的矫饰欺骗。毋宁说,基督宗教代表人物对于爱邻人诫命的积极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诚意向;甚至,他们之所以会极力肯定爱上帝诫命的本根至上地位,也是试图为普世性地实施爱邻人诫命最终确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神性信仰基础。此外,如上所述,在爱上帝与爱邻人两条诫命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和谐统一的一面;并且,这种和谐统一的一面,也的确对基督宗教世界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产生了积极正面的深度效应。因此,公正地说,正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或遗忘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残酷迫害叛教分子、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们的悲剧事件一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或遗忘许多基督徒对于全人类——包括非基督徒——做出的巨大的慈善贡献。全部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基督宗教代表人物对于爱上帝诫命的本根至上地位的极力肯定,反过来又导致了两条爱的诫命之间的张力冲突,乃至最终导致了他们真心希望在爱上帝诫命的基础之上实现的爱邻人诫命不可能真正实现。换句话说,上述悖论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就对非基督徒没有任何真诚的爱,而只是意味着这种真诚的爱最终会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受到消减和否定。就此而言,基督宗教对于爱邻人诫命的真诚肯定,恰恰从一个角度突显了两条爱的诫命之间悖论的深度意蕴——唯其真诚,更显深层。
最后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基督宗教爱的观念、尤其是爱邻人诫命中所包含的那种指向全人类的普世性因素,的确可以为今天人们建构所谓的“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不过,这一观念内在蕴含的深度悖论,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本真性普世伦理的建构,本真性普世之爱的实现,只有可能建立在某种普遍性的人本主义——亦即把每个人都首先当作“人”来对待——的本根至上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特异性的神本主义——亦即把某个特定的“上帝”当作一切人都应当崇拜的信仰对象——的本根至上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宗教只有不再把特异性的爱上帝当作普遍性的爱邻人的本根至上的终极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在理论上确立它大力提倡的爱邻人的普世理想。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基督宗教最终不再把特异性的爱上帝当作本根至上的终极原则,它是否还依然是基督宗教?
这,或许是基督宗教在这个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