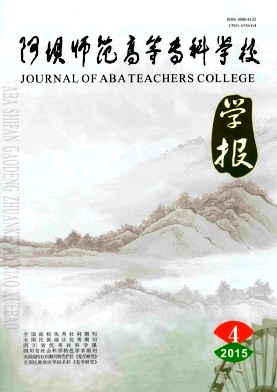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下)
黄玉顺 2003-04-24
五.儒家伦理学的关系映射推定
前面说到,中国思维推衍形式的特征可以叫做“关系映射推衍”,这同样适合于儒家从心性论到伦理学的推衍过程。
儒家有一个向来为人们所忽视的极为重要的观念,叫做“推”:“推己及人”、而且“及物”。此“推”乃是知行合一的,既是“知”(推求),也是“行”(推行)。其实,其他各家也都讲“推”,例如号称“谈天衍”的阴阳家驺衍,其基本方法也是“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以至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有两方面的推:时间上的“五德终始”是阴阳五行纯粹关系的映射推衍,空间上的“大九洲”也是从一九(小九洲)到九九(大九洲)的纯粹同构关系的映射推衍。但儒家的“推”有其特点,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溅起一圈圈的涟漪,一层层地向外波及。这水面便是世界、尤其人伦世界,这石子便是性情(未投为性,已投为情)(41),而这涟漪便是仁爱所及;圈层从中心到边缘,在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异,便是所谓“爱有差等”;最终毕竟波及整个水面,便是修齐治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孟子谈这种“推”:“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我们这里的讨论暂时不涉及“行”,而专言“知”。“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这种“扩充”之“推”,就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
朱熹谈到《中庸》时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这就是说的《中庸》形上的心性论前提与其形下的伦理学定理之间的推衍关系。但实际上是《大学》的“三纲八目”把这种推衍关系进一步细化了,是最为典型的从心性论向伦理学的层层映射推衍过程:
1.心灵伦理结构——修身
前面说过,“八目”当中的格、致、诚、正,其实都是修身;所以,第一层次的映射推衍乃是修、齐、治、平。这种推衍乃是一种“扩而充之”的程序,即体现为时间上、空间上的扩展,所以《大学》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何者为先?按心性论,当然以身为先,以己为先,以心为先。这就是《大学》和《中庸》的共同格局,《大学》指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中庸》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亦即首先确立作为推衍根据的原初结构:心灵结构。而在儒家,这种心灵结构本身已是伦理结构,亦即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所以可称之为“心灵的伦理结构”。
但修身本身又有其内在映射推衍,亦即《大学》的前四条目格、致、诚、正。我的意思是说,并非格致诚正四者是一个心灵结构,而是它们各自都是心灵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这种结构关系之间的映射推衍:
(1)格物:事理结构
儒家把“格物”作为“初学入德之门”的第一步,意义在于确立映射推衍的根本结构。程颐解释“格物穷理”时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遗书》卷十五)所谓“万物皆是一理”是说万事万物具有共同的关系结构,只是“理一分殊”、“月印万川”,所以可以“类推”。再次强调,不能把“类推”理解为“类比推理”。根据上文对“类”与“推”的讨论,“类推”就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所以他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遗书》卷十八),这个“照”字用得好,正是说的映射。其实,西方的“逻辑”也跟“理”一样,“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逻各斯”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
关于“格物致知”,这是关于儒学的一大公案,我不想在这里啰嗦。简单说,我把“格物”视为确立“事理结构”,这并不是“唯物反映论”的观点。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心性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所固有的德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这就是说,五官的好恶是命,五常的精神是性;合起来说即是“性命”,都是天性天伦。因此,我们对“格物致知”之“物”也须按儒家自己的正宗理解来讲:(1)这个“物”不是实体,而是“事”“事理”。这是汉儒以来的公论,如郑玄说:“物犹事也”(《礼记注》);程颐则说:“物犹理也”(《遗书》卷十八)。(2)这件“事”是人自己的事,也就是人自己的人伦存在;这个“理”就是人的伦理,亦即人伦关系。朱熹指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语类》卷五)(3)这种人伦存在本质上是心灵存在,伦理本质上是“心之条理”。朱熹指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语类》卷九、卷十七、卷一百)王阳明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诸阳卷》);“虚灵(心)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用儒家的话语讲,事理与心灵是“知行合一”“打做一片”的。
此固有的心灵存在之所以需要格而致之,乃是基于儒家的一个基本设定:世俗的人心由于感物而动,逐物而迁,总是处于遮蔽状态(故荀子有凭心“解蔽”之说),就必须使之“明”而“诚”(《中庸》)(42)。程颐指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遗书》倦二十五)王阳明则直接把“格物”讲成“正心”,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上》)。其实整个“修身”都是“解蔽”“正心”,亦即确立心灵结构。
(2)致知:认知结构
严格来讲“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如朱熹所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语类》卷十八)所以王阳明讲,一旦身临其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而此“身临其境”,其身亦心,其境亦心。不过从程序上来讲,还是有个先后:先入于事理,才至于认知。程颐指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遗书》倦二十五)所以《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于是,事理结构便映射为知识结构:致知的结果,便是确立了心灵的认知结构。这在过去被称为“体悟”或“体验”,被理解为“直觉”,实质上是心灵的一种自返的映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从格物到致知,不是心灵的“外界反映”,而是心灵内在的“自我映射”:事理结构本是浑全的心灵结构,认知结构只是心灵结构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会自我映射?这涉及对心灵结构的分析。心灵的结构有两方面,即认知和意向。在西方观念中,对心灵的结构有两种划分:三分法,知、情、意(如康德);二分法,即认知(感性、理性)和意向(情感、意志)。(43) 中国观念与二分法类似,这可以从儒家对“圣”的规定中看出来(在儒家观念中,“圣”不外乎心灵的归真返朴)。“圣”有两个方面:“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公孙丑上》)可见“圣”就是“仁且智”。这里“致知”侧重体现了“智”的方面,下面的“诚意”侧重体现了“仁”的方面(“仁”之为“意”是一种“欲”,即孔子所谓“我欲仁”)。
具体来说,所“致”之“知”的内容仍是伦理结构的内容,亦即“良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王阳明《与顾东桥书》)孟子解释良知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尽心上》);展开来说,则是仁义礼智。所以,认知结构只是心灵伦理结构的一个方面。
(3)诚意:意向结构
上面谈到,“致知”和“诚意”是分别地确立心灵结构的一个方面(44)。在对“意”的理解上,刘宗周的“意蕴于心”之说是准确的(《周子全书·语录》),“意”只是“心”的一个内在方面。“意”之为“欲”,有善有恶:“人欲”为恶意;“我欲仁”为善意,即诚意。孟子也对此有过论述:“可欲之谓善。”(《尽心下》)不“可欲”即恶意;“可欲”即“我欲仁”,故“善”,即是善意;而“有诸己”,即是发自内心的诚心,所谓“诚心诚意”。所以,“诚意”所确立的是心灵的“意向结构”。
前面说过,《中庸》以诚为本:人之本,物之本,天地之本。《大学》也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但这儿也有一个先后,《大学》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为什么呢?因为“诚”的意思是“不自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你既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良知(致知)了,也就无法欺瞒自己了。所以,诚意既是致知的映射,也是事理结构的关系映射;而归根到底是心灵伦理结构的映射。
(4)正心:心性结构
致知、诚意分别确立了心灵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以后,自然回归心灵的整全结构,于是就有了“正心”的步骤,亦即整体地确立或者重建“心性结构”。从最初的事理结构到这里的心性结构,就是纯粹关系的同构关系,显然也是关系映射。心性结构的具体内容也是伦理关系,即孟子讲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种心性结构确立起来之前,我们可能行无所得,于是,我们应该“反身而诚”,亦即孟子所说的:“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最后一句“天下归之”,展开了以下的从形上的心性论原则向世俗的伦理学原则的映射推衍进程:
2.宗法伦理结构——齐家
在讨论“齐家”之前,我们先对“修”和“齐治平”的总体关系作一个交代。《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内在未发的心灵结构,也就是“仁爱”之“性”;“和”是已发向外的人伦结构,也就是“义礼”之“情”,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有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个意思(《学而》)。这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关系映射推衍(参见表三)。
八目中的齐家是心灵结构从内向外扩展的第一步,是宗法家庭伦理的关系结构。有关的常见说法,五教:“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外平成。”(《左传·文十八年》)五伦:“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五典:“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舜典》孔安国传)五品:“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五常:“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尚书·泰誓》孔颖达疏)几种说法的对应关系如下:
五品: 父 母 兄 弟 子
五教五典五常: 义 慈 友 恭 孝
| | | | |
五伦: 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 |
| | |
| |
父子有亲
这里的重心不在父母兄弟子五个实体,而在义慈友恭孝五种关系,这是一种情感的、具体说是道德情感的关系。在传统的“礼乐”文化格局中,“有叙”“有别”是“义-礼”的体现,“有亲”是“和-乐”的体现。
儒家明确指出,这种家庭人伦是与五行对应的,《礼记·乐记》“道五常之行”,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疏:“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依金木水土之性也”。难怪董仲舒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繁露·五行之义》)这其中最根本的是夫妇二元关系,即阴阳两仪关系,故《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周易》以八卦的关系来概括宇宙天地人物,其中乾坤两卦是夫妇,其余六卦是他们的子女(《说卦》)。李贽曾经指出:“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夫妇论》)这都表明,在整个修齐治平的“外王”序列中,家庭伦理关系乃是根本结构。
3.政治伦理结构——治国
在上述“五伦”中,“君臣有义”就是治国方面的政治伦理结构(注意:此“臣”包括“民”,即“臣民”)。这种结构在《尚书·洪范》中已有相当充分的表述,诸如“八政”“皇极”“三德”。儒家对君臣关系之关注,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孔子曾经将全部人伦问题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问题在于:这种关注的实质何在?其实,儒家关于政治伦理结构的思想源于周公,周公早已建构了如下一种三角关系:
天
↙ ↖
王 → 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45) 儒家的不同派别,不过侧重这个三角的某一条边。民直接决定天,即间接决定王,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在儒家,基于作为当时的主导意识的宗法观念,政治伦理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映射,所以历代君主常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这种政治伦理结构的根本还是心灵伦理结构,即“治国”是“修身”的映射。这就是孟子讲的“居仁由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居仁即据于心,由义即行于政。所以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反之,“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滕文公下》)。《中庸》也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智、仁、勇是心灵伦理结构的确立,它能映射而推衍出治国之道。
4.人际伦理结构——平天下
在五伦中,“朋友有信”是最富于现代精神的。朋友一伦的提出及得到强调,是因为人际关系不止父子、君臣,“平天下”也不仅仅是政治伦理问题,必须回答其他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儒家建立了两个层次的映射:一是“朋友”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朋友;二是更进一步的“兄弟”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吾同胞”(张载《西铭》)。这里仍然是以家庭伦理关系视为映射推衍的根据。
这方面,儒家提出了“信”的伦理原则。“信”就是“诚”(二字同源),故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尽心下》)“信”之为“诚”,当然本之心灵结构,所以归根到底,“朋友有信”也是心灵结构的关系映射。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这是推己及人的映射推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所谓“推恩”,就是推爱。
5.世界伦理结构——及于物
这种“推”不仅及于所有人,还及于所有物,遍及宇宙世界。所以,儒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伦理的世界。这与西方现代的“意义世界”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区别在于:西方的世界观仍是一个实体的集合,儒家的世界观则是一个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46),而是人伦的。西方关于“意义世界”的观念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科学主义的建构,如分析哲学的逻辑语义学的“意义”理论;一是人文主义的建构,如某些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47)。后者更为接近中国儒家的传统。但是儒家建构的意义世界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人伦的:我们记得前文说过,儒家之赖以进行关系推衍的元结构“两仪”和“五行”,本身就已经是伦理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学本身就有存在论的意义。
儒家传统是通过“推”、亦即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来建构其伦理世界,这种“推”的两大层次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就是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在这方面,张载的《西铭》是个典型的文本,他把天地人物视为一个伦理世界,最后得出了一个著名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
至此,儒家通过纯粹关系映射推衍,由心性论而推出了伦理学的全部原则(参见表四),整个宇宙因此而呈现为一个伦理意义世界。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大学》三纲八目的推衍程序也可分为这样两大阶段:修(格致诚正)是“仁”,齐、治、平是“义”。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以“行而宜”(适宜、适当、恰当)释“义”,这是中国哲学各家的共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中国“义”“仁义”的观念和西方“正义”的观念。西方所谓“正义”(justice)具有这些基本语义:适当,恰当,正当,正义,公正,公平。这些语义其实正是汉语“义”“宜”的意思。换句话说,“义”即儒家的“正义”观念。但是,西方的正义观念根据于理性,而儒家的正义观念根据于情感:义出于仁,仁乃是爱,爱属于情,情即是性。(48)正义是仁爱的映射,仁爱是心性的映射,这就是儒家伦理学的精神实质。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我按儒家的思维推衍形式,从心性论推出了伦理学,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儒家的立场。其理由很简单:我可能并不采纳儒家的那种思维推衍形式,甚至于并不采纳儒家的初始预设条件。但这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西方哲学的立场,理由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是王国维所说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在这点上,我是同意康德的:意志(考虑到中国哲学,还应该加上情感)高于理性。至于意志、包括情感的普遍性,那是只能另文讨论的问题了,我只是想指出一种事实:中国人认为这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恰如西方人认为那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他们何以如此认为?显然,这里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理”,然而这个“理”却不是思维本身的事情、而显然是所谓“信念的确立”(皮尔士语)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却不是本文的任务。
注释:
1、 孔子直接论“性”的,只讲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令其学生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2、 荀子首次将子思与孟子并提。
3、 在重“心性”这一点上,理学和心学并没有本质差异。详见下文。
4、 当代新儒家的鼻祖熊十力先生,就是公然标榜王学的。
5、 本文根据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庸》据传是由子思所作,今为《礼记》的一篇,至少可以肯定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
6、 包括最新出土的郭店楚简。《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整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李匡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例如《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商务1978年版。
9、确立理论理性在现象界领域的合法性、实践理性在自在物领域的合法性,都是理性自己“设立一个法庭来保障它的合法要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A vii?/FONT>xii;《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239页,商务1982)
10、“合理”和“合法”,西语有三类表达,语义一致:legal(合法的、法律的,法定义务的)或者legitimate(嫡出的、正统的,合法的、合理的);Lawful(合乎自然法则的,法定的,合法的);Rightful(合法的,正义、公正、正当的=just)。这里有四个重要观念联系在一起:正统,正当,合法,合理。
11、 确立信念的四种可能方式: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理性主义)、科学的方法(经验主义)。皮尔士只承认最后一种合法。
12、 康德:“现在通过详细分析理性的实践应用我们就会明白:这里所想到的实在性并不涉及范畴的理论规定和知识向超感性界的拓展,……因为这些概念或者包含在先天必然的意志决定之中,或者与意志的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实践理性批判》,第4页,商务1999。
13、 康德:“当事关决定人类心灵一个特殊能力的源泉、内容和界限时,……还有第二个更具哲学意味和建筑学意味的应行注意之点:这就是说,要正确地把握整体的理念,并且从这个理念出发,在所有那些部分的彼此交互关联里面,借助于从那个整体的概念将它们推导出来的方式,在同一个纯粹理性的能力之中考虑这些部分。”同上,第8页。
14、 同上,第14页。
15、 墨辩逻辑是否也是这样的规则,这是一个尚无定见的公案。
16、 康德所谓的理性自己为自己设立法庭、自己为自己作证,这样的做法本身仍然可被质疑:是谁赋予了理性以这种合法性?在我看来,这跟康德所嘲弄的“有人想通过理性证明理性不存在”一样是荒谬的,理性同样不能证明理性自己的绝对权威。
17、 我用“结构”这个词,实在是现代汉语的无奈:这个西来的structure实与中国“结”“构”观念有所悬隔。
18、 这使我们想起维也纳学派的经典之一、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西方哲学家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这种工作。
19、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洪范》文本形成的时代很晚,大约是在战国;但也并不否认,“五行”的观念是很原始的。根据《洪范》所载是殷箕子为周武王陈说,应能肯定这是殷人的观念。
20、 这是我要另文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2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
22、 黑格尔:《小逻辑》,第78、120页,商务。
23、 转以自《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1983。
24、 此说出自周敦颐《通书·理性命》:“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25、 参见拙文《生命结构与和合精神——周易哲学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6、 此所谓“气”也非西方那样的实体概念,我们千万不能按西方现代科学概念来理解这个“气”,以为它是由什么化学元素组成的。
27、 至迟自东汉郑玄以来,儒家都同意此说。
28、 这种“二五合凝”发端于春秋思潮,而完成于战国阴阳家。
29、“宗”原意指祭祖的宗庙,它是宗法关系在观念、制度、器物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30、 我不用“演绎”这个词,以免导致误解。“演绎”通常是说的deduction,但它本来是个中国的术语,如朱熹在谈到子思作《中庸》时就说:“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中庸章句序》)此“演绎”与deduction的意思大相径庭。《洪范》讲“稽疑”时,说到“衍忒”,意为“推变”。兹用此义。
31、 我这里说的“映射”不是现代数理逻辑所讲的那种映射关系。
32、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认识”问题悬为基本问题,即便是在所谓“本体论”时代,认识论也是基础的,本体论问题是在认识论境域中才得以呈现的。“现象”这个观念已经预设了呈现者(谁或什么呈现:现象的本体、本原、本质)、接受呈现者(向谁呈现:认识的主体)。
33、 此所谓“二元”也不是西方的dualism,西方之所谓“元”基于mono(区别于语义学之所谓“元”meta),亦即基于第一实体。
34、 朱熹章句说:“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
35、 这与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不矛盾,只是其思路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36、 邵雍谓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
37、 按西方逻辑的正统观念,“类比”并不是“推理”。
38、《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就是一种纯粹关系。
39、 现代西方哲学有些变化,伦理学问题已被置于存在论层面上来加以思考。
40、《宋史·邵雍传》说:“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41、 朱熹理解《中庸》思想: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而“中节”为“天理”“中和”,发而“无节”为“人欲”。
42、 感物致恶的设定,蕴涵着儒家哲学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另文讨论。
43、 再次强调,此“意向”不是胡塞尔Noesis的用法。
44、《墨子·小取》曾分析过这个问题:“智(即知)与意异。”
45、 在我看来,这是周公在思想史上的最重大的贡献。此前的殷商观念,没有“民→天”这个维度。
46、 此所谓“自然”指西方的nature,而非中国儒道两家的“自然”(自己如此)。
47、 在我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属于科学主义的东西,不同于海德格尔、萨特等的取向。
48、 朱熹的看法,情是已发之性,性是未发之情。
附表1(《洪范》纯粹关系范畴结构):
附表2(心性关系结构映射):
附表3(“修”与“齐治平”之总体关系映射):
附表4(从心性论到伦理学的映射推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