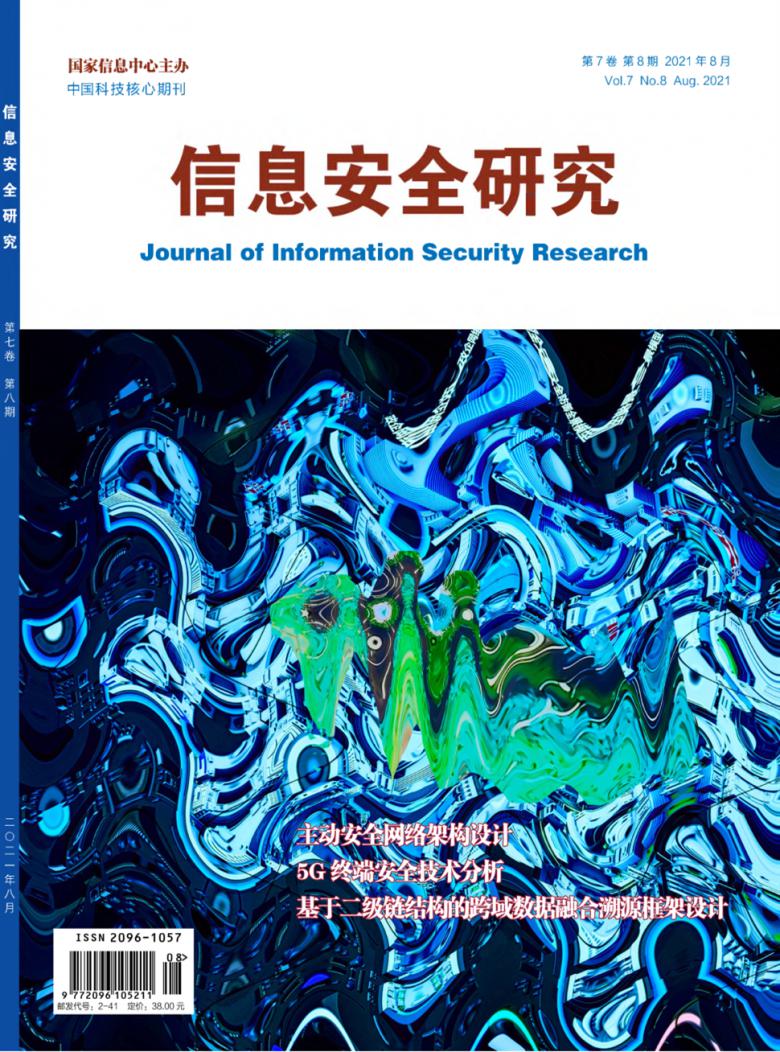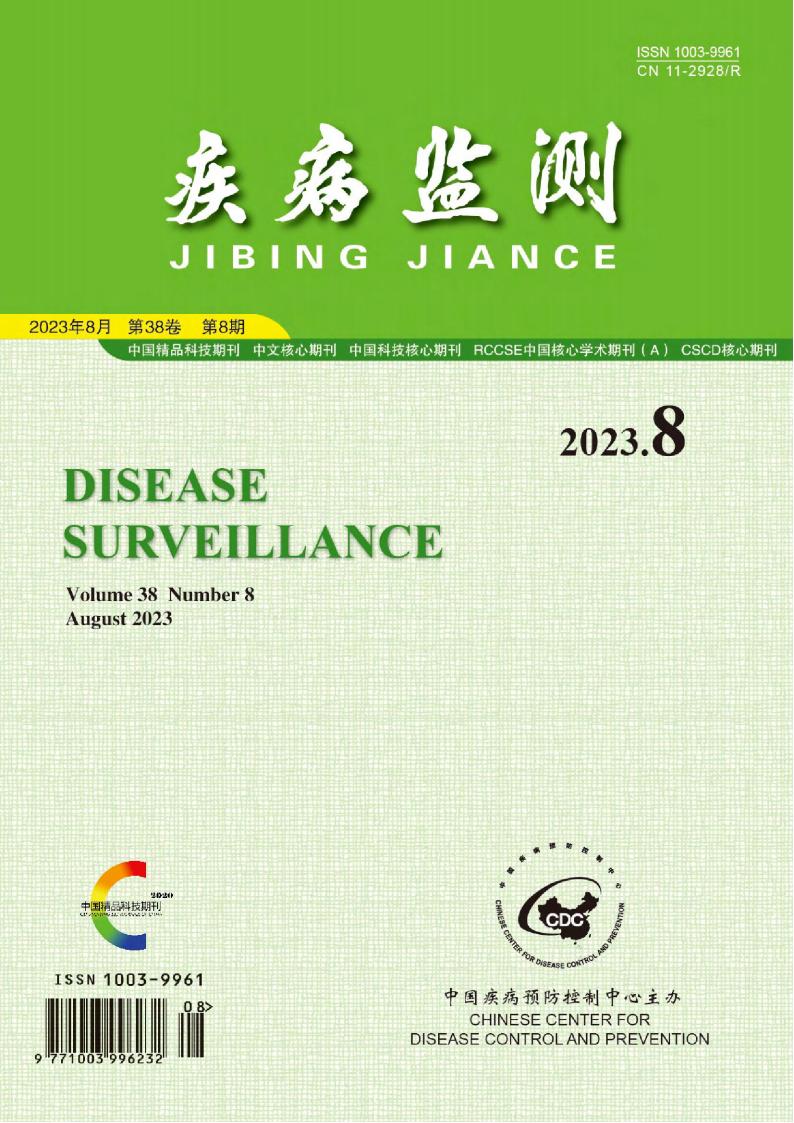试析中国传统社会诚信缺失的伦理学思考
叶青春 2010-12-05
论文关键词:诚信名教道德理想主义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诚信缺失并非今日始有,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首先日益内在超越的儒家伦理思想,专注于不仅是伦理学意义,而且是本体论意义的“诚”,忽视了作为外在行为准则的“信”,其次,名教在统治者操纵下名与实不符,而名与利相符;最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对道德人格的要求与人的现实层面和社会道德现实构成巨大反差,滋生大量虚伪欺
诚信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其实,诚信问题并非今日始有,诚信的缺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只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人们的社会交往日趋频繁,诚信问题才日益凸显。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追溯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思想、社会根源对当代中国建立诚信社会应该是富有启发的。
一、日益内在超越的儒家伦理/思想,专注于不仅是伦理学意义,而且是本体论意义的“诚”,忽视了作为外在行为准则的“信”
春秋之际,周文疲弊,礼坏乐崩,“信”问题日益突出。迄至战国,终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也从《论语》对“信”的呼喊日趋转向《孟子》、《中庸》对“诚”的宣扬并使“诚”本体化、内在化。宋明理学把这一趋向推向极致。因而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旨趣在具有超越性、先验性、内在自主性的“诚”,而不是具有外在行为标准特征的“信”。
春秋之际,周礼失去了原有的规范社会生产生活、维系社会生存运转、协调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习惯法作用。社会信任系统也日趋失范无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杀君者有之,子狱其父者有之。因此,孔子一方面极力维护周礼,另一方面大力呼喊“信”。但是要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恢复周礼所要求的信与礼显然是不现实的。既然统治者不能恢复周礼,孔子就把挽救社会信任的希望寄之于个体人格的建立。所谓“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川因此孔子把“信’,作为仁的具体内容之一,当作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之一,川进把信当作为人的根本。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是孔子的呼喊毕竟太微弱了,始于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局面到了战国终于不可收拾,“尊礼重信”也到了曲终和寡的时候了。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实际上随着社会信任系统的全面崩溃,儒家从孟子开始就更强调具有内省超越特征的“诚”来作为“信”的内在根据。“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诚”诊释天道,以“思诚”诊释人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明诚是反身向内,莫向外求。经过主体内在心性修养,经过自我反思便能达到与天道合一。李泽厚先生认为这是“一条内向归宿路线”。余英时先生也指出“战国晚期讲修身的人愈转愈内向,《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是这一内向发展的高峰。不但儒家如此,其它学派的修养论也有同样的倾向”。由于作为外在行为标准的“信”得不到保障,逼使正直之士走反身而诚的内倾道路。
到了宋明理学,“诚”的本体论特征更加突显,更普遍、更超越,同时也更内在。朱熹《中庸章句》第20章言:“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诚是真实无妄之理,同时也是真实无妄之心,心理合一。《朱子语类》卷六言:“诚乃通天人而言,信则人所为之实”。从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言诚,从人的行为的真实不虚言信,可见信更实际更具体也更外在。到了王阳明则更是用心本体论把“诚”的本体性、自主性推向极致。“诚是心之本体”。“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不但坚持了诚真实无妄的基本涵义,而且把诚作为价值理论的最高原则。“是善者心之本体”。诚是至善的心之本体,也就是良知。但这良知、这诚只是主体内心的体验感悟并没有客观标准与外在约束。可能导致各人的自言其诚,各人自致其良知。正如唐君毅所言:“然此王学之致良知之论,更有可为人所假借者,则要在此致良知之论,乃教人自见其是非而自是是非非。于是我自己之是非,可为他人所不得而是非;而我又可自本其是非,以是非天下人,以为此皆所有自致吾良知之是。”在王阳明,诚、良知、心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都是主体内在的体验感悟,而非具体可感的外在体现。
绝对内在的真实无妄、纯而不己之“诚”是儒家追求的道德境界,也因此儒家对“诈”对“不信”极为痛恨。以至于连自己“逆诈”(预料别人要欺骗)“臆不信”(猜测别人不诚信)都不允许。“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先觉者,是贤乎!。因为在儒家看来“夫逆诈,即诈也,臆不信即非信也”。预料别人会欺骗自己,就是自己也有欺骗之心,猜测别人不诚信,就是自己有不诚信之心。但又要求“先觉”即事先觉察。这就要求“良知莹彻”的贤者圣人才能做到。所以一般的“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己”。即使“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 (《传习录》中)这种态度当然有碍子社会信任系统和个人人格信任的建立。被欺诈了不去研究为什么被欺诈、如何才能尽量减少欺诈的发生,而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应该看到: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都不能仅依据内在的超越本体一诚得以建立。当社会生活需要一种标准作为判断诚伪的依据时,本来只是观念世界中的“诚”就可能成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东西,各人各有自己的诚而很难判断其真伪。诚绝不是一套可以遵守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以判断诚伪善恶,以建立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
二、名教在统治者操纵下名与实不符,而名与利相符
名教制度使中国社会极重“名”,因为与名俱来的是利,遂使名教天下虚名假誉层出不穷。
儒家以何为教?曰:以名为教。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个名必须与实相符,否则伪的产生势在难免。所以要正名,使其与实相符,并把正名提到政治的高度。故,“政者,正也”。但孔子所做的也只能是“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并不惧,其微言大义并无多少人理会,但儒家依然把名作为毕生追求之鹊的,而且大部分儒生、儒士也不求与实相符之名,只求与利相伴之名。班固《儒林传》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使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信,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既然名之下有利,大名之下必有大利,那么统治者就操名利之柄,使天下人守名器、争名誉、别名分、设名位、倡名节。利用名教笼络天下士人之心,栓桔天下万民之行。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人吾靓中矣”。而士人以名教为敲门砖,敲开名利之门。士人为利争名,而争名必争名教之名,争统治者所悬赏之名誉、名位、名节。戴遗《放达为非道论》说:“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其弊必至于末伪”儒家重名,尚誉为求兴贤,但名之下有利,所以为逐利而求名者层出不穷。所兴者并非一定是贤者,而极可能是伪饰之徒。余英时说:“许多人为了博孝之名以为进身之阶,便不忌从事种种不近人情的伪饰,以致把儒家的礼法推向与它原意相反的境地”。葛洪《抱朴子》所记汉末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说明了儒家的名教已经高度形式化、虚伪化。形式化是因为有名无实,虚伪化是因为造假求名,二者都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信任系统。下面我们以两个方面分析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名的栓桔之用,笼络之方,网罗之功,并不很在意是否实至名归,名实相符。《管子·枢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韩非子·扬权》言“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名既然只是工具则可御民治世即可也,固不求一定要循名责实,名实相符。陆蛰在《翰苑集·奏章》一语道破:“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则近实而于德为轻”。这样统治者操名(利)之柄,使人汲汲于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日“名教而已矣”。名教之“名”可以说是统治者为教化百姓而有意设立。因而名之真伪并不十分重要。统治者要的是其羁鞍士人、缨锁百姓之功。循名责实也服从其统治目的,决不会责到自己头上。
“名教”只是统治者一个工具,只能用于制人,岂能用于自制?冯桂芬《校分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所言:“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人殷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应是有感而发。名教于是成为有名无实之教。“儒教的真实-一中国文化的一张皮而已”统治者并不要求自己的统治工具“名”符其实,而他们自己的言行则直接危害名教之实。这构成了对中国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的最大伤害。 从儒家的本意看,确如戴透所言:儒家尚誉,本以兴贤。鼓励人们成圣成贤是儒者的初衷。名的内核是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以名劝善、以名策善、或以名为教也的确使许多中国人珍重名誉、行仁取义甚至杀身成仁。但是过分重名常会成为为名而名,往往变成沽名钓誉乃至欺世盗名。《颜氏家训·名实》中有典型一例:“近有大贵,以教著声,前后丧居,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身为大贵,已有教名,依然弄虚作假,行欺使诈以求更大的名。颜之推道出其中的原因:“乃贪名不已故也”。这也是过分重视名的必然结果。当然为名而名还不足以构成对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的致命伤害,更为严重的是为利而名,趋利而为名,欺诈以求名。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求利必须通过求名以获取。于是贪利者纷纷涌进狭窄的名教之门,为利求名,以利求名,然后以名谋利,以利谋更大的名,获更大的利。最终形成求利须谋名,谋名必求利的局面。顾炎武在《日知录·知教》极为沉痛地指出:“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憧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逐成风流,不可复制。”这样名与实逐成水火不容,而名与利则成水乳交融。名实不符而名利相符,社会的虚伪欺诈弃 礼义,捐廉耻又焉能得免?社会信任系统和人格信任又焉能保有?如果说春秋之际名尚不完全操之于诸侯国统治者之后,名与利尚没有如后世之形影相随,那么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之后,名则完全操之于封建帝王之手,一旦有逸出统治者操纵范围之外的“名”,则必禁之锢之戮之,务使天下之名俱操于其手而后罢,务使天下英雄人殷而后罢。而操之于统治者之手的名作为统治工具,必不可求名实相符。名之下隐藏着利,利驱动下求名,根本不顾名实相符,诚信也无立足之地。
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对道德人格的要求与人的现实层面和社会道德现实构成巨大反差,滋生大量虚伪欺诈现象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绝对主义的伦理主张,使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以圣人为目标,以修齐治平为内容,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以排斥乃至否定欲望为本质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想主义与绝对主义道德要求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过高的道德理想与普遍无耻的道德现状之间的巨大内在紧张,是虚伪欺诈产生的膏腆之地,诚信存在的致命之处。
当我们反思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时,我们总能发现道德理想与道德现状之间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伦理思想家弹精竭虑构制一个人至高无上美仑美灸的道德理想的神圣殿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现状特别是以知识分子(儒生、儒士)为主体的封建官场却有众多的人道德堕落、良知丧失。这二者之间的巨大紧张,使得许多人怀疑几千年道德教化的效果。林语堂就感慨:“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么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用“举世无双”形容中国封建官僚的贪得无厌。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但无论道德现状如何,儒家依然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主张,要求所有人成圣。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己,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把只求成为贤人不求成圣者都列人“自弃”之列。但圣人作为真善美的统一体和“天人合一”境界的体现者并非普遍大众所能做到,这一点连理学家们也认识到了。“圣人既没,旷千有余岁,求一人如颜、阂不可得”。也就是说孔子之后一千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圣人,连象颜渊、阂子赛之 类的贤人也没见过一个。尽管如此,儒家也绝不放弃绝对主义、理想主义的道德主张。实际上就是君子也是普通大众难以企及的。当然道德理想人格在任何社会也只是少数人所会追求所能践行成就的,但问题是儒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道德人格的要求愈来愈峻厉、愈来愈苛刻,到了宋明理学这一趋向被推向了极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王阳明日:“静时念念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要求人们超越功利摈弃欲望达到纯而不已的“圣人之心”“天理之心”。实际上道德理想不能脱离社会道德的现实,不能脱离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多重性的现实,面壁虚构纯之又纯的圣人之境,只会导致虚伪人格的出现,使诚信缺失更加严重。杨国荣指出:“理学家以纯乎天理要求人,其结果往往是人格的扭曲和伪道学的泛滥,它表明天理的纯粹形式一旦与道德主体的现实形态相脱离,则道德理想的追求便会成为背离道德的过程”确实如此,宋明之时,伪道学盛行,伪君子随处可见,说明了与道德主体的现实形态、社会道德的现实形态相脱节的道德理想,无论多么堂皇,多么精致,不仅无益于社会的道德建设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虚伪欺诈现象,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道德氛围,从而背离道德本身。
郑家栋意识到“片面地强调人性的超越层面对人性的现实层面及其价值准则缺少应有发掘和重视,这是传统儒家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正是这一缺陷使儒家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主张却无视社会的道德现实和人的现实状态。缺乏符合社会道德现实和人的现实层面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因此“……宋明以来的学者,动辄教人明心见性,超凡人圣。及其末流,许多人滥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无忌惮,晚明政治混浊,满人人关,从风而靡,皆由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中国传统社会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有三:日益内在超越的儒家伦理思想,专注本体论意义的“诚”,忽视了作为外在的行为的,’.信”;名教在统治者操纵下名与实不符而名与利相符;道德理想主义对道德人格的要求与人的现实层面和社会的道德现实构成巨大的反差,滋生大量虚伪欺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