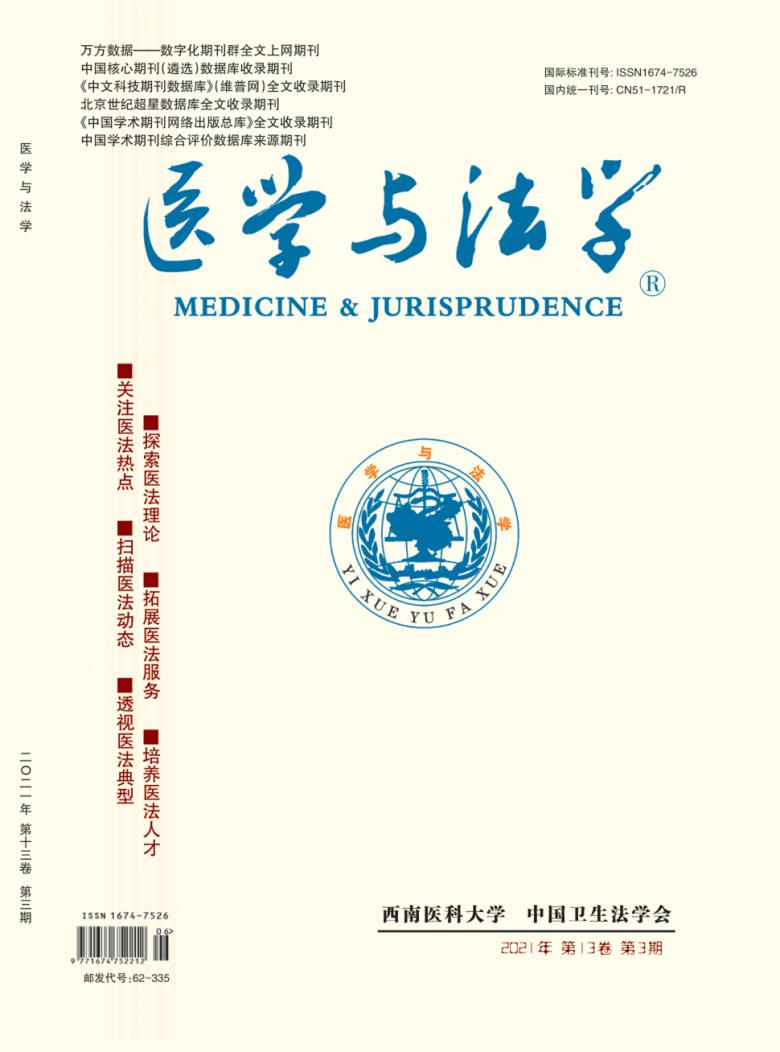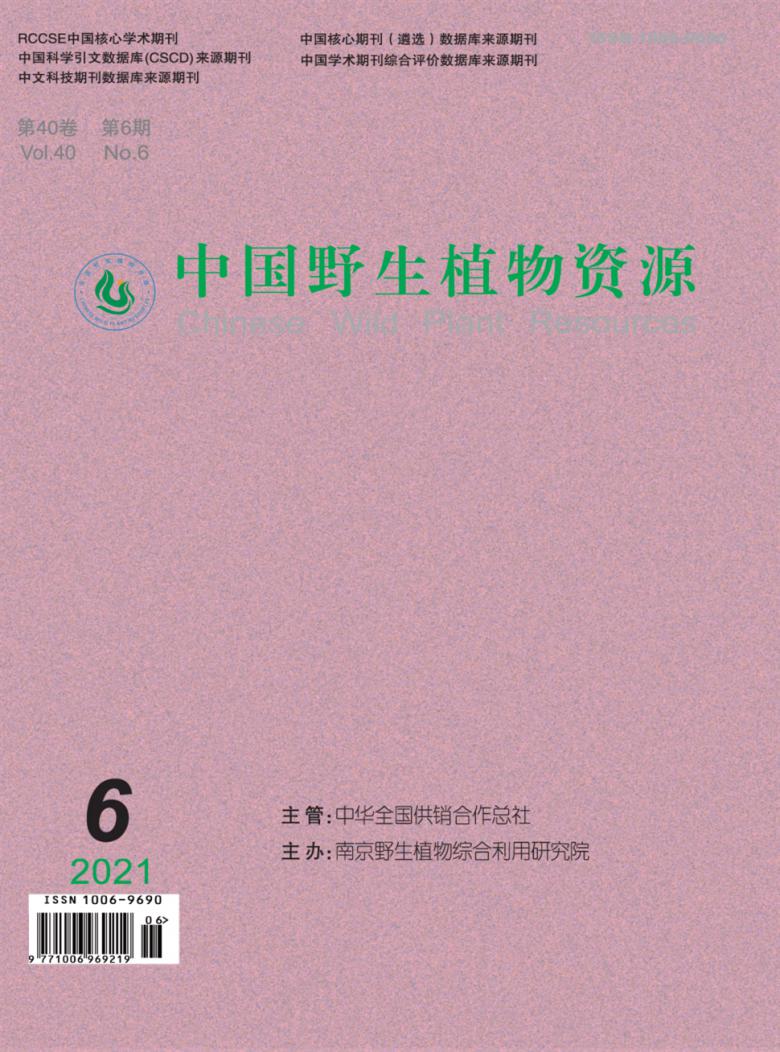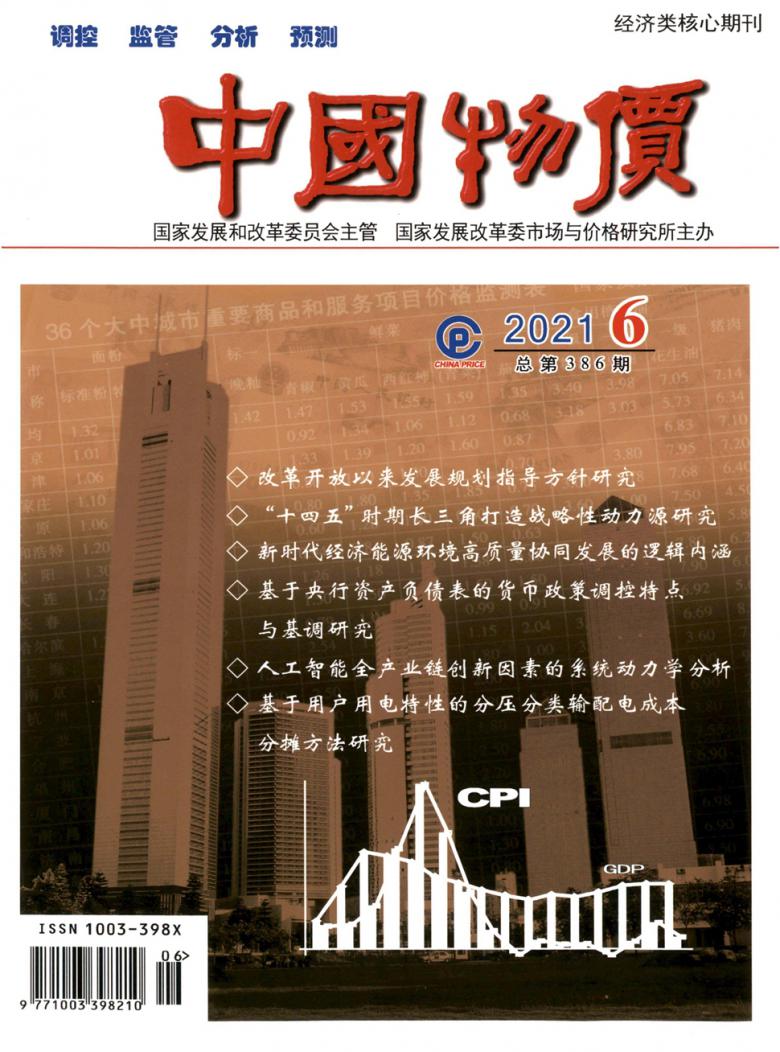试析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
侯建新
【英文标题】Analys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Economic Studies of ChineseCountrysideHOU Jian-xin
【【内容提要】该文就所有制、雇佣劳动的地位和人口因素等三个问题,对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往往也是实践中的误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应当继续清算所有制的神话和迷信。所有制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意识,它总要依赖于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总要以国民个体及其发展水平为载体,而其价值标准的判定,最终也要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改善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另一例证,是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片面拔高雇佣劳动史例的作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首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生产者和市场的交往程度联系在一起,而基本依据不是个别史料,而是较严整的统计。最后该文批评了人口决定论,指出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的原委都归为人口问题,同样不是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英文摘要】This paper makes a intensely analysis of those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always perplexed the rural economic historian,as well as the peasants' economic practice in perspectives ofthe ownership,the status of wage labor and the population fac-tor.It is pointed out that,we must continue to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myth and the blind faith in the ownership.The systemof ownership,as an outcom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outindependent life and consciousness,depends always upon thedevelopment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 and pision of labor insociety,and takes always the national inpidual and theirdevelopment degree as its carrier.Another illustration ofoveremphasizing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is many scholarslopsidedly overstated the role of wage labor played in theseeds of capitalism.This research must do according to themore rigorous and complete statistics,not to one or two histo-rical facts.At last,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populationfactor in modern China wants a scientific judgment,it is not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 neglect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rput all the blame on overpopulation for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关 键 词】中国农村经济/误区/所有制/雇佣劳动/人口问题Chinese rural economy/misunderstanding/ownership/wage labore/population problem
【 正 文 】
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向工业化缓慢迈进的农业大国,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引起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从学术角度而言,中外学者都有不少真知卓见,同时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的至今还在实践上起着直接或间接的误导作用。这里仅就中国农村的所有制问题、雇佣劳动的地位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等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往我们格外看重所有制问题。所有制固然重要,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经济的起飞不是伴随着所有制的创新。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所有制及其他制度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意识,也不能自行运转,它总要依赖于生产力及其社会化、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总要以国民个体及其发展水平为载体,因此,似乎很难孤立地谈论所有制之好坏。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纺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1](第1卷,P108)。 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不能一厢情愿,否则,不管革命、暴力还是某位旷古的贤达,也不管内部的或是外来的力量,都奈何不得;即使一时成功,也断不会长久。世界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实例,就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行的尝试。印度村社制度下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曾长期阻挡着英国商品进入印度,于是英国人凭借着自己作为殖民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行破坏了印度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使一部分印度村社变成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的专业农场,去交换英国的商品;一方面则把纺工安置在靛朗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者干脆把印度古老的手织机和手纺车以及一部分印度纺工和织工一起消灭。马克思起初曾说这是亚洲历史上生产关系的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是由披着强盗外衣的英国人所推动的。而事实上,这场所谓的革命事与愿违:由于这样的所有制变革与印度现实的生产力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相脱节,结果,英国殖民者远未能如愿以偿,对于印度,则陷入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马克思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1](第2卷,P64) 太平天国强制推行“天朝田亩制”的失败,则从另一方面证明,仅凭借强权或暴力,脱离社会现实的所有制“革命”,都是短命的。不论英国人强制推行“先进”的社会分工,还是太平天国强制推行理想主义的“公有化”,也不论推行者有何等的权威,最终都不免被那个现实的社会所抛弃。其实,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设想的那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分配制度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连太平天国本身都没有认真实行,一旦天京出现供粮紧张的情势,很快就回到了“照旧交粮纳税”的老路。 我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个实例,是20世纪中叶以后农村全面推行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制度。解放后,在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进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作一种独立于社会经济之外的、有生命力的实体来看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把公有制简单等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认为只要通过“人民公社”(公有制)这座“金桥”,社会主义的富裕与大同就指日可待了。于是,不是依靠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积月累的改善和发展,包括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市场的交往,不是所有制去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和现实的人,而是人为地定出一些公有化程度的标准和公有化进程的时间表,然后要求生产者及其经济生活去适应那些标准和进程,本末倒置,为此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到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除了政治等因素外,不适宜的所有制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在当时人们的头脑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线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主要是不同生产关系的机械的依次演进图。这是一种单线发展的模式,而且被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我国理论界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后者对人们认识偏见的形成似难辞其咎。 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示,最早是由前苏联理论界提出的。现在一般都追溯到列宁对苏俄大学生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在1929年首次发表。正式提出该图示的是斯大林,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2](P199)不久,该提法被完整地引进《联共(布)党史》,从此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正统学说。“五种生产方式说”强调,所有的民族都要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都要按照这种既定的规律,由一种生产关系向另一种生产关系依次更替。应当严肃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示,是后来者附加上去的,这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与现实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无规律可循,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既是线性的,又是非线性的,既是时间的,又是地域的,无论如何不是“单线”发展的。国内一些学者如罗荣渠先生、胡钟达先生等,已对该图示作了颇有说服力的批评(注:相关论文请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胡钟达:《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高仲君、侯建新:《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10)。),这里不予详细展开。 我们这里只是特别分析一下斯大林关于该图示的要点:显然,斯大林把历史上“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视为相继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核心。生产关系包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等诸方面,它对既定社会形态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种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完全按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发展顺序,衡量社会发展的主次就完全被颠倒了。先进的生产力是很难一蹴而就的,而按阶级斗争动力说的观点,先进的生产关系却是可以通过革命手段迅速达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旦“制造”出来,那就不是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相反,要使生产力的发展跟上“先进”的生产关系。罗荣渠先生尖锐地指出:“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把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这样,往往为唯意志论代替历史唯物论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上述革命公式为一些不发达国家漠视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前苏联,30年代,斯大林可以断然命令刚从农奴制枷锁中解放不久的个体农户“全盘集体化”,同样,我国也可以在50年代刮起“共产风”,相继在农村宣布成立初级社、高级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与此同时,随着城乡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者与国内外市场愈来愈隔膜,“文革”以后,愈发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从“半截子”商品经济,到全部抛弃,全民动员起来“割尾巴”。当然,这是以对生产力的摧残为沉重代价的。 我国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首先打破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进的神话,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逐渐恢复、建立和发展起农民家庭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唤起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再次说明,发展经济不能离开市场,不能离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产权形式。而所有权形式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标准,它最终要由生产力来判断,或者说看它最终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改善广大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此外,对生产力的理解也需避免片面的物化,由于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因此生产力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力是财产和财富静悄悄的、缓慢的积累过程,是包括工具、技术、信息等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逐渐改造过程,与此相关则是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的逐渐健全与发展过程。从主体方面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生产者本身素质包括新的观念、语言、需求和品质逐渐锻造和开发的过程。 所有制不是孤立的,难以对其作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如前所述,公有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有时甚至恰好相反;其实,私人财产所有权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也不是无条件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度及其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私人财产所有权及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非一向如此。近代私人财产所有权在西欧最先确立,并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奇迹;同时我们在西欧历史上还可以发现,土地的公有制安排,共同的牧场,共同劳动或一定程度的协作劳动方式,劳役地租和货币地租,以及近代早期非纯粹私有化的租地农场等,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的发展。西欧中世纪晚期以来,经济发展要求产权制度越来越明晰的总趋势难以否定,但在历史长河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所有权孰优孰劣却不可一概而论。
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尤其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由于我们以往过于看重生产关系,所以也就不适当地夸大了雇佣关系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好像发现了几例农业雇工经营的证例,就可以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几十年来,国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旧的生产关系内部变化和新的生产关系滋长上,哪怕是蛛丝马迹。翻开80年代以前国内出版的任何一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文集,就会发现大部分论文,几乎都在围绕寻觅雇佣关系的史例、史例本身能否成立以及这类史例到底有多少等问题上做文章。似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完全要靠雇佣关系的情况来证明。这样的讨论,往往分歧颇大,有人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追溯到明清,有人追溯到宋代,有人甚至追溯到汉代的雇佣劳动。不是说这样的研究毫无意义,而是说这样的观察视野过于狭小,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即使所举实例本身确属资本主义萌芽,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样的萌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生长点。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没有与生产力尤其劳动生产率以及社会分工的水平联系在一起,没有与农民的物质、精神生活过程及其与市场交往的程度联系在一起,就不能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20世纪中叶以前,旧中国农村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其中租佃制与雇佣制是两种较为典型的方式。前者表现为出租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后者表现为经营地主和农业雇工的关系。按照国内学术界流行的观点,经营地主的出现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所以应该是经济越发达,农业雇工经济越普遍;反之,亦然。这种理论逻辑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可是在解释20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史时,却使人颇为迷惑。当时的实际情况基本与这种理论逻辑相反: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租佃制盛行,而在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雇佣关系大量存在。举例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调查资料中,华北地区如冀中的雇工劳动和经营地主经济存在并不少见,在乡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较为活跃的苏南地区,包括经济较发达的无锡地区,反倒难以发现经营地主的踪影。(注:见陈翰笙等1929年和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现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显然,仅从雇佣关系这一表象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够的。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以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不过个体农户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不论华北地区还是苏南地区的农业剩余总量和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总量尽管有差异,却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长,缺乏雇佣经济滋长的温床。所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出现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雇佣经济组织。华北地区农村雇佣经济多一些,也有一些所谓的经营地主,但规模仍然很有限,所占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而且就雇佣经济的大多数情况而言,不过是小康农家临时找几个帮工而已,不成气候,根本无法与西欧近代早期农村雇佣经济的普遍性相比,亦不能与他们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规模相比拟。有人说起华北地区的经营地主或农业雇佣经济,便简单地冠以“普遍的”、“大量的存在”这样描述性的判断词,缺乏数量的概念和比例的分析(雇佣经济数量与非雇佣经济数量之比),因而不能说明问题。旧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个汪洋大海,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全国就有几千万个生产单位。即使我们举出十条、几十条乃至几千条的事例,也还不到万分之一。它们在整个农业生产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实上,直到1949年前,华北地区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忽视,也不可夸大。 华北和苏南的农业雇佣经济成分毕竟有所区别。为什么苏南商品经济较发达而农业雇佣经济反而较少呢?有人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方面作了解释。旧中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在苏南,收入弹性大的新兴工商业发展较快。由于新兴工商业与传统农业存在不同的利润率,就会改变社会资本与劳力的投入规模和方向。吸收了大量社会新增资本的工业部门,能够率先利用最先进的生产手段,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传统的农业部门由于受到资本积累率低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生产方式依然停滞于传统的水平上。在产业间比较利润的驱使下,苏南地主纷纷离乡进城,跻身于新兴工商业,因而经营地主在这一地区趋于消逝。该观点的解释者还指出了这种探讨的现实借鉴意义:我国产业间的比较利润之不平衡至今仍然存在,甚至益加严重。在商品经济中,农业仍然是最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农业滑坡的原因。它在客观上要求政府的经济决策层必须对农业投入采取倾斜政策,以保证社会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3](P5) 上述两种解释,如果从不同的角度上看都各自有一些解释力的话,那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生产关系领先的逻辑,而是从生产力及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和经济社会的各种实际联系中出发。以上,我们仅在于说明,脱离经济与社会活动领域,原则领先,偏重生产关系的研究思路是如何的狭窄,没有出路,既不能解释问题,也不能给人们提供启示。此外,过于依赖没有数量概念的个别事例,而不靠比较严整的统计方法,同样也很难说明问题。
三
过去我国曾经忽视人口因素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果吃了大亏。有权威机构估计,如果说“大跃进”或“文革”的失误可以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得到调整和纠正的话,那么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误导所产生的后果,显然要延续到21世纪,大概整整一个世纪都难以完全消化掉。(注: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96。)这样的评估并非危言耸听。现在谈人口问题的愈来愈多,不仅谈现实,也追究历史,一部分学者包括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人口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人口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人口问题固然重要,但人口因素也同样有一个科学定位的问题,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问题皆归罪于人口,同样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人口根源说”是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中心,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被称为“新人口论”,以区分于过去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新人口论的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见注①)波斯坦很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但这里的“经济基础”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指人口、物价和农业生产这些“经济事实”,其中人口因素最为重要。波斯坦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人口数量的波动为依据,以14世纪初为分界线,将12-15世纪的西欧分为两个阶段,由此形成波斯坦的经济周期说。第一阶段从12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是因人口膨胀而引起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时期。不过,当人口增长过快而使土地无法承受时,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于是引发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第二阶段从14世纪到15世纪,一方面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另一方面则由于领主之间对日趋匮乏的劳动力的争夺,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带有较强的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人们欢迎的劳役地租,逐渐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也就是说,“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注: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已写进他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的第一章,标题是《中世纪农业社会的最佳部分:英格兰》,剑桥,1966。)。显然,不论是经济的扩张,黑死病的蔓延,还是农奴制的崩溃,波斯坦学派都将其主要归因于人口要素。 曾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新人口论,70年代末受到布伦纳、布瓦等西方学者的广泛批评。(注:相关论文请参见R·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载英国《过去与现在》,1976年(70),引号内的话是布伦纳概括的。布伦纳的批评文章亦见同期杂志。布瓦:《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载《过去与现在》,1978(79)。)虽有波斯坦等人的一再辩解(注:相关论文请参见波斯坦和哈彻《封建社会的人口和阶级关系》,载《过去与现在》,1978(78)。L·R·拉杜里《答布伦纳教授》,《过去与现在》,1978(79)。),但仍然难以改变“人口学模式”渐受冷落的境况。不过,对于新人口学派或应用新人口学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似乎还未见到有分析力的批评,不仅如此,在某种新的形式下还有膨胀的趋势。 “高水准均衡陷阱说”(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始于英国学者艾温(M·Eleiv)1972年的论文和1973年的专著《旧中国的模式》。(注:相关论文请参见M·艾温《高水准均衡陷阱:中国传统纺织业技术发明衰落之原因》("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见W·E·Willmot主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137~172页,斯坦福,1972,并参见[美]王业键《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M·艾温《旧中国的模式》(The Paten of the Chinese Past),斯坦福,1973。)艾温从乡村纺织业入手考察中国的历史,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落后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自14世纪处于停滞应归咎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当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相应增加时,农田不足以维生,农民必须从事副业生产,赚取辅助性收入。这就促使农民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兴起。只要少许投资,购买简单的设备,农民便可利用家庭中的闲散劳力(包括妇女儿童),在家从事纺织,然后每天或定期送到当地市场出卖。只要出卖的价钱超过他们原料和工具的成本,他们便觉得有利可图。同时,由于在市场上有许多农户出卖纺织品,棉布商或经纪人可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比设立工场,亲自监督工人生产更经济。结果形成市场与生产技术的分离,即商人所关心的是市场的运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技术的改进。 在解释中国技术停滞的基本原因后,艾温把公元600年到1800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600——1300年,1300——1600年和1600——1800年。在头两个时期,伴随人口和耕地的扩张,以及一部分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农业产量大致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但在第三个时期,人口大幅度膨胀,而耕地开垦殆尽,传统技术达到顶峰,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的总产量。这样,农业被困在一个“陷阱”(trap)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已达最高水平的平衡,以至失去潜在生产力的积累,即失去内部动力,这时候,只有西方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才能解脱困境。(见上页注⑤) 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即人口与土地等其他资源配置处于何等比例时,农业才会进入一种“卡脖子”的状态?该理论提出一个模式,但并未给出数据。按艾温的意思,中国在18世纪时(当时人口接近4亿)即达到“卡脖子”的境地;敦伯格(R·Deruberger)认为在19世纪末,王业键认为应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而珀金斯认为到20世纪中期也未见到真正的困境。[4]实际上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很快,据何炳棣、珀金斯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乾嘉年间最快时也不超过10‰,而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常在20~30‰。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乃是晚近30多年的事。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从全国范围讲,得不出一个“陷阱”的结论。马克尧先生说,“艾温的学说是一种变相的人口论”,而且“所论不实”,该学说“仍以人口与资源关系为社会发展的杠杆,只是加上了制约技术进步这一曲折”[5],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黄宗智(Philip·C·Huang)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关于他的著述,有一批介绍和讨论文章(注:相关论文请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中华书局,1993;《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1);《商品化过密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4);叶显恩《评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1986(6);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2)等。),笔者也曾谈过一些意见。[6]为避免重复,这里仅述及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主要方面。黄氏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最初在他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概括为“内卷化”(involution),后来在他的论著里又将其改译为“过密化”。“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及由此推及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rygrowth)两个概念成为黄氏理论的核心,我们的分析主要围绕它们展开。 “过密化”观点源于恰亚诺夫关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理论的延伸。恰亚诺夫是俄国农村问题专家,被西方学术界认作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注:相关论文请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三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关于恰亚诺夫理论的评价文章参见徐建青“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4)。)黄宗智将恰氏理论用于明清以来的小农经济研究,即人口压力使人均耕地面积缩小,在达到一定极限后,不是收入与劳动力投入同步增长,而是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这就是所谓过密化的小农经济。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和棉纺织手工业。“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的维持生计的策略”,尽管自明清以来“有五个世纪蓬勃发展的商品化”,然而,“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他认为,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它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即“过密型增长。”(同注①) 首先,说“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这一估价是否过高。许多学者认为即使在江南,这种说法也是过分的。1840年左右的国内市场,总的看,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多寡,还要考虑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也要具体分析。许多实证性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参见侯建新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经济研究——一项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统计分析报告》。),愈是歉收年份,市场愈活跃;越是租债逼人,农民愈需卖出产品或买进产品。这不是与“看不见的手”打交道,而是与死神打交道。这是“饥饿型”商品交换,“萎缩型”商品交换。分析现代商品经济,这些“虚假”成分须予排除。黄氏本人其实也发现中国小农经济为谋生而非谋利,指出明清江南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的局限性,这些均与其“明清高度商品化”的结论相抵牾。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农村没有现代化,是由于农民普遍的贫穷以及在此基础上农产商品化发展之严重不足,而不是由于“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 其次,我国人口过多,农村有剩余劳动力,但何时期能称“过密”,怎样为“过密”,似难以确定。就像艾温的“陷阱论”难以确定人口与土地等资源配置处于何等比例才会“卡脖子”一样。据统计,以每亩田投入劳动日计,我国低于日本和韩国。而且,当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农户的劳力就大量投入非农业的工副业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很难说过密不过密。退一步说,这种人口危机或人口过密化现象,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内是可能的,但未必是一个普遍的、持续进行的过程。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证明中国农业近五百年的完全停滞;相反,我们看到,尽管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相对停滞,但总体讲中国农业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发现,尽管黄宗智试图用三种方法(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小农经济作出综合分析,并说尤其注意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但他的理论模型中的深层次的因素,显然还是归结于人口压力。黄宗智和艾温一样,都不是直接谈人口问题的,艾温从乡村纺织业入手,黄宗智讨论的视野则更为宽阔,包括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内。黄氏提出了若干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见解,但他最终将人口再生产凌驾于物质再生产之上,则属可商。 人口问题在农村的现代化过程中固然是重要因素,不过我们需要有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定位。它与土地等资源的比例,何谓适度,何谓超载和过剩,依据不同的时段和地区等条件,会有不同的答案。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晚近30多年来人口增长显然过快,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把中国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完全归咎于人口。我国70年代后农村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并非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变化的结果,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人均耕地更加狭小了。另一个经常可见的简单事实是,同样的人口和土地等资源比例,往往会有较大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何况,人口无节制的过度增长,像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那样,本身就是贫穷和愚昧的表现,它会随后者的改善而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问题是派生物,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非人口决定论出发,可以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首先需要指出,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饱受内战、外患的蹂躏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农村经济变化相当缓慢,可从整体上讲并非完全停滞,毫无作为。尤其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经济作物种植和乡村工副业的一定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农户的相当一部分产值已在耕地以外实现。这表明了小农家庭经济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当大的适应能力。同时,我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快些,而障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人口问题。 我们发现,社会安定程度,政府的扶植以及产权关系明晰的力度,都是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和不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作用似乎并不亚于人口因素。如果20世纪上半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户及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家庭农场的产出和整个农村生产力本应增长得更快。现代社会中的行业发展,都需要政府的有效扶植,农业尤其如此。要解决旱、涝以及灌溉等问题不是一家一户甚至一村一乡能完全承担的。改良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也是一样,政府都有不可替代亦不可推卸的经济职能。而国民政府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几乎没有任何作为。此外,农村的发展还与经营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甚密,同时也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条件、城乡关系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且笔者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包括人口因素在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政府的低效、无能是农村不发展的主要原因;50~70年代人口激增和“大锅饭”即产权缺乏必要的保护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的主要问题则是土地的过度碎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土地市场流通弱化,以及特定条件下城市工业接纳剩余劳动力的狭隘化等。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恕不进一步论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业经济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5]马克尧.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J].历史研究,1994(1). [6]侯建新.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J].历史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