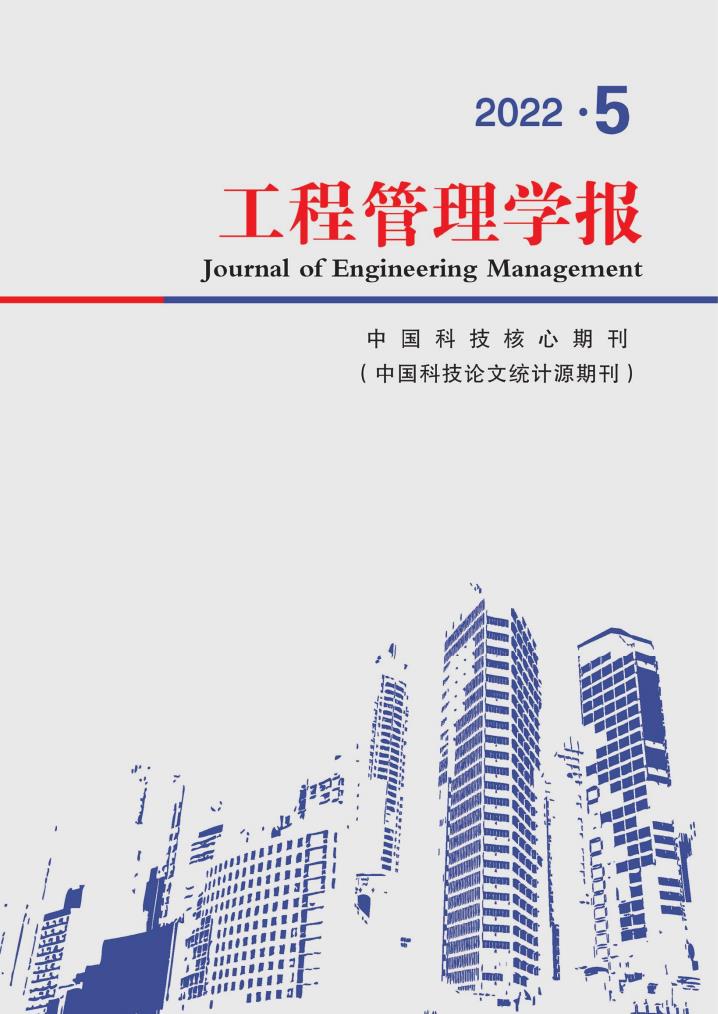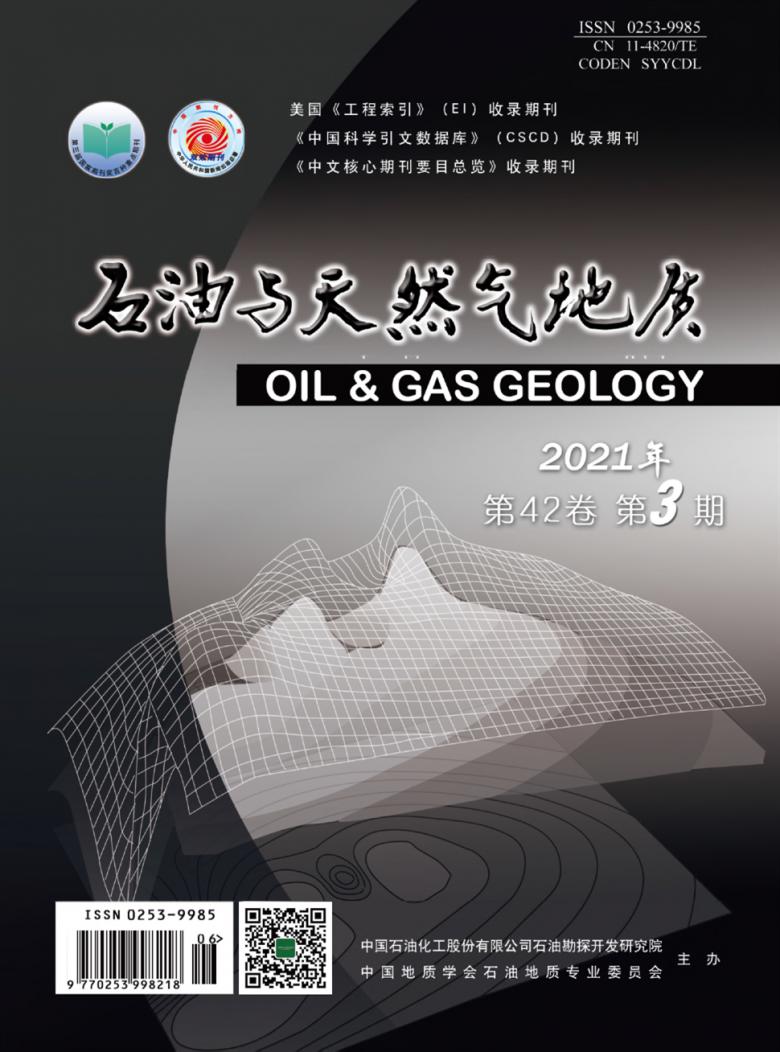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王屏
内容提要: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目前,正处于第4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关键词:中国观 东洋史学 实力主义 现实主义
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几经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归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 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
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体现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当中。《日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隋(1次)、唐(96次)、吴(31次)①。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607年,即从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实际上是我国的隋朝时代)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与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国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本书纪》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年止。
日本直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初次派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开始。本来,从魏朝到隋朝日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到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令皇帝极为不悦。不过,从国书的用语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意识的产生。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感。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另据《旧唐书》(199上 倭国日本传 p5340)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1次变迁。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在日本民族文化——“国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平安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意识并力图超越“大唐文明”。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中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迅速展开,人员、物品的交流及金融业的发展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导致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组。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意识还在持续” ②。到了平清盛时代(1118~1181年),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贸易得到积极推动。宋朝货币大量流入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镰仓时代(1192~1333年),宋钱(即宋朝的铜钱)占居主导地位。清盛所开拓的中世流通经济为日本纳入东亚铜钱经济圈创造了契机,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视” ③。不过,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其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并未打开。
进入室町时代(1333~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日中、日朝外交重开,1373年明朝使节团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的明朝开始了正式的外交往来。明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足利义满从明朝领取冠服并臣服明朝。这样,日本又被重新编入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军都曾接受中国皇帝所派册封使的正式册封。义政、义澄、义晴也都使用过“日本国王”这一封号。幕府将军受到册封“意味着属于天皇的外交权被武家政权所夺取”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不过,这个国王称号在日本国内的正式场合并不使用。
进入15~16世纪后,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当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国际观“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开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观转化。这一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3人不同的对外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织田信长为了获取武器实现国内统一而对“南蛮”文化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对西方基督教也能够容忍,因此,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外交方针。丰臣秀吉实行的是闭锁式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他又对台湾的鹿皮、东南亚的丰富物产垂涎三尺。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大明,并在对女真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他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德川家康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位的含义”⑸。1616年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村山等安率军攻打台湾,惨败后被满门抄斩;中日勘合贸易终结;长崎发生基督徒惨案。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在“锁国”期间日本留出4个对外“窗口”,即对中国、荷兰的长崎;对朝鲜的对马;对琉球的萨摩;对阿伊奴的松前。
16~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在动荡中重组。明朝政府的朝贡贸易受到来自亚洲各国不断扩大的民间贸易的挑战,但为了维护华夷秩序并防范西方的入侵,明朝政府始终垄断着对外贸易。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锁国”既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也是因应东亚国际秩序变动所采取的对策。在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中,中国完成了明清的交替,日本的幕藩体制国家也业已形成。经过东亚各国内部的整合,至18世纪初,东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形成。新秩序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在这一时期还无法触动东亚固有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此时的“西力东渐”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对北亚以及荷、英对东亚的渗透上。西方势力在南北两方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与外交上基本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但在文化上与中华文明仍有共识。
19世纪中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东亚各国的民族危机感同时增加。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又面临着新的整合。1871年“日清友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的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展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需要联合亚洲,扩展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构筑着他的亚洲观与中国观。日本为何会形成这种分裂式的亚洲认识与对华认识,恐怕要从以下2点考虑:“第一,在幕藩权力所培育的国际秩序意识中不存在连带=对等联合的观点。第二,日本是通过屈服于有军事力量=‘武威’的西方列强的方式而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对传统上习惯于以‘武威’为轴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幕藩权力及维新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感觉”⑹。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识以及“尚武”精神,才使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经过了甲午战争后发生了质的转变。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东洋”概念的重新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东洋”(Orient),其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在古代西方社会,它主要指现在的近东(西亚)而言,即小亚细亚、波斯、埃及。而印度、中国则另外称呼。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远东”一词是后来才有的。随着西方人地理知识的扩展,东洋所指范围也在扩大。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之中。在中国人眼中,东洋除作为地理概念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最初,在利马窦与中国人编制的世界地图上,“大东洋”与“大西洋”同指单纯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张燮著有《东西洋考》,其中有“东洋航线”与“西洋航线”的记载。东洋航线的起点在金门,终点在文莱。文莱既是东洋的终点,又是西洋的起点。东洋航线指出金门——取彭湖——达吕宋岛——再南下到爪哇群岛或文莱北岸的航线; 西洋航线指从文莱出发——向爪哇或苏门达腊方向行驶——沿印度支那东岸返回到彭湖——金门的航线。后来,东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东洋,西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西洋。其中,东洋的地理位置虽然包括在后来的东洋概念之中,但是,西洋的地理位置与现在的西洋概念截然不同。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与东方平起平坐的西方,甚至也没有东方的概念,“自古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洪武3年《谕日本国王良怀》)。到了近代,中国人多称日本、菲律宾、文莱北部为东洋,尤其视日本为东洋。
总之,东洋的方位大体“指广东东南部的菲律宾、马来群岛及文莱东部,后来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北部,包括台湾、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称作小东洋。但在日本情况却与此相反,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单词分别是从Orient与Occident翻译过来的。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时指远东。所谓东洋史,是日本学者定位的体系、命名的学问,一般来讲不包括日本,但也存在一会包括西亚、一会又不包括西亚的不妥之处”⑺。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东洋”与“西洋”概念属于地理范畴,而并非历史、文化范畴。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以特殊的含意是有其目的的。日本的“东洋”概念有两层含意。首先,作为地理方位的表记,在狭义上指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即远东地区;广义上指整个亚洲。其次,作为日本在世界史或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东洋”概念有了特殊的指向性。而且,在这一层面上又分别具有普遍与特殊两种性质。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即“东洋”外指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这是“东洋”概念的普遍性质。但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表现出“东洋”概念的特殊性质。
在日本,广泛地使用“东洋”一词是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以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在19世纪初,西方就将自己定位在“文明”的层次上。这种“西洋/东洋”模式无形中就被规定在“文明/野蛮”的框架中。这时的“东洋”与“西洋”已超出了地理概念的范围,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限定性。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东洋概念,其原因所在是由于日本经过“文明开化”后,自觉与“文明”的欧洲属于一类,并刻意与“落后”的亚洲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失败导致日本在亚洲产生了优越感。于是,“文明=西洋、野蛮=东洋”的模式就被简单地套为“日本=文明=西洋、中国=野蛮=东洋”。这时的“东洋”专指中国。“汉学”研究也变成了“东洋史”研究,日本从“远东”一员变成了“远西”一员,即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这样,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扩张与干涉就可以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并在理论上得以正当化。在谈到日本创造“东洋”概念的由来时,丸山真男指出:“它反应了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westernization的过程,因为由(江户中期以来形成的‘国学的’)国家主义与明治以后的westernization合流而产生的文化、政治路线与亚洲各国明显不同”⑻。从近代日本精心构筑“东洋”概念的过程中,我们看出近代日本在亚洲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企图为自己重新定位的打算。而且,由此所产生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规定了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它不仅使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亚细亚主义无法在各国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而且还让日本陷入自己精心设计的“矛盾网”之中,使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因此而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近代日本的“东洋”观具有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
本来,“东洋”一词是相对与“西洋”而言的,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文化上,东洋(亚洲)都应是一个整体。但日本为了“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指中国,福泽瑜吉语)抛弃了传统的“汉学”研究,另起炉灶创立了“东洋史学”理论体系,为近代日本“东洋”观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依据。日本人所说的“东洋学”是以亚洲为研究对象(但不包括日本)。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对外扩张的欲望。以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期结束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为了配合其殖民主义政策日本开始了“东洋史学”的研究。1886年,东京大学招聘德国历史学家里斯?L?赖斯(Riess)来日本讲学。赖斯在东大增设了历史专业,并与刚回国不久的坪井九马三一起讲授历史。1890年,毕业于本专业的白鸟库吉到学习院讲授东洋史,这被认为是日本学术性东洋史学诞生的标志。1894年,根据那柯通世、三宅米吉的提议,日本文部省将中等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
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自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体经历了5个时期⑼。第1期:明治前半期(1868~1888年)。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学界整体的草创期,还不应称为东洋史学,这时的东洋史主要指中国史,它只不过是汉学的一个部门而已。第2期:明治20~30年代初(1888~1900年)。这是东洋史学发展的准备期。1888~1892年期间,出版了那柯通世的《支那通史》5卷及市村瓒次郎、滝川龟太郎的《支那史》6卷。这一时期以教科书、参考书概论的编撰为主,值得注目的专业研究几乎没有。第3期: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1900~1914年)。这一时期,脱离了以往概论编撰的状态,开始了专业性研究。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俄罗斯在“满洲”的所谓权益,并进一步吞并朝鲜。随着日本对亚洲国家侵略的进展东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东京大学设立了国史、西洋史、东洋史学科,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分别开设了东洋史讲座。1907年,岩崎弥之助购进清末4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的藏书,设立了静嘉堂文库,为东洋史的研究带来了方便。第4期:从大正初期到昭和初期(1914~1930)。第1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景气,掌握了东亚霸权的日本更加积极推行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与这一形势相适应有关东洋史学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增设,其研究迅速进展。1917年岩崎弥之助又购入伦敦泰晤士通讯员莫里逊的藏书,在此基础上于1924年设立了东洋文库并成立了研究部。这里作为东洋史学研究的殿堂被许多人所利用。1929年日本用辛丑条约的赔偿金分别在东京(现在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建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第5期:从昭和初年到二战结束(1930~1945年)。这一时期研究者的数量显著增加,研究内容进一步精确化。与以往对历史、地理、表层文化史的研究不同,开始了对社会、经济、各项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日本对亚洲侵略的进展,加大了对中国、朝鲜、“满洲”、蒙古以及东南亚、印度、西亚的研究力度。同时,其研究的侵略性质也越发明显。从上述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是日本用以“发扬国威”的一门学问,是“大日本帝国的学问”。而且这种学问完全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也正是在这种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上发生的。
东洋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是被称为‘东洋史学大御所’的白鸟库吉,他的“尧舜禹抹杀论”反映了日本当时急于树立自己在亚洲的“威信”而对“东洋”重新认识的需要。1909年8月,44岁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演说,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极为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他的“尧舜禹抹煞论”是对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的极大冲击,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不过,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他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蔑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儒学的回归。白鸟库吉认为,中国唐代以前的文化在遣唐使时代日本就已经吸收了。中国唐代以后的文化德川时代也已经吸收了。现在日本人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但白鸟库吉同时又认为自己“不是儒学的敌人,而是儒学的拥护者”。1918年他发表《汉文化的价值》一文,一边鼓吹日本人已把中国文化全部学完了、现在的任务是向西方学习,一边又提醒日本人西洋的东西并非什么都好,“儒教”应该受到尊敬。1930年他发表《日本建国之精神》的公开讲演,大声疾呼“日本人的精神便是吸取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并使之在日本达到统一”。他还把“儒教”推崇为日本国家的基本精神。白鸟库吉自相矛盾的思惟是近代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理论上的真实反应。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继承了白鸟库吉“中国观”的一个方面。津田认为,“东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性质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没有任何影响,印度虽然把佛教传给中国,但佛教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民族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这种理论与近代初期日本所倡导的“脱亚”精神以及创造东洋概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显得有些“过时”。因为当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霸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日本政府需要的不是脱亚入欧的理论,而是如何打“亚洲牌”的理论。1939年,当津田在东大法学部讲演时,右翼学生质问他:“你全面否定儒教与日本文化的联系,否定日本与中国存在共同的‘东洋文化’……这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圣战’的文化性意义吗?”⑽。这里,右翼学生对‘圣战’的认识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单从这段问话中我们就能领悟到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及其中国观在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变化。因为,第一,日本的东洋观此时已由“内指” 转向“外指”,即已由与东洋划清界限转向强调东洋一体共同对付西洋了。第二,东洋史学作为“欧化主义”的理论基础已不适应“超越近代”以及与西方列强争霸的需要。第三,“恢复东洋的文化与传统”是为日本所谓的“圣战”及“大东亚共荣圈”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上寻找理论根据。在这种形势下津田的理论受到冷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更主要的是津田对日本神代史的研究结果(津田称‘天孙民族’、‘万世一系’不过是神话而已)令军国主义者大为不满。津田的理论被右翼团体攻击为“大逆思想”,津田本人也被当时日本的法院判刑3个月并终身禁止其写作。
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轻蔑的程度。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限于孤立地位的日本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又开始寻找“脱欧入亚”的理论。因此,东洋这张曾被日本打过的牌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近代日本自相矛盾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日本政府对待津田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津田发表讲演的同一年,谷川徹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东洋与西洋”,对当时日本的东洋观进行了理论分析。他首先对东洋与西洋对立的现实意义提出疑问。指出“如果说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包括我们从西洋引进的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⑾。谷川认为,在东洋与西洋的称呼中含有历史传统与文化上的意义是无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洋各国即便过去没什么交往但却有一体感。可是,如果把东洋与西洋对立起来,那就必须回到过去,而“过去的东洋无法成为今天的指导原理”、“目前,尤为重要的问题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东洋的新秩序还缺少充分的现实性……(因为)日本立于亚洲文化前列的时日还太浅。我们对异民族进行统治、安抚的经验只有一点点”⑿。所以,他认为日本是在东洋的“大口号”下实施其侵略的真实目的。在当时军国主义者统治下的日本,他能以如此冷静的头脑与明确的语言透彻地分析日本亚洲政策的实质难能可贵。他告戒日本不要步当年入侵中原的异族人的后尘,因为他们“虽然征服了汉人,但不久就被汉人的文化所同化”⒀。 三、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对于日本来讲,“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做‘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⒁。但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3次大的变迁(第1次在大唐衰落之后,第2次在大明鼎盛之时),日本开始蔑视中国。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在日本人眼中重新成为“人类理想之国”,他们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样的中国认识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社会却在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10余年左右的时光。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了近代的原点上。反应这种变化的代表性作品是长谷川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别了!亚州》一书。此书作者认为,“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⒂。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近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80年代福泽瑜吉撰写的《脱亚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指中国)的主张。
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在亚洲推行他的“新战略”,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即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过于衰弱。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过于强大,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其中,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如,有的日本人说,他不喜欢声讨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而喜欢出三国志、汉诗的中国。还有的日本人建议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把金钱与技术作为有效的武器,与中国建立战略式伙伴关系,而这种战略式伙伴关系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另外也有象石原慎太郎这样主张中国分裂的人。
当然,战后50多年来,从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的角度来认真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关于战后日本人亚洲观的问题,最早在理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着手进行研究的是竹内好。1961年,他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沟口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沟口指出,把中国作为方法(对象)来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多元领域。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要素,欧洲也是一个要素。他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被相对化的马克思主义)看西方。沟口试图用从中国导出的价值观来替换东洋这一概念。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研究的中国不应停留在对象上,而应把中国自身再作为一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即通过把日本相对化来把中国相对化,进而再把世界相对化。他认为这样才能在主客体相对化的过程中摆脱欧洲中心史观,同时将追求日本主体性本身也相对化。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在研究中国与亚洲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尝试、一种创新。
日本在研究和看待中国时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如,NHK在做过有关中国的节目后有关负责人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力排除想掌握这个国家整体形象的野心,我们只想挑战局部地区”。中央公论也认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国都是个别印象,想通过一件事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小室直树在《中国原论》”中指出,正是中国的历史才是理解中国的宝库;佛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是拯救个人的,但儒教是拯救集体的。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认识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2002年11月28日,日本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书。这就是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在经过1年零2个月的研究并召开了32次会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最后书面文件《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该报告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⑵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与强化。⑶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在对国际形势进行上述判断的基础上,该课题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及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威胁。强调日本在制定未来的外交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将日本的“国家利益”规定为:⑴维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⑵维持自由贸易体制。⑶拥护自由、民主、人权。⑷推进与各国民众之间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培养人材。但笔者认为,该报告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该报告书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树立新中国观的开始。因为笔者注意到,该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课题组成员不仅将中国因素作为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而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题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论述其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甚至在参考资料中有关对华ODA部分也占有重要的篇幅。所以,笔者将这份报告书看成是即将来临的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的信号。下面分析一下报告书中所体现的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的新特点:
1、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处理日中关系。虽然该文件没有把中国象美国那样定位在“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上,但却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将中日关系定性在“协调与共存”、“竞争与磨擦”两种相反要素相互交织的框架之中。主张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静的心情”加以对待。构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双方的“共同点”要加以扩展,对于“差异点”双方也要有勇气承认。两国当局要确立和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中日关系这一意识”。认为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
报告书指出:“对于日本来说,究竟希望近邻的大国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呢,是一个经济陷入停滞、时而发生猛烈社会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商机的中国?这一点无需讨论”。认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机遇。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题,报告书承认这是事实,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程度有加深的可能,但并不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指出,解决经济空心化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中的一个环节,“使日本自身在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活动中成为有魅力的国家并推进广义上的服务化”。而“胡乱地强调对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国’,走与中国共存共荣的道路,进而推进面向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日中合作这一目标的实现”。
3、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
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书认为,日本与中国的“磨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看成是“对日本的中长期深刻威胁”。说“特别是最近,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游戈,给日本国民带来了不安”。建议日本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安保对话时应向中方提出增加军事预算透明度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指出,中日双方有必要积极开展安保对话,加强军队之间的交流以及军舰的互访。关于“日台关系”,该报告书认为,“自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变化很大,日台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是自然的事情”。这就为日本继续涉足台湾事务埋下了伏笔。报告书还认为,中国应拿出“大国的风度”、“沉着应对”类似李登辉访日的问题。对于“个别问题”,中国政府的主张不应“过度僵硬”。
4、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
历史问题是中日相互认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主张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不应任由歪曲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尤其是日本领导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国以及近邻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卤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增进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中国国内青年人“厌日情绪”的增长,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国国内的教育方式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坦率的协商。并期待中国能通过教育及媒题为改善未来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并向中国人民介绍战后的日本是如何排除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而将所余之力用于支援亚洲各国发展经济的。
总之,在《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所体现出的日本人的新中国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误解的成分。但总的看来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未来的中日关系决不是谁附属谁的问题,是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问题。未来的亚洲在经过艰难的整合后,必定有一个稳步、快速的发展时期。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不论是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是中国人的日本观都存在着误区。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所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因在交流中产生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无疑会捆住日本人民的手脚,同时也会给中日关系投下阴影,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以及中日两国人民相互认识中的最大障碍。日本没有真正解决是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的问题。最近,美国就有人提出要提高美日合作的档次以抗衡中国。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相互晖映、“斗”则两败俱伤。就日本人的中国观而言,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即日本是继续在亚洲保持“光荣孤立”,还是放下包袱与亚洲真正地融为一体,共同开创亚洲的美好未来。我相信中日两国都会更加注重从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追求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走出双方认识上的误区,携手共进,与亚洲个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共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未来的第4次变迁正在形成之中。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波峰方向发展(认同),而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谷底方向发展(不认同)。表现出明显的“实力主义”、“现实主义” 价值取向。如,在大唐衰落后发生的第1次变迁;在大明鼎盛期发生的第2次变迁;在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发生的第3次变迁以及未来的20年中即将发生的第4次变迁,都证明了或即将证明这一规律性特点。 注 释:
⑴ 井上秀雄 著《古代日本人の外国観》学生社 1991年 84頁。
⑵ 片倉穰 著《日本人のアジア観》明石書店1998年 25頁。
⑶ 同上,27頁。
⑷ 同上,38頁。
⑸ 荒野泰典 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8年 162頁。
⑹ 同上,22頁。
⑺ 新編《東洋史辞典》東京創元社 1986年 629頁。
⑻ 丸山真男講演録 第4册《日本政治思想史》1964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8頁。
⑼ 下中邦彦 編《アジア歴史事典》第7卷 平凡社 1985年 96~97頁。
⑽ 严绍 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31頁。
⑾⑿⒀谷川徹三 著“東洋と西洋”《中央公論》1939年11~12月 6頁,15頁,16頁。
⒁ 長谷川慶太郎 著《さよならアジア》文芸春秋 1986年 58頁。
⒂ 同上,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