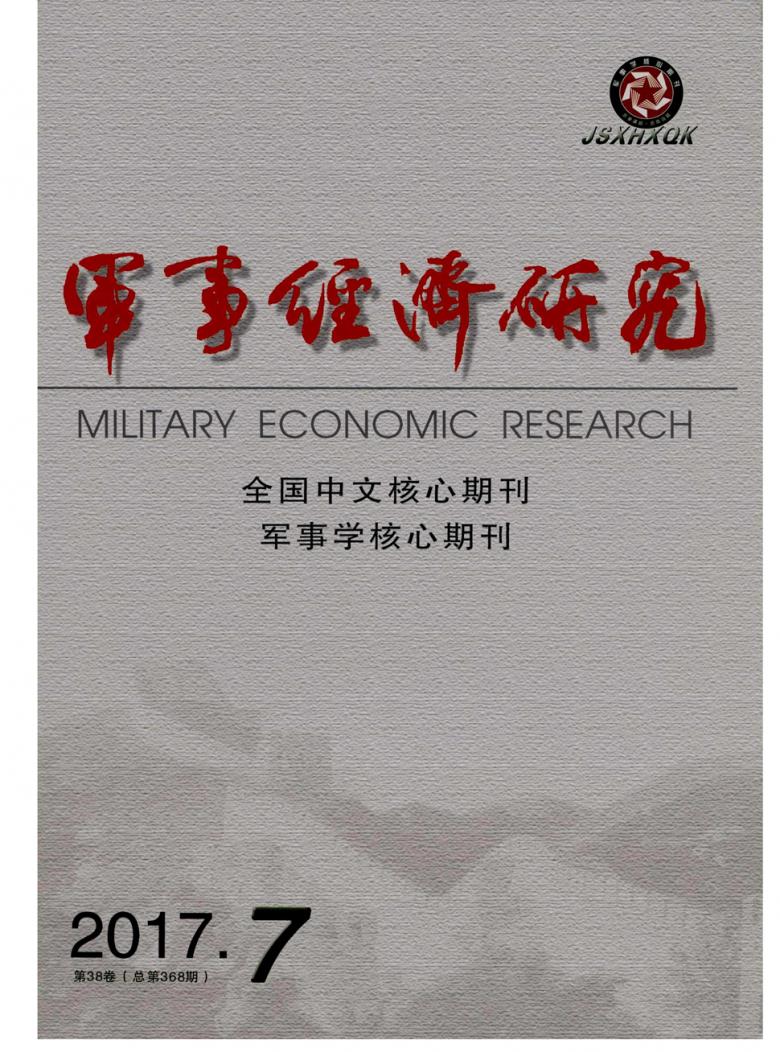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之二)
佚名 2008-02-01
古代世界的各种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
直到最近,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起源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新现实主义(Waltz, 1979)[6]只是假设国家在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但随着它们互动能力的增加,最终达到能够相互威胁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产生了。利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评估。他们证明:在极为广泛的前国际体系的背景中形成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社会,首先是由采猎群建立起来的。此外,由于这些延伸的前国际体系,在不同地方形成的各种国际体系/社会迅速相互接触,并迅速建立起贸易体系,结果是经济领域里的互动远远延伸到社会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里所发生的互动以外。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还显示国际体系和社会能够以两种非常不同的途径出现:一种途径导致城邦国家的无政府体系的建立,另一种途径导致更为等级制结构化的帝国的形成。虽然还不能解释这种差别的理由,但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却预见无政府结构会被证明是反弹的。事实上,历史证据表明无政府是一种比新现实主义的预见更为脆弱的结构,总是让位于帝国体系的等级制度。例如像巴比伦和亚述这类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波斯湾居首位组合起来的苏美尔城邦国家。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存在着城邦国家崛起的途径,但反过来城邦国家又让位于帝国。
然而最早的城邦国家和帝国体系都与反映了一种共同文化存在的礼俗社会的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共同的文化,主要的国际行为体遵守同样的标准原则,以这些原则为基础,行为体能够建立赋予国际行动以合法性的“集体判断”('collective judgements')(Wight 1977:153)。[18]例如,沃森认为苏美尔城邦国家和巴比伦帝国接受了一套共同的宗教信仰,这套宗教信仰在这些背景(settings)中产生了一种权威的合法意识。这些信仰继而倾向于反对一种赤裸裸的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观念。就像沃森观察到的,在同一文化的范围内,人们是“趋向于赞同他们相信应该如此的事情,即使这样并不符合他们的物质利益”。这个评估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因为“法和理论以及什么是适宜和恰当的观念是以文化为条件的,并且与传统和先例结合在一起”,它们“相对地更为坚固,抵制变化,所以是一种它们赋予的合法性”(Watson1992:130, Wight 1977:152)。[19][18]然而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检验这个结论,或至少以某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这个结论表明当一种社会的礼俗社会形式支持一种无政府社会时,那么应该有明显的由这个体系中单位施行约束的证据。例如,里斯·司密特(Reus-Smit, 1997,1999)[37][22]提供了希腊城邦国家代表一种礼俗社会类型的充分的证据。但也可能找到范例显示社会约束如何迅速消失,并被与霍布斯式国家本质相符合的情况所取代。尽管这里不能进行详尽的阐释,但这一论证与普莱斯(Price, 2001:5)[38]对休昔底德斯极具说服力的解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应该被视为“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内战”。普莱斯(Price, 2000:190)认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交流中断,“过去曾经享有共同语言、宗教信仰和实践、道德体系和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人们,“不仅停止分享所有这些相互认同的要素,而且丧失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即使在他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一旦那些相互关系的基础消失了。”交流的中断也与特别突出的野蛮行为和对确立已久的宗教和道德标准的持续侵犯相伴随(Price 2000:273,328)。这种现象代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反常(anomaly),无论英国学派还是建构主义者都没有对这种反常予以重视。同样,它也是一种新现实主义没有能够识别和较少解释的现象。
然而,如果把这种反常放置一旁,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们确曾设法确立布赞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区别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最早的国际社会都是被一种共同文化和一种现存的世界社会所支撑着的。例如苏美尔不同城邦国家的居民享有一整套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有助于为国际行动提供合法性。例如,有一种这样的信仰:每个城市都属于一个特别的神。在众多各种各样的神之中,有一个最高领主,发挥着最高仲裁者的作用。同样,城市国王与天国里的最高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就像万王之王,在城市中间发挥着一种类似功能。后来,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闪米特人王国的居民征服了苏美尔城邦,但他们适应了流行的共同文化,吸纳了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所以无论巴比伦还是亚述帝国,都是通过依靠拥有一个就像天国里的最高统治者那样行动的神,来使他们的帝国权威合法化的。这样一种合法化规则的存在有助于确认这些帝国接受了一种礼俗社会。
然而,沃森承认并不是所有帝国都按照这样一种原则运行,从而为法理社会的思想创造了空间。例如波斯帝国不仅远比先前的各帝国更为广阔,而且是由信奉一神论的部落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宗教信仰否定本土的、嫡传的和泛神论的原则。结果波斯人不得不依赖说服和赞同而不是合法性,所以他们的生存是“基于为那些愿意与他们合作或至少默许波斯人权威的人提供一种好处的平衡基础上的。”(Watson1992:46)[19]可以认为这样的国际社会是在法理社会原则的基础上运行的。
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国家共存,因而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案例,用以说明英国学派把国际体系和社会联系起来的显著特征。希腊人几乎总是被描述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内行事,这个体系由公元前8世纪后出现的大约1500个城邦国家(poleis)组成。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非常小,不比设防的村庄大多少。虽然人们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在了像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和斯巴达这样被视为顶级强国和锡拉库扎这样爱琴海群岛上的国家身上,但当时还有一批像麦加拉(Megara)、埃吉纳(Aegina)和西息温城(Sicyon)这样的中等城邦国家(Starr 1986:46, Cohen 2000:13)。[39][40]英国学派非常清楚,希腊城邦国家构成了一个初生的国际社会,以诸种泛希腊制度、一个简单的外交体系和“战争与和平的调停以及沟通规则”(Watson 1992:50,Reus-Smit1997,1999)[19][37][22]为特征。希腊城邦国家还被认为已经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文化单位,反映在“共同的语言、共同戏剧、建筑和宗教仪式上。”(Watson 1992:50)[19]结果是希腊人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边界,把他们与被视为野蛮人(barbarians)的周边地区的居民分离开来。最初野蛮人还是一个中性用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了轻蔑的内涵(Wight 1977:85)。[18]
与此相反,波斯人被认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化的帝国体系和一个多元文化国际社会的法理社会形式中活动。由于其迅速地拓展,波斯帝国容纳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和古代的文化。当人们发现,就像在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在帝国的中心区有一种流行的文化,也有对帝国持续的不满时,不会感到惊讶。然而这些不满在公元前545年之后有了不祥的含义,当时波斯帝国皇帝塞勒斯把注意力转向小亚细亚,征服了已经在爱琴海东部爱奥尼亚建立起城市的爱奥尼亚人。尽管斯巴达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威胁塞勒斯说,如果伤害了爱奥尼亚希腊人,他要遭到惩罚,但事实上波斯人很快就发现希腊人已经被内部纷争所分裂,以至于难以团结起来抵抗波斯人,他们还发现能够通过金融刺激的手段鼓励这种希腊人的内部纷争(Balear 1995:63)。[41]所以,通过功能性手段,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被带进了波斯人的国际体系和社会。但就世界社会而言,他们仍然留在大陆希腊人的范围之内,扮演着一匹潜在的特洛伊木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