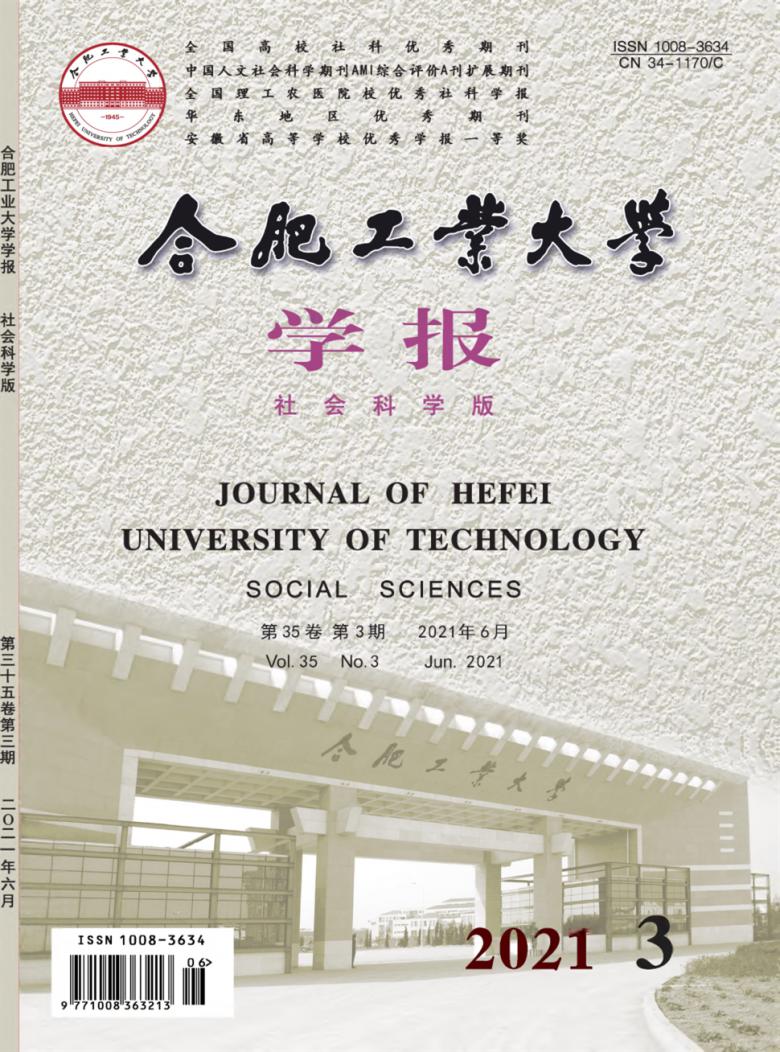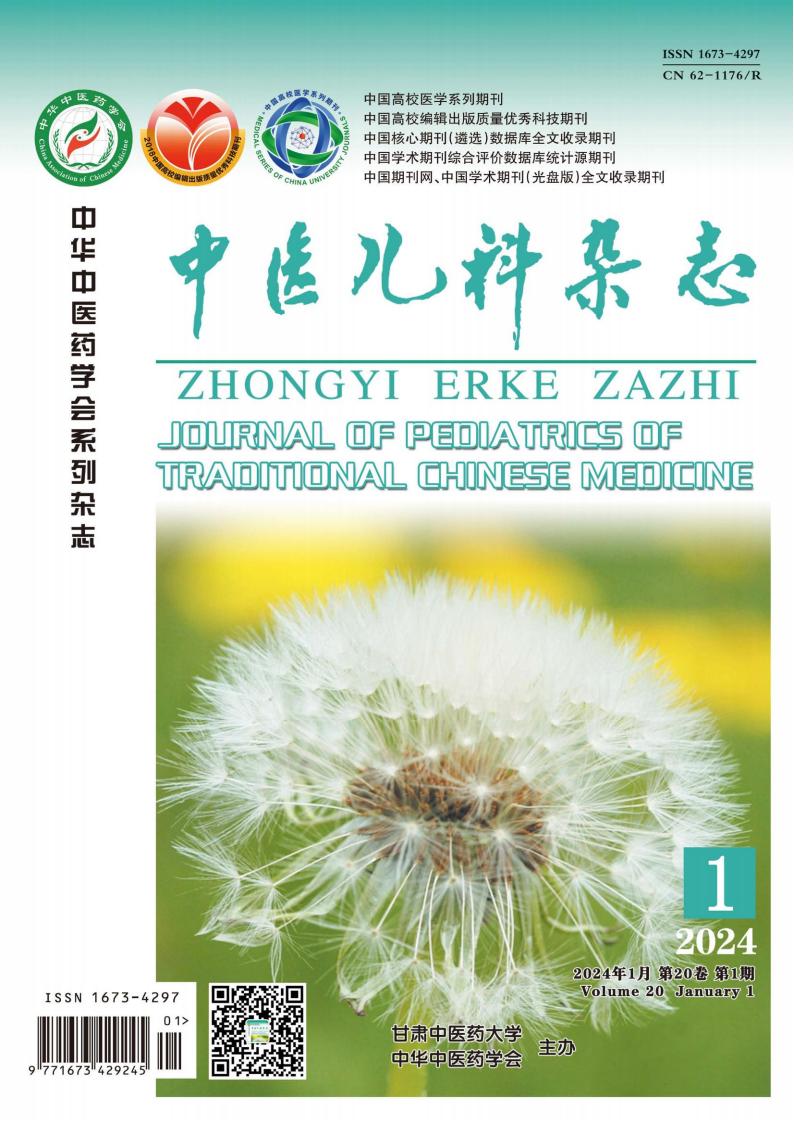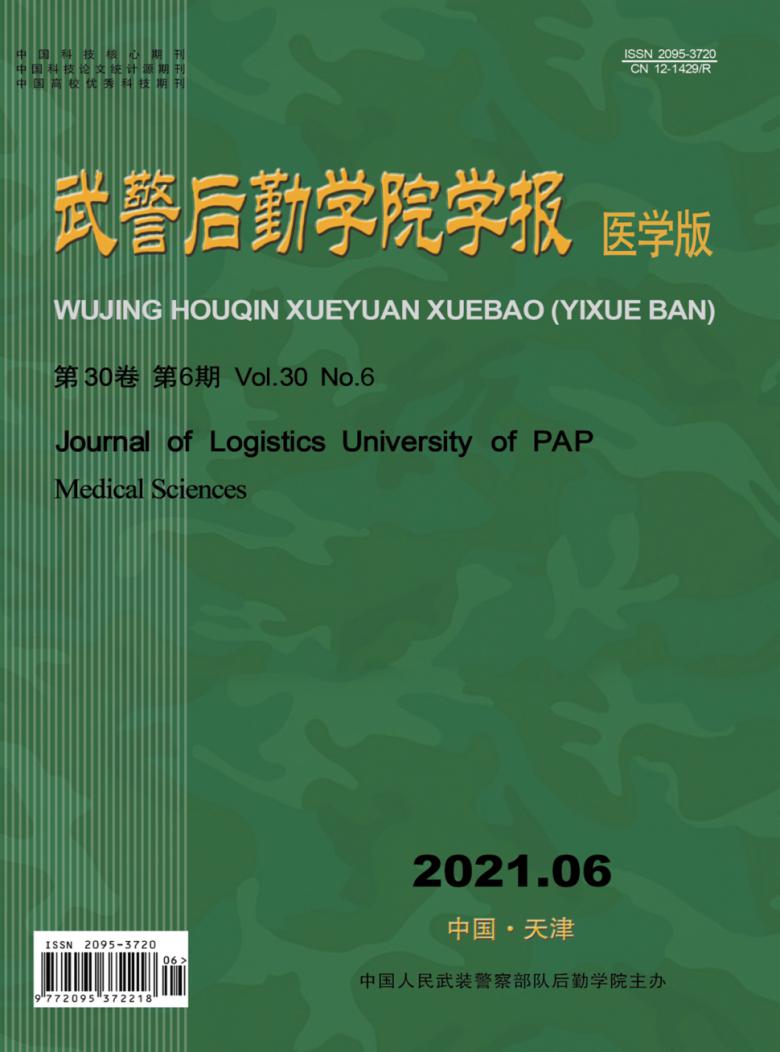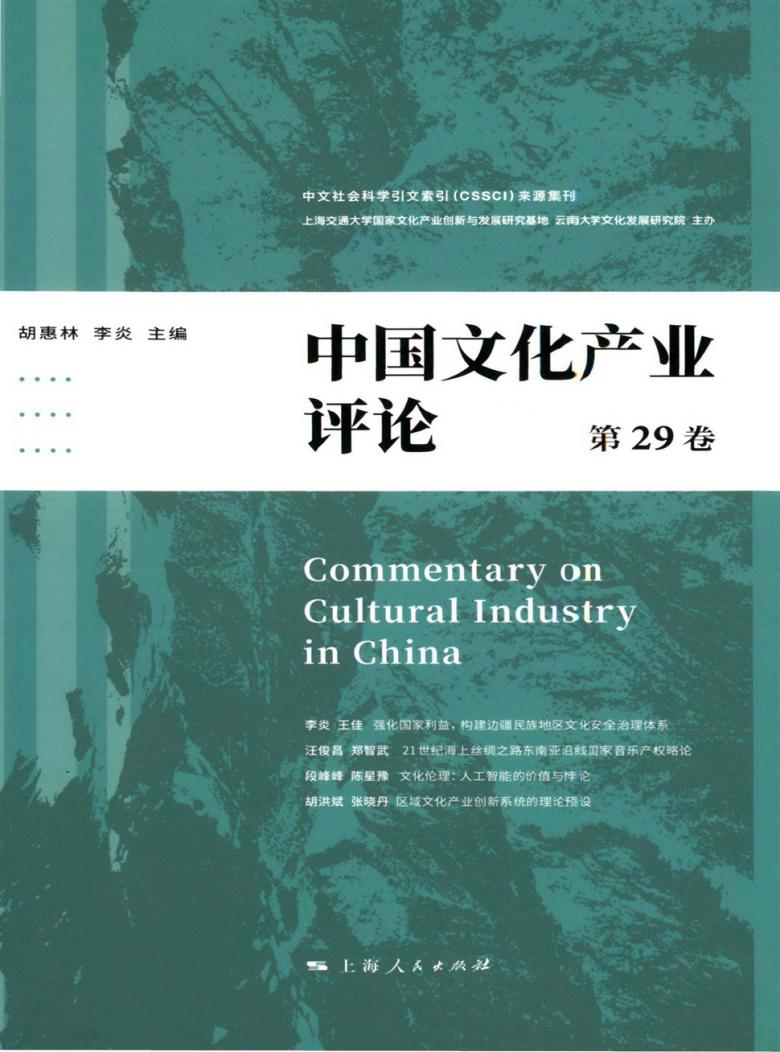唐代小说中的狐故事
韩瑜
【内容提要】 狐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以唐小说为代表,狐形象经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唐小说中狐故事类型的嬗变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从对象到内容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由“实录”到“虚构”的逐步进化。
【关键词】 小说/狐故事/民间信仰
狐故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经久不歇的传统题材,早在魏晋时期志怪小说《搜神记》里就记载有不少的狐故事,后代有代表性的如唐小说集《广异记》、唐传奇名作《任氏传》、清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清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等作品中,都不乏各具风格、面貌迥异的狐形象。从形象类型来看,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狐经历了动物性狐→神性狐→妖性狐→人性化狐的转变过程。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有三个阶段:魏晋志怪小说时期,即妖性狐(狐怪)时期;志怪传奇兼而有之的唐小说时期,是妖性狐向人性狐过渡时期;唐以后基本进入人性化狐时期。这其中以唐小说中的狐故事最具代表性,这一阶段的狐形象经历了由“狐怪”到“狐精”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狐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映射出特定时期民间信仰的特点以及时代思潮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的变化。 一、《广异记》之前——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时期 唐小说经历了从志怪到传奇的发展过程,初盛唐时期仍是志怪小说的天下,上承魏晋时期风格的妖性狐(狐怪)故事自是少不了的题材。不过,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狐故事开始表现出一些不同于魏晋时期的特点: 唐小说中最早出现的狐是初唐时期王度《古镜记》中的一只“妖狐”,在神奇古镜的逼照下现出了原形后哀哀而歌:“(狐)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1] 3 这个“老狸”和魏晋小说中的“狐怪”相去不远,故事本身也带着浓厚六朝色彩。不过,此篇中的“狐怪”在临死之前颇有不卑不亢之风度,正是这样的谦谦风度使其形象平添了几分可爱。盛唐时期的小说中“狐怪”故事并不多见,《广古今五行记》中有《邺城人》、《纥干狐尾》两则故事涉及到狐,不过这两篇故事都是讲述人为了偷盗钱财或其他目的假扮作狐,并非真正的狐故事。 中唐是唐小说的鼎盛时期,狐故事的集中展现也在此时期。《广异记》之前的中唐小说里,较多涉及狐故事的是牛肃所作的小说集《纪闻》。从《纪闻》中已经看出唐人和唐小说作者对狐的态度有所转变,狐的妖性成分少了,人性的成分渐渐多起来。《纪闻》中共有7篇狐故事小说,分别是《王贾》、《叶法善》、《郑宏之》、《田氏子》、《靳守贞》、《沈东美》、《袁嘉祚》。在这些故事中,唐人和狐之间由对立慢慢变成了宽容和接受:《郑宏之》篇中一千岁老狐被人识破后说:“杀予不祥,舍我何害?”[1] 263《袁嘉祚》中的狐亦云:“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我能益于人。”[1] 2949在朴素的唯物论基础上,《纪闻》中甚至出现了反映不信狐和怪由人心起的文章。如《田氏子》这篇文章,它以幽默的口吻讲了两个丛林相遇的人互将对方认为是“狐怪”并相互殴打这样一个笑话。在这里,作者对狐的观念有了新的突变:狐从妖的世界又走回到原初的动物狐世界了,尽管此类回归动物性狐的故事在中唐小说中并不多见。 唐小说《广异记》之前,狐形象经历了由“狐怪”(妖性狐)向“狐精”(人性化狐)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和唐代民间信仰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先秦三代至两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以上帝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为主要内容,随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逐步前进,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沿着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向前发展。到了物质生活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的唐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虚妄性进一步减弱,现实生活的成分逐渐增强,对上帝祖先、风雨雷电的信仰崇拜不象先秦时期是出于惧怕的敬畏,更过的是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唐代的雨神(专司风雨)、灶神(专司炊事)、禄神(专司功名利禄)作为民间神中的首宠就可以看出这一功利化明显倾向。“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到了自信康健的唐人那里,不过是多了可以赏玩、戏謔的灵物(如龙、龟、鱼、犬、马等)为伍为友而已。因此,在唐小说中,狐不再是魏晋六朝时期那种诡异妖惑、与人对立的怪物,而成了让人事敬、与人共存的灵物。唐代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说:“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2] 狐信仰由魏晋时期民众对狐的“惧”发展到唐人对狐的“敬”,由魏晋时期的人狐对立走向唐代的人狐共容,这同唐朝昌盛的国力、宽容的文化精神紧密相连,也是中国民间信仰多神崇拜的必然结果,更是同中国民间信仰向重功利方向发展这一趋向不无关系。 唐代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民众生产生活无多少实用价值的狐便从民间信仰的神圣殿堂渐渐消退,而对狐性灵异、诡魅等特质的想象和把握却被唐小说家转化到了文学世界,成为唐代直至后世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形象。这一转变过程,也正是以实录笔法为特征的古小说向“作意好奇”的唐小说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确切地说,直到中唐小说集《广异记》,作为民间信仰的符号却更具文学意义的人性化狐形象才大量出现。 二、《广异记》——作为民间信仰符号和人性化狐形象的“狐精” 《广异记》二十卷,中唐时期志怪小说集,作者戴孚,谯郡人,生平史书记载不详。《广异记》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狐故事。对此,侯忠义的《隋唐小说史》中有评价:“狐精形象成为妖怪类故事的主角,而且丰富多彩,富于人情味,这是本书的贡献”。[3] 戴氏的这一独特贡献,对我们研究狐故事在唐代的嬗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异记》中有40多则狐故事:具六朝遗风、纯粹谈奇尚怪的“狐怪”(妖性狐)故事仍有,篇目明显减少,只有《代州民》、《刘甲》、《严谏》几篇而已;具人性化特点的“狐精”形象开始频繁出现——从《广异记》开始,我们用“狐精”这一称呼来指称人性化的狐。“狐怪”是与人类对立、令人惧怕的,而《广异记》中精灵古怪、颇通人情的“狐精”们却可以与人为友、令人喜爱: (一)聪慧美丽的“狐精” 《广异记》中的雌狐多聪慧美丽,可爱可亲;雄狐多伟岸潇洒,颇具男子汉的风度。《李黁》中的郑四娘(雌狐)“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声特究其妙;”[1] 511《长孙无忌》中的雄狐是个“身长八尺余”的伟岸男子。这些描写与其说在写“狐精”,不如说是在写人间俊男美女。 (二)天真可爱的“狐精” 唐文化的明朗大度同样表现在狐精形象的塑造上,《广异记》中的“狐精”和前代“狐怪”的不同还来自于它们的可爱天真。《李氏》篇中一大狐来魅人间女子,大狐的小弟帮助被扰的女子家驱逐自己的兄长,连施两种法术后果然灵验,最后小狐来到被扰人家曰:“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1] 500在狐弟弟的帮助下,这个人家果然脱离了狐哥哥的侵扰。读到这里,读者不仅喜欢上这个活泼可爱、好助人为乐的狐弟弟,连同它那个蛊魅人间女子的狐哥哥甚至也一并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