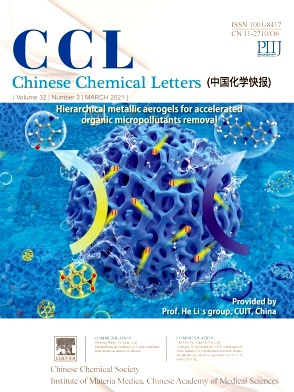分析绘画材质之变与元代山水画观念和技术之变
胡光华 李书琴 2010-11-12
[论文关键词]绘画材质;元代山水画;艺术观念和技术;文人化和人格化;变革
[论文摘要]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由绘画材质的应用变化而引起艺术表现风格形式大变与创新的莫过于元代。本文力图通过对元代山水画家流行在纸地,特别是在生纸上作画的量化分析和现象学定性研究,揭示绘画材质(生纸)的广泛运用是如何引发了元代山水画艺术观念和技术之变,从而又引发了元代山水画文人化、人格化的巨大变革。
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到元代又一大变,是山水画的文人化、人格化。山水画的文人化、人格化,除表现文人士大夫遁世的情怀、抗俗的人格气节之外,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独到的创新与创造,那就是他们擅长干笔效擦,水墨渲染,逸笔草草,悠率写意,这是元代文人写意山水画大变的重要风格形式特征。而风格形式之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绘画材质的变化引起文人水墨写意山水画在观念和技术上的巨变。综观元代文人写意山水画名作,从元初赵孟顺的《鹊华秋色图》、《水村图》、《秀石疏林图》、《双松平远图》,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丹崖玉树图》、《富春大岭图》、《快雪时睛图》,吴镇的《松泉图》、《洞庭渔隐图》,倪珊的《六君子图》、《渔庄秋界图》、《虞山林壑图》、《江岸望山图》、《容膝斋图》、《紫芝山房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夏日山居图》、《春山读书图》、《花溪渔隐图》、《秋山草堂图》、《西郊草堂图》,曹知白的《贞松白雪轩图》、《溪山泛艇图》、《溪山烟霭图》、《双松图》,高克恭的《雨山图》,盛惫的《秋江待渡图》、《清溪渔隐图》,管仲姬的《竹澳览胜图》,陈汝言的《百丈泉图》,赵雍的《松溪钓艇图》、《采菱图》和刘因的《秋江渔艇图》,郭界的《写高使君意图》,方从义的《武夷放掉图》、《高高亭图》,姚廷美的《有余闲图》、《雪江游艇图》,沈钻的《平远山水图》等等,无一不是纸本材质之作。在纸上(尤其是生纸)能充分发挥笔墨起毛渗化变幻的艺术效果,可在其上尽情游戏笔里,这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家的重大发现与观念和技法上的变革创新成就所在。
在纸上作书画始于魏晋时代,东吴的曹不兴在纸地上画过《如意轮图》,川但是,这还不是山水画。迄今所发现最早的纸本山水画,是新疆吐鲁番晋墓出土的《地主庄园图》,但晋代通常是用纸书法、东晋时楚帝桓玄曾下过简用纸令,书家盒从,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多用会稽竖纹竹纸,宋代米带的《书史》,记载了从二王书法用黄麻纸开始,一直到宋朝历代书法家用纸情况.其中唐代书家用纸绢共37例,用纸者就高达三十余例。唐代至五代时,书画用纸普遍进步,运用也广。唐高宗(650一683年)时,就常用黄纸为诏救、写书、写经书用、书法家欧阳询曾用黄麻纸书写孝经。唐末,画家贯休和尚还在纸上用“墨笔”绘制十六应真立轴,至于是何质料纸地,却未见记载。不过,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倒记载了唐代已经开始使用宣纸进行绘画幕拓:“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幕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一一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踪写不掇。五代、两宋时在纸上作画开始漫行,出现了书画专用纸澄心堂纸。据史料记载,南唐李后主遣人在庐山精舍爽恺地,为精舍,极一时林泉之胜,命董源以澄心堂纸写其图,董源还用澄心堂纸为南唐中主在庐山五老峰下的开先寺作过山水画。难怪米带著录所见董源画之材质,均为纸地。北宋用澄心堂纸作画的名画家有李公麟,他也爱用澄心堂纸作画,明代屠隆在《纸墨笔砚笺》中说:“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即李公麟)画多用此纸,毫间有纸织成界道,谓之‘乌丝栏’。李公麟的《白描罗汉卷》,即是用澄心堂纸所画。五代、两宋时的澄心堂纸有所不同,南唐时纸质稍厚而色暗,至北宋李公麟时代已改进成质地坚洁的样子。
宋代叶梦得对书画用纸与笔墨的关系颇有研究,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世言歇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系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叶梦得“不喜用”的是“不受墨”的书写用纸,喜用的是受墨的“麻纸”,因此可见宋人对书画用纸的质地与笔墨效果,已有了相当多的考究。从在纸上书法到在纸上拓画、作画,画材底子的变化为绘画追求笔墨表现效果开辟了新的天地。到南宋时,在纸上作画之风渐开,出现了一批追求笔墨表现效果的优秀作品,诸如杨无咎的代表作《四梅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梁楷的代表作《泼墨仙人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六祖截竹图》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和《踊布袋图》轴(日本香雪美术馆藏)、赵孟坚的《墨兰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陈容的《九龙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等等;特别是出现了一批纸本水墨山水画,如牧溪(法常)的《渔村夕照图》卷(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远浦归帆图》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平沙落雁图》卷(日本出光美术馆藏),以及玉涧的《山市晴峦图》卷(日本出光美术馆藏)、《远浦归帆图》卷(日本德川美术馆藏)等等。
北宋米萧最了解笔墨与用纸的关系,是最早发现生纸作书画的用途和用生纸作画游戏笔墨的画家,他说:“韩退之用生纸录文,为不敏也、生纸当是草上所用。”宋代赵希鹊在《洞天清禄集》中记载米带“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皆后人伪作,米父子不如此。”可见米莆不但精通生纸性能用途,“生纸当是草上所用”,而且专尚在生纸(不上胶矾之纸)上作画,玩弄笔墨,甚至用纸筋、蔗滓、莲房代替笔在生纸上作墨戏。生纸上可以产生笔墨淋漓渗化层次丰富的艺术效果,这是在绢地上作画所达不到的,因而为文人墨戏之作观念和技术变革提供了材质基础。传世南宋米友仁的《远抽睛云图》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潇湘奇观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潇湘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皆粗枝大叶,逸笔草草,水墨淋漓,所以他会在《远帕晴云图》轴上自题“元晖戏作”。
宋人开始在生纸上游戏笔墨,对元代文人画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拙文前段所述,元代文人山水画家广泛使用纸张,尤其是使用生纸作山水画。例如,赵孟顺自少习画,“日数十纸”。他喜用江西出产的白鹿纸(系树皮所造的棉纸)“用以写字作画”。‘”黄公望有“纸上难画”之说,但他又发现笔墨“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之优点,那就是可以充分发挥墨的艺术表现力,技法上“先用淡蟹,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其山水画名作《富春山居图》卷,就是成功地运用树皮棉料纸之半成品生粗易于墨化的材质效果绘制而成。而吴镇“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唯以佳纸笔投之按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故仲圭于绢素画绝少。”吴镇自己也有“古泉老师每以纸索作墨戏”书画题记可作凭证。王蒙拜访袁凯,饮茶未毕,“索纸为作《云山图》”,王蒙还曾用罗文纸为坦斋老师作《泉石图》。就连元文宗图铁睦耳居金陵潜邸时画京都万岁山,也是“索纸”而绘。元人喜爱在纸上,特别是在生纸上作画的结果,是引发了元代山水画艺术观念和技术的巨变。在观念与技巧上的变革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书法笔法人山水画,把“写”作为山水画的观念,追求画法的书法化;二是时尚笔墨游戏,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自出胸臆。
以书画笔法人山水画艺术观念的发生,与元代文人山水画家均擅书法有关。晋唐宋以来书家一般习惯用纸书法,这为作为“良家”(即非职业画家)的元代文人山水画家能把自己在书法上的才能,转化为纸本上作山水画在技法提供了便捷之法。率先提出以书画笔法人山水画主张的是赵孟倾,他在纸本《秀石疏林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自题诗道:“石如飞白木如箱,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元代主张以书法笔法作画并不始于赵孟顺,而是画竹名家柯九思(1290-1343年)。赵孟顺在这一图卷题诗后跋曰:“柯九思善写竹,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显然,柯九思主张以书法笔法人画的是竹石,重点在以书法笔法画竹;而赵孟顺受他的启发,把以书法笔法画竹与石,加以发挥,变通成画疏林秀石山水之法,用箱法(即大篆)画疏林之韧、飞白书写秀石之质,从而使山水画笔法本身具有特殊的笔性和写意的表现力,尤其是他提出了“写”作为山水画的观念,这在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元代文人画家在艺术观念上追求以书法笔法人画,变书法为画法,追求画法的书法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的《水村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就是以书法笔法人山水画的代表作。全卷纯用干笔淡墨挥写山水林木,笔法松秀灵动,含烟带水,笔墨苍润,一展江南山水清秀无尘特质,而笔墨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美感。另外,从画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赵孟顺受董源山水画《潇湘图》卷影响的痕迹,比如画面平淡天真的构图,远岸丘峦用披麻效法,均取法于董源,因为大德六年(1303年)赵孟倾作《水村图》卷时,他已收藏董源山水画《潇湘图》卷多年了,受董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品味“古意”,以“到处云山是我师”创作态度,简率的水墨“写”山水画风格,表现时代的审美情趣,所以能不受前人局限,超越了董源。赵孟顺的另一件以书法笔法入山水画的典型之作是《双松平远图》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画法上像他晚年所作《秀石疏林图》卷那样,全以书法笔法写出,松干用篆法挥写,折转顿挫有力而虚实粗细灵活,彼岸山峦、山石坡丘飞白书笔法历历在目,用笔更加简率放达,简化到仅以大线条写起伏变化轮廓,几乎没有效染。可见,赵孟顺变书法为山水画的画法,追求画法的书法化,并不虚言;他致力于借古开今,变革创新,追求写意。这种简率的“写”山水画之法,可谓“真士气画”之法,对黄公望、王蒙、倪攒等人充分发挥书法笔法写山水,以笔法苍秀灵活多变各成一家风流,产生深远影响。
因受赵孟顺的影响,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的黄公望,干脆把自己的山水画论著作称为《写山水诀》。其山水画的笔法如草篆,如著名的纸本山水画《富春山居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就是如此。是卷写林木,运用草篆变化灵活有力的笔法,出以中锋、秃笔、破笔、聚笔、叠笔、混笔、策笔等书法性笔法,如近岸松林用中锋秃笔,松叶笔墨如燕聚攒,临风掠动;杂树或以中锋针笔,或以中锋叠笔,枝叶纷披;此外,峰峦丛林多中锋干墨秃笔或破笔、聚笔,而云峰水岸岗丘浅滩丛林多湿墨混笔、叠笔、润笔,笔墨牵连混杂,层次微妙湮润,烟林森然如大军领卒,气韵苍浑,其娴熟的草篆笔意确实达到了表现“树要有身分”的艺术效果。就写山石而言,黄公望主张:“先记披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大概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是卷均以干笔淡墨为之,效笔如草篆圆转活脱,似枯而润,似虚而实,笔含飞白,糊突其笔,笔中连勾带效、披中带擦,效染兼施,下笔便有凹凸、阴阳变化,山石见形见质,神彩焕然;尤其是效法忽长忽短,似披麻披又象解索效,潇洒自然;笔法似疏而密,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画卷遥山如黛,摄江南山水秀润多姿神韵。笔墨如此鬼斧神工,既得江山之助,具有富春山水绮丽秀美特征,又神明变化,以手运心,如写字般地神游笔墨,全入熟妙化境,达到了“写真山形”的目的,所以清代画家吴历评道:“大痴晚年归富阳,写富春山卷,笔法游戏如草篆。清代邹之麟也推崇备至地说:“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黄公望的另一件纸本山水画《陡壑密林图双美国怀云楼藏),也是“画法如草篆奇箱”的力作。甚至连他在作纸本雪景山水画《快雪时晴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也是采用草篆飞白书的笔法挥写,以娴熟的渴笔细线勾勒山石,稍加淡墨擦染,几乎不施效笔,山体自然浑厚,别有一种荒率苍莽之气,逸致横生,真可谓“天开图画”也。明代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对大痴的这种以书法笔法入山水画的风格评论道:“体格俱方,以笔腮拖下,取刷丝飞白之势而以淡墨笼之,乃子久稍变荆关法而为之者,他人无是也。”
王蒙也擅长以篆书笔法人山水画。例如,王蒙中晚年时一些以读书、书屋和隐居为画题的“书斋山水”。他的纸本山水画《春山读书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具区林屋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卞隐居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等,往往用篆书笔法人画。这时他喜用细如游丝的草篆书法笔法作画,以变化披麻、荷叶等效法,披法随山形山势山质而旋动,创出了波曲律动的牛毛鼓和解索效法来表现南方松软的山石沟壑,鼓笔干湿浓淡枯实燥润,笔法乱中见质,灵活多变,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江南山川草木葱笼、秀润多姿的丰采。以至于他深有体会地说:“老来渐觉笔头迁,写画如同写篆书。所以,倪攒在题王蒙《岩居高士图》时赞道:“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攒也每每自题山水为“写”(见倪攒纸本山水画《虞山林壑图》、《江岸望山图》等)。此外,还有高克恭、钱选、方从义、马文璧等人,皆深谙“写”画之内涵,论画或题画,以“写”为识。这些都是因为文人士大夫在纸地上作画,观念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把自己的书法技能变为绘画技法所致。正如元代文人画家杨维祯所言:“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擅于书法是文人的特色,画法的书法化或书法化画风无疑是元代文人笔墨使气脱俗的体现,显示了文人士大夫逃往艺术之乡所具有的任性和人格觉醒的灵性。对此,清代画家吴历深有感触地说:“元人择僻静之地结构层楼为画所,朝起看四山烟云变幻,得一新境便欣然作画,大都如草书法,惟写胸中逸趣耳,一树一石迥然不同。”因此,在绘画技法上对书法化画风的自觉追求开启了元代山水画走向文人化、人格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山水画到元代又一大变,“写”山水画观念的提出,毫无疑问是“元画变化”的主要原因。 与以书法笔法人画,“写”山水画,追求画法的书法化相适应的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家时尚在纸质材料上游戏笔墨,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自出胸臆,使笔墨技术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并使笔墨技术的意义提升。如倪攒擅长渴笔淡墨,干笔效擦,逸笔草草,笔法秀峭,以抒写胸中逸气.黄公望笔法游戏如草篆,擅长逸墨撇脱,浅绛烘染,“使墨士气”,王蒙擅长笔法一波三折,灵秀深厚,纵横潇洒,线如秋草,两边生毛,“以兹谢尘嚣”;吴镇以湿笔使气,擅长水墨淋漓、墨法中兼有笔法,以写抗怀鸣高“莽莽林’下风”的墨戏;方从义纵笔水墨大写意,殊草草,只求意到天趣一一等等。这些极富个性化的“写”山水画的作风,不仅使笔墨技术本身开始具有形式美感和独特深邃的审美意义与价值,而且笔墨各领风骚,那就是化笔墨表现形式为情思,同时又将文人的学问、审美意趣自由无碍地渗透在绘画创作之中,以自出胸臆的笔墨游戏形式表现文人士大夫人格的活脱和超越品质。黄公望所追求的“画一案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倪攒所追求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皆一语道破了天机,说明了在纸地上游戏笔墨与文人画家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审美追求和人品气节息息相关,这一切导致了笔墨意义的提升。
黄公望是元代使笔墨技术的意义提升的代表性山水画家。他把山水画写意视为“游戏”,以表现画家的创作思想、艺术凤格、审美追求和人品气节,提出:“是知达人游戏于万物之表,岂形似之徒夸;或者寓兴于此,其有所谓而然耶。”也就是因心造境,不求形似,而求神韵超轶于万物之表,游刃有余,使笔墨具有强烈的写意性、表现性,故大痴能化景物为情思,如清代画家王原祁在《烟客题跋》中盛赞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时所说:“神韵超轶,体备众法,又能脱化浑融,不落笔墨蹊径,故非人所企及,此诚艺林飞仙,回出尘埃之外者也。”所以,不难看到黄公望会在历七年时间完成的《江山胜览图卷》中得意地写道:“余生平嗜徽成痴,寄兴于山水,然得画家三昧,为游戏而已。”可以说,黄公望创造的浅绛山水,就是一种典型的山水画“游戏”。如纸本浅绛山水《丹崖玉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整个作品均以墨笔渗色绘制,山石峰峦用枯淡细如游丝般的披麻披挥写,而不作墨青渲染,代之以浅淡储石、藤黄薄色罩染烘托,即他所谓“画石之妙,用藤黄水侵入墨,自然润色。不可用多,多则要滞笔。间用螺青入墨亦妙。吴妆容易入眼,使墨士气。”原来黄公望创浅绛山水一格,色墨简淡清丽,就是为了提高笔墨的写意性、表现性,妙在突显山明木苍气骨,画境清远闲静,给人以离尘绝俗之想,达到“使墨士气”一一文人化、人格化的审美理想和境界。在中国山水画艺术史上,就理论到创作实践来看,“浅绛”山水之变始于、盛于大痴,他使笔墨技术随着画家的灵性而变化升华,诚如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赞日:“痴翁设色,与墨气融洽为一,渲染烘托,妙奇化工。元代深受大痴“浅绛”山水影响的有王蒙,王概说:“王蒙多以储石和藤黄着山水。”或者“只以储石澹水润松身,略勾石廓,便丰彩绝伦。大痴“浅绛’山水画艺术大大提升了笔墨技术的写意性和表现性,其变法成就影响播及明清,山水画史上谓之“吴装”。
梅花道人吴仲圭是元代使笔墨技术的意义提升的另一代表性山水画家,脍炙人口的“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就出自他之口。在这里,吴仲圭提出了文人墨戏,是追求性灵迸发时的“兴趣”。如吴镇在至元四年(1338年)“奉为子渊戏作”之纸本《松泉图》,至正五年冬十月“奉为大无炼师观静堂”所作的纸本“墨戏”《梅花道人山水》四幅以及《秋江渔隐图轴》等。梅道人还在他的《松图并题》中记述了他与道人隐君的唱和往事:“青云山中太玄道人,隐者也。时扁舟往来茜武之上。与游则樵夫野老而已。余拙守衡茅橡林有年矣,夏末会于幽澜泉,山主常师方吸茗碗。忽若口气逼怀,黄帽催行甚急。别后流光迅速,惜哉!因就严韵戏成四首书于画松之上”。并在画上题诗咏道:“幽澜话别汗沽衣,飒尔西风候雁飞。我但悠悠安所分,谁能屑屑审其微。”可见其墨戏之“兴趣”在于表现隐逸江湖、抗怀鸣高的人品气节。他所画山水《草亭诗意图》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如其题诗谓:“依村构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鸟乐,尘远竹松清。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何当谢凡近,任适慰平生。意在以超尘抗俗的文人化、人格化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审美追求,来陶冶性情和人生,展现文人士大夫人格的活脱和超越品质。因此,其“墨戏”表现的是一种主观情绪,而不是客观实际对象,这种情绪可用水墨淋漓的山水松泉或其它墨戏来写“一时之兴趣”。吴镇一系列以“渔父渔隐”为题的山水画,如纸本《洞庭渔隐图》轴、《渔父图》轴、《芦花寒雁图》轴等名作,就是典型的山水画“游戏”,作品充分发挥水墨氛氯的特性,以淋漓水墨渲染,湿笔浓墨点苔,抒写悠闲澹远的情致,从而使笔墨有力地表现出了“云散天空烟水阔”之境界,山水烟江成为有江湖之思的高人隐士遁世避俗,人格高蹈,逍遥自在,悠情弄性,玩世不恭的精神家园。在元代山水画史上,吴镇开创了与“元四家”其他三位画家别样的“墨戏”风格,那就是以湿笔山水、长于墨法,墨法中兼有笔法的墨戏,创造出游戏于万物之表的闲云野鹤式情调的阔远山水画,使笔墨技术的写意性、表现性提升到“有我之境”的新境地,这从他在纸本山水名作《洞庭渔隐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自题一首《渔父词》中可以见得:“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搅湖心一叶横。兰掉稳,草花新,只钓妒鱼不钓名。”显然,吴镇化笔墨写意表现为情思,为文人化、人格化的审美理想和境界,不但使笔墨技术本身具有独特的“墨戏”审美意义和价值,而且使笔墨技术的意义提升。对此,明代姜绍书深有所察,他在《韵石斋笔谈》中指出:“梅道人画秀劲拓落,运斤成风,款侧墨沈淋漓,龙蛇飞动,即缀以篇计,亦摩空独运,旁无赞词。”难怪倪云林向吴镇“索墨戏”,吴镇会很得意地说道:“戏而作此……聊发同志一笑。”其“墨戏”笔墨技术的写意性、表现性自然会引起同仁的共鸣,倪珊盛赞吴镇“墨戏”时就说:“游戏入三昧,披图聊我娱。
当然,自题山水画为“戏写”的倪珊也是元代“逸笔”墨戏高手,那就是他的山水画作风因“聊写胸中逸气”而放笔游戏笔墨,山水画变实为虚,遥抽平坡,山高水阔,意境深遂,形成独具一格的简率荒老的阔远山水画体貌,即黄公望为云林题画所言:“春林远峋云林画,意态萧然物外情。”诸如,倪珊晚年的纸本山水画代表作《容膝斋图》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坡石以侧锋折带效挥写,笔法细劲有力,折转婉和流利,并以淡墨渴笔披擦山石体面,再稍加清水淡墨渲染,施浓墨横点苔山石之骨,尽显山石清洁斑驳、苍劲老辣之质。树叶以横点墨法、葫寂点法、悬针法写出,稀硫纷披.树千虽枯千细瘦,却腰板挺直而立,大有一种倔傲清高之气,其笔墨技术本身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义及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倪珊鼓吹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自出胸脆,尝言自己画树的“玄思”是树木枯疏,似我容发.画阔远山水是“江水空青好卜居”而卜居孤亭坡岸又是“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亭中无人又是他在《安处斋图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中题诗所云:“幽栖不作红尘客,遮莫寒江卷浪花。”而他中晚年的山水画“在章法笔法之外”的玄机是:“一木一石,自有千岩万壑之趣。”纯然是山水画文人化、人格化之禅趣的表现。所以,清代著名画家挥南田说“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云林,几失云林矣。”倪珊这种以我观物,化景物为情思,化荒天古木为文人君子刚正不阿人格的逸笔游戏作风,使笔墨技术的意义提升到表现文人士大夫人格的活脱和超越品质,“有我之境”的高度。
或许元代这种追崇墨戏、游戏之风也与钱选、赵孟顺的推导有关。元初,山水画名家钱选称这类画作为“翰墨游戏”。赵孟顺作纸本山水画《双松平远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就自题标榜为“戏作”,他还在题陈琳的纸本《溪尧图》(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时赞道:“陈仲美戏作此图,近世画人皆不及也。”所以,元代绘画理论家汤垢在《画鉴》中指出:“若观山水、墨竹、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
总之,元代山水画家流行在纸地,特别是在生纸上作画的材质变革,导致了“写”山水画观念的提出,以及将山水画视为游戏、墨戏、游戏笔墨的结果,是笔墨意义的提升一一把笔墨当为游戏于万物之表的笔墨游戏,从而又引发了元代山水画创作观念和技术的变革,促进了元代山水画文人化、人格化的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