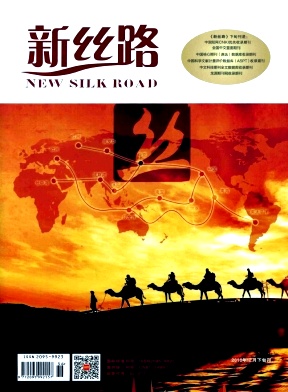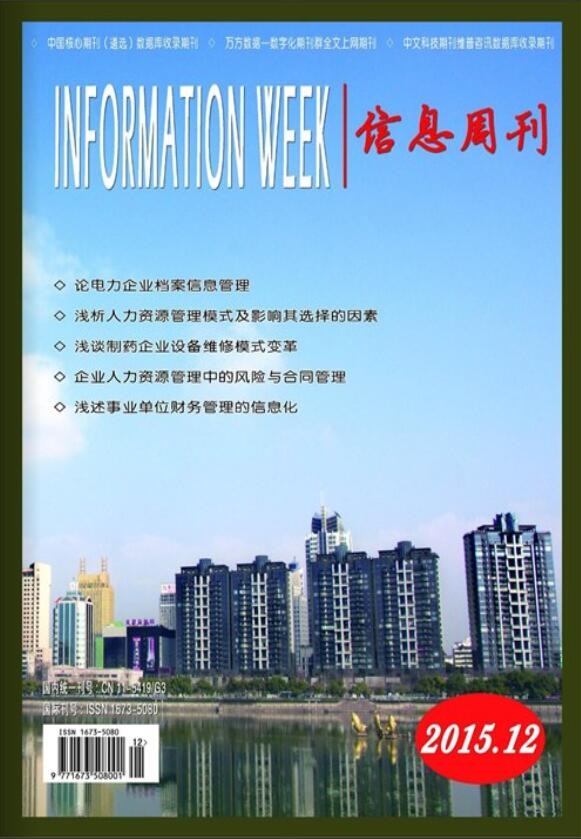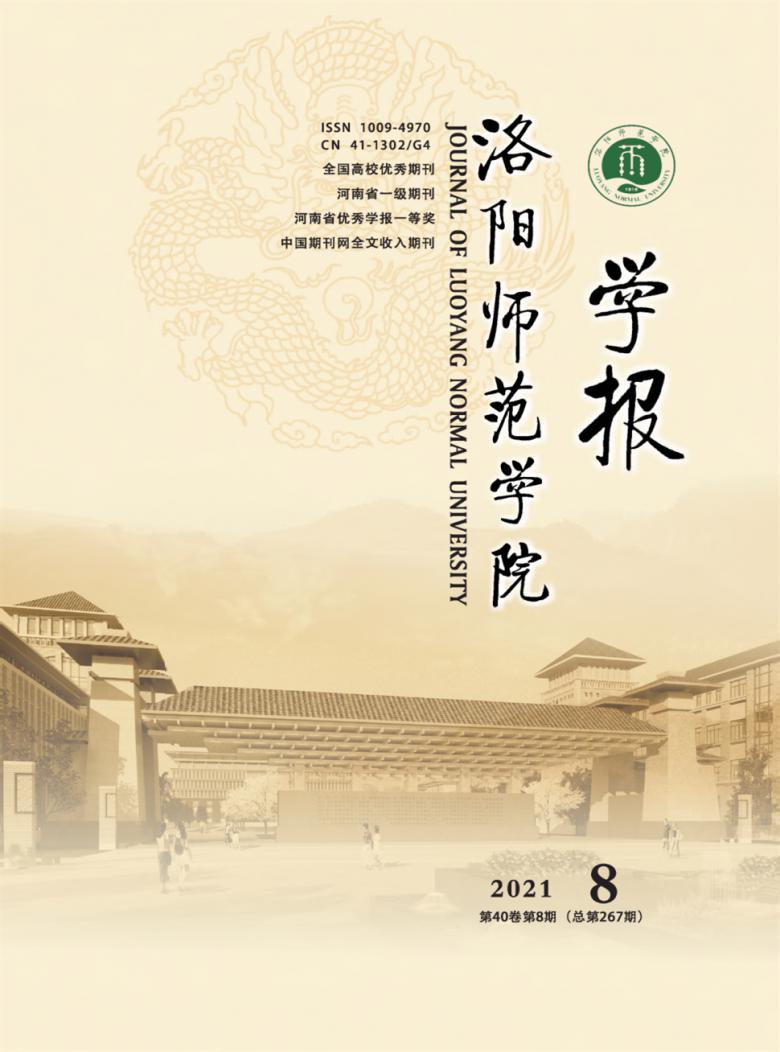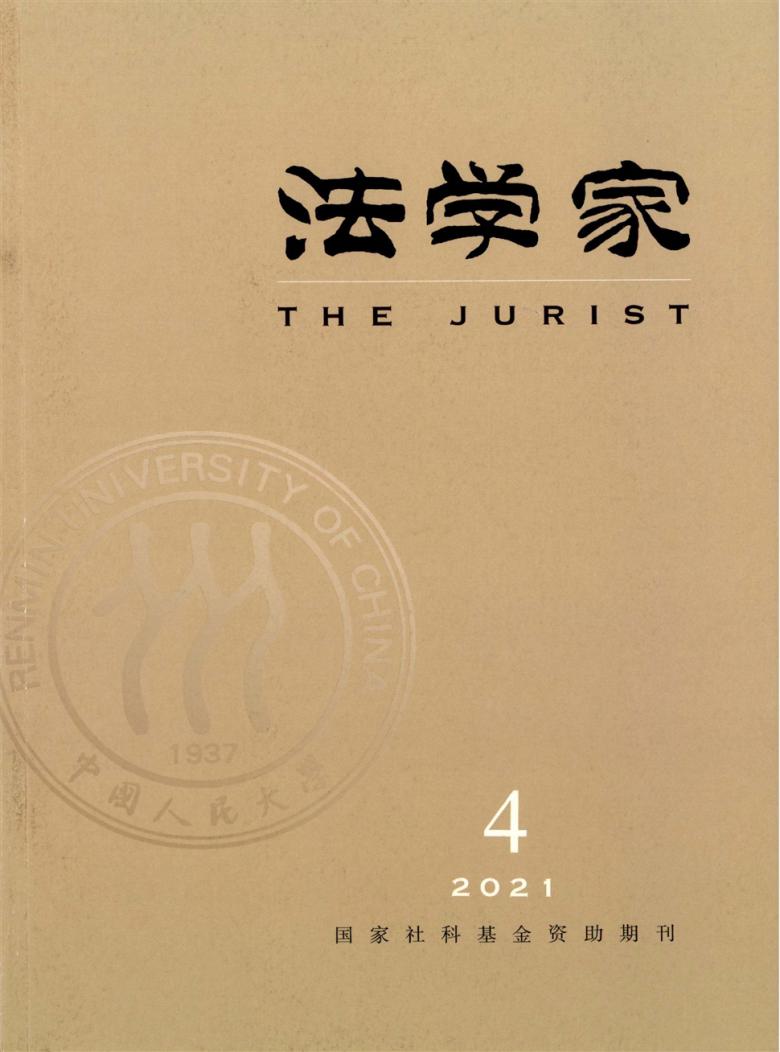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
贾丛江 2006-05-17
元朝前期,因遭受战祸,亦都护王族和大批畏兀儿人东迁永昌,传国400余年的高昌回鹘政权从此除国。《高昌王世勋之碑》汉碑记录其事曰:
“[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城受围六月,不解。……(亦都护火赤哈儿)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诸城下,而与之。 都哇解去。其后入朝,上嘉其功,……还镇火州,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1]
《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取材于虞集撰写的《高昌王世勋之碑》(以下简称《世勋碑》),所记火州之战、入京朝觐、战死哈密、迁居永昌等连续发生的事件,与碑铭文字基本相同。
一、永昌之名的由来
元代有多处地方以“永昌”为名,云南行省就有隶属会川路的永昌州(治今四川会理)和隶属大理路的永昌府(治今云南保山)。当然,它们和畏兀儿迁居的永昌,除名称相同之外,并无别的关系。畏兀儿东迁之永昌,在甘肃行省境内,是元代新出现的地名。
永昌之名,缘起于窝阔台之孙、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自筑城池。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将凉州(今甘肃武威)分封给第三子阔端,把蒙古雪你惕部和速勒都思部共3千户,一同封授阔端。[2] 阔端在当地拓展了大片疆土,也获赐大片封地(也称分地,泛指封户、食邑户、私属户所居地)。1251年蒙哥继任大汗后,对窝阔台系诸王进行打击,阔端因与蒙哥汗友善,封地未受影响。不久,阔端谢世,其王位和包括凉州在内的主要封地,由第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只必帖木儿的封地,即屡见元代文献的所谓“二十四城”,主要分布在在今甘肃、宁夏中南部地区,在其它地区也有少部分封地。在中统(1260—1263)初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期间,只必帖木儿支持忽必烈,虽然为此遭到阿里不哥党羽的攻击,损失惨重 ,却赢得元世祖的信任,在世祖朝前期频繁出现于史册。《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这个“永昌府”是世祖赐予新建王城的名字,不是元朝行政区划中介于路和州之间的“府”。不久,情况又发生变化,《元史·地理志三》载:“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便是永昌城(即王城)和永昌路的名称和建制的由来。
永昌路的设置,与元世祖忽必烈整顿诸王投下封地有关。蒙元前期,各地投下户和诸王封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因此,世祖对封地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使拥有较多投下户的诸王独占一州一路,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永昌路以只必帖木儿的封地为主,故而以他的王城之名,新建一路。另外,他的封地在相邻的巩昌路也占据主导地位。只必帖木儿修筑新城,与中统初年遭受阿里不哥部下洗劫有关。当时,叛军大将“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3] 他的斡耳朵被洗劫以后, 只得率部暂时就食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境内,[4] 即今宁夏省中南部地区。史籍记载,当时担任西夏中兴行省郎中的董文用,曾依法禁止他的王傅府属官滥征投下户税课,因而激化了与只必帖木儿的矛盾。董氏是在“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的,至元八年时调任山东,[5] 双方发生矛盾的时间只会在至元八年(1271)之前。这表明当时只必帖木儿驻牧于该地。在此期间,他在原居地筑建新城。新城落成后,他便迁回那里。这座永昌城,与元朝常见的蒙古王城一样,只是一座类似城堡的小型城邑。
二、对永昌城位置产生分歧认识的历史原因
元代文献有多处提及畏兀儿迁居“永昌”之事。而“永昌”一名是泛指所在的永昌路呢,还是确指永昌城?这个有些吹毛求疵的问题,和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有关,故而先作说明。前文所引《世勋碑》有“遂留永昌焉”一句,从中无法确定究竟何指。再看下文:《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忻都公碑》)有“至顺二年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城里”[6];《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司事和赏公墳记》记末代高昌王和赏“幼亦绍王,封镇永昌”。[7] 以上史料表明,“畏兀儿迁居永昌”之说,源出亦都护家族定居于永昌城。
目前,笼罩在永昌城位置问题上的迷雾已经散开,结合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人们能够确定,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城就是只必帖木儿的王城,它不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而是位于今武威市北郊30里处的永昌堡。然而,现存大量清代文献中,普遍存在着对畏兀儿迁居之永昌城位置的错误记载,这些记载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文献认为,元代永昌城位于清代永昌县境内。而清代永昌县址在今天甘肃省永昌县,位于武威市和张掖市之间,东南至武威约140里,县城西北有古长城遗址。清人饶敦秩等编制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中,有方格地图《元地理图说》一幅,作者在凉州西北、甘州(今甘肃张掖)东南、城址西北紧邻长城(图中有长城标识)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永昌县县址,标有“永昌”之名。而且,该图是将永昌当作元代的地名标著的——按此图凡例,各朝古地名一律于文字外加方框,清代地名则不加。据饶氏在序文中讲,此图册是根据前人所撰《方舆纪要》为蓝本绘制的,[8] 反映了此前已经有了这种错误认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六《汪古畏兀二驸马列传》记曰:“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将齐发,(纽林的斤)遂留永昌”,“永昌”下注曰:“今县属凉州府”,[9] 即屠氏也认为,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在清代凉州府内的永昌县。《宣统甘肃通志》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永昌县,虞集奉敕撰”[10]的记载,其它旧志如《甘肃新通志稿》、《新疆图志》,也分别认为《世勋碑》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立在清代永昌县,[11] 墓碑既然在永昌县,畏兀儿所居之城自然也是这里。
当然,并非所有的旧志书都记载错误,《五凉志》就有“元追封西宁王,忻都墓在武威永昌堡”[12]的正确记录。事实上,《世勋碑》和《忻都公碑》都出土于武威市永昌堡一个叫石碑沟的地方。《世勋碑》原碑左侧刻有近人贾坛、唐发科刻写的跋文,称:“(此碑)于清季被土恶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一九三三年)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13] 高昌乡在永昌堡一带,今乡名已改。石碑沟是当时亦都护和畏兀儿贵族的墓地,盖因石碑多现,后人才以石碑沟名之。
清代文献,尤其是甘肃当地的多种旧志书,将元代永昌城和清代永昌县相混淆,这种奇怪现象并不只是缘于编书者的疏漏,而是此中确有极易混淆的地方。《元史·地理志》“永昌路”条正如上文所引,记述简约,只谈到永昌路建制和名称的源起,却没有说明永昌路路级政府官衙(即治所)和只必帖木儿王城位于何地。永昌城是诸王的小型私城,永昌路治所不会设在那里。《中国历史地图集(七)》“元·甘肃行省图”,将永昌路治所标注在今天永昌县的位置上(未标明该城元代为何名),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该地在元朝叫什么,则查史无证。今天永昌县,汉代叫番和县,一直至唐初县城仍以番和(或番禾)为名,唐天宝年间改名天宝,后陷于吐蕃;[14]从西夏到元朝,该地之名没有再见诸于史册,似乎这座城市已经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既然元代文献没有这个地名的记录,那么,又怎么能确定永昌路的治所在这里呢?这是依据明代文献得出的结论。《明史·地理志三》记载,“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永昌卫)北有金山,丽水出焉,……西北距行都司三百十里”,文中指明,永昌卫北靠金山,西北距陕西行都司治所甘州城(今张掖)310华里,这正是今天永昌县的位置;同时也指出,明朝永昌卫所在地,就是元代永昌路和永昌宣慰司的治所。清朝改永昌卫为永昌县,并延续至今。在我国行政建制史上,当城市的名称与上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相同时,上一级区划的治所往往就在该城,如元代的甘州路治于甘州,肃州路治于肃州等。人们正是基于这种常识,误以为元朝永昌路的治所就是永昌城(实为今永昌县境),而明代偏偏又在那里设立了永昌卫,这更增加了误会。于是就有了,清代的永昌县(今永昌县),就是元代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城的错误认识。
三、东迁的时间
元代文献没有留下畏兀儿何时迁居永昌的记录。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个由连续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链条:都哇围困火州、火赤哈儿入京朝觐、返回后战死哈密、东迁永昌。在这组时间链条中,只有都哇围困火州的时间见诸史册。虞集所撰《世勋碑》汉文碑铭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其事在至元十二年(1275),后者以前者为蓝本,故而两处实出一源。“至元十二年说”在晚清时受到屠寄“至元二十二年(1285)说”的质疑。由于两说均有比较坚实的史料支持,学界至今也没有公认的结论。笔者虽持“至元二十二年说”,但在探讨东迁时间上,是不能采取依次推导的办法,因为在那个时间链条中,既然起点(火州之役)的时间存疑,若由起点来推导终点(东迁永昌)的时间,不论事实是否如此,也都不足凭信了。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第三种,有“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缴给(蒙古)皇帝陛下一锭金子(罚金),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罚金),缴给亦都护(高昌王)一锭银子(罚金)”一段文字。[15] 这份契约原件右边有:“庚辰禩捌月念六日给予新恩沙尔善斌收执”十八个汉字,“禩”即“祀”,意为年。元代共有三个庚辰年:太祖十五年(1220)、至元十七年(1280)、后至元六年(1340)。文书中有“钞”等词,不会是成吉思汗时代的文物;后至元六年时,畏兀儿地区早已并入察合台汗国,契约不应有汉文批语和关防;另外,契文中有“按察使”(ancasilar)一词,《元史》卷一一记载,至元十八年“罢霍州畏兀按察司”。据此,冯家升和捷尼舍夫判定这件文书写于至元十七年(1280)。[16] 这表明当时亦都护政权仍然存在。迁居永昌,使传国400余年的政权就此除国,元廷也少了一个对抗西北叛王的得力助手,因此,东迁只能发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据史籍记载,至元十七年三月,元廷“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当年岁末, 又“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说明这时元廷在当地的统治秩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将至元十七年(1280)作为考察东迁时间的上限,是可以成立的。
东迁发生在世祖朝,至元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294),是此事发生的前后时限。其下限还能提前,《元史·世祖纪十二》记:“[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壬子],孛罗带上别十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此事持续了两年多,至元二十八年岁末,“罢遣官招集畏兀氏”。[17] 依照常制,招集畏兀儿流散民户是由亦都护派员负责,而这次在畏兀儿境内却由朝廷派官主持,说明此时亦都护家族已经入关避难。有证据表明,此次孛罗带是去别失八里组织畏兀儿人往甘肃迁居的。朝廷移民入的举措,只能在亦都护家族已经东迁入关的前提下施行。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以作为东迁永昌的时间下限。
排比中外文献,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间,元朝整个西北防线先后遭到叛王海都、都哇的四次入侵,其中三次被明确记载是以畏兀儿地区为战场的,另一次地点不明。造成火赤哈儿死难哈密、畏兀儿东迁永昌的,就是其中的一次。第一次入侵,是至元十七年七月,《元史·世祖纪八》记载:“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秃古灭以抢夺粮食为主要目标,地点在火州;遭劫之后,驿站能够很快恢复,表明破坏不大;史料也显示,此后几年中,元朝在当地的军政统治均很正常,所以,导致东迁的不是这次入侵。第二次是都哇的入侵,《元史·杭忽思传》记:“[至元]二十二年,征别失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秃呵(都哇)、不早麻(卜思巴) 战”,《史集》也载录了这次战役:“在合罕时代之末,都哇一度率军出征,到达边境上,……而出伯,末通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仓皇出动,当然,他支持不住溃逃了。……合罕知道此事后,责备了阿只吉,给了他九棍”。[18] 包括笔者在内的持“火州之战至元二十二年说”的学者,认为这就是都哇所讲“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的大战,元军溃败后,都哇进围火州。抛开火州之战的疑案不提,没有史料显示,东迁是由这次入侵造成的。第三次入侵,发生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二十二年大败后,元廷在西域组织了自至元八年建立阿里麻里行军大营之后的最大一次军事集结,大批部队开赴天山南北,西域形势为之一变。海都、都哇也倾尽全力与之决战,元军先胜后败。《元史·李进传》记:“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至和州(即火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从李进的行踪可以看出,战火烧到了火州以东。第四次入侵,发生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史·世祖纪》载:当年“[正月],海都犯边。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术伯北征”。我们不清楚这次海都入侵的方位,只知道这一年海都对岭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否同时分兵西域,则史无明文。而驻防哈密一线的元军主帅术伯(出伯),是统兵北上还是挥师西向,也不能确定。尽管文中称“北征”,但考虑到元代蒙古人的方位,与今天有逆转90度的误差,[19] 而元代文献中的方位,正确与错误兼而有之,“北征”也可能是指西征,所以,目前无法确定二十五年西域是否遭受入侵。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导致火赤哈儿战死哈密、畏兀儿余众东迁入关的,就是后两次入侵中的一次。那么,究竟是哪一次呢?笔者认为是第三次,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的战役。有史为证,《元史·世祖纪十一》记,“[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朝廷)遣蒲昌赤贫民墾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蒲昌为西域古地名,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端的鄯善县。[20] 我们知道,从鄯善到哈密有400多华里的戈壁地带,朝廷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蒲昌贫民的生活问题,那么,从甘肃调运粮食去,比把他们迁到甘肃的费用要少得多,他们到甘肃耕种的仍是抛荒的闲田,而屡遭战乱的畏兀儿地区有的是荒地。所以说,此次移民,不是单纯的安置贫民,而是有计划地移民入关,是前文提到的孛罗带在西域组织移民东迁入关一事的发端。至元后期内地之所以出现数万之众的畏兀儿移民,正是和朝廷的移民措施有关。[21]这也说明,二十三年十二月之前,火赤哈儿亦都护已经战死,其家族和余部已经东迁入关。东迁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冬之际。复原后的史实是,至元二十二年某时,都哇击败阿只吉、奥鲁只、出伯所率元军,乘势围困火州六个月,解围后火赤哈儿入京朝觐,二十三年,元军主力进驻天山南北,同年秋,与叛王发生大战,元军失利,在此期间,火赤哈儿也返抵西域,见火州一带陷于战火,故而停驻哈密,观望局势,不久,遭叛军突袭而亡,余部东撤入关,定居永昌。
四、封镇永昌的奥秘
战后余生的畏兀儿残部,没有停驻在河西走廊西部,而是东行跋涉近2千华里,最后定居在位于凉州以北不远的永昌城。该城是只必帖木儿的王城,作为“驸马诸王”的亦都护家族,最终鸠占鹊巢,使永昌城成为本家族的世袭封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日人安部健夫曾经探讨过畏兀儿东迁的问题,其关于至元十七年秃古灭入侵导致放弃火州、二十年走死哈密、二十一年前后迁居永昌的论断,正如前文所述,与史实不符,但安部氏关于畏兀儿得以在永昌立足,是缘于只必帖木儿丧失职权的判断,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22]
曾经显赫一时的阔端王位继承人只必帖木儿,自至元中期以后日趋没落。史册中屡见其贪婪、违法的劣迹,他见诸《元史》的20余次记载,竟有近半数与其贪婪不法有关,[23] 最终受到惩罚,也是势所必然。例如,至元初其暂居中兴路时,纵容王傅府属官滥征投下户税赋,导致与地方官董文用的冲突;《元史·世祖纪七》称,至元十六年,蒙古军士“侵掠平民,而诸王只必帖木儿所部为暴尤甚,命捕为首者置之法”; 《元史·察罕传》载,世祖曾派人巡察河西,其人回“奏诸王只必帖木儿用官太滥”。到至元年间(1264—1294)后期,其敛财之勤,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贪婪之态,已跃然纸上。据《元史·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十月,只必帖木儿“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朝廷)不许”;次月,又“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为朝廷否绝后,他仍不死心,在当月“又请立[二十四城]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按元制,前四汗时期(1206—1259),诸王领主可以自行征收汉地投下封户的丝料和户钞,世祖即位后,规定由朝廷统一征收“五户丝”和“江南户钞”,再由政府将领主应得部分转给诸王,禁止诸王自行征收。只必帖木儿明知有此制度,却累次三番要求朝廷允许他自征税科。而世祖和中书宰臣最终被纠缠不过,只好同意了他的这种请以朝廷命官为课税所正职,以王府私人为副职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但世祖及宰臣深知他的为人,在同意其所请的同时,由世祖给他亲下诏书,责令“(其)大都田土,并令输税;甘州新括田土,亩输租三升”。[24] 从该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向朝廷请求括敛钱财的举动,以及为让他依法缴纳赋税,竟要世祖亲下诏书来看,此人的违法乱纪、贪婪大胆,已到了何种程度。
他的一贯行为,终于在一年多后为其招来灾祸。史载: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朝廷下诏,“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课税)所,以其事入有司”。[25] 这个“巩昌二十四城”,就是前文所述的主要集中在巩昌、永昌两路的只必帖木儿的封地。朝廷将设立不久的二十四处机构一并罢撤,说明该王的不法行为已扰乱了地方秩序。罢拘榷所,只是他这次所受惩处的一部分。有史料表明,这一次只必帖木儿还被削夺了大部分封地,《元史·武宗纪二》载,至大三年八月,“以诸王只必铁木儿贫,仍以西凉府田赐之”,西凉府就是凉州,本是他继承父王阔端的最主要的封地,现在却称“仍以”其田赐之,说明此前已非他所有。当然,这次赐予的只是以前的部分封地。这条至大三年(1310)的史料,是自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受罚之后的14年里,只必帖木儿见诸《元史》的唯一一次,与以前屡屡露面的情形,形成鲜明比照,反映了受惩处后的没落境地。
只必帖木儿被削夺封地不久,至元二十三年秋冬之际,畏兀儿部民护佑着纽林的斤逃入关内。世祖和朝廷就将空出的永昌城和周边部分地区,转封给亦都护家族,作为以身报国者的后裔和部民的栖身之所。
五、亦都护和高昌王双王爵位的设置
按《世勋碑》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录的亦都护传袭世次,从至元二十三年火赤哈儿战死哈密,到至大元年(1308)武宗即位之间应该没有亦都护(当年册立纽林的斤)。然而,《元史·成宗纪一》记载:“[至元三十一年五月]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元史·成宗纪二》也有“[元贞二年三月]诏驸马赤(亦之误写)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之语;《元典章》所录成宗大德五年的圣旨中也提到亦都护。这说明《世勋碑》等载录的亦都护世次中,在火赤哈儿和纽林父子之间有缺漏。有学者注意到,《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所记传主之祖父雪雪的斤“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的身份,认为“很可能在至元末期,他(指雪雪的斤)即回到本部,继火赤哈儿之后为亦都护”,[26] 笔者基本赞同这种判断。雪雪的斤仅在《元史》露面数次,至元二十八年冬十月,“以前缅中行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为中书省平章政事”,[27] 他被调回京师,充任中书宰臣。《元史·诸公主表》有“雪雪的斤公主位”,表明他曾经尚公主。就目前笔者所见材料,畏兀儿王室曾经尚公主的,大都拥有亦都护的头衔,家族一般成员则不见曾有尚公主的。所以,我们认为,前引史料中出现于至元三十一年的亦都护,就是此人。当然,所谓“封高昌王”,其实是指袭承亦都护之位。他可能就是《世勋碑》回鹘碑文第3栏第12、13行提到的“听说出去的五位的斤中有一个进中原还未归还”[28]的人,据碑铭上下文,这是世祖皇帝在用火赤哈儿坚守火州的事迹教诲诸皇子时,转述火赤哈儿朝觐时提出的希望诸位的斤回归故里的要求。由此看来,雪雪的斤可能是火赤哈儿的儿子。据史料判断,雪雪的斤即位的时间,可能就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这一年正月,世祖忽必烈驾崩;同年四月,元成宗即位于大都;一个月之后,史籍中出现了“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的记载;无独有偶,赏赐亦都护一个月后,即三十一年六月,《元史·成宗纪一》记“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蒙元时期常有宗王遗孀获赐其夫封地所得的事情,而出嫁的黄金家族女性成员能享受朝廷赏赐的情况,则极为少见,对雪雪的斤公主而言,也是仅有的一次。看来,它不属于每年例行的岁赐,而属喜庆赏赐,赐“钞千锭”是祝贺她出阁。当时的情况是,成宗即位之初,册立雪雪的斤为亦都护,同时按缘自成吉思汗时的传统,将宗室公主嫁给亦都护。
武宗时期,纽林的斤继雪雪的斤之后嗣为亦都护,《世勋碑》回鹘文碑记其事“在幸福的猴年”,即至大元年(1308)。元仁宗时期,朝廷正式设立高昌王爵位,赐王印,与亦都护印并行。高昌王爵的设立年代,学者尚存不同看法:《元史·仁宗纪一》记:“[至大四年(1311)五月丁丑],置高昌王傅”,王傅是元代专门管理诸王封地和封户事务的私属机构,设立高昌王傅,似乎表明同时也设立了高昌王;第二年,即皇庆元年(1312)八月,有史料称:“亦都护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泽、宣使朵儿只二人,起马二疋,赍本位下王傅差剳”,[29] 这里已经混用“亦都护高昌王”称号。而另据《元史·诸王表》,高昌王爵设立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综合考量,笔者认为以延祐三年为确,虞集撰写的《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记载亦都护家族成员买闾之言:“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启王封于故国,朝廷之恩德重矣”,[30] 买闾之言应该不会有误;而且,高昌王的设置,与延祐年间(1314—1320)西域政局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故而不会设立于延祐以前(下文详述)。至大四年设立的“高昌王傅”,应是“亦都护王傅”之误。设立高昌王以后,王傅府统有两枚王印。
高昌王是按蒙古王爵封袭制度设立的王爵。元朝在元世祖时期已经确立了完备的王爵封袭制度。王爵分“有国邑名”和“无国邑名”两类,入元以后封授的都是有国邑名的爵位,即加封汉地式的王号,分为一字王和二字王等不同等级;王印分兽纽金印、螭纽金印等六级。高昌王为二字王,王印为第三级驼纽金印。“亦都护”虽是原属国的王位,但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承认,被纳入了蒙古王爵体系中。高昌王的设立,使一人身披双王爵位。这一现象的罕见之处,我们可以从秦王爵位的封授、削夺的经历中,窥见一二。忽必烈嫡子忙哥剌是元朝前期唯一受封安西王、秦王两个王爵的诸王,据研究,他所以能身兼二王,是由于忽必烈在立真金为太子以后,为了摆平曾为太子人选的忙哥剌和同母兄长真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特殊处理。[31] 忙哥剌死后,朝廷就以“一藩二王,恐于制非宜”为由,罢撤了秦王爵位。
与此比照,愈加突显了设立亦都护、高昌王双王爵位的不同寻常之处。这种情况,和纽林本人是否受到仁宗宠信等个人因素毫无关联,它是延祐年间元朝西域政策发生巨大转变的产物。刘迎胜教授曾提到,“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这一连串行动无疑与元军战胜也先不花有关”。[32] 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之间,自大德年间约和以来维持的和平局面被打破,双方重启战端。《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诸王复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创兀儿)方接战,……大破之。……二年,与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儿战赤麥干之地,转杀周匝,追出其境铁门关。秋,又败其大军于札亦儿之地”。[33] 延祐元年(1314)爆发的这场战争,在穆斯林史料也有记录。巴托尔德曾转录其文:“根据这一记载,也先不花和怯伯(也先不花之弟——引者注)率领军队反对从哈剌火州侵入的敌人——也先不花来自可失合儿,怯伯来自阿力麻里。……也先不花被打败了,因而怯伯也不得不撤退”。[34] 由于在延祐初年接连打败察合台汗国军队,元朝已经深入西域腹地,重新控制了畏兀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随即命纽林的斤“领兵火州,复立畏吾而城池”。[35] 纽林的斤重回畏兀儿故地,表明当时朝廷准备重新恢复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这是自至元后期元朝被迫退出畏兀儿地区以后,首次将政治势力扩展到当地。而亦都护重回畏兀儿故地,则首先面临着以后如何管理散居内地各路的本族属民的问题。为解决在管理畏兀儿地区和内地两处民众上的难题,朝廷于纽林的斤出发之前,即延祐三年(1316)正式设置高昌王爵,与亦都护之位并立,分别掌管畏兀儿地区(封地)和散居内地各路的部众。针对察合台汗国早已在当地另立了亦都护的现实,这种双王并立的作法,也有着重申纽林的斤对所有畏兀儿人都拥有正统的领有权的意味。《世勋碑》汉文、回鹘文碑铭对两个王印的使用权限作过说明,汉文碑铭称,“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则行诸畏吾而之境”;回鹘碑文说,“把新颁给的高昌王印用在行诸外邦的令旨上,再把以前的那个金印(亦都护印——引者注)用于周围的畏兀儿人民中”。[36] 回鹘文碑文由kiki qorsa icqu撰写,初看起来,与虞集汉碑似有歧义,其实,综合起来就是两印完整的通行范围。从畏兀儿的角度看,散居永昌封地(即“周围”)之外的“诸内郡”的属民,就是地处“诸外邦”,而亦都护印通行的“畏兀儿境”,实际上包括了同为封地性质的原畏兀儿故地和永昌封地。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延祐年间波谲云诡的西域形势,只知道亦都护没能在当地站稳脚跟,元朝不久也退出西域。然而,这次短暂的重回故里,多少加重了从领有权上派生出来的大汗廷和亦都护在当地的特殊权益。后来,元廷在火州“复立总管府”,这是代表领有权和特殊权益的派出机构,而订有长例的进贡蒲萄酒一事,可以看作是这种权益的具体体现吧。
对元朝后期亦都护的传袭世次,学者已多有论及,这里仅就一个悬疑问题,提出拙见。《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记载,传主乃“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孙,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这个曾尚公主的传主之父朵尔的斤,在《元史》中又写作“朵耳只”或“朵而只”,《元史·文宗纪二》记,“[天历二年十一月],命朵耳只亦都护为河南行省丞相”,据此看来,朵耳只在天历二年(1329)时曾担任亦都护之职。但《世勋碑》回、汉碑文都没有提到过此人。汉碑记载帖睦而补化相关事迹如下:“(帖睦而补化)奔父(纽林的斤)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不允。嗣为亦都护、高昌王.……明年(天历二年)正月,以旧官勋封拜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迷(追)念先生(王)之遗意,让其弟籛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根据碑文,帖睦而补化于天历二年正月升任中书省左丞相以后,即让位于其同母弟籛吉,籛吉任职直到至顺三年(1332)薨,在此期间亦都护之位似乎未曾空缺,这是什么原因呢?碑文自相矛盾之处,提供了某些线索:既然帖睦而补化是“追念先王之遗意”而让位给其弟籛吉的,那么,他即位之时何以会“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 钦察台与纽林的斤、雪雪的斤为兄弟辈,而纽林的斤又是经雪雪的斤之手接任亦都护的,因此,我们判断,所谓的“先王之遗意”,在纽林生前是确实存在的,其真实含意,是指王位在雪雪的斤兄弟几支之间的轮替传袭,这可能是雪雪的斤在位时兄弟间达成的约定,所以,当初若由钦察台接任纽林的斤之位,才是“先王之遗意”的真实体现,但是,仕途上颇有作为的帖睦而补化,却是大汗廷中意的亦都护人选,所以,朝廷“不允”钦察台嗣位。当帖睦而补化后来成为文宗皇帝的股肱之臣后(曾参预明、文继统之争),亦都护和高昌王的爵位对身为中书宰相的他,已经没有政治价值,所以,他依照前约,让出了王位。而最初禅让的对象应该是其堂兄弟朵耳只。《元史·文宗纪一》载,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朵儿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此时朵耳只还没有亦都护头衔,而一年以后,即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他出任河南行省丞相时,已是亦都护的身份,这不是巧合。其可能的情况是:天历二年正月,帖睦而补化禅位于雪雪的斤之子朵耳只,后者在渡过短暂的任职后,不知何种原因,又由籛吉接替了王位,朵耳只被改封荆南王。由于《世勋碑》是文宗为表彰其亲信帖睦而补化的功绩而下令撰刻的,故而只刻意记录了纽林的斤一支的事迹,不仅抹去了曾经短暂在位的朵耳只,甚至对纽林的斤之前的雪雪的斤也只字不提。而《元史》的相关篇章,主要是依据虞集所撰碑文,故而造成了传袭世次上诸多晦暗不明之处。
[1]《高昌王世勋之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2]拉施特:《史集》,余大钧等汉译,第1卷第2分册,第380—38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3]《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4]按《元史·地理志》,至元八年,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元贞元年,革宁夏路行中书省,并其事于甘肃行省,为宁夏府路。
[5]《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
[6]《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7]《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司事和赏公墳记》,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五。
[8]饶敦秩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 “凡例”第一条:“一古地名皆于字外加一方格”;另见“序文”;光绪二十四年江南王尚德重绘,上海铸记书局石印本。
[9]屠寄:《蒙兀儿史记》,第316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
[10]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三卷,中国·兰州1990年。
[11]《甘肃新通志稿》载文转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三卷;《新疆图志》卷八九《金石二》,第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2]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三卷。
[13]党寿山:《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14]参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225页,“永昌县条”,第924页,“番和县条”,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
[15]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耿氏对冯家升、捷尼舍夫译文作了修订,耿氏第二件文书对应冯氏第三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6]捷尼舍夫、冯家升:《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17]《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
[18]《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53页。
[19]拙文《海都与窝阔台汗国的创建》,《西域研究》1999第4期。
[20]蒲昌位置,文献记载不一,今依《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边防志》、《释迦方志》。
[21]自至元二十三年末朝廷组织畏兀儿人东迁入关一事的原因,见拙文《元代内地的畏兀儿聚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2]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宋肃瀛、刘美松、徐伯夫译,第92-9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据《元史人名索引》检索而知。
[24]《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25]《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十一》。
[26]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附录一《关于蒙元时代畏兀儿亦都护的传袭世次》,《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
[27]《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
[28]引自卡哈尔译文.
[29]《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0。
[30]《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六。
[31]王宗维:《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第1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会,1993年。
[32]参见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13册,第3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
[34]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206—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5]《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36]引自卡哈尔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