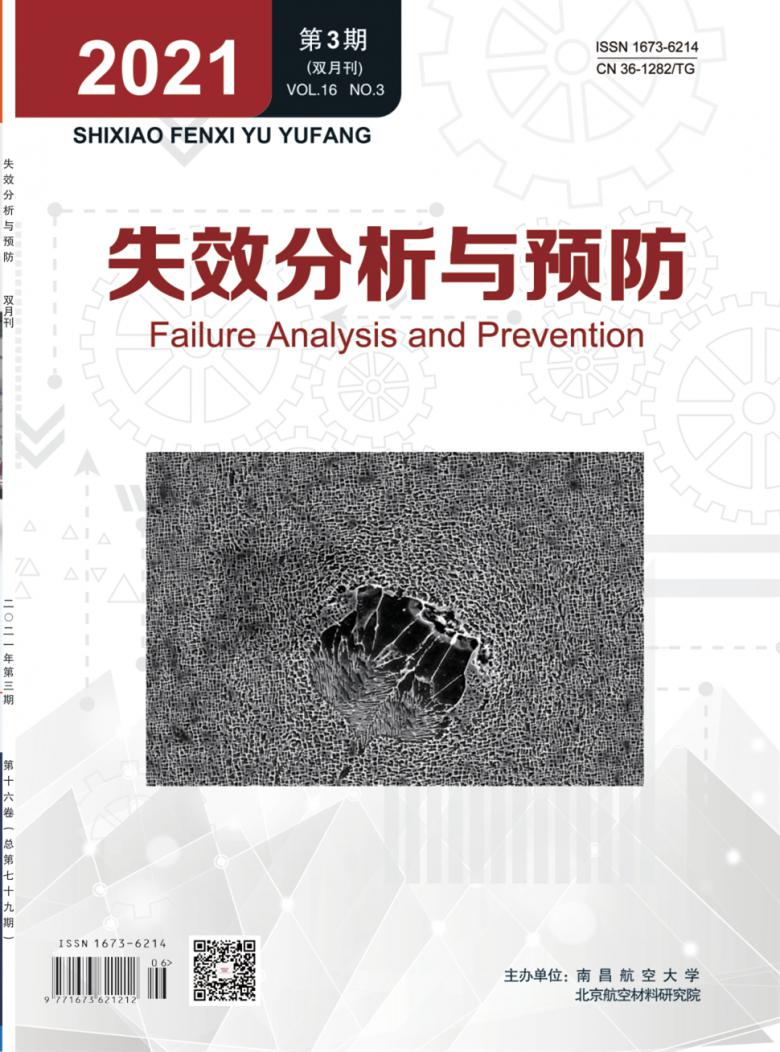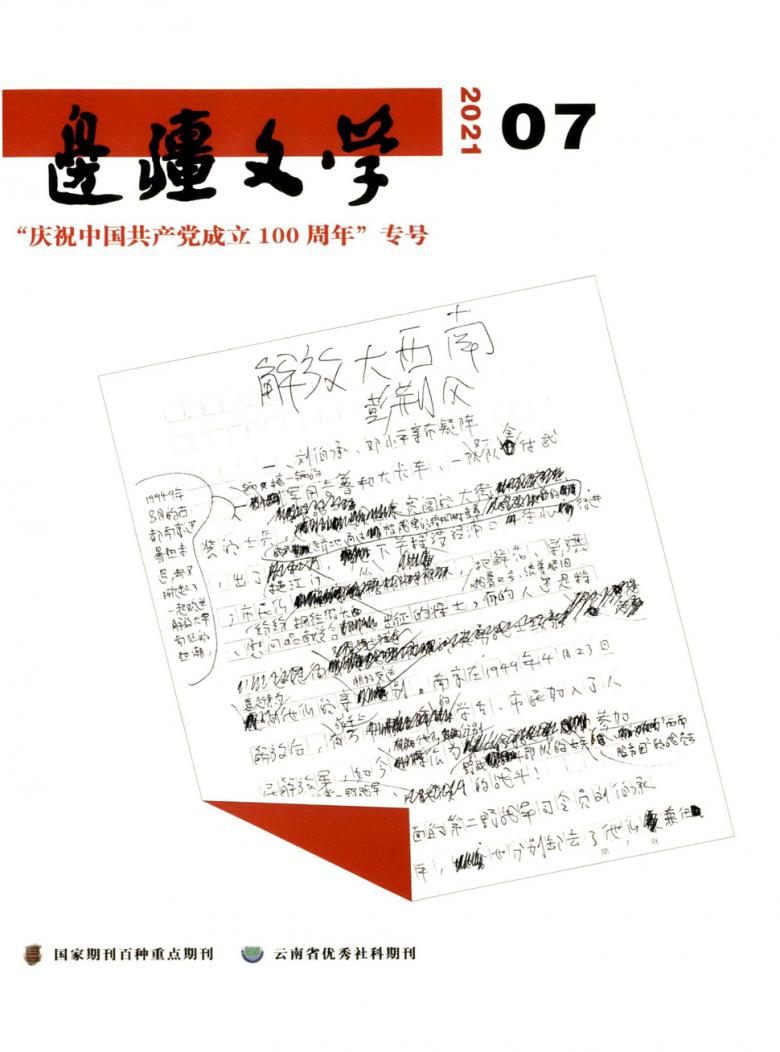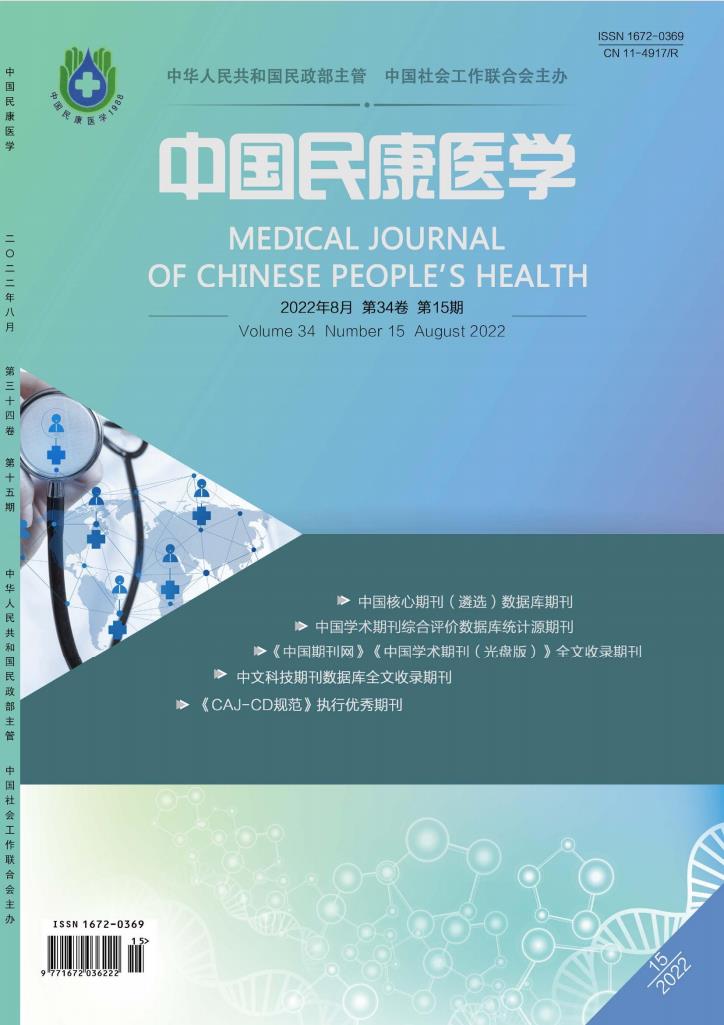矛盾与困惑: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
邹跃进
我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以下简称《他者》)一书出版后,有若干问题还想进一步探讨一下,以求正于读者。
“眼光”与“问题”
《他者》一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怎样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下认识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又以怎样的方式回应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和挑战。在此书中,笔者把“西方的文化艺术”改写为“他者的眼光”,意在说明我的研究对象——中国当代美术——作为承担所有问题的主体,是以“西方的文化艺术”为客体和“他者”的。这一点意味着西方的文化艺术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当代社会和历史的存在者,而是通过中国艺术家的理解、需要而转换成了他们观察生活、体验情感、把握问题、创造艺术的“眼光”。通过“他者的眼光”,中国的艺术家才创造出了一种可称之为“西方主义”的艺术景观。
中国当代美术中的“西方主义”,是在“他者的眼光”与“中国的问题”的相互需要、相互制约、相互生发的辩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这是因为,没有“他者的眼光”就没有当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的问题”,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许多美术家、批评家所摄取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的启蒙思想,从而能以人道主义、自由、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中的问题。从罗中立的《父亲》到陈丹青《西藏组画》,再到后来流行的乡土写实主义,无不是以西方的写实手法、人道主义的观念来观察乡村和农民的。但是,这种艺术中的“中国问题”则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农民,而是直接指向文革中非人道的"阶级斗争"和“红光亮”的“文革艺术”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认同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们则是以西方启蒙话语中的“自由”来面对“中国问题”的。如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的艺术思想所呼吁的就是艺术的自由;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则以隐喻的艺术形象和实际的行为来争取“社会的自由”;因钟鸣的作品《自在者——萨特》而引发的一场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则说明“艺术家的自由”也同时成了艺术家关注的对象。可以这样说,正是通过“他者的眼光”——西方启蒙思想中的“自由”,使这些艺术家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文革”的专制所带来的艺术、社会、艺术家的非自由。
在中国当代美术中,并不是任何一种“他者的眼光”都能栖居在中国艺术家、批评家身上的,这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同时制约着艺术家对“他者的眼光”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流行的新古典主义油画,虽然是以西方古典油画语言和文化精神为学习和研究对象的,但艺术家们对这种特定眼光的选择则首先基于他们对中国油画的艺术水平还远不及西方的认识;其次,在他们看来,在中国文化中,缺乏由西方的古典油画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和学科态度。正是这些“中国的问题”,使这些艺术家开始推崇西方早期的古典油画艺术。1989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起,物欲横流的现实,使西方的启蒙话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迅速衰微,这就促使一批艺术家转向新的中国问题。比如从1995年开始兴起的“艳俗艺术”所思考的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趣的是,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摄取了西方当代艺术家昆斯对待生活与艺术的“眼光”。
“现代化”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
上述例证已足以说明“他者的眼光”与“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当代美术中相互需要、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在当代中国产生这种关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换言之,虽然中国当代每一位艺术家所使用的“他者的眼光”都非常具体(如米勒、怀斯、达利、马蒂斯、弗洛伊德、昆斯等等),他们所关心的“中国的问题”也各有侧重(如人道主义、理性、自由、大众文化等等),但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为什么要以“他者的眼光”来面对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眼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又是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他者的眼光”不仅意指“西方”,而且意味着“现代”。“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其次则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的历史情境,同时也使中国的艺术家看到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经济富裕、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西方现代社会。相比之下,中国在经济上的贫穷与落后就显得触目惊心。与此同时,对内改革,解放思想的环境也为艺术家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来面对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许多美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动力,对他们来说,所谓“他者的眼光”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也意味着“现代”的眼光。正是通过这种眼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不仅对文革,而且对中国的五千年文明都进行了重新理解和认识。那些以西方文明反对中国文明的反传统者,都套上了这一种“西方”的、“现代”的、“他者的”眼光。李小山关于“中国画到了穷途末日”的观点,在当时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这场争论是一个含义众多的个案,其中的含义之一就是,在李小山等许多人看来,中国画因它特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味,已无法在一个需要现代化的中国继续发展。这意味着李小山只不过是以“现代化”的眼光和中国画的名义,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国画是它的代表之一——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已经衰落而已。
虽然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自1840年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近现代文化之中,但从当代美术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的加剧而逐渐鲜明的。如果说在1985年之前,艺术家还忙于用西方的启蒙话语来批判和消解文革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从1985年开始,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也进入了许多艺术家的视野,比如当代美术中的“汉唐情结”。在《他者》一书中,我认为“汉唐情结”表现为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汉唐盛世和明清衰落两个对立阶段,极力赞美、推崇汉唐文化,贬低、否定明清文化。当然,“汉唐情结”在当代美术中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那就是把汉唐文化的诞生地西北地区的文化遗存、黄土高坡、风土人情作为艺术资源,以抗拒西方文化的冲击。像周韶华、丁方在一段时间内都属于这一类艺术家。如果说“汉唐情结”是以艺术题材所涉及的历史内容来唤起中华族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那么,“中西融合”则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以折衷、妥协、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方式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以保持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在外来的艺术(如油画)中加入我们民族的文化因素和艺术形式(如“油画民族化”)的“融合”方式,至于在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中吸收西方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以适应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则与“现代化”的问题相关联。 “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我将中国当代美术中以“他者的眼光”关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艺术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关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和发展,能在各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艺术家看来,中国首先得阔起来,才能对西方的帝国主义说“不!”。不可否认,1840年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历史和民族耻辱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对于身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中,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认识、理解中国问题的美术家来说,产生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如哲学、伦理、对自然和人的态度、艺术形态和观念,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与“国家民族主义”相对的是以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为中心问题的“文化民族义主”。它与前者的差异在于“国家民族主义”想的是怎样保持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生存,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关心中国怎样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从后者的角度看,我们除了以自己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来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之外,别无其它方法。换言之,正是通过汉语、中国画、民乐、京剧、围棋、武术、气功、中医、孔孟和老庄哲学等中国文化,我们才能获得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才能使我们把“我们”与“他者”——西方——区别开来,获得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这意味着文化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决定着人们对待自己和世界的态度,而且在跨文化传播沟通中,文化和艺术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
在中国当代美术中,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对“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和笔者一样都是矛盾的,这是因为对中国当代社会来说,两者都具有合理性和自身价值。一方面我们希望国家强盛,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失去民族身份,随时警惕被“他者”同化的危险。这种矛盾心态使我们的言论行为和作品都充满矛盾。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中国当代美术置入当代世界的两个重要的文化语境——现代化和后殖民——之中加以考察,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还会面临更大的矛盾。
中国当代美术的矛盾与困惑
后殖民与现代化都与同一种国际关系——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联结在一起。首先,后殖民时代是指曾经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获得民族独立之后,仍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以资本渗透为手段,使处在贫穷落后地位的第三世界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这意味着处于强势地位的第一世界在当代历史中仍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塑造着第三世界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当代世界,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为西方的后殖民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第一是由于传媒和交通的发达,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容易;第二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它在目前仍主要是西方强势集团通过跨国公司将剩余资本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渗透的过程。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有西方世界的“资本冲动”和“后殖民”的愿望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为资本冲动找到市场,为后殖民方式找到对象。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语境,即现代化的语境,它主要是指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世界的压力面前,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变革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令第三世界艺术家困惑的地方正在于,这两个语境具有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它们都要求第三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包括艺术作品的含义,都必须以这一语境作为获得意义的条件。这正如杰姆逊所说的那样:“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主义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被纳入了这两个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当代美术不仅被置于这两种文化语境之中,而且也是在这两种语境中进行思考和创作的。前面说到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已任,这使得他们快速引进、认同西方的文化艺术。“文化民族主义”则企图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以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资源为武器,回应西方文化冲击,以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和困难是,我们怎样担保这宏伟抱负和崇高追求就不会落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圈套之中呢?当我们十分自信地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出了一批批传世之作时,我们怎能担保这不过是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无奈地从事一场在后人看来只是一种“自我殖民”的文化活动而已呢?也许我们会认为这种担心言过其实,但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已陷入其中而缺少相应的自我意识,这就像许多好心的父母带孩子去“麦当劳”欢度生日时,已经无意识地向下一代灌输了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当代美术中的许多问题与此相似。为了唤起我们在这方面的自我意识,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例一是有关国家民族主义的,例二是有关文化民族主义的。
例一:’85新潮美术是以引进西方的现代艺术为主要特征的,但是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的意义则能发现,正是西方现代艺术,使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活动在文化上进一步被美化和合法化。这是因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文化资源的掠夺。众所周知,来自非洲、美洲、亚洲等殖民地的艺术品今天仍然存放在西方各国的博物馆中,正是通过它们,许多西方现代艺术家如马蒂斯、亨利·摩尔、卢梭,毕加索才创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与非洲雕刻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虽然我们不能否认’85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以西方现代艺术的眼光来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同时也是使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活动在更大的空间内被美化和合法化。
例二:在我们前面谈到的具有“汉唐情结”的美术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西方的油画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家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方式与所表达的题材内容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来,以汉唐文化、西北高原为艺术表现对象是为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但是,它的证明和呈现方式(油画语言)则恰恰来自西方文化。前面谈到,一种艺术形式,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因为它综合了这个民族在文化、心理、社会、人种、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特点,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这意味着,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就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一种艺术形式(包括一种艺术上的主义、思潮、观念)不仅象征一个民族的身份,它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而具有意识形态性。当一个油画家以西方文化的象征形式——油画来证明中国"汉唐"时代或中华民族的伟大时,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当代美术中,要把迎合西方意识形态需要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为讨好西方游客的猎奇眼光而画的古代仕女、宫女、妓女;为取悦西方画商、古董商而画的明清家具和瓷器的各种油画“精品”等艺术现象与文化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在于我们或是缺乏自我意识,或是缺少自我批判的勇气而能在我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中看到西方的殖民话语、文化殖民主义与中国当代美术中那些宏伟堂皇的叙事话语之间的内在关联。
结语
我在《他者》一书中认为,我们只有完成西方主义(在肯定的意义上表现为西方主义,在否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殖民主义),才能超越西方主义,使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国东方主义艺术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而向世界扩散、传播,获得直接参与未来人类文明进程的能力。然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来说,我们仍然只能在当今世界所提供的规定性与可能性中有所作为。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我们确实已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与第一世界的资本渗透和文化殖民相互依赖的历史情境之中时,如下的问题就值得深思:一、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当我们欲以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来创造当代艺术时,如何才能避免它们在“他者的眼光”面前仅具有博物馆学的价值(如不求革新的中国画与京剧)?当我们以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为艺术题材,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同时,怎样避免在“他者的眼光”面前仅具有民俗学和市场价值的意义(如苏州水乡、北京胡同、藏女村民)?二、从国家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当我们以现代思想观念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低俗、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时,怎样才能使之具有当代性和批判性,从而避免成为取悦迎合“他者的眼光”的奇风异俗(如三寸金莲、宫女、古董)?当我们以西方的艺术形式、观念、手法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思想和情感上的合法性,为现代人提供审美享受时,怎样才能把它与我们的生存所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不致于使其成为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明,落入文化殖民、自我殖民的陷井之中?……
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的美术创作中,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都是我们同时需要的东西。但我们同样有责任避免使自己的崇高追求在无意识中落入文化殖民主义的陷井之中。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美术创作的领域内,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也同样具有矛盾性和对抗性,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其它文章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