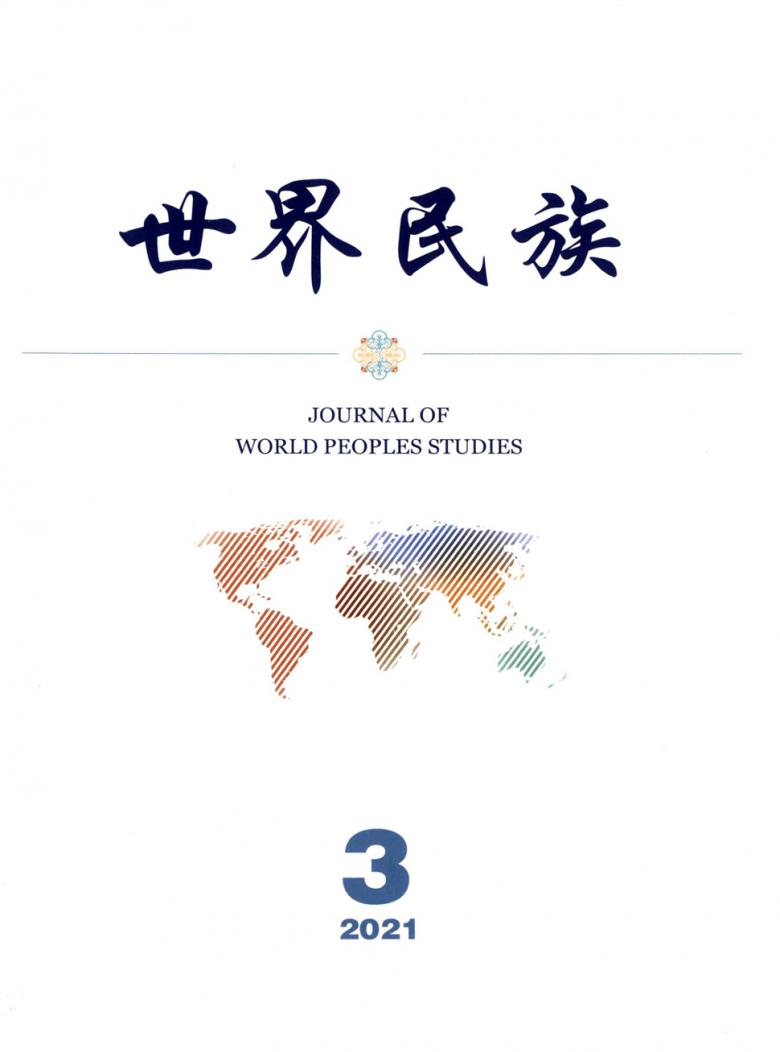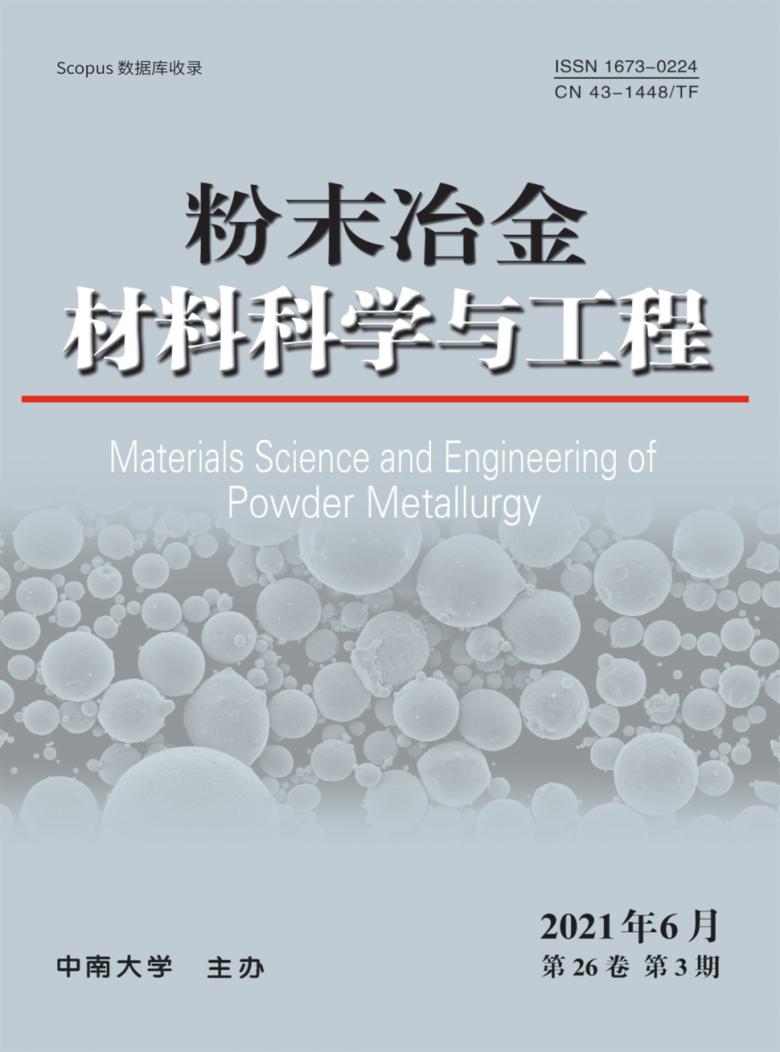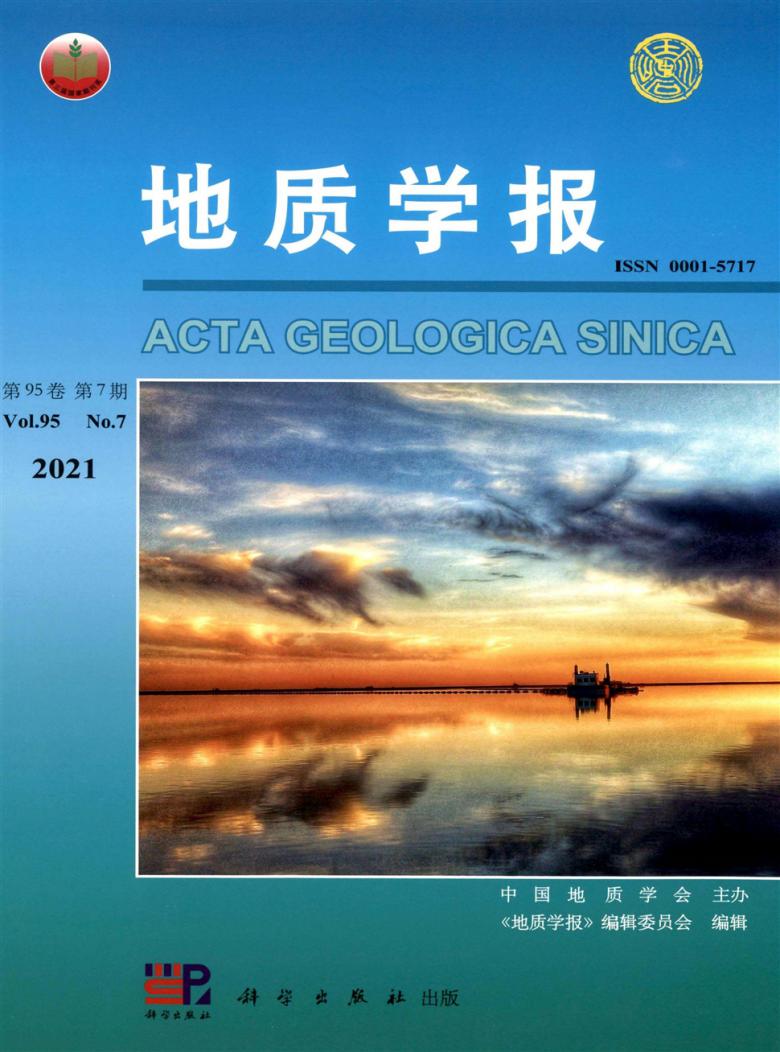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新思维
未知 2007-04-27
非总体性思维
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霸权和纯净主义美学基本上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压迫性总体化”(阿多诺语)来调控和引导建筑的美学走向的。当文丘里、菲利普?约翰逊等人起而挑战这种“压迫性总体化”,当反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领域日益变得蓬蓬勃勃的时候,现代主义的大一统格局很快就被打破,总体性受到重挫。不幸的是,当后现代主义建筑大量涌现时,建筑师们很快就预感到,他们很可能会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从一种处境跳入另一种处境”一样,从一种总体性跌进另一种总体性。这种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美学革命,是当代建筑师和美学家最不愿意看到,最不能接受的,因此,从反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直至当今出现的各种新建筑观念,无不把抵抗总体性、追求差异性作为预防和驱逐任何形式的美学专制妖魅的旗帜。
阿多诺(Theodor W.Adoeno,德国哲学家)说,“人类的解放决不意味着成为一种总体性”。为了在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进行沟通和了解,确实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应该遵循同一种总体性。对审美,具体地说,对艺术和建筑来说,总体性通常只能是一种惰性力量,甚至可以说,它是创造性最可怕的敌人。
总体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周期性病态发作的惯性力量。当艺术上的一种总体性遭到致命打击之时,往往正是另一种总体性悄悄出笼之际。所以阿多诺认为,如果艺术始终是激进的,它就始终是保守的。强化与支配性精神相分离的幻觉,“它在实践上的无效以及与没有减轻的灾难的同谋关系就显然是痛苦的”。它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如果艺术绕开贬黜历史的逻辑,那么它必定要为这个自由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难以符合历史逻辑的再生产。阿多诺对逃离总体性一直持一种矛盾、怀疑甚至是悲观的态度。他曾说过,我们可以忽视总体性,但总体性却并不忽视我们。仿佛总体性是一种如影随形、神出鬼没、无法摆脱的东西。在他看来,逃离总体性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因为你在对抗总体性时,“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可是,大多数建筑师并不同意阿多诺的观点,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建筑师的关注力、知觉和选择的能力,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自主性和捕捉与表现自我差异性的能力,以图逃离总体性的陷阱。
被菲利普 朱迪狄欧(Philip Jodidio)誉为思想型建筑师的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说过:“建筑与其遵从技术或风格的统一,不如让它向场所的非理性开放。它应该抵制标准化的同一性倾向……新的建筑必须这样构成:它既与跨文化的连续性适配,同时也与个人环境和社区的诗意表现适配。”霍尔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总体化,他心中理想的建筑,是既合乎个人生存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境遇,又具有某种异质性因素的建筑。
摩弗西斯事务所的主将汤姆。梅恩一向以特立独行而著称,他虽然没有像屈米和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那样,呼唤丑陋的建筑,但他对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忽视几乎与他对建筑结构和空间的重视一样出名。他对拼贴式的、虚假的后现代主义怀着深深的厌恶,对80年代流行一时的虚假的多元论更是不屑一顾。他曾说,“今天,我们有可能评价我们多元世界里共同的价值系统,在这个世界,现实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因而终究也是不可知的。冒险已经成为我们的操作原则……今日建筑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关于一个建筑师是否可以摆脱内在于我们环境的、腐蚀我们的自主性、自我意识甚至个人心智的心理和社会的势力而独立行动的问题。”梅恩和他的其他合作者们一样,极为重视艺术创造的个人性和独立性。在他们看来,个体不应该受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影响,不应该受制于宏观理性,而应该听从自我的纯粹创造使命的指引,走“小叙述”也即个人化道路。只有这样,建筑才能摆脱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怪圈。
同设计维也纳Z银行的G.多米尼希(Gunther Domenig)一样,蓝天组的沃尔夫?普瑞克斯(Wolf Prix)显然也把建筑当作了一种叙述性和表情性艺术。他真诚地希望建筑师的设计能够和作家们的创作一样,充分构拟、揭示和表现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说:“我们应该寻找一种足以反映我们世界和社会的多样性的复杂性。交错组合和开放的建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怂恿使用者去占据空间。”唯有语言艺术能够自如地描绘、揭示和诠释心灵、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常识普瑞克斯当然知道。但是,他和许多当代建筑师一样,急切地希望建筑能够超越自身的极限,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同总体性抗衡,所以难免对建筑的叙述性和表情性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许。
比起普瑞克斯,迈克尔。索尔金属于那种思想激进、敢说敢干的、富有青春气息的建筑师类型。他的建筑主张往往带有强烈的达达主义式的叛逆色彩。他说:“……应该让建筑出来为无理性的幻想申辩……建筑师应该是最开放的,可以和任何人或任何有意愿达到极佳效果的事物结合。你要想成为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爱你的所有的孩子,尤其要尊重他们的差异性。让我们设计怪异的、拉伯雷式的、疯狂的建筑吧……这是新生的模式也是乌托邦,是对理性的官方风格的一种快乐的戏拟。我喜欢那种具有反讽风格的建筑。”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建筑师在考虑建筑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个性从那种“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救出来,如何充分发展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把大叙述和小叙述对立起来,把总体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把同一性和异质性对立起来,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自我的创造的思维特征,不仅是建筑领域,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福柯都曾明确表示,他们“不再相信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再相信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宣称要“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要把“政治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思想,都具有一种极为明显的反社会、反主流文化的倾向。虽然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很少关注某一具体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情境,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毫无疑问地揭示了并影响了作为最具有大众性的文化情境之一的建筑及其观念。当代建筑审美思维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把总体性作为自己打击和颠覆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当代流行的反总体文化和哲学。建筑创作的变革,从来都是以审美思维的变革为先导的。没有对建筑的审美思维惯性的超越,就不可能实现建筑创作的美学超越。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确认非总体思维的合法性,从理论上说,的确不失为一种逃离总体化或公式
化陷阱的美学策略;从实践来说,它也确实已经(并且必然还将)对当代建筑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但是,非总体性思维或者说差异性思维往往会把建筑师引向另一个极端:畸形的个性或噱头式个性。如果说建筑是一门艺术,那么,它是一门极其昂贵的、实用的、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艺术,并且是一门比较脆弱的艺术。极端的、病态的差异性不仅不会给建筑带来个性,不仅不会给建筑创造美和实用性,而且往往会葬送建筑本身。
混沌—非线型思维
混沌,即英文chaos,是一种研究复杂的非线型(nonlinearity)力学规律的理论。詹姆斯? 格莱克说:“混沌是这样一种思想,它使所有这些科学家们信服大家都是同一个合资企业的成员。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或数学家,他们相信简单的决定论的系统可以滋生复杂性;相信对传统数学来说过于复杂的系统仍然可以遵从简单规律;还有,不论他们的特殊领域如何,相信大家的任务都是去理解复杂性本身。”混沌使人们注意到,简单可以包孕复杂性,复杂也可以遵从简单的规律;在一般人看来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两种(或几种)东西,却往往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或依存关系。混沌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伦兹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的题目“可预言性: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所揭示的蝴蝶效应就是对这种非线型现象(或称为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的最佳注脚。
混沌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人们从机械的宇宙论转变到有机主义新视野。机械论使人们相信,宇宙是静止的,独立的,有着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受决定论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是线型的、同质的、独立的、局部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而有机主义使人们相信,宇宙是变化的、进化的,普遍联系的;时空是不可分的,是非线型的、异质的、相互关联的、非局部的,不受决定论支配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两种世界观,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前者以一种僵化的线型思维为特征,把我们的世界描述成一个稳定、规则、有秩序的并且受决定论控制的世界;后者则以一种非线型思维为特征,把我们的世界描绘成一个变化的、不规则的、混沌的、不受决定论控制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混沌理论建构了一种正反合的思维方式:认为我们世界是以一种混沌和有序的深度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为非线型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是混沌(无序)和秩序的深层结合,是随机性和确定性的结合,是不可预测性和可预测性的结合,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深层结合。
非线型系统之所以有自组织性、自协调性、自发性和自相似性,正在于它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和辩证律。混沌学研究者法默说:混沌,“从哲学水平上说,使我吃惊之处在于这是定义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是可以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调和起来的一种形式。系统是决定论的,但是,你说不出来它下一步要干什么。同时,我总觉得在世界上,在生命和理智中出现的种种重要的问题必然与组织的形成有关……”又说,“这里是一枚有正反面的硬币,一面是有序,其中冒出随机性来,仅仅一步之差,另一面是随机,其中又隐含着有序。”混沌学正是这样,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人们的思维进入到一个多维的、多元的、可预见性、可调节的、富有弹性的开放宇宙。混沌学理论家从自己的专业的角度对建筑中流行的线型性几何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建筑创作的关键在于,建筑师是否以大自然组织自身的方式或人类认识自身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来认识和表现建筑的本质。从事非线型科学研究的德国物理学家爱伦堡曾经这样问道:“为什么一棵被狂风摧弯的秃树在冬天晚空的背景上现出的轮廓给人以美感,而不管建筑师如何努力,任何一座综合大学高楼的相应轮廓则不然?在我看来,答案来自对动力系统的新的看法,即使这样说还有些推测的性质,我们的美感是由有序和无序的和谐配置诱发的,正象云霞、树木、山脉、雪晶这些天然对象一样。所有这些物体的形状都是凝成物理形式的动力过程,它们的典型之处就是有序与无序的特定组合。”
混沌学家基本上认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秩序感是粗俗的、简单的、乏味的。同时,他们对建筑师固有的尺度感也提出了质疑。他们首先向人为万物的尺度这一传统观念发起攻击。曼德勃罗就认为,令人满意的艺术没有特定尺度,因为它含有一切尺寸的要素。曼德勃罗指出,作为那种方块摩天楼的对立面的巴黎的艺术宫,它的群雕和怪兽,突角和侧柱,布满旋涡花纹的拱壁以及配有檐沟齿饰的飞檐,都没有尺度,因为它具有每一种尺度。观察者从任何距离望去都可以看到某种赏心悦目的细节。当你走进时,它的构造就在变化,展现出新的结构元素。
很显然,混沌学家对建筑尤其是当代建筑的不留情面的问难,使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陷入了某种窘迫状态,然而,混沌学所蕴涵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传统思维的颠覆力,在使建筑师因陈旧的思维定式深感汗颜无地的同时,不能不对这种振聋发聩的理论心悦诚服,并且迅速开始寻求去“蔽”求新的路径。
最早接受混沌理论并且把非线型设计引入建筑设计的,是几位活跃的日本建筑师。
出版过《混沌与机器》(1988)的筱原一男,从80年代起,就一直把“进步的混乱”(progressive anarchy)和“零度机器”(zero-degree machine)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所谓“进步的混乱”,实际上是指一种合乎时代发展的、以非线型设计为中心的美学理念,这种理念摒弃肤浅的秩序与和谐,追求高科技的“笨拙”和美丽的“混乱”:“零度机器”则表明筱原一男不是重复现代主义的机器美学,而恰恰是对这种美学的解构和颠覆,以取消意义的方式使之在建筑中获得新的意义。筱原一男说:“这种无意义的机器可能会在建筑中承载新的意义”。筱原一男喜欢在建筑中运用当代高科技飞行器的意象,然而,这种意象往往是片段的、似是而非的。筱原一男总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机的甚至仿佛是即兴的方式把这种意象同一些异质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在一种令人意外的意象组合中传达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所蕴涵的特有的意义。筱原一男像一位从不采用写作大纲的小说家,直到故事写完,自己才知道结局原来如此,于是,自己就和读者或观众一道,为这个意外的、偶然的结局唏嘘、感叹或惊奇。一向被人视为保守派的桢文彦对混沌学也情有独钟。他的螺旋大厦(Spiral Building,1985)不仅采用了分形维度,更采用了多种异质元素的拼贴和混合。桢文彦解释说,“我的螺旋大厦隐喻城市意象:一种主动将自身献出,供人切成碎片的环境,然而,正是从这种肢解中,它获得了生命。”桢文彦显然想以建筑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构拟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像许多混沌学追随者一样,桢文彦虽然似乎把建筑师的业务拓展到哲学家或文学家的范围,然而这丝毫没有损害建筑本身的形式意义和功能意义。因为在这里,混乱与秩序并存,片段性与整体性同在,在一种雅化的秩序原则(a refined principle of order)的统帅下,混沌赋予建筑一种深奥的美,一种有张力的美、甚至还有一种隐嘲的美(以混沌反对混沌一度成为日本建筑界的一种时髦)。这也正是原广司、高松伸等建筑师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使混沌思维贯穿于自己的设计中的一大原因。
虽然欧洲建筑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观察到日本建筑中的第二因素的过剩,即由广告牌、招贴、陈列、霓虹灯构成的混声合唱和异质的立体装配中,感受到某种富有审美意义的混沌特性,并对混沌学产生兴趣的,但是,他们对混沌的理解,最终还是回到了非线型的轨道上。亚历山大。托尼斯,里亚纳。勒芬赫和理查德?戴曼德指出,“从90年代开始,混沌似乎一再成为建筑辩论的中心。仿佛我们又回到了60年代初我们的起点,回到了建筑被宣称进入了一种混沌状况的时期。”
在西方,对混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把自己的那套非线型思维方式推而广之的,仍然是普瑞克斯(Wolf Prix)、屈米、埃森曼这样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建筑师。
“开放建筑”的倡导者普瑞克斯说:从世纪初到90年代的建筑历史可以解释为一条从封闭空间通往开放空间的道路。从愿望上说,我们愿意建立一种没有目标的结构以便让它们可以被自由运用。结果,在我们的建筑中,没有围合空间,它们是组合的和开放的。复杂性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寻找一条足以反映世界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性……
作为著名的设计事务所蓝天组的代言人,普瑞克斯把他们的设计理念——“开放建筑”定位于一种“边缘性”意义之上,使之包含了一切不受局限的、可以充分发挥或选择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恰恰又是建立在构拟我们“世界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之上。其实,这种充分尊重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并依据客观现实重构和模拟这种展示非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空间的精神,也正体现了混沌理论的精神。普瑞克斯是否真正接触过混沌理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理论在客观上真正体现了混沌学某些精髓性的东西。
屈米与普瑞克斯不同,他是混沌理论的热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许多场合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形式和功能之间,结构和经济之间,形式和程序(program)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线型的因果联系,重要是要用“一致与叠加、置换与替代的新概念”,还有混沌的思想,来取代它们。他认为,在建筑设计中,任何追求和谐、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动机都是于事无补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当代建筑师需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穿插与对抗,是各种建筑构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混合。他明确指出:“建筑的定义不可能是形式,或墙体,而只能是各种异质的和不协调因素的结合。”屈米讨厌一切稳定的、确定的、静态的和无变化、非超前性的设计。他宣称,冲突胜过合成,片段胜过统一,疯狂的游戏胜过谨慎的安排。屈米不仅以一套非线型思路来规约单体建筑(如他的成名作巴黎拉维莱特公园,1982~91),而且还把一种非确定性的混沌思想贯穿于他的城市美学之中。他热切希望设计一种可以对发展新的社会形式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文化的和艺术的“语境”,而摒弃那种只是着眼于过去或现在的、不包括任何预见性的僵死的环境。他对等级明确的传统城市极为不满——它们往往以寺庙、教堂、宫殿等为中心;对现代主义的城市同样怀有深深的敌意,因为现代主义也通过严格的分区,把城市空间分成工作空间,生活空间,服务场所等。屈米希望他的城市在形式上是反简洁的、无等级的,在价值上是非传统的。他不希望以一种决定论来限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当代城市应该给人提供无限的自由和可能性。这与他在《事件建筑》中所张扬的那种建筑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屈米的思想中心,说到底,就是要建构一种混沌建筑,一种以非线型形式构造、以混沌思想定义的建筑。
詹克斯认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三座建筑,即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埃森曼的阿诺诺夫艺术中心,李伯斯金柏林博物馆,均为非线型建筑。因为这些建筑不仅仅采用了电脑辅助设计,更主要是采用了混沌思维方法,那种非逻辑的逻辑序列,非秩序的混沌的秩序,既表现了对建筑自主性的充分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建筑与历史的、现实的对应关系。
不过,最能反映混沌思维的成功范例,应该是艾西顿?雷加特。麦克杜加尔(Ashton RaggattMcdougall)的墨尔本(Melbourne)的多层大厦(Storey Hall)。这个工程以分形学为基础,以两种花砖作为象素手段,通过一种视觉拟态,在自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绝妙的融合。在这里,既规则又混乱的分形,组成一个自支撑、自生成的视觉拟态场所,成为新古典主义建筑之间的一个既怪异又新颖、既简单又复杂的和谐空间。在这里,我们无法用普遍的逻辑推理和线型思维解读设计者的意图。因为这里不存在任何点、线、面的关系,只有一种由不规则的曲线、不规则体块和色块组成的大杂烩。正是这个大杂烩,正是这个无设计的设计,在自我呈示的同时也赋予周围的环境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要寻找一种混沌学或非线型的最佳图解,这个设计也许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混沌思维为当代建筑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也赋予建筑师一种更加自由的创造精神。在秩序与混乱、静止与运动、确定与变化这样一些对立项之间,建筑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选择,甚至双极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线型思维方式在这里已经没有立锥之地;建筑师的设计将不再囿于任何固定的框框,而是以自然生物(厥叶的茎线分布)、生命构成(如DNA结构图)和自然现象(如山、闪电的形式)等为灵感触媒,创造出更灵活、更富有有机性和更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生存空间。
非理性思维
对比一下哲学、文化领域与建筑美学领域的互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非理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
当代反现代理性的急先锋福柯说: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然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结局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在建筑领域,最善于制造新闻效应的埃森曼则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建筑现实在媒体化世界的处境。这就意味着移换人们所习惯的建筑的状态。换句话说,要改变那种作为理性的、可理解的,具有明确功能的建筑的状况。
而最有才气也是最善于玩弄理论玄虚的李伯斯金则一边在“大路上钓鱼”(Fishing From thePavement),一边用福柯式的语调向世人宣告:现代性即告结束,人类理解现实的那种启蒙式方式,伟大的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式的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即告结束。人类同世界关联的那种旧有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理性人类对非理性的荒诞的宇宙情景的反映模式——已经结束。
我们不必对福柯和建筑师们对理性的声讨和对非理性的呼唤的语境和时间进行详细的考证。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学对当代建筑的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是,建筑师们在摒弃理性思维之后,是否真的迈向了非理性思维?
在“两线之间”一文中,李伯斯金就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设计柏林博物馆扩建工程时,非理性思维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要讨论建筑,就得讨论非理性的典范之作。在我看来,当代最好的作品就是来自于非理性,虽然当它流行于世界,统治并摧毁什么时,总是以理性的名义。非理性… …是我设计的起点。”
为纪念著名作家马赛尔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而设计过“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的J.海杜克(John Hejduk),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坚定的批判者。和李伯斯金一样,海杜克也认为理性主义建筑是一种已死的建筑艺术,并且在这个方案中运用了非理性设计思路。他说,“ 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是一种“对死亡的建筑艺术的注释和回答……我高度重视大多数的理性主义派建筑师,但是他们都在从事一种死亡的建筑艺术。这就是对他们的评价和答复。”
除了埃森曼(Peter Eiseman)、李伯斯金、海杜克之外,被詹克斯称为理性主义的扼杀者的库尔哈斯,达达主义美学的当代传人索尔金(Michael Sorkin),推崇疯狂(事实上就是非理性)建筑学的屈米,共生理论的倡导者黑川纪章,还有专门设计具有未来主义野性美的景观建筑的L.伍兹(Lebbeus Woods)等人,不仅对理性美学大加挞伐,对非理性美学极力推崇,而且也将非理性思维用之于设计实践。
《建筑中的自由精神》一书的编者安德斯。帕帕达克斯和肯尼思。鲍威尔(AndreasPapadakis&Kenneth Powell)指出:当今的建筑极力追求无限性:打破规则,拥抱自然(和人类),好客空间(letting space),时间和空间自由流动,使我们困惑而不是使我们重新获得确认,把过去、现在、将来联为一体,甚至动摇我们的现实感和理性,尤其是动摇我们的永久感。这是令人不安的,搅乱人心的,使人愤怒的,不可理喻的……
这种“极力追求无限性”的、“令人不安的,搅乱人心的,使人愤怒的,不可理喻的”设计思维,这种“把过去、现在、将来联为一体,甚至动摇我们的现实感和理性,尤其是动摇我们的永久感”建筑作品,其实就是充分体现埃森曼、李伯斯金人等所呼唤、所欢迎的非理性美学的东西,也是他们正在摸索和实践的东西。
当代建筑师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拥抱非理性而贬损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的理性(工具理性),其根本动机即源于一种打破秩序和惯性,挑战平庸,拆解中心、建构充满自由精神、富有个性色彩的另类(otherness)美学的冲动。而要达此目的,首先就必须打破现有的规则,动摇理性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诚如被丹尼尔?贝尔称为在非理性主义运动中“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的西阿尔多?罗斯扎克说的,“目前最要紧的是推翻那种深受自我中心和理智型意识束缚的科学世界观。要取而代之,就必须要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性的非理性能力——从幻想的光彩和人类交流的经验中燃起烈火的能力——将成为真善美的主宰者。”非理性的美学冲动不可能作为一种单一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行为而与非总体化和非线型性思维分离开来。事实上,它们源于同一种反逻辑(或非逻辑)的、自由的美学精神。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非总体性思维更侧重于对一种片断的、差异的、非连续性的、多元性和独立不倚的个性追求;混沌或非线型性思维更侧重于分维(fractal dimension)的、模糊的、流动的、机遇的和非确定性因素;而非理性则侧重于非概念、非永恒性、无意识乃至于神秘的思维方式。
在建筑领域,非理性思维模式,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也不是靠任何招牌或旗帜而标志出来的。那些从不谈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建筑师,同样会在作品中不由自主地运用非理性设计,甚至那些变着花样或打着理性主义招牌的建筑师,也会程度不同地流露出某种非理性的冲动。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即使是挂着新理性主义招牌的罗西、格拉西,其审美思维中依然包含着浓厚的非理性成分。因为,他们极口称赞和推崇的容格的原型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美学的基础之上。作为原型论基础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就是非理性思维的最典型的见证。所以,詹克斯在论及新理性主义时,一定要在前面缀以“非理性”。
不过,罗西等人的非理性,在屈米、埃森曼、李伯斯金、多米尼希和伍兹这样一些极端的先锋派建筑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他们理论的落脚点仍然是理性主义呢。所以,屈米、多米尼希、埃森曼、伍兹等人的建筑,总是以更强劲的反建筑和反造型的形式出现的,是真正革命性的,非常规的,有时甚至是疯狂的、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令人气恼的。比如,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就是以隐喻和解构的方式,通过一种无逻辑的大杂烩式的空间组合,达到嘲讽西方城市的等级和虚假的秩序的目的的;多米尼希的石屋方案(Stone House ,Steindorf,1985)完全是一个非逻辑的无序的堆积物,或者不如说同他的Z银行一样,是一幅地震后的悲惨景象的可怕再现;蓝天组设计的Ufa 影视中心(Ufa Cinema Center,Dresden,Germany)则是一种典型的非逻辑组合,既优雅又怪异,既冲突又统一。埃森曼的一系列住宅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颠覆常规的、理性的建筑观念。比如坎纳乔城市广场、住宅6号和10号,就是对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尺度的传统观念的挑战。埃森曼清楚地知道,“虽然弗罗伊德对无意识的揭示使这种天真的人类中心说观点永远不可能成立,但它的根源在今天的建筑中依然存在”,所以他“要运用‘另一种’话语,一种力图避开人类中心说关于存在和起源的组织原则的话语”,来动摇人类中心说的根基。为达此目的,埃森曼经常劝导人们拓展视界,对客体或主体保持一种超然反观(looking back)的姿态。他说:“‘反观’的观念开始取代这种人类中心论主体。‘反观’并不需要客体变为主体,而是需要赋予客体以人性。‘反观’关心的是主体从理性化空间超脱出来的可能性。”埃森曼的所谓“反观”,其实就是要揭橥一种逆向思维,也就是逆常规、逆理性的思维。埃森曼认为当代审美理性思维有着太多的有害的习惯性和惰性,只有用非理性思维与这种习惯性和惰性搏战,才能产生真正自由的、合乎当代审美需要的作品来。
与前面两位建筑师不同,伍兹的建筑,我们不如称之为非建筑。那些兀然矗立或穿插于广场或街道之间的巨型甲壳状物体,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一些装置,或未来世界的古怪雕塑。伍兹称他的这些建筑为“异构”(heterarchy)。我的确想不出一个比“异构”更准确的词来描述或定义他的“建筑”。这些“异构”,如同一些模样奇特、行为古怪的流浪汉或孤傲而冷漠的摇滚歌星,不邀自来地登上围满人群的舞台之后,除了以默默无语和矗立不动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表演之外,就不再给好奇的观众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观众打他、骂他、劝他,他依然宠辱不惊,我行我素。伍兹说:“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建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把社区中的个人从思想和行为受拘束的惯例中解放出来,以便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个人必须自我设计,因为个人,而不是群体或社会,才是人类最高和最完美的体现。”伍兹以其特行独立的建筑,创造了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非理性的他性景观,对当代人格和个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塑造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致上说,在当代建筑中,非理性思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无意识的梦幻式,追求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梦幻效果。如哈迪德(Zaha Hadid)的早月餐厅(Moonsoon Restaurant),就是一个典型。在这座建筑中,哈迪德塑造了一种富有梦幻感和戏剧性的超现实场景。一种平地腾空而起的旋风构成的旋涡,变成了餐厅的天花——由红、橘、黄三种颜色构成的火炉意象;由灰色的、光洁的玻璃和金属做成的地板,则构成了一种冰的意象;在“火”与“冰”之间,则是一些超自然的、非现实的、非复制的(每一样物件都是独立的设计,绝对不重复)物件,其中有造型奇特、可以随意移动的吧台沙发,有颜色鲜艳、动态古怪的沙发垫、有兀然竖立在吧台后面的像冰块一样尖利的碎片……整个设计,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随意演绎基础上,通过一种梦幻感和混乱的美赋予这座餐馆以无穷的魅力。艾辛姆帕托工作室(Studio Asymptote)的视觉图案方案(Optigraph)和哈尼?雷西德(Hani Rashid )的边缘与未知地带(Fringers And Uncharted Zones)方案,也属于同一种类型,不过这两件设计中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建筑的结构和外观组合上。
另外一种,是非逻辑、非秩序、反常规的异质性要素的并置与混合的方式。如上所述的屈米、埃森曼和伍兹的作品,还有盖里、蓝天组、赛特事务所和摩弗西斯事务所的某些作品,都可以归入此类。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所包含那种反美学的、片断的、荒诞和怪异的倾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总体上说,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是一个中庸的时代,折中主义的时代,一个理论宽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有一种纯而又纯的、不带任何杂质的非理性思维,更不可能存在完全抽空了理性内容的非理性思维。事实上,非理性本身是一个文化合题,它应该也必须是包含了理性的非理性,绝对不可以理解为无理性。就好比我们的“散文”观念并不等于光有“散”而无整体的“文”一样。
共生思维
爱德华。T.哈尔(Edward T.Hall)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也是最直观的危机是污染/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自身的危机——他同自己的联系,他的外延,他的制度和他的观念,他同所有包围他的那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他和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危机,一句话,他同他的文化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所讲的非总体化思维、混沌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主要是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对当代文化危机作出的反应;而共生思维和当代生态学理论则主要是他们对当代环境或生态危机所作的反应。当然,环境危机和文化危机本身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紧密联系着的。人对自然的掠夺,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在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在人类刚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初期,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掠夺就已经引起了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在《吉尔迦美什》这部人类最早的史诗中(比荷马的史诗还要早1500多年),我们看到,为了建造乌鲁克城,伴随国王吉尔迦美什远征黎巴嫩大森林的半神恩启都,在杀死森林守护神芬巴巴的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杀死了自己。史诗通过这个情节,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毁灭自然者最终必将毁灭自己。可是,从那时以来,不知又过了多少个世纪,人类仍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似乎也并不愿意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发展的悲剧”仍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演再演。尤其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的发展,战争的破坏,人口的爆炸与城市建设和开发的无序扩展,使绿地、水资源、大气,甚至农作物,全然遭到污染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而和谐的关系,如何在人与自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如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受污染的绿色的生存空间,这些问题,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了当代西方人的面前。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打破人类中心论,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著名生态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罗。罗伦兹说:人们乐于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然,而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高等生物。很多人对这个谬见恋恋不舍,而无视于一位贤人说的最智慧的警语,即屈龙所说的“认识你自己”。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说:……人类到了重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时候了。人类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大自然的平衡、协调。
生态的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人与人、人与未来的共生问题,实际上是人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伦理问题。如果人能够摆正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如果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能够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尽可能依靠人类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克制无止境攫取的欲望,在保持与他人(包括其他民族和后人)公平合理地共享大自然的赐予和恩惠的同时,拒绝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那么,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共生,与大自然平衡、协调,将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对建筑师来说,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人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榨取,往往以更加直观、更加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建筑师常常被动地成为地产开发商残害生态环境的同谋共犯。
正因为此,一方面是受到当代全球性绿色行动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修复极度恶化的环境的使命感的感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一种原罪感的驱动,当代西方建筑师开始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识当成一种普遍的设计准则。生态意识自然就成为西方建筑师的普遍的、自觉的意识。
黑川纪章于1987年出版的《共生的思想》一书,就把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的建筑与自然的共生作为主要的内容。另一位日本建筑师长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在《作为第二自然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Another Nature)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筑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人工化产物,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的自然。他说:“我的目的之一是重新思考过去的建筑,这些建筑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人类与大自然共生,把人类和建筑视为大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包含着对与新的科学和技术相关的新设计的挑战。”“……建筑不应该被当作一种孤立的作品设计出来,而应当被当作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必须具有某种都市品质。城市是一种变化的、多面的实体,它甚至包容了一些与它对立的东西。”长谷川逸子所说的与城市对立的东西,显然是那些具有非人工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思想前卫的摩弗西斯事务所对重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极为关注,并尽量使之在设计中得以体现。他们不仅渴望建立一种与自然“休战”的环境,而且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把建筑融入自然,使人和自然展开自由对话的环境。
白色派领袖迈耶把建筑与环境的共生作为一种终级追求。他在谈到盖迪中心的创作时曾表白,多年以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建筑中重构古代建筑中那种建筑与环境互相生成、互相融合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思维或共生思维已经催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即生态美学。这是一种具有新的、超越建筑造型或纯形式之上的功能美学,一种既联系着最古老的居住形式又展望着最遥远的未来的生存境遇的生存美学。
生态思维使建筑的当代审美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一种与真和善紧密相关的维度,或者说,一种与科学和伦理紧密相关的维度,一种与人类智慧相关的维度。因为建筑不再把功能和形式或者空间和视觉的美作为设计的终极参量。在生态和共生的视域中,建筑的审美考量必得同对下述诸种关系的考量联系在一起:即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建筑与建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建筑的节能、永续利用、自然对建筑材料的可溶解性等)以及建筑与人类的未来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这就表明,只有建立在超本位、超时代、超人类基础之上的审美思维,才是一种健全的生态思维,一种真正体现了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当前的利益和未来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的共生思维。
共生或生态思维对塑造建筑美的形式来说,即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说是机遇,是因为,生态思维为塑造园林建筑和山水建筑这种富有自然情趣的形式,和使用自然材质表现富有地域趣味的建筑形式,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实践机会。斯蒂芬?霍尔的斯特雷托住宅(Stretto House ,Dalas,Dexas,1989~1992)、查尔斯?格里姆肖的迪斯尼当代游乐园(Disney`s Contemporary Resort,Lake Buena Vista,1991)和安藤忠雄的大山崎山庄博物馆(日本京都,1993)是这类景观建筑的典型;而巴特 普林斯(1947~)的乔和伊佐科。普里斯住宅则是这类以自然材料体现地方趣味的典型。但是,共生或生态思维并不单单执著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形式。如果考虑建筑的治污和防污、节能、永续利用等多方面因素,再要求建筑师考虑建筑美的形式,这对建筑师来说,不仅是挑战,简直是严峻的挑战了。
当代西方建筑师健康的生态观或者说生态思维已经普遍确立起来,这是毫无疑义的。建筑师在实践中,通过资源的节约、资源的再利用和循环利用,通过选择非污染性和再生性原料,或通过对自然的拟态、对生物的仿生等多种方式,使当代建筑迈进了一个革命性的阶段,这是需要加以充分肯定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共生或生态意识与实效性的生态行为并非是一回事;同样的,建筑师的生态思维与业主的生态思维也并非是一回事。虽然付出了较高的投入,生态建筑不能给开发商或业主带有对等的、可触可摸的即时利益,这种投入和产出不符,自然会大大影响并削弱生态建筑的更大、更广泛的拓展。